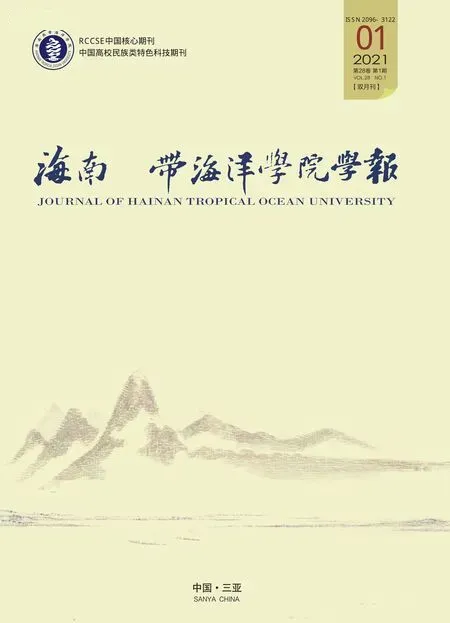民国时期关于南海诸岛问题的社会舆论
刘玉山
(温州医科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浙江 温州 325035)
中国人民在南海活动已超过2 000年,南海诸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神圣领土。中国人民最早发现、命名和利用南海诸岛及相关海域,最早并持续、和平、有效地对南海诸岛及相关海域行使主权和管辖,确立了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相关权益。目前学界对民国时期南海诸岛问题的研究成果丰富,但多从国民政府的视角进行论证,关于民间社会舆论对维护南海诸岛贡献的文章却不多见。事实上,民国时期中国民间对维护南海诸岛主权参与的人员众多,有引入最新国际法原理进行理论论证的,也有进行著书撰述的,也有绘制地图进行位置确认的,更有就南海问题而生发出的一系列中国边疆危机乃至中华民族危机预警的。这些都是为维护国家领土主权所做出的努力,其精神不仅为后世所学习,其所保留的各种撰述也为我们打赢南海问题“信息战”提供了第一手的历史证据。
一、 关于南海诸岛问题社会舆论的特点
民国时期关注南海诸岛问题的社会舆论构成繁多,政商学界都有参与;所依托发声的载体有教科书、期刊与报刊等,而且在时间分布上也呈现一定的规律。
(一)参与人员的构成
参与人员的社会构成有知名专家、知识分子群体,如著名地理学家张其昀、我国现代人工珍珠养殖创始人熊大仁、地理学教授王光玮和冼荣熙、著名地层古生物学家穆恩之和李毓英、地质学家席连之、图书馆学家袁同礼等。介入的媒体,如北平时事日报社、《申报》和《大公报》等主流媒体。有政府官员如前清官员李准、前国民政府铁道部部长叶恭绰、广东省地方官员黄强等。有各级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如国民党省、市、县党部如河南省、宁夏省、汕头市、宁洱县、萧山县、皋兰县、紫金县、会同县、安仁县、儋县、楚雄县、安乡县、文昌县、大定县、中山县、上海法租界纳税华人会、上海市总工会、上海市商会、宁波市商会、中华海员上海党部等。此外还有大量的爱国学生乃至高中生,如后来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外交工作的俞沛文等。
总体来看,民间参与论述的“阵容”没有二战后参与琉球论述的知名人士多、波及范围广。这也可以理解,琉球论述是二战后伴随着国民政府因应对日和约而产生的,未来的对日和会的核心议题之一就是琉球归属问题,所以在社会力量的资源动员方面,肯定是吸引了与之相关的各方面专家的“协同会诊”,有官方的积极推动因素在里面,而南海论述由于时间跨度更长,大致有1933和1947年两个高潮(下文会有比较)阶段,虽然社会关注度不低,但并没有国民政府的积极推动,因而总体来看,专业人士参与相对较少。
(二)民间社会舆论参与的载体
首先,教科书。如林纾1913年《重订中学国文读本》、王钧衡1933年《初中本国地理教科书》、张其昀1935年《本国地理》、江苏省教育厅编1936年《小学教师文库?第一辑(下)》、葛绥成1945年《新编高中本国地理》等。值得一提的是,1936年江苏省教育厅在编写的小学各学科教材指针中,特别将南海九小岛列为“社会科学临时教学事项”[1]。
其次,学术性期刊。如《边事研究》《边疆》《国立中央研究院植物研究所年报》《国立中央大学农学院旬刊》《地理学季刊》《国立中山大学校报》等。
再次,专业性质的期刊。如《水产月刊》《气象年报》《上海市水产经济月刊》《农声》《广东农村月报》《土壤》《农报》等。还有海事方面的报章杂志,如《中国海军》《海军杂志》《海军公报》《海事(天津)》《海事(武昌)》《海事(台北)》《海事(天津)》《航业月刊》等。
最后,国内大报刊如《申报》《大公报》给予持续关注。国内报刊舆论的记载,完整地记录了我国政府机关、各行各业对南海诸岛行使管辖权的过程,这就构成了国际法上证据链的完整性,这些社会舆论资料与政府如外交部门所保存的档案资料一起构成了南海诸岛属于中国的充分证据链。
(三)时间分布特点
可以发现,我国新闻舆论界在历次南海诸岛危机事件中都不缺席,为探寻南海诸岛属于中国在资料搜集方面做足了功课,责无旁贷地完成了报道事实真相的任务。通过比对发现,社会舆论对南海诸岛的关注有两个时间段较为集中,一个是30年代初,尤其是1933年,占全部的近三分之一。第二个是二战后,尤其是1947年,接近全部的五分之一。出现这两个高潮的原因也显而易见,1933年正是法国政府炮制“南海九小岛”事件的年份。1946年底,国民政府派遣军舰分别进驻西沙武德岛(改名永兴岛)和团沙(今南沙群岛)之长岛(改名太平岛),紧接着1947年面临占领西沙、南沙其他附属岛屿及公布收复范围诸问题,同时本年还发生了法占西沙白托岛(珊瑚岛),国民政府与之外交折冲之事件,因而1947年也成为社会舆论关注南海诸岛问题的又一高潮年份。
二、 关于南海诸岛问题社会舆论的主要内容
社会舆论对南海诸岛主权维护的表现形式是多样的,面对法国侵占“南海九小岛”的恶行,曾在清末带兵巡阅南海诸岛的李准拍案而起,向主流媒体《大公报》投书,从而昭告天下。还有很多人翻译当时的国际法最新著作,或对南海诸岛主权属于中国进行理论撰述,表现出了民间舆论的集体智慧与敏锐性。
(一)《李准巡海记》在《大公报》发表
1933年4月,法国乘中国内忧外患,占领了中国南海的九座岛屿,这就是“南海九小岛事件”。国民政府一筹莫展,对“九小岛”的名称、地理经纬度、历史沿革皆无概念,以至于“举国浊浊,无一能道其真相者”[2]。针对这种情况,寓居在天津的清末广东水师提督李准拍案而起,向天津《大公报》投稿,将他于1909年率领170余人的“琛航”和“伏波”二舰,对我国南海诸岛进行考察,探明岛屿15个[3],并用随行人员的籍贯进行命名,有效宣示了中国政府对南海的主权,符合国际法程序。值得一提的是,当时中日东沙岛纷争出现,李准“亲巡其地、鸣炮升旗、勒石命名,并测绘地图,作巡海记事”[4],击破了日本人的东沙岛为“无主荒地”之狡辩,日本被迫退出东沙岛。《李准巡海记》在《大公报》发表后,各大报刊争相转载,比如《申报》1933年8月15—16日两天以“特刊”的形式连载《李准巡海记》。《大中国周报》1933年第3卷第8期、《珊瑚》1933年第3卷第6期、《中央周报》1933年第273期、《国际现象画报》1933年第2卷第9期、《新世界》1933年第34期、《国民外交杂志(南京)》1933年第2卷第5期、《国闻周报》1933年8月21日第十卷第33期在《李准巡海记》的基础上又补充了李准所撰的《东沙岛》。实际上,李准就南海诸岛撰写的文章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就是上文提到的《东沙岛》,而另一部分则是各大报刊所转载的《李准巡海记》,而《李准巡海记》的原名叫《西沙岛》,是为第二部分,将这两部分文章拼接在一起才算完整。
(二)出版专著或译著,论证南海诸岛主权在我
专著如郑资约1947的《南海诸岛地理志略》、冯承钧1936 年的《中国南洋交通史》、凌纯声1934年的《中国今日之边疆问题》、杨秀靖1948 年的《海军进驻后之南海诸岛》等。其中《南海诸岛地理志略》还有人做了书评。资料汇编类如陈天锡《西沙岛成案汇编》、杜定友《东西南沙群岛资料目录》等。
翻译如胡焕庸译《法人谋占西沙群岛》、黄莫京译《西沙群岛》、冯承钧译《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续编》和《昆仑及南海古代航行考》、何健民译《中国南海古代交通丛考》、冯攸译《唐宋元时代中西通商史》等。
报纸杂志及时登载日本国际法学家横田喜三郎有关“先占”著述和其他日本学者相关文章。日本著名国际法学家横田喜三郎在“九小岛事件”发生后给予了关注,并撰写了论文《无人岛先占论》。当时我国的部分报刊及时进行了翻译转载,如《南方杂志(南宁)》1933年第2卷第8期、《国际美日文选》1933年第58期、《中央时事周报》1933年第2卷第38、39期分上、下连载。值得注意的是,这三种杂志发表的《无人岛先占论》分别由梁佐燊、易野、何鼎三人各自独立翻译,可见当时的社会舆论对维护国家领土主权的重视,知识阶层不遑多让,利用自身的文化优势积极贡献心智。
根据当时的国际法,横田[5]8在《无人岛先占论》中提出了符合先占的四个要件:土地是无主的土地;国家自身占有这土地;占有是实效的;通知其他的国家。基于此,日本所谓在该数岛屿曾有拉萨磷矿公司的开采、日本学者在那里研究过地震等“都只是错误的与国际法上的先占毫无关系的事实”[5]2。《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规定,法院对于陈诉各项争端,应依国际法裁判之,各国权威最高之公法学家学说,作为确定法律原则之补助资料者裁判时应适用。当日本政府“突兀”地卷入中法“九小岛”争端时,其国内国际法权威立刻进行“学说”撰述进行反驳,这应视为日本“先占说”不成立之有力证据。
1931年“克利珀顿岛(Clipperton Island)仲裁案”为“南海九小岛”争端提供了现时的极好的案例。该岛1855年被法国占领,次年美国立法列为国土,1897—1917年为墨西哥军队占领并驻守。作为仲裁官的意大利国王维克托·伊曼纽尔三世1931年1月28日在罗马做出裁决,他认为:“克利帕倘(克利珀顿)岛,乃法兰西于一八五八年十一月十七日为法兰西所正当先占,法兰西于其后并无可以认其有抛弃权利而丧失其权利之根据,而且并未尝有欲抛弃该岛之意思,所谓法兰西未尝积极地行使其权力之事实,可不惹起既确定的完成取得之失效。依此等理故,予为仲裁裁判官,对于克利帕倘岛之主权决定为从一八五八年十一月十七日,已属于法兰西。”[6]张觉生将横田喜三郎论文中的这段判决结果做了翻译,登载在国内报刊。
日人金子二郎发表在《外交时报》1933年第67卷第5号有关“九小岛”的文章也被新闻媒体第一时间翻译介绍给国人。翻译者杨祖诒“译出以供国人参考,亦以觇日本之野心”[7]11,该文为日本张目,认为“至今尚留有足迹,不问问题之归结如何,仅此亦足为日本同胞之荣”[7]13。可谓强词夺理到极致。不过该文的直接矛头对准了法国,认为“法国对该岛屿毫无实迹,仅为梦里世界之占领手续,颇使吾人难以谅解”[7]13。这篇译文一方面让国人看透了日本人对我领土的觊觎,另一方面戳到了法方的“痛处”,即法方虽然“形式上”似乎完成了当时国际法意义上的“先占”,实质上却构不成国际法“先占”要件。
(三)撰写论文,多视角阐释南海诸岛主权在我
1.针对“南海九小岛”事件的论证
(1)强调“九小岛”的军事价值
蒋震华认为“从地理上分析,南洋九小岛,真可说是太平洋上航路的枢纽。我们看,无论自菲律宾至夏威夷,香港至新加坡,或者日本海岸至欧美各国,广州湾至西贡的船只,航轮往返都必经过这个地方。这一地带对于海军关系之重要,尤其他在太平洋均势局面之下将发生很大的作用的重大性,我们可想而知了”[8]13。张静民认为“九小岛介于太平印度两洋亚澳两陆之中,东控菲律宾,南制婆罗洲,西达南洋群岛,北逼安南两越,诚交通便利,东亚之要地也。若加以严密之建设,巽日面积扩大,以之为工,则原料四集,源源而来。制品畅销,无所不知,以之为军,则军港机站无所不适,故是地若终为法所有,法人筑之,则大赫的岛与安南联成一线,非特太平洋之势力,不为日美英之所独有,即日之台湾及代管德属太平洋诸岛亦有被胁之势,至我中华,则更无论矣”[9]13。静植认为,法国又多了一项根据地,“不特西沙群岛全部随时有危殆的可能,即琼崖海疆也大感威胁”[2]。有人拿九小岛比作德国黑尔戈兰岛(Helgoland),欧战前却是该国重要的海军基地;本太平洋委任统治地被视为海上重要的生命线;南极圈内各荒岛,英法挪各国争夺激烈[10]16。
(2)论述先占与时效
1933年“南海九小岛”事件发生后,社会舆论已经开始充分利用最新的国际法“先占”概念对法、日的无理证据进行批驳。王英生提出国际法“先占”必须具备的四个要件:被占的土地必须是无主的土地;国家占领;有实力的占领;必须通知其他国家。即使日本最先发现“九小岛”,但这纯属私人发现,“若要先占成立,则日本政府必须于斯人发现华南九岛后,立即树立权力,而作有实效的占领,然而日本政府并未在华南九岛树立任何权力”[11]5,针对日本人可能辩解的“九小岛”是无人居住的荒岛,没有设官驻军的必要,王认为“就是在这种特殊的情形下,亦需在其邻近毗连的土地上设置官吏,驻扎军队,以谋对于华南九岛得意行使监视和保护。但是日本属地的台湾距华南九岛有七百五十海里之遥,不能说是与华南九岛毗连,更不能说日本能以台湾为根据地,对于华南九岛行使权力”[11]6。王敬熙从先占和时效两个相关联的国际法理出发认为,明末清初,郑成功举事不成,即入此土,清政府也派遣官吏置守,属琼崖管辖,华人往来打鱼者甚多,依时效言“实为中国所有,即依先占言,亦不虞他人之责言”[12]。钱彤对于时效的时间断限考证最具学术价值,他认为,“我们知道随便占领并不是一桩合法的事,日本公法学者江木翼认为‘如此无所属土地之经营,除取事实上殖民地占领之形势外,全无适法之形式。’又虽在国法时效之规定,有一定之年限,而国际法则无之;但在一八九七年二月二日英委条约,其第四款中所云‘对方领有,经过五十年,视为合法诸语尚不失为一种有限制之先例’;又公法家斐尔黎亦曾主张以二十五年为期,无论时期为长为短,有人出而辨正,就应终止侵占,此却也是国际应有之美德。日调查诸岛,固已发现了有我国人在岛;法四月六日有军舰至斯巴得来,亦见有华人居住在岛”[10]17,钱提出“国人皆应迅速收集证据,调查事实,准备抗争,谋所以防止列强瓜分中国事实之扩大了”[10]17。
(3)保留了大量的南海九小岛位置地图
1933年第1卷第1期《江苏省小学教师半月刊》[13]、1933年《南海九小岛位置图》[14]、1933年《南海九小岛位置图》[15]、后来成长为我党优秀外交官的俞沛文在1933年手绘的《南海九小岛图》[16]、1937年《中华省市地方新图》[17]等都非常精准地将“南海九小岛”位置标示出来。联想到1947年前后,国民政府为团沙群岛(今南沙群岛)、日人命名的新南群岛之间的关系而一筹莫展,殊不知,30年代的很多舆图都已经将南海诸岛的位置标识出来,至少资料来源上绝对是丰富的。同时,白纸黑字,也为南海诸岛属于中国提供了国际法地图上的证据,现实价值重大。
(4)从国际关系角度论述南海九小岛之重要战略地位
胡墨宣从国际关系的角度论述“九小岛”事件时认为,现在的中国与1850年的意大利相似,意大利在完成统一的过程中,“没有打过胜仗,而且参加普奥战争是弄得全军覆没的,但实际的胜利却属于打败仗的人,意大利就在打败仗的声中一天天健全,统一起来,这无他,由于能利用别人的拳脚而已。”中国怎么做呢?中国可以“照样葫芦地做”,“有赖由我主动地促成并参加鹬蚌相争以收渔翁之利的原则,即欲中华民族挣脱次殖民地的厄运,也是舍此别无他法。”[18]
梁庭栋从中日法三角关系出发认为,南海九小岛为西沙群岛之屏障,我西南海防之第一道防线,“今一旦为法人所领,则广州湾以南之海南岛受其包围,攻之取之,惟其所欲,而侵滇之滇越铁道,得一助手矣;倘为日人所有,则其在太平洋之势力,猛烈增加,我国过去受其侵略,虽失满洲,犹曰江南一隅可守。兹后如其大陆海洋,两策并进,吾人恐无立锥之地矣,观此知可九小岛实为我国之生命保存地也”[19]。
2.阐述中国人最早发现、利用南海诸岛,并有充分的统治痕迹
中山大学地理系教授王光玮从历史学的视角将中国人民在南海诸岛栖息、生存的历史脉络做了系统介绍,并且从国际法的角度阐述了中国人最早发现、利用南海诸岛,并且已经行使了主权,如1883年德国政府派员测量该诸岛,经清政府严重抗议而罢,“是我国在南沙群岛行使主权之充分表示,亦即通告各国当尊重在南沙群岛之主权”[20]。1932年我国西南政委会对华南三年建设计划,亦规定开发南沙群岛,“又有实施统治权之表示,此非我之领土而何”[20]。王的这篇文章还被1948年叶恭绰主编的《广东文物》[21]收录。
3.关于公海与领海事实之辩
20世纪30年代日本经常有人在东沙岛附近滩屿采集海人草,针对日人所谓“系在公海,而非在中国公海”[22],梁朝威经过大量的国际法案例比对,认为“所谓公海者,宜从距离海岸最远之滩屿往外量算,三英里以外之海面,然后可以谓之为公海,若在三英里以内之海面,则为中国之领海也。此一群滩屿在水涨时,虽有被海水淹没,然于潮水落时,则露出于水面,故自以潮落时露出水面之滩屿量起,以决定三英里领海之宽度焉”[22]。基于此,日人“若在东沙岛附近滩屿三里以内之海面耶?则亦显然地为在中国领海私采。若在距离海岸最远之滩屿三英里以外之海面,然后可以谓之为在公海采集”[22]。
1946年8月4日和5日上海《大公报》连载曾达葆的文章《新南群岛是我们的!》,该文章论证缜密,证据确凿,各个岛屿的名称都位列其中,让人感叹文章作者背后做了很多调查研究工作。作者给出的新南群岛的位置在“台湾省高雄市南南西约七百五十里处,当南中国海之中央偏南。正在西沙群岛、菲律宾、婆罗洲和交趾半岛的中间。群岛的水域面积约七万五千六百平方浬,介于北纬七度至十二度,东经一百十七度至一百十四度的海上。这些群岛是十三个大小不同的岛屿组成的,各岛的面积都很狭小,其中以长岛的面积比较大些,但其周围亦不过二千八百公尺。”文章还称,根据昭和八年(民国二十二年)九月号的《世界知识》,日人福岛丈雄的记录,这十三个岛屿有日人所定的名称和英文。这两篇文章并附有新南群岛位置形势图、新南群岛主要岛屿分布图,通过对比二图,可以发现该文章所称的新南群岛就是当时的团沙群岛(即今天的南沙群岛)之一部分。这篇文章可谓来得及时,作为剪报,至今仍夹在《外交部档案》中。
三、 关于南海诸岛问题社会舆论的历史评价
民间舆论对南海诸岛主权的维护所留下来的撰述,保留了大量历史证据,在今天看来,这些社会舆论不仅讨论的问题有一定的理论深度,最关键的是,社会舆论往往其敏锐度或者说“先知先觉”于政府,而官民之间也没有形成一定的良性互动和沟通交流模式,更不用说达成一定的默契,这是一大遗憾。
(一)保存了南海诸岛主权在我的历史文献证据
国与国之间要想在领土争端中占据有利的地位,大面积搜集、整理和研判自身及对方的“证据链”非常重要。这种“证据链”必须丰富、完整和具有系统性,形成一定的“证据链”闭合。南海诸岛是中国人民最先发现、命名和利用的,根据近代以前国际法“谁发现谁拥有”的原则,中国已经拥有了南海诸岛的主权。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大国及周边国家的介入,近代以来南海问题日趋复杂化,将原先并不存在争端的岛屿问题演化成国际“争端”。这种情况下加强自身原始档案、历史文献资料的搜集与整理就迫在眉睫了。民国时期中国民间社会舆论蕴藏了丰富的历史文献证据,这些证据是中国人民自发在第一时间维护祖国领土完整、维护中国南海领土主权所做出的努力和贡献,构成了南海诸岛主权属于中国的原始历史文献证据链重要的组成部分,诚如郭渊所言:“为后来中国政府的维权奠定了基础。”[23]
(二)社会舆论“先知先觉”,惜官民之间未形成合力
1933年“南海九小岛事件”后,大家普遍觉得“交涉起后,我国方面很有临事慌张的情形”[1],从1934年出版的1933年度《中国外交年鉴》专辟“法国占领九小岛之交涉”一节,然从论述看颇为吃力,甚至有“(九小岛)并非西沙群岛,亦无从证明系我国之领土也”[24]之结论,这就颇让人感觉意外。1933年7月15日法占九小岛后,日本反而最先提出抗议,甚至连日本民间都开始行动起来[15]7。又比如针对1933年国民政府对于“南海九小岛”昧暗无知,张觉生不仅及时翻译了日人关于“先占”的最新国际法案例,而且极力提倡成立边政机构,在张看来“(吾)于民元以前民元以后,曾屡上书政府当道,请设垦殖部以重边政,不幸频年国内多故,当局无暇及此,至今未见实行,今政府已有见及,深望此早日成立,并于部中设置移民屯垦及界务诸厅,急起直追,巩固配实边防,则诚大局之幸也”[7]94-95。《申报》1933年7月15日即以《法国占据太平洋岛屿:向为我国渔民居住地》为题,提出“西贡与菲律宾间有小岛九座,住于北纬十度,东经一百十五度左右,向为中国渔民独自居住停留之所,顷据西贡电,现有法差遣小轮亚勒特与阿斯特罗勒白两船,忽往该岛树立法国旗,要求为法国所有”[25]。而有人造访南京外交部探寻国民政府之因应对策,外交部则“尚未接到正式报告,仅于报端阅及”[25]情报讯息之滞后可想而知。
事实上,如全文所述,民间舆论(也包括低级官员乃至极少数高官)已经就南海诸岛从各个方面全方位做了深入研究,这些成果就刻印在著作中或期刊里,但外交部似乎并没有留意。历史有着惊人相似,1946年外交部在为日人所谓“新南群岛”究与团沙群岛是何关系而焦虑时,殊不知在1933年南海九小岛事件之时,已经有很多文章提到了“新南群岛”,如1933年顾秉麟《成为问题的南海九小岛》对日人福岛丈雄所作“新南群岛事情”所述11岛之英文名称、面积等数据都有摘录。1933年《九小岛实况:远眺九小岛之一:[照片]》、1933年钱彤《九小岛事件》、1933年俞沛文《中国南海九小岛问题(附地图)》、1938年干城《日本占据新南群岛与远东局势》[26]等都有记载,虽然笔者翻检“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外交部档案时看到外交部档案中保留有剪裁的1946年8月4日和5日上海《大公报》连载曾达葆的文章《新南群岛是我们的!》(上、下),曾文也提到了十几年前福岛关于新南群岛的论述,显然外交部对于十几年前的民间论述甚少关注,而仅及于眼前。
民间舆论力量蕴藏了强大的理论力量、民意力量,但南京国民政府并没有有效利用和善待这些民间力量及其研究成果,官方与民间难以形成合力,这的确留给我们深刻的教训。与强势的官方话语体相比,民间社会舆论是处于劣势,这就更需要政府善待。带有民间和自发性质的民间舆论先于政府“先知先觉”,希望政府善待民间舆论,重视来自底层的社会体验。带有民间和自发性质的民间舆论是公民社会唯一能与强大的公权力对峙的力量源泉。只有二者在一定层次上协调、对话、平等地发出声音,才能有效地形成合力维护国家领土主权。
(三)参与面广,尤其是学生阶层也广泛参与
如1936年衡湘学校高二班张静民、卄六班汪敬熙、梁庭栋等从历史沿革、国际法先占与时效、中日法三角关系等角度对南沙群岛属于中国做了学术价值较高的论述,理论运用之强,似乎超出了学生阶层的认知范围,反映了他们“事事关心”,对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完整认真准备资料的爱国主义精神。这也给我们提供一定的经验,即加强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边疆历史文化教育等,一方面可以增强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操,另一方面也可以塑造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通过本文对民国时期民间舆论对南海问题的关注,爱国主义教育从小抓起,坚持不懈,迫在眉睫。
结 语
本文对民国时期中国民间社会舆论对南海问题关注群体的构成、载体与时间分布和社会舆论对维护南海诸岛主权所做出的贡献等做了深入的论析,“尤其是民国学者在九小岛事件后对南沙渔民和地理景观进行了历史场景的叙述和勾勒,为深入研究南沙历史保留了珍贵资料”[27]。诚如本文第三大部分谈到的,民间舆论对于南海问题的关注与撰述其实非常丰富且具有一定的深度,但这些研究成果或行动如何能够为政府所熟知,并与政府间达成一定的合作,从而形成全民族维护国家领土主权的合力。很可惜,国民政府都没有有效利用这一点,诚为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