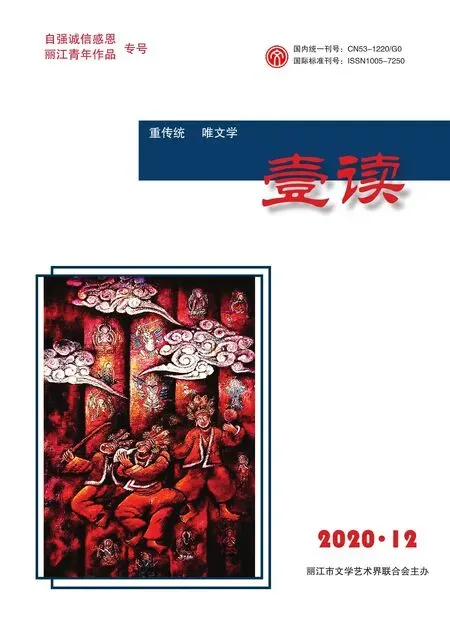花的日记
◆和丽琼
2018年12月28日 晴
蜜蜂采蜜时,花会痛吗?
在梦里,我闻到了青色稻子甜美的味道,以及那些盛开的花泌出的蜜香。我还梦到,稻秆承受不住饱满的谷穗而垂下腰,风一吹,大片的黄色麦浪一边唱歌,一边叹息。花也随着风飘落到地上,消失在泥间。
我醒来。模糊的光线中,表妹笔直的高鼻梁,带着远山的青色,近却又感觉很远。在光线的打磨下,脸颊投下一片冷峻的阴影,她乌黑的辫子随着胸前的隆起而起伏着。暑假的晚上,我和表妹一起睡在我的床上。川端康成说:凌晨四点醒来,发现海棠花未眠。未眠的是人,花总是醒着。表妹睡着了,但花容依然在她脸上、身上醒着。洁白如玉的皮肤,瘦削的肩膀,尚未饱满的胸脯。原来我们的身体有着惊人的相似。我慢慢靠向她,近到几乎贴着她的脸颊。那刻,身体的奥秘离我很近。
表妹的脸上有花的清香,我睡梦中的花香就是来自这片田园。她长而密的睫毛,就像骄傲的羽扇,轻轻落在下眼睑上。嘴唇柔软,湿润,薄且粉嫩,就像她的名字,漾出一朵花。表妹是一朵花,我也是一朵花。我在夜里遐想,我们的身体在往后的时光中会勾勒出怎样的纷繁和锦绣呢?
世界喜欢以花给女子命名。在纳西语里,称女孩子为“含蜜金”或“蜜汁”,意思是:“我家的宝贝女儿”。在我幼小的时候,外婆和母亲常常把我抱在怀里,一声声唤着“蜜金”。纳西族的女人们,想通过含着蜜的叫唤声,把女儿的一生都泡在蜜里。她们假装忘记,蜜从花中来。终有一天,花会被蜜蜂采去蜜汁,在命运的笼罩下,枯萎凋落。
我希望我和表妹永远像花一样盲目美丽,但我无法拒绝、无法逃离世间的因果。女人是蜜,也是花,无论颜色鲜艳还是洁白,花总要在时间中酝酿出蜜汁,无论甜美还是苦涩,沁出的蜜汁总是伴随着疼痛和干涸。我知道迟早有一天我要走上一条路,变成母亲的模样。那是花期少女可以预见的结在时间深处的果实,但在这之前,我的蜜,等待着由我孕育而出的一只蜜蜂来采。
白丁香在午夜开放,它的美先献给夜色。在花瓣的内部,隐藏着雄蕊和雌蕊。它吐着花语:爱的萌芽。它在等待。它的胚珠需要萌芽。我蜷缩着躺在床上,手摸向腹部。母亲打来电话,吐露着迷离的语言,试图给我引路。她嘴里说着古老的纳西语,那些音节带着一种旨意。一个姨妈打电话给母亲,说梦见我和母亲在地里摘包谷,箩筐里装满了金黄色的包谷和大南瓜。一个婶婶告诉母亲,说梦见我家老宅,在厨房供奉着祖先灵魂的神龛前,“玛咪灯”绽放出耀眼的光芒,开出一朵花来。母亲则梦到自己二十几年前大腹便便的模样。原来丛生的花群,各表一枝,根还连着,蜜也还连着。后来我想,那时我的身体大概也像卷曲的花蕊吧,在风中等待。我隐约感到,有个新生命在我身体里发芽了。
孕期的第九个月,我在检查室的走廊画上,见过女人胸前的花心,在皮囊下包裹着一个水系。从侧面看,那是一颗向左倒着生长的树。根系发达,枝叶繁茂,所有的线络往身体的内部伸展开去,只把突出的那头留在人们的视野里。它也像一朵含苞待放的花。它安静着,紧闭着,储存着。假以时日,它要突破,从出口灌溉一个人间。在层层叠叠的线管中,我看到不容易看清楚的输乳管隐藏在某一个枝条下。那个时候,我的输乳管在寂寞的等待,等待它充盈,等待它开花,等待它涨潮。
一只蜜蜂选择了一朵花。
无数鲜嫩的花朵,随着风向它起舞,一些待放的花苞在悄悄躲闪。蜜蜂的目光轻轻拂过,它知道,时候未到,有些花不能去采。它径直飞向一朵全力盛开的花。蜜香招引着它。它轻轻落到花盘上,轻到不愿惊起花粉。几株雄蕊已经熟透,正在阳光下摇坠,底部团着蜜。蜜蜂伸出小管,刺入蜜的深处,吸取蜜汁,汁水从伤口流出,被储存在蜜蜂的蜜囊里。我想知道,蜜蜂采蜜时,花会疼吗?
表姐哺乳的画面,给我带来了阴影。喂奶时,她的小蜜蜂贪婪地咬着花心,表姐被蜜蜂蛰得痛哭,本能地移开花心。但一朵花是无法拒绝蜜蜂采蜜的。表姐只能将花心塞给嗡嗡乱叫的孩子。后来,小蜜蜂长牙了,她的乳汁,一半乳白,一半血红,伴随着花的痛,一口一口被咽进身体之中。
属于我的那只蜜蜂在冥冥命运的感召下,转向我,向我飞来。花会疼,但我无法拒绝、逃避,因为我带着蜜汁。
从新生儿科出院回来,今天是他出生第六天,第一次躺在我旁边。小蜜蜂四处寻找着他的花心。我要迎接第一次哺乳。看着襁褓里小小的脸,我突然心疼他的弱小无助,但内心深处更害怕蜜蜂尾针上带着石磨般的疼。现在,他张着嘴寻过来了,就像医生拿着空空的针筒,准备抽出我备好的血液。针尖在张合。从针孔里,我看到了粉红的嘴唇、牙龈和舌头,它们是柔软还是坚硬呢?我全身紧绷,试图将全身的力气都聚在花心上,让它成为铠甲,抵御外部的入侵。电流一样的冷战传遍全身,我看到手臂上凸起的鸡皮疙瘩,那是来自我身体里的颤栗。开在心底的花想保护我,可是为时已晚,我已踏上新的征程。
在幼发拉底河畔,生长着一种极其稀有的黑玫瑰,它的颜色,是一种极深的深红色。最初在春天的时候,它是鲜艳的红色,在日照、土壤和地下水相互融合之下,娇艳的红色在入夏以后变成了深沉的黑色。
最初几天我流出的初乳是浓稠的金黄色,之后便慢慢淡化,成为乳白色:变换成为天使的颜色。小蜜蜂不断长大,花日渐枯萎。随后的几个月,在哭闹声与疼痛间碾转反侧的时候,我想到母亲和黑玫瑰,我在恍惚间觉得变成了母亲。这是我不得不接受,又无法适应的事实。而黑玫瑰的花语,让我惊醒:你是恶魔,且为我所有。我要对你负责。

和立昌
和立昌,纳西族,1988年5月生于云南丽江,2011年毕业于玉溪师范学院美术学院美术学专业,主攻版画兼修国画、书法。云南省美术家协会会员。工作之余潜心书画艺术创作,长期刀耕不辍,作品多次入选国家和省级展览并获奖。先后在玉溪、丽江、江苏徐州举办个人版画作品展。数十件作品被中国警察博物馆、雁南艺术会馆、丽江书画艺术研究院等机构和私人收藏。30 余件作品在各类艺术周刊发表。2019年获丽江市第六届文学艺术创作艺术类最高荣誉奖。
丽江白沙壁画 木刻临摹作品






杨得圆
杨得圆,纳西族,1980年8月生于丽江市。从事木雕行业25年,擅长线刻与书法。作品有创意,线条流畅无局促感,注重细节表达,人文色彩浓郁。2006年因独具特色的创作而被《丽江柔软时光》一书重点推荐,2013年受英国北安普顿大学艺术学院邀请赴英国展览。

幻想

无题

渔2

鱼

思

渔
2019年1月23日 晴
满月。那轮悬在天边的月,转过阴、晴、缺,如今到了圆。
他圆圆的脸蛋粉嫩嫩的,小嘴边还残留着几滴奶,吃完奶后疲惫又满足的沉睡着。他静静地躺在时光里,就像是一棵植物兀自成长。母亲拿来一个铜铃,用红布串着,系在小床旁边。母亲说,这是她去一个纳西东巴那里求来的,用来辟邪的,里面有东巴文写的符,保佑孩子在夜里睡得安稳。她在铃铛里塞了棉花,下楼招呼客人去了。
时不时有人上来看他,给他带来各式各样的礼物,大家轻声地赞叹着新生命的饱满与鲜嫩,偶尔看向我询问一下他吃奶的情况,晚上哭不哭,好不好睡等问题。瞧,他来到人间一月,便成为焦点。这场满月宴,他是主角,而他在酣睡。
欢笑声,嬉闹声,追逐声,穿过走廊与门窗,混合着阳光的温度,重重地砸进我的耳朵。我为之一颤,并全身不适。我支撑着未愈的身体,尽量认真的回答着人们的问题,尽管他们问的不是我,我只是代为回答。记忆是如此清晰,每每想起生产的情景,我都会感到一股冷意。日子漫漫,才一个月而已,身体的疼痛还如潮水般在我身体里拍击。如今,他们都在高兴,除了我,除了我的疼。我在这场满月喜宴里貌合神离,欢声笑语,那是外面的世界。
当脱离母体,他害怕又惊恐,来不及在我的怀抱逗留一分钟,就去了新生儿科的小床上,与众多新生儿经历一样的无助。在生命的最初几天里,护士的声音、婴儿的哭声、器械转动的声音,以及消毒水的味道,成了他的全部。到了家里,他又重新接纳了许多的陌生。通过乳汁的味道,他首先辨认出了我。一月已满,他甚至在清醒的时候,对前来探望他的人们露出浅笑,或者当有人轻轻拉住他的小手,他会用力抓住。满月,他对这个家已产生足够的安全感,认可了这里的气息。婆婆说,太不可思议了,这么小,居然也会投巧。我说,这是时间的力量。
他本身就是时间。他像一株花,一棵草,开启了属于自己的路程,走到足月,迎来了满月。最初,他以一颗种子的形式在我体内着床,努力生根,12 周时初具人形。16周,我第一次感受到胎动。这一动使我真切地感受到一个小小的身体裹在胎衣中循环于我的体内。我感受到了骨骼,一股力量在滋生,我惶恐却又暗自期待。22 周,腹部开始“出怀”,我时常在肚皮上寻找得到他的踪迹。37 周,他在宫内足月,所有发育基本完成,随时可以出生。在40 周的那天,他终于按捺不住,被新世界的引力吸住,在逼仄的宫内轻轻一跃,学着那只跃进龙门的鲤鱼,来到了新世界。如今,他在人世满月。对于一个家庭,也因为他的到来而圆满。
我也满月了。
我的满月以心里的灼伤和没有流出来的泪水为标记。自从生产那天起,我的生活被劈成了两重天。我开始成为别人口中的妈妈,这是一个让我感到陌生又害羞的词。每当他一哭,家人就说:“找妈妈呢,快让妈妈给吃几口奶。”喂饱他,是我的第一关。积滞的奶水时常制造麻烦,我胸前挂着两颗不定时炸弹,说不准什么时候会在睡梦中被痛醒。有时候肿胀起来,就连胳肢窝里都像灌满了乳汁,摸上去有一大块硬块,旁边还有几个小疙瘩,动一下都让我疼得叫出来。堵奶、硬块、乳腺炎,在梦里化为魔鬼,而我陷在噩梦的沼泽中。痛,突破所有的防御,抓住了我所有的神经。前几天,堵先从乳腺开始,然后蔓延到心,最后全身都烧了起来。39.8℃,我在痛的中心。家人扶着我去最近的诊所,一阵寒风让我把脸埋到高领毛衣里去,我想着还没满月呢,不能受了寒气。乳腺炎引起的发烧,先吃退烧药,再输液消炎,还要把滞留的残奶排出。医生的话语就像是一道命令,我唯命是从。有时候,崩溃近在咫尺,我真怕会把怒火合着委屈扔向襁褓中的婴儿。只有我知道,花在崩溃,花在凋零,花在哭泣。花瓣被风雨打湿,坠落,被碾成泥。
这种时候,我更不能忘记,我们是一步步走向圆,走向满的。他是,我是,那个月亮也是。
我习惯性的把手放在腹部上,想去感受那片凹凸,如今却只有一手的平坦。十一个月前,我感受到了从无到满的过程。一开始,他是隐秘的,我的肚子是隐秘的。一切都在隐秘中发生。后来,我的肚子慢慢被填满,成了一个圆,就像一个装满了甜蜜和焦虑的气球,在光影之中晃晃悠悠。每一天肚皮都被撑得更大,原始的生机,裸露在人们的视野之中。电视上,那只笨拙的向前奔走的企鹅,准备把捕来的小鱼喂给它的宝宝。我抚摸着自己巨大的圆,一半心酸,一半欢喜。有些时候他也会显形,比如我压到肚子,他就会结实地给我一脚,偶尔力度大了还会在肚皮上清晰地印出一个小脚掌,让我即难受又高兴。我被这满满的圆充斥着,从肚子,到心脏。
夜幕拉开,我平躺在床上。这个孕了九月的圆向我压来,心脏受迫,我发出沉重的喘息,我就是那尾搁浅的鱼。每天,我隐藏着满腹的心事,拖着肿胀的双脚行走在路上。在路上,这个肚子,这份圆成了一道标识牌,人们尽量维护着我。变异的身体,带给我高贵的待遇。也许,在此时,我就是圆满。
我迫切地想要知道这个圆里到底包裹着什么样的礼物。我和他共同走到了这一步,很快就是我们要见面的日子。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我别无选择,透支了勇气和疼痛,在注定的那天卸下了这份足月的圆满。现在,我抱着满月的他,他在满月的成为母亲的我的怀里。我们站在窗户边,遥望夜空,那盏光亮的圆月,仍然照向我,让我觉得安心、温暖。
我望着怀里沉甸甸的果实,就像那轮圆月望着我。
2019年6月23日 雨
头枕在我的左臂上,细软的头发已经被汗水染上一层潮湿,我抚弄着他脑门上的头发,听着他的呼吸渐沉。
母亲来了。尽管她把脚步尽量放得轻,我还是听出了是她。她走到房门口,脚步顿住了,愣了一下,才又走进来,挨着我在沙发上坐下。我问,怎么了。她迟疑着,支支吾吾的,捋了捋我额前的头发,说:“也没什么,刚才我在门口看你抱着孩子,突然觉得就像以前我抱着你。”说话间,她的眼里有一团氤氲。
时光在斑驳中留下点点印记。印记带着我穿梭在时光的迷宫中,去寻找属于我的情,我的路。它们在某个地方等着我,会告诉我,路在何方。
“你以前是怎样的?”我看着她眼角的纹路问道。她笑:“奶奶年纪大了,外婆离得远,你爸又忙,都说月子里不能碰水、抱娃、走动,可我哪一样没做过呢。你奶奶睡得早。每天晚上我就点一个油灯,抱着你坐着等你爸。”我说:“怎么没人关心你呢?”“那个时代,女人哪有这么金贵。生个孩子就像下个蛋。两三天就开始下床慢慢做点轻活了。甚至有的人当天就下床干活了。我算好的了。再说了,心思都在娃上,我只要不疼,什么都可以干。”母亲的话说得我心里木木的。她摸了摸我的胸部,问道:“今天有没有按时吸?不疼吧?”我撅着嘴巴,摇了摇头。
娃娃牵挂妈妈,是一根绳子;妈妈牵挂娃娃,是一条路。这是一句纳西族的谚语。我可以想象得到,当我凌晨被送进产房,母亲奔到医院的慌忙。产房门口放着两排椅子,从早上六点到中午一点,在每一个椅子上,她都做了短暂的停留,更多的时候,她抱着双手,在白炽灯下那段短短的路上,眉头紧蹙来回踱步,口中嘀咕着。她在担心着可能发生的意外,但又不敢说出口。她在计算我的产程,或许也在回忆她的生产之路,那条女人都要走的路。
医生向家属交代:男孩,母子平安。母亲的心稳了。后来,她跟我说,听到这句话,她心里无比高兴,不仅因为我平安,更因为我生了男孩。我回嘴:“你怎么还这么重男轻女呢?”母亲摇了摇头,语气放软:“蜜金,你走完生孩子这一遭,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不是我重男轻女,你看男人需要受什么罪吗?纳西女人是蜜,但苦。以后你儿子也不用受苦。生儿子你婆家也高兴的。你不会受气。”我终于又从她的口中听到了“蜜金”,带着疼爱。多年之后,这奢侈却偏偏用在这样的话题里。我像那条缸里的金鱼,眨巴着眼睛,有口无言。
晚风轻易地波动了我的心潮,它却远去,带我进入母亲生第二胎的那个中午。每一次阵痛,她的焦虑就更深一层。她想早点结束这份痛苦,可是她又害怕结束。尽管人们都说这次的肚子形状跟上次不一样,但万一呢?她的害怕阻挡不了新生命的脚步。瓜熟蒂落,她顾不上流血疼痛,屏着呼吸,等着结果的宣判。“男孩。”话音落,她吐出一口气,装作不在意地笑了。出院回家的路上,她走得知足。
母亲生了我和弟弟,在我们身上种下相似的印记,二十八年后,我又结出一个果子,这个果子与当年从她身上落下的那两个果子有着相似的印记。后来,在这条有着印记的路上,我当了母亲,母亲也重新当了回母亲,她时而走在我前面,时而在我背后絮絮叨叨,光影重叠,唯一不变的是,她一直走在这条路上。母亲一直在“母亲的路上”走着,我跟着她,她带着我,一起走上了同一段路。我会变成母亲吗?活成她,在三十年后去印证早在开始就烙下的模印?
吉达说:“我的母亲是父亲的影子。”
在巴西电影《看不见的女人》中,三个女人,三条路。她们是母女、姐妹。父权在一个夜晚割裂了她们,让她们彼此成为了看不见的女人,同在一座城却终生不见。在母亲临死之前,妹妹小心地询问姐姐的下落,身患绝症的母亲轻轻地岔开话题。我看到,秘密被母亲带进了墓里。当潘多拉的盒子打开,抖落妹妹的丈夫遗物上的灰尘,多年来被“隐藏”着的来自姐姐的信件暴露在阳光下,妹妹的错愕与失重交替上演。那一刻,风烛残年的她在阳光下几乎透明,抖成了一粒灰尘,飞进了我的眼眸。
看不见的女人,彼此不见,也被社会隐形。
母亲是传统的纳西女人。她的路在家里,在各个房间与厨房之间。家是她的信仰,家里有丈夫、孩子,她把自己隐形。有一次,我听到她跟别人聊天说:“人活着,就是在活孩子。”她上班,她挣钱,她会买漂亮衣服和金耳环。可是,丈夫、孩子开心,她才真正的开心。父亲的朋友很多,喜欢热闹,经常邀约朋友来家里吃饭,母亲时常需要张罗一两桌的饭菜。父亲在饭桌上兴高采烈,母亲在厨房里心满意足。大部分的时候,弟弟可以跟父亲一起上第一桌吃,而我跟母亲要等他们吃好之后再吃。我说:“妈妈,弟弟跟他们吃,我也要一起吃。”“这是纳西规矩。你跟妈妈等一下一起吃。”母亲轻哼着小调,走进厨房。而我生着闷气,嘴唇撅到天上去。多年之后,我才明白,母亲在她的路上,甘之如饴。而她期望我也跟她一样。
风是风筝的路。从办公室的窗户往广场上看去,偶尔会看到天空中飘浮着风筝。从我的位置看,它就像是自己飘在风里的,它没有牵挂,只跟着风走。“厨房是女人的后花园。”因为我不善家务,母亲总跟我说这句话。在我出嫁之前,她曾忧心,婆家因为我不会做饭会有意见,叮嘱我任何时候都要心平气和,以婆家为大。等我到了婆家,安心地过上自己的小日子,她又嫌我“有了婆家忘了娘家,电话打得少,也不回来”。风筝的线一直被揣在放风筝的人手里,这根线曾被我“看不见”,现在做了母亲,我“看见”了。我觉察到母亲手中揣着我的线,时而松时而紧,当她拉紧的时候,她的手也因此疼痛。她却无法松手,因为她是母亲,是“蜜汁”。那根线,浸透进她的血肉里,成了她的路标。
按照纳西语的叫法,路是“柔骨”。来自于骨的柔,就是母亲。母亲生骨,也生肉。纳西族在日常的话语中,将儿子这边的亲戚称之为“骨这边的人”;若是嫁出去的女儿,那边的亲戚连带着女儿都统称为“肉这边的人”。骨与肉,便在此分了路。我在路的岔口,恍惚着,迟疑着。我想去一一辨认,明明我来的路只有一条,现在,为什么却让我走向别的路。
我手里有了一根风筝线。每当给小小的他洗澡,看到他的两腿之间标记着“男”的印记,有些时候,我是满足的,心想他因此而免去了许多做女人的疼痛。尤其是在我脆弱的时刻,我为自己生的是男孩而庆幸。每当这种时候,我会想起母亲,想起她的路。母亲一直在路上等着我,带着踌躇与心疼。她知道有一天我将走上她的路,在我手里握着一根线的时候。
我握着手中的线,它嵌进我的血肉里,纹路清晰。可是,我不知道该以什么样的力度与温度,去平衡属于我的风筝。路在脚下,脚已迈出,而我在路上,战战兢兢。我努力辨别着方向,尽量避免母亲曾经踩过的坑洼。我需要一阵清风,为我拨开云雾,让路明朗。
我们之间是一条曲线,母亲和我,我和我的儿子。我是中点。半岁的他颤颤巍巍地扑向我,像有根线牵引着他。我盯着这条线,眼睛生疼。
2019年10月23日 晴
我怀了他十个月——我的孩子。
他“怀”了我十个月,用他的气味、声音和体温。我被他包裹,他吐“丝”做茧。
我怀抱婴儿,闻到他身上的香,奶香中混合着青刺果油的香、沐浴露香、衣物上的洗衣液香。这香气甜而干爽,弥漫了整个房间。我被他的气味包裹,像我被他孕育着。最初的时候,他的排泄物也带着奶的味道。一直到开始添加辅食,味道开始加重变得刺鼻,有些时候更是臭气熏天。这样的时候,我就怀念初生儿的香气。后来,我日日站在厨房里、水槽旁,制作、清理各种他的味道。我已经知道答案:当时我怀的那个圆,便是这人间烟火。
我躺在床上,护士拉开我的衣服,胎心仪不断在我的腹部间来回滚动。它在寻找一个声音。我安静地等待着。突然,“咣当,咣当”的声音传来。我再仔细听,还是“咣当,咣当”。这个声音跟美妙差着一截距离。“怎么是一个小火车的声音呢?”我奇怪至极。护士笑:“这就是生命最初的声音呐。”他向我驶来,我怀着陌生和慌乱等他到达。我不知道的是,我需要在寒冷的深夜里,面对比这个更不美妙的声音。我被他尖锐的哭声惊醒,不得不抱起他喂奶。当我怀着他的时候,他的哭声混合在羊水里,回荡在子宫,反射给他自己。而如今,他的哭声,直达我的心里,让我焦虑。唯有他的笑声,是例外的。来自于他的纯粹的快乐,让我觉得不真实。这份不真实,让我格外小心翼翼的呵护。就如母亲呵护怀孕的我。
我们在春天结缘,共度夏天。那个夏天格外的热,不知不觉,后背的衣裳总会被浸湿,我俯下身,时常闻到一鼻子的酸臭。流失这么多液体,让我既烦恼又心疼。我知道,这份超出平常的热气和汗水,正是属于他的。他在我的暗处,我怀着他,我是他的出口。而他给我带来的体温,正在蒸发、消减。这份夏天的难熬,在冬天给了我好处。手脚冰凉、极其怕冷的我,突然热火冲天。因为我怀着这份温度,除了自己之外的37℃。终于,我们在冬季的末尾如期相见,我摸着怀了十个月的这份暖,感觉像隔了两个世纪。在月子里,我握着他热乎乎的小脚,想到了怀抱天下的佛。
前三个月,他是被隐瞒的。纳西族的风俗里,对于不足三个月的胎儿,是不可挂在嘴边的,怕被别人“要”了去。我俯首在这句魔语里。
我常想,如果他能说话,一定会为那无故消失的三个月而发声。直到数月后,攒到藏不住的肚子,让我怀有身孕之事,亮堂如白日。
有些话,不必说出来。而有些话,说出来,那则是要命的事情。当他开口说话,第一次叫我“妈妈”,我知道,我被命名了。当我称呼自己为“妈妈”,抱起襁褓中的他,我知道,我已经启程走上了一条遥远的路。
我在歌里听到:你的身体是个仙境。
我记得有个周末,母亲带着12 岁的我进入了公共澡堂。雾气缭绕,水流絮絮,女人们的声音传来,母亲把我攥了进去,我置身于仙境。我在仙境里,寻找自己的位置。模糊的视线中,白色的身体挂着水珠,晃荡着向我走来。随着距离越来越近,我看得越来越真切。我闭上了眼睛,把那些丰满、松弛、变异关在门外。我进入属于自己的空间,水流从顶而下将我浇透。我站在水中央,一边抚摸自己骨骼分明、线条冷冽的身体,一边想象着与我一墙之隔的母亲。我在仙境里看到了一些痕迹,这些痕迹将我灼伤。水珠随着我轻轻地颤抖,然后,离我远去。
当我在镜子里看到自己变异的身体,我已怀他将近十月。花要结蜜,蜂在酿蜜,而我在等待。
当我又一次站在镜子前,我已生下他十月。花要结新的蜜,蜂在酿新的蜜,我仍旧在等待。月亮覆盖了我的神色,怀里的他将我的心占满。他是新生,我也是新生。
透过镜子,我寻找十月前那个惊慌的女孩。我要拥抱她,轻轻地告诉她:别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