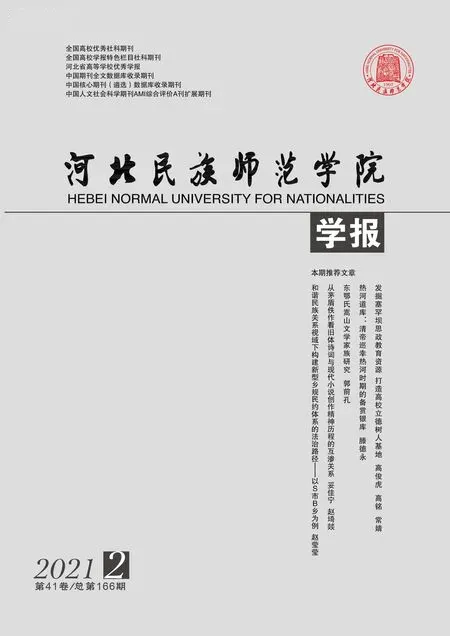流亡中的批评家
——重新发现埃里希·奥尔巴赫
埃里克·林斯特拉姆 著 王晓燕 译
(弗吉尼亚大学,弗吉尼亚洲 美国 22904)
历史记忆的一个特点是,那些复杂而重要的时期往往以几个精简片段来呈现。例如,法国大革命经历了从贵族叛乱到资产阶级自由,再到恐怖的暴民统治,最后到波拿巴主义,但在大多数人的记忆中却仍然是一场以攻占巴士底狱和砍掉贵族头颅为主的运动(占领皇家监狱和处决路易十六实际上间隔了三年半)。同样,随着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战败和民主宪法在安静的图林根市(Thuringian)的推行,现代主义的街头狂欢(street carnival)在1919至1933年的魏玛时代随处可见,弗里兹·朗(Fritz Lang)的电影、包豪斯(Bauhaus)的家具,以及柏林的歌舞厅所带来的慵懒、迷醉,一扫几世纪以来普鲁士的沉闷。而对于这一至少比狄更斯所描绘的法国革命更为准确的画面而言,莎莉·鲍尔斯(Sally Bowles)①音乐剧《歌厅》(Cabaret)中的女主角。——译者注和她在奇巧俱乐部(Kit Kat Klub)的朋友只是部分原因。
事实上,魏玛时代的文化确实出现了大规模的、工业化的发展,以致于我们记住的是电影导演和设计学校的名字,而非首相或议会领导的名字。虽然,先锋派的作品并没有被大众普遍接受,但先锋派的艺术家们确实从新的大众媒体和工业技术中汲取了能量。路德维希·密斯·凡·德·罗(Ludwig Mies van der Rohe)和沃尔特·格罗皮乌斯(Walter Gropius)等建筑师们通过玻璃和钢铁来建造宏伟的工厂、公寓和办公楼;而弗里兹·朗的《大都会》(Metropolis)和《凶手》(M)则将现代城市的人造光和不知名的空间相结合,从而营造出一种新的昏暗意境。
正因如此,魏玛时期的故事中往往会遗漏不少传统形式的知识成就(与电影艺术的即时性相比,德国大学学者的作品便显的过时了)。人文学科的写作尤其如此。比如,一位研究原始文献的学者怎么可能与理论物理学、弗洛伊德心理学或法兰克福兴起的后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相媲美呢?事实上,熟悉埃尔文·帕诺夫斯基(Erwin Panofsky)作品的人都会告诉你,魏玛德国艺术史的发展一直致力于重新勾勒这门学科的轮廓。即使是人文学科的精英,也未能幸免于来自魏玛时代那种震撼人心、打破传统的兴奋情绪的影响。而这一时期最伟大的文学学者莫过于埃里希·奥尔巴赫(Erich Auerbach)了。奥尔巴赫于1936年离开德国,先后流亡于土耳其和美国,并于1957年在美国去世。时至今日,奥尔巴赫的移民及流亡经历对他的作品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甚至于使其黯然失色。他最著名的作品《摹仿论:西方文学中的现实再现》(Mimesis:TheRepresentationofRealityinWesternLiterature,1946),是战后几十年里美国学界经常倡导的那种规模宏大的、反流派的,且已过时了的文本。该书的第一版共十八章,每章针对一部文学作品的原始文本和译文进行讨论。《摹仿论》以《奥德赛》为开端,以19世纪龚古尔兄弟创作的小说为结尾,先后梳理了乔万尼·薄伽丘(Giovanni Boccaccio)、米歇尔·德·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威廉·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弗里德里希·冯·席勒(Friedrich von Schiller)及其他作家作品。尽管这是研究生院的比较文学、英语及文化研究教学大纲的主要内容,但大多数受过教育的人对此却只知道一件事:这本书是在大屠杀最严重的时期由伊斯坦布尔的一名德国犹太人写的。可以理解,如果不去问一个与欧洲完全疏远的欧洲人写西方经典意味着什么,就不可能去读《摹仿论》这一事实。但随着最近奥尔巴赫另一本书的再版①即《但丁:世俗世界的诗人》的再版。——译者注也许是时候来探讨一些其他的问题了,即:奥尔巴赫能否从“流亡批评家”(the critic-as-exile)的流放中解脱出来?
埃里希·奥尔巴赫于1892年11月9日出生于柏林的一个富有的犹太商人家庭。这是柏林从一个由官僚和商人的聚居区向工业大都市转变的最后几年,城市人口在19世纪后半叶达到80万,成为欧洲的第四大城市。同样出生于1892年的犹太作家沃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回忆道,世纪末的柏林,当马车夫们在街上喂马喝水时,城市的地下交通建设正进行的如火如荼。
和许多享有特权的年轻柏林人一样,奥尔巴赫也曾就读于法兰西文理中学(Franzö sisches Gymnasium),即法国中学,并接受了强大的罗曼语文学训练。奥尔巴赫于1913年获海德堡大学法律学位(他的论文题目是“制定新刑法的影响机制”),之后他服役于德军西线,并因腿部严重受伤而被授予二等十字勋章。即使在后来流亡国外漫长的几十年里,奥尔巴赫也从未想过放弃自己的德国身份,并试图总是抱着回国的希望。他于1921年写道:“我是普鲁士人,也是犹太信仰者。”这显然是对那些看到两者之间存在矛盾的人的一种回应。
作为一名坚定的普鲁士民族主义者,奥尔巴赫在战争结束后放弃了他计划中的法律职业而转为学习法语、意大利语和拉丁语,并撰写了一篇关于文艺复兴早期的中篇小说研究的论文来取得他的罗曼语文学博士学位。(当时,语文学在德国是一门非常活跃的学科,它不仅涉及对词汇起源的研究,更如爱德华·赛义德所言,语文学通过对语言的所有现有书面材料及其修辞、法律和文学的研究,再现了一种文化史。)而这种复杂的、充满典故式的阐释文本的语文学方法几乎出现在奥尔巴赫的所有文学批评中。
奥尔巴赫的第一本著作《但丁:世俗世界的诗人》于1929年问世,是一部奠定奥尔巴赫声誉及其在德国学界地位的佳作。(这本书于1961年首次以英文出版,在绝版数十年后,最近才被再版。)在不到两百页清晰独特的阐述中,奥尔巴赫为文学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出发点,即,在任何文本中,对普通人类经验的态度是什么:构成生活的事件、选择、个性、关系和情感?然而,这个被奥尔巴赫称之为起点(Ansatzpunkt)的著名切入点似乎并不像看上去那么明显。众所周知,对生活的描述是一种相对较新的文学现象,而这种现象只有将司汤达、巴尔扎克和福楼拜这三个人进行整合时才会出现。但奥尔巴赫的语文学训练让他清楚地认识到,在他们之前的几个世纪里,文学阐释的基督教模式便提倡人们用寓言、预表学或其他隐喻的方式来解释一切事物。正如1910年一本老版的读者指南对《神曲》所评价的那样,“穿越三界亡灵之旅……只是一个外壳,一件寓言式的圣衣,诗人选择以此来赋予其思想”。奥尔巴赫认为但丁是一位关注世俗(earthly)生活的诗人(标题中的irdischen被不准确地翻译为secular)②作者认为在《但丁:世俗世界的诗人》(德语Dante als Dicher der irdischen Welt;英语Dante: Poet of the Secular World)的英译本中将“irdischen”译成“secular”,是不准确的。——译者注,这显然是一种对传统自觉而大胆的背离。在该书的开篇,奥尔巴赫概述了从古代到但丁时代的文学史,并指出其最显著的特点是荷马史诗与古希腊哲学之间的隔阂。在他看来,荷马史诗将人物的命运与他们作为个体的特征紧密联系在一起。柏拉图教导他的学生们不要相信世俗的存在,因为这是对精神真理的模糊与扭曲的反映;亚里士多德则将人类社会进程看作一种充斥着偶然性的混乱,并以此来掩盖形而上学规律的运作。以奥德修斯为原型的人物形象(其言行具有一系列基本特征:狡猾、多才多艺、渴望冒险)经过充分的发展,最终演变成了希腊悲剧中普通英雄的性格特征。尽管基督受难故事对于肉体痛苦的表现促使对个性化写照的回归,但从东地中海传入的新柏拉图主义的盛行则将新约的文学革命推迟了几个世纪。奥尔巴赫认为,直到但丁时代,对尘世生活的关注才再次成为文学中的重要主题。但颇具深意的是,《神曲》发生在几乎完全远离尘世的地方:地狱、炼狱和天堂。
从一个敏锐的历史主义者的视角来看,奥尔巴赫认为但丁对托马斯主义神学的改造使他能够将逝者的灵魂描绘成个性鲜明、情感丰富且具有活力的人物形象。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在但丁九岁时去世,他指出人类多样性的丰富是自由意志的结果,并坚信人类的每一次行动及意志的努力,都会在灵魂上留下痕迹,因此,每个人的性格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形成。但丁将这一观点进行了延伸,他借鉴托勒密的宇宙学和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构建了一个秩序严谨的地下世界,并通过让每个角色在这个世界里的位置来揭示了他或她尘世生命的本质。因为上帝是针对某个灵魂的某个特征或行为来进行审判的,所以《神曲》中短短几行诗便能唤起对个体生命的整体印象。奥尔巴赫曾言:在每个逝去的灵魂中,“我们看到了他们的生命本质以一种从未在尘世生活过的纯洁和鲜明得到强化,并在广阔的空间中得以永恒”。奥尔巴赫注意到,《神曲》对于每一个手势、姿态或语调的刻画都带有神性判断的敏锐心理。在地狱的第六层中有一个著名的场景(这一场景在《摹仿论》中得到了详细的阐释):傲慢的法利那太(Farinata)笔直地站着,“似乎对地狱表示极大的轻蔑”,他询问但丁的祖先,并鼓吹着佛罗伦萨内战时的旧口号。在旁边阴影里的加发尔甘底(Cavalcante),跪着将自己支撑起来,只露出面孔,拼命地打听着他儿子的消息。对于第六层这一无神论者的空间而言,这种描写是非常合适的,虽然谁都无法让他自己承认是上帝的力量将他从尘世中脱离出来,但人物的个性差异依旧很明显。
奥尔巴赫敏锐的洞察力是把个体的神学和文学的概念联系起来。他认为,但丁通过对个体肉体和灵魂、现世和来世的统一刻画来使普通人的尘世存在成为文学关注的一个合理主题。而在后来的几个世纪里,当灵魂的至高无上不再是教会强制推行的文化要求时,尘世个体生命的内在意义仍然是所有文学的基本命题。因此,奥尔巴赫坚信,《神曲》标志着西方文学的重要转折点,而传说、寓言及其他类型的精神抽象题材便瞬间过时了。尽管奥尔巴赫在接下来的二十年里并未对此进行解释,但他确信但丁使朱利安·索雷尔(Julien Sorel)、艾玛·包法利(Emma Bovary)以及其他十九世纪现实主义小说中的普通主人公的生活成为可能。
虽然《神曲》注重于对个体形象的刻画,但奥尔巴赫对因但丁研究来使他出名的想法毫无兴趣。在这部著作①即奥尔巴赫的《但丁:世俗世界的诗人》。——译者注中,他对现实主义的理解发生了微妙的转变:“因此,这首诗塑造了一系列清晰而完整的自画像,包括那些已逝的和生活在与我们迥然不同的条件下,或者根本就没有生活过的人。由此,我们看到了那些隐藏于我们自身或与我们日常接触的人的思想中东西:影响和支配他们整个存在的简单意义”。奥尔巴赫似乎在说但丁以如此丰富的技巧描绘了他已故的灵魂(“如此清晰而完整”),并为我们这些现代读者了解十五世纪佛罗伦萨人的生活提供了想象的空间。(正如奥尔巴赫所说,《摹仿论》最简单的定义是指“对尘世生活感官经验的摹仿”。)而奥尔巴赫之所以称赞但丁,是因为但丁在《神曲》中并非对生命所有本质的复杂性进行简单地复制,其人物刻画是具有高度选择性的,并以神性审判的“简单意义”作为对整个生命的最终总结。
显然,这里有一个明显的矛盾,但如果我们忽略奥尔巴赫后来更著名的书的标题便可将其解决。奥尔巴赫的一生从未将仅仅摹仿生活的外在表现作为有价值的文学目标,而是注重通过对细节的描绘来促进读者对人类生命本质的理解。在他看来,那些不加区分地堆砌出引人注目的形象的作家(比如但丁同时代的圭多·奎尼泽利(Guido Guinizelli)是缺乏原则的,并坚信但丁对死去灵魂的描述“绝不是一种自然主义观察式的无聊展示”。历史学家卡尔·兰道尔(Carl Landauer,也是来自纳粹德国的难民)恰当地将奥尔巴赫的文学理想描述为,“柏拉图美学的两个极端,将理念和摹仿...合为一体”,即一个包括宏观抽象和微观具体的综合系统。可见,奥尔巴赫希望作家们能通过对细节的关注来建构一个连贯的整体,并以此来提供更广阔的道德视野。
整体来看,奥尔巴赫的这一思想是贯穿其一生的。1929年,奥尔巴赫主要关注个体的统一性,而他在20世纪40年代初写《摹仿论》时,这种理想已经成为一种社会历史的总体主义。奥尔巴赫曾对《萨蒂里孔》(Satyricon)中的著名宴会场景抱怨道:“我们感觉不到任何可能有助于我们从经济和政治背景来解释这一行为的东西。”如果这听起来像巴尔扎克的文学理想一样令人怀疑,那这种共鸣显然并非偶然。可以说,《摹仿论》是辉格史文学批评的变体,与19世纪现实主义小说一样,是经过两千年来一系列历史发展积累的顶峰。虽然,奥尔巴赫在《摹仿论》中明确放弃了用十九世纪的标准来评判古代文学,但他还是难掩自己的真正喜好。他强调说,佩特洛尼乌斯(Petronius)“甚至不需要像巴尔扎克在《欧也妮·葛朗台》中,通过对葛朗台财富增长方式的描绘来反映法国从革命到复辟时期的全部历史。”对于20世纪40年代的奥尔巴赫而言,他已不再是刻画人肖像的拥护者,而是转向对全景式的历史图谱的绘制。
奥尔巴赫在马尔堡大学任职仅六年便被德国历史风潮所驱逐。希特勒上台后,奥尔巴赫因其在一战中的军人身份而可以继续留在德国。但随着这一特权在1935年的纳粹种族法中被废止,奥尔巴赫也被立即撤职。而与此同时,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尔克(Mustafa KemalAtatürk)在土耳其教育体系现代化改革中,需聘请多位德国犹太学者前往伊斯坦布尔任教。奥尔巴赫便随之一同前往土耳其,并成为伊斯坦布尔大学罗曼语文学系主任。也正是在这里——缺乏最基本的学术资源,承担着繁重的、密集的教学任务,以及遭受着外国战时的诸多影响——奥尔巴赫创作了(也许是)二十世纪最受赞赏的文学批评作品。该作于1946年出版,并为奥尔巴赫成功跨越大西洋,进入美国大学体系奠定了基础。他先后到达宾夕法尼亚州和耶鲁,并在耶鲁大学执教七年。
在《但丁:世俗世界的诗人》中,奥尔巴赫将但丁描述为,“孤独无助的流亡者,其社会和物质地位取决于他私人朋友和赞助人的款待”,每当阅读至此,都会情不自禁为之而动容。奥尔巴赫在此书中谈及的一个重要内容是:但丁不仅在《神曲》中描绘了天堂和地狱错综复杂的神学地形,而且还重建了一个包括与他隔绝的人世、朝代变迁以及政治竞争在内的完整世界。奥尔巴赫在《摹仿论》中也以此方式来重构了从荷马到龚古尔兄弟的欧洲文学史,并通过保存和复兴西方正典的理念来拯救一种似乎正在自我毁灭的文明。
奥尔巴赫在战时伊斯坦布尔艰难环境中的卓越表现受到了应有的赞赏。但是,这个故事巨大的情感力量往往掩盖了一个重要事实:他的文学批评不仅是其流亡的产物,也得益于他成长的魏玛时代的活跃氛围。奥尔巴赫亲眼见证了电影的第一个伟大时代,他始终关注艺术形式与观众之间的关系:他认为但丁决定用托斯卡纳(Tuscan)方言写作是对作为欧洲新文化主体的大众的一种前所未有的迎合,而为大众创作艺术也许是魏玛知识分子的核心问题。作为一名文学学者,奥尔巴赫对此做出了回应,并将其自己时代的民主化冲动投射到但丁身上。尽管他对《神曲》复杂神学结构的描述是一次学识乃至其生活经验的胜利,但这一经久不衰的文学理想,即使奥尔巴赫的英雄传记也不应将其湮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