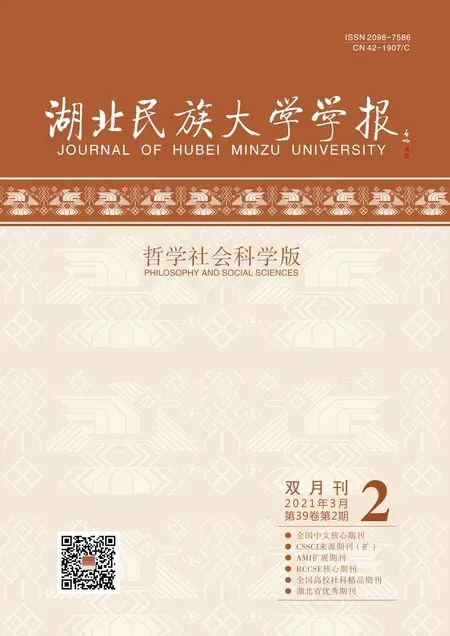清前期滇西南地区的政治生态与边疆治理
——以顺宁府为中心的历史人类学考察
尹建东 王联智
一、作为区域的滇西南:边陲地带的族群与社会
“滇西南”作为一种文化意义上的地理分类和认知,与历史时期的边疆开发及王朝施治密切相关。由于该区域地处边陲,远离统治中心,与内地长期处于隔绝状态,因而一直被视为“蛮荒”和“化外之地”。直到元明以来,随着中央王朝的治边活动特别是明清时期西南疆域的移民开发以来,滇西南的地域环境和社会面貌才逐渐被人们所认识。《明英宗实录》载:“云南东南接壤交趾,西南控制诸夷。”(1)《明英宗睿皇帝实录》卷117,正统九年(1444年)六月乙卯条。文中所说的“西南”便是指与今缅甸接壤的滇西南地区,即今元江以西,保山以东、以南的广阔区域。清代以来,滇西南的地理范围,主要是以顺宁府为中心的云州、缅宁厅、耿马土司、孟连土司等地,以及永昌府南部的龙陵厅、镇康州、孟定府等澜沧江以西、龙川江以东的地区,即今天的临沧市、保山市的施甸、昌宁,普洱市的孟连、澜沧等市县所辖区域。
滇西南地区地形复杂,以山地为主,其主体部分处于横断山系纵谷区的下段,海拔高度一般在600~1500m之间。所在区域纬度、海拔较低,气候炎热、空气潮湿,植被茂盛,属于典型的亚热带季风气候。滇西南山地河谷间虽分布有众多坝子,但因地理环境和交通条件的限制,明清以前内地移民极少进入其地,在人们心中形成了闭塞、落后、蛮荒有别于华夏的“他者”印象,而这种印象又通过汉文化主流意识的文化界定,将边陲地区某些自然现象加以想象,塑造出了滇西南独特的“地域形象”与族群、文化的边界,特别是与“瘴”相关的地理意象,很大程度上就是这种认知模式下的产物。
在文献记载中,“瘴”有两层含义:一是指“瘴气”,即为有毒的气体;二是指“瘴疠”,因瘴气导致的传染性疾病。瘴气在历史上一直是制约云南与外部联系的重要因素,而滇西南地区由于纬度、海拔相对较低、气候湿热,瘴疬肆虐尤甚。瘴气的存在不仅严重阻碍了滇西南社会的发展进程,同时也使历代王朝统治在该地区难以长久维持,形成了“流官不敢入、亦不得入”(2)王士性:《广志绎》卷5,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27页。的境地。清人张泓在《滇南新语》中这样描述道:“滇地多热,而奇热之区,则元江、普洱、开化及马伯、镇沅、威远,顺宁之云州,临安之漫琐、鹤庆之江营,若广南府治,并所属之百隘诸处,常年溽暑,而夏尤甚,瘴疠最酷。”(3)张泓:《滇南新语》,《丛书集成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8页。因此滇西南在当时一直被视为是瘴气肆虐的危险之地,外来者不愿也很难深入进去,其社会文化体系较少受内地影响。能够生活于这些区域的人群,主要以土著族群为主。史称,顺宁府“为滇省僻远之地,在万山之中,他省人鲜知之”。(4)范溥原修,刘靖续修:乾隆《顺宁府志》卷10《艺文志》,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刊本。故而该地区在历史上长期被视为是汉人不能深入和开发的边远荒蛮之地。
正因为如此,居住在顺宁府及周边地区的土著人群,一直以野蛮、落后的“蛮夷”形象出现在官方文献的记载中,并且在族群分类和表述上带有强烈的“异类文化”色彩。如“蒲人”(亦称“蒲蛮”),“在永昌西南徼外,又在顺宁沿澜沧江居者号蒲蛮,亦曰朴子蛮。性尤悍恶,专为盗贼,不鞍而骑,跣足短甲,不蔽膝胫,驰突疾迅,善枪弩”。(5)康熙《云南通志》卷27《土司三十三·种人》,凤凰出版社编纂:《中国地方志集成·省志辑·云南》第二册,南京:凤凰出版社,2009年,第101-102页。“黑猡猡”,“居深山,虽高冈硗陇,亦刀耕之,种甜苦二荞自赡,善畜马、牧养蕃息。器皿用竹筐木盘,交易称贷无书契,刻木析之,各执其半,市以丑戍日。葬贵者裹以皋比,贱者以羊皮,焚诸野而弃其灰”。(6)朱占科修,周宗络纂:光绪《顺宁府志》卷34《杂著》,台北:成文出版社,1975年,第1070页。“僰夷”,亦称作“摆夷”,“顺宁城外村寨皆有之,居处皆与客籍同,惟语言各异。贸迁货居者少,耕织工作者十六七焉。男女妆服近多汉制,婚姻以礼,丧葬以助。俱公法,尚鬼神,量无补欠”。(7)朱占科修,宗宗络纂:光绪《顺宁府志》卷34《杂著》,台北:成文出版社,1975年,第1080页“倮黑,系属化外,性情顽劣,不事耕作,以捕猎为生,男女皆短衣裤裙,遇有仇隙,以勇悍为能。”(8)刘慰三撰:《滇南志略》,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十三卷,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05页。除此之外,清代顺宁府还居住着白人、利米、蒙化夷等族群。
在汉族移民大规模进入滇西南之前,这些广泛分布在顺宁府境内的土著人群一直保持着族群原有的社会组织、生计方式和文化习俗,族群之间维持着相对稳定的互动关系。其中,“摆夷”族群主要生活在海拔和纬度都较低的平坝或者河谷地区,而“蒲人”“猡猡”“倮黑”等族群则大多生活在海拔相对较高的山区。各族群在山区和坝区之间受到地理生态等因素的影响,形成了若干以坝区(低地)为中心,与山区(高地)既联系又分割的地域结构及差异明显的经济文化类型:一是以平坝为主的农耕经济文化类型,二是以山地为主的“刀耕火种”、采集狩猎等多元经济文化类型。这种不同的经济文化类型和族群的分布格局,“主要是各民族根据各自在原生态环境中长期形成的生理特性、生活方式及文化要求,对于客观存在的垂直变异生境进行选择的结果”(9)尹绍亭:《文化生态与物质文化(论文篇)》,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35页。,学术界通常将其称之为“山坝结构”。
滇西南当地著名的“坝子”主要分布在耿马、木邦、景栋、孟连等地。这些坝子普遍具有地势低缓、水利条件较好、土壤肥沃、交通便利等特点,而拥有稻作农业传统的“摆夷”先民,很早就分布在滇西南地区大部分的坝子当中,发展出了以农耕和手工业生产为主的生计类型,并在坝区形成了人口较为集中的村落、城镇以及阶序化的政治结构。自元代以来,被历朝任命的摆夷土司的政治、宗教中心就设在各地坝子的城镇之中,并以之为核心辐射周边村寨和山地族群,形成了以“勐”(即坝区)和“圈”(即山区、半山区)构成的地域性层级体系——如孟连土司设“三勐五圈”,耿马土司设“九勐十三圈”等。在该区域内各土司之间相互通婚,并沿山脉、河流划分辖地范围,维系着较为稳定的地方政治格局。
自元代开始,中央王朝就在滇西南设顺宁府以强化对这一地区的管控,但始终无法将其纳入帝国的有效管辖之内,长期以来实行的是地方羁縻以治夷地的治理模式,如顺宁县、缅宁等地在元朝依然是任命地方土知府进行地方事务的管理。
到明朝时,改元朝地方建制,“省州县人府,改大侯长官司为大侯州,万历二十四年(1597年),土知府猛廷瑞叛,讨平后,设流官知府,改大侯为云州,属府”。(10)王崧撰:《道光云南志钞》卷1《地理志·顺宁府》,杜允中注,刘景毛点校,昆明: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文献研究所,1995年,第33页。万历二十五年(1598年),顺宁土府改流,将原来处于土司管辖之下的顺宁府内边地区改为流官治理,保留耿马等地土司。甚至到清初雍正大规模“改土归流”后,顺宁府还保留着耿马宣抚司、孟连宣抚司、孟定土府、镇康土州等土司、土官。
这表明,在滇西南特殊的地理环境与政治生态的制约和影响下,中央王朝不得不对澜沧江以西的土司势力做出某种政治妥协,只能采取“土流并置”的统治策略,即流官直接控制其边界以内的地区,将那些瘴疠横生的地方让给当地土司去管辖,从而“形成了长期限制行省管理空间的界限”,这对清王朝的边疆控制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11)戴维·A.贝洛:《去汉人不能久呆的地方:瘴疠与清代云南边疆地区的民族管理空间结构》,杨煜达译,陆韧主编:《现代西方学术视野中的中国西南边疆史》,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18页。
总体上来说,在近代之前,云南因地理生态方面的原因,一直被中央王朝视为“蛮荒”“边夷”之地,而地处边陲的滇西南,更是长期游离于王朝政治体系之外。清代早期,滇西南虽然在形式上纳入了中央王朝的统治,但国家与地方社会之间的矛盾、对立关系依然存在,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与该区域的政治生态变迁、地方权力博弈、族群冲突、社会动乱等交织在一起。实际上,在王朝统治伸缩的历史构图中,开发治理与社会变乱,一直是贯穿于清前期滇西南地域社会变迁的两条重要线索。二者之间矛盾冲突与调和妥协的交织更替,始终影响着国家权力在滇西南边疆地区的实际运行,生动地展现出“边疆内地化”过程中政治生态环境的变化,以及国家与地方社会之间复杂互动的历史图景。
二、对抗与妥协:地缘政治生态变迁和滇西南土司的政治归属
滇西南土司对王朝政治认同的过程,经历了一段非常复杂且充满了对抗性的历史。早在清军入滇之初,清廷已经意识到西南边疆路途险远,人群混杂,特别是土司势力强大难治。而此时永昌、顺宁等地是南明势力的最后根据地,承担着南明复归正统的最后希望,当时的大西军将领李定国等人除了利用南甸、干崖、陇川等地土司力量抵抗清军外,还曾一度联合顺宁、元江土司加入到这场斗争之中。如顺治十五年(1659年),元江土知府那嵩、那焘父子主盟,联合各土司反叛,引发“地方震动”。据《元江志稿》记载:“永历帝奔西,嵩与其子迎谒于楚雄,既而李定国传檄号召诸土司,兵户尚书龚彝说嵩与元江,起兵应之。”(12)黄元直修,刘达式纂:《元江志稿》卷12《武备志》,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年,第147-148页。这一时期以滇西南土司为首开展反清活动,成为吴三桂肃清南明势力、控制云南的主要阻碍,可谓“土司反覆,惟利是趋,一被煽获,遍地蜂起,其患在肘腋”。(13)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卷474《吴三桂传》,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12839页。面对边疆地方势力的离心力,清廷亟需通过笼络土司头人来实现其对西南边陲的有效控制。因此吴三桂南征时曾发布告谕:“其中有效力建功者,不靳高爵厚禄,以示鼓励。”(14)《清世祖实录》卷127,顺治十五年(1658年)十二月己丑条。不过,这种招抚措施的成效并不明显,难以从根本上解决土司为患的问题。到雍正时期,澜沧江内外之车里、茶山、耿马、孟定以及缅甸、老挝等地土司,仍旧“争相雄长,以强凌弱”,以致“凶夷肆恶,渐及内地”。(15)《云贵总督鄂尔泰为窝泥既靖,规画宜周、敬陈管见奏事》,雍正六年(1728年)正月初八日,《朱批谕旨》鄂尔泰折五。在这种形势下,如何保证清王朝在西南边疆地区的有效统治,成为了康、雍时期面临的难题——特别是土司纵恣不法带来的社会动乱,以及与朝廷争夺土地、矿藏资源、阻挠驿路开通以及外来移民进入等问题。
面对西南边疆错综复杂的局面,清廷寄希望于通过明确的职能分立来确认土司与流官的势力范围,以便使改流能以较为平和的方式进行。雍正四年(1726年),鄂尔泰上疏建议:“流官固宜重其职守,土司尤宜严其处分。”(16)《清世宗实录》卷51,雍正四年(1726年)十二月戊寅条。但事与愿违,改流之举从一开始就遭到各地土司的强烈抵制,尤其是以江外(澜沧江以西)土司为甚。如当时孟连刀氏土司就曾与官府发生激烈冲突,“官兵各持斧锹开路,焚栅湮沟,连破险隘,直抵孟养,据蛮坡通饷道;其六茶山巢穴四十余寨,乃用降夷向导,……深入数千里,无险不搜”。(17)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卷514《土司传三》,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14257页。最后的结局是以刀氏土司被俘虏削首而告终。
此外,由于改土归流波及面广泛,在顺宁府周边地区乃至东部哀牢山区的不同群体都加入到与官府的对抗中来。特别是当地的传统势力——摆夷土司,因改土归流利益受损,所以常常在动乱中充当着重要角色。如“镇沅自雍正四年改土归流,参革土官刀翰。族舍刀西明等纠合倮黑共千余,放火劫杀。又,余老二供:同伙夷人五百窝泥、四百倮黑、三百大头倮摆、二百摆夷。领头是土官兄弟刀应才、圈罗周倮罗、黄庄长把司。是年,威远倮夷黑老胖等,接连镇沅余贼肆掠乡村,焚烧盐仓”。(18)郑绍谦撰:道光《普洱府志》卷13《兵志》,道光二十年(1840年)刊本,第18页。最后清军动用重兵才把这次叛乱镇压下去。到雍正六年(1728年),经过大规模改流,清初云南境内存留的二百余个大小土司,此时仅剩22家。(19)龚荫:《中国土司制度》,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2年,第113-114页。而这二十余家土司基本上分布在澜沧江以西的顺宁、永昌等地区。其中,顺宁府“直隶耿马宣抚司,……仍授宣抚司,承袭”。“孟连宣抚司,……定为经制宣抚司,颁给印信号纸。”“猛猛土巡检,……仍授世职,颁给铃记”。(20)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卷514《土司传三》,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14266页。这些地方因地处偏远,又临近中缅边境地带,因此,保留了原本土司的地方管辖权,到乾隆年间这些土司皆“隶属于顺宁府”。⑧
学术界通常认为,清廷在滇西南地区改土归流,虽然没有完全放弃其“以夷治夷”的策略,但从结果上来看,改土归流还是有效地维持了中央王朝在边疆地区的“政治合法性”及其治理成果。实际上,清前期国家力量尚无法有效地管控滇西南地方社会,土司与中央王朝之间长期以来主要是通过朝贡关系维系着双方的政治联系和认同关系,加之滇西南地区地处滇缅边境,历史上境内土司与缅甸王朝及境外土司一直有着密切的联系。这种特殊的地缘环境和政治生态,一定程度上成为清初滇西南土司政治上“摇摆”乃至动乱的重要因素。
首先,滇西南大部分土司虽然在清前期已经完成“改流”,但他们依然要向清廷纳贡。相较于元明时期,清代的土司贡奉制度有了较大的改变,“清嗣后境外进献方物一概停止,以免地方解送之劳”。(21)《清世祖实录》卷3,顺治十八年(1661年)六月戊戌条。也就是说,地方土司照例纳贡,但由地方督抚或者流官解纳,这就导致边地土司原本可以直达中央的主要政治联系和沟通方式被阻断,同时也让边地土司无法获取来自中央的认可和赏赐。“如此一来,在西南边疆自土司制度建立以来就一直延续下来的土司与中央之间的‘贡赐’彻底打破。终清一朝,西南边地土司之间的关系变成了土司与土司、土司与流官之间的互动关系。”(22)成臻铭:《土司制度与西南边疆治理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606页。这就极易出现地方督抚和流官压榨边地土司的情况,甚至引起“(土司)往往争为雄长,互相仇杀,一不禁而吞并不已,叛乱随之”(23)蔡毓荣:《筹滇十疏·筹滇第二疏·制土人》,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八卷,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426页。的局面。因此,清王朝一方面实施边疆地区的改流,以防止地方土司的动乱,但另一方面却仍然要倚仗土司势力稳定其在西南边疆的统治。所以在中央与地方的互动中,朝贡成为土司在政治上获得中央认可的重要标志。但与此同时,朝贡问题上出现的争端,也时常对滇西南地区的统治带来较大的冲击。
其次,滇西南与缅甸地域相连,区域间族群、社会、经济、宗教文化等方面长期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使得沿边土司所处的政治生态环境十分特殊,缅方对滇西南边地的侵扰,常常会引发边地土司内部及周边地带的社会动荡。清初缅甸雍籍牙王朝势力崛起后,缅甸多以武力擅闯滇西南边地以索要贡赋,而边地土司为了减少境外侵扰,不得已向缅方送交大量钱财和部分马匹——即“花马礼”作为自保手段。“花马礼”虽然随着缅甸王朝势力的变化而经常发生变动,但它的存在使清王朝“守内御外”的边疆秩序受到挑战,所谓“云南附近普洱之十三土司,久已输诚内向,编列版图。近日莽匪滋扰各土司。边境夷民,鲜得宁居”。(24)《清高宗实录》卷758,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四月丁未条。不仅如此,缅甸方面除了索要财物,甚至还对边地土司进行封敕任命,如曾对孟连土司封以“缅甸宣慰司”以示对滇省土司的统属,造成滇西南部分土司在政治上一度“摆动”到缅方。当然,这种情形只是暂时性的,因为滇西南边境地带发生的土司动乱,很多时候是在缅甸势力崛起的背景下出现的。加之清前期中央王朝对西南边疆控制不力,导致边地土司无法有效应对域外势力的进入,为了获得稳定的生存环境和发展空间,只好以“两属”的方式以求自保。但是,这种双重政治归附和倚靠,有时会导致一部分土司在清朝和缅甸之间来回“摆动”、叛服无常,给滇西南边疆社会的稳定带来极大的隐患。直到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清缅战事平息之后,随着清缅藩属体系的确立和滇西南传统边界的形成,这一问题才得到初步的解决,边地土司的角色也从政治上摇摆不定的“观望者”,逐步转变成中央王朝在西南边疆的“代理人”。
三、民夷的“区分”与“混杂”:边疆治理过程中的族群矛盾和冲突
在清代的文化语境之中,“民”一般是指与“夷”(土著人群)相对的“汉人”群体。清初以来,随着内地移民不断进入云南,不论是滇中腹地还是边远山区已不再是单一的族群构成,内地各省移民从交通沿线及滇东南坝区,向滇南、滇西南汉人较少的区域——如顺宁府、普洱府一带扩散。移民的大量内迁,形成了疆域空间内“汉夷混居”的动态分布格局。这也使得地方官员在施治过程中,不得不根据当地社会形势的变化,而采取相应的政治策略和治理手段。
早在清初,康、雍、乾历代帝王就曾提出过破除“华夷有别”欲行“天下一家”的安边设想,但是在历史传统的惯性作用下,“华夏中心观”仍然在边疆地区的政治实践中占据主导地位。雍正年间,鄂尔泰推行改土归流时称西南地区土司“恃有土官土目之名,行其相杀相劫之计,汉民被其摧残,夷人受其荼毒”。(25)魏源纂:《魏源全集》第17册,长沙:岳麓书社,2004年,第696页。对此,雍正皇帝在回应边地改流的诏令中称:“云南等省所有苗、蛮、僮种类甚多,残忍成性,逞凶嗜杀,剽掠行旅,贼害良民,而众苗繁多……朕念普天率土之民皆赤子……朕亦不忍听其在德化之外。”(26)《清世宗实录》卷75,雍正六年(1728年)十一月乙亥条。故而实行针对边地“夷人”的改流之策。清代学者吴大勋指出:“滇本夷地,并无汉人。历代以来,征伐戍守、迁徙贸易之人,或不得已而居此,或以为乐土而安之,降至近世,官裔幕客流落兹土,遂成家室……永为客户。”(27)吴大勋:《滇南闻见录》,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十二卷,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7页。这里的“客户”指的就是在滇定居的外地民众。“客户”与土著夷人之间的界限,不仅仅是文化上的区分,更多地表现为一种社会身份和心理认同。
清前期滇西南社会的“区分民夷”的措施,直接反映在户籍管理制度当中。按照规定,“民”与“夷人”在户籍登记中,分别是以“计户”和“计口”的方式进行的。到乾隆后期,在滇西南各府、州、县中还存在着大量尚未纳入中央王朝的户籍管理和统计之中的“夷户”,这些人口大部分隶属于原来所在地区的土司。改土归流之后,这些“夷户”就需要承担朝廷的派贡与赋役。这就意味着,分布在滇西南地区特别是“江外”的土著夷众,在面临着向土司供役的同时,还需向中央王朝缴纳赋税,这无疑增加了“夷户”的经济负担。
“民”“夷”二元化的族群分类及政策实施,不仅使边疆社会的治理有了明显的“汉”与“非汉”、“民”与“夷”的双重对立色彩,而且随着汉人移民人口数量的持续增加,也不断挤占着土著人群的生存资源,进一步加剧了夷汉族群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云南巡抚刘藻曾指出:“滇省夷倮散处,种类甚繁;性似诈而实愚,习虽悍而近葸;畏法敬官,极为恭顺。惟间有劣矜地棍与江广游民,每于夷寨中放债盘剥,遇事讹诈;虽历经严饬,此风尚未革尽;必使汉人不敢逞其欺凌,则夷人常得安其耕凿。”(28)《清高宗实录》卷553,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十一月丁亥条。此后,云南巡抚郭一裕上奏时亦称:“滇省夷多汉少,汉人狡黠者每欺之。现饬吏访查,尽法痛处。”(29)《清高宗实录》卷499,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五月戊戌条。但清廷只是在法律上规定:“凡内地民人不准私往夷地贸易,侵夺夷人生计,若有私越边境者查明严禁治罪。”(30)《清仁宗实录》卷329,嘉庆二十二年(1757年)三月丁丑条。然而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这类禁令往往形同虚设,难以实施。随着内地人口的大量涌入,“民”“夷”之间的矛盾逐渐渗透到更为边远的山区。
在“汉进夷退”的过程中,土著人群既有的地方资源和经济利益,进一步被官府和移民挤占和控制,滇西南区域内部原有的社会结构和交换、交往关系被彻底打破,土著民众的抗争活动也逐步升级。早在明清之际,哀牢山区就发生过“倮夷”反抗官府的事件,史载:“罗婺罗应奎、李大等,因时遭兵焚,赋役繁重,民多怨者,乃挟各种倮夷为乱,肆行劫掠。”(31)徐树闳:雍正《景东府志》,云南省图书馆抄本。雍正六年(1728年),镇沅新任知府刘洪度虐待夷民、索要供应、摊派费用,摆夷刀如珍不愿交出土地,联合倮黑头人老胖等聚众反抗。(32)师范纂修:嘉庆《滇系》,台北:成文出版社(影印本),1968年,第150页。同年,“茶山莽芝夷人麻布朋等为变,总督鄂尔泰遣副将张应宗、参将邱名扬率兵讨之”。(33)倪蜕辑:《滇云历年传》卷12,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十一卷,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99页。
乾隆末年到嘉庆初年,包括顺宁等地也相继爆发土著族群动乱。《清仁宗实录》载:“嘉庆元年(1796年)丙辰,冬十月……谕军机大臣等。勒保奏:途次面询威远办事道府,称牛肩山倮匪因前次兵练进攻,未及围困兜捕,复窜往西大黑山,该处山深箐密,人迹罕到,并恐窜出缅宁景东边界及南越猛迺等处,纠煽生事,更难着手。唯有赶蒞威远,设法筹办等语……设各村人数较少,即于山外各要隘提防酌派兵防守,则倮匪等见有防备,自行不敢复行出山滋事。”(34)《清仁宗实录》卷10,嘉庆元年(1796年)十月乙酉条。这些动乱的起因,大多由于地方官员垄断盐、茶贸易及捐税繁重所引起的。如嘉庆二年(1797年)滇西南产盐区发生的“倮黑滋事”聚众反抗事件,“皆由盐斤堕销,地方官按户派买,借债徼课”所致。(35)《清仁宗实录》卷58,嘉庆五年(1800年)正月癸未条。到嘉庆八年(1803年),威远地区的夷人再度起事,由于人数众多,当地官府无力应付,不得已只能让附近村寨自行应对。当时“威远所属倮黑窥伺,查系邦奈之带脚倮,约有千余人,偷渡猛撒江,……又猛撒江边六困土司地方,亦有倮匪在普洱河对岸窥探。该倮匪等虽不过在边境掠食,但猛撒江与六困既有小路可通,恐两处倮黑纠结合夥,自应齐集练勇,两路夹击,驱逐出境”。(36)《清仁宗实录》卷118,嘉庆八年(1803年)八月乙丑条。这里所谓“驱逐出境”,是指将那些反抗官府的“倮匪”驱赶到澜沧江西岸的顺宁府界,不让他们再进入已改流的地区。而这些大量被驱逐到“江外”的人口形成的无序流动,又进一步引发了当地族群间的矛盾、冲突,加剧了顺宁山区社会的动荡。
由此可见,清前期滇西南地区出现的大范围社会变乱,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边疆内地化”进程中地方社会结构变化的一个重要表现。在汉族移民大规模进入之前,滇西南自然环境的相对封闭性使区域内部的土著族群形成了较为稳定的族群关系,同时“山坝结构”下经济、文化方面的互补性,又大大强化了族际之间的交往互动,而且这种交往互动更多的是基于族群自身的内在需求所形成的。但改土归流后随着汉族移民大量涌入,汉夷之间在资源的争夺和重新分配中形成的联系更加密切,就像在官方文献中被称作“倮夷”“倮匪”的人群,其成分实际上是非常复杂的,其中既有摆夷、倮黑、窝泥等土著人群,也有不同时期垦殖或逃亡的汉族移民卷入进来(37)马健雄:《再造祖先:西南边疆的族群动员与拉祜族的历史建构》,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54页。,形成了一定范围内“人群混杂”的局面,从而大大改变了滇西南地区政治生态和族群关系的原有面貌。
四、“矿利衰竭”与边疆秩序:乾嘉时期滇西南山区的社会治乱
清初以来,为满足庞大的军费开支和扭转“银贵钱贱”的局面,开始大规模开采地方银矿。根据《云南通志稿》和《清文献通考》等文献的记载,从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到嘉庆十五年(1810年)云南开采形成规模的银矿就有20余处。(38)转引自张增祺:《云南冶金史》,昆明:云南美术出版社,2000年,第22页。其中顺宁府是清代云南重要的银矿产地,以耿马的兴隆厂、悉宜银矿,顺宁边境的茂隆银厂等最为知名,吸引着来自湖北、湖南、江西等地的大量汉族移民进入山区采矿谋生。云贵总督张允随在奏折中称:顺宁多系汉人前往开采,“皆实力谋生,安静无事”,而“夷人亦享其利”(39)《张允随奏稿》,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八卷,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683页。,以致顺宁山区“商贾云集”,贩夫走卒皆以内地货物往来其间,边省矿工砂丁“不下十万人”。乾隆年间,仅悉宜矿工就不下数万人。由于“夷人不谙架罩煎练”,所以“其打槽开矿者,多系汉人,凡外域有一旺盛之厂,立即闻风云集”。(40)《张允随奏稿》,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八卷,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683页。外来移民的大量聚集,使偏远的顺宁山区一度出现了繁盛的景象。
滇西南地区银矿的开办,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边疆社会的开发,打破了相对封闭隔绝的状态。由于规模化生产的需要,矿区往往和周边山区及坝区村寨形成一定的合作关系,以满足粮食、食盐、薪碳等物资的持续供应。因此大量的商人、脚夫贩运货物进入矿区边地进行售卖,使原本“烟瘴”之地的顺宁地区成为“商贾云集”和“比屋列肆”之地。而当地土著夷众“唯能烧炭及种植菜蔬,豢养牲畜,乐与厂民交易”。(41)《张允随奏稿》,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八卷,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683页。银矿的开采和人口的流动,使族群的交往开始突破文化和地缘的限制,乃至于人群混杂,“难以区分汉夷”。但与此同时,不同人群的聚集也造成了边疆地区的治安隐患和其他社会问题。这主要是因为,“清乾隆中期滇西南边地银矿的开发在一定程度上是为当时的律令所不容的,虽然边地许多银厂都得到地方土司甚至是中央王朝的默认,但是银厂的开发使大量的移民进入边境对王朝边疆治理和管控造成冲击”。(42)杨煜达:《清代中期滇边银矿的矿民集团与边疆秩序——以茂隆银厂吴尚贤为中心》,《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8年第4期。特别是矿主还和境外土司有着密切的联系,如悉宜银厂“与顺宁、云州相距道远,耿马虽系内地,土司究属夷境,若派员前往管理,既恐呼应不足,亦难保其不借端滋扰”。(43)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编:《清代的矿业(下)》,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588页。
上述问题在银矿开采初期尚不明显,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矿厂管理不善、物流不畅、开采无序、资源枯竭、生产成本增加等问题开始暴露出来。加之地方官府对矿厂进行层层盘剥,导致众多矿主无利可图,难以维持。到乾隆、嘉庆年间,顺宁府的悉宜、涌金以及茂隆等大型银厂开始衰败并逐一关闭,原来一度繁荣的矿区也由此日渐没落。嘉庆五年(1800年)富纲上奏称:“近边之茂隆银场,近年矿砂衰息。”(44)《富纲奏折》,嘉庆五年(1800年)正月初四,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军机处附,1795-民族类。嘉庆十七年(1812年)云贵总督伯麟等奏报:“顺宁府属耿马土司经营之悉宜一厂,据报矿砂衰竭,恳请封闭,是否属实,尚须确查另办。”(45)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编:《清代的矿业(下)》,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507页。最后据顺宁地方委员查验后确认“从前所开曹硐俱已衰竭,无人挖采,久成废弃”。(46)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编:《清代的矿业(下)》,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507页。而地处顺宁边外的茂隆银厂也在嘉庆年间没落。
在这个过程中,受冲击最大的莫过于康、雍年间涌入滇西南数量庞大的矿民。由于矿利衰竭造成矿民的流散,使地方社会秩序受得了较大的冲击。这些由内地入滇的矿民,一方面是一个极具流动性的群体,他们为利而来,厂兴则聚,厂衰则散;另一方面他们又由各行各业聚集起来,形成了具有一定组织性的矿民集团,而“这类矿民集团和普通的零散移民并不一样,他们聚集在一起,有相当的规模,有雄厚的财力和武装。在边疆地区,他们不仅和周边的内地土司和山地民族有经济、文化的紧密交流,甚至也和外属土司乃至外国朝廷产生紧密的联系”。(47)杨煜达:《清代中期滇边银矿的矿民集团与边疆秩序——以茂隆银厂吴尚贤为中心》,《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8年第4期。如果一旦发生社会变乱,就能在短时间内形成地方效应。
鉴于滇西南矿民问题的严重性,从中央王朝到云南地方都在严防因矿民流散而导致地方生乱。但当时情形却是“其人既众,其类不一,各结为党,名曰拜把,歃血订盟,谓之烧香弟兄逞强恃勇,不避死亡”。(48)王崧撰:《道光云南志钞》卷二《矿产志·采炼》,杜允中注,刘景毛点校,昆明: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文献研究所,1995年,第123页。加之顺宁地区“山箐丛密本易藏奸,加以铜、银各厂砂丁类,借犷悍之徒,近因厂情疲滞,更易流为盗贼”。(49)中山大学中国近现代史教研组、研究室编:《林则徐奏稿(上、中、下)》,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149页。地方官府、土司对其管控的能力十分有限。因而众多矿民流落山间,以抢劫商旅为生,有的甚至组成匪伙,成为地方动乱的重要力量。与此同时,随着内地移民的进入,一些新兴民间宗教也在当地快速流播开来,与秘密社会组织结合在矿工中迅速发展,进而扩展到矿山周围的土著社会,并最终卷入了与勐勐、孟连等土司的对抗当中。(50)马健雄:《“佛王”与皇帝:清初以来滇缅边疆银矿的兴衰与山区社会的族群动员》,《社会》2018年第4期。
这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以铜金和尚(张辅国)为首的地方动乱,而铜金和尚在顺宁山区的崛起,也正是得益于他在山区土著人群及移民矿工中的宗教(“大乘教”)传播和政治动员。嘉庆初年,铜金和尚及其弟子利用“大乘教”的影响将这些矿民组织起来,在不断争夺边地矿利的同时,还将边地的食盐、粮食等重要物资进行走私贩卖。可见,铜金和尚的“传教网络与贸易网络属于同一个社会体系,成为一个当地土司无法控制的宗教、经济与政治相重叠的系统”。(51)马健雄:《“佛王”与皇帝:清初以来滇缅边疆银矿的兴衰与山区社会的族群动员》,《社会》2018年第4期。而这个政教合一的社会组织,事实上成为了这一时期边疆地区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此后不久,铜金和尚便率众“从李文明作乱,文明败,铜金来降。总督书麟令仍居南兴,约束三勐五圈倮黑,铜金还俗更名张辅国”。(52)朱占科修,周宗络纂:光绪《顺宁府志》卷17《武备志》,台北:成文出版社,1975年,第510页。但此时的张辅国仍然是“大乘教”这一政教体系的领袖。“(嘉庆)八年,巡抚永保给予土目戳,记录孟连土司,辅国以土司削弱,遂侵掠南甸、耿马、猛猛三土司地。十七年,总督伯麟派兵攻破南兴。辅国遁三猛五圈,纠大山黄猡于莽帕抗拒,耿马土司等率土练攻破莽帕擒辅国,磔于市。”(53)朱占科修,周宗络纂:光绪《顺宁府志》卷17《武备志》,台北:成文出版社,1975年,第510页。至此,因为争夺地方政治、经济利益而引发的动乱得以平定。
总之,矿业的开采作为滇西南地方经济的主要来源,所牵涉的是地方政府、土司、矿主和相关民众的整体利益。而随着矿利的衰败,改变了原来顺宁地方社会因矿产开发聚集起来的行业和族群之间的关系格局,并将积压已久的地方矛盾激发出来,从而为铜金和尚等人的社会组织、动员活动提供了较大的空间。另外,从滇西南边疆形势来看,在地方变乱发生之初,顺宁地方官府同时要面对境内外政治势力的双重挑战,无力控制局势的走向,致使这一事件愈演愈烈,打破了山区社会数十年间形成的短暂的平衡局面。直到嘉庆年间,随着事态的平息,顺宁山区的社会秩序才重新趋于稳定。
五、方略与施治:清王朝的治边措施与滇西南社会整合
滇西南的地缘结构和政治生态,决定了这一地区族群社会与国家权力之间的特殊关系,因此在清前期的边疆治理过程中,不论是改土归流还是移民迁入,都因涉及土地、资源争夺和政治利益纠葛而一度遭到土司及当地人的抵制,反映出清王朝以内地政治模式再造边疆社会秩序过程中所引起的社会阵痛。所以,这一时期顺宁府及其周边地区出现的族群冲突、缅酋犯境、矿利之争、宗教动员、边民流散等事件,都对滇西南边疆秩序造成了重大影响,迫使清廷采取一系列措施,来应对不同时期社会动荡对边疆统治带来的重大挑战。
第一,军事征剿。清军进入云南之初,“先革土司,后剿蛮夷”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为滇西南边疆治理的主要目标。改土归流之后,较大规模的土司动乱逐渐减少,但随之而来的汉夷、官夷之间的矛盾冲突,迫使清政府不得不诉诸武力加以解决。尤其是由于内地官员对夷人的歧视根深蒂固,所以多借“改流”对夷人进行武力镇压以稳定边疆局势,同时也借此为自己积累政治资本和谋取经济利益。(54)马健雄:《再造祖先:西南边疆的族群动员与拉祜族的历史建构》,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46页。
顺宁府“地居荒远,外逼强邻,内境辽阔”,是“安边固园,禁暴戢奸”之重地。(55)朱占科修,周宗络纂:光绪《顺宁府志》卷17《武备志》,台北:成文出版社,1975年,第474页。但由于地多瘴疠、交通不便,清初在当地常驻的军事力量十分有限,常备兵力的规模一直都很小。乾隆十六年(1752年),总督硕色称边地厂矿“周六百余里,距内地十五站。……即无官兵塘汛,止委一、二文员,原难总理弹压”。(56)《清高宗实录》卷394,乾隆十六年(1751年)七月辛未条。虽然在乾隆时期清缅边境冲突后,清王朝加强了在顺宁及周边地区的军事防卫力量,但平时主要用来应对山区夷众的反抗。嘉庆初年,威远、顺宁等地爆发了倮黑针对地方官吏压迫的大规模动乱,在官兵征剿的同时,还组织村寨结伙自保或让土官、土目组织练勇抵御“匪患”的侵袭。如“嘉庆元年,倮匪杨扎那滋事,聚众于牛肩山”,孟班土把总周靖“奉调带练协同官兵征剿,贼众逃散。该匪复窜入土地塘焚掠,靖又带练进剿阵亡。周靖子周朝经,以父死于倮匪,日夜思复仇。……督练二百五十名,示以忠义,往剿倮匪人人争先”。(57)夏鼎,等撰:道光《威远厅志·秩官》,道光十八年(1838年)刊本。从文献记载来看,嘉庆年间官府的军事征剿行动,一开始主要集中在澜沧江东岸的威远、镇沅等地,经过一系列军事征剿后,官军把威远山区的反抗群体驱赶到澜沧江以西顺宁府境内的猛缅(今临沧)、猛猛(今双江)、大山(今澜沧)一带。(58)马健雄:《再造祖先:西南边疆的族群动员与拉祜族的历史建构》,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46页。而这里正是孟连土司、勐勐土司的传统领地,也是王朝管控相对薄弱的边缘地带,一直被视为“野倮”的活动地域。由于大量流民的聚集,不久之后,该地区就发生了以倮黑和失业矿工为主的反抗孟连土司和勐勐土司社会动乱,其领导者就是前文中提到的李文明和铜金和尚。
由此可见,军事征剿一直是清王朝维系滇西南统治的重要手段,由于这一区域人群混杂且政治生态复杂,大大小小的地方性动乱持续不断,而与之对应的军事征剿行动也不绝如缕,直到民国初年,随着土司势力的衰微和对中缅边境管控的强化,滇西南长久以来形成的族群政治经济冲突与军事对抗的局面才得到彻底改变。
第二,汛、塘的设立。汛、塘为清代绿营兵管辖地方的最基层的军事单位。其中,“汛”大都分布在险要的边关和厅府交界处,多以把总或者千总统领百余名兵丁驻守,而“塘”则分布在距离城池或重要行政区较近的郊县地区,所设兵丁较“汛”要少,以三五名兵丁为主。方国瑜曾指出:“清代绿营兵制,设镇、协、营于各处驻守,有事调遣,事毕返防,弹压人民。布置军事网,设汛、塘、关哨,委千总、把总领兵驻守,遍于州县境内。”(59)方国瑜:《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下)》,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1229页。在滇西南等较为偏远地区,“大都明时不设卫所,清初改土设流,人口稀疏,山区荒芜,则多设汛分置塘、哨、关、卡”。(60)方国瑜:《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下)》,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1229页。分布于各州县的塘、哨多以地方乡勇为主,其承担的主要任务就是“弹压人民”,防止地方民众动乱恣事。
汛塘制度将清王朝的军事力量延伸至滇西南的边远山区。如顺宁府自改土归流后广设汛、塘、关哨,其中“把边山中有把边关,……为一郡扼吭之地,最为险要”。(61)朱占科修、周宗络等纂:光绪《顺宁府志》卷9《建制志》,台北:成文出版社,1975年,第240页。山关隘口为顺宁边地防守的要地,这些地方多以汛、塘兵丁驻守。又如顺宁县有右甸汛,“设把总一员,兵四十三名”。万年椿汛,“分防把总一员,额外外委一员,步守兵六十名”。“金城见塘、菁中塘、菁口塘、崑南岩塘,……在城东各设步兵三名,归存城官管辖。”此外还有猛右塘、大小桥塘,“各设兵三员”。(62)朱占科修、周宗络等纂:光绪《顺宁府志》卷9《建制志》,台北:成文出版社,1975年,第241-244页。清前期增强顺宁府的绿营驻防和地方汛、塘分布是清代安定边疆、“禁暴戢奸”的必然,因为顺宁府辖地不仅地处极边,其所辖耿马、缅宁等地更是紧邻外境,辖境广阔,地方兵防往往难以应付。在雍正之前,顺宁府仅设顺云营,驻地顺宁县。雍正边地“改流”和乾隆年间清缅关系恶化逐渐让清廷意识到边地军事成为边境要事和顺宁边地绿营不足的现状。因而在嘉庆五年(1800年),“将顺云参将由顺宁移驻缅宁,并于次年在顺云营增兵400名”。(63)秦树才:《清代云南绿营兵研究:以汛塘为中心》,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78页。到道光初年,顺宁府的绿营驻兵最高时达到1796名。同时,在顺宁、永昌以及普洱地区大量设置哨、所,并向边境地方推移,在永昌府的龙川江、猛连、缅箐,顺宁府的把边、等腊、猛托等边境地区也大量分布着哨、汛,以防止境外势力侵入边地,袭扰地方民众。
汛、塘及哨所的设立,使中央王朝对滇西南土司的控制更加牢固,特别是对于尚未改流“世守其土”的远边土司更是如此。它不仅大大降低了土司反叛中央的危险,同时对地方动乱可以起到一定的预防和遏制作用。更为重要的是,汛、塘作为王朝军事最主要的力量存在,显示了清廷在西南边疆拥有的绝对统治权力以及对疆域领土的控制能力。
第三,户籍稽查。清初中央王朝力量在向西南边陲延伸的过程中,内地移民也陆续进入滇西南一带,导致移民人口数量的激增,以至于走夫贩卒“尽皆湖广、江右之人”。与此同时,大量所谓的“黑户”也随之涌入。在这类人群中,充斥着罪犯、商人、流民等,这些未在册的人群使滇西南的人口成分变得更加复杂。外来人口的增加使地方资源的竞争也日益激烈,从而引发族群之间连绵不断的矛盾与冲突,使得滇西南社会秩序一度处于十分混乱的状态,而人口的大量流动也让清廷对边疆地区的治理力不从心。
不仅如此,这一时期滇西南山区因矿利之争引发的流民问题也不断凸显,所谓“厂民逐货贸易,户籍难定。”(64)《张允随奏稿》,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八卷,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642页。在顺宁矿区,“厂之大者,其人以万计,小者亦以千计,五方杂处,匿匪藏奸,植党分朋,互为恩怨,或恣为忿争,或肆为盗贼,所为弹压约束之方,又岂易哉”。(65)阮元等修,王崧等纂:道光《云南通志》卷74《食货志·矿厂二》,云南省图书馆馆藏本,第26页。因此,边地的稽查和户籍的管控在雍正、乾隆年间对边地稳定起着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清缅战争期间,边地各隘口严禁民众私自外出,对边地矿民和外来民众严加排查,从而降低流民越关通敌的风险。
乾隆、嘉庆年间,地方政府一直通过户籍管控来减少外来移民进入顺宁地界,以减少边地生乱的机率。并且“严防沿边各州、县,凡内地民人,不准私往夷地贸易,侵夺夷人生计。若有私越边境者,查明严禁治罪,务令弭患未形,勿在滋事边境为要”。(66)《清仁宗实录》卷329,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四月辛卯条。除此之外,还采取强化地方保甲的举措,让地方民众“三户一甲”,使民众安于地方,听从地方土司与流官的管理,使边民能“各有家室,安于田里,可以供赋役”。(67)蔡毓荣:《筹滇十疏·筹滇第五疏·酌安插》,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八卷,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432页。对于存在的“黑户”,在户籍管理上采取与地方土著编入保甲的方式获取国家承认的户籍。而对有意愿归还原籍的客民,“给以印照,听其回籍”。⑤通过给以地方户籍或者返籍的方式来使地方安定。另外,“滇省永昌之潞江、顺宁之缅宁二处,系通达各边总汇,特派员弁专司稽查,遇有江楚客民,即驱令北回。其向来居住近边之人,或耕或贩,查明男妇户口,照内地保甲例编造册档,并严禁与附近摆夷结亲”。(68)《钦定大清会典》卷158《户部七·户口·保甲》,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八卷,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78页。通过不断的强化户籍的稽查,逐渐将边地的流民与土著居民纳入到户籍管理的序列之中,从而降低了地方动乱的风险。
第四,王朝教化。滇西南社会长期的动荡、冲突,使清廷意识到传统的“以夷治夷”的模式,难以稳固王朝在边疆地区的统治,只有采取“剿抚并用”的方略才可持久。所以在“改土归流”过程中,一方面通过武力打压边地土司势力,来强化其在边疆地区的统治地位;另一方面希望通过文化礼教的浸染,使当地人群“融凝为一”“与华夏同俗”,从而消除地方上的反叛意识。
清初,顺宁府曾在官方的主导下建立书院,承担地方藏书和文化传戒的功能,主要培养当地有一定社会地位和较好经济条件的童生、士子,但规模较小,而在社会中有一定影响的主要是义学和私塾。顺宁府最早设立义学的记载始于雍正十三年(1735年),由知府朱桀英请立,到清末学制改立,先后设立了四十余所义学馆。义学主要用以培养蒙童小子,对当地基础教育的普及起到了一带作用,同时也与中央王朝所推行的“教小子尤急于教成人”“教夷户尤切于教汉户”(69)靖道谟纂,鄂尔泰监修:雍正《云南通志》卷29《艺文志》,南京: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8年影印本,第423页。的教化政策相契合。而在尚未完成改流的耿马、孟定土司管辖的地区,主要通过私人创办私塾来实现启蒙教育,以满足小范围的教育需求。它主要有以下三种形式。一是以私塾教师为中心的家庭教育模式。由村寨统一支付教学费用,聘请教师,需赴教师家学习。二是边地土司独立出资创办私塾,供养土司家族的蒙童教育。这种模式具有较强的封闭性特征,其入学的孩童只限于土司家族。三是以地方宗祠为基础的私塾教育。基于雍正年间大量汉族移民进入顺宁边地的背景,在地方形成众多的汉族村寨,依托血缘宗族的亲近性由族人共同承担相应的费用,共办私塾,从而使家族子弟能够开笔习礼,认字晓礼。
不难看出,清前期地方官员在用政治、军事力量管控滇西南地区的同时,也希望通过文化移植方法改变“蛮夷”的礼仪风俗,打破由于地域文化差异造成的“民”“夷”之间的认知隔阂,让边地夷众逐渐“向化”的同时,进一步笼络地方精英和土司子弟成为王朝在边地统治的可靠力量,从而消弭这一地区长期以来的动乱局面,使边地的政治秩序逐步按照王朝所预设的轨迹发展。
六、余论
清前期滇西南地区的政治生态复杂多变,围绕着地方权力、资源争夺等出现的动乱、冲突,成为这一时期滇西南社会变迁的底色,反映了中央王朝与边疆社会之间存在的紧张关系,凸显出国家、土司、族群相互关系调整中面临的矛盾和难题。边疆治理的目的,主要是对边疆社会组织、结构加以整合与重构,并将其纳入到王朝“大一统”的政治体系当中。这个过程虽然表现为“自上而下”的开发治理活动,但实际上,它并不是王朝主动征服与地方被动接受的过程,而是一个边疆社会与王朝之间的双向调适和彼此互动的结果。滇西南地方社会发展虽然受制于地理生态环境,但有其社会自身的发展逻辑和内在动力,表现出强烈的地方能动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可以把动乱、冲突看作是地方社会与王朝制度互动的结果,同样也可以将其视为是区域社会建构的过程和表现。(70)黄志繁:《“贼”“民”之间:12-18世纪赣南地域社会》,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第12页。基于这一认识,我们有必要对以下几个问题作进一步的思考和讨论。
第一,边疆治理背景下滇西南地区的动乱、冲突与地方社会建构的内在逻辑。滇西南作为远离中原核心区的边陲之地,地方社会的开发和发展成为王朝治边的重要缩影。从吴三桂藩镇云南到雍正年间大规模“改土归流”,再到乾隆年间的清缅冲突、地方动乱,王朝的边疆开发和治理一直持续到晚清。在这期间,围绕着地方权力、资源争夺而出现的社会动乱、冲突,成为滇西南社会变迁的重要内容。由于滇西南土司在地方政治权力体系中长期占据主导地位,其控制的区域也因地理环境和交通的阻隔,长期游离于王朝的统治之外。因此,在清前期滇西南地区的开发过程中,从早期军事斗争中地方权力和地方归属的争夺,再到土司地区的“改土归流”,都曾经历了中央王朝和边疆地方之间的博弈和拉锯,并不断影响和塑造着滇西南疆域的地缘政治格局。
此外,清王朝的开发与移民活动,在一段时间内加剧了滇西南地区族群之间的矛盾和冲突。由于受传统“华夏中心观”的影响,清政府在西南边疆推行的“分别夷民”政策,很容易引起地方族群之间的文化和群体隔阂的产生,从而形成对边疆地方治理不利的局面。尤其是在官方的文化认知与施政过程中,始终存在着“王朝之民”与“化外之夷”的二元认识和分类。大量汉人移民到滇西南山区垦殖,使土著人群受到挤压而不断迁往更加边远的山区,经常出现“汉进夷退”的局面。因此这一时期滇西南地域、族群及文化冲突的背后,从本质上来说,就是对生存空间和资源的争夺。而且因资源争夺引发地方性的动乱,也让清廷的边疆政策由原来的“治边”逐步向“安边”转变。可见,区域性的社会动乱是地方社会变迁的重要推动力之一,也是地方社会张力的重要体现,折射出滇西南区域社会的总体发展态势。但这个过程并非是一个单向度的历史过程,而是多种历史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第二,滇西南区域空间结构及历史文化的多元性对“边疆内地化”进程造成的影响。滇西南的族群政治格局受制于所处的地理和文化空间,呈现出点状分布的特点,不同的族群、社会长期游离于王朝统治的边缘,呈现出了一种半独立的状态,导致滇西南地区的族群政治与西南边疆其他区域一样,始终“处于‘中心’制度与文明之外非此即彼的状态之中,固守着一种古老的以本土为中心的世界观,即‘地方中心性’(local centrality)”。(71)彭文斌:《近年来西方对中国边疆与西南土司的研究》,《青海民族研究》2014年第2期。
尽管中央权力的延伸,使较为边缘的滇西南社会在政治、军事上得到了有效的控制。但是,在边疆开发治理过程中,国家权力经常会受到传统地方势力和底层人群的抵制甚至武力反抗,如与滇西南社会结构密切相关的地方宗教、文化传统、生计方式、域外势力等因素,始终困扰着清王朝在该区域的统治。特别是历史上边疆与内地之间形成的社会及文化差异,并没有随着王朝地方政治体制的建立而得到根本性改变,加之滇西南土著人群居住的分散性和地方民众宗教信仰的多重性,往往成为淡化中央权威的地方性基础。甚至在近代滇西南边地社会中,依然有许多民族群体“不知礼仪”“不习教化”而专事本族习俗。因此,以儒家文化为中心的“化远人”及“教化蛮夷”的文化愿景,始终是王朝政治实践所追求的目标。可见,滇西南特定的地理和文化空间,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阻碍着清前期西南地区“边疆内地化”的进程,并深刻反映出该地区“内地化”转型的整体发展趋势,以及社会整合与重构的复杂面相。
第三,边疆治理过程中山地人群的流动性及其生存策略。一般来说,滇西南地区族群流动的原因,在大多数时候主要是由生计方式造成的,并通过垂直分布带形式的“山坝结构”呈现出来。像傈僳、倮黑、窝泥等分布在山区以“刀耕火种”为主要生计方式的族群,因其临时性农业的耕作特点而需要不断迁移,表现出很强的流动性。但明清以来,因王朝边疆治理和汉人移民的深入所造成的社会动荡,导致了滇西南山地人群更大规模和更大范围的流动。在人类学家詹姆斯·斯科特看来,这类流动现象的实质是山地居民为逃避国家统治和其他掠夺者而采取的应对策略。他将东南亚以及中国云南、贵州、广西等地所有海拔200m或300m以上的地方,都划在一个所谓的“无政府主义”的领域内,称之为“赞米亚”(Zomia),意为“边远的山地人”。(72)詹姆斯·斯科特:《逃避统治的艺术:东南亚高地的无政府主义历史》,王晓毅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第18页。他指出,这一地区的人群在过去数千年的历史中“成功地逃避了各地国家项目的压迫——奴役、征募、赋税、劳役、瘟疫和战争,他们所居住的区域也许更适合被称为‘碎片区’(Shatter zones)或者逃避区”。(73)詹姆斯·斯科特:《逃避统治的艺术:东南亚高地的无政府主义历史》,王晓毅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前言”,第1页。
按照这一逻辑,包括滇西南在内的西南边疆广大山区,都可能成为土著族群因生态或政治原因逃避王朝(或者帝国)统治的区域。但事实上,明清以来,滇西南地区不管是山区还是坝区,都不存在完全意义上的“逃避区”,因为随着中央王朝势力的深入,区域性的政治隔绝逐渐被串连成一个集合体。特别是在清前期,随着开发的深入和边疆地区经贸往来的密切,区域性的文化交往也在加强。地方社会及民众从一个“封闭”社会的“自我”状态中被逐渐释放出来。不管是山区还是坝区民众,从原本游离于国家控制的状态,反过来成为王朝赋税的承担者,这种转变使他们很难成为“逃亡者”。与此同时,外来移民的进入、经济、文化的冲击,也让滇西南地区得到一定程度的开发。尽管这一时期,面对王朝力量和社会动乱时,土著人群流动、迁徙仍是其必要的生存策略,但流动的方向已不仅仅是向外逃离,更多的是向内流动,也就是文献中通常所说的“向化”。如在顺宁府境内的蒲人、阿卡等族群在清前期开始逐渐从山区往平坝迁移,并接受由内地传入的农业耕作和水利技术进行地方开发和农业生产,从而逐渐融入到王朝的政治体系当中。
詹姆斯·斯科特的理论虽然有其内在的合理性及强大的解释力,但就“赞米亚”的中国部分而言,他显然忽略了西南边疆内部业已存在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尤其是历史上西南地区一直面对强大的中原王朝及其从未间断的华夏文明。另外,他也大大低估了该区域山地族群在面对社会动乱时候,实际上有一套自己的应对策略和方法,表现出强烈的地方能动性。他们会有意识地通过社会动员去运用各种社会文化资源,以确立自身在王朝体系与地方社会中的地位及身份认同,从而摆脱现实生活中的生存危机。
总之,清初以来滇西南地区长期存在的社会动乱冲突,反映了中央王朝与边疆社会之间的紧张关系,折射出国家、土司、族群相互关系调整中亟需解决的问题。不论是“改土归流”时的土司动乱,还是汉人移民时的族群冲突,都是边疆社会面对外来“冲击”所做出的“回应”。如果从长时段视角加以考察的话,就会发现清前期滇西南地区尽管各类动乱事件层出不穷,但王朝所推行的仍主要是以“教化”为主导的文化控制策略。也就是说,社会秩序的重建是社会动乱进一步发展的必然结果,而这也正是近代民族国家形成之前“边疆内地化”发展的历史主线。如果从更为宏观的视野来看,滇西南地区政治生态变迁与边疆治理的历史,还可以看作是西南边疆社会逐步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曲折发展历程的一个缩影,即在空间关系上表现为“从分散到整体”“从边缘到中心”的渐进历史过程。而原本相对隔绝、独立发展的边疆与内地社会,在地域及文化空间上联系起来,并且不断强化这种联系;部分土著群体则突破了原有的族群边界,逐渐融入了更大的社会体系,乃至纳入到具有“多元一体”特征的中华民族“大历史”当中。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通过对上述问题的研究将有助于我们从“边疆视角”来探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这一重大命题,特别是透过疆域空间长期、复杂的历史变动过程,来解析和阐释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的动力机制及其所表现出来的不同层次的多元关系。(74)尹建东:《论历史时期西南疆域空间结构的多元属性和流动特征——兼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的“边疆视角”》,《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
(致谢:本文承蒙香港科技大学马健雄教授和唐立教授的校正,在此深表谢忱!)
——李良品《中国土司学导论》读书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