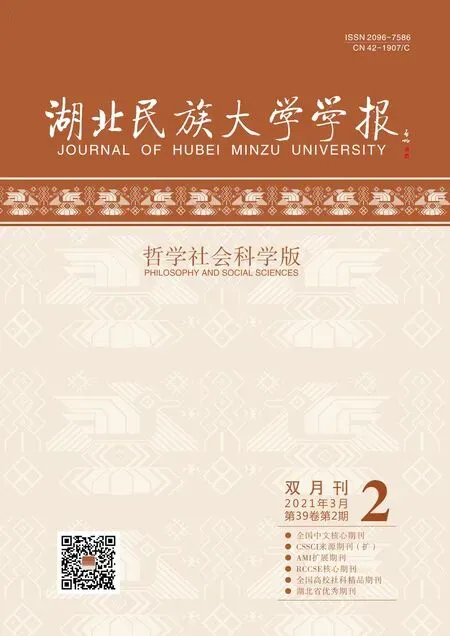从“历史”中寻找身份:傈僳族刀杆节的王骥叙事与文化表述
杨江林 张力尹
傈僳族主要分布于川滇交界的攀枝花、丽江和迪庆等部分地区,以及滇西云龙、泸水、保山、腾冲等滇缅交界地带,其传统节日有阔时节、刀杆节、新米节、澡堂会等。明清时期,滇西傈僳族经历了由川滇交界向滇西云龙、怒江、腾冲等地迁徙的历史过程。清初,“上刀山”(1)“上刀山”仪式是傈僳族“刀杆节”最为重要的内容。目前“上刀山”的最早记载见于康熙《云龙州志》,是云龙地区三崇庙前一种重要的娱神活动。仪式就出现于云龙地区的文献记载中,晚清民国时期,这一仪式普遍流行于滇西的云龙、怒江、腾冲等地。目前,“刀杆节”主要分布于滇缅交界的腾冲、保山、怒江等傈僳族聚居区。
民族节日是凸显民族特征,增强民族自信的文化符号。李晓斌等通过德昂族浇花节与傣族泼水节的比较研究,认为确立本民族的文化身份成为浇花节建构的重要动因。(2)李晓斌、段红云、王燕:《节日建构与民族身份表达——基于德昂族浇花节与傣族泼水节的比较研究》,《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而傈僳族“刀杆节”的文化表述也同样与其族群身份密不可分。高朋从国家治理与文化互动的视角解读腾冲傈僳族刀杆节的民间叙事,并指出“刀杆节”的王骥叙事是滇西傈僳族为进入国家“编户齐民”的文化策略。(3)高朋:《文化互动、地方社会与国家治理:腾冲傈僳族刀杆节叙事解读》,《思想战线》2019年第3期。而高志英等基于傈僳族“刀杆节”的王骥叙事,指出王骥崇拜是滇西傈僳族与汉族接触过程中将本民族原始崇拜与汉族民间信仰相互交融基础上共创、共享的一种区域文化,显示出国家认同(4)高志英、王东蕾:《从王骥崇拜看中缅傈僳族的多重认同演变》,《云南社会科学》2013年第5期。,“上刀山”仪式象征着边地民族从最初的“逃离国家”到再次“归附国家”(5)高志英、和金保:《多重边缘中的中缅跨界傈僳族上刀山仪式及其功能演变》,《世界民族》2016年第6期。。熊迅也通过考察“刀杆节”的仪式结构,来探讨傈僳族的国家认同。(6)熊迅:《仪式结构与国家认同:跨越中缅边境的傈僳族刀杆节》,《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2期。以上研究分别从区域历史、族群互动和仪式过程等角度探讨了“刀杆节”的文化内涵,却缺少了对“刀杆节”的历史梳理,忽视了晚清西南边疆危机这一王骥建构的历史背景。将“刀杆节”的王骥叙事简单理解为滇西傈僳族为进入国家“编户齐民”的文化策略也无法解释三崇神王骥的区域性影响,以及三崇信仰的跨族群特征。如置于历史情境,晚清腾越边关傈僳族社会身份的转变和国家意识的激发与“上刀山”仪式并无关联,而正是晚清西南边疆危机促成了三崇信仰的王骥建构,并融入“上刀山”仪式的民间叙事。从当下来看,“刀杆节”的王骥叙事承载了滇西傈僳族的国家意识与身份认同(7)本文所强调的身份认同是指晚清时期腾越边地傈僳族“为国戍边”的社会身份,而非傈僳族的族群身份。,其核心正是对族群“历史”的建构,而这一基于王骥叙事的历史建构则与近代滇西边地的民族国家建构一脉相承。本文将从“刀杆节”起源传说入手,结合滇西傈僳族的历史迁徙,探讨“上刀山”仪式演变为傈僳族“刀杆节”的历史过程及其文化表述,从历史脉络中探寻傈僳族“刀杆节”的文化内涵。
一、“刀杆节”起源传说
刀杆节,傈僳语称“阿堂得”,意为“爬刀节”。在1949年以前,滇西腾冲、盈江、泸水、云龙等地三崇庙前普遍举行“上刀山”仪式。今腾冲滇滩镇每年农历二月初七、初八两天举行“刀杆节”活动。初七晚上在三崇神祠前的刀杆场,傈僳族“香通”(8)“香通”这一称呼常见于明清时期云龙地区的史料,今傈僳语又称为“尼扒”,即傈僳族巫师。经过艾蒿香洁身、神前祈祷、踏踩香路等程序后表演“跳火海”。他们赤裸上身,光着脚板,在一堆堆烧得通红的栎木炭火上,来回腾挪跳跃,或抓炭火在身上脸上揩抹搓揉,任凭火球在身上扑腾翻滚。他们认为,烈火的洗礼,蕴示在新的一年里解厄降祥,诸事通达。而刀杆场中央,早已矗立着两根约20米长的粗大铁杆,杆上绑有72把(有时36把)锋利锃亮、可吹发断毫的户撒刀,刀口一律向上,寒光闪闪,形成一架直耸云天,令人望而生畏的刀梯。香通们穿着红衣裳,头裹红包头,赤着脚,在祭坛前端酒虔诚祭拜,口中念念有词,接着将杯中祭酒一饮而尽。然后,他们一个个纵身蹿上刀梯,双手握住刀口,赤脚踏锋,迎刃而上。(9)滇滩镇志编纂委员会:《滇滩镇志》,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455页。以上描述呈现了“上刀山、下火海”的仪式过程,并表明傈僳族“刀杆节”与当地三崇庙密不可分,而纪念三崇神(王骥)已成为“刀杆节”的主要文化表达。
1949年以前,云龙地区在祭祀本主(三崇)活动中,“上刀山”是其中的重要内容。但云龙地区的“上刀山”仅是祈福消灾仪式,并没有形成固定节日。“上刀山”一般有两种类型:一种是祈福性的,即通过“上刀山”来祈求赐福,保佑全村一年平安,五谷丰登,六畜兴旺;另一种是消灾性的,如本地发生严重自然灾害、人畜瘟疫或家中有人久病未愈等,就要到本主庙举行“上刀山”,祈求本主驱鬼消灾。消灾性的“上刀山”通常是由祭司“朵兮薄”(10)朵兮薄,为白语称呼,是云龙地区白族对巫师的称呼,朵兮薄有黑白两种,黑朵兮薄的法力更高一筹。打卦来确定“上刀山”的日期,而祈福性的“上刀山”一般在本主会举行。旧州下坞村的本主会是一年一小会,三年一大会,做大会就要举行“上刀山”仪式。(11)政协云龙县委员会:《云龙文史资料》第七辑,2013年,第294页,内部资料。据村民介绍,“上刀山”仪式与明初的“三征麓川”密切相关。据传,过去三崇本主带兵征麓川时,每逢攻城就架云梯,从云梯的刀尖上攻进去,所以后来举行“上刀山”活动,是为了纪念本主老爷和他的士兵,学习他们的勇敢精神。(12)政协云龙县委员会:《云龙文史资料》第七辑,2013年,第294页,内部资料。据侯兴华考察,“刀杆节”在腾冲和怒江地区有两种不同的起源传说。腾冲地区也普遍认为“刀杆节”是为纪念“三征麓川”的王骥。
为了让傈僳族人民过上好日子,朝廷派兵部尚书王骥带兵到边境一带安边、设卡。王骥让散居的傈僳族聚集起来,饲养牲畜,发展农业生产。眼看外敌就快被赶出边境,人民将过上幸福的日子,这时朝廷里的奸臣却上书皇帝,诬告王骥练兵是为了造反,要自立为王。于是皇帝大怒,召王骥回朝廷,并在农历二月初八为他洗尘的酒席上用毒酒毒死了他。王骥死后,他的灵魂升上天空,但他仍惦记着边境地区的傈僳族人,腾云驾雾来到边疆,传口信给傈僳人,要他们在二月初八上刀杆,只要爬到杆顶就能永保平安。他叮嘱上刀杆的头天晚上要踩火塘、洗火澡,把筋骨烧得干干净净,上刀杆时才不会伤到脚。王骥被害的噩耗很快传遍傈僳族山寨,男女老幼无不义愤填膺,决心以王骥敢上刀山、下火海的精神誓死保卫边疆。(13)侯兴华:《傈僳族刀杆节的由来及其演变》,《保山学院学报》2012年第3期。
腾冲地区“刀杆节”的起源传说与云龙地区基本相同,都与王骥和“三征麓川”历史事件密不可分,纪念王骥成为“刀杆节”的主要表述。云龙地区将王骥隐晦为“三崇”,而腾冲地区则直接表达了王骥“三征麓川”时对傈僳族的关爱及滇西傈僳族对王骥的纪念,但两地的“上刀山”仪式均在三崇庙前举行。今天云龙地区也普遍认为三崇老爷就是三征麓川时被当地夷人毒死于漕涧嘎窝的明兵部尚书王骥,至今漕涧嘎窝仍保留民国时期漕涧官吏、乡绅等为王骥重修的八尺墓塚。然而,怒江地区的“刀杆节”传说却与王骥和“三征麓川”的历史并无关联。
有一年,怒江边的一个傈僳族村子出现了瘟疫,很多人得了重病,家畜也死完了,庄稼颗粒无收,人们面临死亡的威胁。大家怀疑有人从中作梗,于是全村人要进行捞油锅。当天晚上,天神托梦给村里的头人,说并非有人从中作梗,一切都是住在村子后山悬崖上的恶魔所为,只有踩着刀子连接成的刀梯爬上悬崖,杀死恶魔,村民才能得救。于是,人们用各家拼凑的刀子连接成刀梯。一名年轻人自告奋勇,告别心爱的女友,踩着刀梯爬上悬崖,与恶魔大战起来。好长时间过去了,年轻人始终没能杀死恶魔,这时,他的女友在山下大喊了一声,恶魔以为救兵到了,吓出一身冷汗,年轻人乘机抱住恶魔的腰部,一同滚下悬崖。等人们急匆匆赶到崖底,却没有发现年轻人的尸体。为纪念年轻人,同时也为了庆祝人类得以生存和发展,人们相聚在一起,唱歌跳舞,并举行上刀杆活动。(14)侯兴华:《傈僳族刀杆节的由来及其演变》,《保山学院学报》2012年第3期。
以上两个传说表明怒江和腾冲两地不同傈僳族群体对“刀杆节”的起源叙事各不相同,怒江地区认为“刀杆节”是纪念本民族英雄,而腾冲地区的傈僳族认为“刀杆节”是为纪念帝国英雄王骥。虽然各地传说差异很大,但其表达的均是“消灾祈福,清吉平安”的内在意义,这与云龙地区也基本一致。侯兴华通过对各地民间传说的分析,认为“刀杆节”原本是傈僳族祭祀鬼神、祈求平安的祭祀活动,后来逐渐发展为节日庆典,而并非是为纪念尚书王骥。②那么,王骥如何成为云龙、腾冲等地“上刀山”仪式的共同表述,这就与云龙三崇信仰的区域传播与文化建构密不可分。
二、“刀杆节”的历史源流
过去关于“上刀山”仪式研究大都基于滇西傈僳族“刀杆节”的民间叙事和仪式过程来考察其文化内涵,而忽视了对“刀杆节”历史源流的梳理。明末清初,“上刀山”仪式就是三崇庙前的娱神活动,至今傈僳族“刀杆节”仍在三崇庙前举行。明清时期,三崇庙的传播与三崇神的建构对滇西傈僳族“刀杆节”的文化表述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三崇庙与“上刀山”仪式
明嘉靖年间,云龙土知州段文显在三崇山麓建三崇神祠,行春秋祭祀,云龙的本土信仰进入了官方祭祀体系。(15)邹应龙修,李元阳纂:万历《云南通志(下)》,刘景毛、江燕等点校,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13年,第1070页。此后,三崇信仰被流官知州所推崇,并在云龙五井地区具有重要影响。自明清以来,“上刀山”仪式就与三崇庙密不可分,目前关于这一仪式的最早记录见于清康熙《云龙州志·风俗》。
凡病者,酬神必宰猪羊,备烧酒纸锭,延巫曰香童者数人,歌舞以乐神,葜铁链于火,口唧之,出入踢跳,缚数十刀于木端似梯,赤足升降,曰“上刀山”。牲醴必先尝,然后敢祭。相传三崇为汉将,于漕涧中彝毒,故祭如此。然灵应甚著,祷赛者无虚日。(16)王符编纂:康熙《云龙州志·风俗》,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本,第123页,云龙县志办手抄本。
这一记载生动形象地描述了清代初期云龙民间“上刀山、下火海”的仪式场景。明末清初,“上刀山”仪式是云龙地区三崇庙前举行“消灾祈福,清吉平安”的娱神活动。至今傈僳族中“上刀山”表演者仍然称为“香通”,而这一称谓应当源自汉语,并常见于云龙地区的历史文献。明清以来,云龙虎头山就是道教圣地,清康熙《云龙州志》记载的“上刀山,下火海”仪式可能与云龙的道教仪式有密切关联。在云龙漕涧村,自认为是道教“武行”的高公(17)高公是云龙各地民间百姓对道士的称呼,其中在白族中最常用。高林杨就曾表演过“下火海”仪式。明末清初,云龙地区已有傈僳族居住,雍正《云龙州志·风俗·种人》记载如下。
傈僳:于诸夷中最悍,不栉不沐,语亦与诸夷别。处兰州界连云龙,依山负谷,射猎为生。利刃毒矢,日夜不离身。射兽即生食,间事耕种,唯荞稗。祭赛则张松棚燃炬,剥獐鹿诸兽骨用,有隙辄相仇杀。散游于僰子寨、瓦窑场、马椒甸、鸡踪洞之间,不时伺隙,劫掠行旅,抢牛羊、大为归化、师、顺之患。康熙五十三年,知州王符通详上宪,啄落兰州土舍纳解法究。后始知法纪,近今敛迹。(18)政协云龙县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云龙县志编纂委员会:雍正《云龙州志·种人》,陈希芳编纂,周枯点校,保山:保山报社印刷厂承印,第45页。
以上记载描述了清初云龙地区傈僳族的分布及其生活习俗等。云龙地区傈僳族不时伺隙,劫掠行旅,抢牛羊,大为归化、师、顺之患,与云龙盐井地区生活习俗差异较大,直到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后才始知法纪。清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云龙知州王符在《详究傈僳抢劫》中指出:“查云龙西北一带,接壤兰傈僳乃舍目罗维馨土民,丽江土府木兴所辖也。向来维馨纵贼抢杀,卷案重迭。”(19)政协云龙县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云龙县志编纂委员会:雍正《云龙州志·申文》,陈希芳编纂,周枯点校,保山:保山报社印刷厂承印,第149页。清代的《木氏宦谱·文谱》还记录了明万历二十年(1592年),云龙州傈僳抢掠五井提举皇盐的情景。(20)张永康、彭晓:《木氏宦谱》,昆明:云南美术出版社,2001年影印本,第44页。因此,清初傈僳族参与云龙盐井地区三崇庙“上刀山”仪式的可能性不大。滇西傈僳族有可能在云龙三崇庙传入六库五土司地区之后才参与“上刀山”仪式,这也就与云龙段氏土司的向西分防密不可分。
民国《泸水志》记载:“六库五土司地区,各有三崇庙一座。”(21)段承钧纂修:民国《泸水志》,台北:成文出版社,1975年,第55页。今老窝乡老窝村仍建有三崇庙一座。而六库五土司中的六库土千总、老窝土千总、登埂土千总、卯照土千总均是云龙段氏土司分支。据光绪《云龙州志》记载,“明万历年间,蒙上宪赏授六库巡捕之职,分防六库”。(22)张德霈等修,杨文奎纂:光绪《云龙州志·土司》,光绪十八年(1892年)本,第48页,云龙县志办手抄本。永历二年(1648年),六库土司段其辉征服片马,得地三百余里,遂分段其先为登埂土司,同时有潞江上游怒夷为害,分段其威为卯照土司,防止怒夷。(23)段承钧纂修:民国《泸水志》,台北:成文出版社,1975年,第39页。清乾隆十二年(1747年)段复健随征秤戛有功被授土把总职,后征茶山,十七年授土千总世职,正式建立了六库土司。清道光《云南志钞》载:“云龙州归化里老窝土千总段克勋,其先段惟精,明土知州段保之裔。乾隆十二年,率土练随总统谢岳征秤戛夷贼,招抚鹅毛顶夷民十寨归顺,屡立战功。十七年,授千总世职。”(24)王崧撰:道光《云南志钞》,杜允中注,刘景毛点校,昆明: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文献研究所,1995年,第308页。而登埂土司于雍正八年(1730年)从六库土司段其辉“兄弟分防”中分支而立,先在片马大坝地河建土司署,后将土司署迁往登埂村,管辖登埂至片马大片土地。清雍正八年(1730年),卯照土司从六库土司中分支产生。段其威在卯照设立土司署,其子段联甲因应征镇压称戛傈僳族弄更扒起义有功,乾隆十七年(1752年)被封为卯照土把总职。三崇庙作为段氏土司家庙,在清初就随段氏土司进入六库、老窝等地,三崇庙前的“上刀山”仪式也随之传入怒江地区。因此,如怒江地区的“刀杆节”传说,“上刀山”仪式与傈僳族的本土英雄传说相结合,而与“三征麓川”的王骥没有关系。
(二)王骥与“上刀山”仪式
从田野考察来看,纪念王骥已成为“刀杆节”的主要表述,然而王骥成为“上刀山”仪式的主要表述却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并与三崇信仰的建构密不可分。康熙《云龙州志》指出,三崇庙所供奉之神相传是被毒死于漕涧的汉将,但并未指出具体为何人。(25)王符编纂:康熙《云龙州志·风俗》,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本,云龙县志办手抄本。而清乾隆年间诺邓人黄桂的《沧江赋》才首次提到“王骥筹边于远涉”的描述。可见,这里所指的“三崇”并非王骥,直到清光绪《云龙州志》才指出,三崇神,姓王讳骥,并在其后附有王骥“三征麓川”的描述。(26)张德霈等修,杨文奎纂:光绪《云龙州志·祠祀》,光绪十八年(1892年)本,第6页,云龙县志办手抄本。
王明珂指出,将文献与口述历史视为“历史记忆”,我们所要了解的是留下这记忆的“社会情境”及“历史心性”。(27)王明珂:《历史事实、历史记忆与历史心性》,《历史研究》2001年第5期。明正统年间的“三征麓川”对西南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然而,明清史籍中对“三征麓川”大都持否定态度,对王骥批评较多。(28)陆韧:《泛朝政化与史料运用偏差对边疆史地研究的影响——以明代”“三征麓川”研究为例》,《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0年第3期。而晚清时期,滇西边地对王骥“三征麓川”的赞颂却遍及诗文。如清光绪腾冲亚元刘宗鉴的《咏王靖远三征麓川》(29)赵端礼:光绪《腾越厅志》,台北:成文出版社,1967年,第367页。,腾越岁贡李雨农的《戛鸠江怀古》(光绪壬寅)、《月夜泊大金沙江》(光绪甲辰)(30)尹明德:民国《云南北界勘察记》,滇缅界务调查小组报告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刊本,台北:华文书局,1969年影印本,第77-78页。,民国元老李根源的《咏古》(31)腾冲县旅游局:《历代名人与腾冲》,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7年,第6页。等都有对王骥和三征麓川的赞誉。以上诗文与清末滇西边地的民族国家建构直接相关。随着边疆危机的爆发,滇西腾冲等地的知识分子重新思考王骥“三征麓川”的历史意义,并将其塑造成为“保边安民”的地方英雄,而民间也将其奉为迤西、滇缅一带最大保护神。在与滇西腾冲等地的密切交往之中,云龙五井地区已深感边疆危机(32)清道光云龙贡生黄云叶在《论平夷事宜拟》中就已深刻论述了英国对缅甸的入侵和中缅边疆的局势。,同时也主动融入滇缅边地的国家整合。面临缅甸私盐的入侵,“三征麓川”的王骥也被地方文人建构于云龙本土的三崇信仰,王骥也就成为“威震滇西,保境安民”的三崇神,并融入了“上刀山”仪式的文化表述。因此,滇西腾冲等地也普遍认为“刀杆节”的起源是纪念“三征麓川”的王骥,这也与云龙漕涧左土司在腾北地区的影响密不可分。
漕涧左土司家族在明末曾分支到腾冲明光,清乾隆年间授予左正邦茨竹寨土把总职。清光绪《腾越厅志》记载:“左文伟,漕涧人,九夷为患,官招文伟率弓弩手五十三名驻防明光,传至正邦,称戛军务奏准世袭土把总。”(33)赵端礼:光绪《腾越厅志》,台北:成文出版社,1967年,第155页。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明光土守备左大雄撰写的《明季诰封世守漕涧武节将军早公讳陶墓志铭》记载:“永历八年,缘腾越明光地方时被野匪残毒,禀垦腾越,详请制宪,扎仰腾越、云龙会调,文伟前往明光防守,文伟携生母刘氏,弟文星、文彦率弓弩手百余名迁往明光,漕涧承袭左文灿。至清乾隆十二年,左文伟四世孙左正邦随征称戛有功,设茨竹隘,辖22寨,委正邦为世袭土把总职管理隘务。左正邦五世孙左大雄英功卓著,道光二十五年征上江李妹波、傅四有功,赏五品顶带,升授土守备职。”(34)左大雄:《明季诰封世守漕涧武节将军早公讳陶墓志铭》,左骞、左治华编著:《云龙阿昌史话》,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47页。虽然左土司自南明永历八年(1652年)就进入腾冲明光地区,但三崇庙却到清中后期才在腾北地区修建。今腾冲明光、自治、滇滩、猴桥等地均建有三崇庙,并在农历二月初八在三崇庙前举行“刀杆节”。据庙碑简介,明光三崇寺和滇滩三崇庙均建于清代中叶,但年代却误写为1580年。经笔者考证,时间可能在1850年左右。首先,乾隆《腾越州志》有大量王骥“三征麓川”的记载,而并无三崇庙记载。其次,明光麻栎大寨ZML也作了介绍。
三崇寺以前是个小山神庙,我们祖先左大雄去今临沧云县平叛(滇西回民起义),结果被围困三天三夜,死了很多人。后左大雄发愿,如果打了胜仗就重修一下寺庙。后来,打了胜仗回来左大雄就重修了寺庙。然后,也就在寺庙里面纪念战死的战士,也有纪念王骥的意思。(35)ZML,男,明光茨竹左土司后代,67岁,明光镇麻栎大寨,2019年1月31日。
民国《云南北界勘察记》指出:“道光二十六年,左大雄征云州有功,袭守备职,加管小江十八寨。”(36)尹明德:民国《云南北界勘察记》,滇缅界务调查小组报告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刊本,台北:华文书局,1969年影印本,第116页。而云龙漕涧还发现了道光二十八年明光土守备左大雄撰写的《明季诰封世守漕涧武节将军早公讳陶墓志铭》,充分说明了明光左土司与漕涧左土司之间的密切往来。道光二十六年,左大雄征云州取胜后,还愿重修寺庙,此后,三崇庙和“上刀山”仪式才进入明光麻栎大寨及周边地区,而王骥也就成为腾冲等地汉族、阿昌、傈僳等共同供奉的三崇神。民国《腾冲县志稿》中对腾冲“上刀山”的记载就与王骥密切相关。
“腾冲隘地尚有巫教之香童,其术无师传,信之以为神附之,能跣足于炽炭之中,烧铁练缠于脖颈,空中借火,赤足履利刃,咬磁瓦如嚼饼饵,所奉为三崇之神,每年二月八日演刀杆之剧,相传此种巫教乃明正统间王骥征麓川时设之以威服诸夷也,否欤?”(37)许秋芳、李根源、刘楚湘纂修:民国《腾冲县志稿》,昆明:云南美术出版社,2004年点校版,第443页。
民国时期,腾冲边隘每年农历二月初八在三崇庙前举行“上刀山”仪式。“上刀山”也被认为是明正统年间王骥征麓川时用于震慑蛮夷而举行,这也是借用王骥“三征麓川”的历史表明了三崇庙和“上刀山”仪式由外来传入的事实。腾冲古永(现猴桥镇)苏江村有三崇庙一座,村里以王姓和郭姓为主,据其家谱记载,其祖上为戍边军人,据该村老人郭金仪口述:“年轻时听祖辈传言,刀杆先是由苏江村王家上的,是为纪念他们的统领王尚书安边定疆而举行,后来传到二十多里外的边境傈僳族地区。”(38)转引自何马玉涓:《文化变迁中的仪式艺术——以傈僳族刀杆节为例》,博士学位论文,昆明:云南大学,2015年,第47页。
三、傈僳族“刀杆节”的王骥叙事
高志英等指出:“明清以来,因中国中央王朝势力深入,世居金沙江、澜沧江、丽江、维西一带的傈僳族生存空间受到挤压而被迫向中缅边境迁徙,从而处于被多重强势力量边缘化的境地。”(39)高志英、和金保:《多重边缘中的中缅跨界傈僳族上刀山仪式及其功能演变》,《世界民族》2016年第6期。明清时期,滇西傈僳族长期处于强势族群的奴役之下,反抗和“逃离”成为其主要的生存策略。15-16世纪,居住在丽江、维西一带的大批傈僳族沦为丽江木氏土司的农奴。乾隆《丽江府志》记载,木土司在其领地内拥有“庄奴”及“院奴”共达2344人之多,其中大多数就是傈僳人。傈僳族不仅要为木土司服劳役、缴赋税,同时还成丽江木土司对外征战的工具,而傈僳族迁入怒江地区也与木土司的对外征战直接相关。
据傈僳族老人世代口传,最早进入怒江地区的是属于荞氏族(括扒)中的“木必”家族。明嘉靖、万历年间,丽江木土司和藏族争夺维西的战争中,木土司指挥下的一支傈僳族军队打得很出色,木必带领着傈僳族军队与藏军多次交锋,连续取胜。后来,藏族骑兵大量增援,木必便带领傈僳族退到澜沧江西岸。藏军撤退后,木必带领伙伴越过碧罗雪山,进入怒江。(40)《傈僳族简史》编写组:《傈僳族简史》,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0页。
据德宏州盈江县苏典乡傈僳族先民余氏碑文记载,傈僳族17世纪末开始迁入盈江县境,其迁徙路线为:怒江—片马—腾冲古永,然后进入盈江沿边一线的支那、盏西和苏典。(41)盈江县志编纂委员会:《盈江县志》,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7年,第557页。滇西傈僳族居无定所、善于狩猎,因此易于迁徙。加之地方土司的压榨,傈僳族在反抗中被迫逃离。在17-19世纪的两百年中,傈僳族又经历了几次大的迁移。如清嘉庆八年(1803年),傈僳族恒乍起义后的大迁徙;道光元年(1821年),永北傈僳族唐贵起义后的大迁徙;光绪二十年(1894年),永北傈僳族丁洪贵、谷老四起义后的大迁徙。傈僳族由东向西顺着太阳落山的地方迁移。在19世纪中后期,成批的傈僳族向西越过高黎贡山,进入缅甸境内,也有的傈僳族向南沿澜沧江、怒江,经镇康、耿马进入沧源、孟连,抵达老挝泰国等地。③清末民国时期,傈僳族广泛分布于滇西云龙、泸水、保山、腾冲等地。
清乾隆十二年(1747年),泸水称戛傈僳族发动叛乱,漕涧、六库、老窝、卯照、明光等地土目、团练均参与平叛,并立有军功。清王朝为进一步加强对这一地区的统治,于乾隆十七年(1752年)将老窝、六库、漕涧等地划归云龙州管辖,并授予云龙州段氏土司族人段复健六库土千总世职,段惟精老窝土千总世职,段联甲为卯照土把总职,并委左正邦为世袭土把总职,管理明光茨竹隘务。此后,云龙以西的傈僳族地区处于各土司管辖之下,部分骁勇善战的傈僳族逐渐发展成为各地土司的武装力量,并承担边地防务的重要职责。乾隆《腾越州志》记载,“古勇、明光、滇滩诸隘之设,防野夷也”,而防守滇滩隘,除部分溏汛兵,主要依靠傈僳族弩手,归滇滩隘土统领。(42)滇滩镇志编纂委员会:《滇滩镇志》,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300页。道光《云南通志》记载如下。
道光七年,署腾越厅广裕详请设立河西外围香柏岭十五卡,招募傈僳三百七十五户分驻,于盐课溢余留半银支给口粮盐菜,限满听其种地守卡。嗣因山地硗确,不敷口粮,永昌府胡启荣、腾越厅周澍,详请奏明借藩库银二二万两,置买练田,分给各傈僳口粮;府、厅各捐银一万两,五年归款。内香柏岭立二卡,安设傈僳六十户;三级箐一卡,安设傈僳三十户;麦瓜林二卡,安设傈僳七十户;三台山一卡,安设傈僳十五户;喂羊路二卡,安设傈僳四十户;春花地、大草坡两处分扎三卡,春花地安设傈僳四十户,大草坡安设傈僳四十户;莳竹脑安设傈僳四十户。以上共设傈僳三百七十户,随带眷口一千一百十七名,分扎十五卡。又马安山一卡,捐设傈僳二十户;象脑山一卡,捐设傈僳十五户。谨按,右新建碉堡屯田为现在边防要务。(43)道光《云南通志》卷106《武备志二·戎事六》。
清道光七年(1827年),腾冲地方官员招募傈僳人来担任边境关卡守兵,安设傈僳三百七十户,分扎十五卡,并支付口粮,发放饷银。滇西傈僳族在不断逃离和迁徙中开始定居,并纳入国家“编户齐民”(44)高朋:《文化互动、地方社会与国家治理:腾冲傈僳族刀杆节叙事解读》,《思想战线》2019年第3期。,而地方土司是其直接管理者。三崇庙作为土司的家庙,在六库五土司地区和明光左土司管辖区域兴建,并成为地方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作为土司部属的傈僳族守兵自然也就参与到了三崇庙的“上刀山”仪式之中,并扮演了重要角色。随着滇西社会的动乱和地方文人的塑造,王骥以“威震滇西、保境安民”的形象成为民间对三崇神的表述,这也是战乱之际滇西各族人民对社会秩序和地方英雄人物的期盼,作为国家象征的地方英雄人物王骥成为了滇缅一带的最大保护神。三崇神王骥成为国家在滇西边陲的象征,纪念王骥成为滇西三崇庙和“上刀山”仪式的共同表述。高志英也指出,王骥崇拜是滇西傈僳族与汉族接触过程中共创、共享的一种区域文化,显示出国家认同。(45)高志英、王东蕾:《从王骥崇拜看中缅傈僳族的多重认同演变》,《云南社会科学》2013年第5期。在与周边民族的交往与互动之中,滇西傈僳族的国家意识得到强化,这种国家意识表现在傈僳族对外来侵略的反抗和斗争。清末,英国殖民者从缅甸入侵腾冲、片马等地,傈僳族在抗英作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左孝臣带领傈僳族兵马在甘稗地抗击英军,英勇壮烈。(46)《大寨早姓左宗谱》,腾冲明光麻栎大寨ZML提供,2019年1月31日。清宣统三年(1911),英军由缅甸进入,强占片马,登埂土司片马管事勒墨夺扒(傈僳)和景颇族头人带领片马人民抗拒英军。(47)泸水县志编纂委员会:《泸水县志》,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61页。
正如刘志伟指出:“如果国家建造的过程是包含着本地人如何用自己的办法去将自己同中心联系起来,我们与其将边疆视为一个承受国家制定扩张的开放空间,不如更多关注地方上的人们如何运用他们的创意和能量建立自己的身份认同。”(48)刘志伟:《地域社会与文化结构的过程——珠江三角洲研究的历史学与人类学对话》,《历史研究》2003年第1期。“刀杆节”的叙述不仅表达了滇西傈僳族的国家意识,同时也是滇西傈僳族基于族群历史的建构来表述身份认同。明清时期,傈僳族处于不断反抗和“逃离”之中,对缺乏文字书写的傈僳族来说,历史记忆是模糊的,也是没有意义的。斯科特指出:“如果说游耕和散居是为了阻止被征用的生存策略;如果说社会碎片化和没有首领是为了阻止被国家统合;那么同样,没有文字和文本也使他们可以自由地操纵历史、谱系和清晰性。”(49)詹姆士·斯科特:《逃避统治的艺术:东南亚高地的无政府主义历史》,王晓毅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271页。因此,正是缺乏文字和书写文本的模糊历史也为滇西傈僳族的历史建构创造了条件。清中后期,滇西傈僳族开始融入国家的管理体系,在与周边族群的交流与互动之中国家意识和身份认同开始突显,而历史表述成为表达族群身份的重要内容。只有将族群历史悬挂于国家机器之上,才能表达滇西傈僳族为国家戍边守卡,保卫边关的身份认同。因此,缺乏历史书写的傈僳族也就将族群历史建构于作为国家象征的王骥之上,而关于王骥的知识也是来源于周边民族关于“三崇”的传说。晚清时期,云龙地区三崇庙的对联就有大量赞美“三崇”抗击南蛮、保境安民、传播文明的表述。“刀杆节”的叙事主要表达国家派来的王骥带领傈僳族人民过上了好日子,傈僳族人民为纪念王尚书而举行“上刀山”仪式。这一表述与滇西汉族、白族等对三崇庙的表述基本一致,三崇庙也被认为是纪念王骥“三征麓川”对滇西各族人民的贡献而修建的。傈僳族在参与三崇庙“上刀山”仪式过程中,也自然将周边族群所供奉的三崇神王骥奉为自己的保护神。“刀杆节”的叙事表达的也是傈僳族与保护神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表现为傈僳族如何建构保护神的形象,而作为保护神的王骥又如何参与傈僳族的历史。“上刀山”仪式诉说了傈僳族的“历史”和身份,尽管这种历史是被建构的,但傈僳族通过对历史的建构,由“逃离”的历史融入到国家历史叙事,从而与清代中后期腾冲傈僳族“为国戍边”的身份相匹配。关于历史的表述和身份的认同也就成为滇西傈僳族“上刀山”仪式传承和发展的动力。
1949年后,滇西边地三崇庙前的“上刀山”仪式陆续中断。20世纪50-60年代的民族识别也强化了民族之间的差异,而民族节日成为彰显民族特色的文化符号。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三崇庙的恢复,腾冲等地傈僳族逐渐恢复了“上刀山”活动。以下是腾冲县文化馆原馆长和编导马天菊的回忆。
傈僳族刀杆节在当时是被当做文化挖掘完成的一项工作。当地人想要恢复,有迷信的意思。但在政府看来,应该是一个民族的文化精神。杨馆长做了很多的调研和汇报,最后给予恢复。1981年,在古永轮马村坡头,盖有供奉王骥将军的小庙,香通门在那里请神。我们工作人员认为既然要恢复,就要轰动。于是我们组织当地村民参与到我们的活动中来,并将傈僳族的三弦调子、跳嘎等民族艺术加入到刀杆节的流程中,就是想让刀杆节的形式更丰富、意义更广泛。(50)何马玉涓:《文化变迁中的仪式艺术——以傈僳族刀杆节为例》,博士学位论文,昆明:云南大学,2015年,第80页。
作为三崇庙前娱神活动,女性是不能参与“上刀山”仪式。然而,傈僳族歌舞表演的融入将“上刀山”仪式由“封建迷信”活动转变为傈僳族的“传统节日”,这对傈僳族“刀杆节”的恢复具有重要意义。据熊迅等调查,1979年农历二月初八,轮马羊肠河恢复了中断二十多年的“刀杆节”。1989年后,古永傈僳族的刀杆表演队伍开始“走出去”,相继参加了“民族艺术节”“中国艺术节”“中华民俗风情艺术节”等,并在全国第五届少数民族运动会中获得一等奖。(51)熊迅:《仪式结构与国家认同:跨越中缅边境的傈僳族刀杆节》,《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2期。1997年怒江州泸水县恢复“上刀山”仪式,2006年5月20日泸水县傈僳族“刀杆节”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刀杆节”的申遗也就进一步强化了滇西傈僳族对历史的表达和族群身份认同,“敢上刀山,敢下火海”的勇气成为傈僳族的民族精神,这也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上刀山”仪式也就由三崇庙前的娱神活动演变为傈僳族的传统节日。
四、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52)习近平:《坚持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 各民族共建美好家园 共创美好未来》,《人民日报》2019年9月28日,第1版。明清以来,“上刀山”仪式的文化内涵经历了由祈求“消灾祈福,清吉平安”到纪念地方英雄王骥的演变过程,“刀杆节”也由三崇庙前的娱神活动转变为彰显傈僳族民族特色的传统节日,这与滇西傈僳族的历史迁徙和社会身份的转变密不可分。
明清时期,滇西傈僳族相继处于不同土司的管辖之下,为躲避地方土司的压榨和繁重的苛捐杂税,傈僳族选择了反抗和“逃离”的生存策略,并经历了由东向西的迁徙过程。清中后期,迁徙至滇西腾冲等地的傈僳族在当地官员和土司的招募下,与周边族群一道成为戍边守卡、保边安民的“边防卫士”。身份的转变也强化了滇西傈僳族的国家意识和身份认同。而晚清西南边疆危机进一步强化了滇西边地民族的国家意识,滇西腾越等地知识精英基于“三征麓川”的历史重塑王骥形象。王骥作为“威震滇西、保境安民”的形象融入滇西边地三崇信仰和“上刀山”仪式的民间叙事,并成为边疆民族抵抗外敌入侵、表述国家认同、建构区域历史的文化符号。在近代滇西边地的民族国家建构中,作为帝国“臣民”的腾越边关傈僳族借用王骥形象表达身份认同和国家意识,从而主动融入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历史叙事。“刀杆节”的王骥叙事也基于族群历史的建构强化了滇西傈僳族由“逃离”族群到帝国“臣民”的身份认同。20世纪70年代以来,滇西腾冲等地陆续恢复了三崇庙前的“上刀山”仪式,而傈僳族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此后,“刀杆节”成为傈僳族的传统节日和文化符号,并在傈僳族的历史、文化和民族精神的建构中发挥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