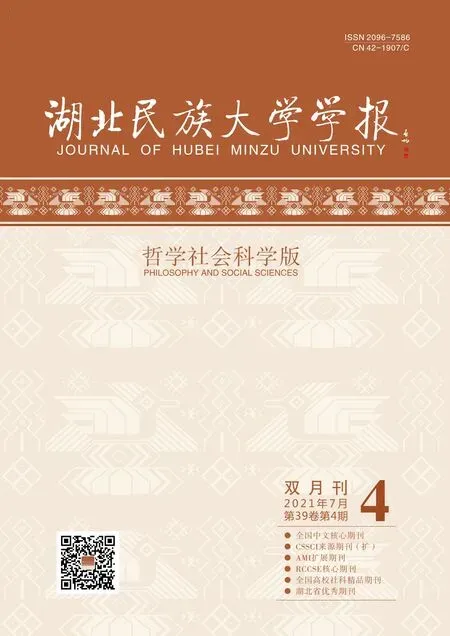概念民族志:基于欧文·戈夫曼的探讨
王晴锋
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既是社会理论家和社会批评家,同时也是研究自身所属文化的人类学家和民族志学者,他被誉为“20世纪最出色的社会科学实践者之一”(1)Greg Smith, Erving Goffma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p. 1.。在很多人看来,戈夫曼是日常生活的阐释者和细节观察的高手。在近三十年的学术生涯里,戈夫曼致力于探究那些尚未被正式命名且无法言说的现象,即日常生活中面对面互动的过程及其动力学机制。正因如此,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称他是“无穷小世界的发现者”(2)Pierre Bourdieu, “Erving Goffman, Discoverer of the Infinitely Small,” Theory, Culture, and Society, vol.2, no. 1, 1983, p. 112.。戈夫曼亦认为自己是“微小实体的民族志学者”(3)Jef C. Verhoeven, “An Interview with Erving Goffman, 1980,” Research on Language and Social Interaction, vol.26, no. 3, 1993, p. 323.,践行的是一种“休斯式都市民族志”(4)Jef C. Verhoeven, “An Interview with Erving Goffman, 1980,” Research on Language and Social Interaction, vol.26, no. 3, 1993, p. 318.。自从20世纪50年代末出版《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以来,戈夫曼的论著颇受世人关注,尤其是他关于被污名化者和在精神病院进行的民族志研究给人以深刻印象。作为一位经验研究者,戈夫曼具有很强的理论取向,极为重视民族志的理论探索,其民族志的重要特征是在对互动系统进行细致观察和描述的基础上生成理论。
民族志既是一种社会研究方法,也是一种书写方式,它强调行动及其意义是具体情境中主体互动和集体协商之结果。近些年来,海内外学术界不断拓展关于民族志的理论与经验研究。国内人类学、民族学与社会学等学科除了从一般意义上探讨民族志科学范式的转换以及方法论反思之外,还提出了新的民族志范式,诸如主体民族志、感官民族志、线索民族志以及虚拟民族志等,在经验研究领域更是涌现出大量民族志研究文本,其中包括不少开拓性的海外民族志。总之,民族志已成为学术界重要的知识生产领域。早在20世纪40、50年代之交,戈夫曼在英国北部的设特兰岛开展人类学田野研究。与传统民族志写实性的书写策略和专注于个案的研究不同,戈夫曼的民族志更多地是为了阐释,它广泛采用虚实结合的资料,不仅关注现实本身,如精神病人的处境、污名者的遭遇、赌徒的心态、女性的社会地位等,而且设法将现实的要素概化,从而提炼出普遍性的概念与理论框架。本文通过系统性地解读戈夫曼的经验研究,旨在探讨一种独特的民族志类型,即“概念民族志”。正是通过这种研究方法,戈夫曼用他锋利灵巧的“概念解剖刀”解析日常生活的复杂肌理。概念民族志的提出,不仅概括了戈夫曼研究社会事实的一种重要方法,而且也可以回应认为戈夫曼的社会学缺乏经验细节的批评。
一、学术渊源与民族志特质
戈夫曼受教于芝加哥大学社会学派,他的研究取向也深受其影响。除了美国本土的社会思想之外,通过芝加哥大学诸先辈,戈夫曼也感受到西欧传统社会科学的魅力。早在芝加哥大学的研究生时代,戈夫曼就很有个人见地,他还曾获得一个绰号——“短匕”。戈夫曼的民族志有其独特之处,无论是设特兰岛上的田野调查还是内华达赌场的参与式观察,抑或是对圣伊丽莎白精神病院开展的民族志研究,他都颇为注重对生活进行细致敏锐的体验式观察。大体而言,戈夫曼践行的是一种“本土民族志”或“在地民族志”,它很好地结合了经验与理论、事实与阐释,并通过将熟悉的事物陌生化、异常或越轨的行为正常化等策略,从而达到重新认识社会现象之目的。
(一)芝加哥社会学传统
20世纪30年代,在美国的芝加哥社会学派中,赫伯特·布鲁默(Herbert Blumer)综合了从乔治·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到查尔斯·库利(Charles Horton Cooley)的理论传统,形成了符号互动论。埃弗雷特·休斯(Everett Hughes)则首次将社会学的田野工作系统化,使之成为一种严谨的、具有正当性的社会研究方法。1945—1953年,年轻的戈夫曼在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在此期间,他深受休斯、劳埃德·沃纳(Lloyd Warner)等人的影响。通过芝加哥学派,戈夫曼又间接地受到米德(现实的社会建构)、涂尔干(日常仪式的观念)和齐美尔(形式社会学)等学术巨擘的思想熏陶。大体而言,布鲁默关于符号互动论的理论假设(尤其是关于客体的意义共享)、休斯提出的一整套建立在长期观察基础上的资料搜集技术以及以参与观察为主的民族志构成了戈夫曼社会研究方法的前提与基础。(5)Philip Manning, “Three Models of Ethnographic Research: Wacquant as Risk-Taker,” Theory and Psychology, vol.19, no. 6, 2009, p. 763.
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芝加哥大学的不同学科和学术阵营之间尚未壁垒森严,尤其是社会学与人类学在学科与机构设置中很好地得到融合。不同学者之间互通有无,避免画地为牢。社会生态学、社会组织学、阶级分析、都市研究、人类学田野调查等不同的研究取向自由结合,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之间也没有形成严格对立。戈夫曼那一代芝加哥大学的学生广泛地选修各类课程,也阅读学术刊物上所有不同研究取向的论文,而田野研究则是他们教育历程里的重要成年礼。戈夫曼的两位学术导师(休斯与沃纳)力主无论在方法论还是在学科设置上,社会学与人类学都不应该割裂开来。(6)Michael Pettit, “The Con Man as Model Organism: the Methodological Roots of Erving Goffman’s Dramaturgical Self,” History of the Human Sciences, vol.24, no. 2, 2011, p. 143.因此,在戈夫曼身上,人类学与社会学之间没有明显的界限,他可以自如地跨越。
但在这一时期,美国社会学界也出现另一股趋势,它表现为专业化倾向愈演愈烈。定量研究的兴起也与芝加哥大学社会学派的地位衰落有关,当时哥伦比亚大学在保罗·拉扎斯菲尔德(Paul Lazarsfeld)的带领下逐渐兴起,成为全美社会学界最有影响力的大学,拉扎斯菲尔德方法论也一度成为美国社会学的核心。20世纪40、50年代,问卷调查开始成为主导性的研究模式,这表明该时期社会学家的科学化意图。相当部分的芝加哥学者追随这股学术潮流,因此,芝加哥社会学派逐渐分裂成定量与定性两个不同的派系。20世纪50年代初,由于巨额科研经费的投入,作为芝加哥社会学派传统的定性研究尚能继续与拉扎斯菲尔德倡导的定量社会学分庭抗礼,此后,芝加哥大学的学术取向越来越定量化。与这种趋势不同,戈夫曼以及他的主要导师代表了芝加哥大学定性研究的传统。但是,作为芝加哥大学民族志社会学代表人物的休斯并不排斥定量数据,沃纳也强调调查和统计的重要作用。20世纪50年代,戈夫曼先后进行了多项参与式观察研究,这培养了他对日常生活极其敏锐的经验感知,也影响了后来以具体的经验研究为基础、以普遍性的理论建构为宗旨的学术研究路径。
(二)戈夫曼的民族志特质
戈夫曼的民族志很好地结合了理论研究与经验调查。菲利普·曼宁(Philip Manning)曾认为存在两种不同风格的戈夫曼,即“欧式戈夫曼”与“美式戈夫曼”(7)Philip Manning, “Credibility, Agency, and the Interaction Order,” Symbolic Interaction, vol.23, no. 3, 2000, pp. 283-297.。前者追求关于互动秩序之抽象和一般化的理论体系,表现为安东尼·吉登斯所说的“系统性社会理论家”(8)Anthony Giddens, “Goffman as a Systematic Social Theorist,” in P. Drew and A. Wootton eds., Erving Goffman: Exploring the Interaction Order, Cambridge: Polity, 1988.;后者主要进行参与观察和经验研究,表现为“休斯式都市民族志学者”。作为戈夫曼在芝加哥大学时期的导师,休斯认为戈夫曼式研究方法的实质是“(首先)进行细致地观察,将行为置于‘微小’却是戏剧性的和至关重要的情境中进行描述,然后采用精致的、非定量的方法,将其外推至更大范围的关于物的体系”(9)E. C. Hughes, “Review of ‘Interactive Ritual’,”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75, 1969, p. 425.。
通过民族志研究,戈夫曼希望能够描述日常生活中社会互动的本质单元,揭示这些单元内部或不同单元之间的规范性秩序。为此,他提出“严谨民族志”的主张,其主要目标是“辨析当一个人进入另一个人的场景时,产生的无数行为类型和自然序列”(10)Erving Goffman, Interaction Ritual: Essays on Face-to-Face Behavior, New York: Pantheon, 1967, p. 2.。戈夫曼颇为推崇行为学家的研究方式,将自然主义式观察作为首要研究方法,它包括各种非正式访谈、无意中听到的谈话片段等,该方法的要旨是将被观察的行为置于自然状态的环境里不加任何干扰。自然主义式观察既可以是系统性的,如戈夫曼对设特兰岛和精神病院的长期田野研究;也可以是非系统性的,如戈夫曼对日常生活的体验式观察,这是一种主体性的经验感悟,它是时刻都在进行中的生命经历。从这些系统性或非系统性的观察中,戈夫曼提炼出新的概念和阐释框架。
在戈夫曼看来,“激进的民族志必须将寻常人所做的寻常事作为核心议题”(11)Erving Goffman, Relations in Public: Microstudies of the Public Order,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1, p. 260.。他的社会学研究对象包括骗子、赌徒、罪犯、精神病人、间谍、污名携带者以及形形色色的越轨者。在《收容所》(Asylums)里,戈夫曼指出研究这些人的恰当方法是参与观察。
我始终认为,由这些个体——囚犯、原始人、领航员或病人等——构成的任何群体产生了一种他们自身的生活,你一旦靠近它就会变得富有意义、合情合理和正常的,研究任何一种这样的世界的恰当方法是与群体成员一起共同经历他们在日常生活中遭遇的各种琐碎的偶然性。(12)Erving Goffman, Asylums: Essays on the Social Situation of Mental Patients and other Inmates, New York: Anchor, 1961, pp. ix-x.
在三十年的学术生涯里,戈夫曼主要对三个地方进行了参与式观察,即英国北部的设特兰岛、美国华盛顿的圣伊丽莎白精神病院以及拉斯维加斯的赌场。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戈夫曼还专门对加州伯克利的赫里克纪念医院(Herrick Memorial Hospital)进行观察。他仔细研究住院实习医生、护士以及主治外科医生的角色,尤其是外科手术室的医护人员之间的互动与沟通,以论证他关于“角色距离”的概念。当很多社会学家在书斋里埋头编织宏大的社会理论时,戈夫曼“正在设特兰岛透过农舍小窗注视着外面发生的一切,或在封闭、隔绝的病房里与紧张症患者一起解烟瘾,或在拉斯维加斯的各大赌场里抛头露面”(13)Laurie Taylor, “Erving Goffman,” New Society, no. 5, 1968, p. 835.。与很多民族志学者和定性研究者主要依靠第一手田野观察和访谈记录不同,戈夫曼的民族志广泛采取不同类型的资料来源,通过比较的方法淬炼新的概念,提出新的理论体系。他关于精神病人的民族志也建立在有关互动组织的理论观念之基础上,诸如“全控机构”“道德历程”“隐秘生活”“次级调适”等。凭借着敏锐的现实感受力和极强的概念提炼能力,戈夫曼期望自己的研究提供的是“一种视角,而非照片”(14)Gary Alan Fine and Daniel D. Martin, “A Partisan View: Sarcasm, Satire, and Irony as Voices in Erving Goffman’s Asylum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thnography, vol.19, no. 1, 1990, p. 95.。
二、概念民族志:认识论与方法论
戈夫曼式社会研究的特点在于它是聚焦于生活经验的观念性研究。在戈夫曼那里,概念框架是抓住重要现实维度的合成性法则,他试图通过概念赋予现实以秩序性。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戈夫曼强调对互动行为的基本领域采取一种“松散的推测性方法”(15)Erving Goffman, Behavior in Public Places: Notes on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Gatherings, New York: Free Press, 1963, p. 4.。从整体上而言,尽管戈夫曼无意建构宏大抽象的理论体系,但他确实致力于提出在一定范围内适用的关于互动秩序的分析框架。
(一)认识论基础
概念是重要的思维工具,它不断地推进戈夫曼对现实的思考,同时也是其理论建构的基础。戈夫曼提出的关于面对面互动的观念框架类似于齐美尔抽离出的关于社会交往的形式,这些形式概念更多的是韦伯意义上的理想类型。戈夫曼认为,既有的“通俗的概念装置”不足以阐释日常互动的特征,而且概念和术语通常以某种先后逻辑次序逐渐发展,但线性陈述可能会对循环发生的事件特征产生限制。对戈夫曼而言,框架分析的问题不在于线性描述,也不在于那些权宜性的术语和定义,而是一旦引入已经承载太多意义和关系的术语,它就会被不断地再运用于已经被运用过的论述,导致研究变得更加错综复杂。(16)Erving Goffman, Frame Analysis: An Essay on the Organization of Experience,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4, p. 11.为此,他提出了一系列概念,其中很多源自日常用语,他将这些常用词汇转变成学术用语,或组合成分析性的概念,使之获得新的学术生命。这些词本身不难理解,它们能够使读者较为容易地进入文本世界。戈夫曼还大量采用隐喻式理论概念,诸如“拟剧论”(角色理论)、“游戏/博弈”(马基雅维利式操控、算计)以及“仪式”(关心、尊重与体谅)等。
这些概念作为认知中介,在常人与专家、读者与作者之间架起了桥梁。在这之前,人们熟悉生活世界的常识,却不知如何谈论它。人们通常不会刻意地去思考他们的生活经验,这一方面是由于习以为常,另一方面是缺乏相应的话语体系,从而使这些经验处于意识的边缘和模糊的认知状态。戈夫曼通过细节观察以及反常识、反直觉的思维方式,提炼出新的概念,为谈论、分析与反思日常经验提供了可能。由此,他对生活经验进行了梳理、命名和定义,区分和明辨社会生活里尚未被发现的各类社会单元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因此,戈夫曼强调概念性区分的重要性。
我热切地渴望作出一些概念性的区分(虽然不是像理论那样显得雄心勃勃),它们表明我们在揭示那些能够精简和整理、描述普遍性类别——其构成要素共享诸多特性,而不仅仅是某种资格上的相似性——的基本变量中发挥着一定的作用。若要这样做(即概念性区分),我认为必须从行为的某个独特领域的民族学或学术性的经验出发,然后沉浸于任何有助益的文献,朝着不可预期、但大致明确的方向行进。其目标是遵循概念(或一小撮概念)的指引之处。正是这种演进式发展,而不是叙述或戏剧,起着决定性的作用。(17)P. M. Strong, “Minor Courtesies and Macro Structures,” in P. Drew and A. Wootton eds., Erving Goffman: Exploring the Interaction Order, Cambridge: Polity, 1988, p. 229.
概念性区分能够整顿、阐明和反省经验材料,以新的方式发现和理解被熟视无睹的互动系统。例如,在《污名》里,戈夫曼区分了很多概念,它们包括“社会身份”与“个人身份”“声望符号”与“污名符号”“认知识别”与“社会识别”等(18)Erving Goffman, Stigma: Notes on the Management of Spoiled Identity, New Jersey: Prentice Hall, 1963, p. 41.;同时,他还使用在各类自助手册、自传和励志书籍中出现的第一人称叙述,以证明某个概念的潜在效度。
相互关联的概念与观察框架之间未必完全契合,任何概念都无法涵括社会实在的总体性与复杂性,科学的表述也可能是主观的或局部的。也就是说,概念并无法全面或一劳永逸地反映现实,它们是以粗糙的方式呈现或逼近事实。因此,概念仅是权宜性的思维工具,它无法取代现实本身。这是为何戈夫曼不断地提出新的概念和术语并对之采取“用毕即弃”态度的原因。一方面,概念是建构理论和认识现实的手段,是思维的“拐杖”和理论体系的“脚手架”;另一方面,戈夫曼试图通过从不同的视角“多次切入”现实进行复调式描绘,以尽可能地接近生活世界本身。戈夫曼还认识到概念形成的任意性,但他认为这种“任意性”对现实和理论探索而言是必要的。这是戈夫曼关于社会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的认识论基础。
戈夫曼指出,每一个社会学概念“必须追溯至最适合于运用它的地方,遵循着它所引导的方向并揭示它具有的其他含义”(19)Erving Goffman, Asylums: Essays on the Social Situation of Mental Patients and other Inmates, New York: Anchor, 1961, p. xiv.。戈夫曼承认他对初始概念和术语的处理方式是“抽象的”,并且从现代哲学的标准来看,“对它们的阐述和界定是粗糙的”(20)Erving Goffman, Frame Analysis: An Essay on the Organization of Experience,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4, p. 10.。在理解瞬息万变的现实世界的过程中,需要不断地对这些粗糙的概念进行反思、锤炼、扬弃,不断地创造出更贴切、敏感度更高的概念。戈夫曼通常从一些“世俗概念”(lay concepts)出发,但他不满足于这些概念,在研究新的主题时往往“另起炉灶”。对戈夫曼而言,没有一种概念是终极的,因此不能要求他一以贯之地使用同样的概念术语。通过汲取社会学、人类学、动物行为学以及心理学等不同学科的思想,戈夫曼构造出一系列概念“脚手架”。这些临时搭建的“脚手架”其真正意图是建造互动秩序的理论大厦,也即概念是构造思想系统的“建材”,而戈夫曼正是面对面互动思想体系的“建筑师”。
正因如此,即使是对于为他带来极高学术声誉与社会声望的拟剧论,戈夫曼也持谨慎态度。早在20世纪50年代末,戈夫曼已经指出拟剧论或戏剧隐喻存在的方法论局限性,他提醒人们注意关于拟剧论的概念框架仅仅是一种类比,是修辞与策略。拟剧论作为一种概念工具,它与现实之间存在区别,这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的序言里表述得颇为清楚。在该书的最后,戈夫曼又明确指出:“舞台语言和面具终将脱落。”(21)Erving Goffman, 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 Garden City, New York: Anchor, 1959, p. 254.而在二十年后《谈话形式》的开篇,戈夫曼写到:“这里详细阐述的每一个概念都可能不会有将来。”(22)Erving Goffman, Forms of Talk,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81, p. 1.从这种意义上而言,戈夫曼的概念是“自毁性的”,它们是理论建构过程中的过渡性手段。总之,戈夫曼民族志中的经验描述是以概念为导向的,同时这种概念本身不是最终目的,它是言说和理解现实世界的认知工具。
(二)方法论地位
在社会学分析中,概念的形成与社会事实的确定性等基本议题涉及根本性的认识论问题。戈夫曼的概念民族志体现了自狄尔泰、文德尔班和李凯尔特等人以来的人文阐释学传统。(23)Philip Manning, Erving Goffman and Modern Sociology, Cambridge: Polity, 1992.在戈夫曼看来,“概念的有效性不仅取决于实践运用,而且还取决于彼时的实地状态和行为特征等因素”(24)Jef C. Verhoeven, “An Interview with Erving Goffman, 1980,” Research on Language and Social Interaction, vol.26, no. 3, 1993, p. 327.。戈夫曼的民族志通常没有大量引用主体的话语,它不是科林·杰罗马克(Colin Jerolmack)和夏莫斯·卡恩(Shamus Khan)所批评的“基于说明的研究”(account-based studies)(25)Colin Jerolmack & Shamus Khan. “Talk Is Cheap: Ethnography and the Attitudinal Fallacy,” Sociological Methods & Research, vol.43, no, 2, 2014, pp. 178-209.。戈夫曼认为,若要理解社会行动的意义以及它与说明之间的关联,最有效的方式是直接观察面对面互动,而不是通过被研究者的“自我说明”,也即援引主体的话语,因为个体在不同时空中的态度以及潜在的观念、看法与显在的行为之间很可能出现内在不一致。
戈夫曼意识到,通过社会学方法获得的知识本身具有脆弱性。概念的运用、发展与数据处理等都离不开分析,但分析本身的脆弱不仅在于其起点上的任意性,而且在于它的建构包含着诸多实践与理论困境。(26)Robin Williams, “Understanding Goffman’s Methods,” in P. Drew & A. Wootton eds., Erving Goffman: Exploring the Interaction Order, Cambridge: Polity, 1988, p. 85.在《公共场所的关系》的前言里,戈夫曼认为那些专注于“假设—验证”的社会学家正在上演一种“移情戏法”(27)Erving Goffman, Relations in Public: Microstudies of the Public Order,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1, p. xvi.,仿佛遵循着实验操作步骤按图索骥,就能成为一名真正的科学家。社会生活的发现远非如此机械、简单。戈夫曼反对在实验室里研究社会互动,因为此类研究的诸变量是人为设计的,它们并不存在于实验室之外的真实场景里。“通过这些方法,没有揭示自然主义研究的领域;也没有产生新的概念能使我们重新整理关于社会活动的观点,更没有确立能连续不断地将大量事实置于其中的新框架。我们对普通行为的理解没有增加,反而变得更加疏离。”⑦
戈夫曼使用不同研究资料的意图不是对某种独特的社会设置进行精确或事无巨细的描述。例如,在《框架分析》中,他援引的虚构事例“不是为了事实,而是为了类型化”(28)Erving Goffman, Frame Analysis: An Essay on the Organization of Experience,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4, p. 14.。戈夫曼将这种虚构的事例严格限制在概念特征的阐释性范围内,而不是通过它对概念或结论进行合法性的论证或辩护。因此,在戈夫曼的民族志研究里,“思想观念是第一位的,其次才是人和地方”(29)Javier Trevio, “Introduction: Erving Goffman and the Interaction Order,” In Javier Trevio eds., Goffman’s Legacy, New York: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3, p. 31.。不同于帕森斯气势恢宏的关于社会结构及其过程的理论体系,戈夫曼的概念民族志关涉互动细节,并显得更加实用主义。譬如,戈夫曼对拟剧论的核心术语“表演”作了不同的定义。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里,它的定义较为宽泛,指“既定场合的参与者以任何方式影响其他参与者的所有活动”(30)Erving Goffman, 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 Garden City, New York: Anchor, 1959, p. 15.。在拟剧论的构成里,剧场提供了一种基本的观念性区分,它区分了社会生活中的个体行动者和舞台上的表演者以及个人与身份(个体在不同场合履行的特定功能)。在《框架分析》中,戈夫曼也区分了舞台行为和现实生活,但他在限制性的意义上使用“表演”这个术语,它是指“将个体转化为舞台表演者的设置安排”,而舞台表演者则是这样的对象,即“可以被扮演‘观众’角色的人们置于剧场中央的舞台上,进行全方位地、详细地端详而不致于构成冒犯,并期待着引人入胜的表现”(31)Erving Goffman, Frame Analysis: An Essay on the Organization of Experience,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4, p. 124.。这些定义已经没有了原先的隐喻色彩,它们是不带夸张意味的平实表述。
三、形式概念及概念民族志的生成
为了阐释人际互动的微观秩序,戈夫曼通常先提出关于面对面互动的定义和分类体系,然后聚焦于与初始定义和分类无法契合的实例,从而调整、改变原始的定义和分类以涵括这些异质性和分歧性的个案,同时继续探讨不符合新的定义和分类的例外。在如此不断地进行比较和修正的过程中,戈夫曼的概念图式呈螺旋式上升状态:定义、分类、举例、例外、弱点、新定义……,菲利普·曼宁将这种策略概括为“戈夫曼螺旋”(32)Philip Manning, “Resemblances,” History of the Human Sciences, vol.2, no. 2, 1989, p. 230.;罗宾·威廉姆斯(Robin Williams)则称之为“交互式双重契合”,这种交互发生在经验观察和概念模型之间(33)Robin Williams, “Understanding Goffman’s Methods,” in P. Drew & A. Wootton eds., Erving Goffman: Exploring the Interaction Order, Cambridge: Polity, 1988.。戈夫曼创造概念图式的各个步骤之间具有层次递进性,它们并非处于同一个平面上。既有概念或模型的局限性、数据的异值等能反映出一般情况下难以察觉的重要信息。在不少学者看来,将例外的事物作为论证基础似乎有问题,但戈夫曼认为,社会研究必须得出一些权宜性的结论,而现阶段能做的最好的事情是“弄清楚从其基本形式那里获得意义的各种变体”(34)Erving Goffman, Relations in Public: Microstudies of the Public Order,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1, p. 183.。也就是说,对于戈夫曼的交互螺旋式演进的思维方法而言,关键不在于证伪。为了获得更好的认知效果,戈夫曼在追求精致的概念和忠于经验细节之间达成了某种妥协,即在“分析性的简洁和经验的冗杂之间采取一种实用主义的折衷态度”(35)Philip Manning, Erving Goffman and Modern Sociology, Cambridge: Polity, 1992, p. 16.。
通过在社会事实与抽象观念之间反复穿梭的方式,戈夫曼不断地接近他试图描述的现象,并确立某种普遍性的联系。他新创造的概念“以一种原则性的方式继续培育和更新原有的思想,将概念发展和社会学发现的机会最大化”(36)Greg Smith, Erving Goffman,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p. 121.。在这种分析过程中,原先粗略、含糊和未定型的解释框架通过重新定义逐渐形成明确而稳定的结构,并获得更具普遍性的特征。有些形式概念及其意象的运用非常广泛。
戈夫曼将博弈的意象几乎运用到他能够染指的一切事物……由蜚短流长、关于谎言的谎言、荒诞不经的真相、恐吓威胁、折磨拷问、收买贿赂和敲诈勒索所构成的间谍世界被解释为一种“表意性游戏”;……礼仪、交际手腕、犯罪、金融、广告、法律、诱惑以及日常生活的“调侃性礼节的领域”则被视为“信息博弈”——关于演员、剧班、行为举措、位置、信号、信息状态、孤注一掷以及结局等迷宫般的结构,这其中只有“具备相当的博弈水准”——那些愿意并且善于“掩饰任何事物”的人,才能成功。(37)Clifford Geertz, Local Knowledge,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3, pp. 24-25.
早在1953年的博士论文里,戈夫曼已经指出初始的术语是为后来的术语奠定基础,它们的旨趣并不在其本身。(38)Erving Goffman, “Communication Conduct in an Island Community,”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53, p. 8.这是一个在不断试错中双重适应的过程,尤其是通过寻找反例来完善原有的逻辑框架。因此,戈夫曼提出的很多概念都具有“蠕变效应”,它们最初只是用于客观地描述日常经验组织的某种现象,但是到后来会逐渐发现,倘若缺乏这些概念将无法理解这些社会事实。随之,这些概念和术语也登堂入室,成为专业的学术语言。作为一位形式社会学家、概念的提供者和阐释者,戈夫曼在其论著里枚举的大量事例都是为了阐明并精细化概念和分类,以增强其对互动行为的解释效力,而这些定义和分类本身逐渐上升为一种中层理论。创造概念需要现实的综合概括能力与理论的抽象能力,如同齐美尔一样,戈夫曼遵循归纳逻辑,从具体的经验内容中抽象出社会交往的形式。例如,他强调关于设特兰岛研究运用的术语与概念“不是产生于事实之前,而是之后”(39)Erving Goffman, “Communication Conduct in an Island Community,”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53, p. 9.。因此,处于正在形成过程中的概念组织与通过实地调查搜集到的资料之间存在一种互动关系。戈夫曼试图用这一整套术语和概念工具捕捉和锚定现实。他的分类法或概念体系旨在勾勒出某种现象的普遍性特征,而不是提供具体的概念标准,这种探索性研究与布鲁默的“敏感性概念”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大体而言,概念民族志是以田野调查和实践感为基础,以理想类型为升华工具,以提炼概念和普遍性的解释框架为宗旨的民族志研究范式。概念民族志类似于中层理论,其特点在于以概念为核心,这些概念是对经验事实的理论提炼与抽象概括,代表着对普遍性解释框架的诉求。戈夫曼的概念民族志有两个典型的特征或表现形式。第一,资料来源丰富多样,体裁不拘一格,从大众流行的小说、杂志、新闻简报到严肃的学术研究,都成为概念民族志的资料库。戈夫曼的大多数著作都充分体现了其研究素材的多样性,尤其是《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污名》和《框架分析》等。第二,通过将纷繁复杂的数据资料进行比较、类型化而提出理想型概念,并以一般化的理论为导向。例如,在《收容所》里,“全控机构”不仅指向精神病院,而且还包括修道院、军营、寄宿学校、监狱甚至集中营等不同的机构设置形式。通过实地调查,戈夫曼对精神病院这一原型进行描述、概括和升华,提炼和分离出普遍性的特征要素,这些要素也可以运用于其他社会机构。
戈夫曼关于全控机构的研究可以被视为概念民族志生成的典范。1954年,戈夫曼完成博士论文之后,加入了美国的国家精神卫生研究院“社会与环境研究”实验室,对一些临床中心进行参与式观察,在这期间,他甚至与病人共同生活。这些关于病房行为的田野研究后来用于《论恭敬与风度的本质》一文。(40)Erving Goffman, “The Nature of Deference and Demeanor,”American Anthropologist,vol. 58, no. 3, 1956, pp. 473-502.1955年,戈夫曼举家迁往华盛顿附近,以便对当地的圣伊丽莎白医院开展为期一年的田野研究。圣伊丽莎白医院是当时全美最大的精神病机构,有超过7000位住院病人。戈夫曼在医院里担任体育部主任助理,这一特殊的身份使他有机会接触到整个机构的各个部门。在戈夫曼开展研究之时,几乎所有关于精神病人的专业文献都是从精神病医生的视角来书写的,而戈夫曼则站在精神病人的立场上,从病人的视角看待精神病院的生活世界。戈夫曼采取以参与观察为主的民族志方法,认为定量研究无法收集到“病人生活的组织与构造”(41)Erving Goffman,Asylums: Essays on the Social Situation of Mental Patients and other Inmates, New York: Anchor,1961, p. x.。
概而言之,戈夫曼关于全控机构的研究包括三个方面:首先,具体阐述其潜在的结构及其运作;其次,厘清不同类型的被收容者的典型经验;最后,为病人描述一种预期性的社会心理障碍序列。(42)Philip Manning, “Three Models of Ethnographic Research: Wacquant as Risk-Taker,” Theory and Psychology, vol.19, no. 6, 2009, p. 767.戈夫曼几乎没有对他开展研究的圣伊丽莎白医院提供背景性的资料和说明,也没有如传统民族志叙述那样大段地援引信息提供者的话语。因此,《收容所》被指责为是“随意的、方法论上不够严谨周密,甚至无法可信地提供关于社会机构的状况”(43)Gary Alan Fine and Daniel D. Martin, “A Partisan View: Sarcasm, Satire, and Irony as Voices in Erving Goffman’s Asylum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thnography, vol.19, no. 1, 1990, p. 94.。正是由于戈夫曼很少呈现原始的田野记录,批评者认为他的叙述风格更像是一种“准民族志”。但正如菲利普·曼宁所指出的,《收容所》“不是一项对特定精神病院的民族志研究,它更多的是对‘全控机构’这一概念本身的研究”(44)Philip Manning, Erving Goffman and Modern Sociology, Cambridge: Polity, 1992, p. 9.。也就是说,戈夫曼最终的意图是探讨一般意义上的思想观念,而非独特的个案。他的总体目标是将关于场所的民族志转变成关于概念的民族志,圣伊丽莎白医院的住院制度文化是他次要的考量目标。戈夫曼关注的是制度性权力,而不是精神病学家的诊治能力或精神病机构的独特性,他的理论旨趣远比他关于圣伊丽莎白医院的观察和描述重要。正因如此,戈夫曼没有详细交代医院本身的情况,如它的组织构成、空间结构以及历史变迁等,也不关注病人特殊的个人经历。然而,戈夫曼在《收容所》里发展而来的一整套术语和概念可以用于描述与被制度化的精神病人遭遇类似情境(时空不间断地受到监控)的任何群体。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戈夫曼扩展了我们对民族志研究的理解。
四、概念民族志对“经验假象”之回应
由于戈夫曼追求普遍性的解释框架,无论是虚构还是真实的事例,在他那里都可以成为阐释性的工具。在学术生涯的后期,戈夫曼更加倾向于抽象性的思辨,譬如,《谈话形式》里甚至虚构了很多谈话情景。然而,此类研究往往给人以经验性不足甚至不是民族志文本的印象,或者缺乏社会研究应有的科学性。而拟剧论探讨剧本、舞台设置、表演工具箱等,也让人以为它谈论的是观念化的现实,而非社会实在本身。对此,理查德·桑内特(Richard Sennett)批评戈夫曼的世界“有情境无情节”“有行为无经验”(45)Richard Sennett, The Fall of Public Man, New York: Penguin Books, 2002, p. 36.。菲利普·冈萨雷斯(Phillip Gonzales)认为戈夫曼的分析更多地基于经验话语而非真实的经验(46)Phillip Gonzales, “Shame, Peer, and Oscillating Frames in DWI Conviction: Extending Goffman’s Sociological Landscape,” Symbolic Interaction, vol.16, no. 3, 1993, p. 269.,所有细节都消失了,只剩下概念和分类。类似地,安东尼·吉登斯也认为戈夫曼的社会学缺乏“深描”,忽视个体行为和活动周围的细节。(47)Anthony Giddens, “Goffman as a Systematic Social Theorist,” in P. Drew & A. Wootton eds., Erving Goffman: Exploring the Interaction Order, Cambridge: Polity, 1988.戈夫曼关于尴尬、自尊和羞耻的分析亦缺乏大量的细节研究,它的观点仅是启发性的。(48)Philip Manning, Erving Goffman and Modern Sociology, Cambridge: Polity, 1992, p. 169.而且戈夫曼还以概化的方式处理互动的道德特性。常人方法学和会话分析学对戈夫曼的批评尤为激烈,认为他在具体分析中低估甚至忽略细节性、经验性的研究,论证过程过于抽象,缺乏真正的经验事实,这导致戈夫曼分析性的观察与描述更多地是一种“点画法”(pointillism)和一种“缩影社会学”。(49)Emanuel Schegloff, “Goffman and the Analysis of Conversation,” in P. Drew & A. Wootton eds., Erving Goffman: Exploring the Interaction Order, Cambridge: Polity, 1988, p. 101.总之,戈夫曼的社会学具有高度概括和浓缩的经验叙事风格,但它却给人以充斥着大量事实的经验主义印象。对此,伊曼纽尔·谢格洛夫(Emanuel Schegloff)以充满嘲讽的口吻进行解释。
这是一种强大的方法;它将读者套上轭,然后朝着其目的行进;它拨动着读者的心弦和过去的经验……他的观察实现了他们对典型性(typicality)的感知,无论真实的场景多么迥异,通过一两笔、一两次观察、一两个细节,暗示着作为读者的我们从记忆中、从个人经验或想象中唤醒这些场景。倘若他成功了,那是因为我们在脑海里成功地召唤起这样的场景,我们从他展示的一两个细节就能这样做的能力正是这种典型性的“证据”。场景或行动的典型性不仅得到了“展示”,而且还被征集和利用,从而展现他对局部特征化的充分描写。倘若他和我们都失败了,也并不会有多少损失。任何“个案”只不过是一两句话;尽管如此,仍然很可能是我们弄错了,因为我们知道他是一位多么敏锐的观察者;尚且,在诸多的其他情形下,还有剪报、实例、插图等。(50)Emanuel Schegloff, “Goffman and the Analysis of Conversation,” in P. Drew & A. Wootton eds., Erving Goffman: Exploring the Interaction Order, Cambridge: Polity, 1988, pp. 101-102.
在谢格洛夫看来,戈夫曼通常仅是提供一些概括性的经验描述,正是读者通过回忆和想象将它们栩栩如生地还原到自己曾经历的现实场景,并自动填充所有具体的经验事实。“过剩的案例以及当我们通过他布置的典型化的细节想起各种场景时,我们获得了比他所提及的更多‘细节’,这使戈夫曼的著作及其场景充斥着各种细节。”(51)Emanuel Schegloff, “Goffman and the Analysis of Conversation,” in P. Drew & A. Wootton eds., Erving Goffman: Exploring the Interaction Order, Cambridge: Polity, 1988, p. 102.由于戈夫曼研究的是他自身所属的社会,评论者和读者也大多共享着同样的经验与文化,戈夫曼完全可以假定人们知道他要谈论的事实。(52)Richard Handler, “Erving Goffman and the Gestural Dynamics of Modern Selfhood,” Past and Present, Supplement 4, 2009, p. 290.因此,每位读者眼里都有着不同经验程度的戈夫曼,是读者自身成就了作为“经验研究者”的戈夫曼。
对于很多强调人类学式深描的经验研究者而言,此类批评不无道理。但是,倘若我们将戈夫曼的社会学理解为概念民族志,那么可以对会话分析学者的这种批评作出有力的回应。事实上,戈夫曼并不避讳自己的文本对读者经验的调动和组织化,相反,这正是他的意图所在:“将不同的例证共同置于内在一致的框架之中,从而将读者已经具有的经验片断结合起来。”(53)Erving Goffman, 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 Garden City, New York: Anchor, 1959, p. xii.另一方面,如本文已阐述的,戈夫曼在社会分析中枚举的事例并非为了阐明现实生活的某种社会行为或现象,而是为了表明某种普遍性的分类图式或概念。戈夫曼曾解释道,“对互动进行记录或拣选要比编造它们更容易。但是在所有情况下,它们预期的价值不是记录真实发生的事物,而是为了表明倘若它们一旦发生并具有我赋予它们的阐释意义时,将会容易得到理解”(54)Erving Goffman, Relations in Public: Microstudies of the Public Order,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1, p. 140.。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戈夫曼的概念民族志是杂乱无章的,他不是散乱地、毫无目的地提出一些孤立的概念,相反,概念民族志具有系统性地累积和不断向前推进的特征。
总之,戈夫曼的主要角色是一位试探性的概念提供者。(55)Gregory W.H. Smith, “Ethnomethodological Readings of Goffman,” In Javier Trevio eds.,Goffman’s Legacy, New York: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3, p. 268.他的民族志研究方法先是详尽地描述某个特定的群体或机构,然后创造出可用于比较研究的概念框架。尽管有时这些概念框架出现在先,但它们事实上产生于经验观察之后,只是在写作时置于前面。戈夫曼至始至终追求的并非琐碎的经验细节本身,而是一般化的形式理论。除了全控机构之外,戈夫曼早期关于设特兰岛的研究实际上构造了一种纯粹的“互动人”的理念。(56)Michael Schudson, “Embarrassment and Erving Goffman’s Idea of Human Nature,” Theory and Society, vol.13, no.5, 1984, p. 640.此类理想类型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时间与空间、历史与传统以及亲密关系。戈夫曼的民族志还强调概念的累积及其阐释、例证,因此它不采取古典民族志的叙述方式,其结果不是现实的文本再现,而是“现实效果”的生产。通过概念民族志,戈夫曼弥合了现实与虚拟之间的鸿沟,从而拒斥实在论民族志的封闭性叙事。
五、总结与讨论
本文以戈夫曼的社会学研究为基础,探讨了作为一种社会研究方法的概念民族志,它是以概念为核心的思维方式与研究方法,它的锤炼过程尤为注重概念图式与分类体系。在描述面对面互动系统时,戈夫曼不仅广泛地采取各种异质性的情境实例,而且还频频使用源自日常生活的各种概念与术语,这些概念是权宜性的智识建构物,进一步对它们进行形式化的分析可以修改和完善原有的概念,最终形成较为完善的分析框架。对戈夫曼而言,概念是认识现实和生成理论的工具,因此他对概念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并借此对现实保持着高度的敏感性与反思性。通过概念民族志这种独特的方式,一方面,戈夫曼的社会学获得了系统性的特征,从而使人们谈论原本被熟视无睹或不可言说之物得以可能;另一方面,由于概念在戈夫曼社会学里的这种独特属性,它也使戈夫曼的社会研究方法呈现出一种“适应性”的特征,即通过不断地自我调适、修正和扬弃接近复杂的现实生活本身。
戈夫曼的概念民族志及其实践活动诞生于20世纪50、60年代,这种努力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现代西方民族志探索的发展方向,即从传统民族志向后现代民族志转变,该趋势不断地强调反身性和主体间性,以突显研究者自身与被研究者之间的交互卷入、生命体验以及主体性阐释。在这一时期,“概念民族志”这种崭新的民族志写作范式具有重要的现实和理论价值。就戈夫曼关于精神病院的研究而言,他根据这种思维方式提出“全控机构”的概念,抽离出此类现实机构设置的核心特征,从而抓住现代西方社会运作的重要机理。就戈夫曼的整体社会学而言,概念民族志实际上涉及形式社会学的具体操作问题,即如何将细微琐碎的日常经验观察统合起来形成富有意义的学术研究,概念民族志的处理手法有助于戈夫曼实现他的理论抱负。
概念民族志也涉及研究者如何处理经验与理论之间的复杂关系。戈夫曼不仅是一位社会事实和经验材料的搜集者,更是生产者、建构者和阐释者,他不像传统的民族志工作者那样致力于全面、细致和忠实地再现研究场景。作为社会理论家,戈夫曼关注的不仅仅是获得描述性术语以及如何对它们进行操作化,而是创造各种概念和分类体系,追求形式化的社会理论。在锻造概念民族志的过程中,戈夫曼采用了理想类型的方法,描绘和确立普遍性的特征,突显其重要差异。概言之,戈夫曼的经验主义是为理论服务的,他可以被视为一位不从事纯粹理论研究的重要理论家。戈夫曼毫不隐讳他的社会研究具有探索性特征,确切而言,他是一位对熟悉而陌生的日常生活领域进行开拓性研究的先锋者,并致力于民族志的理论探索。他践行的概念民族志可以深化我们对生活世界的理解,推进新的知识探索方式,这对于我们当前正在开展的海外民族志事业不无借鉴意义。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我们面临的海外田野也是一个“熟悉而陌生”的生活世界,异域文化与华夏文化之间存在诸多异同之处;同时,海外民族志亦尚处于探索性阶段。因此,以概念为导向的民族志可以成为一种选择性的研究路径,它寻找差异,反观我们自身的文明与知识体系,在此基础上探求普遍性的解释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