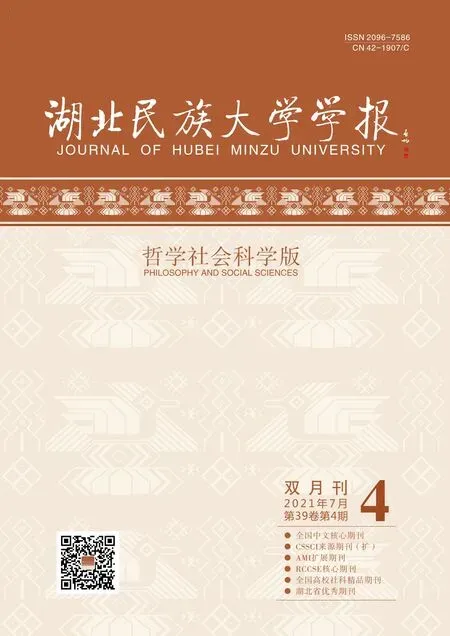空间外延与共谋逻辑:边城“庙宇—学校”的民族志研究
张智林
关于国家和地方社会之间关系的讨论一直是历史学、人类学的核心问题,而这种关系的呈现方式各有差异,庙宇作为公共空间在研究中国历史演进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也是体现二者关系的重要场域。高丙中采用民族志方法研究了河北范庄一座庙宇—博物馆的修建史,基于国家与地方社会互动的视角,讲述了地方庙宇的生存之道和合法化过程,从而探讨民众在面对社会张力和冲突等紧张关系时所表现出来的文化逻辑,进而提出“双名制”(1)高丙中:《一座博物馆—庙宇建筑的民族志——论成为政治艺术的双名制》,《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1期。作为一种政治艺术普遍存在于当代中国社会,他强调地方社会在整个实践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而关昕则考察了北京东岳庙的历史变迁过程,提出作为庙宇—博物馆的“双线叙事”(2)关昕:《民俗文化与制度宗教:庙宇博物馆的双线叙事》,《民俗研究》2016年第5期。,阐述了东岳庙内存在两套班子,二者“各行其是、貌合神离”。但无论是从博物馆民俗化还是宗教制度化的合法性而言,国家都通过不同层级、职能和管理手段体现着它的“在场性”,因此他认为国家“无处不在”,彰显了福柯意义上的权力毛细血管化。两人的研究对象皆为“庙宇—博物馆”这种具有双重乃至多重身份的建筑空间,但却在国家与地方社会互动的张力间各执一词。
从历史维度出发,河北范庄的庙宇建成至今仅仅几十年,对于反映中国社会的传统与现代、历史与当下、小圈子与大社会之间的紧张关系在解释力上略显逊色。而东岳庙所承载的泰山文化自先秦时期便成为国家符号,既反映了帝制时期的合法性与权力获得,又表明了当代背景下的合法性实践,但二人的研究忽视了重要时间节点和历史情景下的叙事。从空间类型学而言,河北范庄的“龙祖殿”属于“二合一”式空间运行模式,而北京东岳庙则是“一分二”的空间生产类型。关昕也表明在以后的空间再生产有机体研究中,不仅会有相互依存、各自生长的运行逻辑,还有一方消弭或弱化另一方凸显的空间整合过程。但是他们讨论空间微观政治都停留在从某一空间的内部寻求出路,忽视了空间所具备的“外延性”,边城庙宇的空间实践则阐述了作为方法的“空间外延”(3)本文中使用的“空间外延”是相对于“空间内部”而言,属于“空间再生产”的一种类型。。另外,二人的讨论都没有将“中央与边疆”的视角纳入自己的研究中,从地域而言他们的调查范围都处于“中央”,而如果是地处“边疆”,多重身份的庙宇空间存在何种表现则是一个问题。若从“社会生命史”“空间外延”“中央与边疆”的视域出发,则会发现国家与地方社会之间存在某种“共谋逻辑”(4)本文所使用的“共谋”概念,借鉴于周雪光的表述“在中国行政体制中,基层政府间的共谋行为已经成为一个制度化了的非正式行为;这种共谋行为是其所处制度环境的产物,有着广泛深厚的合法性基础”。本文解释为:国家与地方社会之间的“共谋”是社会发展的产物,更是社会治理的途径,国家与地方社会之间通过共同协作处理二者之间以及其他社会关系中存在的张力与博弈,这里所谓的“共谋”是一种积极的策略和解决问题之道。参见周雪光:《基层间的“共谋现象”——一个政府行为的制度逻辑》,《社会学研究》2008年第6期。,因此本文立足于此,探究国家与地方社会之间存在何种“共谋逻辑”,并阐述“空间外延”何以形成。
“庙宇—学校”与“庙宇—博物馆”不可避免在某些层面存在差别,但同样作为多重身份空间和体现国家与地方社会互动的场域,实则“异曲同工”,但边陲“少数民族地区文庙”(5)陈兴:《异域儒思——中国少数民族文庙发展概述》,《建筑学报》2017年第7期。中却隐藏了多重维度的权力关系和微观互动,更具有历史探究的意义和价值。因而本文将立足于边城文庙,深描一座“庙宇—学校”的社会生命史,利用“点、线、面”相结合的方式,试图完整地呈现边城文庙的发展全貌,通过这个具有双重乃至多重身份的建筑空间,阐明国家与地方社会之间的“共谋逻辑”。同时,在边城文庙的空间互动实践过程中,它经历了“二合一”“一分二”到“空间外延”的变化过程。因此对于边城文庙的研究既回应了国家与地方社会之间的关系,又为庙宇空间生产的讨论提供了案例,而且彰显了中央与边疆之间的联系,更为研究地方社会和区域历史提供了支撑,呈现了边地人民的生活哲学。
一、传统中的“庙学合一”
建水文庙位于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建水县,此地世居有彝、哈尼、回、傣、苗等少数民族,全县总人口55万,其中汉族与少数民族人口比例为3∶2,汉族人口约占全县总人口的60%,由于地处喀斯特地貌区,人口分布极为不均,坝区人口稠密,山区人口稀少。(6)建水县党史研究和地方志编纂办公室编:《建水年鉴》,芒市:德宏民族出版社,2019年,第61页。虽诸多文献记载称之为“极边之郡”“徼外夷地”“蛮荒夷地”(7)杨丰:《建水文庙历代碑文选注》,建水县文庙管理处编印,2004年,第2页,内部资料。,但明清时期获得了“临半榜”“滇南邹鲁”“文献名邦”(8)杨丰:《建水文庙研究资料汇编》,建水县文庙管理处编印,2002年,第14页,内部资料。等美誉,成为滇南的文化中心和高地,这种局面的形成与中央王朝的统治和治边术直接相关,自汉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便成为历代皇帝推崇的治国之道,文庙作为儒学传承和祭祀孔子的公共空间逐渐被重视。唐贞观元年(公元627年),李世民诏“天下学宫皆另立孔子庙,以左丘明等二十二人从祭”③,开创“庙学合一”的文庙建设模式之后,历代统治者开始在边陲地区大规模兴修文庙传播意识形态,以控制边疆,保证社会平稳运行。
南宋宝祐元年、蒙古宪宗三年(1253年)十二月,忽必烈率领蒙古大军进攻云南,并最终掌控云南全境。元朝统治初期,因政策不能适应地方实情,导致云南政局动荡。1273年,忽必烈委命赛典赤为云南平章政事,负责调查云南情况并推行相应政策措施,经实地考察,他提出并实行“云南内地化”(9)建水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建水文史资料选辑》第7辑,2002年,第95页,内部资料。政策。随后赛典赤因地制宜、因势利导,坚持“以夏制夷”,在云南提倡儒学,主张教化治滇,以柔性手段渗透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开启了边陲的“庙学”之路。元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赛典赤的拥护者张立道为积极响应政策,“复创庙学于建水路”。这是继昆明文庙后云南省最早的庙学(与大理文庙同时),兼具祭祀与教育双重职能。明清两代,随儒学之风兴起、科举考试繁盛,孔子地位不断提升,建水文庙内容日益丰富,形成了“一庙三学”(10)明洪武十六年(1383年),建水庙学改制为临安府学,之后临安府通判许莘进行重建,规模日渐扩大。据《元江州志》记:“元江府学建于公元1393年。”可知建水文庙此时已经形成了“一庙两学”(临安府学与元江府学)。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建水知州赵士龙请示增设州学,经巡按御史吴应琦奏请朝廷批准,于1616年增设建水州学。从此,“一庙三学”正式形成。的特有格局。这也为建水乃至整个滇南地区教育发展带来了新机遇,强化了建水文庙的学宫身份。
另外,祭祀仪式和典礼也在明清时期臻于完善。关于祭孔活动的记载最早可追溯到明朝,《重修临安府庙学碑记》载:“睢阳李公孟晊,弘治壬子秋自贵州按察佥事迁云南副使,奉敕整饬兵备,驻节临安府。……庙之祭器与乐舞,岁久亦弊。又以修葺之余力,咸一新焉。落成之日,殿宇增辉,礼献益虔,士民相庆,咸谓前此所未闻,宜有言以垂后。”(11)杨丰:《建水文庙历代碑文选注》,建水县文庙管理处编印,2004年,第8页。清朝时期祭祀内容已相对完整,嘉庆《临安府志·典礼》:“每岁仲春、秋月,文武官以上丁之日致祭先师孔子。”(12)江濬源修、罗惠恩,等纂:嘉庆《临安府志》,《中国地方志集·云南府县志辑》第九卷,南京:凤凰出版社,嘉庆四年(1799年)刻本影印,第90页。且庙内《丁祭严饬碑文》中,对于秋祭(祭孔大典)有着明确、细致的描述和规定。而作为祭孔仪式的主要组织——洞经会也随之建立和兴起,它属于民间组织,会长一名主要负责建水文庙的日常运营和祭祀活动,另设“引赞”“陪赞”“纠仪”(13)汪致敏:《建水洞经音乐初探》,《民族艺术研究》1994年第5期。等司置人员,负责组织和联络乐队。另外,建水文庙现存79块碑文,其中不乏祭孔典礼的记载,地方材料中也有众多关于祭祀仪式的描写和记录。
由此可知,建水文庙作为“庙学合一”的场域在王朝国家的安排之下诞生,它不仅仅是一种帝国象征,也是国家边界和朝贡的符号表征。正是祭祀与学宫的不同功能使其成为具有双重身份的“叠合空间”(14)方文:《叠合认同:“多元一体”的生命逻辑》,《社会学研究》2008年第6期。。国家话语的建立使其嵌于国家体系之内,成为“神圣性”祭祀空间;“学宫”的身份又使其能够“入世”,与地方社会的命运相勾连,这种双向嵌入使其与“庙宇—博物馆”的双重身份空间性质一致。
二、实践中的“庙校合体”
随着光绪三十二年(1905年)科举考试废除,“庙学相伴”的模式被打破,建水文庙成为祭祀空间。辛亥革命之后,政府虽然有尊孔命令和祭孔举措,但孔庙除祭祀外已无实用,加上云南长期处于兵灾动乱之中,大批孔庙被改作机关、兵营、工厂和市场。1913年袁世凯发布《尊孔令》,次年9月又颁发《祭孔令》,并进行中华民国首次“官祭孔子”活动。1916年袁世凯复辟,登上洪宪皇帝宝座,为了表示帝制合法,曾大规模祭孔,建水文庙的祭祀活动恢复如初。但1919年后受“打倒孔家店”影响,建水文庙跌落到“低潮期”,公祭活动基本停滞,只有洞经会内部维持每年的祭孔大典。
在历史车轮的驱动下,建水文庙又迎来了春天:1931年下半年云南省教育厅为推广边地教育,决定在建水创办临安中学(现名“建水一中”(15)建水一中始建于1917年,至今已逾百年。其间四易其址:1917年创于建水古城外焕文书院内,名为“建水县立中学校”;1928年因社会治安问题将学校迁至古城内崇正书院;1932年,为“推广边地教育”选建水文庙及其旁边的岳鄂王庙为校址,校名改为“云南省立临安中学”,1956年秋改为“云南省建水第一中学”;1992年,“腾让文庙”工程实施后建水一中搬出文庙,迁至文庙西侧。),任命刘嘉镕为筹备员并训令建水教育局协助办理。刘嘉镕经实地考察,考虑到学校规模和未来发展,选定建水文庙作为临安中学校址,但一些地方士绅和洞经会成员闻风而起,纷纷反对此举,认为建水文庙为祭孔圣地,不应在此办学,因此联名呈请教育厅仍沿用崇正书院校址,但是省厅仍坚持听取刘氏意见,将文庙作为临安中学校址,否则将省立中学改建到蒙自。由于事关地方发展前景,刘氏想尽办法,最后由县政府出面与地方士绅等协商,终于将文庙和岳王庙划给临安中学,并协定保留先师殿和东西两庑的牌位,以方便祭孔。1932年秋季开始招生,省立临安中学正式创办起来,完成“庙校合体”(16)云南省建水第一中学校志编纂委员会:《云南省建水一中学校志》,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52页。。“庙校合体”的实践过程不仅是对传统的继承,更使建水文庙在政府、乡绅和洞经会等多重主体的“共谋”下重新获得合法性,成为具备“庙宇—学校”双重身份的公共空间,更为建水文庙深深嵌入地方社会生命打了一针“催化剂”,这一具有前瞻性的举动对建水文庙以后的生命历程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此时的建水文庙便成为高丙中所谓的名副其实的“双名制”公共空间,不过祭祀和学校二者在活动上却属于关昕所说的“双线叙事、双轨并行”。
建水一中在文庙办学七十三载,它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临安中学时期(1932—1965年)为平稳期;二是20世纪60至70年代(1966—1976年)为冰冻期;三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1978—2005年)为兴盛期。而在此期间建水文庙的祭祀活动主要由洞经会负责,主要的祭祀活动为“祭孔大典”,日常的祭祀极少,学校和洞经会之间各行其是,“文革”期间祭祀仪式被隐藏至“天君庙”内举办,因此“庙宇—学校”的身份名存实亡,变成了完全的学校教育空间,出现了关昕所讲的另外一种空间组合形式“一种主体特征渐占主宰地位、而其他主体特征处于依从地位甚至消弭的融合”(17)关昕:《民俗文化与制度宗教:庙宇博物馆的双线叙事》,《民俗研究》2016年第5期。。
作为教育空间的建水文庙,通过教育教学活动与地方社会的互动进一步增强,不仅强化了建水文庙的在地化和地方感,也为它即将面对的风雨提供了“主力军”。从“特殊时期”地方社会的表现便可窥知一二,笔者访谈得知建水文庙免遭破坏的原因有二:一是地理位置的优势,因其远离中央而受“文革”的影响很小;二是建水一中的师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关于此,笔者结合两个田野故事进行描述。首先是先师殿前的“石龙抱柱”,访谈人口述:“我外婆是建水一中的老师,当她们知道红卫兵要对建水文庙下手时,学校的老师们便想了办法,当时有个叫施文昌的老师带领学生去挖建水陶土,另有老师带着学生连夜在家搓麻绳,之后他们用陶土和泥粘在麻绳上将整个柱子从上到下地裹住、抹平,最后在柱子外边写上‘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等标语,这样红卫兵看见了也不敢动手,所以那两根柱子才能被保存下来。”(18)访谈人:LYQ,男,建水旅游投资有限公司员工,35岁,2018年8月19日于建水文庙。其次是先师殿内的匾额与殿前铜鼎,据访谈人描述:“当时先师殿是建水一中的图书馆,里面没有雕像。那时候‘洙泗渊源’牌坊中间的‘文庙’匾额已经被砸了,先师殿前的‘先师庙’三个鎏金匾额和历代帝王所题的八块匾额外加铜香炉也有被毁掉的危险,于是建水一中的师生就把匾额拆下来,用纸封裱起来后藏到先师殿里的书架后边,躲过了红卫兵的搜查,最后又将它们转移到其他地方藏起来。当时他们直接把铜鼎搬到一位老师家里藏了起来,直到后来‘批林批孔’时才被重新搬出来放回原处。”(19)访谈人:长春宏一,男,道士,30岁,2018年7月16日于建水天君庙。因而现在展现于世人眼前的珍贵文物是地方情感的寄托和依附,不仅记住了历史更记录了真实,成为时代记忆的空间符号和象征。“我们必须追寻物自身,因为物的意义铭刻在它自身的形式、使用及其轨迹里,我们只有通过分析这些轨迹才能理解人的行为和算计激活了物。”(20)舒瑜:《物的生命传记——读〈物的社会生命:文化视野中的商品〉》,《社会学研究》2007年第6期。
20世纪70年代“批林批孔”大潮席卷建水文庙,在文庙内办学的建水一中师生也投入到此运动中,但他们采用了一种“明批暗保”的形式又一次保护了自己的“家园”。“明批暗保”正是戈夫曼在“表演”与“戏剧论”中提出的“前台和幕后”的微观互动,外表看来就是借建水文庙来批判孔子及其思想,并大力鼓吹其思想适应反动统治阶级的需要,但实质上却借由此事对文庙的历史沿革、碑文、地产等作详细调查与介绍,并由李明川老师执笔编写“批林批孔”宣传小册子——《文庙简介》(21)建水一中革委会:《建水文庙简介》,中共红河州委员会“批林批孔”办公室印,1972年,内部资料。,书中大量引用毛主席语录,充分揭示建水文庙是一个吹捧、宣传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场所,同时对建水文庙进行了深入细致的介绍,并描写了新中国成立之后建水一中在文庙中的主要办学场所:“‘先师殿’被改造成图书馆和阅览室,供奉七十二贤的两庑被改成教室,过去不让妇女进去的‘圣地’,成了师生学习、娱乐的场所。”此宣传手册印发之后在全国引起轰动,建水文庙成为当时“批林批孔”的主要活动地点,而“文革”时期被拆除的文物也被当成一种剥削的见证重新放回原处,吸引了全国各地的“积极分子”前来参观,当时文庙接待了省内外17万人次参观访问。建水一中的师生采用反讽手法,在这场关乎文庙生死的考验中取得了成功,更举一反三、大获全胜,让处在边陲的学海圣境得以保留,使得一个灾难性空间转化为一个弘扬孔子和儒家思想的传播场域。赫兹菲尔德在研究“大传统和小传统”时提出“文化亲密性”(22)Michael Herzfeld,Cultural Intimacy: Social Poetics in the Nation-State, New York: Routledge, 2005, p.53.表明,有时候地方社会对国家进行的批评、反讽和模仿等“社会诗学”行为是“二元”框架下被忽略的“诗性逻辑”的实践,更使得国家权力得以界定,权威得以认可。因而国家与地方之间是“结构性共谋”关系,双方共同协作、相互共存,从而携手共建文化亲密性的不同维度。(23)Michael Herzfeld,“History in the Making: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 a Rural Cretan Community,”in De Pina-Cabral and John Campbell, eds, Europe Observed,1992, p.107.
综上,作为“庙宇—学校”的公共空间,建水文庙在政府主导之下经历了“合二为一”“双轨并行”的过程,使历史传统与现代实践相结合,充分体现了国家在场的作用,而且从它的发展过程可以看到地方社会的能动性对命运留存的重要意义。是二者的共同作用使其能够在社会张力和紧张结构中经久不衰,并获得了不同层面的合法性:首先是行政合法性(24)关昕:《民俗文化与制度宗教:庙宇博物馆的双线叙事》,《民俗研究》2016年第5期。,建水文庙自建立以来,历代中央政权都不断强化它的“学宫”身份,而且由官方举行“祭孔大典”。另外,临安中学属于省立中学,其行政合法性直接来自于省教育厅。其次是增强了社会合法性⑥,受历史影响,建水文庙的教育空间身份早已成为地方共识,而且临安中学的建立能够为建水县的发展带来利益,不论对政府还是地方社会都是机遇。当然从政治和法律合法性⑥而言也是毋庸置疑的,学校作为传播教育的空间,不论何时它的政治导向性都不言自明,而没有政府登记注册,学校是不能存在的。
三、作为方法的“空间外延”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建水一中终于开始恢复以往的繁盛,逐渐步入正轨。但随着中国经济不断发展,建水的发展也迫在眉睫。建水县政府依托历史传统将旅游开发作为头等大事,而建水文庙作为文化遗产与当地旅游业发展息息相关。1992年,按照省、州、县三级政府统一规定,建水文庙作为旅游景点单独开发,因此制订了“腾让文庙”政策,提出“庙校分离”的策略。为此省教育厅、省文化厅、省财政厅与红河州政府、建水县政府签订协议书,要求建水县政府专门负责此工程,协议书中提到:“搬迁建水一中校舍及维修文庙共需383.3万元,其中包括搬迁校舍280.1万元,维修文庙103.2万元,这些钱由云南省、红河州、建水县政府按照4∶3∶3的比例负担(即省150万元、州县各115万元),一次性解决此事,之后省里不再负责此事……建水一中原占用文庙的古建筑按此协议规定搬迁后交由文化文物部门维修并管理使用,全部手续于1994年底前完成。协议规定后,1992年及1993年工程项目情况实际费用见表1。”(25)云南省建水第一中学校志编组委员会:《云南省建水一中学校志》,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附录”,2007年。

表1 建水一中1992、1993年项目实施情况
由此可知,建水文庙作为旅游空间再次被政府开发。此时,建水文庙的庙宇身份被凸显,它从学校变为旅游场所发挥了自己作为祭祀空间的作用,而且经过岁月洗礼的建水文庙已经褪去了青涩,留下的是成熟稳重的“遗产”。建水文庙从历史上的国家符号、教育空间变为现代背景下文化符号和旅游空间,其发展更是从神圣到世俗,即由王朝统治下的神圣空间变成了现代的旅游空间。
关于上述“庙校分离”后建水一中的选址情况,笔者在调查期间发现一份《2001年房地产置换通知》(26)建水县人民政府文件:《关于建水文庙、建水一中和县政府大院房地产置换的通知》(建政发[2001]7号)。,“为确保建水文庙、建水一中和县城新区开发建设和长期发展需要,根据县委2000年12月12日现场办公会议精神,县政府将文庙、一中政府大院房地产置换的意见分别提交县政协常委会协商和县人大常委会议审议,并获得通过……通知如下:一、建水一中原用文庙的房产由一中划归建水文庙建设使用,由建水文庙付给建水一中搬迁费150万元;二、县政府大院产权属国有,全部划给建水一中建设使用,由建水一中承担从部队购买政府大院的全部转让费用,一中建设规划必须按照程序报批,并经县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审定后方可进行建设;三、原州体中房地产仍由建水一中管理使用,但必须保持现状,未经县政府批准,不得建盖房屋和增设永久性设施,如今后城市发展需要,由建水一中有偿划拨按规划建设……五、文庙、一中、政府大院房地产置换,事关教育、旅游和城市建设发展大计,对建水经济社会的发展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2001年将校址定在文庙西侧,建水一中搬离文庙,文庙交由政府发展旅游,县政府为了配合此工程顺利实施也充当了“润滑剂”功能,让渡一部分政府财产,这在“房产置换通知”之中有明确描述。自从建水一中搬离文庙之后,文庙作为学校空间的身份便从物质升华为一种精神,这种精神已经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历史记忆和现时祭祀行为。
从空间生产而言,上述“庙校分离”过程是一种“空间外延”的运行逻辑,这种逻辑的运行并非是由国家或者地方社会某一方的力量所决定的,而是多重主体配合之下的作用,它不仅涉及基层政府和管理部门,也牵扯到全省的发展包括建水一中师生的未来,所以从过程论的视角出发,这是一个“共谋”的过程也是“互相调适”的结果。因此当现代市场经济以一种新的冲击加入到地方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博弈时,它们可能不再向内寻求空间生产和再生产的机会,而是通过“空间外延”的方法达成“共谋”,进而使得地方社会、国家和市场之间能够在更大的空间内共处,从而不断产生新的有生力量。

表2 建水文庙儒家三礼时间表
2005年9月28日,适逢孔子诞辰255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儒联、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国家旅游局及山东省人民政府等共同主办“2005年全球联合祭孔”活动。全球三十多家孔庙共同举行了祭祀仪式,建水县政府依托此次国际祭孔活动,联合洞经会和众多地方团体举办了“祭孔大典”(暨第一届中国红河·建水孔子文化节),正式将建水文庙打造成为一个“旅游符号”,为了显示祭祀仪式的正统性,建水县政府组织专人去曲阜孔庙取来“圣水”“圣土”置于学海和先师殿前。此后,建水县政府将建水文庙等古城内的众多景区交由建水古城投资旅游有限公司负责运营,而在企业的市场运作之下,建水文庙背后的儒家文化资源被进一步发掘。2010年元旦,建水旅投公司建构了传统儒家三礼:开笔礼、成童礼、成人礼,而后又打造了“敬老礼”“拜师礼”等活动。建水文庙被市场化之后,作为文化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这三个仪式分别面向不同的学生群体,开笔礼针对幼小衔接,成童礼面向小升初,成人礼则向高考生开放。三礼仪式的收费标准也不断变化,比如2014年360元,包含门票、租用服装等费用,2018—2020年则调整为180元和560元两种标准。儒家三礼的举办时间及详情见表2。之后又相继推出了“简餐礼”“传统古式婚礼”“国庆体验活动”等。2018年祭孔的活动主题为“祭万世先师·展上善建水”,并组织了“千人儒家三礼”活动。市场经济时代,建水文庙作为学校的身份已处于幕后,而此时其作为庙宇和祭祀空间的身份被置于台前,建构出来的仪式也在市场的运行下将文化资本和象征资本转化成一种经济资本进行消费。
至此,不同主体“共谋”下的“空间外延”不仅成为处理社会张力和紧张结构下的政治艺术,而且“庙校分离”后的建水文庙在地方政府和市场的运行之下,实现了布迪厄意义上的“资本转化”和“文化再生产”,既展示了“文化”“象征”“经济”资本之间的转化,又从仪式继承和再造的角度展现了市场经济下的文化再生产过程。从历时性出发,不同历史时期建水文庙代表的象征符号不同,从国家符号到教育符号、灾难符号、旅游符号,建水文庙从一种文化资本转化为经济资本和象征资本,又不断生产着社会资本,在建水文庙场域内,国家与地方社会不断进行着符号和资本之间的互动。从共时性层面,建水文庙的空间变化是一种身份之间的转换,这契合了戈夫曼所说的“前台和幕后”(27)欧文·戈夫曼:《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1页。,庙宇—学校作为公共空间为地方社会和国家之间的互动提供了“展演舞台”。
四、空间何以“共谋”?
历史的视角是人类学、社会学研究中不可或缺的洞察途径,空间的维度也是民族志研究中必不可少的探讨话题。通过梳理建水文庙的变迁过程可知,建水文庙作为“庙宇—学校”共同体能够延续近千年之根源在于地方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共谋”,而这种“共谋”的逻辑主要通过历史、空间生产、中央与边疆三个维度展现。
在历史层面,建水文庙呈现的是一个完整立体的变迁史。高丙中所研究的河北范庄的“庙宇—博物馆”兴建于2003年,站在长时段的视角下,它对于反映历史与当下、传统与现代的张力只是“事件性策略”(28)高丙中:《一座博物馆—庙宇建筑的民族志——论成为政治艺术的双名制》,《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1期。。关昕对东岳庙的调查展现了东岳庙和东岳信仰的长时段历史背景,表明“双线叙事”是一种“历时性方案”,但是在处理短时段的叙事上相对较弱,省略了很多关键时间节点的描写。(29)关昕:《民俗文化与制度宗教:庙宇博物馆的双线叙事》,《民俗研究》2016年第5期。而如图1、图2和前文所示,本文利用“点、线、面”相结合的方式,不仅描述了不同时间节点和情景下的庙宇空间发展,更利用时间线索将建水文庙的社会生命史进行串联,进而从宏观历史脉络中呈现一幅清晰的空间变迁画卷,它反映的是一种“事件性”和“历时性”相结合发展历程。在近千年的历史演变中,建水文庙经历了“在地化”和“地方化”的过程,封建时期建水文庙在中央王朝的庇护之下诞生和发展,利用教育空间和祭祀空间的身份不断增强其认同感。清末民初,随着科举考试废除、封建帝制终结,建水文庙出现了断裂带,但地方实践中的“庙校合体”恢复了它作为教育场域的功能,并真正经由“入世”与地方社会相连接,强化了它与地方社会之间的情感勾连。在中国社会形势极为紧张的20世纪60、70年代,地方民众利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建水文庙已经成为“地方社会成员”。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得建水文庙嵌入地方经济发展之中,经历了“庙校分离”的建水文庙作为旅游空间继续在地方社会中展示着自己。但在其整个生命历程中,并非只是中央王朝、国家、地方社会、基层政府某一方的力量使其能够游走于社会矛盾和张力之中而不断获得合法性和生命力,它是多方主体“共谋”的结果。如果仅从“事件性策略”视域看待庙宇空间的时段性表达,或仅从“历时性方案”中理解庙宇空间的叙事性呈现,都会导致功能主义的“以偏概全”或者结构主义的“二元对立”,应该立足于庙宇空间的社会生命史并结合重要时间节点进行动态立体式描写,从而反映出公共空间的完整生命互动轨迹,彰显国家、地方社会、民间团体等多方主体的“共谋”作用。

图1 建水文庙变迁图

图2 建水文庙空间变化示意图
在空间层面,建水文庙展现的是一种“空间外延”的动态再生产过程。河北“龙祖殿”的“双名制”,从空间生产而言是“合二为一”的合并型运行逻辑,“一套人马,两块牌子”①的实质是叠合空间带来的双重或多重身份使其能够左右逢源。北京东岳庙的实践则与之相反,是“一块牌子,两套人马”,在空间视域下,它是“一分为二”的分割型再生产过程。此外关昕还提出“在今后庙宇—博物馆的社会文化有机体间的生产与再生产博弈中,可能依然存在双方共存、各自生长的拼贴组合,也可能出现其中一种主体特征渐占主宰地位、而其他主体特征处于依从地位甚至消弭的融合”(30)关昕:《民俗文化与制度宗教:庙宇博物馆的双线叙事》,《民俗研究》2016年第5期。。但是上述二者的阐述皆表明在处理张力与博弈时,人们寻求的是一种空间内部的“生产和再生产”实践逻辑,忽视了空间的“外延性”。如图2所示,建水文庙的空间变化表明封建帝制背景下它是“二合一”的双重或者叠合空间,从总体而言皆服务于中央王朝统治。而清末民初受社会和政治环境影响,学校身份渐失而庙宇空间凸显。之后因地方实践的“庙校合体”,又重新恢复了“庙学合一”,但此时的运营模式却是一种“双轨并行”,庙宇、学校分别管理各自事务。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出现了“庙校分离”的“空间外延”,使建水文庙成为单一旅游空间。因此立足于整体和比较的视野,建水文庙的空间发展史表明,空间内部生产的“双轨”“拼贴”“共存”“消弭”都是缓解社会张力的策略,也是反映国家与地方社会之间互动的轨迹。
从前文可知,在建水文庙的空间再生产过程中,不论是“二合一”的地方实践还是“一分二”的双轨并行亦或是旅游发展下的“空间外延”都远非某个单一主体所能控制。在此过程中国家从未缺席,国家通过不同层级的管理手段进行体现,如同关昕所谓的“国家处在社会中”。当然地方社会的作用和能动性也从未消失,因为庙宇在地方化过程中与地方社会形成了一种“情感”纽带和“共生”体系,如同建立了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所以高丙中所讲的“民间自发”“草根社团”确实具有重要意义。因而国家与地方社会之间并非“二元对立”或者“此消彼长”的关系,它们之间更多的是“调适与共谋”。比如“双名制”的前提是国家政策的松动致使龙牌会兴起,而“双名制”的达成也在于政府赋予“龙牌殿”以合法性身份。“双线叙事”之所以能并行也源自地方社会对传统民俗的传承和延续,不仅靠国家力量的在场。此外,之所以出现空间生产的内部出路和外部走向,应该与所处的地理位置有关。在“中央与边缘”的框架之下隐喻的是权力的强弱和密集程度,而且建水文庙位于中国的西南边陲,龙祖殿和东岳庙都处于中国的腹心地区,因此“中央与边缘”的视角在理解中国庙宇的空间生产中不可或缺,这也是边城“庙宇—学校”研究的关键之处。
在中央与边疆层面,讨论集中点便是国家权力的强弱是否受到地理位置的影响。弗里德曼曾考察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表明在“边陲地区”由于政府的社会控制力较弱因而导致宗族组织壮大强盛。(31)莫里斯·弗里德曼:《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刘晓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94页。而斯科特则讨论了“逃避统治的艺术”,认为生活在中国西南边陲的人们在寻找“中心以外的避难所”,隐喻着边缘山区国家权力的弱化。(32)詹姆士·斯科特:《逃避统治的艺术:东南亚高地的无政府主义历史》,王晓毅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第410页。那么建水文庙的历史变迁过程和空间发展模式是否也反映了这种论点?首先,建水文庙表明了国家和地方能动性之间受到权力密集程度的影响。东岳庙地处北京,在权力高度集中的地区庙宇空间所展现的是国家在场的密集型,能动性则有所忽视,而且作者本身作为东岳庙的管理人员,其参与观察的视角难免受职业影响而“客观”程度不够。而从河北的龙祖殿中则看到地方能动性有所发挥,因而出现了“双名制”作为政治艺术,只是国家并未缺席,因为修建博物馆的动机来源于“学者发言”,地方社会团体只是这个想法的执行着和实施者,在此过程中各级政府部门仍然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从边城文庙的空间实践可以发现,由于其地处边城,因而地方社会的能动性得到了更大的彰显,比如“文革”十年,龙牌会的“一切相关活动都消失了”,东岳庙则因属办公用地损失减轻,保留了主要建筑和整体格局。但是边城建水的情况则大为不同,地方社会充分利用其能动性,不仅使庙宇免遭破坏而且还“举一反三”,利用“明批暗保”的方式进行了大规模的宣传。其次,空间再生产的路径选择也反映了中央与边疆的差异性,地处中央的“龙牌会”和“东岳庙”虽然可以保存并获得合法性,但其由于地理位置所限只能在空间内部寻求出路。“边缘”地带则不同,因为边缘既是分界线又是连接线,受此影响边陲地带的人们在处理社会张力和博弈时,便出现了两种选择,一是与中央庙宇一样从空间内部找出路,二是向空间外部寻求发展,建水文庙的“空间外延”便是一个典型的案例。但上述两个讨论并非表明弗里德曼和斯科特的结论是完全正确的,他们忽视了特定时间背景和历史情境的影响,而且都带有结构、功能主义的片面分析视角,因为在建水文庙的“社会生命史”和“空间变化”实践中,国家权力与地方社会之间从来不是“零和博弈”,而是“调适共谋”。
因此,本文所谓的“共谋逻辑”是一种国家宏观背景下地方社会与基层政府间的微观互动,不论是“国家处于社会中”还是“社会处于国家中”,二者之间从来不是“二元”关系。而且不管是“庙宇—博物馆”或是“庙宇—学校”这种具有双重乃至多重身份的建筑,它们的空间生产和再生产实践都映射了国家在社会治理中的不同文化逻辑,都为中国社会建设发展提供了路径探索。另外,建水文庙的发展史也暗含着另一条线索,即随着民族国家的建立和全球化发展,国家的重心已经从封建帝国时期的“中央”,逐渐履盖到现代国家的“边疆”,因此边城庙宇的研究不仅彰显着国家与地方社会的共谋,更反映着中央与边缘之间的互动,回答着“何为中心”“何为边缘”的重要命题。
——巍山文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