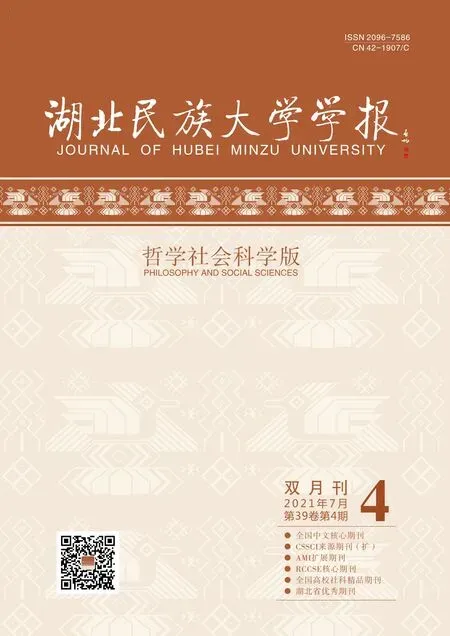农村女性健康贫困脆弱性及影响因素研究
韦 艳 李美琪
一、问题的提出
摆脱贫困、改善民生、共同富裕,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内容。2020年,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创造了减贫治理的中国样本,为全球减贫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习近平总书记于2021年2月25日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提到,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仍然任重道远。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针对“十四五”时期的社会发展提出,要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战略有效衔接,健全防止返贫监测和帮扶机制,持续推动脱贫地区高质量发展。《“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调整优化健康服务体系,坚持预防为主,制定实施重点人群健康干预计划,突出解决好妇女儿童、老年人、残疾人等重点人群的健康问题。农村女性的健康与贫困对家庭、社会以及健康乡村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因此,建立农村女性防贫返贫长效机制,提升女性抗疾病风险能力,对提高女性幸福感和生活质量以及巩固拓展健康扶贫成果和建设健康中国意义深远。
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底线任务和标志性指标,实施健康扶贫工程,是打赢脱贫攻坚战、实现农村贫困人口脱贫的一项重要举措,是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内在要求。截至2019年底,全国未脱贫的建档立卡户共98万户(266万人),其中因病致贫返贫贫困户37.5万户(96.8万人),户占比38.4%,2016-2019年,因病致贫返贫始终保持在40%左右的水平(1)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全国健康扶贫数据监测报告(2016-2020)》,2020年10月。,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比例仍相对较高。因此,扶贫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在于健康扶贫,未来稳定和巩固健康扶贫成效的难度依然较大,需要面对减少因病致贫存量和预防因病返贫增量的双重压力。由于重大疾病和自然灾害等风险因素的长期存在,偏远农村地区及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弱势群体返贫风险较高。当前,我国进入以转型性的次生贫困和相对贫困为特点的后扶贫时代(2)高强、刘同山、沈贵银:《2020年后中国的减贫战略思路与政策转型》,《中州学刊》2019年第5期。,贫困边缘和潜在贫困人群成为新时期扶贫的目标对象,事前测度未来遭受健康风险冲击的可能性以及预测未来陷入贫困的概率,是斩断疾病与贫困之间因果链接,降低农村人口健康贫困脆弱性以及新时代新型贫困治理的关键。
随着农业女性化、农村空壳化和社会老龄化趋势的加剧,女性成为农村发展建设的主体,女性的健康贫困程度对家庭与社会发展至关重要(3)刘欣:《近40年来国内妇女贫困研究综述》,《妇女研究论丛》2015年第1期。,尤其对民族地区和深度贫困地区的影响更为深远。女性贫困是由于生理、制度、资源和环境等诸多因素导致女性生活和发展处于一种“无能”状态,包括健康贫困、政治贫困、教育贫困和经济贫困等。(4)王一妃:《女性贫困及消除路径研究》,南京:南京中医药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8年。诸多研究表明女性贫困具有多维性和特殊性,农村女性极易遭受健康风险的冲击(5)徐彬:《生命历程视角下农村老年女性贫困的影响因素研究》,《农村经济》2019年第5期;柳建平、刘咪咪:《贫困地区女性贫困现状分析——多维贫困视角的性别比较》,《软科学》2018年第9期;李颖慧、窦苗苗、杜为公:《我国城乡女性贫困成因与治理方式研究》,《河南社会科学》2020年第9期;叶普万、贾慧咏:《我国农村妇女贫困的现状、原因及解决对策》,《理论学刊》2010年第9期。,导致健康能力剥夺和健康机会丧失,呈现健康脆弱性、经济脆弱性和社会脆弱性等脆弱状态(6)翟绍果:《健康贫困的协同治理:逻辑、经验与路径》,《治理研究》2018年第5期。。在家庭和社会发展中,农村女性难以获得稳定的经济收入,缺少社会及家庭权利,社会资本存量过少,导致贫困女性很难改善贫困局面。农村地区医疗资源匮乏、疾病防控意识淡薄、自然环境恶劣等交错叠加现象普遍,加之农村女性承担着照料家庭、赡养老人、承担劳务等多重责任,使得农村女性成为健康贫困的高发群体。个别民族文化和宗教信仰把女性“生育”当作自然法则,不干预(不避孕、低龄妊娠、不人工流产)的选择使女性面临较高的生育风险。(7)邓睿、焦锋:《时间、资本、环境三维视角下深度贫困地区健康脆弱性解析》,《医学与社会》2020年第11期。女性贫困与健康存在双向作用机制,健康与贫困互为因果可能会导致贫困的代际传递和“恶性健康贫困循环”。因此,女性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后小康社会的女性贫困等议题,都应得到更多关注。(8)杨菊华:《推动新时代女性人口学研究的多元观照》,《中国妇女报》2020年1月7日,第5版。
贫困脆弱性是“度量对冲击的复原—冲击造成未来福利下降的可能性”(9)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00/2001-Attacking Povert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贫困脆弱性克服了传统贫困测度静态性和事后性的不足,从前瞻性的视角预测未来贫困发生的可能性,拓展了贫困治理的相关研究(10)祝建华:《城市居民家庭贫困脆弱性的测度、因素识别与消减策略》,《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健康贫困脆弱性是指个人、群体或组织在遭受健康风险冲击后陷入贫困的概率,在消除现有贫困的基础上,还需要识别因病致病返贫的风险。已有少量学者对健康贫困脆弱性展开了研究,主要涉及健康贫困脆弱性的测度及影响因素等。刘军军等从个人特征、健康状况、卫生服务、医疗保障和疾病预防五个维度对慢性病患者的健康贫困脆弱性进行综合测度并分析其影响因素。(11)刘军军、王高玲、严蓓蕾:《慢性病患者健康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因素研究》,《中国卫生经济》2019年第5期。严蓓蕾采用三阶段广义最小二乘法(FGLS)测量健康贫困脆弱性指数,并用分位数回归法分析慢性病患者健康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因素。(12)严蓓蕾:《慢性病患者健康贫困脆弱性测度与影响因素分析》,南京:南京中医药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9年。张怡青从个人特征、医疗卫生服务、保障制度、疾病预防与控制四个维度构建指标体系测算农村老年人口的健康贫困脆弱性,且从时间和空间角度探索其异质性。(13)张怡青:《农村老年人口健康贫困脆弱性测度及其异质性研究》,南京:南京中医药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9年。对健康贫困脆弱性测度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能有效识别因健康风险而陷贫的潜在群体及其致贫因素,进而促进新时期健康扶贫政策的转型和有效实施。
综上所述,已有研究对于女性贫困和健康贫困脆弱性测度进行了有益尝试,但针对女性健康贫困脆弱性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仍较少,主要存在以下不足。第一,健康贫困脆弱性的性别研究较为缺乏。对于健康贫困脆弱性的研究主要对老年人和慢性病患者,而对于女性健康贫困脆弱性的研究还很少见。已有对于女性贫困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老年女性贫困和女户家庭贫困,健康贫困研究较少,或只作为多维贫困研究的一部分。第二,微观层面的脆弱性精准识别研究较少。已有关于健康贫困脆弱性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总体脆弱性指数,对特征人群健康贫困脆弱性的识别和比较分析较为缺乏。第三,健康视角下民族地区的贫困脆弱性研究较少。已有对民族地区的贫困研究主要涉及收入贫困和多维贫困,从健康风险视角研究民族地区的贫困脆弱性尚不多见,从区域比较方面研究健康贫困脆弱性更为缺乏。
农村女性健康贫困脆弱性的程度如何?哪类女性群体的健康贫困脆弱性更高?健康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因素有哪些?针对农村女性健康风险的防贫路径有哪些?这一系列问题目前还缺乏实证研究。因此,本文利用2018—2019年全国五省“精准健康扶贫与人口发展”专项调查数据,采用三阶段广义最小二乘法(FGLS),从个人特征、卫生服务、医疗保障和疾病预防四个维度对农村女性的健康贫困脆弱性进行测度,并分样本进行脆弱性比较,通过回归分析找出关键的影响因素。本文的贡献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从性别和区域视角丰富健康贫困的研究。首先,从性别视角出发,将收入贫困与健康风险、疾病风险结合起来,创新性地引入脆弱性指标量化农村女性的致贫风险,然后分析农村女性健康贫困脆弱性在民族自治地区和非民族自治地区上的差异,为后扶贫时代健康防贫的治理研究提供新的思路和方向。第二,为精准识别高健康贫困脆弱群体和判别健康致贫风险提供科学依据。从微观角度比较不同特征农村女性的健康贫困脆弱性,精准识别高健康贫困脆弱群体,探究健康贫困的影响因素,从而提升农村女性的抗疾病风险能力,以期丰富性别视角下健康扶贫政策的常态化转型研究,为后扶贫时代健康扶贫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二、数据与方法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所用的数据来源于课题组于2018年12月至2019年2月开展的“精准健康扶贫与人口发展”专项调查。中国贫困人口大多集中于中西部,2017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支持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的实施意见》对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工作做出全面部署,重点支持西藏自治区、四省藏区、南疆四地区和四川凉山州、云南怒江州、甘肃临夏州(简称“三区三州”)以及贫困发生率超过18%的贫困县和超过20%的贫困村。因此,此次调查综合考虑了深度贫困地区“三区三州”和健康扶贫的重点区域,选取了四川凉山州、甘肃临夏州、湖北恩施州、安徽安庆市和陕西商洛市五个地区作为调查地。其中四川凉山州和甘肃临夏州属于国家精准扶贫界定的深度贫困地区,也是少数民族聚居较多的民族自治地区,主要特征表现为气候恶劣、山势陡峭、交通不便和经济不发达等。湖北恩施州是中部地区湖北省唯一的少数民族自治州,也是典型的多民族集聚区,安徽安庆市和陕西商洛市是健康扶贫重点区域。
此次调查采用多阶段抽样方法,第一阶段抽取四川凉山州、甘肃临夏州,安徽安庆市、湖北恩施州、陕西商洛市五个地区作为初级单位,第二阶段按照地域进行配额抽样,尽量均匀覆盖5个市/州所辖的各个区县。每个地区选取1所高校作为协作单位,5所高校共选取252名问卷调查员。每位调查员在其所在的调查村做10份家庭问卷和1份村级问卷。家庭问卷主要包括家庭基本信息、社会支持以及户主个人基本信息、健康状况、医疗服务满意度及健康扶贫项目感知5个部分;村级问卷包括村干部个人基本信息、村基本信息、生活条件及区域环境、村卫生室卫生情况等内容。此次调查中建档立卡户和非建档立卡户的样本比例保持在1∶1左右,通过培训、跟访以及对数据进行逻辑关系检验并进行10%抽样复核来确保质量。本次调查共发放2500份家庭问卷,回收有效问卷2102份,有效回收率为93.4%。
本次调查的数据与全国卫生服务调查数据对比,具有较好的一致性,调查详情可参考已发表的成果(14)韦艳、徐赟、高迎霞:《贫困地区健康扶贫绩效评价研究——来自全国5省调查分析》,《调研世界》2019年第4期。,此处不再赘述。基于研究目的,本文将受访者为女性和受访者为男性时其配偶信息样本进行合并,将部分村级问卷变量并入家庭问卷变量,剔除主要变量缺失严重的数据后,最终纳入分析的农村女性样本为1150个。经检验,样本数据的信度系数为0.70,大于0.60;KMO值为0.76,大于0.60,证明数据通过信度和效度检验,可以进一步研究。
(二)研究方法
1.健康贫困脆弱性测度
学界对贫困脆弱性的测度方法有期望贫困脆弱性(VEP)、期望效用贫困脆弱性(VEU)和风险暴露贫困脆弱性(VER)三种,目前已有研究普遍采用的Churidar等(2002)提出的期望贫困脆弱性,即衡量目标个体或家庭在未来陷入贫困的可能性(15)S.Churidar,J. Jalan,and A. Suryahadi, “Assessing Household Vulnerability to Poverty from Cross-sectional Data:A Methodology and Estimates from Indonesia,” New York:Department of Economics, Columbia University,2002.。该方法的优点在于可以使用截面数据估计贫困脆弱性,克服了面板数据缺失的不足。本文研究的健康贫困脆弱性主要用于描述农村女性因遭受健康风险冲击而陷贫的概率,故选取期望贫困脆弱性(VEP)的方法测算健康贫困脆弱性,其表达式如下。
Vi,t=Pr(Yi,t+1≤Z)
(式1)
Vi,t表示农村女性i在t时期的健康贫困脆弱性,Yi,t+1表示该农村女性i在t+1时期的年均纯收入,Z表示贫困线标准,即需要估计农村女性未来的收入水平。根据永久性收入假说,未来收入的均值和方差可以看成现在收入均值和方差的无偏估计量。(16)N.McCulloch, and M.Calandrino, “Vulnerability and Chronic Poverty in Rural Sichuan,” World Development, vol.31, no.3, 2003, pp.611-628.借鉴Churidar等(2002)、Zhang和Wan(2006)(17)Y.Zhang, and G.Wan,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Household Vulnerability in Rural China,” Journal of the Asia Pacific Economy, vol.11, no.2, 2006, pp.196-212.的研究,本文采用Amemriya(1977)(18)T.Amemiya, “The Maximum Likelihood Estimator and the Non-linear Three Stage Least Squares Estimator in the General Non-liner Simultaneous Equation Model,” Ecnometrica, vol.45, no.4, 1977, pp.955-968.提出的三阶段可行广义最小二乘法(FGLS)对农村女性的收入水平及方差进行估计。同时,FGLS可以容纳一阶自回归和异方差引起的误差,具体步骤如下。

LnYi=Xiβ+ei
(式2)
(式3)
其中Yi表示农村女性在i时期的收入水平,Xi表示影响农村女性收入波动的健康风险变量,即个人特征、卫生服务、医疗保障和疾病预防四维度的特征变量。

(式4)
(式5)
(式6)
(式7)
第三步,选择合适的贫困线标准,已有研究证明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更适合用对数正态分布描述(19)S.Singh and G.Maddala,“A Function for Size Distribution of Incomes,”Econometrica, vol.44, no.5,1976, pp.27-35.,则农村女性的健康贫困脆弱性指数表示如下。
(式8)
测算贫困脆弱性的准确率取决于贫困线和脆弱线的选择。文本采用2018年我国农村扶贫标准贫困线3535元。参考已有的研究(20)万广华、章元:《我们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准确预测贫困脆弱性?》,《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9年第6期。,本文选择0.5作为高脆弱线标准,脆弱性大于0.5的为高健康贫困脆弱的农村女性,脆弱性小于0.5的为低健康贫困脆弱的农村女性。
2. Tobit回归分析
由于健康贫困脆弱性指数分布在0~1之间, 属于“受限被解释变量”,具有被截取的特点。因此,本文采用双边受限的Tobit回归模型来确定影响农村女性健康贫困脆弱性的关键因素,以及判别这些影响因素的作用方向,具体模型如下。
(式9)

(三)女性健康贫困的影响维度
健康贫困是健康能力的剥夺和健康能力的缺失而导致的贫困,是由于经济发展落后所导致享受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和参与医疗保障的机会丧失,由此造成健康水平的降低,致使参与经济活动的能力被剥夺,造成贫困的发生或加剧。(21)孟庆国、胡鞍钢:《消除健康贫困应成为农村卫生改革与发展的优先战略》,《中国卫生资源》2000年第6期。农村女性的健康水平既与自身特征、身体素质和健康行为有关,还受卫生服务与医疗保障能力的影响。个体的健康致贫风险主要来自个人特征、卫生服务、医疗保障和疾病预防四方面。(22)刘军军、严蓓蕾、王高玲:《基于德尔菲法的慢性病患者健康贫困脆弱性评价指标体系研究》,《中国医疗管理科学》2019年第3期。其中健康风险的内源性维度包括个人特征和疾病预防,卫生健康风险的外源性维度包括卫生服务和医疗保障。
一是个人特征。本文中的个人特征泛指人口的社会属性,如年龄、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和健康状况等。未成年人、成年劳动力、老年人的健康资本存量存在差异,相同健康冲击造成的疾病严重程度和卫生服务利用深度不同,各生命周期的农村女性抵御健康风险的韧性有差异。丧偶或离异的农村女性不仅缺少经济和社会支持,而且还缺乏情感慰藉,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都极易受损。教育作为广大人民群众提高人力资本存量的有效途径,对改善农村女性健康观念和提高创收能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但农村女性深受社会经济、民风习俗和重男轻女观念的综合影响,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少数民族女性的健康贫困是自然条件、文化历史、个人条件及现实社会条件等诸多因素长期作用的结果。健康水平的降低会引起医疗和保健等方面支出的增加,健康恶化进而导致劳动力退出或劳动时间损失,间接地降低了农村女性的生产效率,影响其劳动参与能力,最终带来经济损失的增加和贫困脆弱性的上升。
二是卫生服务。卫生服务是指向居民提供医疗、预防、保健和康复等各种活动。在公共医疗体系中女性处于不利地位,女性欠缺足够的营养健康和可利用的卫生资源,健康不公平现象突出。基层医疗机构的卫生服务缺乏性别敏感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农村女性的就医行为。在更多优质妇幼资源向城市集中的背景下,基层妇幼机构呈衰退趋势。农村地区卫生服务的可及性不足、乡村医生专业水平有限、医疗设备落后、药品配置不充分,这些因素都增加了贫困女性的健康风险。由于生理结构、孕育条件以及健康脆弱性较强等特殊性,农村女性的卫生服务多元化需求未得到满足,“看病难”成为农村女性的突出问题。(23)沅芳、熊昌娥、陈海莲,等:《脱贫攻坚背景下咸宁市农村贫困妇女健康扶贫路径研究》,《河南社会科学》2020年第9期。另外农村女性偏向于自我治疗和到村卫生室就诊,治疗无效时才会上级转诊,直接到县级及以上医院就诊的概率较低。(24)黄佳妮、朱孝金:《就医行为研究》,《农村经济与科技》2012年第10期。部分女性不就医或者少就医,使得疾病恶化或反复。女性的患病率和残障流行率均高于男性,且存在卫生服务需求高而利用不足的现象。(25)姜秀花:《社会性别视野中健康公平性分析》,《妇女研究论丛》2006年第4期。因此,卫生服务能力的提升可有效促进健康改善,避免农村女性陷入“贫困陷阱”。
三是医疗保障。医疗保障指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医疗救助等制度。医疗保障体系作为疾病经济风险的保障载体,是防止因病致贫返贫的重要政策工具,具有较强的保护功能。农村地区医疗保障较为单一,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简称新农合)是当前农村居民最主要的医疗保障选择,也是大多数农村居民进行医疗报销和减轻医疗费用负担的主要途径。随着新农合的普及和各级政府的不断努力,农村居民“看不起病”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有效缓解,但农村女性的健康状况没有得到很好的改善,贫困边缘人口医疗保障不足的问题依然突出,尚存在报销程序复杂、统筹层次较低、抗风险能力不足等问题。(26)任志江、苏瑞珍:《农村医疗保障制度反贫困的传导机理、当前困境与对策创新》,《理论探索》2019年第1期。研究表明医保制度中医疗费用报销比例偏低、自付比例较大、部分治疗费用高昂的药种并没有全部纳入医保名录。(27)林闽钢:《在精准扶贫中构建“因病致贫返贫”治理体系》,《中国医疗保险》2016年第2期。医疗保险可通过改善健康状况进而增加劳动供给,降低预防性储蓄以增加生产性和人力资本投资。(28)刘子宁、郑伟、贾若,等:《医疗保险、健康异质性与精准脱贫——基于贫困脆弱性的分析》,《金融研究》2019年第5期。新农合具有亲富性,虽然能改善个体的健康水平,但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不同收入群体的健康不平等。(29)彭晓博、王天宇:《社会医疗保险缓解了未成年人健康不平等吗》,《中国工业经济》2017年第12期。农村地区的医疗救助范围窄且救助能力不足,而新农合制度通过保障基本卫生安全,可以有效缓解农村女性因病致贫返贫的困境。
四是疾病预防。疾病预防指通过一定的方式预防疾病的发生。农村女性疾病预防意识淡薄,经常会出现该就诊时而未诊、舍不得花钱做健康检查等现象,低收入农村女性存在“小病拖,大病扛”的不良习惯。由于过度劳作,农村女性大多深受疾病困扰,然而对疾病的处理方式却表现出消极态度。如农村地区存在一定的讳疾忌医现象,特别是民族地区及偏远落后地区,有的女性选择传统的“偏方治病”“气功治病”等不科学的治疗方式(30)白描:《乡村振兴背景下健康乡村建设的现状、问题及对策》,《农村经济》2020年第7期。,会导致病情加剧。另外,有研究表明农村家庭的有限支出和营养食物总会首先满足男性的需要,女性的生活质量可能会被降到最低,有时还会被“习惯性地”忽略,致使农村女性健康状况不佳。(31)刘雁:《农村女性人力资本开发研究》,西安: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性知识、生育常识和健康保健意识缺乏常会导致农村女性早产率高,健康观念滞后的女性疾病抵抗能力弱。通过疾病预防可有效提升自身抵御风险冲击的能力,降低未来发生健康贫困的概率。
(四)变量设置及描述性统计
被解释变量为健康贫困脆弱性。基于期望贫困脆弱性(VEP)的研究方法,考虑健康风险对农村女性收入波动的影响,结合三阶段广义最小二乘法测算结果,分析农村女性遭受健康相关风险冲击后陷入贫困的概率。健康贫困脆弱性越大,意味着农村女性因健康风险陷贫的可能性越大,其值分布在0~1之间。该指标从前瞻性的视角预测农村女性未来的健康贫困状态,具有动态性和预期性的特点,对健康防贫具有可行性和科学性的参考价值。
解释变量有四个。一是个人特征,选择年龄、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民族和健康状况,表示农村女性的经济状况、能力剥夺及机会丧失程度,也可反映抵抗疾病风险能力。二是卫生服务,采用首选看病地点、到最近看病点时间、医生水平满意度、药品种类满意度和村卫生室数量,侧面反映农村基本公共卫生现状、卫生资源配置状况和卫生服务在空间上和时间上的可及性。三是医疗保障,选用参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医疗自付费用比例两个变量。作为农村最基本的医疗保险,新农合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医疗保障水平。自付费用比例为报销后的自付费用与医疗总费用的比值,反映医疗医药的报销程度。四是疾病预防,选择及时就医、定期健康体检、常关注健康保健知识和合理安排饮食变量反映农村女性的就医行为和健康素养。
各维度变量的均值和标准差见表1。计算可得,农村女性的年人均纯收入为4770元,低于农村居民的年人均纯收入6910元,说明农村女性的收入水平较低。随着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加速发展,年轻的农村女性大多向城镇转移,农村空壳化和老龄化现象日趋严重。农村地区有92%的在婚女性,有8%的女性处于离婚、丧偶和未婚状态,与预期结果相同。调查发现有71%的女性受教育程度在小学及以下,农村女性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因调查地区中涉及多个民族地区,样本中少数民族农村女性占38%。25%的女性患有慢性病、重病或伤残,总体上农村女性的健康状况欠佳。34.3%的女性首诊地点在村/社区卫生室,首诊地点在镇街道卫生院的女性占29.7%;农村地区到最近就医点时间平均为37分钟,标准化村卫生室的覆盖率为91%;54%的女性觉得常看病点医生水平高,39.8%的女性对常看病点药品种类感到满意,农村地区的医疗卫生服务水平有待提高。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女性占92%,医疗自付费用比例平均在56%的水平,说明贫困地区的农村女性医疗保障水平还需要进一步完善;19%的女性会定期健康体检,37%的女性会常关注健康保健知识,68%的女性有合理安排饮食的习惯,农村女性的健康素养水平不高。

表1 变量含义及描述性统计
三、实证结果分析
(一)总体测度结果
根据总体样本的测度结果,农村女性的健康贫困脆弱性均值为0.388,有17.56%的农村女性是高健康贫困脆弱的,即健康贫困脆弱性超过0.5,这部分群体极易陷入健康贫困。总体上,农村女性的健康贫困状况不容乐观:一方面,农村地区卫生资源薄弱、自然环境恶劣、卫生条件堪忧和饮食结构单一,农村女性对健康风险的认知程度低,因此容易遭受健康危险因素的侵害;另一方面,农村女性收入水平低而医疗费用高昂,支付能力不足限制其对卫生服务的充分利用,引起健康水平的下降。健康状态的恶化会降低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创造力,进而降低农村女性的长期创收能力,造成贫困脆弱性的上升。(32)刘跃、刘慧敏、李艾春,等:《农村家庭健康贫困脆弱性多维风险因素探析》,《中国卫生事业管理》2019年第5期。分样本发现建档立卡贫困户女性的脆弱性均值为0.408,高脆弱率为23.38%;而非贫困户女性的脆弱性均值为0.373,高脆弱率为12.79%。贫困户女性陷入健康贫困的可能性更高,社会经济水平往往会抑制农村女性投资自身健康的积极性,不同收入水平的女性所拥有的健康资本存在差异,面临相同健康冲击时的策略选择不同。低收入农村女性拥有较少的资产存量,难以获得充足的卫生保健服务。在非贫困户女性中潜在贫困人群比例较大,究其原因,精准扶贫过程中政策大多仅将建档立卡户居民纳入救助网,且存在健康扶贫对象界定模糊的问题。近年来国家对建档立卡户的健康扶贫力度大,医疗费用实现了大幅度的下降,有效缓解了疾病负担,然而大多非建档立卡的边缘户只享受一般普惠的医保政策,从而具有较高的因病致贫风险。在后扶贫时代,精准识别高脆弱农村女性对一系列政策的有效实施显得尤为重要。

表2 不同地区农村女性的健康贫困脆弱性
表2为不同地区农村女性健康贫困脆弱性情况。四川凉山、甘肃临夏和湖北恩施是民族自治地区,民族地区的脱贫攻坚是整个脱贫过程中的硬仗,也是脱贫中“最难啃的硬骨头”。三地农村女性的脆弱性均值分别为0.459、0.429和0.391,高脆弱率分别为31.4%、29.0%和18.7%,脆弱性均值和高脆弱率均高于非民族地区,意味着民族地区农村女性不仅陷入健康贫困的概率更高,而且高脆弱人数的占比也更大。由于历史、地理和基础设施等因素影响,中国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发展相对滞后,医疗资源供给和收入分配不平衡,农村女性普遍存在患病多、身体差、卫生服务需求高但利用不足、医疗保障有限和疾病防控意识差等现象,表现为对健康风险的抵御能力弱,产生的疾病经济负担重。这与已有研究高脆弱农户更可能分布在革命老区、少数民族聚集地等特殊类型的贫困地区的结论一致。(33)杨龙、汪三贵:《贫困地区农户脆弱性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5年第10期。民族地区和贫困地区在空间上具有高度的重叠性,地理区位处于劣势,社会生产力较为落后、生态环境脆弱,其传染病、地方病和慢性病频繁发生,而疾病防控难度却较大。在非民族自治地区中,安徽安庆市的脆弱性均值和脆弱率都最低。通过对不同地区农村女性的健康贫困脆弱性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得到F值为41.311,P值小于0.05,说明农村女性健康贫困脆弱性在地区间存在差异。经济发展水平较好的地区,农村女性的健康贫困脆弱性较小。
(二)分区域个人特征的健康贫困脆弱性
为精准识别健康贫困脆弱较高的群体,分样本对不同特征女性的健康贫困脆弱性均值进行比较。如表3所示,与非民族自治地区农村女性相比,民族自治地区女性在不同特征上的健康贫困脆弱性均值都更大,民族地区女性的健康贫困程度更深,其原因复杂多样,体现在自身发展能力不足、制度保障不全面和民族传统文化等多方面。乡土习俗对民族地区女性的健康贫困有着深远的影响。在促进全民健康公平的背景下,民族地区不同生命周期的农村女性都应被给予更多的关注。具体来看,健康贫困脆弱性随着年龄的增大而升高,55岁及以上女性的脆弱性均值最大;农村女性受教育程度越高,其健康贫困脆弱性越低,未上过学的农村女性脆弱性均值最大;少数民族农村居民的健康贫困脆弱性相比汉族较高;在健康状况方面,患病或伤残的农村女性脆弱性较高。上述分析表明,老年、受教育程度低、少数民族和健康状况欠佳等处于社会弱势的农村女性面临更高的健康风险。

表3 分区域个人特征的健康贫困脆弱性均值
(三)影响因素分析
通过分样本测算健康状况发现,健康农村女性的脆弱性均值为0.354,患病或伤残农村女性的脆弱性均值为0.493,两类群体的脆弱性均值相差0.139,健康状况恶化是农村女性陷入健康贫困的根本原因。伤残或患病群体面临灾难性卫生支出的可能性大,因此其因病致贫返贫的概率较大。而健康群体也存在着疾病风险,面临着健康危险因素的侵害,在未来有陷入贫困的可能。为更清晰地探究两类群体的影响因素,本部分通过Tobit回归模型进行分样本分析,其中模型1为全样本回归,模型2为非健康组(伤残或患病)回归,模型3为健康组回归,具体如表4所示。

表4 健康贫困脆弱性的Tobit回归结果
从个人特征看,年龄、受教育程度、民族和健康状况是影响农村女性健康贫困脆弱性的主要因素,三组模型均在0.05水平上显著,而婚姻状况却未通过检验。随着年龄的增大,农村女性陷入健康贫困的概率越高,高龄女性在身体健康、经济收入、精神慰藉等方面存在弱势叠加的情况,整个生命周期患慢性病等疾病的概率大,更容易发生健康贫困。提升受教育程度能有效降低农村女性的健康贫困脆弱性,文化水平高的农村女性创造财富的能力强,容易获得医疗保健资源,健康素养也相对较高,发生健康贫困的可能性较小。少数民族农村女性的健康贫困脆弱性更高,少数民族女性受地域、性别、文化、宗教、经济、交往等多方面的影响,缺少家庭权利和社会权利,对身心健康产生不良作用,其健康贫困是各种不平等叠加的结果。在模型1中,健康状况的回归系数为0.1272,回归系数最大,即影响程度最深,患病或残疾会加剧贫困脆弱性,疾病冲击不仅会加大医疗支出和家庭负担,还会通过降低劳动时间和劳动效率来影响健康人力资本存量,健康状况欠佳的农村女性发生灾难性卫生支出的可能性更大。婚姻状况对农村女性的健康贫困脆弱性无直接影响。
从卫生服务看,常去看病点、到最近看病点时间、医生水平和药品种类对两类农村女性的健康贫困脆弱性有影响,均在0.05的水平上显著,村卫生室数量对伤残或患病农村女性无显著影响。常去较高层次医院看病的农村女性健康贫困脆弱性更低。一般来说,不同层次就诊机构的医疗水平和收费标准存在差异,首选优质看病点能得到高质量的卫生保健服务,可以降低健康贫困脆弱性。到最近看病点时间与健康贫困脆弱性呈正相关,到最近看病点时间长不但影响农村女性的就医行为,还会延误病情治疗,缩短就医时间能有效降低农村女性的健康贫困脆弱性。农村基层妇幼机构稀缺,面临着医疗人才匮乏,医疗水准不高的窘境,医生水平越高,则农村女性的脆弱性越低。而对药品种类满意度越高的农村女性发生健康贫困的概率越大,可能是高脆弱农村女性对药品的需求度大,产生额外的医药费用。村卫生室数量在模型3中呈显著负向影响,村卫生室数量的增多会降低健康农村女性的健康贫困脆弱性,而对伤残或患病农村女性无明显作用。
从医疗保障看,参与新农合对两类农村女性的健康贫困脆弱性有负向影响,均在0.05的水平上显著,即新农合等医疗保障的缺失将会增大农村女性健康贫困脆弱性,而医疗自付费用比例仅对伤残或患病农村女性的健康贫困脆弱性有影响。在农村地区,医疗保障制度的反贫困效果主要集中在新农合,但新农合的减贫效应有限。新农合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阻断健康与贫困的恶性循环,其作用点在于补偿机制能够减轻农户的医疗负担以及改变居民健康投资不足的现状。(34)左停、徐小言:《农村“贫困—疾病”恶性循环与精准扶贫中链式健康保障体系建设》,《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在制度优化上仍需改进,尤其在加大宣传、简化程序、充分利用结余资金、降低省外报销难度等方面。(35)骆怡:《新农合缓解农民“因病致贫”的效果分析及其制度优化建议》,成都:西南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还有一些花费多的大病尚未列入报销范围。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在一定范围内可以降低健康冲击对女性物质资本的负向影响,增强风险承受能力,提高女性处于非贫困状态的概率,对抑制因病致贫和因病返贫具有良好的政策效应。提高医疗自付费用比例能有效降低伤残和患病农村女性的健康贫困脆弱性,伤残或患病农村女性可能会发生更多的灾难性卫生支出,报销力度越大,医疗自付费用越低,因疾病负担陷入贫困的可能性越小。
从疾病预防看,及时就医、常关注健康保健知识和合理安排饮食对两类农村女性的健康贫困脆弱性均有影响,定期健康体检在0.05水平上仅对伤残或患病农村女性的健康贫困脆弱性有显著影响。良好的看病习惯、常关注健康保健知识和合理安排饮食能有效降低农村女性健康贫困脆弱性。农村女性疾病预防意识淡薄,储蓄性和资产性收入缺乏,大多存在“小病熬、大病拖、绝症弃”的不良习惯,而预防为主是降低女性疾病负担的有效途径。及时就医能提前筛查出农村女性的隐性疾病,使病情得到及时地预防、控制和治疗;常关注健康保健知识能提高农村女性的健康素养,增强其疾病预防与控制意识,在一定程度上能预防健康贫困的发生;营养品的匮乏对农村居民的身体健康有很大影响,对女性的影响更大。(36)王冬梅、罗汝敏:《健康方面的性别不平等与贫困》,《妇女研究论丛》2005年增刊。在家庭资源分配上,女性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农村地区妇女仍信守孩子、老人和丈夫优先的传统观念,女性欠缺足够的营养。定期健康体检与伤残患病农村女性的健康贫困脆弱性呈正相关,这可能是由于定期健康体检的农村女性大多健康状况不佳,且会产生一定的费用,即常定期健康体检的农村女性会表现出较高的脆弱性。
四、结论与政策启示
(一)结论
本文利用全国五省“精准健康扶贫与人口发展”的专项调查数据,对农村女性健康贫困脆弱性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主要有如下发现。
首先,农村女性的健康贫困脆弱性均值为0.388,17.56%的农村女性陷入健康贫困的可能性较高,民族自治地区农村女性的健康贫困脆弱性更高,意味着民族地区农村女性因遭受健康风险冲击而陷入贫困的概率较大。可以看出,农村女性健康贫困状况不容乐观,性别视角下农村健康防贫形势依然严峻,虽然贫困人口数量急剧下降,但是部分农村女性仍处于健康贫困脆弱状态,因病致贫返贫的可能性相对较高。随着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健康扶贫的治理目标将过渡到对社会福利的健康保障,但疾病风险的社会适应性仍然较弱,脱贫后的反弹和内卷化现象严重。前期过硬的政治任务和过高的兜底保障可能引发“棘轮效应”,产生“等、靠、要”的懒惰思想,导致贫困户脱贫后的内生发展动力不足。(37)贾清萍、李丹:《健康扶贫常态化转型的优化策略:基于核心利益相关者的博弈分析》,《中国卫生经济》2020年第11期。当前脱贫评估主要采用以“脱贫摘帽”为目标的量化指标,缺少对贫困人口人力资源“质”的持续改善。从当前健康扶贫的情况来看,经济发达地区卫生资源富足,而民族地区和贫困地区则较为薄弱,基础设施建设不足等问题在短时间内难以有效解决,即使消除了绝对贫困,但依然面临较高的返贫风险。在全面乡村振兴进程中,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关键点仍是这些重点地区。
其次,老年、受教育程度低、少数民族和伤残患病的农村女性具有较高的健康贫困脆弱性。本文发现弱势女性更容易陷入健康贫困。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女性群体面临着较高的健康风险,由于“精英捕获”现象的存在,在平等资源竞争中弱势群体难以获得充分而有效的健康资源。同时,扶贫资源“扶富不扶贫”的问题未得到根本性改善,健康扶贫依然存在卫生资源瞄准偏差等问题。(38)王高玲、叶天瑜:《基于制度供给视角的健康扶贫政策探析》,《中国卫生经济》2018年第1期。“全面脱贫”是举全国之力和大量资源消除的区域性整体贫困,存在突发性的贫困风险,因病致贫返贫问题可能会日渐凸显。而老年人、妇女、儿童、伤残患病等弱势群体是遭受健康风险冲击的首要对象,且抵御风险冲击的能力不足。(39)徐佳琳:《老年人慢性病患者的健康贫困脆弱性研究》,广州:广东药科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0年。进入后扶贫时代,帮扶对象也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主要着力于相对贫困人群的治理。基于此,构建健康扶贫的接续机制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应有之举。
最后,卫生服务好、医疗保障高和疾病预防到位三方面因素均对农村女性健康贫困脆弱性有显著的降低作用,对健康农村女性和伤残或患病农村女性的健康贫困脆弱性分样本回归发现,部分因素的影响作用存在差异。农村地区妇幼保健机构的卫生服务能力是保障女性健康的客观条件和重要基础,然而农村地区基层医疗卫生能力有限,难以满足妇幼保健服务需求和健康资源在性别间的有效配置。其主要表现在乡村医生诊疗水平有限、医疗效果不佳等,使得农村女性极易陷入健康贫困的窘境。农村女性的生理和生育需要更多的健康资源,然而现有政策在实施过程中缺乏将社会性别意识融入健康促进等措施。由于新农合制度保障能力的不足和保障形式的单一化,偏远地区仍然存在着发展效率与社会公平之间的冲突,且新农合制度仍存在社会性别盲点,存在保障措施家庭化和偏男现象等问题。大病保险和商业保险的参与率较低,农村女性缺乏对“两癌”等保险补偿机制的正确认知,存在不会患病的侥幸心理和参保是浪费钱的错误心态。健康素养关乎健康状况,也关系到患病后对医疗机构和治疗方式的选择和信任程度。饮食结构不合理、健康观念陈旧、生活习俗不良、卫生环境恶劣等诸多因素导致疾病易生,不正确的就医行为和讳疾忌医的迷信思想会延迟治疗的最佳时机,加剧病情蔓延,从而造成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发生。
(二)政策启示
健康是脱贫和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和动力,农村女性健康贫困脆弱性的研究对于精准识别高健康贫困脆弱群体和判别健康致贫因素有着实际的作用,并有助于从健康视角阻击女性贫困。基于以上结论,本文对后扶贫时代农村地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健康防贫治理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建立健康风险预警机制,精准识别健康贫困高脆弱群体。应改变单一的收入贫困评判标准,界定更加完善的因病致贫监测线,建立疾病经济风险参照指标,其中民族地区应因地制宜构建科学的脆弱性评价体系,从多角度建立精准的因病致贫返贫风险预警机制。同时将巩固脱贫成果的工作重心转移到对高脆弱农村女性的精准识别和有效帮扶上来。建立居民主动申请、部门信息比对、基层干部定期跟踪回访相结合的女性易返贫致贫人口发现和核查机制,实施贫困女性动态管理。加强医疗健康数据的搜集和分析,充分利用大数据、云计算和仿真模拟技术等手段,借助统计模型预测脱贫地区健康贫困的类别特征、分布范围及变化规律。剖析“疾病—贫困”之间的内在逻辑,靶向瞄准疾病成因、高危群体和重点区域,实施动态管理、风险评估及精准施策。加强对老年、受教育程度低、少数民族和伤残患病农村女性的信息网格化管理,完善健康扶贫信息系统,实现健康贫困脆弱农村女性帮扶的整体性覆盖。坚持预防性措施和事后帮扶相结合,精准分析返贫致贫原因,并及时采用前瞻性的措施降低农村女性的健康贫困脆弱性,提高其健康修复能力,防止健康致贫现象的发生。
第二,从性别视角提高农村地区的卫生服务水平,统筹完善农村女性的医疗保障制度。政策支持和资源输入重点向民族地区倾斜,增加对经济落后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优化卫生服务资源配置,构建更加完善的健康卫生体系。分阶段、分对象、分类别调整脱贫攻坚期超常规保障措施,如建设合理的乡村医生队伍,增补女性医生的数量和加强乡村医生的社会性别培训;增添先进的配置设施,如妇科孕产等方面的医疗器材。进一步完善村卫生室、乡镇医院的规范化建设,提高卫生服务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可及性,在落后地区建立妇幼危急重症救治中心。通过“互联网+医疗健康”等手段将优质妇幼资源向基层下沉,加强县域医疗资源共建共享,实施家庭医生签约全覆盖,建立婴幼儿托育管理服务,提高妇幼健康服务质量。完善农村医疗保障制度,鼓励农村女性享有平等的医疗保险参与权,构建女性特有疾病的多重保障,如针对宫颈癌、乳腺癌等大病,合理建立大病保险、补充保险、商业保险和医疗救助等兜底保障。调整医保支付结构,提高农村女性的医疗报销比例,扩大医疗救助范围。对妇科疾病进行分级诊疗、随访评估、适时转诊等工作,避免过度医疗引起额外的消费负担。
第三,加强健康教育和健康管理,通过提高农村女性的健康素养来增强可持续脱贫能力。基于“大卫生、大健康”理念,引导农村女性养成良好的健康生活习惯,提高健康素养。政府主管部门应加大卫生保健和膳食营养等基本疾病预防知识的教育力度,在农村地区开展健康教育专题报告或座谈会,加强女性对妇科疾病和生殖健康的正确认识,了解科学避孕节育常识,提高女性的疾病应对能力。鼓励农村女性积极参与和配合“两癌”和其他疾病的筛查工作,定期派遣医疗队下乡开展免费健康检查和产前孕育检查,将疾病预防关口前移。同时纳入以人格塑造和自信培育为导向的心理健康教育,激发农村女性自我发展的内生动力。坚持扶贫与扶志、扶智相结合,防止政策泛福利化倾向,发挥奋进致富典型示范引领作用,增强社会性别意识和女性赋权,通过提高女性地位促进女性健康,建立本土化健康理论。以政府主导、社区协助和个人参与等多元形式提高女性健康自我管理能力,满足女性不同生命周期的健康需求,提高健康人力资本存量,培育农村女性的可持续脱贫能力,推动健康乡村建设与产业振兴协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