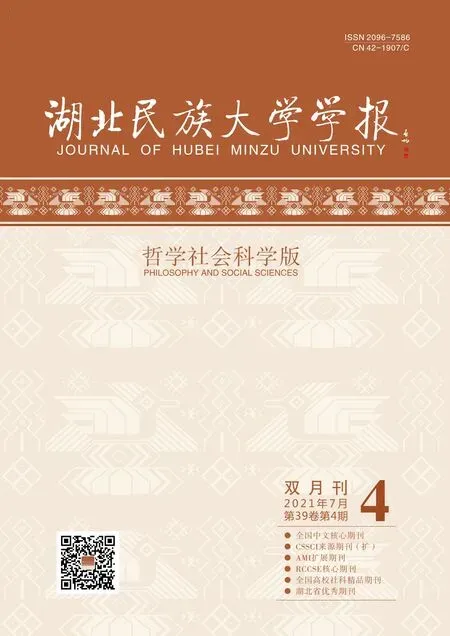真善之间:民族志书写的价值性探析
李银兵 赵琳琳
20世纪末,随着弗里曼与米德、奥贝赛克里与萨林斯、斯图尔与孟朱、蒂尔尼与沙尼翁等人类学者之间针对同一社会现象或文化事实而引发的几场著名争论的出现,再加上《一本严格意义上的日记》《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摩洛哥田野作业反思》《天真的人类学家》等民族志理论反思作品的推动,民族志写作将“人类学置于当代话语中有关表述社会现实的问题争论的漩涡中心”(1)乔治·E.马尔库斯、米开尔·E.费彻尔:《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一个人文学科的实验时代》,王铭铭、蓝达居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8页。,并“被想象为人们认为事物看起来像什么和事物的真实情形是什么之间永无休止战争的战场”(2)Clifford Geertz,Works and Lives:The Anthropologist as Author,Palo Alto:Standford University Press,1988,p.9.。面对这些争论,绝大多数人类学者认为其不仅仅是简单的“科学”与“非科学”立场之间的方法论之争,更是人类学内部“科学”与“人文”立场之间的价值观之辨。比如,穆尔在总结蒂尔尼揭露沙尼翁在雅诺玛迷人中做研究期间严重违反伦理而引发的争辩时说:“然而令人惊讶的是,这场争论中的许多主要人物都以一场‘科学的’和‘人文主义的’或者‘后现代的’或‘反科学的’人类学家之间的斗争来看待这场论战。”(3)杰里·D.穆尔:《人类学家的文化见解》,欧阳敏、邹乔、王晶晶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387页。的确,“如通常一样,人类学的独特性和贡献在于其既舒适又很尴尬的在事物之间的位置,在科学与人文之间,在历史与文学之间,在我们与他们之间,在客观性与主观性之间,在具体与抽象之间,在特殊与普遍之间”(4)Gregory Reck,“What We Can Learn From the Past,” Anthropology Newsletter,vol.36,no.4,1996,p.7.。学科的折中性质规约着其表述方法的折中性,民族志书写理应是“志”“论”“文”三种文体融合的产物。因此,针对当前人类学界存续的“马林诺夫斯基是优秀田野工作者或种族主义者”“米德是世界母亲或骗子”“巴利天真或深沉”“萨林斯是历史学家或神话学家”的灵魂拷问时,我们不应用老套的方式,无奈而又简单地再一次发出“人类学究竟是什么”的跨世纪追问和感叹,而应像拉比诺倡导的那样,把研究重心放在“对文化中的表征传统和元表征的元传统(metatraditions of metarepresentation)的一般性关系关注”(5)詹姆斯·克利福德、乔治·E.马库斯编:《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高丙中、吴小黎、李霞,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304页。上,才能最终抓住人类学和民族志书写的本质及其背后潜存的深层逻辑关系。基于此,本文在把握民族志书写历史的基础上,牢牢抓住民族志书写中存续的真善关系,着力对民族志书写的价值关联性、价值多维性及价值选择性进行较为详实的探析,以期推动求真至善唯美的民族志书写范式的最终形成,以就教于大家。
一、从真到善:民族志书写的价值关联性
人类学家罗伊·拉帕波特指出,自人类学诞生之日起,其内部就有客观主义和人文主义两种传统齐头并进,但在人类学发展中,这两种传统并不总是和谐相处的,特别是当它们共存于同一批人的头脑中时,两种传统的激进分裂就显而易见,进而导致误导性的后果出现。(6)Roy Rappaport,Humanity’s Evolution and Anthropology’s Future,in R.Borofsky,eds.,Assessing Cultural Anthropology, New York:Mcgrawhill,1994,p.154.而《东方学》作者萨义德更是直言不讳地指出:“在后启蒙时期,欧洲文化正是通过这一学科以政治的、社会学的、军事的、意识形态的、科学的以及想象的方式来处理甚至创造东方的。”(7)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第4-5页。的确,纵观民族志书写历史,从科学民族志书写的“价值无涉”到后现代民族志书写的“价值关联”,从坚守民族志书写的“科学性”到倡导后现代民族志书写的“人文性”,马林诺夫斯基式的“日记病”(8)所谓“日记病”(Diary Disease)的说法,源自于罗兰·巴特的文学批评。罗兰·巴特原初的意思是指,日记作为作家惯用的文本书写策略和修辞手法,能使作家更好地表达自己、解释自己及评判自己。因此,长期以来“日记”作为一种书写体裁被许多作家使用。但后来,随着一部分作家对这种体裁的滥用,再加上在一些强有力的批判理论的影响下,特别是萨特对不诚实的批判和马克思对意识形态的批判,“日记”这种书写策略和修辞手法内部存在的矛盾和弊端逐渐显现,“日记”这种修辞手法随之也从最初的极为前沿、先锋、新锐、让人耳目一新的形象,沦落为一种“病”,一种病态和毫无创意的“二等货色”。都在其中时隐时现地折磨着人类学家,以致于使人类学家几乎不堪重负而陷入“精神分裂”。因为“如何探寻这种氛围——一个知识论的、道德的、意识形态的、职业性的和个人困惑的巨大纠缠物,一个为另一个提供养料,并且有时蔓延到了非常接近皮罗主义的地方——是它本身的一个问题”(9)Clifford Geertz,Works and Lives:The Anthropologist as Author,Palo Alto:Standford University Press,1988,p.90.。可以说,“日记病”的产生及解决尝试,是对民族志书写中科学与艺术、真理与价值、文本化与主体化等各种潜存关系的最好表征。“文化和历史是互相容受的,而不是实质上分离的两个实体。隐喻和真实合而为一,启动了社会。”(10)克斯汀·海斯翠普:《他者的历史——社会人类学与历史制作》,贾士蘅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5页。因此,笔者在本部分主要通过民族志书写历史去探寻价值性在民族志书写中从“遮蔽”到“暴露”的历程及背后缘由,以此彰显民族志书写的价值关联性。
马林诺夫斯基和拉德克利夫-布朗作为现代民族志的奠基者,他们在20世纪20年代共同确立了被后人称之为现实主义风格的民族志范本。现实主义写实风格的民族志文本,也就是今天人类学界普遍言说的科学民族志。具体而言,科学民族志立足于自然主义、化约主义、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等理论之上,用“作者疏离型”的方式去保证描述文化的客观性,以此来支持其方法的科学性和描述文化或生活的具体感,最终实现民族志书写对于大理论、整体观、真诚性的承诺。而从科学民族志发展史来看,不管是作为科学民族志集大成者的功能学派,还是后来接踵而至的文化人格学派、新功能学派及新进化论学派,他们确实很好地维护和践履了“要把社会事实作为物来考察”(11)埃米尔·迪尔凯姆:《社会学方法的准则》,狄玉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25页。的传统和承诺。理由如下。首先,在科学民族志书写中,作为书写主体的作者始终处于隐身的状态,其对于书写的文化或社会的认识和理解都来自于田野观察,书写主体仅仅是以一个对特定文化或社会的反映者或摹写者身份出现。再加上书写中缺少文化主体的介入和发声,更是使得科学民族志得以最终消弭不同主体的价值需要,呈现一种书写“文化”的客观态势。其次,从科学民族志书写的过程看,科学民族志书写中建构了一套客观的书写范式。科学民族志书写拥有保持“中立”的书写主体、直观实存的书写对象、科学的田野调查实践和客观的书写方法,实现了文化事实性、田野实在性和书写真实性的“三位合一”。再次,从科学民族志书写结果看,科学民族志仅仅追求对静态文化、客体文化及直观文化的书写,而不关注文化的动态变化、文化主体的深层价值和文化建构中的主体意识。诚然,从马克思主义科学认识论角度看,科学民族志书写方式是建立在形而上学基础上的消极的、被动的直观反映论,但在科学民族志作者眼中,这样的“我—见证”(I—Witnessing)类型的认识方式在无形中更能维持或增强其对于文化书写的科学性。因此,最终的结局则是,在科学民族志书写中,价值无涉的中立立场使得民族志书写的价值性被民族志作者有意或无意地遮蔽了。
后来,民族志书写的价值性从遮蔽走向暴露,实属偶然中的必然。让人意想不到的是,科学民族志在民族志书写中的核心地位率先被一个“靠婚姻挤进人类学圈子里的女人”所打破。马氏遗孀抛出的《一本严格意义上的日记》,不仅曝光了其前夫的“丑闻”,也曝光了人类学乃至民族志书写的“丑闻”。正如有学者指出:“与作为伟大人类学家的马林诺夫斯基在《西太平洋的航海者》等书所呈现的‘文化移情’相悖,作为‘常人’的马林诺夫斯基在《日记》中所流露出的‘无法移情’,令不少人对于马氏人文科学的方法与理论顿失信任。”(12)勃洛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一本严格意义上的日记》,卞思梅、何源远、余昕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中文版序”,第6页。《日记》发表后,虽然当代美国最负盛名的人类学家格尔茨多次著文强调《日记》所揭露的与其说是关于道德的问题,不如说是涉及书写策略和方法选择的认识论问题。但毫无疑问的是,自《日记》出版之后,《日记》所富有的文献价值之外的学理价值在人类学家的推动下不断得到提升。特别是《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的相继出版,更是把民族志书写中的真实性问题和价值性问题推向了学术前沿。总之,《日记》的出版使得民族志书写的价值性问题从被遮蔽状态走向了书写实践场,并受到了学界的高度重视。因此,可以说,《日记》的出版是导致人类学界关注民族志书写价值性的导火线和直接原因。
而从深层视角去看,促使民族志书写价值性受到高度关注的因素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首先,解释人类学横空出世,不断冲击英美百年来的书写传统与模式。在现象学、符号学、解释学及语言哲学等理论流派的指引下,格尔茨对胡塞尔、许茨、伽达默尔、巴尔特、维特根斯坦等人的思想进行创新性转换,创造了解释人类学。正如格尔茨所说:“我们想要做但仍未做到的,是发展出一种描述和分析一个特定社会在一个特定时间点上代表性成员经验(指人的经验)的意义结构的方法——也就是说,一门科学文化现象学。”(13)Clifford Geertz,Person,Time and Conduct in Bali:An Essay in Cultural Analysis,Cultureal Report Series no.14,Southeast Asia Study of Yale University,1966,p.7.这样,解释人类学基本上将文化当成意义系统来研究并强调民族志是一种人为的认识过程。同时,在文化意义建构的每个环节,都渗透着民族志作者的个性、情感、价值及观念等主观性因素。因此,解释人类学以倡导人文主义、相对主义和操作主义为核心的解释模型不仅与科学民族志书写的科学模型形成了强有力对照,也架起了民族志书写与价值之间的关联性纽带。
其次,价值性是对日渐增长的人类学实践政治衍生结果的自我批判的产物。自人类学诞生之日起,人类学家就对学科内部蕴含的政治问题进行过争论。比如,人类学学科的产生是否与殖民扩张直接相连,人类学家是否为了获得调研资金而为政府提供特殊服务,民族志书写是否内涵着宣扬西方中心论主张等。到20世纪末,随着殖民体系的彻底瓦解,人类学实践先天具有的政治意蕴日渐鲜明,一系列关于少数民族权力分化与转移的话题得到了进一步深化。比如,民族志书写应该对科学负责还是应该对文化主体负责,少数族群文化是否应该得到保留与保护,西方意识形态是否应该在民族志书写中得到批判与反思等。又如,萨义德作为一位来自东方而又生活于西方的学者,其在《东方学》中指出:“东方学作为一种话语方式在文化甚至意识形态的层面对此组成部分进行表述和表达,其在学术机制、词汇、意象、正统信念甚至殖民体制和殖民风格等方面都有着深厚的基础。”(14)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第2页。因此,中国学者王铭铭认为,萨义德之所以书写《东方学》,“不在于学科范畴的创设,而在于采取知识社会学的分析方法,揭示隐藏在学科背后的意识形态”(15)王铭铭:《非我与我》,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241-242页。。总之,在对人类学及民族志书写背后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主张进行批判与反思过程中,民族志书写与价值的关联性得到了进一步拓展。
再次,民族志书写的多元性引发了人们对书写价值性的考量。20世纪中叶以来,随着殖民体系的逐步瓦解、社会生产力的不断进步,人类社会也随之不断发展。在这种时代大背景下,人类学及其民族志书写也走过了过去为殖民服务的“不光彩”历史,迎来了为文化多样性和人性普同而书写的“高光时刻”。而在人类学及民族志书写的这次伟大转变中,主体及人文性在民族志书写中慢慢得到张扬。体裁多样、范式多样及主体多重,则是这种张扬在民族志书写上的具体表现。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主体及人文性一旦进入民族志书写实践场,过去那种从17世纪以来的西方科学合法库中早已排除了的某些富于表现的样式——以“直白”、透明的含义之名的修辞,以事实之名的虚构,以客观性之名的主观性等科学品质就落户于文学范畴之中。因此,“文学文本被认为是隐喻和寓言性的,由杜撰而非观察到的事实构成;它们为作者的情感、沉思和主观‘天才’保留了大片天地”(16)詹姆斯·克利福德、乔治·E.马库斯编:《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高丙中、吴晓黎、李霞,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33页。。这样,影像民族志、关系民族志、实践民族志、感性民族志、线索民族志等不同书写范式,交互主体、日记主体、口述主体、记录主体等多重书写主体以及书写为文化自身、文化主体、书写主体、西方主体等多重价值随之出现。但毫无疑问的是,民族志书写多元性的出现,不仅是对传统民族志书写科学性批判的产物,也内涵着对民族志书写价值性的考量,还凸显了民族志书写的价值性。
最后,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理论为民族志书写的价值关联性提供了坚实的学理支撑。一般而言,民族志书写范式一般经历了三种理论传统:以涂尔干为代表,把书写对象作为客观事实,追求科学性为目标的实证主义传统;以韦伯为代表,把书写对象作为文化事实,追求解释性为目标的人文主义传统;以马克思为代表,把书写对象作为社会事实,追求批判性为目标的批判主义传统。(17)李银兵、曹以达:《民族志的三重叙事与实践反思》,《云南社会科学》2019年第1期。针对实证主义书写传统“见物不见人”和人文主义书写传统“见人不见物”的不足,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不断开拓创新,逐渐成为分析社会科学的核心理论。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作为分析资本主义世界科学的理论,以对资本主义内部矛盾的剖析、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批判及倡导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闻名于世。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把科学实践观、实践与认识辩证关系及真理和价值的一致性等观点用于民族志书写分析,则使民族志书写的实践性本质和关系性特征得到了最大程度彰显。同时,在实践基础和理论基础双重作用下,民族志书写从追求单纯的真实性,逐渐走向了追求科学与价值的统一目标诉求。当前,针对资本主义的不断发展导致西方工人阶级在精神上有所懈怠的问题,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纷纷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意识形态”和“文化批评”。比如,卢卡奇、葛兰西及詹姆逊等,更是把马克思主义价值批评理论不断向前推进。综上,民族志书写在追求真实的过程中,其内含的价值关联性也得到了正式确认与彰显。
总之,民族志书写的价值关联性从遮蔽走向彰显的过程,是和科学民族志书写走向后现代民族志书写的历程息息相关的。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说,民族志书写的价值关联性和民族志发展历史是同步的。同时,我们也要承认,在民族志书写中,遮蔽价值有遮蔽价值的客观性理由,彰显价值有彰显价值的主体性诉求。个中利弊,看似难以明晰,但恰恰是在人类学的学科属性和民族志书写的历史实践中早已得以明示。因为我们相信埃里克·沃尔夫所说的,人类学是“人文科学中最科学的,是科学中最人文的”(18)Eric Wolf,Anthropology,Englewood Cliffs,N.J.:Prentice-Hall,1964,p.988.“文化身份与文化政治学密不可分”(19)Adam Kuper,“Culture,Difference,Identity,”转引王晓路、石坚、肖薇:《当代西方文化批评读本》,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79页。的经典概括。因此,我们始终坚持“民族志无论其在田野作业中的调查,还是调查之后的书写,都不仅仅是简单的对象还原和重现。因而,它依据的标准不是纯粹的客观主义。同时,承认民族志的建构性亦非否认民族志对象的客观性”(20)李立:《民族志理论探究与文本分析》,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32页。。
二、真善之间:民族志书写的价值多维性
从字面意义上看,民族志就是关于民族的写作实践。而在这个实践中,没有理论的民族志写作是不可能的,没有田野的民族志理论也是毫无意义的。(21)阿兰·巴纳德:《人类学历史与理论》,王建民、刘源、许丹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年,第5页。因此,在学术界,作为理论的实践和实践的理论于一身的人类学,一直以来都是作为一门折中性质的学科而出现。同时,“众所周知,人类学作为社会科学的一门学科主要是探究社会和文化之间的关系。如果要给这门学科下个定义,而又不带一丝恶作剧色彩的话,它应该是在文化形式和社会意义两方面对人类的常识进行比较研究的一门学科”(22)麦克尔·赫兹菲尔德:《什么是人类常识:社会和文化领域的人类学理论实践》,刘珩、石毅、李昌银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年,“前言”,第1页。。相应地,其表述方法也应该是折中的。(23)奈杰尔·拉波特、乔安娜·奥弗林:《社会文化人类学的关键概念》,鲍雯妍、张亚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年,第211-214页。此外,对于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的人类学来说,其和自然科学的最大不同在于它的研究对象是人的社会活动或文化活动,且研究人的社会活动或文化活动内部存在很多自然科学没有的困难。其最大的困难在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是一种双向获取信息的关系,且双方都受主体的主观意愿影响。简言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与价值有关。“具体地讲,价值作为哲学范畴,表示客体对于主体所具有的积极的或消极的意义。价值关系就是意义关系。”(24)袁贵仁:《价值观的理论与实践——价值观若干问题的思考》,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4页。价值的本质告诉我们,价值是一对关系范畴而不是某种实体范畴。价值离不开客体,但不能归之为客体;价值离不开主体,但也不能归结为主体。价值是主体和客体之间的一种基本关系,但在这种基本关系下,主体是处于优先地位的。因为真理要求主体去符合客体,价值则需要客体去满足主体。基于此,就民族志书写来说,应该把文化事实和主体需要形成的辩证关系作为出发点,结合民族志书写实践,着力去探析主体在文化书写中的表现,最终才能实现“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的统一,内在地体现了人的创造活动中体现事物及其规律的‘物性’特征和凝结着人的本质力量的‘人性’特征的内外尺度的统一”(25)郑杭生、杨敏:《社会学方法与社会学元理论——个人与社会关系问题的方法论意义》,《河北学刊》2003年第6期。。因此,在民族志书写中,书写者要大胆承认自身对客观事实的需要和对价值诉求的渴望,在真善之间,充分展现民族志作者的主体价值性。
当然,主体价值性在民族志书写中得到充分展现,则是在后现代实验民族志阶段的事情。“出于极为重要的理论原因,目前民族志实验文本给予作者相当重要的角色,让他出现在关于其田野工作及其发现的陈述中,对自己的思考作出解说。作者的暴露已成为当前实验的深刻标志。”(26)乔治·E.马尔库斯、米开尔·E.费彻尔:《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一个人文学科的实验时代》,王铭铭、蓝达居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68页。民族志作者一旦暴露在实验民族志书写实践中,科学民族志书写“文化”的传统瞬间就转换到实验民族志文化“书写”上。比如,弗里曼在与米德的隔空争辩中认为,米德笔下的萨摩亚文化,无非是她本人想象力的产物,因而米德文本是虚构的。同样,王铭铭也认为:“为了本文化的改造,而通过文化翻译的‘讹’来构造异文化的‘诱’,是米德人类学的主要特点。”(27)王铭铭:《西方人类学思潮十讲》,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83页。这样,“作者渗透型”的书写方式无疑凸显了主体及其价值在民族志书写中的地位与作用。因此,民族志书写什么、如何书写及书写价值等一系列问题,则与书写主体的价值性有着直接的关联性。具体就后现代实验民族志来说,处于真善之间的民族志书写,其内在的主体价值性主要通过书写的价值多维性得到了集中表征。具体而言,本部分笔者主要从本体论、认识论及价值观三个层面去探析民族志书写中的价值多维性。
首先,范式并存反映书写主体的本体论。简单地说,民族志就是“写文化”。在其中,文化是客体,书写者是主体,因而书写范式就是书写主体选择的民族志书写本体。当前,作为“写文化”的民族志在激烈争论情境下陷入了严重的“表述危机”。而“现时代的表述危机是一种理论的转变过程,它产生于一个特定的变幻时代,与范式或总体理论处于支配地位的时期让步于范式失却其合理性和权威性的时期、理论中心论让步于现实细节中心论这一过程有着密切关系”(28)乔治·E.库斯、米开尔·E.费彻尔:《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一个人文学科的实验时代》,王铭铭、蓝达居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30页。。这样,书写范式作为民族志书写的本体,在兼具解构和建构的实验民族志中,有人企图对其实现彻底建构,有人寻求对其进行延存,有人希冀对其创新创造。影像民族志、虚拟民族志、主体民族志、感性民族志、线索民族志、在线民族志、关系民族志等争相斗艳,充分说明了书写主体对于书写范式的多样诉求。但总的来说,多种多样的民族志书写范式可以归为三种类型:一类是以《西太平洋的航海者》为标志的把研究对象作为描述对象的写作范式;一类是以《摩洛哥田野作业反思》为代表的把人类学家实地调查过程作为描述对象的写作范式;一类是以《纳文》为基础的把人类学家的民族志写作过程当作描述对象的写作范式。(29)格雷戈里·贝特森:《纳文——围绕一个新几内亚部落的一项仪式所展开的民族志实验》,李霞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代译序”,第16页。书写范式的选择及范式多样化的并存,都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书写主体在书写范式选择上的价值诉求。简言之,主体价值导引了书写范式的产生及存在状态,范式并存是主体价值观在民族志书写中的写真。
其次,部分真理展现书写主体的认识论。相对于科学民族志一味地追求事物的客观性来说,后现代实验民族志注重把主体性和客观性结合起来,认为文化分析本质上是不完全的相对主义认识。比如,格尔茨通过乌龟驮乌龟的故事告诉我们,文化分析本质上是不完全的,你越是深入,就越是不完全。因此,人类学不以达到观点的一致性为目的,而应以书写或辩论的巧妙为标志。又如,克利福德在看到民族志的文学性远远超出了好的写作或独特风格所能概括的地步,并在民族志书写中大展修辞、虚构、主观性等科学民族志书写所排除的品质时,他得出了民族志书写本质上是有承诺的、不完全的部分真理的结论。同时,在文化相对主义的指引下,诗歌、小说、戏剧、对话、反讽、暗喻、深描、虚构、反思等多种体裁和多元修辞手法在民族志书写中交叉运用,更是体现了实验民族志“实验”的属性。比如,拉比诺把自身的田野过程作为研究对象,运用小说家方式对田野经验进行建构。虽然布迪厄称之为一种明显的自恋面向自我的转折、与文学灵感迸发之自我满足的决裂,是一种对求知主体的对象化,但拉比诺自己却认为,“在其各种表现形式中,文化是由多种因素武断地决定的,不可能自我中立地呈现,或以一种声音呈现。每一文化事实都可以既被人类学家,也被其持有者,赋予多种解释”(30)保罗·拉比诺:《摩洛哥田野作业反思》,高丙中、康敏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143页。。又如,巴利在与多瓦悠人的互动中,用自我戏谑的方式告诉我们:人类学者必须调整其学术成见、反思研究盲点,在自我反讽中才能摆脱“天真”,走向成熟和理性。此外,巴利还用反讽的方式向我们传达了这样的信息:民族志作者和文化主体之间的认识是交互式的,民族志作者对文化主体和特定文化的认识是有限的。总之,后现代实验民族志书写打破了传统民族志对于书写主体的约束,使书写者在书写中变得更为自由。相应地,民族志作者对于认识论上的目标也变得不那么绝对化,他们逐渐放弃了对于绝对真理的追求,转为对相对真理的诉求。
再次,多重意义彰显书写主体的价值观。“在传统民族志中,通过给一个声音以压倒性的权威功能,而把其他人当作可以引用或转写其言语的信息来源,‘被访人’之复调性受到限制和整编。一旦承认对话论和复调是文本生产的模式,单声部的权威就受到质疑,这种权威也被揭示为一门主张再现文化的科学的特征。”(31)詹姆斯·克利福德、乔治·E.马库斯编:《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高丙中、吴小黎、李霞,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44页。的确,后现代实验民族志多声部的发声,使多元书写主体得以形成。相应地,多重意义也在后现代民族志书写中显露出来。而对于民族志书写中的多重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是指由于多重主体的介入,文化意义变得更为丰富,因而对文化意义的探析也就变得更为复杂和深入。比如,格尔茨在分析巴厘人日常生活的文化世界时,借用现象学社会学大师许茨的主体分析框架去探析文化意义。他认为巴厘人的文化世界是由“前辈”“同时代人”“同伴”“后继者”在交互中共同创造出来的意义结构。而对这个意义结构的“深描”,则是文化人类学者的核心任务。其二是指民族志书写的价值指向变得复杂多样。在传统民族志书写中,民族志书写的最终指向,也是其唯一指向,则是达致对文化的客观呈现。而在后现代实验民族志书写中,由于多重主体的彰显和参与,民族志书写的价值指向变得复杂起来。比如,萨义德在《东方学》中揭示了知识与文化霸权和政治支配的密切关系,揭露了西方中心论和文化霸权对东方民族渗透的本质事实。又如,列维-斯特劳斯在《忧郁的热带》中那一句“我讨厌旅行,我恨探险家。然而,现在我预备要讲述我自己的探险经验”(32)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忧郁的热带》,王志明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第1页。的开场白,不仅把民族志作者在民族志文本中的曝光度展现得淋漓尽致,也把民族志书写的价值指向推向更为迷离的状态。此外,对话式和日记体民族志书写,更让人对民族志书写的价值指向捉摸不透。那么,主体性的全面介入,民族志书写的价值和意义究竟何在?文化真实探寻、殖民霸权渗透、作者意图展示、文化主体情感抒发、西方意识形态批评……但不可否认的是,由于多重主体的介入,不仅使得文化的多重意义得到了揭示,也增强了民族志书写的多维价值性。
正如罗萨尔多所说:“历久不变的原始人形象并非一项发现,而是人类学研究卓有成效的方法创造出来的幻象。”(33)罗纳托·罗萨尔多:《伊隆戈人的猎头——一项社会与历史的研究(1883—1974)》,张经纬、黄向春、黄瑜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页。的确,在从科学民族志书写的“价值无涉”到后现代实验民族志书写的“价值关联”的转换中,以往那种以绝对主义、机械主义和客观主义为特征的现代主义民族志书写范式在一定程度上遭到了摒弃,而以多种范式并存、多样体裁运用、多元修辞使用及多维价值融入为特征的后现代实验民族志书写方式则得到了极大提倡。当然,对于后现代民族志书写方式的形成来说,诸如列维-斯特劳斯等人类学者在田野中进行的自我批判与自我反思在其中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为什么我跑到这里来?我到底是希望些什么?我的目标到底是什么?人类学研究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它是不是像其他正常的职业那样的一种职业。”(34)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忧郁的热带》,王志明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第488页。因此,后现代书写方式是民族志书写与价值关联的具体表征,也是对民族志书写的价值多维性的最好印证。因此,“当代人类学的‘本体论转向’强调多重宇宙论比较,但不能武断‘异文合并’以求纯化。阐释实为同一世界多元文化主体的话语权实践,仅从认识论上强调‘裸呈’田野对象叙事或不同主体视角,并不能消除权力不对等。在此意义上,民族志并非 ‘写’而是 ‘做’出来的,‘做’得好坏,不仅与不同主体的认识角度、水平有关,更与阐释的权力实践有关”(35)谭同学:《多重宇宙论并接的交互主体性阐释——兼论 “做” 民族志》,《思想战线》2017年第5期。。
三、求真至善:民族志书写的价值选择性
综上,我们不仅知晓了价值的关系性本质及人文底色,也明白了民族志书写的价值关联性和价值多维性。特别是民族志书写的价值多维性,更是使后现代实验民族志书写呈现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但实验时代处于学术传统的不确定和暂时性过渡期,所以我们难以估计其未来的发展趋势。实验时期最大的危险恰恰在于,有人将它的未成熟状态说成定式。因此,实验时期真正的任务在于跨越现存民族志文体的局限性,描绘出更全面、更丰富的异文化经验图景。(36)乔治·E.马尔库斯、米开尔·E.费彻尔:《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一个人文学科的实验时代》,王铭铭、蓝达居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67-69页。的确,在一定条件下,真理只有一个,价值可以多元。面对多元的价值观,我们必须选择一个最为准确和合理的价值观去指导我们的实践。这对于民族志书写来说,也是如此。正如克利福德在总结《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一书时所说的那样:“本书中的作者没人认为任何文化描述都一样好坏。如果他们支持一种如此无足轻重和自我拆台的相对主义,他们就不会花那么大的力气去写作详尽的、有承担的批评研究文章了。”(37)詹姆斯·克利福德、乔治·E.马库斯编:《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高丙中、吴小黎、李霞,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54页。因此,在真善之间,民族志书写必须进行价值选择,用正确的价值观来引导民族志书写,才能更好地推进求真至善唯美的民族志书写方式的最终形成,才能最终实现民族志书写的价值。
具体而言,民族志书写要在价值多维性中进行选择,最终确定民族志书写的价值导向,则应该从如下几个方面入手。首先,明确民族志书写的相关元问题。真理是主体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价值是指客体满足主体与主体对客体满足自身与否的评价所形成的意义关系。在真理和价值的关系中,真理是基础和前提,价值是对真理的进一步深化和真理发展的动力。任何一次成功的实践活动都是真理和价值统一的产物,即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统一。就民族志书写而言,其是人类学者经过“在这里—去那里—回这里”的田野工作后,对特定文化或社会进行的描述和分析的过程和产物。从本质上说,民族志书写是一次完整的实践活动。实践活动的基本结构包括实践主体、客体及中介三大基本要素,主体客体化、客体主体化的双向运动是推动实践活动顺利运行的机制。基于此,我们认为,只有在理顺真理与价值关系基础上,人类学和民族志书写才能明确自身的价值定位,作出自身的价值选择,实现自身的价值诉求。换句话说,当前人类学界首先应该明确民族志书写究竟是为谁书写、书写什么、如何书写及书写诉求这些元问题,才能进一步发挥书写主体的主观能动性,最终实现推进民族志书写向前发展的目标。同时,在正确的价值观引导下,后现代实验民族志书写中存在的范式并存、部分真理及多重意义等问题,才有可能被视为一种书写策略和方法而存在,并得到进一步承认、规范和统一。一言之,只有明确了民族志书写的本质定义,才能理顺民族志书写中的真善关系,也才能进一步推动民族志书写的价值选择和实现民族志书写的价值追求。
其次,坚守民族志书写的本分。基于人类学的实践理念和民族志书写的目标诉求,笔者认为,文化描述和文化批评是民族志书写的两大功能或者两大维度。但在这两大功能中,文化描述是基础,文化批评是建立在文化描述基础上的产物。因为只有“通过提高传统人类学的异文化描述功能,我们才能提高人类学的本文化批评功能”(38)乔治·E.马尔库斯、米开尔·E.费彻尔:《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一个人文学科的实验时代》,王铭铭、蓝达居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21页。。“在实验性的转换和批评的可能性里,我们把民族志理解为经验研究和写作的一种训练工具,它探究艺术和哲学关注的问题,但它的角度不是超社会的思辨,而是对世界范围内的不同文化的地方情境的独特刻画。”(39)乔治·E.马尔库斯、米开尔·E.费彻尔:《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一个人文学科的实验时代》,王铭铭、蓝达居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229页。因此,在对文化的描述中,民族志作者可以适当置入书写的诗学和政治学,但置入的限度则以不冲淡和提高对文化的描述以及提升对文化的批评功能为限度。反观科学民族志和后现代民族志书写,前者为了科学的原则而缺少了主体人文色彩,后者过分强调主体的能动性而削弱了文化书写的整体性,两种民族志书写方式在文本与主体关系的处理上,都陷入了形而上学的陷阱。如今,针对当前后现代实验民族志书写中存在的“本末倒置”现象,应该运用矛盾的不平衡性原理,找到民族志书写的重心,才能达到民族志书写追寻真实的目的。因此,“在所有的这种多样性和后殖民的转换中,作为基础的马林诺夫斯基式的民族志仍然占据着学科的中心地位,这种实践反过来又继续嵌入在训练模式中,定义着在学者们进入到人类学的学徒工作中什么能做和什么不能做”(40)詹姆斯·克利福德、乔治·E.马库斯编:《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高丙中、吴小黎、李霞,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2页。。坚守民族志书写的本分,不仅是民族志书写的真理性表现,也是民族志书写的价值性追求。
再次,秉承民族志书写的初心。一直以来,人类学都是以实现“文化多样、人性普同”为学科发展目标,民族志书写始终践履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书写理念。从学科属性和书写价值去看,保护文化多样性、发挥文化批评的推动力和促进世界各民族的团结进步,则应是民族志书写初心的具体表现。第一,文化多样性和生物多样性一样,其最大的功用在于当人类遇到危机时,我们可以想到更多的解决办法、找到更好的发展出路。“单一的世界文化将是乏味而令人担忧的,它缺乏多样文化中所具有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一种标准化文化会导致适应能力的丧失,因而将来必定会产生危机。”(41)威廉·A.哈维兰:《当代人类学》,王铭铭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589页。第二,文化批评不是简单的否定,而是在文化比较的基础上,扬长避短,发挥自反性所具有的消解、反思、批判及建构等多种意义,去推动人类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进步。因此,这种批判必须是建立在平等、真诚、理性、善意、和谐基础上的批评。只有这样,其批评基础上的建构才会较之以前的传统文化或社会事实显得更为本真、灵动、丰盈和鲜活。第三,在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因势利导而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人类学及民族志书写倡导的理念是一致的。因此,在世界局势动荡不安、多边主义世界格局逐渐形成的当前,民族志书写更应为促进世界各民族的团结进步提供更多的事实依据。秉承民族志书写的初心,不仅是民族志书写的动力源泉,也是民族志书写的价值性诉求。
最后,推动人类学学科的发展。一般来说,一个学科的发展是与其理论的成熟度、实践的效用、时代发展的需要等因素息息相关的。近年来,公共人类学由于其对世界范围内的某些问题及事件所作出的直接和实质性的贡献而声名鹊起。特别是在新冠病毒全球肆虐的当前,面对东西方政府、社会及民众不同的病毒认知、采取的不同防疫措施和最终导致的不同治理结果,作为以研究文化或社会见长的人类学,更应在这次百年不遇的公共灾难中,很好地展示人类学对公共事务和公众的责任、伦理及义务,为世界人民取得最终的抗疫胜利发挥文化力量并作出贡献。只有这样,人类学学科才能摆脱自身在当前学术研究中不尴不尬的地位,抓住发展时机,促进学科的快速发展。因此,“在当代民族志复杂的多点区域中,人类学自身是它自己最好与最具创造性作品的最终的元公众。在这种立场看来,人类学不得不重新定义在这种以公众为核心的研究特性中,什么是它的支柱”(42)詹姆斯·克利福德、乔治·E.马库斯编:《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高丙中、吴小黎、李霞,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19页。。“疫情面前无旁观者,我们都是疫情中的公众。”当前,利用国内和国际主流媒介、借助最大限度的支持者,把习近平总书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费孝通先生提倡的“人民的人类学”或“迈向人民的人类学”价值关怀传播给世界人民,这理应成为当前人类学关注的焦点、民族志书写的核心以及民族志作者该有的担当。推动人类学学科的发展,不仅是民族志书写的内生动力,也是民族志书写的外化条件。
总之,人类学复杂而多元,因为人类是复杂而多元的。而作为人类学两大标志之一的民族志书写之所以能用自身的方式去反映人类学的复杂,关键在于民族志书写中内含着科学与人文、自然与文化、过去与现在、我们与他们、人类学与世界等学科应有之义和核心主题。特别是价值性融入民族志书写,更是以其复杂性很好地表征了人类学的复杂性,以其人文性很好地展现了人类学的人文性。诚然,从科学民族志书写主张的“价值无涉”到后现代民族志书写倡导的“价值关联”,价值性在民族志书写中从无到有、从少到多的发展态势,很好地展现了人类学和民族志书写的关系性本质和人文底色。而价值性渗入民族志书写,不仅使科学民族志书写的真实性受到了广泛质疑,也增强了后现代民族志书写的情境复杂性。随之而来的多重主体、多种范式及多样体裁的并存,更是彰显价值选择性在民族志书写中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因此,在科学与艺术、真理与价值、文本化与主体化的不断碰撞与交融中,把握好民族志书写的价值关联性、价值多维性及价值选择性,才能理顺民族志书写真善之间的辩证关系,促使求真至善唯美的民族志书写范式的最终形成。“人类学家所要指出的,正是对纯粹的‘真’与置身于生活的善和美之间的关系,因为只有在极不正常的社会中,这三个东西才是分离的。”(43)王铭铭:《人类学是什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6页。民族志书写是科学,也是艺术,是真理与价值碰撞与交融而成的科学艺术和艺术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