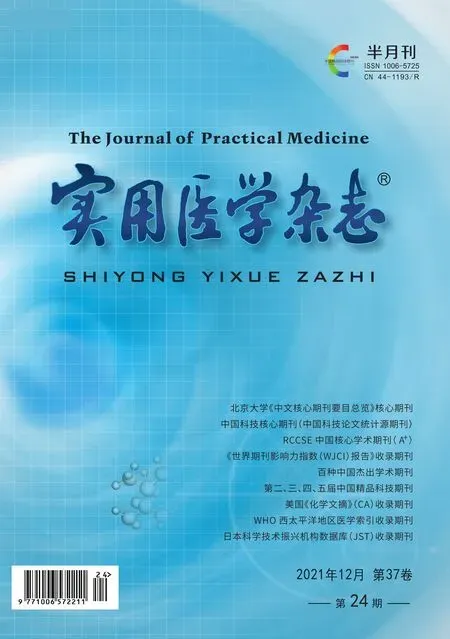复杂高危冠脉病变患者介入治疗现状及进展
马贵洲 徐荣和 蔡志雄 余丹青
1广东省汕头市中心医院心血管内科(广东汕头515041);2广东省人民医院,广东省医学科学院,广东省心血管病研究所(广州510080)
随着我国人口的老龄化,复杂、高危冠脉病变且有治疗指征的患者(complex high risk and indi⁃cated patients,CHIP)越来越多,这类患者往往无法耐受外科冠脉搭桥手术,因此倾向于选择冠状动脉介入治疗(percutaneous coronary intervention,PCI),但其潜在的高风险使其成为冠脉介入医生面临的一大挑战。目前国内外针对这类患者的最佳治疗策略仍然存在争议。既往由于认识不足、器械及技术条件限制,大部分CHIP 未能接受PCI治疗。近年来随着介入新策略、新技术、新器械的出现,以及在现代机械循环辅助支持下,CHIP 行PCI 治疗已逐渐增多。本文针对CHIP 行PCI 治疗的现状与进展作一综述。
1 CHIP 的定义
目前对CHIP 的定义仍缺乏共识[1-3],一般认为包含两个层次的含义及三方面的内容。两个层次的含义:(1)高危复杂,无法耐受外科冠脉搭桥术(coronary artery bypass grafting,CABG);(2)血运重建的必要性,血运重建能改善患者的临床症状及预后。三方面的内容[1,3-5]:(1)冠状动脉解剖/病变的复杂性:多支冠脉病变、无保护性左主干病变、前降支开口病变、慢性完全性阻塞性病变(chronic total obstruction,CTO)、严重钙化病变、真分叉病变、冠脉严重迂曲病变、静脉桥血管病变、唯一残余供血动脉病变等;(2)存在或潜在血流动力学不稳定:休克或左心室射血分数(LVEF)≤35%;(3)合并多种疾病:高龄(>75 岁)、糖尿病、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或肺纤维化、严重肺动脉高压(≥55 mmHg)、慢性肾脏疾病(肾小球滤过率<30 mL/min·1.73 m2)、严重的主动脉瓣/二尖瓣疾病、严重的周围血管疾病、慢性肝脏疾病等。
2 CHIP 的概况
目前关于CHIP 临床数据的报道仍然相对缺乏[2],尤其是那些可能从血运重建术中获益却未得到治疗的患者数量[4],主要原因[4,6]可能包括:(1)许多患者可能从未引起介入医生或心脏外科医生的关注;(2)这类患者的处理复杂且风险大,被大多数临床试验排除在外。甚至有学者[7]认为临床上可能有相当大比例的严重冠心病患者因为没有进行相关的检查而漏诊。
既往研究[8-10]表明:相对于药物治疗,高危冠脉病变患者血运重建术既可以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也可以减少不良临床事件,包括降低心衰发生率、再住院率及病死率。目前的指南[11-13]也支持对高危患者(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或具有高危解剖或难治性症状的稳定型缺血性心脏病)进行冠脉血运重建。
高危冠脉病变患者行血运重建,一直以来存在两个争议的话题:(1)CABG 与PCI 孰优孰劣。2008年欧洲心脏病学会(ESC)年会上公布12 个月随访结果的SYNTAX 研究[14]表明CABG 组的再次血运重建率和主要不良事件发生率均显著低于PCI 组,但非致死性脑卒中发生率CABG 组却高于PCI 组。PCI 组脑卒中发生率降低的优势并未能抵消其再次血运重建率升高所带来的劣势。(2)完全血运重建与不完全血运重建。Meta 分析[15]表明:对于多支冠脉病变的高危患者,与不完全血运重建相比,完全血运重建能明显降低患者的病死率,减少再次血运重建及心梗的发生率。另外对于大多数患者而言,与PCI 相比,CABG 更能达到完全血运重建的目的[15],从而降低病死率[16],改善预后。因此,针对复杂高危冠脉进行完全血运重建,CABG 比PCI 具有更大的优势,然而仍然有部分患者无法耐受外科手术或者不愿接受外科手术治疗。
近年来,随着介入新器械、新技术的出现,PCI解决复杂高危冠状动脉病变已经成为可能[17],尤其是那些无法耐受CABG 手术或手术死亡风险>5%的患者,PCI 是一种有效的替代策略[4,6,18]。近期KINNAIRD 等[19]报道在英格兰和威尔士的稳定型心绞痛患者的PCI 中,CHIP 所占的比例逐年上升,由2007年28.1%升高至2014年的36.2%。尽管血运重建技术的进步,以及各种危险分层策略的优化,接受PCI 手术的CHIP 患者仍然偏少[4,6],其原因可能包括:(1)患者合并多种疾病,即使血运重建也无法改变结局;(2)相当一部分介入医生无法胜任,由于手术成功率低、风险大的特点以及对这一人群PCI 适应证的困惑,医生会选择避免对这类患者进行手术;(3)医生的错误认知,高估了手术潜在风险,而低估了获益。为了改变这一局面,安全有效地应用PCI 救治这类患者,需要训练有素及具备相应技能的介入医生,同时也需要有效的辅助支持器械为PCI 手术“保驾护航”。另外,精确的风险评估模型将有助于患者的危险分层以便选择合适的治疗方法。总之,大多数CHIP行PCI 治疗的风险高、难度大,但患者的获益也更显著[18],具备“高风险与高获益”的特点。
3 CHIP 的风险评估
由于CHIP 治疗的复杂性,风险评估应该是一个综合的过程(综合患者的临床特点、功能检查及冠脉解剖等情况),个体化地评估风险与获益,确定治疗策略,包括冠脉血运重建(CABG 与PCI)或指南指导的药物治疗(guideline⁃directed medical therapy,GDMT)。
目前已经有多个冠脉血运重建风险评估模型,包括additive EuroSCORE、logistic EuroSCORE、STS mortality score、STS morbidity and mortality score、Mayo Clinic risk score、New York state PCI risk score、SYNTAX Ⅱscore、EuroSCOREⅡ、SinoSCORE、NC⁃DRCathPCI risk score system 等。其中临床常用的主要有:(1)EuroSCOREⅡ评分系统:既往的EuroS⁃core 评分是1995年确立的欧洲血管手术危险因素评分系统,由于高估了血运重建风险且校准能力差,国内外指南已不再推荐EuroScore 评分,而推荐使用EuroSCOREⅡ预测冠脉搭桥的病死率,该评分系统通过18 项临床特点评估院内死亡率,可指导选择血运重建策略;(2)STS 评分:美国胸外科医师协会评分,主要用于预测住院期间或术后30 d 的病死率,以及住院期间并发症发生率;(3)SYNTAXⅡ评分:优于SYNTAX 评分,可比较准确预测复杂冠脉三支病变或左主干病变患者的远期死亡率,目前临床上推荐优先使用SYNTAXⅡ评分进行风险评估;(4)SinoSCORE:基于中国心血管外科注册登记建立的风险模型,针对我国患者CABG 手术的风险预测模型;(5)NCDRCathPCI:美国国家心血管注册数据库风险评分体系,仅用于PCI 患者的评估,近期有研究[20]认为该模型能够准确预测PCI 术后的短期和长期全因死亡率。然而,这些风险模型都存在局限性[21-22]。因此,学者仍在不断地探讨更加精确的风险模型。最近,BRENER 等[2]提出了一种用于预测CHIP 行PCI 术后1年死亡率的新型风险评估模型,然而仍有待进一步验证。
2016年的美国ACC/AHA 指南[23]建议应用STS和SYNTAXⅡ评分对多支冠脉病变和无保护性左主干进行危险分层。2020 美国心血管造影和介入学会(SCAI)发布的《复杂冠状动脉病变最佳经皮冠脉介入治疗术的立场声明》[24]中提出了冠脉介入治疗A⁃C⁃E 风险分层金字塔。
4 CHIP 冠脉腔内影像学及生理学评估
目前临床上常用的冠状动脉腔内影像学和生理学评估方法有血管内超声(intravascular ultra⁃sound,IVUS)、光学相干断层成像(optical coher⁃ence tomography,OCT)、血流储备分数(fractional flow reserve,FFR)。IVUS 和OCT 通过冠状动脉内成像可提供比冠脉造影更有价值的信息,因此可用于临床优化支架植入和降低支架相关并发症[25-26]。
2017年一项网络荟萃分析(共31 项临床研究,纳入17 882 例患者)表明[27]:与冠脉造影比较,腔内影像学指导的PCI 明显降低了心血管死亡与不良事件,但IVUS 与OCT 指导并无差异。2018年冠状动脉内影像学临床应用专家共识[28]也指出:IVUS 和OCT 在指导和优化大多数PCI 流程方面是等效的,均优于冠脉造影。然而IVUS 与OCT 也各有优缺点,对于CTO 病变、弥漫病变、左主干开口病变和肾功能不全患者(减少造影剂用量)的PCI时,IVUS 应作为首选;而OCT 的分辨率较高,能更准确地识别管腔内膜面和支架相关的病变特征,因此专家共识推荐对支架失败(支架内再狭窄或支架内血栓形成)的患者应常规进行冠状动脉内影像学检查,并首选OCT。2020年IRIS⁃DES(Inter⁃ventional Cardiology Research In⁃cooperation Society⁃Drug⁃Eluting Stents,NCT01186133)注册临床研究表明[29]对于复杂冠脉病变,PCI 术中应用冠脉腔内成像能降低患者3年的心脏事件,包括心脏性死亡与靶血管的再次血运重建率,而这种临床获益可能归因于有效的后扩张,冠脉腔内成像指导选择更大尺寸的后扩张球囊。因此PARK 等[29]建议在复杂冠脉病变患者PCI 术中,应该更积极地应用冠脉腔内成像。总之针对CHIP 行PCI 治疗,术中应用腔内影像学检查对冠脉管腔和病变特点进行评估,有助于制定合适的PCI 策略,如钙化病变的预处理[30](旋磨、切割等),改善临床预后。
临床实践中,IVUS 或OCT 只能对冠脉病变进行解剖学评估,无法客观准确地评价病变与缺血心肌之间的关系[31]。目前指南公认的冠脉病变有创功能学评价指标为FFR,临床研究认为FFR 指导的PCI 策略是安全经济的,并且能改善患者的预后[32]。2016年FFR 临床应用专家共识[33]指出:对于复杂多支冠脉病变,推荐测量全部和/或冠脉病变的FFR,以计算功能学SYNTAX 评分,指导血运重建的策略。
5 CHIP⁃PCI中经皮机械循环辅助设备的应用
2020年《经皮机械循环辅助临床应用及管理中国专家共识》指出:CHIP 行PCI 术风险大,经皮机械循环支持设备(percutaneous Mechanical Circu⁃latory Support,pMCS)可作为术中及术后循环辅助手段,降低手术风险,改善预后[34]。高危PCI 患者围术期应用pMCS 的获益机制[34-35]主要包括:(1)维持循环,保证重要器官的灌注;(2)降低心腔内充盈压,减轻肺淤血和肺水肿;(3)降低左心室容积、室壁张力和心肌耗氧量;(4)在复杂介入过程中提供循环支持,使患者能够接受更完全的血运重建治疗。然而,目前大部分pMCS 的指导方案仅仅基于专家共识,仍缺乏大规模随机临床研究支持[36]。
目前主要的pMCS 包括主动脉内球囊反搏泵(intra⁃aortic balloon pump,IABP)、左室⁃主动脉辅助装置(impella)、左房⁃主动脉辅助装置(tandem⁃Heart)、体外膜氧合(extracorporeal membrane oxy⁃genation,ECMO)。其中IABP 和Impella 系统置入速度快、能有效改善冠脉血流和降低心肌耗氧,我国专家共识推荐可以优先选择[34]。另外,IABP与ECMO 联合应用具有协同优势[34],IABP 可以在ECMO 流量支持的基础上,增加0.5~1.0 L/min,同时可以克服因ECMO 平流灌注导致左室后负荷增加的副作用。
5.1 IABPIABP 是临床上应用最早且最广泛的pMCS。IABP 能增加心排血量约10%~20%,血液动力学效果明确[34]。在2012年之前,国内外指南均推荐在急性心梗合并心源性休克的患者中应用IABP,推荐级别为Ⅰ类。然而,2012年IABP⁃SHOCKⅡ研究[37]结果表明IABP 并不能降低30 d的病死率,因此指南的推荐级别均进行了下调。美国ACC/AHA 指南[38]及欧洲ESC 指南[39]将IABP的推荐级别降低为Ⅱa 类(推荐用于因机械并发症导致的心源性休克/血流动力学不稳定患者),2019年我国的STEMI 指南[40]也指出:IABP 不能改善STEMI 患者的预后,不推荐常规使用(Ⅲ,B),但对于因机械并发症导致血液动力学不稳定的STEMI 合并心源性休克患者,IABP 可作为辅助治疗手段(Ⅱa,C)。虽然指南均不推荐在急性心梗合并心源性休克患者中常规应用IABP,但是IABP仍然可以使缺血性或非缺血性心源性休克患者短期内得到血流动力学的改善[41]。BCIS1 研究结果[42]表明,在CHIP 行PCI 治疗中应用IABP,51 个月随访结果表明全因死亡率相对降低了34%。
5.2 Impella提供主动前向血流,增加心排血量;直接降低左心室压力和容量,降低心肌氧耗;增加冠脉血流,改善心肌灌注[34,43]。2009年的PRO⁃TECTⅠ临床研究[44]首次证实了Impella 在高危PCI中的有效性、安全性及可行性。随后的2012年PROTECTⅡ临床研究[45]表明在CHIP 患者PCI 中,与应用IABP 相比,Impella 可以提供更有效的血流动力学支持,使患者得到更完全的血运重建,降低术后90 d 主要不良病事件的发生率。
5.3 TandemHeart经股静脉置入导管,穿房间隔后将血液从左心房分流至股动脉。TandemHeart的应用需要房间隔穿刺,故在急诊室或心肺复苏时难以迅速置入[36]。2012年梅奥诊所的一项前瞻性研究[46]表明CHIP 在TandemHeart 辅助下行PCI是一种可行的治疗策略。
5.4 ECMO一种兼具呼吸替代和循环辅助的pMCS 设备,目前常用的模式为静脉动脉ECMO(VAECMO),可同时进行呼吸和循环支持。目前关于CHIP 在VA⁃ECMO 辅助下行PCI 的研究资料有限,数据往往来源于有限的单中心经验[35]。TOMASELLO 等[47]与SHAUKAT 等[48]的单中心数据表明CHIP 在ECMO 辅助下行PCI 是安全可行的。
6 CHIP 的治疗策略
2016年发布的《中国心脏内、外科冠心病血运重建专家共识》及2020年SCAI 发布的《复杂冠状动脉病变最佳经皮冠脉介入治疗术的立场声明》均对CHIP 的血运重建进行了阐述,均强调“多学科协作的心脏团队”在血运重建治疗决策中的地位,以及“以患者为中心”的治疗理念[17,24]。我国学者一直在不断地探索并优化CHIP 治疗策略,北京安贞医院周玉杰教授团队提出了PIE⁃2R(Pace⁃maker + IABP/Impella + ECMO + Respiratory Sup⁃port + Revascularization)模式[49],提倡整合当前最优的救治策略来达到CHIP 的最佳治疗效果。西京医院的陶凌教授也针对CHIP 血运重建提出了“术前评估⁃术式优化⁃并发症防治⁃心衰管控”的综合治疗策略。
心脏团队协作,术前充分评估表明多学科心脏团队的经验对患者的预后至关重要[4]。心脏团队应该在术前对患者的临床合并疾病、血流动力学、冠脉解剖等情况进行详细评估,权衡风险与获益,制定出最优的血运重建策略。美国ACC/AHA 指南[23]建议应用STS和SYNTAXⅡ进行危险评分。
制定详细策略,选择合适循环辅助,防治并发症:针对不同的病变制定个体化的血运重建策略,必要时分期血运重建以降低手术风险,保证患者的安全;恰当的时机选择合适的循环辅助设备,维持血流动力学稳定,为完全血运重建“保驾护航”;积极防治相关并发症,减少并发症抵消手术获益。优化药物治疗:贯穿整个疗程,遵循指南指导的药物治疗,改善患者合并疾病的状况。术前优化药物治疗,为手术治疗创造条件,降低风险;术后优化药物治疗,改善患者长期预后。
7 总结及展望
人口的老龄化使CHIP 越来越多,PCI 是改善CHIP 预后的重要措施,然而CHIP 行PCI 的潜在高风险已经成为冠脉介入医生必须面临的一大挑战。新药物、新器械及新技术的出现为冠脉介入提供了有力的保障,使CHIP 接受PCI 的比例逐年增多。CHIP 的治疗,需要多学科协作的心脏团队进行准确的风险评估,需要规范完善的手术流程,需要技术娴熟的介入医生,需要优化的药物治疗。CHIP 的治疗仍然存在一定的争议(风险评估模型、血运重建策略、循环辅助的应用等),因此需要更多的临床研究。总之,只有不断地探索并优化CHIP 的治疗策略,才能使CHIP 的“高风险”治疗达到“高获益”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