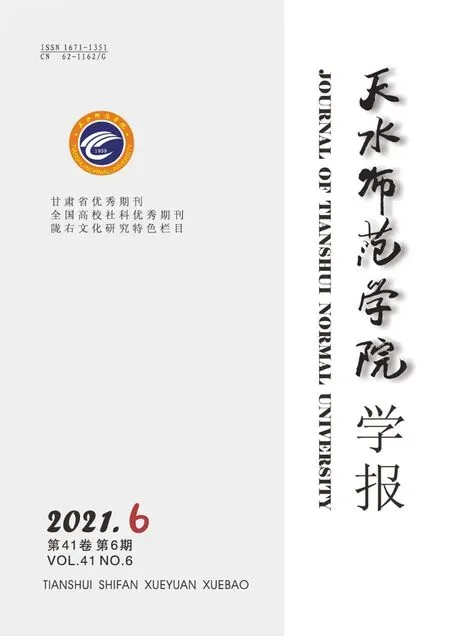论《蒹葭》与秦文化的突变
杨世理
(兰州理工大学 党委宣传部,甘肃 兰州 730000)
《诗经·秦风》共10首诗,其中《车邻》《驷鐡》《小戎》《无衣》均以描写战争见长,可谓中国最早的边塞诗。秦人之俗,大抵尚气概,先勇力,忘生轻死,故其见于诗亦如此。然《秦风·蒹葭》却格外独特,从风格而言,《蒹葭》其诗风神摇曳,意境飘逸,神韵悠长,迥异于《秦风》其他粗犷直质、好战斗乐的作品。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当与秦早期文化史上的一次突变密切关联,也是秦人积极学习周文化的成果。
一、关于《蒹葭》的本事
《秦风·蒹葭》诗云: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
蒹葭萋萋,白露未晞。所谓伊人,在水之湄。溯洄从之,道阻且跻。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坻。
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谓伊人,在水之涘。溯洄从之,道阻且右。溯游从之,宛在水中沚。
对于此诗本事,众说纷纭,大致有以下四种观点:
其一,刺襄公“未能用周礼”说。《诗序》云:“《蒹葭》,刺襄公也。未能用周礼,将无以固其国焉。”《毛传》亦云:“秦处周之旧土,其人被周之德教日久矣。今襄公新为诸侯,未习周之礼法,故国人未服焉。”《孔疏》曰:“作《蒹葭》诗者,刺襄公也。襄公新得周地,其民被周之德教日久,今襄公未能用周礼以教之。礼者为国之本,未能用周礼,将无以固其国焉,故刺之也。经三章,皆言治国须礼之事。”胡承珙竭力为《序》说辩护:
案《序》首但云刺襄,而其下乃有未能用周礼之说,自必有所受之,《毛传》最简,此首章《传》如此委曲发明《序》意,亦是见《序》在《传》前,未可谓毛公未见《诗序》也。赵氏文哲曰:“《诗序辩说》谓此诗不详所谓,而斥《序》之凿。于是后之说诗者,如朱氏公迁、黄氏佐、唐氏顺之,或以为朋友想念之词,或以为贤人肥遯之作,都无确指。试思作《序》者如果凿空妄说,则必依附诗辞,若近世伪为《申公诗说》者,谓此乃秦之君子隐于河上,秦人慕之而作。于以欺天下万世,岂不易易?必不凭虚而创一襄公不用周礼之说,与诗辞绝不相比附。以自纳于败阙也。”[1]
而王照圆《诗说》反驳道:
《蒹葭》一篇最好之诗,却解作刺襄公不用周礼等语,此前儒之陋,而《小序》误之也。自朱子《集传》出,朗吟一过,如游武夷、天台,引人入胜。乃知朱子翼经之功不在孔子下。[1]386
其二,求贤说。姚际恒《诗经通论》曰:
此自是贤人隐居水滨,而人慕而思见之诗。在水之湄,此一句已了。重加洄遡、遡游,两番摹拟,所以写其深企愿见之状。于是于下一“在”字上加一宛字,遂觉点睛欲飞,入神之笔。上曰在水,下曰宛在水,愚之以为贤人隐居水滨,亦以此知之也。[2]
魏源论此诗,谓为讽襄公求贤尚德之作。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云:
魏源云:“襄公初有岐西之地,以戎俗变周民也。豳、邰皆公刘太王遗民,久习礼教。一旦为秦所有,不以周道变戎俗,反以戎俗变周民,如苍苍之蒹葭遇霜而黄。肃杀之政行,忠厚之风尽。盖谓非此无以自强于戎狄,不知自强之道在于求贤。其时故都遗老隐居薮泽,文武之道未坠在人。特时君尚诈力,则贤人不至,故求治逆而难。尚德怀,贤人来附,故求治顺而易。遡洄不如遡游也。襄公急霸西戎,不遑礼教。至春秋,诸侯终以夷狄摈秦,故诗人兴霜露焉。”愚按魏说于事理诗义皆合,三家义或然。
江阴香《诗经译注》认为:“这是讥刺秦襄公不能够诚意求贤,致使贤士隐居,不肯出来做官。”[3]汪梧凤曰:
《蒹葭》,怀人之作也。秦之贤者抱道而隐,诗人知其地,而莫定其所,欲从靡由,故以蒹葭起兴而怀之,遡洄遡游,往复其间,庶几一遇之也,自毛、郑迄苏、吕无不泥《序》说秦弃周礼。黄茅白苇,《朱传》一扫空之,特未定其所指耳。然谓秋水方盛之时,所谓伊人者,乃在水之一方,上下求之而皆不可得,则已明为怀人之作矣。[1]388
其三,“不知其何所指”说。朱熹认为:“言秋水方盛之时,所谓彼人者,乃在水一方,上下求之而皆不可得。然不知其何所指也。”[4]黄中松《诗疑辨证》云:“细玩‘所谓’二字,意中人之难向人说,而在水一方,亦想象之词。若有一定之方,何以上下求之而不得哉?诗人之旨甚远,固执以求之抑又远矣。”[1]387陈子展先生认为:“《蒹葭》,诗人自道思见秋水伊人,而终不得见之诗。”[1]387又说:“《蒹葭》一诗是诗人思慕一个人而竟不得见的诗。他思慕的这一个人是知周礼的故都遗老呢?还是思宗周、念故主的西周旧臣?是秦国的贤人隐士呢?还是诗人的一个朋友?或者诗人是贤人隐士一流,作诗明志呢?或者我们主观地把它简单化、庸俗化,硬指这首诗是爱情诗,诗人思念他的爱人呢?”[5]
其四,爱情怀人说。高亨先生《诗经今注》云:“这篇似是爱情诗。诗的主人公是男是女,看不出来。叙写他(或她)在大河边追寻恋人,但未得会面。”[6]余冠英先生认为:“这篇似是爱情诗。男或女词。诗中所写的是:一个秋天的早晨,芦苇上露水还未曾干,诗人来寻所谓‘伊人’。伊人所在的地方有流水环绕,好像藏身洲岛之上,可望而不可即。”[7]王守谦、金秀珍《诗经评注》也说:“是一首怀人的诗。……这首诗是写一个男子(或女子)思慕他(她)所爱的人,虽然日夜思慕,又在大河上下寻求。但最后还是可望而不可即的。……总之,这首诗是写一个男子(或女子)思慕他(她)所爱的人而难于亲近的爱情诗。”[8]蓝菊荪先生认为:“依我看本篇纯粹为民间恋歌无疑。”[9]袁梅先生也认为是爱情诗:
秋晨,天高云淡,芦花翻白,清露为霜,碧水澄莹,烟波万状。一个痴情的青年,正热烈追求着心爱的姑娘,想去找她,却难找到。徘徊往复,神魂颠倒。伊人宛在,觅之无踪,似有若无。然而,此景此情,并不使人感到虚幻。[10]
蒋见元、程俊英《诗经注析》云:“这是一首描写思慕、追求意中人而不得的诗。”[8]344
上述诸说,陈子展先生的推测似更为可取:“《蒹葭》,诗人自道思见秋水伊人,而终不得见之诗。”[1]387准确地讲,《蒹葭》乃“思宗周、念故主的西周旧臣”所作,表现的是对“宗周”“故主”的思念之情,从一定方面也反映了对理想政治及明君的渴望与追求。可能作于平王东迁、襄公立国之后,或者作于秦文公时代也极有可能。作者当为留秦的西周旧臣。
西周后期,王室衰微。其实早在周昭王时,就已经“王道微缺”了,“懿王之时,王室遂衰,诗人作刺”,《索引》引宋忠云:
懿王自镐徙都犬丘,一曰废丘,今槐里是也,时王室衰,始作诗也。
周夷王、周厉王时“诸侯或不朝,相伐”,“诸侯或叛之”,情形更为严重。到了西周最后一个王周幽王时,周王朝便濒临灭亡了。据《秦本纪》载:
七年春,周幽王用褒姒废太子,立褒姒子为嫡,数欺诸侯,诸侯叛之。西戎犬戎与申侯伐周,杀幽王郦山下。而秦襄公将兵救周,战甚力,有功。周避犬戎难东徙雒邑,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平王封襄公为诸侯,赐之岐以西之地。曰:“戎无道,侵夺我岐、丰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
平王东迁之后,宗周王畿之地为秦所有。值得注意的是,周平王不可能把国人悉数迁至雒邑,必然有大批原西周的臣民滞留于秦。尤其是秦文公十六年,据《秦本纪》记载:“十六年,文公以兵伐戎,戎败走。于是文公收周余民有之,地至岐,岐以东献之周。”“周余民”中自有不少作策的太史文人,这对于改变秦国文化落后的状况,具有决定意义。须知,秦在建国之前相当落后,没有文字,没有自己的典籍。立国之初,秦文公十三年(公元前753年),才“有史以记事”,从而“民多化之者”。正因为秦国直接从周人那里吸取当时最先进的文化,使秦文化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达到较高的水平。《蒹葭》的作者,当为“周余民”中的一位具有极高文学素养的旧臣。在经历了西周灭亡的刻骨铭心的痛楚之后,创作了这首寄托着政治理想的风神摇曳的《蒹葭》。
二、关于《蒹葭》“秋水伊人”独特的文学范式
从风格方面来看,《蒹葭》意境飘逸,神韵悠长,与《秦风》中的其他作品有很大差异。诚如清人方玉润所云:“此诗在《秦风》中气味绝不相类,以好战斗乐之邦,忽过高超远举之作,可谓鹤立鸡群,悠然自异者矣。”[11]又说:“三章只一意,特换韵耳。其实首章已成绝唱。古人作诗,多一意化为三叠,所谓一唱三叹,佳者多有余音。此则兴尽首章,不可不知也。”[11]273钟惺读完首章后写道:“异人异境,使人欲仙。”[1]385王照圆也评论说:“《小戎》一篇,古奥雄深。《蒹葭》一篇,夷犹潇洒。”[1]386准确道出了《蒹葭》与《秦风》典型风格的差别。王闿运《湘漪楼说诗》则云:“写情入物而苍劲凄动,如‘洞庭秋波’之句,千古伤心之祖。”王国维给予很高评价:“《诗·蒹葭》一篇,最得风人深致。”陈子展先生认为:“我们不能确指其人其事,但觉《秦风》善言车马田猎,粗犷直质,忽有此神韵缥缈之作,好像带有象征的神秘的意味,不免使人惊异,耐人遐想。在三百篇中只有《汉广》、《月出》、《鹤鸣》和本诗相仿佛。”[5]318陶侃如、冯沅君在《中国诗史》中说:“在慷慨悲歌的《秦风》中,忽有这么一篇优游闲暇、含蓄蕴藉的诗,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蒹葭》整饬的形式和优美的意境创造,构成了“秋水伊人”的文学范式,对中国文学造成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就形式而言,《蒹葭》三章,章八句,每章前七句四言,末句五言,前四句写景,后四句抒情。全诗采用重章形式,每章首句以“蒹葭苍苍”“蒹葭萋萋”“蒹葭采采”起兴,只换了三组叠字。次句则随时间的逐渐推移,依次写出白露的三种形态,由“为霜”,到“未晞”,再到“未已”,白露的凝结,融化,蒸发,其中暗含了情感的投注,加深,升华。而“所谓伊人”,则设置了三种不确定的场景:“在水一方”“在水之湄”“在水之涘”,意象空灵,给人以无穷的遐想。方玉润云:“兴起,虚点其地。展一笔,实指居处,仍用虚活之笔,妙妙。”“遡洄从之”“遡游从之”,朱熹《集传》云:“遡洄,逆流而上也。”“遡游,顺流而下也。”姚际恒赞曰:“重加遡洄、遡游,两番摹拟,所以写其深企愿见之状。”“伊人”究竟身在何方?“宛在水中央”“宛在水中坻”“宛在水中沚”。姚际恒说:“于是于下一‘在’字上加一宛字,遂觉点睛欲飞,入神之笔。”[1]386《蒹葭》艺术技巧高度成熟、圆融,是《国风》乃至《诗经》中唯一具有完整统一意象群的作品,可以上升到意境和风格的高度,也是中国第一篇成熟的抒情作品,其艺术手法连同诗中那些意象及由此形成的幽远意境成为古典美的代名词,至今并将长久地拥有蓬勃的生命力。[12]
三、《蒹葭》独特的艺术风格是秦文化突变的结果
《蒹葭》在艺术风格上表现出的这种特殊性,并不是偶然的,当与秦早期对周文化的继承和学习有关。诚如林剑鸣先生所说:“秦国的文化能够突然达到这样高的水平,除了全盘接受西周先进的文化以外,不可能做其他的解释。”[13]如果这篇作品确为留秦的西周旧臣所作,并在秦地广泛流传,它足以表现秦人对周文化的积极学习的态度。从一定角度来说,《蒹葭》,实际上代表了秦文化的一次突变,这次突变是在秦原有戎狄优秀文化的基础上,对先进的周文化的广泛借鉴与吸纳的结果。按照《史记·秦本纪》的记载,秦襄公立国后,并非“不能用周礼”,而是积极学习周人的礼乐文明:“襄公于是始国,与诸侯通使聘享之礼,乃用骝驹、黄牛、羝羊各三,祠上帝西畤。”《车邻》所展示的礼乐文明,也正是秦襄公时代对周文化学习的结果。
《诗经》时代的《石鼓文》与《秦风》在风格上的差异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秦文化在该时期的突变现象。唐代在天兴县(今陕西凤翔)出土十块鼓形石,《元和郡县志·天兴县》载:“石鼓文在县南二十里许,其形如鼓,其数有十。”每块石上均刻有四言诗一首,由于诗歌内容多记录和歌颂渔猎之事,又由于石形如柱础,故又称“猎碣”。郭沫若作《石鼓文研究》,批评了前人仅从字形的比较上着手研究的方法,考证了石鼓文中“汧”字的地理位置。他认为,这是汧水发源地蒲谷乡,也即秦襄公作西畤的所在地,就是石鼓的出土地,因而得出石鼓文作于秦襄公时代(前777—前766)的结论。[14]林剑鸣先生《秦史稿》亦赞同郭沫若先生的观点,认为石鼓文当作于秦襄公时代。本文取郭沫若和林剑鸣二先生的观点:石鼓文当作于秦襄公时代。其产生年代,历史上纷纭其说,诚如罗君惕云:“或曰周,或曰秦,或曰汉,或曰北魏,或曰北周,未有定论。清乾隆五十年重摹勒石,定位周宣王时物,而后人不敢复议矣。清末主秦之说复兴,然由或曰某公,或曰某王,亦无定说也。”[15]学术界亦有不同观点,近世研究者基本认同石鼓文为秦人制作。唐兰《中国文字学》主张石鼓文作于秦灵公时代(前424—前415)。根据《史记·秦本纪》记载,秦文公十三年(前753年)“初有史以纪事”;再按《吕氏春秋·音初》记载,秦穆公时始有诗歌,因此石鼓文之作不可能早于秦穆公时代。同时,他找出一个新的确定石鼓文制作时代的原则,即铜器中用“朕”而不用“吾”作人称代词,用“吾”时又不用“朕”,用“朕”在前,用“吾”在后。秦景公时的铜器还都用“朕”,而秦惠文王时的《诅楚文》都用“彳吾”(即吾)字,故推断出石鼓文作于秦灵公时代。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赞同唐兰提出的原则,同时指出石鼓文诗歌类似《诗经》风格,大约为春秋中晚期物。李仲操先生撰文确认《石鼓文》作于秦宣公四年(公元前六七二年),张启成先生也持此说。李仲操先生提出两条理由:其一,《石鼓文》出土地点与秦宣公作密畤地点的一致性;其二,《石鼓文》所载的周天子平息内乱的时间与秦宣公四年的一致性。张启成先生在此基础上又补充了三条理由:其一,字体上的新证据;其二,从祭祀的角度看秦宣公四年狩猎与祀青帝的一致性;其三,从炫耀武力向东扩张看秦宣公四年狩猎行动与祀青帝的一致性。[16]
从《诗经》的体例来看,狩猎诗仅见于《国风》与《小雅》。《国风》中,《周南·兔罝》三章,章三句;《召南·驺虞》,二章,章三句;《郑风·大叔于田》,三章,章十句;《齐风·还》,三章,章四句;《驷鐡》,三章,章四句;《小戎》三章,章十句。《小雅》中,《车工》,八章,章四句;《吉日》,四章,章二句。《石鼓》诗共十章。一章,章十九句;二章、三章,章十八句;四章,章十七句;五章,章十八句;六章,章二十二句;七章,章十九句;八章,章二十句;九章,章十七句;十章,章十一句(有残缺)。总字数为四百六十五。[13]卷16,333两相比较,同是狩猎诗,《石鼓》诗的章数、句数与总字数都大大超越了《国风》与《小雅》的狩猎诗。其诗体与《大雅》《鲁颂·閟宫》类似。譬如,《大雅·卷阿》共十章,章数与《石鼓》诗同;《閟宫》八章,句数有十七句、十八句不等,每章的句数与《石鼓》诗有类同之处。可以推测,《石鼓》诗的体例,其章数与句数,可能有意模仿了《大雅》与《鲁颂·閟宫》。
从创作风格而言,《石鼓》诗与《秦风》亦有类似的地方:其抒情写景朴实而浑厚,意趣刚健、沉实。但在描写车马田猎之事方面,《石鼓文》中的诗篇表现比《秦风》更丰富、更浓重,要比《秦风》中的同类诗篇更细腻。就作品整体格局来看,《石鼓》诗的严整和平正更接近于《雅》诗。作品在整饬之中蕴含着雅正的韵味,与《风》诗的跳宕活泼略异其趣。诗篇在“铺陈其事而言之”的过程中表现着一种恢宏的气势。显然,《石鼓》诗相对《秦风》而言,出现了特殊的变体,这种变化具有双重的意义:
其一,与襄公时代的《车邻》《驷鐵》等诗相比,虽然题材相似,但诗体相差很远。可知自襄公时代,在积极学习周文化的基础上,秦诗的风格已经开始了某种突变,趋于多样化,《石鼓》诗与《蒹葭》就是典型的例证;
其二,秦人在文学上的突变,本质上是秦人崛起过程中顽强生存意志的体现,也是秦文化能够长期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并在民族融汇中显示出不可战胜的主导性原因之一。
地下出土文物也证实了秦人对于周文化的继承与学习,最典型、最突出的是青铜制作。邹衡先生说:“起初,周人几乎是全盘接受了商人的青铜文化,到了后来,才逐渐发展起来具有一定秦人风格的青铜文化。”[17]秦人对周人青铜制作的承袭也完全如此,这是华夏青铜文明的递接规律。根据祝中熹先生的研究,秦器的习用纹饰,持续了西周后期流行的纹饰,喜用窃曲、垂鳞、瓦垅、波带、重环、云雷、蟠虺等纹样。礼器的配置也如出一辙,重食器而轻酒器,通常组合为鼎、簋、方壶、圆壶、盘、匜、甗等,鼎为奇数列鼎与偶数簋相配。从工艺水平上来看,春秋初年的秦器,形制、纹饰虽承袭周器式样,而铸作技术却与周器有较大差距。许多器物器形不够规整,器壁厚薄不匀,纹饰也颇粗糙,线条滞涩不畅,有的铭文系凿刻而成。正如李朝远先生研究了上海博物馆所藏出土于礼县大堡子山秦公陵园的一批青铜器后,撰文指出:“秦公诸器的铸造颇有西周晚期的气度,却缺乏西周器的精致,将秦公簋与类似的史颂鼎相比较,其粗糙程度显而易见。”在谈到鼎的蹄形足断面呈内凹半空弧状时,认为原因“可能是秦国工匠尚未掌握内范悬浮法所致”,“说明秦人尚未掌握大型器内外范的等距技术”。[18]而甘肃博物馆所藏同一陵区所出时代更早些的秦公器,制作工艺与铭饰水平比上博所藏还要粗陋。当时秦国青铜器的制作的确还不够成熟。但值得注意的是,随后,秦国青铜器制作工艺就出现了极大的突变,令人惊异。时代比大堡子山秦陵稍晚的赵坪圆顶山秦贵族墓葬中出土的青铜器,无论就造型还是纹饰精美程度而言都远远超过了大堡子山秦陵器物的水平,“圆顶山墓葬的年代应属春秋早期,……这批墓葬及车马坑的发掘,为研究西周晚期到春秋早期秦国考古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实物资料。”[19]再如出土于宝鸡太公庙的秦武公钟、镈,以及出土于礼县东境的秦桓公簋,其铸作工艺绝不居于中原列国之后。桓公簋的纹饰已用模印法,而铭文也是先制好单个字模而后在胎膜上一一打印而成的,至今在其铭文行间尚能窥见其字模方块的留痕。这种技法实开活字印刷之先河,在当时属最先进的青铜工艺。秦人青铜武器的铸造水平,春秋早期即已具较高水平,这与秦人的尚武精神有关。最值得一提的是秦兵器的镀锡工艺。襄公时代《小戎》诗中,多次出现“鋈”字,如:“阴靷鋈续”“鋈以觼軜”“厹矛鋈錞”,这是中国镀锡青铜器的最早记载。[20]这种镀锡工艺,并不是秦人的发明。在甘肃灵台白草坡西周墓地出土年代稍早的青铜器所显示的镀锡传统,已被秦人继承和发扬。这说明,秦人的青铜制作技术,自襄公后在学习周人的基础上,出现了跳跃性的发展。这种情况,与以《蒹葭》与《石鼓文》为代表的文学上的突变遥相呼应,构成了秦人积极学习周文化的主旋律。
四、结论
综上所述,《蒹葭》在艺术上所达到的高度,实际上是当时秦人积极学习周文化的结晶。自襄公时代起,伴随着秦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对外扩张的日益加快,秦文化也展现出积极进取、借鉴吸纳的强大力量,广泛学习外族特别是直接吸收先进周文化的速度之快,已足以形成了一次秦文化发展史上的突变。这种突变表现在包括文学、青铜器铸造等诸多领域,使秦文化在很短的时间内,从没有文字典籍的状态,迅速达到较高的水平,发展了极富兼容性和进取性的秦文化。《蒹葭》就是这次秦文化突变在文学上的杰出代表,且以其整饬的形式和优美的意境创造,构成了“秋水伊人”的文学范式,意境飘逸,神韵悠长,对中国文学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