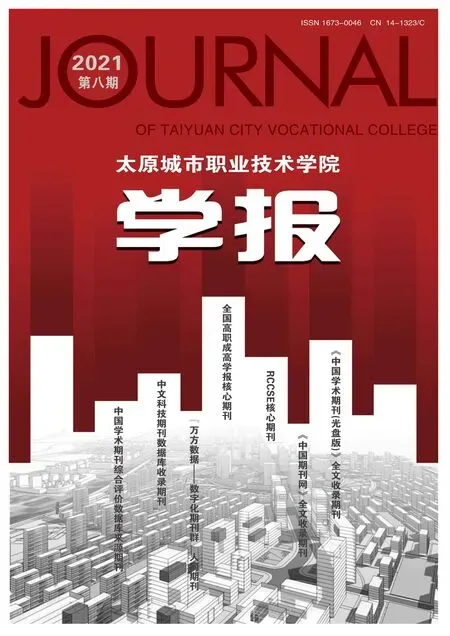“一带一路”建设下英语教育的ELF思路转型
■王翔敏
(中国矿业大学外国语言文化学院,江苏 徐州 221116)
“一带一路”建设在努力打造国际合作新平台的同时,对我国国际人才培养与外语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与其他语种相比,英语是我国外语教学中开设最广泛的语种,也是国际社会使用最普及的通用语种。伴随全球化的发展,非英语本族语者已然成为以英语为媒介展开国际交流的主体,英语通用语(English as a Lingua Franca,简称ELF)在国际事务中扮演着越发关键的角色。正如蔡基刚在“2019国际英语教育中国大会”后发文所言:“我国的英语教学已不再是典型的外语环境”“中国的英语教学应该是国际通用语教学”[1]。因而,立足于“一带一路”对国际人才建设的需求,我国需要在全球多语主义的语境趋势下,探求更具当下性与推广性的英语教育转型思路。
一、“一带一路”建设下我国外语教育的现况分析
“一带一路”强调与沿线国家实现各领域的互联互通,在互联互通建设中,语言互通是基础。就我国高校外语教育现况与沿线国家使用英语的情况而言,语言的互通未必只能依赖外语专业人才对非通用语种的学习。
(一)开设非通用语课程的办学条件有限
就我国外语专业的现有教育资源而言,多数高校不具备广泛筹措非通用语课程的基础。自“一带一路”建设以来,北京外国语大学已新增近40种非通用语语种,语种的覆盖范围之广在全国可算首屈一指。但即便拥有如此雄厚的办学实力,北京外国语大学部分已设立的非通用语专业也是隔一年或数年才招生一次。我国超过1500所普通高等院校都设有外语类专业,但大多都是以英语专业为主,能够陆续开设非通用语课程的高校总量寥寥无几。此外,国内一类外国语大学非通用语种课程的设置一般也不超过20种[2]。客观而言,我国多数高校(遑论中小学)从硬件与软件上皆不具备广泛开设非通用语课程的办学条件。
(二)掌握非通用语技能的人才数量有限
与其他领域的专业人才相比,外语专业人才的数量毕竟有限,其中掌握非通用语种的外语专业人才就更为稀缺了。专业外语教育历来有周期长、成本高、区域外语学习资源贫乏等现实问题,且难以在短期明显改观[2]。同时,由于师资与课时的局限,我国大部分普通中学与高校无法在外语课程中系统培养学生应用非通用语种进行跨文化的国际交流。因此,倘若“一带一路”建设单纯依靠非通用语外语人才的培养,将意味着大量非外语专业学生被排除在外,这不仅限制了人才培养规模,且局限了推广性,无法在短时间内实现“一带一路”对人才建设的规划。
(三)外语人才对其他学科知识了解有限
总体来说,我国外语专业由于受到各方面因素的限制,在复合型与国际型人才培养中普遍存在重语言技能、轻专业知识的问题。这令国内很多外语人才在学科知识结构的深度和广度无法同专业人才相比,无法胜任国际化专业领域工作与高层次的学术研究,专精外语且精通一门专业的高水平人才更是凤毛麟角、一将难求[3]。以此为鉴,培养通语言、精领域的复合型国际人才,不仅是外语专业人才培养的必然趋势,也是所有专业人才培养的共同趋势。因此,我国在加速建设外语非通用语教育的同时,仍需重视英语作为通用语的教育理念改革与转型,这对实现“一带一路”建设中的语言互通具有不可小觑的推广意义。
(四)沿线国家的语言生态符合ELF理念
近年来的调查显示,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高校中,英语仍是外语专业开设最广泛的通用语种[4]。具体而言,沿线范围内的东南亚与南亚一带是以英语为第二语言或官方语言的外圈国家,英语在这些国家中通常是双语或多语资源并用中的一种;剩余中亚、西亚、中东等地区的多数国家与中国相同,属于以英语为外语的扩展圈国家,英语在这些国家不具有官方地位,亦不发挥主要的社会功能。由此可见,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中国人使用英语并非与内圈的英语本族语者交流,而是与外圈与扩展圈的非英语本族语者进行跨语言、跨文化的互动,这恰好契合ELF的语境与理念特点。
二、“一带一路”建设下我国英语教育ELF转型的理念依据
长期以来,我国英语教育一直秉承“英语作为外语”(English as a Foreign Language,简称 EFL)的理念,以本族语英语作为判定英语学习成功与否的唯一基准,过度追求语言形式的地道与完美,未及时关注国际交流中不断深化的多语主义语境趋势,忽视了多元语言与文化互动过程中的动态性、复杂性与临场性,从一定程度上加重了英语学习者的交际压力与自卑心理,减弱了他们的学习热情与交际自信,致使不少中国学生努力学习了十多年的英语,只习得了哑巴英语,这显然不符合“一带一路”建设在语言互联互通中对国际人才的实际需求。
相较之下,ELF是20世纪80年代由少数德国学者提出的研究视角,现已发展成为独立的研究领域,已然成为国外应用语言学界的热门话题。近四年来,ELF研究越来越关注多语、多模态资源并用的交际,其内涵发展也从萌芽阶段的“共核特征”与兴盛阶段“再概念化”,步入至最新的第三阶段,重点强调多语种框架,关注ELF交流中的多语主义特征。在理念内涵的不断发展中,ELF越来越倡导逾越单一语种与文化意识的界限,关注国际交流中多语化与多模态资源并用的趋势,引导教师与学生将英语教育的焦点从语言形式的“地道性”与“标准性”,转向英语表达的“可理解性”与“有效性”,这一理念恰适用于我国“一带一路”建设对于跨语言、跨文化实现互联互通的迫切需求。
ELF在理念内涵上主张不再将英语本族语视为学习与模仿的唯一规范,不再过度纠正学习者不够标准的英语口语或者语法形式。鉴于英语在世界范围内的通用语作用,ELF主张英语应该属于所有英语使用者,而非英语本族语者所独有。如果英语的所有权已经从本族语者移交至所有英语使用者,那么英语本族语自然就不该是英语学习者的唯一标准[5]。因此,ELF理念倡导在教学活动中改变围绕英语本族语规则的示范与纠错为主的传统模式,将师生追求英语本族语目标的时间与精力节省下来,用以推行更切合时代与社会真实发展趋势的教学模式。ELF理念认可非英语本族语者在真实交际中对英语进行的临场改造与随之反映的文化身份,与英语作为外语的传统教育理念相比,它显然更顺应“一带一路”建设中开展国际交流的真实需求,为我国英语教育转型真正体现“国际性”价值,提供了与时俱进的理念依据。
三、“一带一路”建设下我国英语教育ELF转型的实施策略
ELF研究发展至今,已吸引国内外不少学者将目光投向教学研究,并提出了教学大纲、教学目标、教学方法、教材建设以及教师培训等各方面的改革建议。针对我国“一带一路”建设与英语教育的实际情况,笔者仅从教学目标、内容、方法、评价四个方面阐述“一体四维”的ELF转型实施策略。
(一)调整单维度、“乌托邦式”的英语教育目标
英语教育对国际人才的界定不应限于对语言能力的单维度要求,更不可认为培养国际人才的关键在于训练学生尽可能接近本族语者的英语水平,这种单维度、“乌托邦式”的教育目标,一则是不合实际且难以实现的,尤其在语音习得中;二则更无法顺应“一带一路”对国际人才培养提出的新挑战。
为了更好地服务于“一带一路”建设,我国各阶段的英语教育目标需依据具体情况,融入ELF理念赋予的启示:一是引导学生转变长期以来对英语本族语的单向膜拜与顺同,促进英语语言态度的与时俱进;二是重点提高学生英语表达的可理解性,而非地道性;三是增强学生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英语变体与当地文化的了解与宽容,而非单向接受与习得英语国家的语言规则与文化取向;四是有效提升学生的语用技能与跨文化交际策略,提高他们使用英语介绍中国政策与文化的能力;五是结合学生自身的专业特点,加强他们应用英语在国际社会展开专业领域交流的能力。
(二)更新语言、语用与文化三方面的教学内容
虽然国内已有出版社在新建教材中纳入ELF的教学内容,但整体而言,ELF教材建设仍相对滞后。在既有教材匮乏的条件下,各教育阶段的ELF教学在内容上应注意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在语言层面,我国英语学习者需采取循序渐进的方法。对此,文秋芳倡议,学习者从初学阶段学习本族语变体,中级阶段接触非本族语变体,高级阶段习得英语的本土化特征[5]。值得注意的是,沿线65个国家涉及的官方与民族语言多达2000余种,教师无需在内容上涵盖ELF的各种变体,而应因地制宜地选取英语变体纳入教学中,同时当然也不应将英语本族语变体完全排除在外。
第二,在语用层面,初等教育以上的英语教学内容应围绕多元语境展开语用策略的显性示范、案例分析及实践演练,以培养学生运用动态多变的语用技巧实现信息共建、关系管理与文化互融的意识与能力。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复杂多变的英语交际语境,语用教学应涵盖ELF视角下的语言语用与社交语用两个维度,包括自我修复、澄清、重复、合作性重叠、语码转换以及文化身份建构等语用策略[6]。
第三,在文化层面,各阶段的英语教学应超越英美国家的文化视野,重视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新内涵。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文化与企业“走出去”的核心动力便是跨文化的理解与沟通能力,因此在ELF视角下的文化教学应注重培养学生的国际性文化视野与文化自信,锻炼他们表达本土文化,展开文化观察与反思的能力。
(三)采取融合互联网+与跨学科的教学方式
首先,虽然ELF并没有完全自成一体、独辟蹊径的教学范式,但其可以与时俱进、因地制宜地在以下两个方面与现有的教学方式相融合,以体现ELF的核心理念。首先,英语教育应立足ELF语境,充分利用“互联网+”的新型模式。一方面,教师可以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构建跨洋互动。在课上,教师可以邀请沿线国家的教师或专家,以研讨、访谈的形式与学生展开即时互动,利用真实语境,增强学生对ELF英语变体、语用技巧以及跨文化交际的敏感度;在课下,教师可以安排学生与沿线国家的学生,通过网络社交平台完成定期交流的任务,并于学期末用书面形式总结交际心得。另一方面,教师还可以借助慕课越来越广阔与便捷的平台,鼓励学生学习合乎学科专业需求的英语或双语在线课程,并安排他们在课上口头汇报与推荐自己完成的课程。
其次,立足ELF倡导逾越语言教学单一层面的理念,在英语教学中尽量结合跨学科的专业知识。一方面,高校可争取在人才培养模式中尽快实现产教融合与校企合作,以便有的放矢地将英语教学与具体行业需求进行接轨。另一方面,高校也可在英语教学中利用内容依托模式(content-based instruction),将语言学习的素材与专业知识的内容有机结合,实现语言与专业学习的双向互促,增强学生利用英语探讨专业领域的能力,从而更有针对性地适应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时代新要求。
(四)构建体现ELF语境与文化自信的英语测试
适逢“英语热”开始在我国降温,高考也开始适度降低英语比重。有学者认为这恰为我国英语测试的ELF转型提供了更多的空间,是利用测试走出英语本族语单一导向的绝好时机[7]。针对我国英语测试现况而言,建议在高等教育先展开逐步变革。第一,在笔试的听力与阅读部分,可适度加入非本族语英语变体的语言素材;在翻译与写作部分,则可加入围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当地文化与中国文化的主题,一方面检测学生对各种英语变体的辨识力,另一方面也检验学生用书面英语诠释中国文化的能力。
第二,在口试中,ELF的测试标准重视语言的可理解性、易懂性与交际的有效性,关注具体语境与交际意图的实现,着重考核学生在交流中对英语的实际运用,这与刚出台的《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在建设理念上是基本一致的。为了达成“以考促学”的新型测试目标,英语测试还应在口试内容中,侧重检验学生利用口头英语介绍中国文化、沟通中国政策、探讨专业知识等方面的复合型能力。
英语教育的ELF转型不仅在全球化进程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也在我国“一带一路”建设中承担培养国际人才的关键角色,为我国英语教育提供了符合时代要求、契合社会经济发展的新路径。因此,我国英语教育亟需利用ELF理念优势,反思、改革与优化现行英语教育的不足,为“一带一路”国际化人才建设提供更有效的外语教学新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