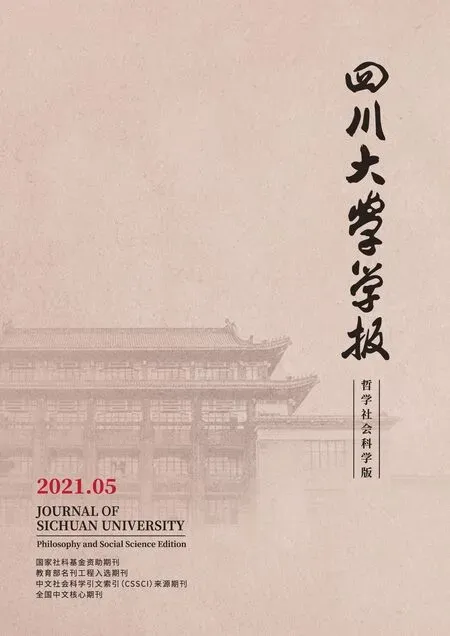身份、创伤和困境意识:《金锁记》译写再探
段 峰
张爱玲作为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位重要作家,在她的文学作品中有一部分是英文翻译作品,既有对他人作品的翻译,也有对自己作品的翻译,且以后者为重。作为一种跨语际和跨文化的双语实践,作品自译在张爱玲的文学创作活动中占据了较大的比重,特别是她对自己的某些作品,如《金锁记》的翻译显示出一个特殊现象,即往复译写。有研究者指出,“张爱玲的文学成就部分缘于她的双语实践,这点恰恰在关于她的文学批评中被忽略了。通过自译,她颠覆和操控了中国和英语世界的文学和文化规范”。(1)Jessica Tsui Yan Li,“Politics of Self Translation:Eileen Chang,” Perspectives:Studies in Translatology,Vol.14,No.2,2006,p.99.关于张爱玲的文学自译,学界已有一定的研究,(2)关于张爱玲文学自译研究的专著,国内主要有陈吉荣:《基于自译语料的翻译理论研究:以张爱玲自译为个案》,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桑仲刚:《二十世纪中国作家短篇小说的汉-英自译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阮广红:《张爱玲自译风格研究》,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6年;黎昌抱:《基于平行语料库的文学自译现象研究》,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年;以及一些相关论文。国外有少许论文提及,本文以下讨论中将随文注出。但相较于文学自译在张爱玲文学创作和翻译中所占的分量,以及张爱玲之于中国现代文学史和文学翻译史的影响,目前的相关研究仍有待进一步拓展和深入,特别是她对《金锁记》的往复译写现象的探讨尚有未尽之处,本文即从身份、创伤和困境的理论角度出发再作探析,以期为张爱玲研究提供更多元的视角。
一、《金锁记》的往复译写与接受
《金锁记》是张爱玲的成名之作,初载于1943年11月和12月《杂志》第12卷第2期和第3期,1944年又被收入其小说集《传奇》。小说描写一个小商人家庭出身的女子曹七巧,为求富贵,嫁给一个破落封建家庭的残疾儿子为妻,忍受封建礼教的压迫,最后在财欲和情欲的双重折磨下变得性格扭曲,行为乖戾,并亲手毁掉了自己儿女的幸福。小说发表后获得好评,傅雷(化名迅雨)就在1944年5月的《万象》第3卷第11期上发表了《论张爱玲的小说》一文,其中称:“《金锁记》是张女士截至目前为止的最完满之作,颇有《猎人日记》中某些故事的风味。至少也该列为我们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3)傅雷:《傅雷文选》,海拉尔: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01年,第167页。夏志清回顾中国小说史,也认为这篇小说体现了张爱玲的创作特色,即“意象的丰富和复杂,她的历史感,她的处理人情风俗的熟练,她对于人的性格的深刻的揭发”。(4)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42-343页。《金锁记》在张爱玲的文学创作生涯中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从她本人对这篇小说的反复译写中亦可看出。
张爱玲在中英文之间数次自译和改写《金锁记》,这在20世纪中国文学翻译史上绝无仅有。1943年,以太外祖父李鸿章次子李经述一家人的生活为背景,张爱玲创作了《金锁记》。(5)张子静、季季:《我的姐姐张爱玲》,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年,第195页。1956年,在美国东岸的麦道尔艺术村(MacDowell Colony),基于《金锁记》的人物和情节,张爱玲用英文改写了这篇小说,取名为PinkTears(《粉红的泪》),希望以此进入美国文坛,然而她的英文写作生涯并不顺利,小说改写完成后一直找不到出版商。(6)林以亮:《私语张爱玲》,陈子善编:《私语张爱玲》,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5年,第41页。于是,张爱玲又将PinkTears重新进行修改,取名为TheRougeoftheNorth(《北方胭脂》),但还是未能出版。1966年,张爱玲将TheRougeoftheNorth翻译成中文,取名《怨女》,在香港《星岛晚报》连载并由台湾皇冠出版社出版。1968年,皇冠出版社又出版了经张爱玲修改后的《怨女》第2版。1967年,张爱玲将《怨女》重新译回英文,仍用TheRougeoftheNorth书名在英国伦敦Cassell公司出版;1998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再版了这部小说。1971年,张爱玲再次将1943年版《金锁记》自译成TheGoldenCangue,收入夏志清主编的Twentieth-CenturyChineseStories(《二十世纪中国小说》)中,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
《金锁记》的中英文往复自译和改写错综复杂,“张爱玲至少7次改写了这个特别的故事”。(7)Jessica Tsui Yan Li,“Self-translation/rewriting:The Female Body in Eileen Chang's ‘Jinsuoji’,the Rouge of the North,Yuannü and ‘The Golden Cangue’,”Neohelicon,No.37,2010,p.392.目前研究者倾向于认定张爱玲四度自译和改写《金锁记》,即第一文本《金锁记》到第二文本PinkTears的语际改写,PinkTears到第三文本TheRougeoftheNorth的语内改写,TheRougeoftheNorth到第四文本《怨女》的自译,最后是第一文本《金锁记》到第五文本TheGoldenCangue的自译。“五个文本间既包含勒弗维尔(Andre Lefevere)所提倡的较为宽泛的现代意义上的翻译文本(包括改写或重写),也包括较为严格意义上的传统翻译文本,而所有的翻译和改写活动都由原作者一个人来承担,因此文本间的互文关系较为复杂”。(8)陈吉荣:《基于自译语料的翻译理论研究:以张爱玲自译为个案》,第69页。《金锁记》的译写文本,无论是严格意义上的中英传统翻译文本,还是现代意义上的中英改写翻译文本,都是基于原创小说文本且由张爱玲本人完成,因而都可视为她的“文学自译”。
文学自译是文学翻译的一种特殊形式,其作者和译者同为一人的事实,使得传统翻译理论中的忠实、对等之类的确定作者和译者二元关系的理念受到挑战。自译者在翻译活动中的自主和自由度,使得作者和译者、原文和译文之间的界限变得难以辨认,翻译与改写的边界也变得模糊,尽管在具体的自译实践中,忠实于原文者也不少见。如何看待翻译作为意义的传达或者再生产,决定了20世纪翻译研究领域中语言学转向和文化转向的分界。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提出:“关于意义,一篇译文的语言能够——实际上必须——随心所欲,这样就能把原文的意图不是作为再生产,而作为和谐,作为对自行表达的语言的补充,作为它自身的那种意图来表达。”(9)瓦尔特·本雅明:《译者的任务》,陈永国主编:《翻译与后现代性》,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9-10页。显然,本雅明关于翻译的观点更加殊于传统,他将译文视为自足的存在,译文与原文的关系是相互补充的关系,译文是原文后世的生命。文学自译长期缺席翻译文学史,中西方皆然,原因就是在文学自译到底是翻译还是双语写作这一问题上,论者莫衷一是。本雅明所代表的解构主义翻译观重新定义了“翻译”,为我们审视翻译活动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研究视界的扩展也为文学自译作为翻译的特殊形式提供了合法性。
张爱玲文学自译文本间的互文关系较为复杂,尽管本文认为张爱玲基于原文的改写应该属于宽泛的“文学自译”,但为分析张爱玲在自译《金锁记》时所采用的不同翻译策略,还是采用了文学自译和改写的区分,即:TheGoldenCangue是《金锁记》的英文自译本,PinkTears和后来的TheRougeoftheNorth则是《金锁记》的英文改写本,而《怨女》和TheRogueoftheNorth之间则是往复自译的关系。有学者认为,《金锁记》的自译可分为“即时自译”和“延时自译”,如第三文本TheRougeoftheNorth到第四文本《怨女》几乎同时产生,属于“即时自译”,而第一文本《金锁记》到第五文本TheGoldenCangue则有28年的时间差,属“延时文本”。(10)陈吉荣:《基于自译语料的翻译理论研究:以张爱玲自译为个案》,第86-88页。也有研究者认为,“张爱玲在故事的自译和改写中,打破了翻译中从一种语言到另外一种语言和文化语境的线性进程,针对翻译过程提出了一种多元的、非层次的结构”。(11)Jessica Tsui Yan Li,“Self-translation/rewriting,” p.393.这些研究都表明了张爱玲文学自译的特殊性,《金锁记》往复译写也成为文学自译研究难得的典型案例。
对于《金锁记》各文本之间的复杂关系,研究者从各自不同的角度进行了解读,例如将这种关系看作是“古老记忆的重复叙事”(12)王德威:《张爱玲再生缘——重复、回旋和衍生的叙事学》,刘绍铭、梁秉钧译,许子东编:《再读张爱玲》,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第7页。“转换性互文关系”(13)陈吉荣:《转换性互文关系在自译过程中的阐释—— 〈金锁记〉与其自译本及改写本之比较研究》,《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8年第2期,第69-72页。“自我改写”(14)游晟、朱健平:《美国文学场中张爱玲〈金锁记〉的自我改写》,《中国翻译》2011年第3期,第45-50页。等等。有关《金锁记》各文本之间的语言表达、叙事方式、文化传达的对比分析,以及运用翻译理论和文化理论来阐释各文本在上述方面表现出的趋同或差异的研究成果近年来较多,在此不赘述,本文所关注的是《金锁记》各译本的接受情况。《金锁记》的接受在中英文世界中出现了中文热、英文冷,冷热不均且呈一边倒的情况,这与张爱玲自译和改写的初衷大相径庭,究其原因则涉及自译者的文化身份和母语文化困境问题。
张爱玲的小说在华语世界广受欢迎,在英语世界却屡受挫折,反响平平。对此现象及其缘由,相关评论甚多,其中较有代表性的看法是,张爱玲在自译和改写中努力去“迎合当时英文读者对于中国情节的期待; 却踌躇于对自我中国情结认知的执着”,(15)於涵、李新国:《中国文化情结的消解与重构——〈金锁记〉与〈北地胭脂〉的对比研究》,《长春大学学报》2019年第5期,第88页。从而使她始终游弋在英语世界的边缘,陷入窘境。但另一个原因,即作为一名文学自译者,张爱玲在使用非母语时的劣势常常被忽略。《金锁记》及其改写本《怨女》在华语世界受到欢迎,是因为这些作品所表现出来的新颖和独特性——既有受中国传统文学的浸润和对传统中国小说叙事手法的娴熟运用,同时也有受西方文学的影响和对西方小说创作技巧的创造性运用,而前者的比重更大。阅读张爱玲的小说,华语读者能从她的语言中感受到“母语的温暖”,但“可惜张爱玲离开母语,知音寥寥”,何以如此?刘绍铭曾向当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社长米歇尔(Karen Mitchell)询问她对TheGoldenCangue的印象,米歇尔的回答是,张爱玲的英文很不错,但故事里的人物对白听起来有点不自然,英美人不那么说。(16)以上参见刘绍铭:《到底是张爱玲》,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第127、89、110页。无疑,张爱玲的自译作品在英语世界的遇冷有其自身非母语劣势的原因,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自译者的尴尬。
自译者有别于双语者,通常自译者的外语能力经后天学习而成,如张爱玲的英语能力就是后天习得,她没有像双语者——如纳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那样从小生活在双语或多语的环境中,外语能力天然而成。但即使是双语者,实际也很难达到天然的双文化境界,毕竟每一种文化身份的获得都需要有文化环境的浸润。而自译者,即便是成功的自译者,其本身都有一个母语和母体文化,任何后天习得的外语都受会制于对母语的娴熟和对母体文化的敏感,造成外语表达“听起来有点不自然”。就此而言,《金锁记》在由母语和母体文化向他语和他语文化的进发过程中“铩羽而归”也就不难理解了。然而,张爱玲为什么不断自译和改写同一个故事?这是对她的“文学自译”进行研究所不可回避的一个问题。而本文更想继续追问的是:张爱玲对《金锁记》的往复译写,于她究竟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她通过这种特别的书写方式表达了什么?以下试论之。
二、《金锁记》译写中的多元身份建构
《金锁记》的英文改写文本在英语世界遭到冷遇,但张爱玲还是执着地将之翻译成最后的英文本TheGoldenCangue,这除了应夏志清之邀以外,是否还有别的原因?从《金锁记》到PinkTears,再到TheRougeoftheNorth和《怨女》;以及从《金锁记》到TheGoldenCangue,就关系脉络来看,张爱玲对《金锁记》的自译和改写,主要方向是从中文到英文,《怨女》从英文自译到中文是次要方向。张爱玲将TheRougeoftheNorth翻译成《怨女》,仅是一个自他语向母语的短暂回归,并非她自译和改写的初衷,从翻译学的角度看,这仅是一种自我回译现象。张爱玲的英文翻译,如果说早期是以练习英文为目的,那么在移民美国后则意在以作家的身份进入英语世界,而非作为异国他乡的移民过客,但她的这个目标却变成一个欲求不得的心结。王德威认为,张爱玲对《金锁记》的重复叙述有三种原因:一是由于张爱玲到美国后的现实处境不佳,经济拮据,事业不顺,使她急于要打入英美文学圈,而《金锁记》发表后获得的巨大成功,使她相信书中的女性主人公、东方情调和家族叙事结构一样也能吸引西方读者。二是上海在张爱玲的小说中始终是故事的发生地,上海的物、事、人是她创作的灵感与源泉,成为她的故事符号。而通过跨语际的译写,她可以保留和延长对“上海”这一符号的记忆。三是张爱玲年少时所经历的家境衰落、父母离异和孤独无助这些难以言表的心理伤痛,通过自译中的他语书写加以释放。(17)Eleen Chang,The Rouge of the North,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8,pp.ix-xi.经济拮据、故土记忆和心理伤痛等个人缘由,促使张爱玲在中英文语际之间往复讲述《金锁记》的故事,这种循环叙事又在有意无意之中,不断强化小说内外弥漫着的浓厚的身份、创伤和困境意识。如果说张爱玲的文学自译有其个人化的动因,那么她所表达的身份、创伤和困境意识则不仅是其个体和私人的,更有着群体性特征,这种从一种语言、文化到另一种语言和文化的迁徙,通过同一个故事跨越语际的重复叙述而实现,同样的主题在重复叙述中挣脱了具体语言和具体文化的桎梏而获得普遍的意义。
张爱玲1955年离开香港赴美,成为离开母语文化的一代移民,由此也真正开始了她以自译与改写作为一种表达方式的离散生活。文学自译现象的发生有诸多原因,迁徙移民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正如有研究者所指出的,“由于流亡和移民所带来的社会经济等原因,自译者迫切希望在新的环境中展现他们的双语能力以求谋生”,(18)Jan Hokenson,“History and the Self-translator,” in Anthony Cordingley,ed.,Self-Translation Brokering Originality in Hybrid Culture,London & New York:Bloomsbury,2013,p.40.这是许多离开故国迁徙他乡的作家从事文学自译和他语写作的最直接的动因,无疑也是张爱玲自译与改写的动机所在。“移民直接不可避免地就是一个跨文化的翻译过程,一个不同语言、文化和世界的迁徙”,因而“自译这个术语提醒我们注意在自译过程中的主体性,以及我们在从事文学翻译时‘翻译’一词的含义:翻译并不简单是个语言转换的问题,而经常是一个身份的问题”。(19)Rita Wilson,“Forms of Self-Translation,” in Nicholas Monk,et al.,eds.,Reconstructing Identity:A Transdisciplinary Approach,Cham,Switerland:Palgrave Macmillan,2017,pp.159,158.移民可说是“不同文化、语言和国别身份之间被翻译的存在(translated beings)”,(20)Carolyn Shread,“Redefining Translation Through Self-translation:The Case of Nancy Huston,” French Literature Series,Vol.36,No.1,2009,pp.51-66.或者也可以理解为“被迫迁徙的存在”,因为“translate”一词既表示语言转换,也表示移动的意思,而后者是词源学意义上的最初意义。有研究者指出:“语言行为是身份行为,跨语际书写的作家的语言选择经常是他们身份的意识形态昭示。通过选择一种语言写作,他们表达对政治的远近、文化的亲疏或者一种创造性的偏爱:我们所使用的语言是我们民族性的基本构成,是我们作为人的理由。”(21)Wilson,“Forms of Self-Translation,” p.163.在文学自译的跨语际表达中,由于自译的作者和译者同一,这与他译中作者和译者之间是明确的自我和他者关系完全不同,自译者的自我和他者身份不断转换,甚至模糊不清,因而在翻译中会表现出两者之间的冲突和调和。张爱玲在自译和改写过程中,往复穿梭中英两种语言之间,从她对文本的语言处理上,可以看出她在自我和他者之间的协商。张爱玲的自译,不断使用克罗宁(Michael Cronin)所谓“翻译同化”(translational assimilation)和“翻译和解”(translational accommodiation)方法,(22)Michael Cronin, Translation and Identity,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6,pp.52-56.即采取改变原文的语言特征和文化色彩以适应译入语文化的阅读习惯,同时也保留原文中的一些文化词项以增加译文的异质性。在使用后者时,张爱玲常采用文内注和脚注的方式予以说明。显然,《金锁记》的自译和改写,并非仅仅是简单地从中文到英文的语言转换,它伴随着张爱玲身份的迁徙,映射着她在他文化中的自我表达和身份的建构。在她的跨语际书写中,既包含着她的女性身份和女性心理,也投射着她的中国文化身份和远离故土的离散作家的情怀,这是一种多元的身份建构。
作为女性作家,张爱玲在《金锁记》中以女性身份关注和描写女性的生存状态和细腻心理。小说主人公七巧是20世纪初新旧世界交替时期的女性,为求富贵而被嫁与残疾人为妻,深感整个家庭的人都轻视自己,在令人窒息的生活环境和氛围中,她极力压制自己对爱与情欲的向往,一步步走向变态,最终将自己所受的苦难通通发泄到儿女身上,造成悲剧的轮回。七巧除了有作为人女、人妻、人母的社会角色,还是个有血有肉、有个体情感的女性,小说中有一段描写七巧与她心仪的三公子见面时讲到自己残疾丈夫的情景:
七巧说道:“天啊,你没挨着他的肉,你不知道没病的身子是多好的……多好的……”她顺着椅子溜下去,蹲在地上,脸枕着袖子,听不见她哭,只看见发髻上插的风凉针,针头上的一粒钻石的光,闪闪掣动着。发髻的心子里扎着一小截粉红丝线,反映在金刚钻微红的光焰里。她的背影一挫一挫,俯伏了下去。她不像在哭,简直像在翻肠搅胃地呕吐。(23)张爱玲:《倾城之恋》,北京:北京出版集团公司,2019年,第226页。以下所引皆出此书,不一一出注。
这段描述通过极其细致的动作和风凉针头、钻石和红丝线等意象符号的摹写,展示出七巧复杂而压抑的心理状态,充满隐喻的中国传统头饰描写显示出作者的身份意识。张爱玲的叙事主题不同于她所处时代那些受西方小说影响下的女性书写,她没有描写社会变革时期的新型女性和重大事件,而是将笔触聚焦于传统女性的悲惨命运,以女性的情感体察去揭示女性细腻的心理状态,以东方女性的身份表达东方女性受到的压抑。其文本叙事既包含传统中国文学的故事讲述方式,也运用西方文学中的心理和意象描写技巧。张爱玲在自译本TheGoldenCangue中,非常忠实地再现了这一段文字:
“Heavens,you've never touched him,you don't know how good it is not to be sick... how good...” She slid down from the chair and squatted on the floor,weeping inaudibly with her face pillowed on her sleeve; the diamond on her hairpin flashed as it jerked back and forth. Against the diamond's flame shone the solid knot of pink silk thread binding a little bunch of hair at the heart of the bun. Her back convulsedas it sank lower and lower. She seemed to be not so much weeping as vomiting,churning and pumping out her bowels.(24)Eileen Chang,“The Golden Cangue,” C. T. Hsia,ed.,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Storie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1,p.150. 以下所引英文翻译皆出此书,不一一出注。
这一段的英文翻译紧扣原文的叙事方式,除了将“天啊”翻译成“Heavens”,原文的叙事语态清晰可辨。可以看出,自译本TheGoldenCangue与原文本《金锁记》之间存在着非常严格的对应关系,这与之前的改写本PinkTears和TheRougeoftheNorth截然不同。PinkTears和TheRougeoftheNorth以及后者的自译本《怨女》,都对原文本《金锁记》做了大刀阔斧的改写,在描述女主人公(改写本将女主人公的名字由“七巧”改为“银娣”)与小叔子“三爷”的感情纠葛时,删去了原文本中精炼、细腻、象征性的人物心理和关系描写,而代之为较长篇幅的、直白的、以动作和对话为主的人物关系描写,这种稍显冗长的叙事应该是以不熟悉中国文化的西方人为目标读者的,其努力趋同和迎合他语文化阅读期待的自我改写,反映了张爱玲在移民早期时的心态和目的,也映射出她当时的翻译观。28年后当张爱玲重译这篇小说时,她选择了回归传统的翻译忠实观,就翻译中的身份建构而言,这种翻译策略的选择表现出张爱玲在远离故土的迁徙中,在中西方文化身份的杂糅和离散中,对自我东方身份的回归,也可以说是她在一个他者文化中,对自我性别和文化身份的昭示。
张爱玲将她的上海故事通过自译和改写在主流英语文化中讲述,这实际上也是一个意图从边缘走向中心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如何保持自我身份并同时被主流和中心文化所认可和接纳,是每一位迁徙者都必须面对的问题。对张爱玲而言,自译和改写是表达诉求和构建身份的最佳方式,但问题在于如何才能在自我和他者之间的协商中达到平衡。常规的文学翻译,即他译中,由于时间差和文化差,作者和译者经常会出现视域的错位,译者在翻译中并不能完全理解和传达作者的意图。从这个意义上讲,即使译者宣称他如何忠实于作者,译文始终不能源自作者的心灵,而是译者基于理解的再创造。文学自译则不存在意图谬误的问题,自译者不仅能够在译文中完整传达自己的创作原旨,还可以增加新的意图,即达成在另一语言和文化环境中的文化身份构建。有研究者将英语之于张爱玲比作是“身份的勋章”,(25)Ian Buruma,“The Road to Babel,” Steven G. Kellman,ed.,Switching Languages:Translingual Writers Reflect on Their Craft,Lincoln: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2003,p.19.这实际说明了迁徙中语言对于身份建构的重要性,“在任何时候,当讲述者将自己翻译成另外一种语言时,他不光是要对这种语言熟练掌握,更重要的是,他必须拥有自我意识,清楚他要讲述的内容,以便能建立各种对话关系并找到自己讲话的位置”。(26)Wilson,“Forms of Self-Translation,” p.163.张爱玲对《金锁记》反复译写,这种回旋往复于同一故事的叙事方式,显然与她的身份建构意识相关,她在找寻自己“讲话的位置”。现在看来,《金锁记》的译本在英文世界是否被广泛接受已经不重要了,事实上张爱玲以他语叙事的方式,通过语际转换已经完成了向另一个文化传达专属于她的身份特征和身份意识,而TheGoldenCangue的忠实自译,或许是她在内心最终达成了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平衡,从这一点来讲,无疑她的文学自译表达是成功的。
三、《金锁记》译写中的创伤和困境意识
张爱玲对《金锁记》的往复自译和改写,除了其移民的身份意识和诉求表达,还映射出该作品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即作者的创伤与困境意识。张爱玲年少时的家庭变故无疑给她留下了心理阴影,这在她日后的写作中表现出来,通过鲜活的人物形象使其个体心理意识以外化的形式获得普遍意义。《金锁记》中主人公七巧的生活境遇和命运的悲凉,尤其是作为旧式家庭女性的宿命,在深层次上体现了写作者的创伤感,如小说中描写七巧临终时想起了生命中曾对她表示好感的男人,这样写道:
如果她挑中了他们之中的一个,往后日子久了,生了孩子,男人多少对她有点真心。七巧挪了挪头底下的荷叶边小洋枕,射上脸去揉擦了一下,那一面的一滴眼泪她就懒怠去揩拭,由它挂在腮上,渐渐自己干了。
这段描述是细腻而感伤的,以张爱玲在写这篇小说时的年龄,她对曹七巧这样的女性生存境况的体察可谓深刻而世故,又是彻悟人性的,女人多少能得到点儿真心就足以生活下去,而这对许多旧时中国女性而言却是奢望。寥寥数语已透露出作者何其悲凉的心境和对女主人公无限的同情。可惜,这段描写在改写本中同样没有得以保留,或许在张爱玲看来,这种感伤是那些无法感同身受、对中国文化缺乏了解的西方读者难以体味的,张爱玲早期进行大幅度自我改写或许有这方面的考量,但减少了文化和文学异质性的他语改写,其接受效果与原著相比,却大大降低。这应该也是《金锁记》改写本在西方遇冷的原因,好在最后的TheGoldenCangue译本对忠实翻译的回归,保留了小说的原汁原味:
but if she had chosen one of these,it was very likely that her man would have shown some real love as years went by and children were born. She moved the ruffled little foreign-styled pillow under her head and rubbed her face against it. On her other cheek a teardrop stayed until it dried by itself:she was too languid to brush it away.
其实,文学书写对创伤心理的表达,往往体现出个人经历与语言之间的内在矛盾,语言的不确定性和歧义性常常使创伤感难以言说。拉康和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模式已经得出,创伤所带来意识的扭曲和分离会长时间地驻留在受创者的心里。(27)Michelle Balaev,ed.,Contemporary Approaches in Literary Trauma Theory,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 2014,p.2.《金锁记》通过主人公的性格和命运投射出作者深层创伤心理,但这种创伤的表现范围以及传达对象都是有限的,或者在某种程度上说,对创伤的表达并非是有意识的。而《金锁记》的自译和改写则表现了作者努力突破语言的藩篱,同时让创伤情绪有了一个新的发泄口,在创伤心理和语言表达之间形成一种张力,就如王德威所阐释的那样,“她仿佛不能再信任她的母语,切切要找寻一个替代声音以一吐块垒。……在传达、翻译人我关系的(不)可能性时,异国的语言未必亚于母语”。(28)王德威:《张爱玲再生缘——重复、回旋和衍生的叙事学》,许子东编:《再读张爱玲》,第12页。跨语际书写虽然受非母语表达的限制,但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母语文化的心理压制,在将创伤以另一种语言进行表述的过程中,更希望被另一个文化的人们所感同身受,创伤表达的价值得以体现。亦即,当这种创伤被传达到另一种语言和文化中去的时候,创伤所带有的个人特征和历史文化印记会受到一定消解,而触动人心的则是人类共有的对生存的体认,这种共同体认具有普遍的意义。后结构主义创伤理论认为,“创伤会随着语言、社会和历史的变化呈现出多样性并通过心理、语言和社会的机制体现价值”;并且“创伤不属于个人,一个人的创伤和另一个人的创伤紧紧连在一起,形成跨越历史的创伤概念”。(29)Cathy Caruth, Unclaimed Experience:Trauma,Narrative,and History,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6,p.6.张爱玲有其个人在特定时期遭遇的心理创伤,而通过写作以及自译和他语改写,她唤起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对这种创伤的感知,即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在物我、他我等关系中遭遇的创伤记忆。换言之,创作主体的隐秘情绪在文学书写中得以表达,而这种情绪通过自译的方式又会以另一种语言——一种非母语表达在异国传播,使原本带有族裔色彩的创伤书写超越个体成为一种穿越时空的历史记忆和表达。
《金锁记》的自译和改写表达了张爱玲进一步通过文学书写释放其创伤情绪的愿望,在另一种语言中,她以打破语言隔阂和时空限制的他语表达,将《金锁记》中烙印着历史印记的创伤情绪,扩延成具有普遍意义的创伤记忆,成为研究其他问题的切入点,如语言、心理和行为之间的关系。通过文学自译的方式,张爱玲将她的故事和所表达的创伤感传达给更广泛的读者,使更多的人对跨越文化和种族的女性的命运进行思考,由此个体的创伤被升华为一种普罗大众的创伤记忆,唤起人们对命运和人生意义的追问。《金锁记》或许不过是对一个普通的女性及其家庭琐事的描写,但其中反映出的关于人的贪欲、自私与绝望无助则是人类共有的困境。刘再复称张爱玲的小说重要的“并不是它的历史感,而是它的哲学感。她是一个逼近哲学,具有形而上思索能力的很罕见的作家。她的作品浸透着很浓的世界和人生的哲学氛围”。(30)Caruth, Unclaimed Experience p.35.这一点在《金锁记》最后一段的描述中有充分表现:
七巧似睡非睡横在烟铺上。三十年来她戴着黄金的枷。她用那沉重的枷角劈杀了几个人,没死的也送了半条命。她知道她儿子女儿恨毒了她,她婆家的人恨她,她娘家的人恨她。
Ch'i-ch'iao lay half asleep on the opium couch. For thirty years now she had worn a golden cangue. She had used its heavy edges to chop down several people; those that did not die were half killed. She knew that her son and daughter hated her to the death,that the relatives on her husband's side hated her,and that her own kinsfolk also hated her.
对于这一段点题文字,张爱玲在TheGoldenCangue中的翻译也忠实对应。七巧的人生困境在于她戴着“黄金的枷”,而这又何尝不是人类共有的困境,人们贪婪地追求财富、满足私欲不知不觉中已戴上囚禁自己的黄金枷锁,而这亦是小说原名《金锁记》的深刻寓意。张爱玲在早期的自译和改写中,将小说的名字改为《粉红的泪》和《北方胭脂》,虽然能够迎合接受文化对东方女性的猎奇心,却失去了书名原来所蕴含的人生哲学感悟。在《金锁记》往复译写的最后,或许是不再考虑商业出版的利益和不再着意求同于他国文化,她最终选择了自我文化体认与回归,译本还原了小说的本来面目。
张爱玲突破历史的、文化的和语言的局限,将她对一个悲剧人物的描写引向对人类命运的哲学思考,这一点或许她自己未必有明确意识,然而一个作家的优秀本就在于能够通过平凡人物的命运书写人性的悲剧,张爱玲之所以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重要作家、作品受到世人青睐的原因正在于此。同样值得肯定的是,她通过文学自译和改写,往复深化她对自己所深切感受到的人生悲剧意识和伤痛情绪的表达,并由此使作品原有意义成功地得以扩延和升华。
综上所述,“张爱玲有作品自译的习惯,且相当在乎英语读者对她的英文作品的评价”。(31)刘绍铭:《到底是张爱玲》,第99页。当我们更加深入地聚焦张爱玲的自译和改写时,就会发现通常所认为的张爱玲的文学自译,早期是出于英文练习的目的、后期则多来自在异国他乡的生存压力、翻译策略迎合英语世界等说法,只是指出了其文学自译现象某些层面和原因,而本文重在揭示的是现有研究未尽之处。实际上,从张爱玲开始从事文学自译和改写,就已经确定了她的作品不仅仅属于一种语言、一个文化和一段历史时期,因为翻译是原文意义不断扩延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作品中被单一性所禁锢、遮掩的意义得以释放,获得普遍的价值。而文学自译则是作者主动地促进意义扩延的形式,张爱玲在28年之间数次往复自译和改写《金锁记》表现了她的这种努力,文学自译是她的作品的另一种存在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