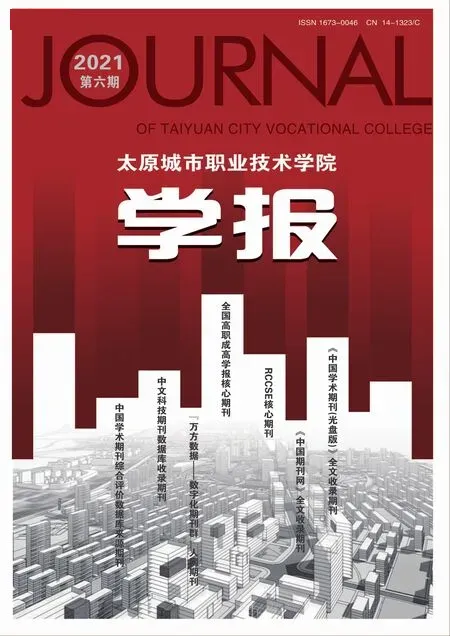巴金《寒夜》中的隔阂主题探析
■张坡
(河南大学文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
《寒夜》是巴金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开始写于1944年冬,完成于1946年底,被称为是“巴金创作历程中一座不朽的丰碑”[1]。作者以生动细腻的笔触书写了在抗战胜利前夕的陪都重庆,小职员汪文宣一家四口包括祖孙三代的悲欢离合。值得注意的是,文中无处不在地充盈着令人扼腕叹息的“隔阂”之感,这一家人明明相爱,相互之间却总是难以了解,最后沦落至家破人亡的悲惨结局。他们不幸的遭遇引起了读者的无限同情,同时也促使着人们去探求“隔阂”的真实面目,研究造成“隔阂”的具体原因,以及反思“隔阂”带来的深刻启示。
一、难以规避的情感疏离
汪家的家庭成员包括儿子汪文宣、妻子曾树生、汪母和孙子小宣,可以说,他们互相之间都存在着难以规避的情感疏离,包括夫妻之间的隔阂,婆媳之间的隔阂和母子之间的隔阂。
汪文宣和曾树生在上海念大学时相识,他们志同道合,共同怀抱着为教育事业而献身的崇高理想。作为沐浴了新思想洗礼的进步青年,他们大胆地冲破了封建礼教的条条框框,在没有经过旧式礼仪的前提下就同居结合了,并且孕育了爱情的结晶小宣。然而,曾经的豪情壮志被残酷的现实打击得面目全非,为生活所迫,汪文宣在一个半官半商的图书文具公司卖命,拿着少得可怜的薪水,整日埋头伏案,逐字逐句地校对那些似通非通的译文和用法奇特的字句。曾树生则是在私立大川银行做职员,负责装点门面,同样从事着与教育毫无关系的职业。多年庸庸碌碌的生活,使得他们的心理距离已经越拉越远。
在文中开头,曾树生负气离家出走,托人去取她的随身物品,此刻汪文宣的内心其实十分盼望妻子回来,但他的做法却是故意说反话,表示对方回来不回来,自己并不关心。这样的举动,不仅没能表达出自己的心意,还增加了彼此的误会,白白地在两人中间添设了一层隔阂。当汪文宣身患肺病,发现自己的身体越来越虚弱时,他的内心五味杂陈,暗潮涌动,他想要在有限的时间内将自己热烈的爱意传达给妻子,但又担心会给对方造成负担,惹得爱人身心不爽。两人虽然同岁,妻子精力充沛,活力四射,他却病病殃殃,萎靡不振,这让他觉得他俩“相差的地方太多,他们不像是同一个时代的人”[2]。由此,他选择闭口不言。当曾树生忙于交际顾不上他时,他总是沉默不语,在深夜里等着爱妻回家,却不曾明白表达。曾树生对他表示,“我在外面,常常想到家里。可是回到家里来,我总觉得冷,觉得寂寞,觉得心里空虚。你近来也不肯跟我多讲话”[2]82。他同样还是惶恐地以怕她精神不好为托词,掩盖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当曾树生犹豫要不要前往兰州时,他仍然选择将自己的留恋与不舍憋在心里,怯于袒露。就连曾树生即将离开的最后一晚,汪文宣在家中终于等到在外应酬的妻子回来时,他还是没能坦白自己的情感,反而谎称自己已经睡了一觉,在妻子转身整理行李时,蒙着头躲在被窝里默默流泪。最后,即使是汪文宣的病情发展到危重阶段,他在信中也并不曾告诉远在天边的妻子实情,而是常常编造一些假话,直至病逝。反观曾树生,她从头到尾同样很少主动地去观察丈夫的真正状态和内心世界。
汪母和曾树生之间的隔阂可以说较之更甚。汪母看不惯儿媳的任性做派,无法理解对方的所作所为,总是几次三番地主动挑衅,甚至是无端咒骂。她嘲讽曾树生每天打扮得妖形怪状,私交“男友”,并在汪文宣耳边喋喋不休,唆使儿子好好教训妻子一番,或者直接离婚,再找一个。在她的认知里,曾树生轻视自己,毫无做儿媳的恭顺模样,甚至被气得直呼“我什么苦都受得了,就是受不了她的气!我宁肯死,宁肯大家死,我也不要再看见她!”[2]142即便是汪文宣向她极力解释,她也丝毫没有改变固有的想法。面对汪母的破口大骂,曾树生并不会甘心忍气吞声,她坚决捍卫自己的权利和地位,反抗婆婆的说三道四,因此两人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多次争吵,结果导致隔阂越来越深。
汪母与汪文宣、曾树生和小宣这两对母子之间,同样存在着隔阂。汪文宣一心痴恋曾树生,然而汪母却并没有真正理解儿子的心意,虽然她为了这个家洗衣做饭,任劳任怨,汪文宣也多次发自内心地感叹母亲的不易,但是她不懂得他的内心,也是铁一般的事实。当曾树生因为种种原因,终于下定决心离开家庭,奔赴兰州,汪文宣对此深感痛苦,却无人诉说,只能到冷酒馆买醉。当汪母得知曾树生写信来要与汪文宣分开的消息,她的反应竟然是仿佛终于出了一口恶气一般,觉得痛快不已,丝毫没有想到这对儿子来说会是多么残忍的打击。
作品中对小宣的着墨并不多,只是将其作为翻版的汪文宣来进行刻画,他少年老成,性格沉闷,由于忙于学业,很少回家,就连和自己母亲的关系也很疏远。曾树生接受过新式教育,明白教育的重要性,即使是条件有限,也坚持将儿子送到贵族学校接受更好的教育,然而小宣对母亲的良苦用心并未能够完全理解,与其也是基本无话可说,交流甚少。
二、森然交错的壁垒探源
《寒夜》以巨大的吸引力引领着读者去阅读,去感受,去揣摩,这充斥其间的厚重的隔阂之感不仅使得作品中的人物彼此疏离,也使得读者随之感叹神伤。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他们之间如此隔阂?
从根本上来说,这一切都是由社会政治经济环境造成的。当时,“抗日战争已经进入到最艰难、最疲惫、最惨烈的后期阶段,内忧外患,家国危难。日本侵华敌机屡屡轰炸重庆,防空警报时时响起,驱使人们四处逃散,物价飞涨,生活异常艰难,人们朝不保夕,时时面临死亡的危险”[3]。包括汪文宣一家在内的普通老百姓就是生活在这样的水深火热之中,不知什么时候耳边就会突然响起警报声,如何尽可能迅速地逃往防空洞避难,成为了每一个男女老少的生存必修课。战争年代的物价急速飞涨,人们的生活成本急剧升高,更是加深了身体和精神上的压力。到处人心惶惶,保存性命成为了第一要事,哪有工夫再去高谈阔论交流理想,再去轻声细语谈情说爱,再去和颜悦色倾听心声?所谓的幸福,已经被残酷的现实吃抹干净,什么也不留了。
文化方面也具有重要的影响力。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新旧思想文化同时并存。汪母是旧式思想文化的典型代表,时刻保持着捍卫封建传统教条的姿态,这与她出生于晚清书香门第,从小接受封建伦理文化的浸染有关。汪母以传统的三从四德的规矩来审视儿媳,自然不能接受对方的所作所为,尤其是“越矩行为”。在她的认知里,真正的贤妻良母应该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伺候丈夫,教育子女,孝顺老人,而不是整日在外招蜂引蝶,不守妇道。她常以“八抬大轿”“明媒正娶”的由头来攻击儿媳,自恃高人一等。曾树生是新型思想文化的典型代表,她坚信女人可以自主独立,有自己的一方天地。在汪母恶毒无理的攻击面前,她竭力抗议:“我老实告诉你:现在是民国三十三年,不是光绪、宣统的时代了”,“我没有缠过脚——我可以自己找丈夫,用不着媒人”[2]149。“新旧文化由于文化立场的对立处于互不相容的两极境地。书中婆媳两人各处一极,以致矛盾重重。两人争执时,各执一词,咄咄逼人,这倒并非有意强词夺理。在相互攻击过程中,她们凭借的是各自的文化观念”[4]。于是,谁也无法理解谁,陷入了无法相容的尴尬境地。
不同的性格也加剧了他们之间隔阂的程度。汪文宣的性格属于传统内敛型,年轻时可能尚有些许激情,但随着生活的压力越来越重,他不知不觉中变得越来越胆怯懦弱,顶着一个“老好人”的名号,却没有半点男子气概,如同没有长大的孩子一般软弱无能。面对上司他不会阿谀奉承,面对妻子他不会花言巧语,面对母亲他不会据理力争,无论受到什么样的欺负、误会与逼迫,他总是百般隐忍。在公司,他整日小心翼翼地蜷缩着,别人的无心举动在他的眼中可能是对自己的蔑视,主任、科长无意的一声咳嗽,他就胆战心惊地以为自己又做了错事,更是一动也不敢动。同事们之间的正常交流,他认为是在对自己评头论足,躲闪得更加迅疾。母亲和妻子没完没了地争吵,他夹在中间无法做出抉择,只能无力地淌着眼泪,惩罚自己。他“害怕看母亲的憔悴的愁容,也怕看妻子的容光焕发的脸庞。他变得愈不爱讲话了。他跟她们中间仿佛隔着一个世界”[2]85-86。
曾树生的性格与汪文宣是截然不同的,她勇敢无畏,敢于反抗,不会在汪母的咒骂讥讽中委曲求全,不会在沉闷的死水生活中坐以待毙,她清楚地明白,“她并没有犯罪,为什么应该受罚?这里不就是使生命憔悴的监牢?她应该飞,她必须飞,趁她还有翅膀的时候。为什么她不应该走呢?她和他们中间再没有共同点了,她不能陪着他们牺牲。她要救出她自己”[2]168。于是,她尝试着勇往直前,去追求未来的幸福与美好,即使困难重重,她也不轻言放弃。
汪母本是大家闺秀,人到晚年却穷困潦倒,还要仰仗儿媳工作养家,这样大起大落的经历造就了她守旧固执的性格,由原先的知书达理变得自私尖酸。再加之丈夫早逝,自己孤身一人带大孩子,寡母心态更是加强了汪母性子的强势。从头到尾,她总是在指责儿媳的不是,悲叹儿子的不幸,当汪文宣的病已经进入晚期阶段,连话都说不出来,她依然与曾树生僵持着,不肯让步,可以说,汪母对儿子的爱护再深也抵不过对自己尊严的保护。
小宣少年老成,虽然还是个十三岁的孩子,但是他的身上似乎永远都没有青春的痕迹,就连说话都有气无力的,像他生病的父亲,他永远将自己的内心封闭着,任谁也走不进去。可以看出,汪家每一个人的性格,都阻碍着他们的心意互通,层层隔阂的壁垒森然耸立。
三、发人深省的启示思考
汪家没有一个人是坏人,却难以相濡以沫,心贴心地共渡难关,反而互相折磨,将彼此推得越来越远。《寒夜》透露出来的无处不在的隔阂之感并非是单纯的沟通障碍,它牵引出来了诸多问题,有待人们深思。
首先是小人物的精神困境问题。《寒夜》以一代知识分子理想的破灭、家庭的破散和生命的终结,记叙了没有抢过人、偷过人、害过人的小人物的悲惨生活,揭露了小人物彷徨在残酷世间的精神困境。汪文宣的家人们一个个各行其是,虽然打着爱的名义,却无法真正地理解他、同情他,反而有意无意之中刺激他伤害他;同事们一个个相互防备,除了钟老之外,没有人能够给他以温暖和帮助。最后,汪文宣在举国欢腾中,无声地死去。“与同事、家人在精神上的隔阂,使他陷入了显而易见而又刻骨铭心的孤独,感受到人与人之间沟通的不可能”[5]。作者以沉重的笔调书写出了小人物的无奈,并向人们提出了这样一个深刻的问题:在艰难的时代条件下,人们不仅面临着物质方面严重匮乏的问题,精神方面同样面临着无以诉说的困境,到底应该如何打破沟通阻碍,实现心灵交流?时移世易,在如今的现代社会中,问题同样存在,又该如何化解?《寒夜》通过对个体的描述,揭示了跨时代的群体的问题。
其次是女性的生存与出路问题。巴金在《寒夜》中对女性的生存与出路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五四运动高举反封建反传统的大旗,呼唤着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女性意识也随之剧烈地震动生发。曾树生不同于传统封建社会中如藤蔓一般依附于家庭而丧失自我的守旧妇女,她的女性独立意识已经觉醒。她是勇猛无畏的,对封建伦理制度选择不屑一顾,毅然决然地与情投意合的汪文宣自由恋爱,自主结合;她是敢于担当的,丈夫卧病在床无力赚钱养家,她孤身在外想尽办法挣得薪金,并搞起投资以补贴家用;她是卓有见识的,深谙教育的重要性,她想尽办法将儿子送去贵族学校学习,而不是限于简单的读书认字;她是机警前卫的,当她发现自己的家庭就像一滩沼泽地,她无法救出别人而只能自救时,拼力做出了多次尝试。可以看出,她的身上充满了现代知识女性自我主体意识的独特魅力。然而,这些付出和牺牲,并没有得到家人该有的认同和支持。除此之外,曾树生也是新旧历史更迭时期多种因素的综合体,身上存在着某些无法规避的弱点。在特殊的社会环境下,她在银行充当“花瓶”,以取悦领导和顾客为业,这无疑具有某种不可靠性和依附性。她得以保住饭碗,实现经济独立,甚至是升职加薪,大部分原因是青睐她的主任所特殊赋予的。而当她想要逃脱沉闷的生活时,又情不自禁地被软弱的丈夫所牵制,内心被两个不同方向的力量所拉扯,身不由己地陷入左右为难的境地,不知如何是好。“一方面,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现代女性们对封建意识有一种自觉的背弃和批评;另一方面,传统文化观念、价值体系、伦理规范已内化为一种心理沉积,客观上不时地隐现在她们的意识深处”[6]。在曾树生身上,明显地显示着这两种矛盾冲突,她想要追求自由与幸福,但她的脚步是踉踉跄跄的,游移不定的。
再次是启蒙现代性后续生发问题。一个受到五四启蒙主义影响的家庭,本来应该脱离沉重的窠臼,赢得新生的,结果却是最终在社会中分崩离析,启蒙思想后续产生的问题不容忽视,巴金敏锐地察觉到症结所在,并对此进行了深刻地反省。从《寒夜》中可以发现,文中提到的知识分子无一例外,都落得了悲惨下场:汪文宣由一个气宇轩昂的才子变成了一个唯唯诺诺的懦夫,曾树生由一个朝气蓬勃的才女变成了一个贪图享乐的花瓶,汪母由一个贤惠端庄的淑女变成了一个尖酸刻薄的老妇,唐柏青由一个才华洋溢的硕士变成了一个醉生梦死的酒鬼,他们都曾饱腹学识,然而为之赋予宝贵时间和精神重托的知识却不能在解决小人物出路问题上起丝毫作用时,知识成了“千人所指”的对象。知识的“虚无”性可见一斑[7]。巴金对所谓的自由也打出了问号,曾树生的言行举止,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夹带着自私自利的印记,抛弃重病的丈夫,冲撞年长的婆婆,不顾年幼的儿子,这些做法很难不被人诟病,更何况,她所追求的自由,其实质内涵是很有必要商榷的。
四、结语
20世纪的中国现代文坛,巴金以其独具魅力的文学写作,成为了不容忽视的文学大家。他“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多产的作家之一,也是中国现代中长篇小说的开拓者之一”[8],在他的一系列文学作品中,《寒夜》“不仅为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文坛抒写了凝重厚实的一笔,也成为中国现代小说的经典之作。”它的魅力不会因为年代的逐渐远去而褪色,反而历久弥新,留给后人无限的探索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