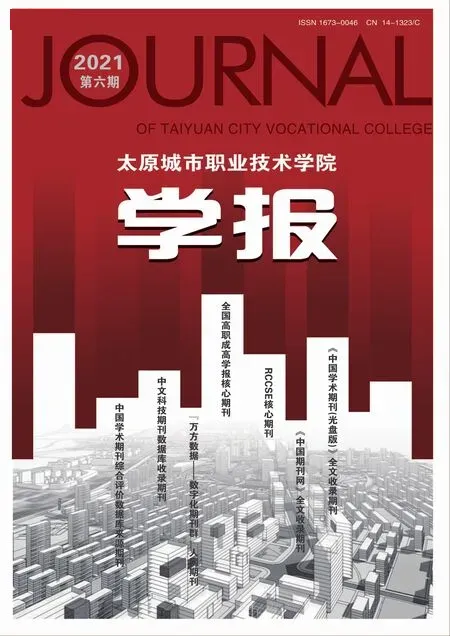身份意识的破碎与重建
——镜像理论分析安托瓦内特的身份认同之路
■祁 慧
(沈阳师范大学文学院,辽宁 沈阳 110034)
19世纪英国作家夏洛特·勃朗特创作的《简·爱》自问世以来,便受到了人们的热烈追捧与高度评价,出身低微、相貌平平的简·爱却有着强烈的平等、自立、自强的观念,人们为她这样一个不向命运低头的坚强女性形象而感动;与此同时,也痛恨于那个被幽禁在阁楼上,破坏简·爱幸福婚姻的疯女人。然而,20世纪的英国女作家简·里斯却有着不同的看法,她认为夏洛特·勃朗特仅仅站在自己的女性立场上进行创作,站在帝国主义文化中心的立场上创作作品,为此,她要为这个疯女人写出生命,发出她自己的声音。在这样的心境下,简·里斯作了充分的研究,《藻海无边》作为《简·爱》的前篇应运而生。小说一问世便好评如潮,成为女性主义文学、后殖民主义文学的经典作品。
小说的主人公安托瓦内特居住在西印度群岛牙买加的一个岛屿,正值黑人奴隶解放、种植园经济解体的时代。父亲是一名纯正的英国白人,母亲是克里奥尔人,他们家是种植园主。当地的白人太太小姐嫉妒她母亲是美人胚子,把她排斥在外;黑人奴隶在解放法案颁布后终于获得了自由,他们将殖民者剥削他们的罪恶,全部发泄到了安妮特母女身上。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期,安托瓦内特一家人的特殊身份使他们感到了极大的耻辱与不安。无论是黑人、白人,还是男人、女人,都将仇恨与不屑的目光投向了他们。“在你们中间,我常常弄不清自己是什么人,自己的国家在哪儿,归属在哪儿,我究竟为什么要生下来······”[3]安托瓦内特的困惑正表明了她想要得到身份的认同感与归属感,能够有自己的话语权,能够从世界的边缘走向世界的中心,而不是被排斥在外。从安托瓦内特到伯莎,从伯莎到简·爱,这一过程的转变,可以用雅克·拉康的镜像理论进行分析。
雅克·拉康作为法国精神分析学派和结构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其镜像理论是他整个精神分析理论的起点,具有重要的意义。他指出,自我的建构离不开自身也离不开自我的对应物,即来自于镜中自我的影像,自我通过与这个影像的认同而实现[4]。根据拉康的理论,镜像是一个人建立身份意识、获得身份认同感的首要途径。主体自我意识的形成阶段正是对应着镜子阶段,镜子阶段是自我意识形成的关键时期[5]。在他有关“镜像阶段”的著名论文中揭示了儿童确认自身主体的过程。它分为三个时期,从“将自我与他人混淆”到“学会把影像从他人的现实中区分开来”,再到“能够确认自己的影像”,逐步确认了自身身体的同一性。再往深的说,不是只有儿童才可以通过镜面获得形象,每一个成人主体在与他人接触的过程中,通过他人的凝视与评价,同样能够获得自我形象。因此,身份的确立与镜像密切相关。拉康认为“主体起初就不是协调一致的,从根本上说她是被自我弄得支离破碎的,自我从来就不完全是主体,从本质上说,主体与他人有关”[6]。
一、黑人同伴与安托瓦内特的镜像关系
(一)寻找身份认同的困惑
从哲学上讲,身份(Identity)即同一性。身份认同就是寻找个人生存的根基,即“我”之所以为我的理由[7]。安托瓦内特从小与黑人生活在一起,他们对她的评价对于安托瓦内特建构自我身份具有重要的意义,尤其是与黑人同伴蒂娜的关系尤为明显。安托瓦内特作为有着白人“高贵”血统的克里奥尔女性,对于黑人的态度也存在着某种种族歧视的看法,虽然同住在一个地域,却从不正眼看她们,有意地称她们为“黑种女人”,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在疏远她们之间的关系,难以形成统一的认同。但是,当地的黑人对于她们一家的态度与做法对尚在童年时期的安托瓦内特产生了深重的影响,使她难以确定自己的身份,对自我产生了困惑。
正如加布丽埃·施瓦布在《认同障碍——罪、羞耻和理想化》一文中所说“一旦权力关系逆转,施暴者变成了受害者,受害者则成了施暴者。但这不是简单的逆转,因为曾经的施暴者带着罪恶和耻辱被卷入新一轮的暴力,昔日的受害者则满怀愤怒和仇恨。在另一个不同的权力格局中暴力再次粉墨登场”[8]。当地的黑人奴隶将曾经种植园主带给他们的压迫与剥削全部发泄到了安托瓦内特母女身上:庄园被烧毁,弟弟被烧死,母亲被逼疯,这一切都给她的内心造成了深重的影响。为了不给自己“惹麻烦”,即使被人当面辱骂为“白蟑螂、僵尸般的眼睛”,也忍气吞声。在这个地方,她是孤立的,是独自一人的,她不可能依靠自己的身份,与他人理论。“在你们中间,我常常弄不清自己是什么人,自己的国家在哪儿,归属在哪儿,我究竟为什么要生下来!”[3]安托瓦内特的这一句话正道出了她的困惑,身为女人,已经没有了发言的权利,而第三世界这一身份使得她更是在夹缝中生存,一旦稍有不慎,便会没有存在的权利与空间。
(二)黑人朋友蒂娜与安托瓦内特的镜像关系
如果说陌生黑人与她难以建立身份认同,这种情况可以理解。但是那个与她一起洗澡,一起玩耍,一起睡觉,甚至穿走她唯一一件干净的连衣裙的黑人“朋友”,一样对她不屑一顾。表面看似很平静,那层复杂的关系却使她们的内心难以达成统一。在平日的相处中,已经体现出了彼此之间的矛盾。安托瓦内特称蒂娜为“骗人的黑鬼”[3],而她骨子里流出的高雅也被蒂娜击得粉碎,“黑鬼比白皮黑鬼还强呢!”[3]这对“朋友”一个为“黑鬼”,一个则是“白皮黑鬼”,在镜子中彼此审视对方,却总是在互相伤害,这种紧张的关系在安托瓦内特一家所生活的庄园被烧毁的时候发展到了高潮。
庄园被毁后,她们一家打算离开库利布里,走的那一刻,安托瓦内特看到了蒂娜。“今后我要同蒂亚一起住,我要向她那样。”[3]她用尽全力跑向心中的彼岸,她生活中的一部分,希望能够得到她的怀抱。然而,迎来的却是尖棱的石头。“可我没看见她扔。我也没感觉到,只觉得有什么湿漉漉的东西从脸上淌下。我瞧着她,只见她放声大哭时一张哭丧脸。我们互相瞪着,我脸上有血,她脸上有泪。就像看到了自己。像镜子里一样。”[3]这是安托瓦内特在文本中第一次提到镜子,她在这个镜子里看到了与自己一样受到伤害的落泪的蒂娜,同时,更是映射出了自己,是自己的身体在流血,心在流泪。这面扭曲的镜子,也同样映射出了两人扭曲的关系,种族冲突是不可调和的矛盾,即使两人再想要拥抱彼此,也会被冰冷镜面或者扭曲的镜像拆散,身份认同最终因破碎的镜像而宣告失败。
二、罗切斯特与安托瓦内特的镜像关系
(一)身份意识的重塑
长大后的安托瓦内特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在同父异母的兄弟理查德·梅森和罗切斯特父亲的安排下与罗切斯特相识并很快举行了婚礼。除了自己的父亲,从没有接触过纯正英国白人男性的安托瓦内特,爱上了她所谓的丈夫罗切斯特。看到他,就好像看到了希望,看到他,就好像自己也即将成为一名纯正的英国姑娘,她希望能够通过与他的结合,改变自己的尴尬处境与身份,把自己从“白蟑螂”转变成她最喜欢的画《磨坊主的女儿》中那个纯正的英国姑娘。事情好像顺着她的想法向前进行着。蜜月初期一切平静如水,安托瓦内特享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安全感”和“幸福感”,她以为真的可以不用再像母亲一样:一生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家园被烧毁,孩子变成痴呆,丈夫相继离去,被人嘲笑,受尽侮辱,成为彻彻底底的疯女人。她以为罗切斯特许诺给她的安宁会一直持续下去。
然而,这只是她的一厢情愿,罗切斯特从来就没有真正爱过她,仅仅是为了那3万英镑的财产屈身来到这里,与她成婚。“我渴望得到她,可那不是爱。我对她没几分温情,她在我心中是个陌生人,是个思想感情的方式跟我那套方式不同的陌生人”[3]。安托瓦内特审视罗切斯特的过程中,罗切斯特也在观察着她,也在用自己的眼光,用英国人特有的文化对她进行评价。在他眼里,这个岛屿,这里的花花草草,这里的所有的人,都是陌生的、异样的,包括安托瓦内特在内,都是野蛮人的形象,是低级生物的代表。在这面异化的镜子中,罗切斯特占据主导地位,他是文明的象征,是权利的象征,掌控着改变妻子身份的权利,作为他者,他忽视或者肆意剥夺妻子建构身份的权利,都会将她逼向绝望。可见,他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二)身份权利的丢失
真正改变安托瓦内特,并使她真正成为一名疯子正是从她与丈夫的结合开始。文章第一句话写到“常言道同舟共济,白人就是如此。可我们跟他们不是同舟”[3]。这一句话道出了英国白人与安托瓦内特之间的隔阂,虽然她有英国血统,虽然她同样身为白人,但父权制社会下,在英帝国体系与男权话语的建构下,他们不可能产生真正的认同。罗切斯特最终听信了科斯韦与阿梅莉的话,不顾妻子的感受,在与妻子仅有一墙之隔的屋子里与黑人女仆发生关系,将格兰布瓦这个承载着安托瓦内特美好回忆、唯一赖以维系身份的地方一并玷污了。他一遍遍地叫着安托瓦内特“伯莎”,如同当年安妮特被人叫成疯子一样,将自己的妻子定义为疯子。西蒙娜·德·波伏娃的《第二性》中提到,“他是主体,是绝对,而她是他者。”在父权制的文化氛围里,男性就是标准,而女性则是消极的,反常的,是他者[9]。安托瓦内特没有任何话语权,身份只能由他人界定。拉康曾指出,他者话语或者说他者对自己名字的称呼是人们确认身份的重要途径。安托瓦内特痛恨自己的丈夫,她明白罗切斯特是想用别的名字将她变成另一个人,但是却没有做到真正独立,没能像女仆克里斯托芬对她讲的提起裙摆就走,拿回属于自己的财产,而不是受制于男性。她的这份软弱使她最终走向了疯狂的路程。
随后,就像她的母亲被梅森先生带走一样,安托瓦内特被丈夫带到了英国,这个曾经她梦寐以求的地方,却成了葬送她生命的地方,她不仅被幽禁起来,还被人冠以“疯子”的头衔,没人敢接触,或者有些人根本就不知道她的存在。“这里没有镜子,我不知道现在自己变成了什么模样。现在他们把一切都拿走了。我在这地方干什么,我是谁啊?”[3]安托瓦内特再一次提出了自己的困惑,只是这一次她无法再向先前那样,能够通过与他人的接触,了解自己。她不仅被幽禁了起来,连唯一可以见证她身份的镜子也被丈夫一并拿去,这从根本上阻断了她身份认同的道路,从根本上否定了她的存在,致使她完全成了一个“疯女人”。福柯指出疯癫是大多数人对少数人压迫的产物。当一部分人的思想与言行举止违背了自己的主流价值和意识形态标准时,就会将这一部分人视为疯癫[10]。安托瓦内特的身份与行为正是因为不符合罗切斯特这个男权体系下权威人物的标准,违背了大英帝国的权力体系,罗切斯特才将她定义为疯子,最终将她逼疯。
三、简·爱的镜像关系
(一)简·爱愿望与行动的代理人
《简·爱》中的安托瓦内特被剥夺了话语权,成为了人们口中的“伯莎”,那个“魔鬼”,那个“德国吸血鬼”。她没有办法讲出自己的故事,因此只能靠罗切斯特的话与简·爱的梦讲述出来。她的出现是在场的缺场。斯皮瓦克认为,小说作者把简·爱塑造成一个敢于追求自身幸福权利的个性主义和女权主义英雄,而对疯女人伯莎·梅森进行了妖魔化处理。似乎她们两人之间是对立的、冲突的。然而,细看简·爱儿时的生活,她的梦以及她与罗切斯特相处时的心理活动,可以看出她的内心实际上住着一个“魔鬼”,而这个“魔鬼”由安托瓦内特扮演。
简·爱儿时阅读书籍《英国鸟类史》,关注的不是严谨的文字,不是有关生物的图片,而是那些“说不清什么情调弥漫着孤寂的墓地、颓败的围墙,海上的鬼怪”[12]。她面对约翰·里德的恐吓无处哭诉,佣人们不理睬,里德太太装聋作哑,对约翰逆来顺受,被骂为“耗子、鬼样、坏畜生”,甚至砸伤头部。这些无不让我们联想到安托瓦内特受到的黑人的嘲笑与折磨,即使被人当面嘲笑为“白蟑螂、疯姑娘”,被蒂娜用石头击中,却依然想着“少惹麻烦为妙”。随后被禁闭在红房子更是与安托瓦内特幽禁在阁楼上相似。里德太太的那句“有一次她同我说话,像是发了疯似的,活像一个魔鬼”[12]。这不禁让我们想到伯莎的疯狂,她们都是被别人定义为疯子。简听到罗切斯特给自己起的“简·罗切斯特”这一名感到恐惧,其实质就和安托瓦内特不愿被丈夫称为“伯莎”一样,她认为那是一个目前她自己尚不认识的人,她感到自己的身份受到了危机因而害怕。
而在桑菲尔德庄园的生活应该是她们共同的经历,她们之间的镜像关系表现得尤为明显。我们可以说,安托瓦内特的每一次出现都是简内心的呼唤。她为了简而来,为了简而存在。无论是她撕了简·爱的婚纱,还是出现在婚礼现场,甚至最终将罗切斯特烧得双目失明,无不是简·爱的意图。简不喜欢那些“幽灵似的奇装异服”伯莎为她撕毁;简内心抗拒这个有着强烈等级观念、对自己不能够平等相视的丈夫,并且希望能和他公平较量,梅森以及高大的伯莎出现,阻碍了婚礼;简梦到桑菲尔德庄园变成一处废墟,自语道“你得剜出你的右眼;砍下你的右手”[12]。这些都通过伯莎最后点燃的一场大火实现了,罗切斯特双目失明。从这些情节来看,安托瓦内特既是简·爱行动的代理人,同时也是她愿望的代理人。换句话说,她正是简·爱内心黑暗阴冷和真实一面的化身。每当简·爱极度愤怒,想要发泄心中的怒火时,安托瓦内特就作为她愿望与行动的代言人,将简·爱从盖茨黑德到桑菲尔德的日子里所受到的折磨与不公,全部发泄了出来。直到安托瓦内特火烧庄园,简·爱能够真正与罗切斯特平起平坐,终于有了身份的认同。
(二)梦的预言性
拉康提出的镜像理论是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中面对后者所主张的心理发生和人格历史建构逻辑所做提出的颠覆性观点[13]。按照弗洛伊德的观点,人的本我只有在睡眠或其他朦胧状态时,才能释放出来。无论是《藻海无边》还是《简·爱》,都对两位女主人公的梦进行了特别描写,似乎它们都有一定的预言性,且彼此相关联。
在《藻海无边》中,安托瓦内特的三次梦境很有意义。第一回梦到深夜在森林里走,有个恨她的人跟着,尽管安托瓦内特挣扎喊叫,却都动弹不了。第二回便梦到那个男人将她带到一座石墙围住的花园里,顺着梯级一直往顶上走。第三回伴随着梦的结束,她的生命也就结束了。而这一梦正与简·爱三回梦境相对应。简·爱在梦中不停地梦到一个孩子,深夜抱着孩子向前走着,总是在追赶着她的丈夫罗切斯特,希望他能够停下来,却总是被什么东西束缚着。安托瓦内特梦中的男人正是她的丈夫罗切斯特,每一次梦境的出现,都推进了故事情节的发展,并且就是现实生活中的缩影。而简·爱的第二回梦是她在一片废墟上走着,一方面映衬了她后来做的有关桑菲尔德庄园变成一片废墟的梦,同时也与安托瓦内特的第三回梦境有关,用蜡烛点燃了桑菲尔德庄园。而那个孩子从简·爱身上掉了下去,也就意味着安托瓦内特从一片火海的庄园上跳下去,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从这些方面看出了简·爱自我内部分裂的过程:简·爱和简·罗切斯特的分裂、孩提时代的简和成年之后简的分裂、简的映像与简身体怪诞的分裂[14]。
(三)身份意识的最终确立
安托瓦内特的死同样是伴随着简·爱的“预感”而来,“我挣脱了圣·约翰······该轮到我处于支配地位了。我的力量在起作用,在发挥威力了”[12]。简·爱想要冲破阻碍,想要在这么多年的生活中真正发挥出一次自己的力量,而不是由别人指挥,由别人命名。她的这种呐喊不仅表现了自我的释放,同时更是唤醒已经疯了的安托瓦内特,告诉她应该做出一些行动来捍卫自己的权利,来保住自己的身份与存在。同时,她也在警告罗切斯特,不要总是恶意诋毁安托瓦内特——他的疯妻子。而安托瓦内特似乎也听到了简·爱的呐喊,她从阁楼上走出来,拿着已经燃起的蜡烛,点燃了这里。此时,安托瓦内特看到了一切,回想起这一路寻找身份认同的路途,母亲养的鹦鹉、她所恨的男人叫着她“伯莎!”;还有那个肖像画里的英国姑娘,以及她的朋友蒂娜。只是这一次,她们不再两眼相瞪,不再头破血流。而是招招手,哈哈大笑起来。蒂娜的笑,也意味着安托瓦内特的笑,最终,她向蒂娜身边的池塘跳了过去。一场大火烧毁了这里的一切,成为了一片废墟,罗切斯特也双目失明。但是,安托瓦内特却真正地从丈夫手中抢回了本属于自己的权利,建立起了自己的身份。
四、作者与安托瓦内特的镜像关系
身份的建构与每一社会中的权力运作密切相关[15]。简·里斯作为一名地道的白种克里奥尔人,她一生路途艰辛,经历家道衰落,婚姻破裂,疾病折磨,战时艰辛,贫穷孤独。不仅如此,她还被男人沦为玩物,时常衣食无着,绝望许久,甚至有过精神崩溃。这一切都使她成了克里奥尔女性的代言人,为她们立言立声。从《藻海无边》到《简·爱》,安托瓦内特的故事无不渗透着简·里斯的影子,两人在互相讲述对方的故事,也正是因为对于这一身份特殊性的了解,对当时时代背景的了解,简·里斯才能创作出伟大的作品。童年的里斯就见证了种植园经济的衰败,目睹了种族冲突引来的巨大变化。因此,她更有可能创作出专属于那个时代的作品。“我确信夏洛特·勃朗特肯定有某种反西印度的东西,我为此而感到愤怒。要不然,为何她把一个西印度人写成一个可怕的疯子,那个实在令人感到恐惧的生物?”[16]作为一名白种克里奥尔人,简·里斯希望能够真正写出一部属于女性文学的代表作,不仅仅白人女性有地位,处于世界边缘的第三世界的女性一样可以发出自己的声音。为此,简·里斯通过后殖民话语,抵抗父权制社会的权威,使第三世界女性拥有自己的话语权,从世界的边缘走向世界的中心。
五、结语
斯皮瓦克认为“身份认同的危机事实上更尖锐地体现在第三世界妇女群体上”[17]。许多英国女作家创作的作品,可能或多或少地都体现了女权主义意识,但都是站在英帝国主义白人体系下的角度,向世界发出的质问,挑战父权社会、男权社会的权威。作为处在世界边缘的没有身份归属的克里奥尔人,却从没有包含在里面。安托瓦内特从对身份的归属产生困惑,到身份意识的丢失、破碎,再到真正建立身份的认同感,这一过程艰难而曲折,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简·爱》虽说是女权主义理论的代表之作,却依然将第三世界女性和黑人女性排斥在外。她们依旧处于树枝的末端,不仅仅受到男性的驱使,同时也受到纯正白人女性的鄙夷。
安托瓦内特由于身份的特殊性,一直受到牙买加当地黑人的仇视与白人小姐、太太的鄙夷,被他们排斥在社会整体之外,找不到身份的归属。为了找到自我身份的认同,她先后从牙买加黑人同伴蒂娜与英国白人丈夫罗切斯特的身上找寻归属感,但都以失败告终。被幽禁在大英帝国桑菲尔德庄园的阁楼上的日子里,安托瓦内特回想起了一切,并且最终找到了自我的出路。《藻海无边》作为《简·爱》的前篇,对她进行了重写,以殖民地人物的身份重新叙述了疯女人的故事,给予她话语权,给予她建构自我身份的权利,颠覆了夏洛特·勃朗特对于女权主义创作的意图。从身份意识的破碎到重建,安托瓦内特通过镜像不断从他人身上找寻自己的身份归属,并最终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了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