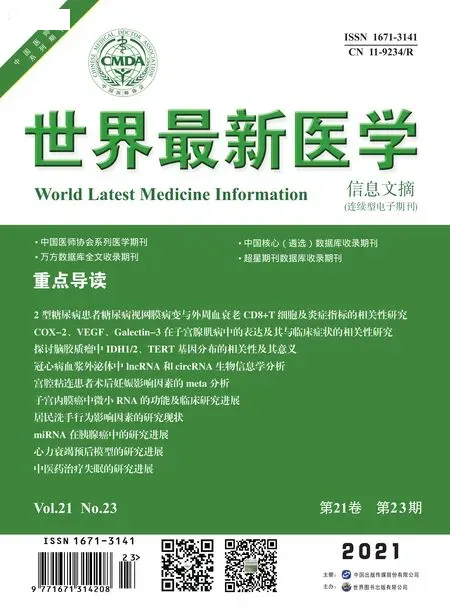具有自身免疫特征的间质性肺炎(IPAF)的研究进展
刘磊,高俊珍
(1.内蒙古医科大学,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30;2.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30)
1 流行病学
早在上世纪90 年代,就有报道提出多达25%的自身免疫性疾病患者不符合美国风湿病学会(ACR)的CTD 分类标准[2]。近些年,根据IPAF 的标准来报道的间质性肺疾病的报道较少,有N.O 等人报道IPAF 在间质性肺炎中的发生频率从7.3%-34% 不等[3]。人口统计学方面,IPAF 患者大多为非吸烟的女性,平均年龄为60-65 岁[4-5],这些特征不同于CTD-ILD 患者的临床特征,在CTD-ILD 中,主要以年轻女性集中,而在IPF 中,以老年吸烟男性为主。
2 临床特征及诊断
根据2015 年ATS/ERS 对IPAF 的审查标准,诊断IPAF前需要满足三个先验证条件:(1)首先必须通过HRCT 或外科肺活检获得诊断ILD 的依据;(2)经过临床评估后必须排除已知的ILD 的病因;(3)无法定义为CTD。在满足以上三个先验条件的基础上要具备以下三个领域的至少两个领域的特征,分别是临床领域、血清学领域和形态学领域。
2.1 临床领域
临床领域由CTD 的某种胸外特征组成,但并不能诊断出某种特定的CTD。特征包括技工手,指端溃疡,关节炎或多关节晨僵持续超过60 分钟,手掌毛细血管扩张,雷诺现象,无法解释的水肿和指伸肌表面固定皮疹。在几个已经发表的研究队列中,符合临床领域标准的患者患病率较高[4-5],并且有研究表明最常见的临床体征是雷诺现象(28%-39%),其次为技工手(4%-29%),关节炎及晨僵(16%-23%)和Gottron征(5%-18%)[6]。
2.2 血清学领域
该领域由与CTD 相关的自身抗体组成,并且排除了非特异性的炎症标志物,例如红细胞沉降率或C 反应蛋白。但对于特异性比较低的抗体,例如抗核抗体(ANA)和类风湿因子(RF),这类因子在正常人体内或IPF 体内均有低滴度的表达,所以需要足够高的滴度才能满足血清学的标准。在血清学领域,ANA 滴度>1:320(无论是弥漫型、斑点型、均质型或核仁型)都是最常见的(17.77%-77.6%),其次是SSA(16.6%)和RF ≥正常值2 倍上限(13%)[6-7]。
2.3 形态学领域
该领域包含三个子域:HRCT 的影像学表现,手术肺活检病理学诊断及多室特征。满足以上三个子域中的任何一种特征即达到形态学领域诊断标准。
IPAF 在HRCT 上的表现主要包括:非特异性间质性肺炎(NSIP),组织型肺炎(OP),OP 与NSIP 重叠和淋巴细胞性间质性肺炎(LIP)。IPAF 中最常见的HRCT 模式为NSIP[6],但也有部分研究显示最常见的模式为普通型间质性肺炎(UIP)[8],UIP 为类风湿关节炎(RA)相关ILD 最常见的影像学特点,在其他CTD 相关ILD 中也会出现类似改变,因此UIP 模式较其他IIP 模式特异性较低,在临床中,如果出现NSIP、OP 或LIP 等改变时,特别是NISP,应着重排查自身免疫相关ILD 的可能。
肺活检组织病理学是第二个子域,该子域也包含有NSIP,OP,伴有OP 的NSIP 和LIP,虽然命名相同,但是肺活检病理学与HRCT 的影像学模式无相关性[9],这也为指南里将二者区别开来提供了证据。我们应该注意,在Kais Ahmad等人的研究中发现在IPAF 中的UIP 模式都是“不明确”的UIP,并且包含弥漫性淋巴浆细胞浸润、间质淋巴聚集这些形态学域的次要特征[10],因此目前大多的观点认为肺活检中的UIP 模式并没有形态学模式的加分,因为它缺乏与CTD 之间的关联性,但是有研究表明,尽管UIP 不是IPAF 的形态学标准,但是在那些重新归类为IPAF 的组织学病理中发现UIP模式会与NSIP 或OP 模式共存。这可能提示我们不能完全否定UIP 的诊断价值,在面对UIP 病理模式时,应该全面评估IPAF 的可能[11]。
形态学域的最后一个子域为多室特征,包括无法解释的气道、肺血管、心包积液或胸腔积液,但当前关于此方面的研究较少。因此多室子域的识别及定义由临床医生自行决定。
OLD 等人的研究中报告,结合以上三个领域的组合来进行诊断IPAF 中,通过血清学和形态学领域的患者比例最高(50.7%),其次为通过全部三个领域的患者(26.4%),最后为通过临床和血清学领域(14.6%)以及临床和形态学领域(8.3%)的患者[7]。
3 发病机制
目前IPAF 的发病机制尚不明确,目前对于ILD 的发病机制一些基因多态性是已知的。IPF 患者的基因改变发生在表面活性物质相关蛋白C(SFTPC),表面活性物质相关蛋白A2(SFTPA2),P53,人黏蛋白5B(MUC5B)以及与端粒相关的基因[12]。而Newton 等人的研究表明IPAF 和CTD-ILD 患者的端粒长度长于IPF 患者,并且MUC5B 的多态性在IPAF患者中比IPF 中更为常见[13]这为IPAF 的发病机制提供了新的认识,也为与IPF 做相关鉴别提供了依据。
4 治疗及预后
目前由于缺乏IPAF 患者的临床试验,对于其管理仍要以CTD-ILD 和IIP 的临床试验为基础,主要还是激素、免疫抑制剂及抗纤维化药物。对于CTD-ILD,长期以来以糖皮质激素以及免疫抑制剂为基石的方案一直起到支柱性作用。但是有研究显示使用激素联合免疫抑制剂并没有降低IPAF 的死亡风险比[14],而李英等人的研究则表明,IPAF 的患者在接受免疫抑制剂治疗后的FVC 和DLCO 得到了明显改善。近年来,两种新型的抗纤维化药物(吡非尼酮和尼达尼布)越来越多地用于IPF 乃至CTD-ILD 的患者中,特别是尼达尼布,在治疗SSC-ILD 方面展示了更好的预后。但是在IPAF 的研究中,抗纤维化药物没有展示出任何有益的作用[15]。因此就目前来讲,对IPAF 的患者治疗决策必须基于对个体受试者获益为目标,对风险仔细评估,并且如果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进行多学科探讨。尽管在目前医疗背景下IPAF 的药物有限,但是也有人提出是否可以将免疫抑制剂联合抗纤维化药物可能会起到更佳的效果[16],将来需要继续更多的临床研究来探索。
对于IPAF 患者的预后,OLD 等人队列研究中的生存分析表明,归类为IPAF 的患者的生存期要短于CTD-ILD,但其结局相比于IPF 的患者要好的多[7],然而比较有趣的一点是,伊藤等人的队列显示98 名IPAF 的患者中有12 名最终发展为CTD[17],近年来,临床前性CTD 已经逐渐被临床医生认识到[18],这提示我们IPAF 可能会作为一种临床前性CTD 疾病被对待,并密切监测转变为CTD 的可能,并开始早期治疗。
5 总结及展望
IPAF 观念的提出是为ILD 提供统一分类标准的一个较为重要的跨越,它为学者们在ILD 与CTD-ILD 的临床研究之间提供了一个新的平台,IPAF 可能只是一个暂时的疾病状态,它可能会继续发展,也可能会原地停留,但是目前仍然存留较多的问题及争论,例如其诊断分类标准并不完善,特别是形态学领域,将UIP 模式排除在外一直是学者们争论的地方,种种问题还需要我们今后更多的临床研究去统一标准,总之IPAF 将ILD 带入了一个新的模式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