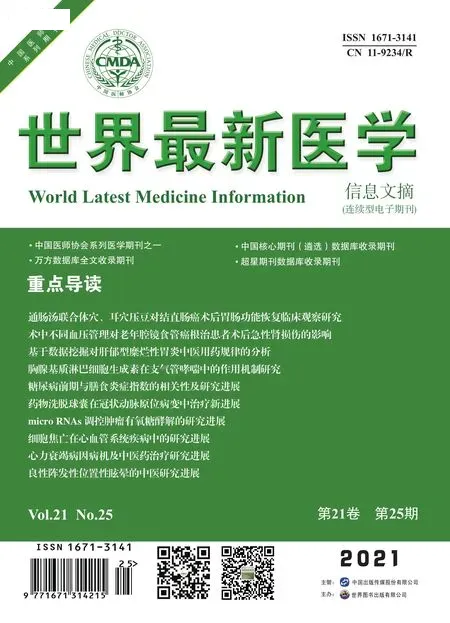对协和医院崔丽英所报大宗“肌萎缩侧索硬化”的鉴别
——肌型脚气病并发干性脚气病、脑桥中央髓鞘溶解症及SCD
王志湖,张海鹏,2(通信作者**),姜龙,李明亮,郝固磊,谷云飞,张文煜,张青松
(1.涿鹿县医院神经外科ICU,河北 张家口075600;2.涿鹿县医院放射医学与应用物理研究所,河北 张家口075600; 3.河北省涿鹿县妇幼保健院,河北 张家口075600;4.河北省涿鹿县中医院外科,河北 张家口075600; 5.解放军总医院第七医学中心(原北京军区总医院)神经外科护理部,北京100700)
0 引言
肌萎缩侧索硬化(ALS)在亚洲属罕少见疾病,但又是成人运动神经元病最常见的类型。我们在文献[1]中指出文献“亚急性联合变性”病例可能漏诊的ALS及原发性侧索硬化;然而,ALS的过度诊断性误诊或更为严重。兹结合北京协和医院的“ALS”病例予以分析。
1 关于“ALS综合征[2]”诊断——兼与管宇宙、刘明生两博士商榷
北京协和医院神经内科教研室主任、中华医学会神经病学分会肌电图和临床神经电生理学组“名誉组长”、ALS的“破冰人”崔丽英报告了2例浸润型胸腺瘤手术中急性发作的“副肿瘤综合征”——“ALS综合征[2]”。经我们重新分析,其中管宇宙博士[3]报告的1例的主要诊断应该是麻醉并发的脊髓前动脉综合征[4],遂与管博士商榷;但崔丽英[4]主动答复我们,其称该患者没有血管病基础;然而:(1)该女性患者尽管非高龄(48岁),但更年期后高脂血症风险无疑加大,仅以原作者提供的有限资料,并不能除外已有血管病的基础;(2)第4胸髓(T4)由于脊髓血管纵向发布的特殊性而更易缺血,是为胸髓型脊髓前动脉征发病的解剖学基础——我们在文献[4]中的这个表述被该刊“编辑”篡改……大部分参考文献被删除;(3)已知手术麻醉应激可诱发心梗以及脑梗;(4)事实上,肋间肌反射有助于鉴别诊断[5],但崔丽英等未检查之;其随访结果[2,3,4]亦未提供上运动神经元受累的明确证据如锥体束征。由于该例四肢的肌电图示广泛神经源性损害,我们考虑其为副肿瘤性的脊髓性肌萎缩(SMA)。该例所谓“貌似运动神经元病”的病例不过是继发性运动神经元病;但是,由于其四肢无肌萎缩症状、体征,此神经系统副肿瘤综合征不过是亚临床性的;而我们提出的作为主要诊断的脊髓前动脉(闭塞)综合征不仅可以解释其胸髓肌的肌电图表现,更且可以解释其“主诉”的呼吸肌无力……此2例所谓“ALS综合征”客观上从反面说明:肌电图的广泛神经源性损害,不是诊断ALS的充分条件。
据崔丽英在答复我们中介绍“此患者在术后4个月呼吸机辅助呼吸,26个月时患者仍存活,气管切开仍保留[4]”……而另1例术中发病的“ALS综合征”则“失访[2]”。
崔丽英还介绍“10例患者中4例符合经典的肌萎缩侧索硬化症。另外6例临床上以下运动神经元受累为主,是否为上运动神经元受累的体征被下运动神经元体征掩盖,难以定论。其中3例合并感觉神经受累,与经典的MND(注:运动神经元病)明显不同[2]”。兹分析如下:
关于其“另外6例临床上以下运动神经元受累为主,是否为上运动神经元受累的体征被下运动神经元体征掩盖,难以定论[2]”,我们认为:(1)该6例“ALS综合征”如果随访中仍无锥体束征(1999-2002年首诊,随访至2003年6月[2],再到答复我们时的2009年[4]。崔丽英答复[4]时并未述及发现上运动神经元损伤证据),则属于我们前述的获得性(非遗传性)SMA(6例去除2例脊髓前动脉征与亚临床性SMA则为4例);而SMA国内文献仅50篇(未检索PubMed等国外文献),其中成人型SMA已属罕见,而该4例成人获得性SMA可能是国内首组(例)病例……比ALS报告的意义更大;(2)尽管下运动神经元病变可掩盖上运动神经元疾病导致的腱反射亢进,但众所周知:除非由下运动神经元及其以远因素导致的肌力为0级(这时相关腱反射亦消失),则难以掩盖上运动神经元及其下行传导束病变导致的锥体束病理征;而具体到ALS,正是主要由锥体束征推测其上运动神经元及侧索病变的存在。本文的鸣谢作者陈萌医生报告的1例脑桥中央髓鞘溶解症(CPM)之证据包括双侧巴氏征阳性与MRI显示CPM典型的脑桥基底蝙蝠翼样图像[6],但崔丽英以该刊总编辑(注:陈医生该稿发表前的终审者)的名义提出该例不是CPM[7];而另一例36岁孕妇锥体束征阴性却被崔丽英仅根据CT图像即诊断为“CPM”并报告于众(我们发现、论证了该孕妇系因脚气性心脏病去世[8])[8,9]。孔夫子曾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意为“此”)知也”。我院虽然著述了较多的“疑难病例”商榷文,但我们个人认为,写商榷文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仅需要较广的知识,而且需要物理学大师杨振宁先生所说的一定的洞察力。就腱反射而言,尽管我院在2010年从协和医院漏诊发现的很可能国内首例的非创伤性肺/脑脂肪栓塞文献[10]中已经独立[8]提出单纯后索病变并不导致腱反射减弱或消失,但直到我们检索了大量的国内和国外亚急性联合变性病例文献并去伪存真地分析后,才在2018年[5]慎重地作为结论提出,从而纠正了诸《神经病学》教科书(包括八年制)很可能错误的观点。就我院发现的国内外新疾病——肾性血小板减少症,最早正是2012年从国际最顶尖的哈佛大学麻省总医院的专家误诊为“血栓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的个案中收到启发,但直到2019我们较系统地例证后才慎重得出“疑似”肾性血小板减少症较常见的结论[11]……
关于崔丽英提出的“其中3例合并感觉神经受累,与经典的MND(注:运动神经元病)明显不同[2]”,我们认为:(1)众所周知,MND包括但绝不限于ALS,其还包括原发性侧索硬化[1]等等;也未检索到文献[2]之前崔丽英报告过非ALS的MND;(2)早在2001年,Graus等即已发现:高达54%的抗Hu抗体阳性神经系统副肿瘤综合征表现为感觉性周围神经病[12],而崔丽英提到“检测Hu抗体的4例患者已有1例呈阳性[2]”,因此我们认为这3例合并感觉神经受累的病例——如以副肿瘤性感觉神经病解释符合诊断的一元化原则;然而,维生素B1缺乏性周围神经病(干性脚气病)毕竟比神经系统的副肿瘤综合征更为常见,而肿瘤是脚气病的典型病因之一[8,13],因此我们认为该3例“ALS综合征”并存周围神经性(干性)脚气病的可能性更大,此同样是一元化诊断;而干性脚气病可视为代谢性副肿瘤综合征;(3)然而,更重要的是,此3例非“经典的”的“ALS综合征”应该首先排除CPM并发干性脚气病(后详述)!排除原发性亚急性联合变性(SCD)或文献[14]报告的副肿瘤性SCD!SCD(或脚气病)可以一元化解释其运动、感觉症状;而崔丽英在文[2]中只字未提SCD或CPM等。我们在著述文献[4]时已经发现了崔丽英文献[2,3]的3篇文章,基于此,我们于2009年、2016年两次呼吁ALS应注意与SCD鉴别诊断(但并未引用、展示崔丽英的两个文献)[8,15]。SCD(及脚气病)是神经内科为数并不很多的可治性疾病之一,即使对不排除SCD者,首先予以治疗性诊断。我们另外发现2例可能被协和医院误诊为感觉神经元病的SCD(崔丽英是其中1例的神经科首诊医生。该患者去世)[16]。
需注意的是,国外及国内少数ALS作为神经系统副肿瘤综合征的存在,客观上提示部分ALS不排除病毒等隐性感染后自身免疫性炎症,文献[17]报告ALS合并干燥综合征4例客观上也提示这一点,诚如此,则ALS有丙种球蛋白、糖皮质激素的应用指征,然而此二药的常规剂量疗效并不显著[17],而如以较大剂量地塞米松短期冲击3天(并预防其副作用[18])然后以常规剂量的强的松维持或/和血浆置换的效果如何尚不知晓。而系统地筛选自身抗体、肿瘤抗原、脑血管星形胶质细胞受体、神经元的受体和抗原、脑脊液的抗体浓度、白细胞、小胶质细胞等有助于明确ALS发病的分子细节与共同通路;我们提出ALS可能与多种原因导致的运动神经元甲状腺素受体表达减少有关[19]。
2 关于“ALS伴颈椎病”诊断——再论ALS,SCD之鉴别
与3例并存感觉神经受累的“ALS综合征”[2]不同的是,崔丽英报告的“ALS伴颈椎病[3]”病例有详细的临床资料(尽管随访资料缺如),其述及:(1)“右下肢SEP(注:体感诱发电位)显示胸12以上中枢性损害,提示脊髓双侧后索受累可能性大[3]”,“双侧L1以下音叉觉减退[3]”(2)“SCD:患者有胃大部切除史,临床表现为双侧锥体束征、后索病变以及下运动神经元病变,应与维生素B12缺乏引起的SCD所导致的后侧索病变以及周围神经受累鉴别。但是患者胃大部切除史已经24年,无偏食,血常规、叶酸和维生素B12正常;进行性病程和真性球麻痹不支持诊断[3]”……(3)“该患者诊断为ALS合并为颈椎病[3]”。对此,我们分析如下:
2.1 关于该例“真性球麻痹”的病因
对SCD诊断而言,该例唯一不典型的临床表现就是“真性球麻痹”,然而,约半数SCD患者累及周围神经,而脑神经/颅神经除嗅神经、视神经外均为周围神经。已知维生素B1缺乏性周围神经病可累及迷走神经而表现为无心绞痛的冠心病而猝死率很高(我们提出检查耳廓浅感觉有助于及早发现迷走神经损害)[20],而对SCD而言,延髓(球)神经等周围性颅神经受累在理论上完全可能,文献[21]报告的35例SCD中2例脑干听觉诱发电位异常,文献[22]报告的31例SCD中2例周围性听力障碍,文献[23]报告的31例SCD中“颅神经损害:2例出现视力改变,1例听力下降”,而天津医大总医院、白求恩医大2所附院联合报告的27例SCD中“脑神经受累者2例, 其中1例出现视物模糊,1例出现双眼外展受限伴眼震、复视, 这两例患者头部MRI均正常[24]”,外展神经是运动神经,而舌咽神经则包括疑核发出的躯体运动纤维。因此SCD累及舌咽神经是完全可能的。
2.2 关于崔丽英文献[3]该例血维生素B12正常问题
早在1993年,Reynolds等[25]即已提出血VB12降低对SCD诊断敏感度不高,进而推荐敏感度更高的红细胞内VB12检测,我院则提出后者结果正常同样不能排除神经细胞缺乏VB12(造血系统可与神经系竞争血VB12)[15];而在2004年河北医大附属三院王冰教授[26]报告了血VB12未降低的SCD病例,2016年,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获得者、现中华医学会神经病学分会名誉主任委员贾建平教授的团队[27]亦认为血VB12正常不能排除SCD。同理,我们认为协和医院魏妍平教授等的文献[28]病例同样不排除SCD。需注意的是,SCD可急性发作[15];此外,SCD的侧索病变尚可累及侧索中的脊髓丘脑束而表现为传导束型感觉障碍[29],后者应与周围神经及感觉神经元病[16]的浅感觉障碍鉴别。
2.3 关于崔丽英文献[3]病例的诊断
“患者有胃大部切除史,临床表现为双侧锥体束征、后索病变以及下运动神经元病变[3]”——完全可以说其脊髓SCD表现典型,同时其颈椎病明确,因此以常见的SCD与颈椎病完全可以解释其全部临床表现,恐怕不涉及“ALS[3]”。早在1993年,富有真才实学的中华医学会神经病学分会前主任委员、著名女神经内科学家、北大一院陈清棠教授就提出颈椎病与ALS的临床表现极其相似[30]!这两种没有关联的疾病同时发生的可能性——即使在理论上也是极小的。事实上,崔丽英文献[3]的ALS和颈椎病难以解释该例的后索病变,该例是《<协和医生临床思维例释>[3]之例释》十几例(涉及该院内科的各个专科及普外科的病例)[31]之后的又一“例释”;然而,崔丽英将该例“ALS伴颈椎病[3]”作为“结论”写进其 “中国肌萎缩侧索硬化诊断和治疗指南(2012版)”(“金标准”)中:“颈椎病、腰椎病等可与ALS合并存在[32]”——此势必导致ALS过度诊断的进一步扩大化。
济南军区总医院报告1例颈椎病合并“以呼吸肌麻痹为主要表现的成人型SMA[33]”个案,经我们重新分析发现该例急性运动轴索性神经病的可能性更大,依据如下:(1)该例严重的呼吸困难是突发性的,不符合成人型SMA的慢性、轻度表现,况且该型SMA累及呼吸肌本来就很少;(2)其“双手及双下肢肌肉萎缩3年,近3个月明显加重, 行走困难[33]”以颈椎病完全可以解释;(3)腓肠神经活检见“部分轴索空泡样变性, 无明显雪旺细胞增生[33]”;(4)脑脊液“细胞数正常, 蛋白0.9g/L[33]”;(5)没有前驱感染史并不能排除吉兰-巴雷征(GBS);(6)该患者68岁;(7)无SMA家族史。须指出的是,(1)该例存在较重的代谢性酸中毒;(2)其心律失常提示GBS可能累及迷走神经,后者属危重型;(3)患者经机械呼吸支持后四肢肌力提高得非常显著(亦不支持SMA),说明了缺氧对运动神经元功能的影响很大(后详述);(4)成人型(即4型)SMA应与肌型脚气病[1,8]鉴别,可行基因检测。
而“ALS伴颈椎病[3]”使用的单纤维肌电图除对神经肌肉接头病有辅助诊断作用外[34],其它作用甚小,甚至增加患者的经济负担。汤晓芙、许贤豪两位学者早在1995年之前就已将其引入国内进行了开拓性研究。
3 关于“ALS合并额颞叶变性”诊断——兼与崔博、高晶两位教授等商榷
崔丽英[35]报告了8例“ALS合并额颞叶变性”,8例均显示颈髓肌电图异常,7例显示胸髓肌电图异常,6例存在颈髓下运动神经元受累证据。由于颈髓涉及支配膈肌的膈神经,胸髓则支配肋间肌肉,我们推测,这些“额颞叶变性”者的呼吸肌至少完全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受累,其意识、精神异常及颅脑影像不限于额颞叶亦佐证了这一点。然而作者并未与缺氧(包括隐性缺氧)所致认知障碍鉴别(而后者属于一元化诊断),亦未提供血氧饱和度以及血气分析证据。
该文引用了Science杂志的文献观点“散发型ALS和非SOD1突变的家族型ALS主要病理沉积蛋白为TAR DNA结合蛋白(TDP-43),而FTLD(注:额颞叶变性)病理沉积蛋白亦可为TDP-43蛋白、tau蛋白或FUS蛋白,共同的病理基础为两组疾病叠加提供了依据[35]”,然而,该组接受基因检测的4例患者TDP-43的基因并未见异常(且至少7例患者无家族史),因此该组ALS合并“额颞叶变性”[35]至少不是一元化诊断;而与额颞叶变性关系较密切的Tau基因则未检测;该文提出“本组例5为国内首例C9ORF72基因阳性ALS-FTLD患者[35]”,该例患者可确诊为FTLD,但其认知障碍并不排除前述缺氧的一定的作用,而早在2009年,内蒙古1例缺氧性脑病的MRI即以额颞叶明显萎缩为主要表现[53];由于成人大脑质量仅占体质量的40分之一而耗氧量高达全身的4分之一以上,因此大脑皮质对缺氧最为敏感。须指出的是,呼吸肌麻痹是ALS死亡的主要原因,而呼吸肌上下运动神经元受累后,即与缺氧形成恶性循环,ALS病程则加速进展。因此,及早通过无创的血氧饱和度发现缺氧并予麻黄碱加尼莫地平或氨茶碱加特布他林干预(必要时加低流量吸氧)十分重要[19],而及早预防缺氧则可能有效地延缓ALS[19]。
而ALS尚可因吞咽障碍导致维生素B1摄入减少而发生脑型脚气病(Wernicke脑病)[1,20],后者眼部症状可缺如[1],其共济失调亦可被ALS掩盖;“额颞叶变性”应与该病鉴别。
受文献[35]启发,2018年,我们让一例有精神症状的时年62岁的女性患者(电工,最晚于2012年即成天幻想“达到国际顶尖水平”,2018年11月因公然对外宣称而表现为缺乏自制力而被送诊)到北大医学遗传学系教授赵红珊领导的实验室做基因检测,结果发现该患者C9ORF72基因阳性,因此我们认为其可能属额颞叶痴呆之早期,也不除外Pick病。
崔丽英的该文献[35]尽管详细地罗列了上、下运动神经元受累的表现,但其中肌电图所见引用(自引)文献[36]为其依据,基于此,我们认为该组8例“ALS[35]”可信度不一定高。此外,大多数额颞叶痴呆是散发性的,且发病率较高,因此其诊断不能依赖基因检测;早在2011年,商秀丽课题组[37]即已报告了其合并ALS的病例,该文提供了很多“干货”。
4 关于崔丽英报告的(21+192)例“ALS”诊断及其蹊跷的“结论”
崔丽英文献[36]报告了首诊肌电图不表现为广泛神经源性损害的“ALS”病例——高达21例!其还写到“我们对数据库中的所有患者进行整体分析时,并未发现病程与肌电图广泛神经源性损害之间的关系。这里可能存在多种因素的影响:首先,有些患者病程已经很长,但肌电图仍表现1个或2个区域的受累;而有些患者,病程尽管很短,甚至临床刚刚发病,但肌电图上已经表现为广泛神经源性损害,这可能是由于不同患者病情发展速度确实存在很大差异所致,这应该是影响肌电图改变和病程相关性的关键因素[36]”。
众所周知,(1)尽管肌电图示广泛神经源性损害并非ALS的充分条件,却是ALS诊断必不可少的!这仅仅是ALS诊断的常识和肌电图学的常识。而对肌电图不表现为广泛神经源性损害者,则首先考虑肌肉原发性病变(肌源性肌萎缩);(2)神经电生理检查暨肌电图属功能诊断,其敏感性极高,如糖尿病并发周围神经病尚无明显症状时,感觉神经电生理即可显示阳性[20];而ALS尚无明显肌萎缩、无力时,肌电图即可出现显著阳性,因此ALS因肌萎缩、无力而就诊时肌电图不表现为广泛神经源性损害[36]——其可能性几乎可以完全排除(而没有症状则不会到医院尤其大型医院[38]就诊);而“有些患者(注:ALS患者)病程已经很长[36]”而肌电图仍无广泛神经源性损害——其则可能性更小;而高达21例这样的“ALS”愈加难以置信。此外,为什么SMA肌电图没有这种现象?该院文献[2]的“ALS综合征”病例四肢尚无萎缩、无力——其四肢肌的肌电图已经表现为广泛神经源性损害。
崔丽英提到的“有些患者病程已经很长,但肌电图仍表现1个或2个区域的受累[36]”,其肌电图最后终于表现为“广泛神经源性损害”了[36](肌电图表现1个或2个区域的受累也进入“拟诊ALS[32]”或“可能ALS[32]”诊断“指南[32]”)。然而,这21例无疑并非ALS的典型肌电图表现;而如果以我们(2018)“报告”的肌型脚气病[1]并发干性脚气病[8,20](此也属于一元化诊断)则可以解释其整个肌电图表现:初期以肌肉病变为主,神经源性损害相对较轻,后期则神经病变显著。尽管仅以崔丽英提供的有限资料尚不能确定之,尽管在PubMed等国内外文献未检索到肌型脚气病报告,但张洪林学者早在1993年在《神经病学(第二版)》本科教科书中已经明确提出之[8];而且肌型脚气病未必罕见(21例当然完全有可能),其“罕见”更可能是因为临床中的误、漏诊[1]。至于干性脚气病,易忽视的是其急性型,1999年,包头医学院一附院神经科杨巧莲学者报告1例急性干性脚气病(“肌电图为神经源性损害[39]”)合并脚气性心脏病的较疑难病例[39](我们认为其疑难病诊治确实达到国际顶尖水平);2019年,新加坡学者[40]呼吁警惕干性脚气病所致的急性软瘫(“Do not forget beriberi neuropathy![40]”);而后者还可以累及舌咽神经等延髓神经[20,40]与视神经[1],因此上述21例“ALS”中的“延髓部起病者4例[36]”同样应与干性脚气病鉴别,而后者尚可并发CPM(脑桥中央型脚气病)[8]!而如果这些“ALS”存在锥体束病理征或三重刺激[5]阳性,则CPM是其应首先考虑的解释;2020年,已掌握脚气性心脏病[41]的日本学者则坦陈医学发达的日本对B族维生素(包括B1、B12)缺乏的研究很少[41]。
“ALS诊治中心[36]”崔丽英报告的另外的超大宗的192例“ALS[36]”均未排除干性脚气病并发CPM[49],而干性脚气病在早期即可能表现出“广泛神经源性损害[36]”;ALS在黄种人毕竟属罕少见疾病,其患病率恐怕没有想象中那么高[8]。
而相对于令人绝望的ALS,脚气病(包括其混合性、复合型或重叠型)更加常见且对维生素B1及补镁有良好反应[8]……因此药物诊断十分重要!部分CPM疗效欠佳可能与未同时补镁有关,而诊治延误半年以上者疗效也相对差。须指出的是,CPM一般在其发病10天后才在MRI上有阳性、特征性体现[50]。这无疑是其容易误漏诊的重要因素之一。
崔丽英报告的以“呼吸困难起病者1例[36]”“肌电图仍表现1个或2个区域的受累[36]”者尚应注意与前述的GBS尤其轴索性GBS鉴别,轴索性GBS早期即可出现肌萎缩[42],贾建平课题组报告的9例患者中5例有肌萎缩[43],该病尚可亚急性[43]或慢性发病,因此肌电图可能表现为广泛性或非广泛性神经源性损害。
5 关于崔丽英文献[51]的68例“ALS”
(1)关于崔丽英所述的“86例ALS患者中,9例(10%)随访自然病程在5年以上,均为下肢起病,平均起病年龄(45±15)岁,年龄范围20~60岁[51]”,我们认为:(1)20~40岁的散发性“ALS”并不典型,其尤应与前述脚气病及平山病鉴别;(2) “下肢起病的39例ALS患者,随后有32例(86%)出现上肢症状[51]”,此与上下肢同时发病的“ALS[51]”——客观上均与干性脚气病的特征较符合,而随着VB1缺乏的加重则可并发CPM而出现“上运动神经元”损伤征;(3)这种脚气病(混合型)比ALS进展慢,因此其存活时间在5年以上是正常的;脚气病的生存时间其实与是否进展为致死性的脚气性心脏病(后者系VB1重度缺乏所致,易误漏诊)关系很大[8,13]。
关于崔丽英所述的“11例(注:ALS)合并2型糖尿病[51]”,我们认为此11例系干性脚气病并发CPM的可能性相当之大——因为糖尿病是脚气病的典型病因[8,13]!此外,ALS尚应与糖尿病后侧索硬化[5]鉴别。
而崔丽英对上述86例患者“每6个月进行一次随访[51]”——则无疑不利于早期发现、干预(药物和吸氧)与预防缺氧(前已述及)。
6 上述所谓“ALS”病例的诊断商榷之前(即桂哌齐特新药试验之前)的部分资料
对崔丽英文献[35]引用的国际最顶尖的Science杂志,我院早在2012年就发文推翻了该刊所载的“渗透性”CPM实验结果[44],但直到2016年我院[45]才引用、展示了该杂志。我院2012年发文(被该刊编辑崔戾蝇及李武营大肆篡改,包括作者单位[44]、英文摘要[46])后迄今,省级及其以上医院神经内科已极少报告“渗透性脱髓鞘综合征”病例,而2012年之前,全国的此类病例报告则每年有几十篇之多[46]!我院一向秉持不唯书,不唯上、不唯洋(包括哈佛麻省总医院学者/专家)而唯实的理念(尽管我们做得不一定好)。2010年~2011年,我院从国内外文献的漏诊中,先后独立发现了很可能国际首例的双侧型脑桥中部内侧综合征、双侧型脑桥下部旁正中综合征(均为确诊)[16]——原病例文献的客观资料(包括MRI图片)均非常可信。而我院发现、论证的国际新疾病——肾性血小板减少症则是在委托中国医学科学院行国内外文献查新的结果基础上提出的[11]。
7 结语
(1)已知原发性侧索硬化首先累及皮质脊髓束髓鞘,进而累及锥体束轴索,最后出现上运动神经元病变,部分甚至可能发展为ALS。此客观上提示运动神经元相关少突胶质细胞在运动神经元病中可能有重要作用,而神经节苷脂以及VB12可能有一定疗效[19],但前者应与小剂量强的松合用,以预防GBS。ALS是否可能累及侧索中的网状脊髓束(由延髓网状运动核发出)而影响自主呼吸?值得研究。(2)近年发现星形胶质细胞在突触功能中的重要作用;但我们认为:星型细胞增生可能在ALS等神经系变性疾病、脑脊髓创伤、卒中及朊蛋白病等的病程中具有很重要的病理作用,可能属神经组织纤维化,其除了在脑出血早期有积极作用外,弊大于利,因此,治疗肺纤维化的吡非尼酮/尼达尼布能否通过血脑屏障、有无防治作用?——值得研究。(3)与遗传性SMA不同的是,ALS迄今尚无药物可逆转其病程,基于此,我们提出小剂量甲状腺素(促进神经干细胞分化)等系列方法用于肿瘤[47]、ALS(包括转基因),阿尔茨海默病、路易体病以及额颞叶痴呆等神经系变性病、持续性植物状态等脑脊髓创伤/脑卒中后遗症的治疗[19];重复经颅磁刺激亦可用于之。(4)家族性ALS的SOD1基因变异尽管不能解释其病变对运动神经元的高度选择性,但客观上提示自由基在其发病中的重要性,而ALS髓鞘、轴突的邻近性扩散客观上提示自由基就近扩散及小胶质细胞吞噬的作用;因此ALS特别是散发性ALS应补锌以增加SOD活性[19]、以谷胱甘肽、维生素C(每日2克)及E清除自由基[19]。(5)罕见病暨ALS主要依靠排除性诊断,ALS诊断尤须排除干性脚气病并发CPM[49]!对“ALS”的“破冰人”崔丽英报告的超大宗“ALS”病例诊断提出有力商榷与诊断建议;(5.1)(a)获得性成人型SMA4例;(b)高度疑似脊髓前动脉综合征2例;(c)临床诊断SCD 1例、疑似3例;(d)疑似缺氧性脑病7例;(e)高度疑似肌型脚气病并发干性脚气病及CPM 21例,此可能是国内、外首组肌型脚气病及其并发干性脚气病、CPM病例“报告”;(f)疑似糖尿病并发干性脚气病、CPM11例;而崔丽英所报(192+86)例“ALS”均未排除后二者;(5.2)ALS的肌电图特点是肌电图学的常识;呼吁尽快修正ALS“指南”;(5.3)呼吸衰竭是ALS的主要死因,而缺氧使其病程加速进展,因此对缺氧的早期发现、干预与预防非常重要;(5.4)文献报告甚多的SCD是常见病,也是神经内科为数不多的可治性疾病之一;(5.5)维生素B1缺乏性周围神经病,特别是锥体束征的机理都是神经内科学的常识,是该科实习生、见习生应该早日掌握的;应努力做到著名神经内科专家李舜伟教授所说的“脑子清楚”乃至思维缜密。
该院有不少优秀的女性医学专家,发现全国首例艾滋病(医科院建院60周年十大科研成果)、被张孝骞泰斗誉为才女的王爱霞教授[31]、病理学院士刘彤华教授[8,31]、精通消化科(消化内科和普外科)与老年医学的理学(日本九州大学)/医学双博士刘晓红博导、精通神经内科、神经病理学(真正的诊断金标准)与风湿病的陈琳教授[16]、风湿免疫科张文主任[16]均是其中卓越的代表,尽管她们(内科)曾被我院神经外科商榷过,但从她们的其它论文中可以看出专业水平非常高(包括魏妍平教授)。另外,赵丽丹博士在免疫病及其神经系并发症方面的造诣很深。
崔丽英2009年(时为协和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国际临床神经电生理联盟执委、中华医学会神经病学分会主委,2016年再次[48]担任该分会主委)执笔披露其2例手术中急性发作的“ALS综合征”中1例“26个月时患者仍存活[2,4],气管切开仍保留[4]”(而另1例“失访[2]”),2012年则得出其21例“ALS”首诊肌电图无广泛性神经源性损害和其病程无关的结论[36]与 “颈椎病、腰椎病等可与ALS合并存在[32]”并写进ALS“指南[32]”,此势必导致ALS过度诊断的进一步扩大化。
而崔丽英执笔的两篇CPM相关病例[7,9]时间跨度为23年(1987年-2010年);到2012年发表(通讯作者)未考虑CPM的(21+192)例所谓“ALS[36]”的时间再过2年,到2014年以通讯作者发表11例糖尿病合并所谓“ALS[51]”又过2年。
诊断需要科学思维、循证,而治疗则需要工程技术思维[8,52,57]。
国内三重刺激技术由天津医大硕士苏红军学者[54]最早从国外引进、研究、应用于锥体束和锥体细胞功能评估(其硕士学位论文则发表于2007年),而文献[55]的发表时间是2009年12月[56]。
致谢
感谢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神经内科/上海交大神经病学研究所陈生弟教授、解放军总医院第三医学中心神经外科杜长生教授、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院王伟教授、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宋红松教授与鲁明教授、中山大学第一医院曾进胜教授、301医院王鲁宁教授、首都医大宣武医院宿英英教授、复旦大学华山医院WHO神经科学研究与培训中心史玉泉教授、秦震教授与吕传真教授、中国医学科学院谭铭勋教授(中华医学会神经病学分会前主任委员)、陈琳教授、汤晓芙教授、洪霞教授与刘晓红主任、中国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张朝东教授与商秀丽教授提出宝贵意见;感谢山东东营市鸿港医院陈萌医师、华北石油总医院崔松主任医师参与!
感谢沈阳“维郁欣”新药临床试验中心/法库县依牛堡子自治乡卫生院肌电图室崔痢萤技师暨沈阳北协医院精神卫生中心马保国系主任提供部分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