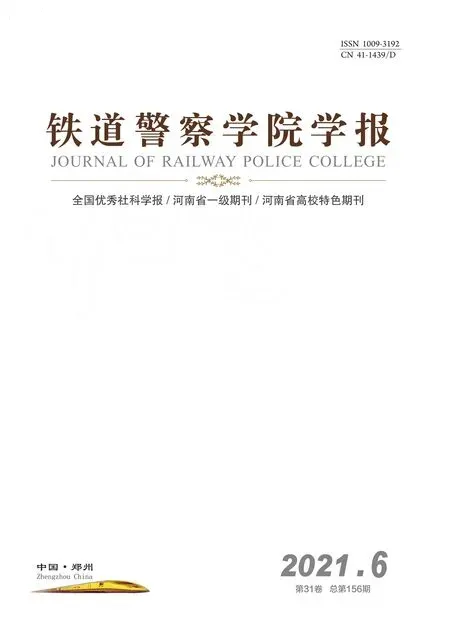“套路贷”案件司法认定的疑难问题分析
——以苏州市为样本
杨 俊,张其忠
(苏州大学 王健法学院,江苏 苏州 215006)
一、问题的提出
“套路贷”并不是一个独立的罪名,而是一系列犯罪活动的概括总称,是民间借贷市场乱象的反映。为了有效甄别和打击“套路贷”刑事案件,“两高两部”在2019年出台了《关于办理“套路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①根据《意见》第一条规定,“套路贷”是对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假借民间借贷之名,诱使或迫使被害人签订“借贷”或变相“借贷”“抵押”“担保”等相关协议,通过虚增借贷金额、恶意制造违约、肆意认定违约、毁匿还款证据等方式形成虚假债权债务,并借助诉讼、仲裁、公证或者采用暴力、威胁以及其他手段非法占有被害人财物的相关违法犯罪活动的概括性称谓。,《意见》着重强调了“套路贷”案件不同于普通的民间借贷,其本质是为了实现行为人非法敛财目的的犯罪。最高人民法院的法官也发文指出,“套路贷”案件的行为人,以虚假的债权债务关系为名目,通过并施多种“讨债手段”,来达到非法占有目的[1]。此外,《意见》还对“套路贷”的常见犯罪手法和步骤、犯罪数额认定作出归纳,为地方法院处理类似案件提供了统一的裁判依据。
但是,“套路贷”案件往往与民间借贷交叉在一起②“套路贷”案件包括民事违法案件、行政违法案件、刑事犯罪案件。本文的“套路贷”案件仅指刑事犯罪案件。,民间借贷的外观假象、证据的不易收集,都使得办案机关难以“刺破民事外观探究刑事实质”,从而有效精准打击。刑民交叉历来就是实践中的难点重点,所以如何从民间借贷中筛出“套路贷”便显得尤为重要。此外,由于“套路贷”案件分布的不均衡、法院对《意见》不同的理解,导致了实务中对“套路贷”的犯罪数额、罪数的认定也产生了较大争议。
“套路贷”作为新型的侵财型犯罪活动,在沿海经济较发达地区尤为猖獗,故笔者以苏州市为样本,在“北大法宝”上以“套路贷、苏州中院”为关键词检索相关案例①访问日期:2021年2月22日。,共检索到刑事案件33件,行为人被判处的罪名从高到低依次为:敲诈勒索罪21次;诈骗罪11次;寻衅滋事罪6次;非法拘禁罪4次;窝藏罪,聚众斗殴罪,伪造公司印章罪,强迫交易罪各2次;故意伤害罪,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开设赌场罪各1次。
结合这些“套路贷”案件,我们可以做出以下归纳:首先,该类案件涉及罪名繁多,侵犯法益也不尽相同。其中,以逐利为核心的“侵犯财产类犯罪”最多,这也体现了“套路贷”案件非法占有的实质。其次,为了顺利“讨债”,行为人会根据被害人的不同情况选择有针对性的索债方式,而这种索债行为本身可能因其符合具体的犯罪构成,而另外构成他罪。如采用非法拘禁、武力方式索债的,会侵害公民的人身权利;采用蹲门、泼油漆等“软暴力”方式的,会涉嫌寻衅滋事罪等。本文将结合苏州地区的实务判例,对“套路贷”中的几个典型性问题进行分析。
二、“套路贷”案件的入罪标准
(一)“套路贷”构成犯罪的依据
犯罪构成由行为的主客观要素组成,是成立犯罪的唯一标准。“套路贷”案件之所以由刑法规制,是因为“套路贷”案件事实符合了不同的犯罪构成,而不是因为是“套路贷”就能得出行为是犯罪的结论。换言之,“套路贷是犯罪”这一“结论”由“事实符合犯罪构成”这一“前提”推导而来,所以案件是否入罪必须先审查“前提”,没有“前提”就没有“结论”。但实践中却存在本末倒置的情形,将“结论”当作“前提”,形成因为案件事实符合“套路贷”所以就是犯罪的荒谬逻辑。
例如,在某敲诈勒索案件中,一审法院得出被告构成敲诈勒索罪的结论,并不是根据行为符合敲诈勒索罪犯罪构成要件,而是通过行为人存在“虚高借款本金”“软暴力催收”等“套路”行为加以认定,这就犯了上述错误。该判决最终被二审法院纠正,认定行为人的“套路”仅属于民事违法行为,没有以犯罪论处[2]。一审法院的分析实质是机械僵硬地理解了《意见》精神,错误地将“套路贷”当作独立的犯罪构成。这样的思路暴露出以下问题:第一,违背罪刑法定原则。“套路贷”并不是刑法的规定,对犯罪的认定必须遵从刑法条文,不能从刑法规定的犯罪构成外寻找定罪的依据[3]。第二,容易滑向客观主义的深渊。退一万步说,即使直接套用《意见》归纳的“套路贷”行为特征不违背罪刑法定原则,也容易陷入客观主义的窠臼。本案中一审法官在论证被告人的行为符合“套路贷”行为特征后,径直认定成立犯罪,忽视了对主观要素的判断,便是犯了客观主义的错误。认定成立犯罪除了审查客观的行为要素外,还需考察主观的目的与故意要素。事实上,为了解决实务中的疑难问题,刑法往往会采用列举的方式将难以判断的要素类型化。如对“非法占有目的”的判断,《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合同诈骗罪条文中就罗列了数种行为类型。但应当注意列举的行为与要素的判断不是必然的关系,应坚持“可推论”立场,即行为人符合《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的行为类型并不必然成立犯罪,而只是判断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重要参考资料,具体结论还需司法机关结合全部案件事实综合认定[4]。
综上所述,在“套路贷”案件的入罪问题上,只能依据犯罪构成。如果“套路贷”案件事实在符合财产类等犯罪的构成要件基础上,同时具备“套路贷”的行为特征,则可以认为其属于“套路贷”。如果“套路”的行为不满足刑法规定的任一犯罪的构成要件,则无论其在行为特征上是否符合“套路贷”的特征,都不是犯罪行为[5]。此外,还应当重视主观要素的判断,坚持“可推论”的立场,结合全案事实综合认定,而不能客观归罪。
(二)“套路贷”案件与高利贷的区别
在“套路贷”的入罪问题上,容易与之混淆的是民间借贷中的高利贷问题。虽然“套路贷”与民间借贷相似,是从高利贷衍生而来,但二者性质却是天壤之别。首先,二者的出借目的不同。“套路贷”案件的行为人寻找被害人、诱骗签订借款合同,目的就是非法占有被害人的财产,而不是获得借款本息回报。而高利贷是超出法定利率的民间借贷,出借人的目的是为了到期获取高额利息收益,并不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6]。其次,二者的行为方式不同。“套路贷”的行为人会采取各种手段虚构事实、隐瞒真相,制造虚假的债权债务关系,把受害人蒙在鼓里。行为人往往还会采取“找不到人、电话打不通”等方式肆意制造违约,以方便后续抬高债务。而高利贷的借贷双方对合同本金利息规定均已知晓,并且出借人衷心希望贷款人能如期还本付息,所以会积极配合债务人履行债务[7]。再次,二者侵犯的法益不同。“套路贷”是一系列犯罪活动的总称,根据其具体采取的不同“套路”,可能会侵犯财产法益、公民人身权利法益、社会秩序法益等。高利贷超高的利息扰乱了经济秩序,相比较前者,其侵犯的法益单一。最后,二者的法律后果不同。“套路贷”本质是犯罪行为,由刑法进行规制。高利贷本质上是民事法律行为,本金和合法利息都受法律保护,超出规定的利息部分并非属于犯罪,只是不受法律保护[8]。此外,尤其要注意的是对于债权本身合法而讨债行为非法的情形,不能因其讨债行为的违法性,就认定为“套路贷”①《意见》第二条明确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也未使用“套路”与借款人形成虚假债权债务,不应视为“套路贷”。因使用暴力、威胁以及其他手段强行索债构成犯罪的,应当根据具体案件事实定罪处罚。。
结合上述分析,笔者认为甄别“套路贷”案件,可采取如下路径:首先判断客观上行为人是否故意制造了被害人违约或肆意认定被害人违约的事实,若得出肯定结论办案机关则应保持高度警惕。其次要考察行为人主观上是否以非法占有本金、利息外的公私财物为目的。由表及里,最终精准打击“套路贷”案件。
三、“套路贷”案件的罪名适用
从上文可知,“套路贷”案件涉及罪名多达十余种,笔者将重点分析其中发案率较高的诈骗罪、敲诈勒索罪和寻衅滋事罪,以期厘清“套路贷”案件中的罪名适用问题。为便于分析,可以将“套路贷”案件的犯罪过程划分为两个环节:一是借款阶段,即“下套”环节,这一阶段行为人往往会欺骗受害人与之签订虚高的债务合同;二是讨债阶段,即“收套”环节,在这一阶段行为人会实施多种软硬手段(包括但不限于暴力、威胁、非法拘禁、滋扰、虚假诉讼等)来实现暴利[9]。
(一)诈骗罪
“套路贷”案件中,欺诈是行为人的常用手段,具有典型性,所以对于诈骗罪的认定较为容易,存在疑难的是诈骗罪与合同诈骗罪的界分。如在“林某某诈骗案”中②参见苏州市吴中区人民法院(2019)苏0506刑初773号刑事判决书。,林某某以民间借贷为诱饵,诱骗被害人签订了13万元的借款合同,以行业操作惯例为由将被害人名下的奔驰汽车抵押,同时给汽车安装GPS,以扣除“手续费”为名义,实际给予被害人十万元借款。然后林某某以第一期还款超时两小时等为借口单方面肆意认定违约,并在未通知被害人的情况下,将上述轿车开走变卖。辩护人认为被告人构成合同诈骗罪,而法院最终认定为诈骗罪。
笔者认为,林某某的行为成立诈骗罪而不是合同诈骗罪。合同诈骗罪是诈骗罪的特殊法条,区分二者应从合同诈骗罪的法益保护目的出发。刑法之所以将诈骗罪中的“合同”要素单独类型化成合同诈骗罪,是保护特定法益的需要。张明楷教授认为,利用经济合同实施骗财的行为,使得民众对合同丧失了信心,侵犯合同的诚信交易制度,也就侵犯了市场秩序[9]。换言之,合同诈骗罪强调对合同公平交易、诚信交易制度的违背,合同制度必然存在于经济活动的流转中,实践中不能简单地认为只要存在合同欺诈就是合同诈骗罪,而要考虑这种合同欺诈行为是否在经济活动的流转中扰乱了合同制度。在本案中,林某某从一开始真实目的就是侵占被害人的车辆,借款合同的签订只是顺利实施诈骗犯罪的铺垫。在被害人基于错误认识签订借款合同后,行为人已经通过欺诈取得被害人的债权,此时成立诈骗罪。虽然被害人遭受了财产损失,但财产只是从被害人流转到行为人,并未影响到市场交易中的其他主体,也就没有违背合同制度,因此用诈骗罪予以规制即可。
(二)敲诈勒索罪
在笔者搜集的案例样本中,敲诈勒索罪判决次数最多,反映出“套路贷”的“收套”手段愈发地压制被害人意志,已经从相对温和的欺骗往威胁方向发展。这种趋势不容忽视,说明对“套路贷”案件的规制迫在眉睫。
敲诈勒索罪与诈骗罪的目的都是为了非法侵财,二者主要区别是:诈骗罪中行为人利用被害人的错误认识获得财物,而敲诈勒索罪中被害人无认识错误但基于恐惧心理交付财物。此外,还应当注意本罪与抢劫罪的划分。敲诈勒索罪与“以暴力相威胁”型抢劫罪在客观方面相似,都是通过威吓使被害人产生了恐惧心理。但相比抢劫罪,敲诈勒索罪强制的“程度”较低,不要求达到足以压制被害人反抗的程度,这是两罪区分的关键。如在“姚某某、孙某某敲诈勒索罪、寻衅滋事罪”一案中①参见苏州市工业园区人民法院(2019)苏0591刑初346号刑事判决书。,被告人采用非法侵入住宅、聚众造势、言语威胁、往床铺泼水、向水壶内尿尿等“软暴力”手段②“两高两部”《关于办理黑恶势力犯罪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首次在规范层面将“软暴力”规定为“暴力、威胁色彩虽不明显,但实际是以组织的势力、影响和犯罪能力为依托,以暴力、威胁的现实可能性为基础,足以使他人产生恐惧、恐慌进而形成心理强制或者足以影响、限制人身自由、危及人身财产安全或者影响正常生产、工作、生活的手段”。,向被害人孙某丙亲属索要欠款57万元,后因被害人孙某丙离开住所躲债、被害人亲属不予理睬而未得逞,法院据此判决被告人犯敲诈勒索罪。该案中被告人的“软暴力”手段已经使被害人及其家属产生恐惧心理,符合敲诈勒索罪的构成要件,但“软暴力”手段未达到抢劫罪要求的足以压制被害人反抗的程度,故不以抢劫罪论处。此外,从实践来看,针对相关被害人实施敲诈勒索犯罪,造成部分被害人意欲自杀等恶劣后果的,酌情从重处罚。
(三)寻衅滋事罪
在“收套”环节,行为人为了讨债,会有组织地采用滋扰等手段扰乱他人正常生活秩序,为此,《刑法修正案(十一)》增设了《刑法》第二百三十九条之一对之予以规制③《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之一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催收高利放贷等产生的非法债务,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一)使用暴力、胁迫方法的;(二)限制他人人身自由或者侵入他人住宅的;(三)恐吓、跟踪、骚扰他人的。”。但应当注意,寻衅滋事罪是“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的兜底罪名,为避免不当扩大其适用范围,应进行严格解释。一方面,应准确区分本罪与敲诈勒索罪。主观上,寻衅滋事罪并无非法占有目的。但从客观表现来看,二者容易产生混淆,都是通过一系列手段滋扰被害人,使其产生恐惧心理“乖乖”还债。基于“行为与行为目的同时存在原则”,构成敲诈勒索罪要求被告人实施滋扰行为时需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所以对于中途参与讨债行为、不知道贷款实情的行为人,因没有非法占有目的,不能以敲诈勒索罪论处。在一个案例中,法官也特别指出,黄某某受被告人的指使,为讨要非法债务,非法侵入他人住宅并居住一晚进行滋扰,被告人黄某某此时尚未加入公司,不知真实借贷情况,其滋扰讨债行为以寻衅滋事论处,而知道贷款实情的其他同案犯以敲诈勒索罪论处。因此《刑法》第二百三十九条之一的适用范围有限,仅针对主观上无非法占有目的、客观上实施了滋扰行为的行为人。另一方面,对于滋扰行为的定性,应符合刑法谦抑性要求,滋扰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未达到需要刑法介入的程度,通过其他法律介入即可保障权利时,不宜发动刑法。如行为人尾随受害人、守在受害人的家门口等行为,以《治安管理处罚法》处理即可。
(四)虚假诉讼罪
样本中虽未出现虚假诉讼罪,但不可否认的是,利用诉讼是“套路贷”团伙用来讨债的常规手段。在“套路贷”案件中,若被害人拒绝履行债务,行为人除了使用暴力、软暴力手段威胁被害人外,还会利用犯罪实施过程中收集的对己方有利的证据,诸如虚高的借款合同、伪造的银行流水、房产抵押合同等向法院提起虚假诉讼,此时便有可能触犯虚假诉讼罪④《刑法》第三百零七条之一规定:“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妨害司法秩序或者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例如,被害人向行为人借款十万元,行为人将其虚高至三十万元并提起诉讼,那么就相当于捏造了二十万元的债权,应当认定为虚假诉讼罪。只要行为人提起虚假诉讼该罪就既遂,不要求胜诉。
但是,司法实践中囿于原告的证据充足、法官素养的参差不齐、刑民交叉的迷惑性等原因,“套路贷”团伙提起的“民间借贷”诉讼往往得到法院支持,使被害人遭受严重财产损失。值得庆幸的是,最高人民检察院注意到了该类虚假诉讼行为,有针对性地颁布了李某某等“套路贷”虚假诉讼的指导案例⑤参见《最高人民检察院公报》2021年第2号(总第181号)。。根据指导案例的精神,判断“套路贷”案件中的虚假诉讼行为,应当重视一方是否为职业放贷人、借贷合同是否为统一模板、被告是否缺席判决、原告提供证据是否符合常理等情形,为有效甄别虚假诉讼行为提供了重要参考。与之相关的便是虚假诉讼罪与诈骗罪的关系。根据《刑法》第三百零七条第三款的规定,应当择一重处罚⑥《刑法》第三百零七条第三款规定:“司法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与他人共同实施前三款行为的,从重处罚;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从重处罚。”。从法定刑来看,诈骗罪重于虚假诉讼罪。因此事实上虚假诉讼行为基本上都以诈骗处理[10],这也合理解释了上述样本为何不存在虚假诉讼罪的原因。
四、“套路贷”案件的罪数评价
在“套路贷”案件中,“套路”环环相扣,行为人通过采取不同犯罪手段的“组合拳”以达到侵财的目的,因此如何准确评价行为人实施的数行为就显得尤为重要。《意见》第四条笼统规定了罪数问题①根据《意见》第四条规定,对于在实施“套路贷”过程中多种手段并用,构成诈骗、敲诈勒索、非法拘禁、虚假诉讼、寻衅滋事、强迫交易、抢劫、绑架等多种犯罪的,应当根据具体案件事实,区分不同情况,依照刑法及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数罪并罚或者择一重处罚。,但并未正面回答何时数罪并罚、何时以一罪论处,导致实践中关于“套路贷”案件的罪数判断仍存在较大争议。
在“杨某某、王某某敲诈勒索罪、诈骗罪”一案中②参见苏州市相城区人民法院(2019)苏0507刑初392号刑事判决书。,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犯诈骗罪、强迫卖淫罪。而法院认为,被告人先行制造了虚增债务后,逼迫、介绍被害人卖淫还债,属于实现犯罪目的的手段行为,系手段行为与目的行为均构成犯罪的情况下的竞合,故对被告人杨某某应当按重罪介绍卖淫或强迫卖淫罪定罪处罚,对被告人杨某某的诈骗行为不再进行评价。笔者认为法院作出的认定存在一定瑕疵。首先,行为人实施的虚增债务行为与后续的讨债行为不具有类型化的牵连关系[11]。根据通说,对于类型化的判断要求具有常见性、伴随性。行为人对采取暴力还是诉讼方式抑或是逼迫卖淫行为并不关心,只要能达成被害人履行债务的目的即可,因此手段选择具有一定的随意性,并不符合牵连性要求。其次,对诈骗罪不予评价,会导致遗漏评价财产法益。因此笔者认为,在“套路贷”案件中,“下套”行为与“收套”行为的牵连性应严格解释,必须要求“常见常发生”,在行为分别侵犯了财产法益、公民人身权利法益的情况下,必须数罪并罚才能全面评价。
五、“套路贷”案件犯罪数额的认定
“套路贷”作为侵害财产权的新型犯罪,犯罪数额的认定决定了定罪量刑,所以在实践中其往往是控辩双方针锋相对的“攻击点”。通过归纳苏州地区的法院判决来看,法官的认定思路如下:第一,根据《意见》第六条的精神,予以整体否定性评价③根据《意见》第六条规定,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际给付被害人的本金数额之外,“虚高债务”和以“利息”“保证金”“中介费”“服务费”“违约金”等名目被非法占有的财物,均应计入犯罪数额。。在“何某、陈某等敲诈勒索罪”一案中④参见苏州市吴中区人民法院(2019)苏0509刑初1871号刑事判决书。,被告辩护人提出,被害人前期支付的GPS安装费、家访费、中介费等不应计入犯罪数额。该辩护意见最终被法院驳回,笔者却认为辩护意见具有合理性。“套路贷”的根本目的在于敛财,给被害人增加的额外费用或者被告人的“合理支出”都是常见“套路”,本质都是被告人意欲侵占被害人财产,只不过换了个“冠冕堂皇”的理由。第二,给被害人带来财产利益的犯罪成本(本金)应从犯罪数额中扣除。根据责任主义要求,行为人只有在行为时存在相应的故意或过失,才能要求其对行为以及造成的结果负责。本案中被告人的犯罪故意所指向的对象限于实际或意欲占有的被害人财物,即对于超出本金以外的财物才是行为人非法占有涉及的犯罪数额。第三,应按照共同犯罪处罚原则认定犯罪数额。应区分不同被告在犯罪中起到的作用大小,而不是将某起案件被骗的数额都认定为犯罪数额[12]。例如行为人虽然全程参与了某起犯罪,但对其他被告人另行收取的费用不知情的,或者行为人前期参与了犯罪随后退出的,此时应区别对待,以行为人知情范围为限认定犯罪数额,这也是责任主义的必然要求。
此外还应留意,行为人提供给被害人的借款本金是犯罪成本,由国家予以依法没收,被告人无权要求被害人返还。实践中也会发生被害人如“约”自动还款的情形,该部分还款资金能否计入犯罪数额呢?《意见》没有阐明,笔者认为被害人无论以什么名义归还的资金,都是行为人意欲骗财的被害人财产,均应计入犯罪的数额。
六、结语
“套路贷”作为近几年出现的新型的违法犯罪活动,社会危害巨大,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相应的司法解释予以规制,但鉴于各级法院对文件理解的偏差、“套路贷”案件本身涉及的罪名繁多、取证困难等原因,使得在处理“套路贷”案件时仍会力不从心,因此亟待解决“套路贷”案件司法认定的疑难问题。笔者以苏州市的审判实践为样本,分别从四个维度探究“套路贷”案件司法认定过程中的疑难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对策。第一,在入罪标准上,应坚持罪刑法定主义,《意见》中的行为类型只是综合判断的参考,而不能错误地将“套路贷”当作独立的犯罪构成,也不能唯客观主义论。此外,还应把握其与高利贷的界分,二者在本质上存在不同。第二,在罪名适用上,应把握公平交易、诚信交易的合同制度,以区分诈骗罪与合同诈骗罪。着眼于压制被害人反抗的程度,用以区分敲诈勒索罪与“胁迫性”抢劫罪。对寻衅滋事罪要严格解释,也必须重视虚假诉讼罪的认定。第三,在罪数评价上,对牵连犯限缩解释,行为在侵犯了不同类型的法益时,必须数罪并罚才能全面评价。第四,在数额认定上,应当予以整体否定性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