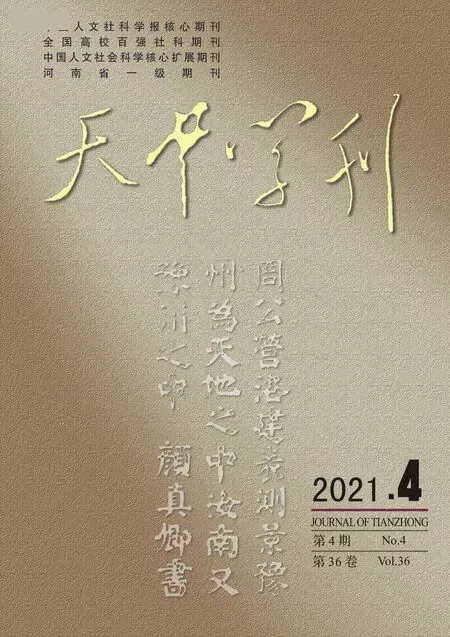班固与汉代史学的转向
黄海涛,庞伟伟
班固与汉代史学的转向
黄海涛1,庞伟伟2
(1.云南省社会科学院 人事教育处,云南 昆明 650034; 2.云南国土资源职业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云南 昆明 652501)
纵观两汉史学发展,有几点明显的转变:在史学功能方面,从以批判为主转向以颂扬为主;在史书体例方面,从以通史为主转向以断代史为主;在史书撰写方面,从以个人为主转向以团队为主;在修史组织方面,从以私撰为主转向以官修为主。这既是汉代史学的转向,也是整个中国古代史学的转向,对传统史学的发展影响深远。在汉代史学转向的过程中,班固或主动作为,或被动加入,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班固;汉代史学;转向
从《史记》到《汉书》,两汉史学有了较大的变化,这尤其体现在因著史宗旨不同和史书体例创新导致的编撰风格迥异上,前人对此多有论述。此外,还有一种虽不是那么明显但影响深远的变化:伴随着对史学功能认识的加深,统治者对史学的控制日益加强,史官制度也随之发生变化,史书编撰逐渐从私撰向官修转变。《史记》是司马迁私撰的“一家之言”,《汉书》一开始也是班固私撰,但从明帝“乃复使终成前所著书”[1]1334开始,其修史就难免会受到统治者的影响。无论是著史宗旨的转变、史书体例的创新,还是史官制度的变化及史学控制的加强,无论是主动作为,还是被动加入,班固都在汉代史学的转向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著史宗旨的转变:从批评到颂扬
从孔子作《春秋》开始,中国古代的史学家对历史撰述的目的与作用,就有了明确的认识。身处春秋乱世的孔子之所以作《春秋》,孟子认为是“世道衰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君者有之,子弑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2]2714。至于结果,孟子指出:“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2]2715可见孟子认为《春秋》是批评现实的作品,具有讨贼垂法的作用。孔子作《春秋》时,“笔则笔,削则削”[3]1944、“以一字为褒贬”[2]1707的褒贬用讳手法,也被后世尊称为“春秋笔法”或“春秋书法”,认为其中寓有“微言大义”,具有政治目的。《左传》以史事解经,归纳出了《春秋》褒贬用讳的各种义例,往往用“凡”字引领,晋代杜预统计有“五十凡”。
司马迁对《春秋》之中的褒贬笔法极为推崇,并肯定其政治作用。《史记·太史公自序》云:“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3]3297而且,《史记》的褒贬手法深受春秋笔法的影响。比如:《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以《春秋》“据鲁,宗周”[3]1943、“内诸夏而外夷狄”[2]2297为依据,将诸侯按周、鲁、齐、晋、秦、楚、宋、卫、陈、蔡、曹、郑、燕、吴排序;《春秋》对人物的称谓有严格义例,以正名分,如称吴、楚国君为“子”,齐国君为“侯”,宋国君为“公”,《史记》中人物称谓也各不相同,如孔子、老子、孙子、孟子称子,郦生、贾生、伏生、董生称生,荀卿、虞卿称卿等。
纪实直书是《春秋》基本书法之一。孔子非常推崇先秦史官的纪实精神,其作《春秋》便遵循古代良史的纪实书法,晋代杜预评价称:“尽而不污,直书其事,具文见义。丹楹刻桷、天王求车、齐候献捷之类是也。”[2]1706《史记》受其影响,也以实录著称,刘向、扬雄赞曰:“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4]2738《史通·曲笔》云:“史之不直,代有其书。”[5]143迫于政治上的压力,很多史书作者不得不为尊者讳饰,而司马迁敢于大胆揭露和讽刺当朝开国君主和当代皇帝的丑恶行径。他在《史记·高祖本纪》中直书刘邦“好酒及色”[3]343,在《史记·樊郦滕灌列传》中记载刘邦极端自私自利,“汉王败,不利,驰去。见孝惠、鲁元,载之。汉王急,马罢,虏在后,常蹶两儿欲弃之”[3]2665。对汉武帝迷信神仙之术、屡次被方士戏弄的愚蠢行径,他在《史记·封禅书》中也做了详尽的描述。
论、赞是古代史家对史事或人物进行批评的重要方法,如《左传》在叙述史事后,常用“君子曰”的形式发表议论,有时也用“君子谓”“君子以为”“君子以知”等。这是一种很有影响的议论方法,先秦典籍中《国语》《战国策》也用“君子曰”发论,《公羊传》《谷梁传》分别有“公羊子曰”“谷梁子曰”。司马迁著《史记》,也沿用此例,以“太史公曰”发论,并将其发展为序、赞、论三种史论形式。《史记》中的“太史公曰”虽承自《左传》,但其使用比《左传》的“君子曰”更加系统,内容也更为广泛。据统计,《史记》全书有序论23篇,赞论106篇,论传5篇,共计134篇,对王侯将相、先圣今贤均有所批评,“乃《史记》一书之血气”[6]。
与司马迁不同,班固著史的目的是宣扬汉家之德。他在《汉书·叙传》中直言:“固以为唐虞三代,《诗》《书》所及,世有典籍,故虽尧舜之盛,必有典谟之篇,然后扬名于后世,冠德于百王,故曰:‘巍巍乎其有成功,焕乎其有文章也!’汉绍尧运,以建帝业,至于六世,史臣乃追述功德,私作本纪,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太初以后,阙而不录,故探纂前记,辍辑所闻,以述《汉书》。”[4]4235从这段话来看,班固以“宣汉”为著史宗旨,主要有以下两个原因:其一,是对唐虞三代以文章扬名的效仿;其二,是因为以往的历史撰述未能肩负起“宣汉”的历史重任。在他看来,西汉王朝是历史上最强盛的王朝,远非孔子及儒者们推崇的周王朝所能比拟,而《史记》将其“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显然贬低了大汉王朝的历史地位。况且《史记》所载西汉历史并不完整,“太初以后,阙而不录”,之后褚少孙等十余家的续作,更不足观。因此,所有对西汉王朝的记载,无论从断限,还是从内容上说,都达不到班固“宣汉”的要求。
班固著史,公开标榜以歌功颂德为宗旨,在中国史学发展中还是第一次。其“宣汉”的著史宗旨在《汉书》的体裁和思想上也有所体现。在体裁上,《汉书》沿用司马迁所创纪传体,是因为纪传体有包容量大的优点,能够更为全面地记载西汉大一统盛世的历史。同时,改通史为断代史,断汉为史,对纪传体体例进行调整,这些都是“宣汉”的需要。在思想上,班固以董仲舒天人相关的理论为基调,宣扬“王者受命于天”“汉为尧后”“断蛇著符”等说法,期望达到“宣汉”的目的。
班固以“宣汉”为宗旨著《汉书》,反映了这个时代统治阶级的需求。东汉初年,刘氏政权失而复得,引发统治者对政权更替以及如何巩固刘氏统治的思考。班固的“宣汉”,一方面是从思想上说明刘汉政权出自天授,证明其存在的合法性;另一方面是从西汉的历史兴衰中总结出经验教训,为现实政权提供历史借鉴。吴怀祺认为,班固是“以‘宣’西汉的途径,达到‘宣’东汉的目的”[7]。
班固的《汉书》以“宣汉”为宗旨,正是顺应潮流之作,观其《汉书》十二纪之赞语,几乎全是溢美之词。作为封建正统史学的代表,《汉书》的做法对后来的史书产生了重要影响。如《汉纪》的赞语大多直接引用《汉书》,其字数虽不及《汉书》的四分之一,但全面保留了《汉书》中所记祥瑞,宣扬“汉为尧后”。又如《东观汉记》对东汉光武帝至灵帝这十一位君主,无一例外加以美化,吹捧他们“幼而聪明睿智,容貌庄丽”[8]54、“幼而聪达才敏,多识世事,动容进止,圣表有异”[8]76等。
二、史书体例的创新:从通史到断代
受通变思想影响,先秦史书无论是何种体裁,均为通史。对通变思想较早而全面的阐述,来自《周易》。《周易·系辞下》云:“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2]86这里所谓的穷、变、通、久,就是历史上的古今变化法则,其核心是“变”和“通”。《周易·系辞上》云:“是故,阖户谓之坤,辟户谓之乾。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2]82,“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2]83。司马迁把“通古今之变”作为著史宗旨之一,就是对通变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史记》所记载的时代之长是前所未有的,上至传说中的黄帝,下至汉武帝时期,共计两千余年。在司马迁之后,刘向所撰的《列女传》,虽体裁单一,但也属于通史著作。
《汉书》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全书由十二本纪、八表、十志、七十列传组成,共100篇,80余万言,完整记录了西汉一朝的历史。断代为史,从历史编纂学来说,是一大创举,因为在此之前,没有任何一部史书完整记录过一个朝代的历史。《史通·六家》云:“历观自古,史之所载也,《尚书》记周事,终秦穆,《春秋》述鲁文,止哀公,《纪年》不逮于魏亡,《史记》唯论于汉始。如《汉书》者,究西都之首末,穷刘氏之废兴,包举一代,撰成一书。言皆精练,事甚该密,故学者寻讨,易为其功。自尔迄今,无改斯道。”[5]19
班固之所以写断代史,有其特殊的原因。从客观上来说,这是史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选择,因为“他生活的时代,正是东汉社会生产发展、经济文化繁荣的时期,这就为史学的发展提供了物质条件;而东汉统治者为了总结前朝的历史经验,迫切需要编写前朝的历史”[9]。从主观上来说,则是“宣汉”的需要。班固认为,司马迁将西汉王朝的历史“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而且也不完整,这与“汉绍尧运”的历史地位实不相称,只有断代为史,才能突显西汉大一统皇朝的历史成就。与通史相比,断代史虽然有不易反映历史发展联系的缺点,但也有其优势。许殿才认为,断代史与纪传相结合,使他们各自的长处得到充分发挥,是记载中国历史最好的表现形式,其长处主要有四:一是限断清楚,可明确区分历史时期并反映其特点;二是包容量大,可全面反映一个朝代的整体面貌;三是便于编写和阅读;四是容易满足修史者褒贬前朝的要求,也便于人们总结经验教训[10]221。
除了改通史为断代史以外,班固还调整了纪传体史书的体例。《史记》虽然首创了纪传体体例,但在体例上并不严整,所以《汉书》对《史记》体例进行了调整,进一步明确了各部分的功能,确立了整齐划一的纪传体编撰体例。首先,改本纪为纪,抬高纪对全书的统帅地位,增强纪的纲领性。许殿才指出:“《史记》的本纪体例繁杂,五帝、夏、商、周、秦、项羽各本纪的写法都很不同。《汉书》则把本纪统一改为以帝王为中心的编年大事记,确立了一帝一纪的基本模式。《史记》的项羽、高后二本纪,名曰本纪,实则传体。《汉书》对本纪做出统一要求,如《高后纪》只详大事,摒弃琐碎,把一些具体史实归入相应列传中,这就使本纪体例更为严整,更好地发挥了它的纲领作用。”[10]222–223《汉书》还纯化了纪的范围,将项羽剔除,称帝的王莽也不列入。其次,改书为志,除篇名有所改动,又新增《刑法志》《地理志》等篇目。《史记》的篇章排列,没有统一的义例,《汉书》则将之整齐划一。譬如《汉书》对各志的排列顺序,相比《史记》就有所调整。近代史家刘咸炘在《汉书知意》中对此有所论述:“按班书《律历》居首,重授时也,黄钟为万事根本。次之以《礼乐》《刑法》《食货》《郊祀》,皆制度也,礼不行而刑始生,货财盛而淫祀始兴,平准均输,则酷刑所由起也。次《天文》而《五行》联,次《地理》而《沟洫》联,皆有源流,无定制者也。《艺文》为学术总汇,而《天文》《五行》《地理》《沟洫》皆专家之学,实统于《艺文》也。”[11]最后,改列传为传,取消世家,将其内容并入传中。《汉书》对列传部分的改动非常大,安作璋指出:“《史记》的专传或合传与类传的次序间杂,或以时代相同,或因事迹相关,体例很不统一。如《刺客列传》本属类传,竟置于专传吕不韦、李斯列传之间;《汲郑列传》本是专传或合传,反置于类传循吏、儒林列传之间;《匈奴列传》置于《卫将军骠骑列传》之前,《游侠列传》置于《大宛列传》之后。《汉书》则一律以时代的先后顺序为主,先专传、合传,次类传,再次为边疆各族传,而以‘贼臣’《王莽传》居末。又如《史记》列传的篇目,或以姓标,或以名标,或以字标,或以官标,或以爵标,体例也很不统一。《汉书》则大体上都是以姓或姓名为标题,这样就统一了纪传体史书的体例。”[12]
《汉书》体例严整,对后世史书撰写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班固以后,纪传体断代史成为中国史学的主导体裁,现存的二十四史中,除《史记》《南史》《北史》外,其余都是断代体制,这是《汉书》的一大贡献。章学诚评价说:“迁《史》不可为定法,固《书》因迁之体而为一成之义例,遂为后世不祧之宗焉。”[13]
三、史官制度的变化:从太史到著作
史官一职在我国设置得相当早,《后汉书·班彪列传》云:“唐虞三代,《诗》《书》所及,世有史官,以司典籍。”[1]1325相传黄帝时有史官仓颉、沮涌,虞舜时有伯夷,夏有终古。商代的史官,在甲骨文中称作“史”“尹”“作册”。到了周代,周王室设置了多种不同职掌的史官,如太史、小史、内史、外史、左史、右史、御史等。不仅王室有史官,各诸侯国也设置有史官,如楚国有左史,郑、齐、卫、虢有太史,郑、秦有内史,秦、赵有御史。有些诸侯的史官,还是周王赐予的,如《左传·定公四年》记载:鲁国初封,周王室“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备物典策”[2]2134。其中的“史”,便是太史。
先秦史官的职掌范围相当广泛,包括保管各种历史资料和官府文书,起草、宣读文件,记录某些活动及天子言行,主管天文历法,推断未来之事的吉凶成败等。因此,最初史官的地位很高。王国维指出:“史为掌书之官,自古为要职。殷商以前,其官之尊卑虽不可知,然大小官名及职事之名,多由史出,则史之位尊地要可知矣。”[14]譬如,内史的职位便与东汉以后的尚书令、唐宋的中书舍人、翰林学士、明代的大学士相当,实为中枢要职。但随着职掌范围变小,史官的地位逐步降低。李宗侗认为史官的职权有三变:“总全国一切之教权政权,最初之职务也。盖最古教权与政权原不分,史既掌管一切天人之际的事务,则总理一切政权教权,亦极合理。后渐演变,因政权与教权分离,天人之际属于教权范围,故史官职权缩小,只包括天人之际的事务及其记载而不能参与政权,此第二阶段也。只以著国史为事,此第三阶段。亦即后世对史官之普通观念。”[15]4–5基于此,他总结出:“盖时代愈后史官之权愈小,愈古权愈广,明乎此,方能知史之真谛。即以地位而言,亦最初极尊,而后转卑。”[15]5到秦汉时,史官的地位已极低,正如司马迁所说:“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蓄之。”[4]2732
汉初的官制多因循秦朝,《汉书·百官公卿表》云:“秦兼天下,建皇帝之号,立百官之职。汉因循而不革,明简易,随时宜也。”[4]722史官制度也是如此,西汉的史官设置与秦大体相同,有御史中丞和太史令。御史中丞为御史大夫的属官,“在殿中兰台,掌图籍秘书,外督部刺史,内领侍御史员十五人,受公卿奏事,举劾按章”[4]725。可见虽然御史中丞的职责很广泛,但只有掌图籍秘书属于史官的职责范畴。太史,或称太史令,武帝时才恢复设置,司马谈和司马迁父子先后担任此职。太史令的职责与古代史官类似,既掌星历,又掌记事,天官、史官合一。西汉时,太史令的史官功能开始逐渐弱化,这种趋势从司马迁就开始了。譬如改历和著史是司马迁人生中的两件大事,其中改历属于官方行为,著史则是私人行为。因此,牛润珍认为:“西汉太史令能称得上史官者,实即司马迁父子两任。”[16]42王莽时,又曾置柱下五史。据《汉书·王莽传》记载,居摄元年王莽称帝,“祀上帝于南郊,迎春于东郊,行大射礼于明堂,养三老五更,成礼而去。置柱下五史,秩如御史,听政事,侍旁记疏言行”[4]4082。刘知几指出:“听事,侍旁记迹言行,盖效古者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此其义也。”[5]220
到东汉时期,太史令已没有了史官的职能,完全变成了天官。《史通·史官建置》论及此事称:“于是太史之署,非复记言之司。故张衡、单扬、王立、高堂隆等,其当官见称,唯知占候而已。”[5]218东汉专门设置的史官是兰台令史和校书郎。兰台令史是由掌管兰台图籍秘书的御史中丞演变而来,但职掌比较单一,主要是掌校图书、编修汉史。校书郎的职责应当与兰台令史相似,如班固就先后任兰台令史和校书郎,参与撰修国史。班固在撰写光武一朝君臣事迹上显露出卓越的才华,深得汉明帝的赏识。章帝即位以后,班固更加受到器重,常常被招进皇宫,与皇帝一起读书。章帝每次外出巡狩,总让班固随行,献上诗词歌赋助兴。朝廷有大事,也让班固列席,参与公卿大臣的讨论。建初四年,章帝下诏召集诸儒于白虎观讲论五经异同,班固以史官身份出席会议,并兼记录,会后他按章帝的旨意,将会议记录整理成《白虎通德论》。
章帝以后,撰史之所改称东观,由皇帝选派有才学的官员参与撰史,不论职务如何皆称“著作”。刘知几指出:“至章、和以后,图籍盛于东观。凡撰汉记,相继在乎其中,而都为著作,竟无它称。”[5]220顺帝时,曾任太史令的张衡,要求参与修史,其他史臣也大力推荐,但始终未能如愿。著作虽然不是正式的官职,但职掌撰修国史,是事实上的史官。这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如从魏晋开始,各朝逐渐有了著作郎、著作佐郎的专职史官,他们从事日常的修史工作。然而,一旦有了重大的修史任务,各朝还会在官僚队伍中广泛选择才学出众者“兼修国史”。
四、史学控制的加强:从私撰到官修
政权对史学的干预由来已久,先秦比较著名的史官如晋国的董狐、齐国的太史和南史氏,都因反对统治者的干预而显名。《左传·宣公二年》记载:赵穿杀了晋灵公,太史董狐认为责任在赵盾,便书“赵盾弑其君”,并公示在朝廷。孔子感慨说:“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2]1867《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记载:崔杼杀了齐庄公,太史实录“崔杼弑其君”[2]1984,崔杼把他杀了,太史的两个弟弟又继续这样写,先后被杀,太史的第三个弟弟仍然这样写,崔杼只得放过他,南史氏听说太史全死了,拿着竹简前往,了解到已经如实记载,才回去。他们因此被称为“古之良史”,被后世史家所敬仰。
不利于统治者的史书,通常逃不脱被焚烧的命运,如《孟子·万章下》就云:“北宫锜问曰:‘周室班爵禄也,如之何?’孟子曰:‘其详不可得闻也。诸侯恶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2]2741可见在秦始皇焚书之前,战国的诸侯们已经开始了焚书。当然,最为著名的还是秦始皇接受李斯的建议而实行的“焚书”政策。《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3]255钱穆指出:“秦代焚书,最主要者为六国史记,其次为诗、书古文,而百家言非其所重。”[17]秦始皇的焚书打断了中国史学的正常发展,终秦一朝,只留下不载年月的《秦记》。
汉王朝建立之初,统治者还来不及对史学进行过多干预,也不反对私人撰史。陆贾《楚汉春秋》、贾谊《过秦论》、司马迁《史记》、刘向《列女传》等,都是私撰。《汉书旧仪注》记载:“司马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过,武帝怒而削去之。”[3]3321汉武帝的“怒削”可能是汉代统治者对史学最早的干预,但由于是孤证,学者多不信。成帝时,刘向父子受诏校勘图书,并撰成《别录》《七略》,由于参与者都是成帝指派,这无疑具有官方背景。但此次校勘图书的目的是整理杂芜、方便使用,与控制史学扯不上关系。但随着史学的发展,统治者对史学功能的认识开始加深,对史学的干预也明显加强。如光武帝曾说:“忠臣孝子,览照前世,以为镜诫。能尽忠于国,事君无二,则爵赏光乎当世,功名列于不朽,可不勉哉!”[1]910同时,光武帝还直接干预史书的编撰,《隋书·经籍志》云:“后汉光武,始诏南阳,撰作风俗,故沛、三辅有耆旧节士之序,鲁、庐江有名德先贤之赞。郡国之书,由是而作。”[18]
当然,汉代统治者从秦始皇焚书招致的骂名中汲取了教训,转而采取另一种控制史学的方式,那就是禁止私人撰史。及至明、章时期,私作国史成为犯法之事。譬如班固撰写《汉书》时,曾因私作国史的罪名下狱,明帝审查书稿,知其志在宣汉,便令其继续编撰,《汉书》也就从私撰变为半官修性质。汉代官修史书的最大成绩是编撰《东观汉记》,该书是我国第一部官修纪传体史书,是东汉人自己所写的东汉历史。章、和以后,藏书、校书之所迁到东观,于是修史也迁到东观。《东观汉记》本名《汉记》,后世因其成于东观,故称其为《东观汉记》。《东观汉记》主要有4次大规模的编撰。班固被选中参加了第一次的编撰,与陈宗、尹敏、孟异等人记述光武帝时的史事,所记包括纪、列传、载记。《后汉书·班彪列传》云:“召诣校书部,除兰台令史,与前睢阳令陈宗、长陵令尹敏、司隶从事孟异共成《世祖本纪》。迁为郎,典校秘书。固又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孙述事,作列传、载记二十八篇。”[1]1334
《东观汉记》的缺点很多,且记述颇为繁杂,但它对我国史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为后世历代国史的修撰提供了有益的经验。从《东观汉记》开始,出现了当代人撰写当代史的现象,至此开创了历代官修本朝史的传统,后世逐渐形成了国史著作制度,或一朝一修,或一朝数修,“东汉凡四修,曹魏三修,孙吴四修,东晋三修,南朝宋四修,北魏六修”[16]230。《东观汉记》先后在兰台、东观进行修撰,以此为契机,东汉逐渐形成了固定的修史之所。后世也依此法,比如从魏开始便设立了专门的修史机构——著作局,到唐贞观年间又别置史馆。
官修史书有很多优点,比如有多人参与、可以使用政府收藏的大量图书、因统治者的支持而具有较高的权威性等。但其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比如必须按照统治者的意旨行事,个人的发挥受到限制,为宣扬统治者的功德,难免有很多曲笔、回护。统治者对史学逐步加强控制的原因,是惧怕史学发挥正常的道德评判功能。如《后汉书·蔡邕列传》记载:董卓死后,蔡邕被治罪,“邕陈辞谢,乞黥首刖足,继成汉史……允曰:‘昔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流于后世。方今国祚中衰,神器不固,不可令佞臣执笔在幼主左右。既无益圣德,复使吾党蒙其讪议’”[1]2006。总之,从私撰到官修,“是官方对史学日益加深认识的过程,也是对史学日益控制的过程,更是史学日益成为政治工具的过程”[19]。
[1] 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2] 阮元.十三经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0.
[3]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4] 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5] 刘知几.史通[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6] 张大可.史记研究[M].北京:华文出版社,2002:252.
[7] 吴怀祺.中国史学思想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112–113.
[8] 刘珍,等.东观汉记校注[M].吴树平,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8.
[9] 仓修良,魏得良.中国古代史学史简编[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94.
[10] 许殿才.中国史学史:第2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11] 刘咸炘.刘咸炘学术论集:史学编[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187.
[12] 陈清泉,苏双碧,李桂海,等.中国史学家评传:上册[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80.
[13] 章学诚.文史通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15.
[14] 王国维.观堂集林[M].北京:中华书局,1959:269.
[15] 李宗侗.中国史学史[M].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4.
[16] 牛润珍.汉至唐初史官制度的演变[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
[17] 钱穆.国史大纲[M].修订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141.
[18] 魏征,等.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982.
[19] 许凌云.儒学与中国史学[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2:105.
BAN Gu and the Historiography Turn in the Han Dynasty
HUANG Haitao1, PANG Weiwei2
(1. Yunnan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Kunming 650034, China; 2. Yunnan Land and Resources Vocational College, Kunming 652501, China )
Viewing the development of historiography in the Han Dynasty, there are several obvious changes: in terms of functions, it has shifted from criticism to praise; in the style, it has shifted from general to chronological; in writing, it has shifted from individual to group; in the editing, it has shifted from private to official. This is not only the turn of Han Dynasty historiography, but also the turn of ancient Chinese historiography, which has a profound impa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historiography. In the whole process, BAN Gu played an irreplaceable role by either actively acting or passively involved.
BAN Gu; historiography of the Han Dynasty; turn
K234
A
1006–5261(2021)04–0128–07
2021-02-03
黄海涛(1986―),男,河南信阳人,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 赵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