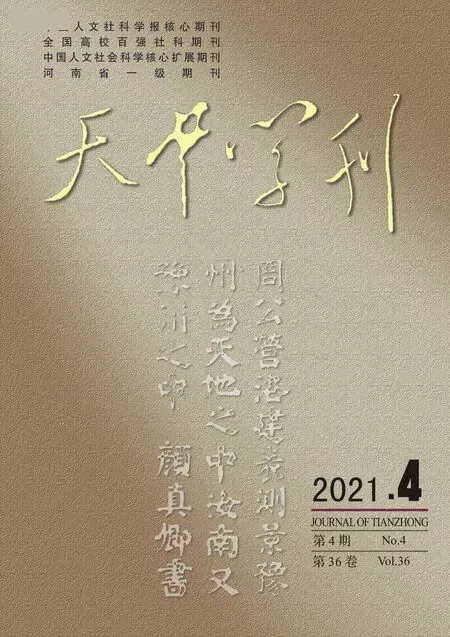论当事人否认具体化义务之设定——基于诚信实效化的考量
黄毅,赵一平
论当事人否认具体化义务之设定——基于诚信实效化的考量
黄毅,赵一平
(西南大学法学院 公法与国家治理研究中心,重庆 400716)
设定当事人否认陈述具体化义务,是落实诚实信用原则的有效举措,它内含着当事人否认陈述之完整性与真实性两个面向。受制于辩论主义向下的证明责任分配原则,当事人否认抽象化现象长期得不到有效规制,这既有悖于诚信原则、平等原则,又妨害诉讼效率的提高,与2020年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决定》的立法目的相悖。出于保障双方当事人诉权平等以及推动诚实信用原则实效化的考量,确有必要在规范层面设立当事人否认陈述具体化义务,并应从体系化规范设定的立场,制定配套的“义务提醒”“义务履行”和“履行不能之救济”细则,以提高当事人否认陈述具体化的可操作性,防止义务虚置或者矫枉过正。
否认陈述具体化义务;诚信原则;诉权平等原则
“否认陈述具体化义务”是指非负证明责任一方就对方主张向法院做出否认时,必须保证否认事实具体完整、陈述内容真实诚信的义务。显而易见,设定否认具体化义务的目的在于保障诉讼公平、提高诉讼效率。根据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90条的规定,除了法律规定的例外情况,当事人应就自己提出的用于反驳对方主张的事实进行证明。若当事人不能在规定程序中证明其事实的真实性,那么将会承担证明不利的责任①。
我国虽然在应然层面建立了公平兼顾效率的民事诉讼制度,但是“非具体化的否认”作为实践中常见的反驳手段,却使我国民事诉讼审判活动迟滞,导致我国民事诉讼制度实然与应然的分离。目前,实践中已经有部分案件出现因否认不具体导致的诉讼效率低下的情况,例如,在2016年“戚国昌、曹建刚与谈芹宝所有权确认纠纷案”[1]中,因为被告方坚持否认,导致事实难辨,期间原告甚至申请测谎鉴定,被告方对此表示接受但又在司法鉴定中心接受委托后反悔;在“浙江长源锦纶科技有限公司与江阴天顺纱业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2]中,被告方于质证阶段在规定的期限内对原告提供的“证据3”既不给出翔实的否认陈述,亦不肯承认对方陈述的真实性。不言而喻,在诉讼中无论是“前后反复”还是“故意拖延”,均是对我国司法资源的浪费。而且,否认不具体往往伴随虚假否认的现象,这不仅严重影响诉讼效率,而且直接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如在“厦门喜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仙游县鲤城向阳坊烘焙国货店、莆田向阳坊食品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纠纷案”[3]中,原告喜阳公司有关“品牌使用费对账单”的否认陈述,经过法院调查之后认定为虚假否认,这给司法工作人员增加了非必要的工作负担,浪费国家司法资源的同时也践踏了司法的严肃性。以小见大,随着我国法治进程的推进,民事诉讼案件激增,当事人否认不具体将会成为我国民事诉讼案件高效审理以及民事诉讼中诚实信用原则实效化的“拦路虎”[4]103–113。
2020年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决定》(下文简称《民诉证据规定》)在第63条、64条、65条新增“当事人应为真实、完整陈述”②、“当事人到场接受询问”③、“当事人签署询问保证书”④三项规则,从规则设定上确立了当事人真实、完整陈述的义务,其旨在规制民事诉讼中常有的“诉讼拖延”[5]、“虚假陈述”[6]、“诉权滥用”[7]等乱象,以实现“正确确认事实”“公正、及时审理”之目的,从当事人陈述方面为落实《民事诉讼法》第13条第一款之诚实信用原则提供支撑。但《民诉证据规定》中仍然没有关于“当事人否认具体化义务”的相关规定,这使得当事人否认陈述制度的漏洞仍旧有碍我国诉讼制度的完善。鉴于此,本文就当事人否认具体化义务之设定进行学理探讨。
一、我国当事人否认具体化义务研究现状
(一)“直接否认说”
“直接否认说”,是我国目前的主流学说。该说认为,否认是民诉中典型的诉讼行为,基于“利己诉讼”的价值理念以及责任分配之“谁主张,谁举证”原则,“当事人故意做出有利于自己的诉讼状态,这是他的自由”,非负证明责任一方无须为对方举证提供便利[8]。直接否认仅要求非负证明责任一方进行明示否认,而不必就否认进行具体说明,这是一种诉讼中常见的防御型回应[9]291。
民事诉讼审理过程中,双方当事人必须在辩论阶段“就自己做出的利己主张进行有责陈述”[10],而且要“回应对方主张和陈述从而形成博弈”[11]。在直接否认说看来,“否认”只是作用于对方当事人的主张陈述的真实性,通过否认来实现对对方主张的完全否定的意思表示,使得对方的主张陈述出现瑕疵,从而让法官不能直接采信对方的主张陈述,降低法官依据对方陈述形成心证的盖然性[12],以达到保护自身合法利益的目的。该说认为,一方面,由于当事人在否认陈述中并未提出“新的利己主张”,所以不需要负担具体化说明义务;另一方面,由于否认者必须在辩论中明确表达自己的否认意思,这就要求否认一方当事人必须做出明示否认。
(二)“附理由否认说”
“附理由否认说”肇始于德国,又被称为“间接否认说”,它要求“否认一方向法院陈述与对方主张事实不可并存的另一事实,以实现间接否认对方主张真实性的目的”[4]103–113。该说在“明示否认”的基础上,进一步要求否认者将支撑否认的案件事实进行完整陈述。占善刚教授在《附理由的否认及其义务化研究》一文介绍了德国民事诉讼中有关当事人实质化义务的规范与司法经验,从比较法的视角发掘我国立法与德国立法在当事人否认陈述规定上的差异,指明我国存在否认陈述义务缺失的现状,并站在宏观角度对我国民事诉讼立法与司法完善提出建设性意见。
该说着重强调诉讼双方通过有效的辩论来形成明确的争点,从而减少法官的证据调查负担、缩小法官无效的调查范围,避免司法资源浪费,同时为对方当事人进行证据补足指明方向,避免诉讼冗长给双方带来不必要的经济负担。相较于“直接否认说”,该说一方面有利于当事人双方快速形成有效对质,使得双方高效把握对方否认的前因后果;另一方面有利于受诉法院依法推动诉讼进程、依法调查案件事实,从而实现保障公平兼顾效率的目的,体现对传统辩论主义的反思,在平衡当事人双方权利义务的问题上有较大的突破。但是,该说在“信息偏在”情况下,容易出现“间接否认”与“案件解明”的混同,妥善解决这一问题,已经成为当事人否认具体化义务自洽的关键。
(三)“积极否认说”
“积极否认说”发轫于日本,较早被我国台湾学者关注,骆永家先生在其著述的《民事法研究》一书中对当事人否认陈述进行了“消极”与“积极”的划分,所谓“积极否认”,指的是“无责任一方就对方提出的主张事实向受诉法院做出否认陈述时,积极提供与对方主张事实完全对立的否认事实”[13]。近年来,以学者包冰锋为主的内地学者也对“积极否认说”进行了探讨和丰富。总体上看,“积极否认说”与“附理由否认说”是一脉相承的,但“积极否认说”又在“诉讼时间成本”方面有所突破。
综上,我国对于当事人否认问题的研究起步虽晚,但通过广泛吸收域外经验,在理论上已经形成与德、日一脉相承的诉讼优化观念,并希望通过设立“独立义务条款”的形式规制否认陈述。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在推动民事诉讼制度进步的过程中,也应从域外立法历史中吸取教训,比如在设定否认具体化义务时,应该吸取日本相关立法的教训,不仅要设立义务条款,而且要构建与之相配套的运作、惩戒、救济机制,以防在否认具体化义务的设立上重蹈日本立法的覆辙。
二、设立否认具体化义务,推动法制完善
当事人否认具体化义务的缺失,阻碍了司法的高效审理。因此,确有必要通过设立否认具体化义务修补我国现有制度的漏洞。
(一)否认具体化使“公正兼顾效率”的司法理念得以落实
当事人否认具体化义务,是诚实信用原则下民事诉讼应当予以确立的法律概念,它主要内含着“明示否认”“限时否认”“真实否认”“非负证明责任”四大要素,这四大要素共同促进“真实陈述”。第一,无责任一方必须以明示的方式进行否认,“我国民事诉讼中不承认‘默示否认’的表达形式”⑤。在质证过程中,如果一方对相对人的陈述始终持沉默态度,则法院应推定其认同相对人陈述,也就是默认。这是防止当事人前后反复和意思偷换的必要方法。第二,否认一方应当在法定期限内及时明确否认,如果在既定时间内未明示否认,此后无充分理由而提出否认的,法院可以不予支持。这是防止当事人故意拖延诉讼的必要手段。第三,否认陈述必须附带相关的真实事实。相较于主张陈述,否认陈述仅要求所述事实达到主观真实的水平,这要求“当事人不可对自己主观明知正确的事实进行否认”[14]。或者说,“只要否认者在主观层面实事求是,即便其陈述有可能与客观事实有所出入,也不妨碍其否认陈述的真实性”[15]。这是促使当事人真实否认、增加虚假否认难度的关键。第四,否认陈述不要求提供证明证据。否认陈述具体化义务在于促进诉讼,而非减轻对方当事人的证明责任,原主张一方仍对待证事实承担证明责任,这一要素是对否认一方诉讼权利的必要保障。
可见,当事人否认具体化义务的设立兼顾了双方当事人的权利。它在实质上不会增减当事人原有的证明责任,其作用突出表现为消除无效争执,并督促双方及时高效地给出自己所掌握的事实,极大提高诉讼效率,使得民事审理高效化的同时不失公平正义。
(二)民诉法于否认陈述部分存在漏洞
1. 否认与抗辩应当泾渭分明
否认与抗辩虽然同属反驳的常见方式,但是二者同中有异不该混同。然而,实践中当事人抗辩常与否认混同,这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诉讼的权威性。例如:《原告李某某诉被告张某婚约财产纠纷一审判决书》〔(2017)辽1324民初1552号〕写道“原告起诉要求被告返还彩礼50000元。被告予以否认,陈述原先只给彩礼40000元”[16];《余某某与向太平杨某某民间借贷纠纷一审判决书》〔(2020)渝0235民初1641号〕写道“原告自认从借款后被告共支付原告41,500.00元,被告对此否认,陈述已给付97,000.00元,而被告对已给付的97,000.00元未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17]。之所以在判决中会出现“否认”与“抗辩”混同的情况,主要是因为“否认陈述”概念独立性较弱。其实,“否认”与“抗辩”并不难区别,二者区分的要义在于审视无责任一方反驳对方主张陈述时是否承认了对方的部分主张。其中,“完全否定”即为“否认”,而“部分否定”则为“抗辩”[18]232。“否认”必须是完全、彻底的否定对方主张,因此否认具体化意义下的否认事实必须与原主张事实完全互斥,即“有你无我”,二者不可并存。与前者不同,抗辩是一方“在承认对方部分主张之基础上,通过向法院提出利己新主张的方式来否定其余部分”的诉讼行为[19],即抗辩以承认对方部分主张为基础。在希厄尼西著述的《民事诉讼法》(第27版)中“抗辩”被细分为三类:第一类,阻却权力的事实;第二类,消灭权力的事实;第三类,阻碍权利的事实[18]233。相较而言,否认不具有可再分性。显然,否认与抗辩有质的差异。设立当事人否认具体化义务可以从根本上扭转二者混同的不利局面。
2. 否认与解明必须明确切分
“案件释明义务”又称为“解明义务”,即“当负责任一方因远离案件本身而无法具体陈述时,由无责任一方对案件事实与证据承担解明责任,并承担证明不利之后果”[20]。换句话说,该义务要求在证据偏在的情况下,无责任一方由于自身在证据获得或事实掌握方面占据绝对优势而被设定证明责任[21]。就此来说,当事人否认具体化与解明义务有本质差异。其一,解明义务是负担证明责任的特殊情况,并以证据偏在为前提,而在当事人否认的场合,绝大多数不属于证据偏在的情况,否认具体化义务的设立不以证据偏在为前提;其二,解明义务与否认具体化义务存在性质差异。“否认是一个在对方当事人就某一事实担负证明责任的场合下才存在的概念。”[22]也就是说,否认陈述必须以对方承担证明责任为前提,而在证据偏在场合,由于证明责任发生了转移,实际掌握证据一方已经丧失了否认的资格,所以解明与否认在性质上有根本性区别。其三,案件解明义务与否认具体化义务责任后果不同。否认具体化义务设立的主要意义在于落实诚实信用原则,推动诉讼高效审理,否认一方未尽否认具体化义务,只会导致其否认陈述不被采信,而不会直接导致法官对对方当事人主张形成心证,主张一方仍需要负担证明责任。但是案件解明义务是在证据偏在情况下对当事人举证能力不足的一种救济,根据我国《民诉证据规定》第48条、第95条的规定⑥,在证据偏在情况下,如果证据掌握一方没有尽到解明义务,那么法官就应当支持对方主张。可见,试图利用案件解明义务弥补否认具体化义务在立法上的空白是不可行的,现有的“案件解明义务+当事人完整、真实陈述义务”的制度框架,无法实现对当事人否认陈述的合理规制。同时,这一漏洞对我国的民事诉讼规范体系的影响不可忽视,如果放任不管,将使我国提高诉讼效率与公平、落实诚实信用的立法目的难以实现。
综上,在民事诉讼中“抗辩”与“否认”、“解明”与“否认”表面上同属反驳陈述,但实际上同中有异,无论是从陈述内容还是从证明责任问题上均需要明确区分,不能混为一谈。因此,现行规范在当事人否认问题上显然存在漏洞,这导致当事人否认随意化乱象多发。要解决这一问题,确有必要在立法层面设立当事人否认具体化义务。
(三)法治建设要求设立否认具体化义务
当事人否认具体化义务,是在诚实信用原则下应当建立的基础性措施,该义务是扭转民事诉讼中诚实信用原则虚化[23]、否认陈述随意化乱象的有力举措,是推动民事案件高效审理、高质量审理的可行性路径。
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推动严格司法、促进公正司法、提高司法公信力成为司法实践的核心目标[24]。自从2012年《民事诉讼法》将“诚实信用”引入其中后,我国在程序法规范领域就确立了诚信原则。但是,实践中,“当事人是否遵守诚信难以评判”“陈述不实代价轻微”“故意增加诉讼负担”等现象屡见不鲜,致使规范层面确立的诚实信用制度成为虚设。虽然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及2020年《民诉证据规定》,均对落实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补充,尤其后者从“事前签订保证书”“事后强化处罚措施”两个方面强化诚实信用原则下的“真实义务”的落实。不过,2020年《民诉证据规定》关于当事人陈述的规定,在“当事人否认陈述”部分尚存在义务设定不明的漏洞,这一漏洞主要是由“辩论主义下的证明责任分配原则”与“诚实信用原则下的真实义务、具体化义务、诉讼促进义务”的价值冲突造成的。我国现行规范将“辩论主义”与“诚信原则”放在同一地位加以明确,而辩论主义下“谁主张谁举证”的责任认定模式,肯定了当事人在非负证明责任的情况下,不承担证明不利之后果的责任分配制度。在这一逻辑中,当事人在否认场合,因为无证明责任,所以不需要进行具体化否认陈述;而诚信原则恰恰要求双方当事人均需为真实具体陈述,并推动诉讼程序前进。这就形成了鲜明的价值冲突,客观上导致了我国司法实践中当事人否认缺乏有效规制的窘境,亟待从立法层面加以明确和补足。所以,在我国法治进程不断推进的过程中,司法实践向立法与学理提出了新的问题,设立当事人否认具体化义务,是对新问题较为妥帖的回应。
三、设立否认具体化义务,推动诚信原则实效化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传统辩论主义片面强调当事人主导的理念越来越丧失优越性,旧有的依靠辩论技巧、证据突袭、故意拖延诉讼期限等行为不再被允许,辩论主义的诸多元素得到修正。
(一)否认具体化义务保障当事人诉权平等
1. 否认具体化义务未违背主张责任原则
当事人作为诉讼的原动力[25],双方的互相博弈是案件事实发现、诉讼争点形成的关键。实践中,出于利己主义的一般理性考量,双方当事人都会在诉讼中尽可能提出有利于自身的事实和证据,对不利己的内容往往会避实就虚,甚至虚假陈述。在2020年《民诉证据规定》实施之前,我国在立法层面一直将“当事人陈述”作为可以单独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类型予以确认。在2002年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69条之“无独立证明力证据类型”规定中,并未将当事人陈述列入其中⑦。在此情况下,无证明责任一方在其否认陈述中采取抽象化陈述并非不合理。但是,学界对当事人陈述的证据效力以及证人证言的证明力保持怀疑,甚至否定。所以,学界一直将“直接否认说”作为通说。2020年施行的《民诉证据规定》第90条之“无独立证明力证据类型”条款中,以列举形式于第一款明确指出“当事人陈述”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这从根本上切除了“当事人陈述”的独立证据资格。在此背景下,设置当事人否认具体化义务显然不与主张证明责任相冲突。
2. 有利于形成平等的诉讼权利义务架构
平等原则作为民事诉讼的核心原则之一,在我国《民事诉讼法》第8条有明确表述⑧,即在民事诉讼中当事人双方,在诉讼全过程应拥有平等的诉讼地位。所谓“平等”,是保障诉讼双方在追求公平正义的机会平等和能力平等,主要表现为权利与义务的平等、接触案件事实的机会平等、平等地接受审判、获得平等的救济等。
在辩论阶段,当事人双方的平等地位,最应表现为辩论武器的平等性,而在我国民事诉讼当事人否认随意化的场域下,诉讼双方存在较为明显的武器不平等问题[26]。在辩论中,根据主张责任与证明责任的衍生关系,提出主张一方必须积极举证并履行其义务,出于对胜诉的渴望,其在陈述过程中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完善自己的主张陈述和相关证据,以期让法官根据其陈述和证据达到对事实认定的高度盖然性的标准。而作为相对人的否认一方,由于其不承担责任,所以在主观上不需要承受证明压力。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否认一方可以消极应诉,因为其消极行为会阻碍对方当事人有效行使权利,属于权利妨害行为。根据我国现行法律关于当事人权利义务的规定,大致上可以把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分为“双方均可独立实现的权利”“专属于单方当事人的权利”“必须双方合作实现的权利”三大类⑨,而“否认陈述”虽是被告一方的专属权利,但却直接涉及“辩论权”“质证权”的实现,后者均属于“附带义务性权利”,双方当事人不仅是权利享有主体,同时也是义务履行主体。因此,否认一方当事人在行使否认权利的同时,必须承担不妨碍对方实现辩论权和质证权的义务。这样,其否认陈述就必须是主观真实、客观具体化的。所以,明确当事人否认具体化义务,是我国民事诉讼法秩序的应有之义。
同时,为了避免证据摸索、隐瞒事实真相等不利于否认当事人的情况出现,提出主张一方作为负担证明责任的主体,必须在诉讼中率先尽到主张陈述之真实、具体义务,如果负证明责任一方未尽到应尽的义务,否认一方当事人可以拒绝进行否认陈述;另外,在负证明责任一方陈述完毕之后,经过法官确认没有其他事实和证据补充之后,负证明责任一方不能将否认当事人具体陈述中提出的事实和证据作为支持自己主张的依据。如此一来,就在权利义务建构层面确保了当事人双方的平等地位。
(二)否认具体化是落实诚信原则的关键举措
否认具体化义务既是诚实信用原则的具体表现,也是落实诚实信用原则的关键措施。2012年《民事诉讼法》新增诚信条款⑩,表明诚信原则从实体法迈入程序法,旨在规范诉讼行为。其“要求诉讼当事人必在行权、履义时报以善良之心态,不以恶意损害他人、社会、国家利益的同时维护个人利益”[27]。要切实保障诚实信用原则的落实,就必须从两个方面进行检视:一方面,各个主体要自觉履行法定义务,合法行使权利;另一方面,这些权利和义务本身也必须形成对等公平的关系。由这两点着手不难发现,我国现行诉讼制度在“当事人否认陈述”之义务设定上存在缺失,致使当事人双方诉讼权利失衡。在2020年《民诉证据规定》实施后,从立法层面强化了书证提交、证人出庭陈述、当事人真实完整陈述、当事人陈述不可独立为证等重要内容,诚实信用原则在诸多方面都得到了补足和强化。但是,现行规范在当事人否认陈述义务设定上的漏洞仍在,亟待通过立法确立当事人否认具体化义务。
1. 设置否认具体化义务以促使真实否认
随着协同主义诉讼理念的兴起,当事人之真实义务相伴而生,传统辩论主义下当事人不必对任何人负担诚信义务的观念被彻底否定。作为法定义务,而非习惯或道德约束,真实义务是诉讼当事人必须依法履行的。从我国规范内容看,真实义务具有三大特点:第一,真实义务与证明责任无关,当事人双方在质证过程中均须严格履行。第二,真实义务表现为陈述形式的完整性、陈述内容的主观真实性。第三,真实义务贯穿于诉讼的全过程,当事人进行前后矛盾的陈述是不被允许的。从上述内容不难看出,真实陈述义务属于共担性义务,既是义务又是权利,双方共同履行的情况下将会对诉讼审理起到促进作用。
基于此,有必要“建立健全当事人双方平等的诉讼权利、义务体系”,设定当事人否认陈述具体化义务,使之与当事人具体化义务形成义务平衡。否认具体化义务的确立,能极大提高当事人虚假否认陈述的成本,从当事人主观层面降低虚假陈述的可能性,同时,也给法院判断当事人陈述真实性提供了查证的具体方向,这在程序上进一步强化了否认的真实性。当然,需要强调的是,明确否认具体化义务之后,还应当设立“针对履行不足、惰于履行甚至不履行义务当事人的制裁机制”和“当事人履行不能的救济机制”。
2. 设置否认具体化义务以提高诉讼效率
在法治社会,诉讼是解决纷争的最后保障途径,所有诉诸法院的当事人都渴望自己的利益得到充分保护,但在现实生活中很多人宁愿放弃维权也不愿意起诉,究其原因大致是费时、费力、费钱,这正如棚濑孝雄所言:“假如代价太过昂贵,就算审判再怎么完美地实现正义,贫穷者也唯有放弃以此来实现正义的想法。”[28]从法律经济角度看,“投入与产出是诉讼所无法回避的机制”[29]46。所以,由诚实信用原则衍生的“诉讼促进义务”,要求当事人双方出于善良之本意[30–31],在诉讼中积极促成争点,明确事实,推动案件审理,担负起促进义务。在这方面,从德国有关“诉讼促进义务”的改革不难发现,德国法律关于当事人双方的陈述实质化义务的规定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反观我国,否认具体化义务缺失,难免会影响诉讼效率,甚至导致案件事实认定的困难,严重妨害诉讼效率和诉讼公信力的提高。所以,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精神,设立当事人否认具体化义务,以助力民事诉讼高效审理,有其现实必要性。
如果当事人在辩论中无法尽快明确争点,势必造成案件审理的拖沓不前,这会在相当程度上加重诉讼当事人的经济、时间、情绪、身体等负担,从而有损当事人的利益。此外,法庭辩论制度旨在建构一个让当事人主导的公共辩论空间,其目的是维护私权利的自由处分权,但是这一空间绝对不能被浪费于无益的争执,同时,私权利的自由处分也要受到程序正义的规制。近年,学界关于“诉讼促进义务”的研究渐繁[32],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提出有关提高民事诉讼效率的建议。对此,当事人否认具体化义务的设定不失为一则良策。虽然从某种意义上说,程序效率和程序正义是一对矛盾,在追求效率的情况下很难确保正义不受侵害,但是如果效率不高,必然会导致更多权益难以得到及时的保护,而且从世界范围看,各国的司法改革都将提高效率作为目标,各个国家都把效率的提高作为司法改革的绩效。结合我国的司法现状和基本国情,在民事诉讼中设定当事人否认具体化义务,在证明责任上并未给否认当事人增添负担,设立该义务更多的是追求程序的效率价值,可以说是既提高效率又不损害正义的良策。
总之,否认具体化义务的确立,符合我国法制建设的合理性要求,确立该义务有利于节约司法资源,推动诉讼高效审理,提高审判公信力,加快民事纠纷解决。所以,我国确有必要对当事人否认具体化义务予以明确。
四、当事人否认具体化义务立法规范预设
(一)否认具体化义务及惩戒规范
原则上,不负证明责任的一方当事人,在其否认陈述中,应履行完整、真实的否认陈述义务。
1. 当事人否认具体化义务的主体条款
履行主体条款:第一,原告提出主张并已经完成陈述后,被告做出否认的应在其明确表达否认态度后对其否认内容进行完整、真实的陈述;第二,被告针对原告的主张提出抗辩并已经完成陈述后,原告就相对人抗辩做出否认的应在其明确表达否认态度后对其否认内容进行完整、真实的陈述。
具体化义务的提醒主体:第一,民事诉讼案件中,人民法院有义务提醒做出否认的一方当事人进行具体化的否认陈述;第二,民事诉讼案件中,当不负担证明责任一方当事人自觉履行否认具体化义务的情况下,负担证明责任一方当事人可以直接提醒对方当事人进行完整、真实的否认陈述,或者请求法官提醒做出否认的一方当事人进行完整、真实的否认陈述。
2. 当事人否认具体化义务的程序条款
(1) 义务履行前提条款:当负证明责任一方当事人已经做出完整、真实的主张陈述,且经在审法官确认再无补充内容后,不负证明责任一方当事人应就对方主张陈述做出具体化回应。
(2) 启动条款:第一,被告可以在答辩期届满前提出书面答辩,阐明其对原告诉讼请求及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的意见;第二,庭审辩论中不负证明责任一方当事人可以主动向法官提出否认陈述请求并做具体化陈述,或被提醒后配合履行否认具体化义务。
(3) 明确否认对象条款:在否认陈述中,否认对象涵盖了相对人的诉讼请求、部分陈述事实、全部陈述事实、个别证据或全部证据等诸多内容,做出否认一方当事人在具体陈述前应明确说明自己的否认对象。
(4) 否认陈述期限条款:当事人做出否认应当及时进行具体化陈述。人民法院应结合诉讼标的、纠纷类型、社会影响力等情况,明确告知否认一方当事人进行具体化陈述的期限。否认一方当事人在该期限内完全履行义务确有困难的,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延长期限,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的申请适当延长。当事人逾期未完全履行义务的,人民法院应当责令其说明理由;拒不说明理由或者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根据不同情形可以视为其放弃陈述或部分支持其陈述,但予以训诫、罚款等。
(5) 否认具体化标准及履行瑕疵惩戒条款:第一,完全履行。当事人在其否认陈述中明确提出否认对象,并附带给出与之完全相反、不可同时存在的事实,已经达到明确争点标准的视为完全履行否认具体化义务。第二,主观完成而实际存在瑕疵。当事人在其否认陈述中明确提出否认对象,并附带给出否认事实,在主观上认为已经履行了具体化义务,但由于其表述不清、事实与本案关系不明、事实内容与否认对象不匹配等客观原因,无法达到明确争点的视为履行瑕疵,人民法院应要求否认当事人补足或重新组织其陈述,以达到明确争点的标准。第三,客观履行不能的抽象否认应予支持。当事人在其否认陈述中明确提出否认对象,并附带给出否认事实的大体方向,但由于客观条件的缺失而无法进一步详细陈述的,否认一方应当对自己无法具体陈述的原因进行详细陈述,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双方当事人陈述的案件事实和证据,根据否认一方当事人的客观实际,判断是否具有要求其进一步详细陈述的期待可能性。在无期待可能性的情况下,法院应当支持其否认陈述。但是,发现否认一方当事人存在捏造事实逃避履行义务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要求其继续履行具体化义务,并对其进行训诫、罚款等处罚,案件影响较大的可以酌情加重处罚。第四,否认当事人可以向法院申请书证提交。否认一方当事人认为相对人掌握了于己有利的相关事实或者证据时,可以依法向法院申请书证提交,经审查申请合理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相对人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交的视为认同对方否认陈述。第五,放弃陈述。当事人仅作抽象化否认,经人民法院提醒仍不履行具体化义务的,应视为放弃陈述权利。
3. 当事人否认陈述异质下的义务衔接条款
在诉讼中,不要求当事人对自己所负义务类型有清醒认识时,人民法院应根据当事人提出的否认对象判断其义务类型,并及时告知当事人履行相应义务。第一,否认具体化义务。不负证明一方当事人对相对人的主张进行完全否认,并未提出利己性新主张,人民法院应提醒当事人履行否认具体化义务。第二,抗辩举证。不负证明一方当事人对相对人的主张进行不完全否认,并提出利己性新主张,人民法院应提醒当事人履行举证义务。第三,附带解明义务。不负证明一方当事人对相对人的主张完全否认,虽未提出利己性新主张,但提出掌握反证的,人民法院应当提醒否认当事人在否认具体化义务履行过程中附带履行解明义务。
(二)当事人否认具体化义务救济规范
1. 否认当事人表达能力缺陷之救济
第一,器质性缺陷之救济。当事人存在聋哑等不便于口头辩论的身体缺陷时,人民法院应当为其提供必要的替代性陈述设施,当事人自备助听、助写、助述设备的,在确认其不触犯禁止性规定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二,心理性缺陷之救济。当事人于法庭上表现出情绪激动、泣不成声,甚至因情绪或心理原因突然出现口吃、失语、耳鸣、幻听等情况无法进行否认陈述的,人民法院应当中止诉讼,并对其进行心理疏导。
2. 案件事实或证据获取能力不足之救济
该部分内容应参考2017年《民事诉讼法》第64条的规定,对当事人否认陈述的无法自行获取的事实和证据,或者法院认为应当依职权获得的事实和证据,法院须给予救济。
① 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90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做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
② 2020年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决定》第63条:“当事人应当就案件事实作真实、完整的陈述。当事人的陈述与此前陈述不一致的,人民法院应当责令其说明理由,并结合当事人的诉讼能力、证据和案件具体情况进行审查认定。当事人故意作虚假陈述妨碍人民法院审理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情节,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的规定进行处罚。”
③ 2020年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决定》第64条:“人民法院认为有必要的,可以要求当事人本人到场,就案件的有关事实接受询问。人民法院要求当事人到场接受询问的,应当通知当事人询问的时间、地点、拒不到场的后果等内容。”
④ 2020年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决定》第65条:“人民法院应当在询问前责令当事人签署保证书并宣读保证书的内容。保证书应当载明保证据实陈述,绝无隐瞒、歪曲、增减,如有虚假陈述应当接受处罚等内容。当事人应当在保证书上签名、捺印。当事人有正当理由不能宣读保证书的,由书记员宣读并进行说明。”
⑤ 2020年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决定》第4条:“一方当事人对于另一方当事人主张的于己不利的事实既不承认也不否认,经审判人员说明并询问后,其仍然不明确表示肯定或者否定的,视为对该事实的承认。”
⑥ 2020年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决定》第48条:“控制书证的当事人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交书证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对方当事人所主张的书证内容为真实。控制书证的当事人存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三条规定情形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对方当事人主张以该书证证明的事实为真实。”
⑦ 2002年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69条:“下列证据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一)未成年人所作的与其年龄和智力状况不相当的证言;(二)与一方当事人或者其代理人有利害关系的证人出具的证言;(三)存有疑点的视听资料;(四)无法与原件、原物核对的复印件、复制品;(五)无正当理由未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
⑧ 201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8条:“民事诉讼当事人有平等的诉讼权利。”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应当保障和便利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对当事人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
⑨ 第一类,任意一方当事人独立实现型权利。例如《民事诉讼法》第44条赋予当事人申请回避的权利,第49条中委托代理人、提供证据、提起上诉、申请执行、查阅本案相关资料等权利,均属于任意当事人均可独自实现的权利类型。第二类,原告或被告一方专属型权利。例如《民事诉讼法》第51条规定的“变更诉讼请求权”以及第145条规定的“申请撤诉权”,均属于原告一方的专权。而第51条规定的“被告反驳权”和“提起反诉权”以及2020年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决定》第45―48条关于“申请提交书证”的规定,都赋予了被告一方专属的权利。第三类,基于双方共同作为才能实现的权利。这一类权利比较特殊,任何一方的不作为就会使得对方权利无法实现,所以笔者认为其是“附带义务性权利”。例如《民事诉讼法》第12条规定的“辩论权”,第68条规定的“质证权”,第76条规定的“申请鉴定权”,第93条规定的“调解权”,都属于依靠双方共同作为的情况下才能实现的权利类型。
⑩ 《民事诉讼法》第13条规定:民事诉讼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
[1] 戚国昌、曹建刚与谈芹宝所有权确认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EB/OL].(2016-12-02)[2021-02-02].https://wenshu.court.gov.cn/website/wenshu/181107ANFZ0BXSK4/index.html.
[2] 浙江长源锦纶科技有限公司与江阴天顺纱业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EB/OL].(2020-01-22)[2021-02-02].https://wenshu.court.gov.cn/website/wenshu/181107ANFZ0BXSK4/index.html.
[3] 厦门喜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仙游县鲤城向阳坊烘焙西门兜店、莆田向阳坊食品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EB/OL].(2020-08-31)[2021-02-02].https://wenshu.court.gov.cn/website/wenshu/181107ANFZ0BXSK4/index.html.
[4] 占善刚.附理由的否认及其义务化研究[J].中国法学,2013(1):103–113.
[5] 刘荣军.诚实信用原则在民事诉讼中的适用[J].法学研究,1998(4):125–132.
[6] 纪格非.我国民事诉讼中当事人真实陈述义务之重构[J].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6(1):162–173.
[7] 翁晓斌.民事诉讼诚信原则的规则化研究[J].清华法学,2014(2):35–46.
[8] 杨建华.民事诉讼法论文选集:上册[M].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84:10.
[9] 占善刚.民事诉讼中的抗辩论析[J].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3):38–42.
[10] 张卫平.诉讼构架与程式[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0:152.
[11] 谷口安平.程序的正义与诉讼[M].王亚新,刘荣军,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23.
[12] 谢怀栻.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论[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70.
[13] 骆永家.民事法研究(II)[M].台北:三民书局,1999:3–4.
[14] 张卫平.民事诉讼中的诚实信用原则[J].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2(6):153–158.
[15] 高桥宏志.民事诉讼法:制度与理论的深层分析[M].林剑锋,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378.
[16] 原告李某某诉被告张某婚约财产纠纷民事判决书[EB/OL].(2017-11-30)[2021-02-02].https://wenshu.court.gov.cn/website/wenshu/181107ANFZ0BXSK4/index.html.
[17] 余国宪与向太平杨玉青民间借贷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EB/OL].(2020-06-24)[2021-02-02].https://wenshu.court.gov.cn/website/wenshu/181107ANFZ0BXSK4/index.html.
[18] 希厄尼西.民事诉讼法[M].周翠,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231–232.
[19] 胡学军.从“抽象证明责任”到“具体举证责任”:德、日民事证据法研究的实践转向及其对我国的启示[J].法学家,2012(2):159–175.
[20] 吴泽勇.不负证明责任当事人的事案解明义务[J].中外法学,2018(5):1360–1379.
[21] 汤维建.民事诉讼法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200–201.
[22] 占善刚.主张的具体化研究[J].法学研究,2010(2):110–122.
[23] 杨秀清.民事诉讼中诚实信用原则的空洞化及其克服[J].法学评论,2013(3):37–44.
[24]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EB/OL].(2014-10-29)[2021-02-02].http://cpc.people.com.cn/n/2014/1029/c64387-25927606.html.
[25] 唐力.辩论主义的嬗变与协同主义的兴起[J].现代法学,2005(6):80–87.
[26] 马龙,刘显鹏.德国逾时提出攻击防御方法之规制及其启示[J].法律适用,2017(3):112–120.
[27] 梁慧星.诚实信用原则与漏洞补充[J].法学研究,1994(2):22–29.
[28] 棚濑孝雄.纠纷的解决与审判制度[M].王亚新,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74.
[29] 柴发邦.体制改革与完善诉讼制度[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1:46–47.
[30] 王合静.论当事人之诉讼促进义务[J].河北法学,2009(6):156–159.
[31] 刘萍.论民事诉讼当事人之诉讼促进义务[J].天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45–49.
[32] 唐力.民事审限制度的异化及其矫正[J].法制与社会发展,2017(2):179–192.
On the Creation of the Party's Denial of the Obligation to Concretize——based on the Effectiveness of Integrity
HUANG Yi, ZHAO Yiping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6, China)
Setting a specific obligation for parties to deny statements is an effective measure to implement the principle of good faith. It includes two aspects: the integrity and credibility of the party's denial statement. Subject to the downward allocation of the burden of proof principle of arguments, the parties deny that the phenomenon of abstraction has not been effectively regulated for a long time, which is not only contrary to the principle of good faith, the principle of equality, but also hinders the improvement of litigation efficiency. For the protection of the parties to the right to equality and to promote the principle of honesty and integrity, it is necessary to set up the parties to deny the specificity of the obligation, and should be set from the standpoint of systematic norms, the development of supporting the “obligation to remind” “obligation to perform” and “perform the relief” rules,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specificity of the parties to deny the operability of the statement, to prevent the obligation of false or overkill.
Denial of the obligation to specify statements; faith principle; principle of equality of arms
DF72
A
1006–5261(2021)04–0029–11
2021-02-10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西部和边疆地区项目(17XJA820001)
黄毅(1975―),男,四川南充人,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赵一平(1993―),男,河南焦作人,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 叶厚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