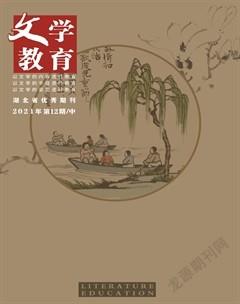花木兰故事迪士尼真人版电影再编码分析
周雯婕 陈宝琳
内容摘要:中国花木兰故事借迪士尼再编码又一次走向世界。论文认为,真人版《花木兰》对源故事的再编码具有故事主线的漂移性、人物性格的颠覆性、主题内涵的附加性等特点,这与迪士尼“公主系列”的立意需要、“自由”文化核心的流露、弱化中国历史的展示倾向等原因有关。通过对源故事再编码的全面分析,论文也对当下讲好中国故事的问题提供了借鉴性思考。
关键词:花木兰 真人版电影 再编码 特点 反思
“木兰代父从军”的故事源于中国南北朝时期长篇叙事民歌《木兰辞》(简称源故事),它不仅在中国多次被搬上银幕,而且于1998年被美国再编码成迪士尼动画版电影《花木兰》(简称动画版《花木兰》)而风靡全球。时隔二十多年,好莱坞迪士尼影片公司又斥巨资于2020年出品真人版剧情电影《花木兰》(简称真人版《花木兰》),这部电影能否讲好中国的花木兰故事,是中国观众共同关心的问题。笔者拟通过展开迪士尼真人版《花木兰》对源故事再编码的特点及原因分析,进而对中国故事再编码问题进行现实的反思性探讨。
一.真人版《花木兰》再编码的特点分析
1.故事主线的漂移性
首先,故事叙述时间浓缩。源故事讲述北魏和柔然的战争期间,木兰代父从军,浴血沙场,最后平安归来的故事。诗中有“壮士十年归”“同行十二年”等较为明确的时间表述,由此可知,木兰在外征战十余年。真人版《花木兰》则将叙述时间浓缩为一年,大大缩短了木兰故事的演绎时间。
其次,“女扮男装”设定改变。源故事对木兰从军有一个关键设定:“开我东阁门,坐我西阁床。脱我战时袍,著我旧时裳。当窗理云鬓,对镜帖花黄。出门看火伴,火伴皆惊忙:同行十二年,不知木兰是女郎”,它说明木兰从军过程中一直未被识破女儿身,立功回家才披露真相。真人版《花木兰》剧情过半时,木兰就因军中“忠、勇、真”三个原则而主动回归女儿身,因此被逐出军营,为情节推进设置了矛盾冲突,也为女性主义主题埋下了伏笔。
最后,叙述主题发生变化。源故事分离别、战争、归来、偈语四章,主要通过离别和归来两章描写木兰从军前及战后回归的细节,重点表现亲情,而对战争则一笔带过。[1]真人版《花木兰》则渲染了诗中省略的部分,重点描述木兰在军旅生活中如何隐藏女儿身份与男子相处等情节,体现出木兰军旅生活的心酸与不易,衬托出木兰的顽强不屈。
2.人物性格的颠覆性
源故事开头“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点明木兰代父从军完全是无奈之举:父亲年迈,家中无其他人选。诗中木兰孝顺贤淑、知书达理,是中国传统女子形象,诗歌以“弱”衬“强”,凸显了人物内在精神的崇高。真人版《花木兰》中,小木兰如同一个“假小子”,在部落里上蹿下跳追赶一只从圈中跑出来的鸡,弄得四下鸡犬不宁,可谓顽皮至极。这里的木兰身具强大“元气”,崇尚武力,在当时武力是男人的专属,女子尚武会让家族蒙羞,所以,父亲劝慰木兰“隐藏天赋”。电影中木兰本身很“强”,却不得不学会“示弱”,后来在征战过程中自我意识觉醒,实现了个性自由与解放,这与中国传统的木兰形象完全不同。
3.主题内涵的附加性
真人版《花木兰》格外强调女性主义,木兰的女性身份体现了这一点,巫女仙娘一角的增设更是如此。巫女仙娘在某种意义上是另一个木兰,两人都有勇有谋,拥有威力超强的“气”,都因女性身份不被根深蒂固的父权、夫权文化承认。但她们的区别在于,木兰坚守“忠、勇、真”,坚信自己可以比肩,甚至超越男性。同时,木兰和巫女仙娘又形成了参照,巫女仙娘虽拥有强大的能力,却依附于男性寻求生存之道,她映射出木兰作为女性参战可能拥有的悲惨结局。但木兰明确了自我定位,与普世价值观形成对抗,最终借助女巫寻回自我,以女性身份坦荡面对世人。而巫女仙娘也打破“女子本就低人一等”的观念,随心意奔赴自由,体现出创造的潜能与自立自强的女性主义色彩。
此外,真人版《花木兰》带有强烈的个人主义色彩。在抵制柔然的战争开始前,木兰曾鼓起勇气想向教官坦白女扮男装的事实,不料教官希望她能够像其父一样勇敢坚强,建功立业,为国尽忠,并且打算战后将女儿许配给她,导致木兰未能说出真相。战争中,木兰因追击敌军落单,与女巫的打斗时受伤,醒来看到剑上所刻的“忠、勇、真”时,决定不再隐瞒,向大家坦白了真实身份。此时,柔然大军在战争中占据上风,木兰急中生智,利用“气”制造雪崩扭转了战局,敌军被尽数掩埋。回营后,木兰被逐出军队,遇到女巫,得知敌军调虎离山,将保护皇帝的军队牵制在外围,并派遣精锐力量潜入皇城,欲杀死皇帝夺取皇城。木兰又以女儿身赶赴京城,与皇帝里应外合杀了博里可汗二世,解除了京城危机,最终被誉为“王朝最好的战士”。雪山之战和京城保卫战并没有突出团队作战的重要性,而是彰顯了木兰的个人特色,这是典型的美国个人英雄主义的色彩。
二.真人版《花木兰》再编码的原因分析
1.迪士尼“公主系列”立意的需要
真人版《花木兰》中的“花木兰”形象是迪士尼公主系列的第八位成员,也是首位亚裔“公主”。源故事中木兰从军十二年,成功隐藏女性身份,无需面对性别歧视带来的各种问题,可以顺利尽孝尽忠。而真人版《花木兰》中,木兰需直面女性身份造成的性别话语冲突,从军途中回归女儿身,最后超越性别偏见被皇帝授予官职。[2]它通过木兰一个人的“战争”,让整个性别制度和话语环境为她让路,木兰性格的颠覆性体现出新时代女性独立自主、个性自由的气质,这正是“迪士尼公主系列”大力宣扬的个性化女性主义性别观。
2.“自由”核心文化的流露
中国奉行集体主义文化价值观,强调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必要时会舍弃小我成就大义,且通过自我价值的实现来获得社会的肯定,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文学作品的面貌。而美国“自由”的核心文化意识更强调个性解放,通过个人奋斗实现自我价值。真人版《花木兰》一开始虽然从普世价值观上认为女子无论能力如何,应依附于男性,温柔贤淑、相夫教子。但当征兵令到来时,木兰反对身有残疾的父亲上战场,尽管其建议被父亲多次打断,甚至忽略,木兰还是选择在夜晚带上父亲的佩剑盔甲离家,女扮男装代父出征,开始了自己的传奇故事。雪山之战、京城保卫战,几乎都是木兰凭借个人勇气和智慧跳出“女大当嫁”“三从四德”的常规,追求自我价值的体现,也是个性自由的体现,这无疑与崇尚“自由”精神的美国核心文化相契合。
3.弱化中国历史的展示倾向
中国花木兰的故事在某种意义上是正史所佐证了的野史,其历史存在的真实性是毋庸置疑的。[3]源故事主要强调代父从军的“孝”与忠君爱国的“忠”。目前,中国传统影视剧中的花木兰故事多忠于原作,敬畏历史、敬畏人文,表现出较为宏大的中国历史叙事倾向。而真人版《花木兰》浓缩叙事时间,将十年光阴缩为一年,还将木兰从忠孝、坚强、隐忍的普通女孩改编成超现实的、具有自我“元气”的女超人,更多体现的是木兰思想与个性的解放特色。在情节设置上,木兰雪崩后独自策马救人英雄壮举的描写带有西方不切实际和不合情理的浪漫主义色彩。而新增角色“巫女”也极具西方色彩,其超自然的易容换装、幻化飞鸟等情节都十分魔幻,有违中国源故事的情理逻辑。真人版《花木兰》弱化源故事的历史背景等因素,符合西方习惯戏谑英雄、消解历史的特点。
三.真人版《花木兰》再编码的反思
不可否认,新的文化传播语境下,真人版《花木兰》对源故事的再编码具有创新性价值,但是,它与源故事有着本质的不同,是属于美国“迪士尼公主花木兰”,面对的是中国之外的受众市场,所以,影片的历史文化等设定存在一些问题,这应当引发我们对如何在世界范围内讲好中国故事,让世界听到真实的中华优秀文化声音等问题的思考。
在真人版《花木兰》对源故事再编码的过程中,除以上结合受众市场的针对性再编码外,笔者认为还存在一些中华文化理解方面的问题。
首先,历史硬伤显见。一是南北文化硬伤。源故事写道:“旦辞爷娘去,暮宿黄河边,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黄河流水鸣溅溅。”木兰辞别爹娘从家乡到黄河,朝发夕至,是典型的中国北方文化场景。而真人版《花木兰》开场是一片南方水田,体现的是南方文化。二是历史时间硬伤。木兰家住的福建土楼产生于唐宋元时期,现存最古老的土楼是福建省永定县湖雷镇下寨村的馥馨楼,建于公元769年的唐代,而木兰故事发生在公元384年到534年的北魏时期,比土楼出现早了几百年。另外,源故事中“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绝非围绕土楼转圈。三是服化道具硬伤。妆容上,源故事中“对镜帖花黄”,重点是“贴”,而真人版《花木兰》却是用颜料涂抹的“额黄妆”。此外,南北朝时期妇女唇妆样式以扇形居多,且古代中国大部分唇妆都是“樱桃小嘴”式风格,而非流行电影中的满唇妆。服饰上,魏晋南北朝时期平民妇女较为流行上着襦衫、下着长裙的服装样式。真人版《花木兰》中木兰相亲穿的紫衣却是旋转缠绕的穿着方式,应是多出现于西汉的曲裾深衣礼服。道具上,真人版《花木兰》中出现“椅子”也与历史不符,因为南北朝时期中国人多席地而坐,直到唐代之后才有胡床(即后代的“椅子”)传入。
其次,画蛇添足的“气”。花木兰之所以在中国受人敬佩而代代流传,因为她是普通女子替父从军,于平凡中体现了不平凡,精神品质格外感人。而真人版《花木兰》将木兰与众不同、强于男儿的生命特征归于身体内在的“元气”,使其成为具有隐藏技能的“超级英雄”,能在战场上有如神力、百发百中、飞檐走壁。可是何为“气”?木兰为何拥有“气”?电影语焉不详。所以,笔者认为“气”的设定不仅暴露出影片存在理解偏差和底气不足等问题,还折损了木兰来自寻常人家的平凡与伟大气质,让人难以产生精神情感的共鸣。
综上,全面审视迪士尼真人版电影《花木兰》的再编码情况后,笔者以为,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优秀中华文化应当做如下努力。
首先,讲好中国故事要主动打造属于中国独有的影视IP。一国范围内文学文本向影视剧转化原本就存在一定的“变异”,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化差异无疑会加剧跨文本形态、跨文化传播“变异”的产生。跨文本、跨文化影视作品直接诉诸于观众的视听,潜移默化地传导某种思想价值观念,真人版《花木兰》即是如此。在中国花木兰故事向迪士尼电影再编码过程中,美国文化的浸润性阐释会加剧“变异”的产生,扩大“变异”传播的范围。因此,在中华文化跨文化传播中,我们应该主动把握影视这一重要传播途径,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优势,主动对中国故事进行再编码,打造属于中国的影视IP。只有掌握跨文化传播的话语权,才能在文化碰撞中讲好中国故事。
其次,对中国故事适度的本土化再编码必须把握中华文化的内核与特色。真人版《花木兰》是对中国花木兰故事的想象性重塑,在美国奔放热情的文化语境中,木兰不再是内敛含蓄的中国古代女性形象,而是性格跳脱的女孩,她更能让美国观众获得身份的代入感,成为观众情感的投射对象。对此,笔者认为在输出中国故事时,应基于中国特定时代的价值观对中国故事进行适当的本土化再编码,使之能够同时获得中国本土观众与他国观众接受与认同的文化信息,进而实现语言的转换和文化的对接。
最后,传播中华优秀文化也可借用他国故事作为载体。真人版《花木蘭》虽然在文化再编码传播中存在诸多问题,甚至有“虚假东方化”的倾向,但我们无法否认其世界影响力。中国花木兰故事在真人版《花木兰》中为美国所用,其再编码处处可见美国对本土文化的自信和传播,这是一种外国故事的文化内化性改造与借用。在中华优秀文化跨文化传播中,讲好中国故事也可以创新故事载体,将中华优秀文化加载在美国或其他国家的故事上,形成借用他国故事传播本国文化的新途径。
中国的花木兰从诞生之初就一直承载着中华文化的期望,在不同的时空演绎着各样的故事。作为北地佳人,花木兰身后是华夏千年的沟壑、民族峥嵘的春秋。时至今日,被重新装扮的迪士尼花木兰从福建土楼走来,演绎着美国人眼中的“迪士尼公主”故事,用东方的形象向世界输出美国的文化价值理念。我们从中可以看出,由于主客观的原因,世界对中国故事仍然存在着某种误读。当下,讲好中国故事是时代的要求,也是每一个中国人的使命,笔者认为,我们应当推动中华优秀的文化资源突破跨文化传播的种种障碍,主动地、创新地讲好自己的故事,来引起世界文化的共鸣,彰显中华文化的力量。
参考文献
[1]张丽霞.花木兰形象的跨国变异研究——《木兰诗》与迪斯尼动画《花木兰》的对比[J].山西农经,2017(14):123.
[2]林丹娅,张春.性别视角下的迪士尼改编《木兰》之考辨[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06):156-163.
[3]峻冰.讲好中国故事是我们的使命担当[N].四川日报,2020-10-16(019).
(作者单位:湖北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