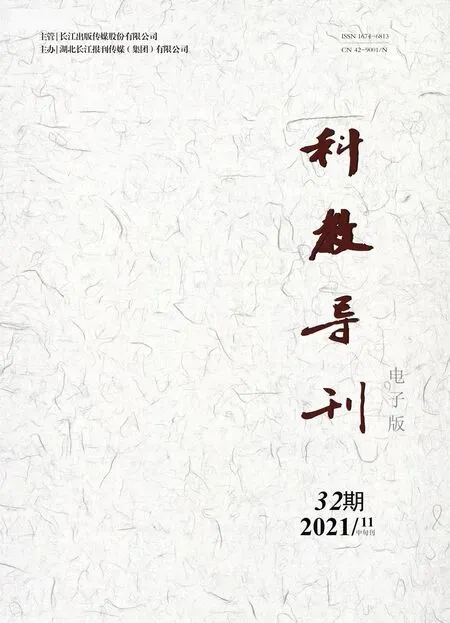代持股权强制执行问题研究
赵子健
(青岛科技大学法学院 山东·青岛 266061)
1 问题的提出
伴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商业投资形式更趋多元化,代持股权被广泛应用于企业投资和经营过程中,为市场注入活力的同时也出现了诸多问题,导致关于代持股权诉讼案件逐年上升,例如对股东代持协议性质、效力、隐名股东和名义股东责任承担、债权人保护等方面,且实践中法院判决也大相径庭。代持股权有其存在的正当性与合理性,也有对其规制的必要性,如何从程序上保障隐名股东的权益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2 基于判决支持与否的理论依据
2.1 支持隐名股东对抗金钱债权人的理论依据
2.1.1 “存在信赖利益”是适用商事外观主义的前置要件
《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26条规定实际出资人即隐名股东因名义股东处分股权的行为遭受损害时可参照适用善意取得制度。有学者便提出只有标的物为股权的交易方才属于“存在信赖利益”这一前置要件的范畴之内。[1]股权只是金钱债权人申请执行的财产内容之一,并非全部,从这点上看,股权并非信赖利益的保护范畴之内,因此金钱债权人对于名义股东的债权并不能优先于实际出资人即隐名股东的保护,不能适用《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26条参照使用善意取得制度之规定。因此,经法院审理认为代持股协议有效,金钱债权人的强制执行便无法进行。
2.1.2 隐名股东已显名
基于商事外观主义,即使代持股协议认定有效,但未办理股东变更登记,此时代持股协议并不具有外部效力,仅在隐名股东与名义股东之间产生具有相对性的合同效力,并不能对抗名义股东债权人的强制执行权利。但隐名股东显名化后,便产生了外部效力,基于隐名股东的权力外观便可以对抗外部债权人,突破了合同的相对性原理。
2.1.3 债权人非善意[2]
《公司法》第32条第三款规定未经登记,不得对抗第三人。《民法典》第65条规定法人的实际情况与登记的事项不一致的,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实践中对于上述规定不同的争论,其实质在于对“第三人”范围的界定。目前理论界倾向于将其解释为“善意第三人”,由此可纳入“信赖利益”保护之中。对于实践中第三人在与名义股东实施民事法律行为时明知其代持股权,便可认定第三人为非善意,不能基于公示公信原则主张信赖利益保护。隐名股东能够举证证明其明知,则名义股东金钱债权人无法越过隐名股东执行股权。
2.2 支持名义股东债权人强制执行的理论依据
2.2.1 《公司法》第32条优先于《民法典》适用
部分法官认为“第三人”不能仅将其限缩解释为善意第三人,还应包括恶意第三人,亦不能将标的物限缩为“股权”。如赵敏、尚桂兰二审案中法院认为名义股东金钱债权人与名义股东之间债权债务关系非股权交易也可强制执行。[3]基于商事外观主义,金钱债权人应当属于信赖利益保护范围之中。
2.2.2 代持股协议仅具有相对性,是债权债务关系,并非物权关系
基于的合同相对性原理,代持股协议本质上是隐名股东与实际股东之间就股权代持签订的合同,理应仅在合同双方当事人之间有效,其效力不可外溢。若隐名股东因名义股东处分股权行为遭受损害,只能依据合法有效的代持股协议主张返还投资款本息,不能直接对抗名义股东债权人申请执行的权力。另外,隐名股东基于各方面原因无法直接持有股权,在签订代持股协议时应注意到实施该行为时未来可能遇到的法律风险,该风险只能由其本人承担,而不可转移至善意第三人。
3 隐名股东另案生效裁判与执行异议的程序适用
一旦名义股东金钱债权人申请执行法院强制执行债务人财产,执行法院并非仅对标的物为股权的债务人财产强制执行,法院通过登记部门股权登记和公示信息对债务人名下包括但不限于股权的所有可执行财产均采取强制执行措施。基于商事外观主义原则,登记部门登记的权利人被推定为股权的所有人,因此,名义股东便具有外部效力,名义股东金钱债权人基于商事登记所产生的信赖利益应当给予保护。若隐名股东即实际出资人主要其股权为自己所有,应当承担举证责任。目前我国案外人的救济方式基于当事人的诉讼请求是执行行为或生效判决,主要分为第三人撤销之诉、对执行行为的异议和案外人对执行标的的异议制度。名义股东金钱债权人申请执行的生效裁判的执行范围并不局限于股权,因此,隐名股东作为案外人需要通过执行程序进行救济。
《执行异议及复议规定》强调效率是执行程序的价值追求,执行程序一般以形式审查为主。执行异议之诉作为执行阶段最后的权利救济方式,其作用在于纠正执行错误,刺破商事外观主义原则的推定表象,确定执行标的的真实权利人。在此程序中,不应当仅仅以形式审查结果排除真实权利人救济,必须要坚持实质审查,即首先要确定执行标的权利归属,其次要审查该标的是否能被强制执行。因此,对于执行异议之诉,不仅具有确认之诉的性质,还具有形成之诉的性质。
实践中较为常见的是隐名股东依据合法有效的代持股协议以名义股东为被告提出确认执行标的的权利。[4]从性质上说,确认之诉其立法初衷在于确认权利归属,并不当然的具有排除强制执行的效力,隐名股东想要通过确认股权诉讼达到排除强制执行的效果就必须同执行程序衔接,《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26条可进行适用。
3.1 案外人先于股权查封前获得完整股权,可排除股权强制执行
对法院执行行为存在纠纷首先要提出执行异议,执行程序追求效率价值,以形式审查为主,案外人权属已经过法院确权后便优于债权,应当保护实际权利人的利益,阻断强制执行,此即物权优先效力的体现。其要件应当满足:第一,显名化的要求即生效裁判确认股权归属,并经公司内部股东大会同意取得股东资格,此时便可阻却强制执行;第二,显名化必须在法院采取强制执行措施之前完成,否则当事人会以此规避金钱债权人申请强制执行的权利。此外,若案外人在查封股权之前已经完成股东名册变更但尚未办理变更工商登记,不可以股东名册作为对抗执行程序的依据,其法律依据在《执行异议与复议规定》明确了确认之诉仅具有阻却执行的可能性但不具有当然性,执行程序只在程序上执行不进行实体判断,所以对于非判决类执行异议依据不能对抗基于商事外观主义下的权利推定,其权利归属的实体判断需要在执行异议之诉中予以解决。
3.2 股权查封后,隐名股东只能通过执行异议之诉阻却执行
实践中经常有名义股东与隐名股东相互串通恶意起诉,损害金钱债权人的执行利益,因此,隐名股东获得法院生效法律文书时间应早于金钱债权人对名义股东强制执行时间,否则便不具有请求权基础。除此之外只能通过提起执行异议之诉解决执行纠纷。
实践中有的法官坚持执行效率原则,多倾向于金钱债权人,若隐名股东无法提供完整证据则不能对抗金钱债权人对名义股东的正当权利;还有法官对执行财产采取较为谨慎的态度,只要隐名股东提供相应证据能够使法官存疑便会中止执行。在代持股权强制执行中,要注意分阶段考察强制执行可否排除,保障各方合法权益。
4 余论
对于代持股权的性质存在有多种观点,如信托关系、代理关系、合同关系或无名合同关系等,在法律尚未明确前,对于其性质的认定更有必要,要综合考察权利义务设定,尤其是在商事活动中,顺应市场需要灵活多变,作为无名合同处理可能更能尊重商事主体的意思自治,保护商事实践活动的自由创新。对于股权代持的原因也各有不同,大体分为身份规避性和担保型。[5]要综合考察各种证据,有的代持原因并未以书面形式呈现,是否符合虚假意思表示或是无效情形,这就增加了对其认定的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