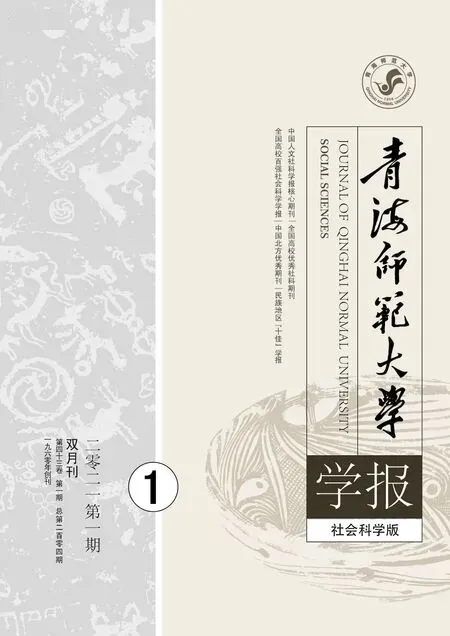“孔门之乐”的审美心理内涵及对道德教育的启示
苏 中,宋琛琛
(徐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江苏 徐州 221004)
《论语》乃至整个孔门系统都重视一个“乐”(音洛)字[1],如“不亦乐乎”(《论语·学而》)、“乐在其中”(《论语·述而》)、“乐而忘天下”(《孟子·尽心》)、“易直子谅之心生则乐”(《礼记·乐记》)、“无万物之美而可以养乐”(《荀子·正名》)、“寻孔颜乐处”(《程氏遗书》卷二上)。徐复观先生以为儒家道德理性人格至于“乐”始告完成[2],所谓“成于乐”(《论语·泰伯》),即成就一“艺术的人生”,此所以孔子独许曾点之志而喟然叹曰:“吾与点也!”(《论语·先进》)李泽厚先生在论及孔子的美学观时亦指出:在孔子看来,仁学的最高境界是一自由的、审美的境界,也就是“不改其乐”《论语·雍也》)的人生境界;[3]王建疆先生认为孔门之“乐”,表征了儒家人生境界修养美学的“内审美”特征,体现了人的精神慰藉和心理幸福,“当儒家的‘风乎舞雩’‘孔颜乐处’再次被国人想起之日,也就是中华传统‘乐感文化’真正复兴之时”[4]。学人们不约而同地指出了孔门之“乐”在审美人格养成和审美人生境界呈现上的重要作用。本文解析了“孔门之乐”的审美心理内涵,讨论了孔门之“乐”对当今青少年道德教育所具有的启示意义。
一、“乐”(音洛)的情绪特征
愉快和快乐是主要的正性情绪,是人们享受的重要来源。孟昭兰区分了生理上的快乐(愉快)和心理上的快乐(快乐),认为心理上的快乐才是真正的快乐。[5]其所谓愉快是指处于本能和感觉水平的快乐情绪,它来自生理需要的暂时满足,如感觉愉快、驱力愉快(内驱力释放);而快乐则附加着更复杂的心理上的含义。这些心理上的含义是由社会情境关系和人际关系的介入,从而在感受、体验上附加了更多的内容,如满意和幸福感。它产生于有意义的、建设性的活动和良好的人际关系中。美国心理学家弗洛姆认为,幸福、快乐感不仅仅是一种情绪状态,而且能提高人的心理功能,带给人日益增长的活力和健康。同时,它与生产性人格有关,是人的各种潜能得到实现时的一种状态。就是说,幸福感是心理健康的标志之一。[6]
快乐包含着一定的社会内涵,具有整体性和相对稳定性,会对人造成长期而稳定的影响。所以,有研究者认为快乐应被看成为一种心境或情感,[7]或者说是一种态度,一般来说,快乐感表示个体较少地感受到生活事件的压力,正向情感(positive affect)多于负向情感(negative affect)。这也就意味着,除了情感成分外,快乐也包含着认知的成分。[8]它不仅是一种情绪体验(如愉快、兴趣、惊奇、害羞等),还包含着乐观解释、希望以及行动。
二、孔门之“乐”的基本意蕴
“乐”(音洛)是儒家一个普遍而重要的概念。根据朱熹《论语集注》,“乐”字有如下几个音义项:(一)音岳,义为音乐,如“礼乐”;(二)音五教反,义为喜好,如“智者乐水,仁者乐山”;(三)音洛,义为快乐、高兴、喜悦,如“乐在其中”。考察《论语》二十一章,不计算同义字词句,如“莞尔而笑”、“说”(悦)等(据统计,“悦”出现16处,“喜”出现5处),仅“乐”(音洛)字就出现了16处,涉及十章。[9]另外,对下列“乐”字,徐复观先生同作“乐”(音洛)字[10]。杨伯峻先生将(十三)之“乐”字,除“礼乐”之“乐”字外,其余十个“乐”字均解作快乐之“乐”(音洛)[11],而朱熹注“骄乐”“宴乐”之“乐”为快乐之“乐”(音洛),“礼乐”之“乐”作音乐解,音岳,其余均作喜好之“乐”(音五教反)。这样一来,“乐”(音洛)字出现的次数或可增加到24处[12]。现将有关语句摘录如下,并择要予以疏解,以见孔门之“乐”的基本内涵:
(一)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论语·学而第一》)
(二)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同上)
(三)子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第三》)
(四)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论语·里仁第四》)
(五)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论语·雍也第六》)
(六)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论语·雍也第六》)
(七)子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论语·雍也第六》)
(八)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论语·述而第七》)
(九)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论语·述而第七》)
(十)“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论语·述而第七》)
(十一)闵子侍侧,誾誾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贡,侃侃如也。子乐。(《论语·先进第十一》)
(十二)人之言曰:“予无乐乎为君,唯其言而莫予违也。”(《论语·子路第十三》)
(十三)夫子时然后言,人不厌其言;乐然后笑,人不厌其笑;义然后取,人不厌其取。(《论语·宪问第十四》)
(十四)孔子曰:“益者三乐,损者三乐。乐节礼乐,乐道人之善,乐多贤友,益矣。乐骄乐,乐佚游,乐宴乐,损矣。”(《论语·季氏第十六》)
(十五)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论语·阳货第十七》)
另外:
(十六)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第八》)
(十七)(点)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论语·先进第十一》)
(十八)子之武城,闻弦歌之声。夫子莞尔而笑,曰:“割鸡焉用牛刀?”(《论语·阳货第十七》)
在(一)中,朱熹注云:说,悦,同。悦,喜意也。乐,音洛。(程子)又曰:“说在心,乐主发散在外。”《朱熹·论语集注》,齐鲁书社,1992;下同)按注③,所以“不愠”,是因为悦之深。上引《论语》首篇,开宗明义,三句都落到一个“乐”字上。按照中国古代经典义例及解经时所秉“微言大义”原则,《论语》的这一安排,绝非偶然,当有深意在焉,我们完全可以揣想孔门的用意所在。所以,《论语》乃至孔门系统都十分重视一个“乐”字的说法绝不是空穴来风。我们还可以接着说,上引《论语》句中,“乐”字是“文眼”,以“乐”开篇,提纲挈领,“乐”字成为统领整部《论语》的关键所在,是孔门的“正法眼藏”。(二)(四)(五)(七)(九)(十)(十七)诸则,集中体现了在“乐”的圆融中所呈现的诗意的人生境界,而这一“乐”(音洛)的境界标识着儒家道德理性人格的最终落实。借用佛家的说法,迦叶“拈花微笑”,得佛法“心印”;修得最上果位者,入极乐世界,得大自在,所谓“平安喜乐”“天花乱坠、满心欢喜”。孔门之“乐”,与佛家宗教体验是相似的,也体现为一种精神慰藉和心理幸福。不过,孔门之“乐”乃由“美善统一”,特别是“仁和乐(音岳)的会通统一”而来,所谓“尽善尽美”,“即是艺术与道德在其最深的根底中,同时也即是在其最高的境界中,会得到自然而然的融合统一,因而道德充实了艺术的内容,艺术助长、安定了道德的力量。”[13]对此,朱子体认最深,他在解释上引(十七)孔子何以嘉许曾点之志时说:“曾点之学,盖有以见夫人欲尽处,天理流行,随处充满,无少欠阙,故其动静之际,从容如此。而其言志,则又不过即其所居之位,乐其日用之常,初无舍己为人之意。而其胸次悠然,直欲天地万物上下同流、各得其妙,隐然自见于言外。视三子之规规于事为之末者,其气象不侔矣。故夫子叹息而深许之。”[14]不过徐复观先生认为朱子以道德精神的最高境界即仁德精神状态来解释在曾点身上所呈现的人生境界及孔子深许之意,对孔子及孔门所重视的艺术精神体认未及,尚未说透。曾点此处所呈现的其实是更高一层的人生境界,即艺术境界,它本是可以与道德境界相融合的。[15]这就把孔子发现的艺术精神完全指明了,即孔子仁的最高境界,实际上就是一审美的境界,也就是“艺术的人生”境界,换言之,也就是“乐”(音洛)的境界。后来冯友兰先生将人生境界划分为“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16],宗白华先生提出艺术之“灵境”[17],都有这个意味。
孔门之乐的人生境界之所以不同于庄子之“乐”,是因为孔子“乐”不是脱开人伦世俗,而是在“爱人”“行道”追求努力中获得的,背后潜藏着对道德修养、人伦天下的深沉之忧;超越的乐和沉潜的忧共同刻画了孔子的人生境界。因为忧,所以才努力践行仁,也因为“为仁”,才自然得到超越性的真乐。可以说,忧与乐是仁的两端,其圆融对待,才是仁的最高境界。这是孔门之乐的深刻之处。[18]
三、孔门之“乐”的审美心理内涵
胡伟希先生曾用“存在认知”概念来解释朱子对孔门之“乐”的运思。在胡伟希先生看来,存在认知是论证人伦道德之所以当然的思考方式,不同于一般对自然法则的认知,类似于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所谓“高峰体验”概念,朱子所体认到的道德境界,就是在这一认知状态下达到的,所以它同时是一种极乐的境界,也就是理学家们津津乐道的“孔颜乐处”——“圣人之乐”。这种“心体浑然”的境界,既是仁的最高道德境界,也是“乐”的境界。“因为在这种境界中,人已自觉到他与天地合一,这种人与天地合的境界,必然带来心灵的陶醉与美感。因为在这种状态下,他已感觉到超越了自然律强加于他的种种限制,换言之,人发觉他从有限走向了无限。”[19]这也就是自由的、审美的境界,也就是“艺术的人生”境界;海德格尔所谓人“诗意地栖居”。
孔子反复强调要使“为仁”成为人们内心情感上的自觉要求,而不是出于强制(这于当今我们对道德理性主义的反思和批判具有启示意义)。在上引(六)中,“知”“好”“乐”可以说是循序而进的三种境界,而“‘乐’——外在的规范最终转化为内在的心灵的愉快和满足,外在和内在、社会和自然在这里获得了的统一,这也就是‘仁’的最高境界。它不只是认识、语言,不只是规范、善行,而是美,艺术”[20]。对此,徐复观先生反复解释道:“人仅知道之可贵,未必即肯去追求道;能‘好之’,才会积极去追求;仅好道而加以追求,自己犹与道为二,有时会因懈怠而与道相离:到了以道为乐,则道才在人身上生稳了根,此时人与道成为一体,而无一丝一毫的间隔。因为‘乐’(音洛)是通过感官而来的快感,通过感官以道为乐,则感官的生理作用不仅不会与心志所追求的道发生摩擦,并且感官的生理作用已完全与道相融,转而成为支持道的具体力量。此时的人格世界,是安和而充实发扬的世界。”[21]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徐先生将“成于乐”(音岳),等同于“不如乐之者”的“乐之”(音洛),而认为儒家道德理性人格至“乐”(音洛)始告完成。《论语》中对这一人生进阶有更为具体的描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这种“从心所欲,不逾矩”的状态,实际上就是现代西方人本主义心理学家所谓“自我实现了的人”,也就是实现了潜能的“机能完善的人”的状态;而这一“美好人生”过程与儒家审美的人生境界(乐)是会通同一的。张之沧在阐述福柯(M.Foucault)的生命美学思想时写道:“没有审美就没有人生。”“人类生存的真正目的并不是去寻求那旨在约束自身的真理、权力地位、道德荣誉,而是旨在成为自身命运的主人,满足自身的审美愉悦和生命快感,将生命活动提升到艺术高度,成为人类特有的审美实践和审美属性。”“美既是智慧的人类在其艺术般的生活技巧和特殊风格中造就和展现出来的感性形式或知觉属性,也是其追求最高自由境界的一种自身技巧或自身实践”[22]。
四、孔门之“乐”对道德人格养成的意义
探讨青少年道德发展一般包括对是非标准的认知、行为和情感方面,以及人格等。其中,道德情感和青少年的认知与社会性发展交织在一起,对青少年道德觉悟、道德责任、道德行为具有深刻影响。当今,发展心理学家认为,“移情、同情、崇高、自尊等积极情感与生气、暴怒、羞耻、内疚等消极情感都有利于青少年的道德发展。强烈地感受到这些情绪后,青少年会在它们的影响下做出符合是非标准的行为。因他人违反道德标准而出现的移情、羞耻、内疚、焦虑等情绪在发展早期就会出现,并且贯穿于整个童年期和青少年期的发展变化中。这些情绪为青少年形成道德观提供了自然基础,它们既可以把青少年引向道德事件,也会激发他们积极地关注这类事件”[23]。古希腊思想家亚里士多德强调情绪陶冶对德行培养的重要性,在他的思想中,“德行不只是有关适当行动的品格状态,并且也是关于各种情绪及苦乐的品格状态”。[24]孔子也说“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以沙夫茨伯里、哈奇森和休谟为代表的西方道德情感主义(moral sentimentalism)坚持道德的情感本质,认为个人本性即情感才是道德的基础,把伦理的心理根柢从理性认识的领域移植于心灵的情感领域,直接与美感相邻。在意志和行为的领域里,善表现为美;善基于自然天赋的完美发展,有如美基于多中的谐和统一;善正如美给人以满足、给人以幸福;善又与美一样,是人植于最深本质中的原初认可对象、“审美力”是伦理的能力,也是审美的能力。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言,伦理学就是美学。在石中英先生就孔子的“仁”多包涵的丰富的情感意义,特别指出:加强道德情感教育对当今教育,特别是个体道德发展和社会道德重建具有心理基础作用。[25]
在世俗的生活中,人们很难以道为乐,如孔子所云:“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论语·子罕》)。将道德归结为普遍的律令,本身就不能令人满意,况且用规则来规范人,可能会发展为对人的压迫,甚至戕害[26]。道德理性主义因此多被诟病。怎样才能做到“说之不以道,不说也”(《论语·子路》)、“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孟子·告子上》)?孔子认为可以通过艺术(在孔子主要指音乐)来通达人心。正如《荀子·乐论》所云:“乐(音岳)者乐(音洛)也。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在孔子看来,乐(音岳)是养成或助成乐(音洛)的重要手段。“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说的都是这个道理。用悦乐的情怀和审美的体验去成就个人道德,去实现政治理想,这就是孔子美学的精华和魅力所在。[27]通过审美来造就人,也是康德、席勒以来西方美学家的一贯思想。康德曾经指出:“美是道德的象征”。“美使人愉快并提出人人同意的要求,在这场合人的心情同时自觉到一定程度的醇化和昂扬,超越着单纯感官印象的愉快感受,别的价值也按照着它的判断力的一类似的规准被评价着。”[28]审美活动对道德发展的意义就在于,审美判断“所引起的感觉和道德判断所引起的心情状况有类似之处”。所以“鉴赏使感性刺激渡转到习惯性的道德兴趣成为可能而不需要一过分强大的跳跃,设想着想象力在它的自由活动里对于悟性是作为合目的性地具有规定的可能性,并且甚至于教导人在感性的对象上没有任何感性的刺激也能获得自由的愉快满足”。[29]席勒更是认为“人是审美教育的产物”“道德状态只能从审美状态发展而来”“要使感性的人成为理性的人,除了首先使他成为审美的人之外,别无他途”。[30]根据黑格尔的思想,这和人的本质具有精神的理性方面有关,即人要求着并也能够脱离其直接性和本能性而向着普遍性提升,所以人需要教化。而“能够采取审美的态度,就是已经得到教化的意识的要素”。[31]
上引(三)(八)(十四)(十八)诸则,集中表现了音乐对道德人格养成的重要作用及效果。对于此点,徐复观先生进一步分析说:“礼的最基本意义,可以说是人类行为艺术化、规范化的统一物”“音乐当然含有规范的意义,但礼的规范性表现为敬和节制,……乐的规范性则表现在陶镕、陶冶,这在人类纯朴未开的时代,容易收到效果,但在知性活动已经大大地加强、社会生活已经相当地复杂化了以后,便不易为一般人所把握,也是一般人在现实行为上无法遵行的。”[32]孔子反复申明“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论语·颜渊》),始终把规范性和艺术性的统一作为礼的基本性格,“礼乐并重”,且把乐(音洛)安放在礼的上位,认定乐才是一个人格完成的境界,建立了“为人生而艺术”的典型。黑格尔曾正确地指出:审美具有令人解放的性质。孔子以艺术(音乐的“和”“中”)为道德教育之本,并以“艺术的人生境界”(乐)为仁学的最高境界,正如李晓林女士所言,“把道德放在美学的根基上,意味着道德获得了超越和自由的品格,意味着道德不再是对生命的戕害”[33]。在此,我们不由地联想到福柯“生活是艺术品”的思想。他说:人能通过审美经验改变自己,“从自我不是被给予的观点出发,我想只有一种实际的结果,即我们必须将自己创造为艺术品”。[34]个体通过“自我技术”(Technologies of the self)构成为主体(Subjectivity),“‘自我技术’允许个体以自己的方式,或通过他人的帮助,对自己的身体、心灵、思想、行为、生存方式施加影响,以改变自己,达到某种快乐、纯洁、智慧、美好、不朽的状态”。[35]这种状态不就是“乐”(音洛)的境界么,而其所谓“自我技术”,与儒家修养美学所谓“修齐治平”自我成就何其相似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