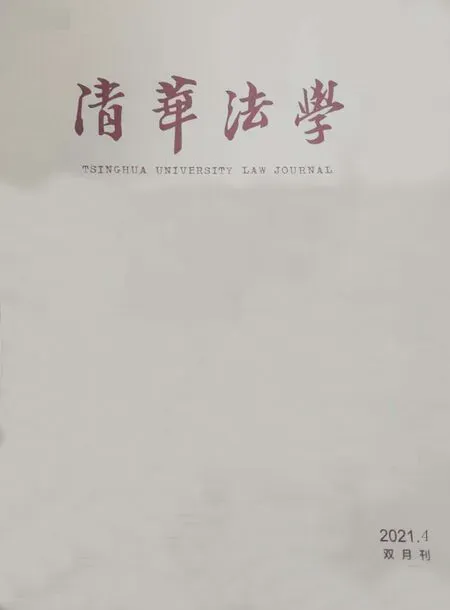法学交流的实践理论
朱明哲
一、导 言
中西法学交流一直是我国法学界研究的重心,其中关于法律移植的作品可谓汗牛充栋。〔1〕代表性文献包括何勤华:《法的移植与法的本土化》,载《中国法学》2002年第3期,第3-15页;李秀清:《中国近代民商法的嚆矢——清末移植外国民商法述评》,载《法商研究》2001年第6期,第126-140页。最近,更多的关注放在了对具体制度或者概念的移植进行分析上,参见陈新宇:《继受与变革——以日本过渡刑律下“断罪无正条”与“不应为”的变化为中心》,载《清华法学》2008年第3期,第107-118页;李启成:《法律继受中的“制度器物化”批判》,载《法学研究》2016年第2期,第191-208页;鲁楠:《正法与礼法——慧远〈沙门不敬王者论〉对佛教法文化的移植》,载《清华法学》2020年第1期,第28-51页。我国在20世纪先后移植欧洲法典、苏俄法律,改革开放后又为了加入WTO而大规模参考外国民商法修订法律,这样的历史经验使得理解我国现行法几乎离不开对制度移植的研究。〔2〕参见孙宪忠:《中国近现代继受西方民法的效果评述》,载《中国法学》2006年第3期,第166-174页;王晨光:《法律移植与转型中国的法制发展》,载《比较法研究》2012年第3期,第25-35页。除了制度之外,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成果重视中西交流在彼此法文化演变中的作用。〔3〕参见李秀清:《中法西绎》,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2015年版;于明:《晚清西方视角中的中国家庭法——以哲美森译〈刑案汇览〉为中心》,载《法学研究》2019年第3期,第190-208页。研究的对象不再是立法文本,而是法学知识与法文化的形成过程。随着研究素材的丰富和深入,人们开始更加重视具体历史时刻的中国现实对制度与知识形成的塑造作用。单向的“移植”或“继受”也让位于更强调互动关系的“交流”。同时进入研究视野的还有投身于法学知识交流的个人与他们的社会关系和策略性选择。〔4〕比如刘星:《民国时期的“法学权威”——一个知识社会学的微观分析》,载《比较法研究》2006年第1期,第20-35页;朱明哲:《中国近代法制变革与欧洲中心主义法律观——以宝道为切入点》,载《比较法研究》2018年第1期,第155-170页;陈霓珊:《民国民事立法中的“保守”与“激进”——基于爱斯嘉拉本土化立法方案的考察》,载《近代史研究》2018年第3期,第141-154页;朱明哲:《法学知识的跨国旅行——马建忠和19世纪末的法国法学》,载《政法论坛》2020年第1期,第177-191页。
对于法学知识传播的研究同时也暴露了缺乏方法论反思和忽视社会理论的缺陷。如果说社会理论已经在近年成为研究当代中国法实践的一种重要范式,〔5〕参见泮伟江:《超越“错误法社会学”:卢曼法社会学理论的贡献与启示》,载《中外法学》2019年第1期,第37-53页;陆宇峰:《社会理论法学——定位、功能与前景》,载《清华法学》2017年第2期,第93-109页。那么它在法史学和比较法上的应用还较为少见。〔6〕从知识社会学角度探索我国法学现代化的代表性成果,参见张生:《王宠惠与中国法律近代化——一个知识社会学的分析》,载《比较法研究》2009年第3期,第123-138页;同前注〔4〕,刘星文。其结果是即便人们意识到有必要把法学知识的传播和形成作为一种事件来研究,却缺乏足够成熟的分析框架从当时的人物与机构之间的关系之中去理解各种策略性选择,并最终呈现甚至评价这一事件的结果。
本文试图用布迪厄的实践理论构建一种围绕“法学场”展开的分析框架,以期为现有关于法学知识传播的讨论增添新的可能。目前,我国社会理论法学界较为关注的是卢曼、哈贝马斯、福柯等人。这种社会理论视角的共同点是有助于超越规范与事实的二分法。其中,卢曼以“意义”为核心范畴,展现法律发展的演化过程。〔7〕参见同前注〔5〕,泮伟江文,第51页。哈贝马斯以“商谈理论”为民主法治国条件下政治和法律决定的合法性找到程序基础。〔8〕参见同前注〔5〕,陆宇峰文,第101页。福柯则试图揭示法律所构建并维系权力关系的微观运作。〔9〕See Bertrand Mazabraud,Foucault,le droit et les dispositifs de pouvoir,Cités,n°42,2010,pp.127-189.相比之下,布迪厄视实践活动为不同的行动者在社会场中的象征性竞争,他们根据自己所掌握的社会资本总量和各种不同资本的比例关系,选择不同的行动策略并展开互动。社会场为这种互动提供了前提,又不断地为这些持续性的活动所塑造。〔10〕See Pierre Bourdieu&Loïc Wacquant,An Invitation to Reflexive Sociology,Polity Press,1992,p.101.布迪厄的实践理论把法学知识的形成、理解、传播视作在特定社会关系之中的实践活动,从而呈现法学交流动态的一面,并理解各种不同行动者的所作所为。最近已经有研究者有意识地采用资本、习性和场域等概念分析法治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人物或事件。〔11〕参见朱明哲:《从民国时期判例造法之争看法典化时代的法律场》,载《政治与法律》2018年第11期,第127-142页;陈征楠:《社会理论视野中法律移植困境的重释》,载《法学》2020年第8期,第74-85页;王人博:《张之洞:一个法政改革者的行动逻辑》,载《法学评论》2021年第1期,第175-196页。不过,从方法论角度做系统反思的努力,目前尚付之阙如。本文致力于把“法学场”概念化,作为未来研究的可能分析框架。
下文将首先介绍研究法学交流的三种范式,并重点讨论实践反思范式的可能贡献。然后,本文将通过特殊利益、习性、等级秩序等关键概念阐述“法学场”的构成。最后,本文利用里昂中法大学作为实例展示实践反思范式的应用。
二、理解法学交流的三种范式
(一)继受移植范式
我国研究法律移植的最主要范式是将其视为一种现代化手段的继受移植范式。移植范式首先阐述了一种师生之间的尊卑关系。王泽鉴就在演讲中承认:“我个人学习的经验就是台湾继受德国民法的一些过程。”〔12〕王泽鉴:《德国民法的继受与台湾民法的发展》,载《比较法研究》2006年第6期,第3页。接着,他回忆起在学术生涯中始终要求自己坚持在德国学到的法律解释学、教义学、比较法等研究方法。演讲继续阐发德国法的制度和方法如何优秀,继受德国法又能有如何的好处。诚然,留学生负笈异乡、寻访名师,理当以谦虚的态度向老师学习。但这种尊卑关系中的学生往往进一步把他们学到别国法学知识普世化、理想化为一种可以在母国适用的科学真理。在这种叙事之中,知识在中心国家完成生产和包装,原封不动地送到处于知识版图边缘的地区,寄望于好学生们以“原汁原味”的方式再现。人的主体性缩减到只剩下充满敬畏地学习先进法学知识的学生形象。中心国家知识界内部的竞争、继受者自身的思考和阐释、不同继受者之间的互动都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中。
与这种被动接受的态度相关的则是稍微更看重有意识选择的主动性的“法律移植”。〔13〕See Alan Watson,Legal Transplants:An Approach to Comparative Law,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1993.正如“移植”一词所暗示的,外来的法律不一定真的能发挥移植者所期待的作用,它终究会在与原有制度、知识、文化系统的互动中形成一种移植者自己也无法预料的新制度。〔14〕See Gunther Teubner,Legal Irritants:Good Faith in British Law or How Unifying Law Ends Up in New Divergences,61 The Modern Law Review 11,11(1998).同样的观察也适用于对法学知识的传播。外国学生并不仅仅是课堂上所教授的法律学说中立、被动的接受者。他们有自己的抱负和眼光,了解自己祖国的过去与未来,并根据这些因素挑选和重述他们所接触到的学说。当人们用“移植”替代“继受”时,似乎已经承认在中心学习后回到边缘的法学家的能动性,因为他们可能已经根据本地的实践选择了最适宜的商品。而且,他们移植而来的学说也将在新的社会中发挥不一样的作用。
然而,无论是被动的继受,还是主动的移植,都在两个方面无法满足历史—哲学探问。首先,它们预设了一个法律文明比另一种优越,一个国家比另一个更文明。这一范式最重要的特点是强调不同法学知识的等级秩序,法治文明程度更低的国家只能向更文明的国家学习。它不但粉饰了继受国的知识,也粉饰了作为知识交流之冰人的留学生和教师,让他们通过教与学所能实现的社会目标隐而不彰,并忽略了他们的动机、策略、行动结果。其次,它们都假设知识生产与继受国经验无关。当一个社会问题在别国已经有更好的解决方案的问题时,就应该向别国学习,从别国引进一个更“先进”的法律制度和学说。这种解决方案只能在中心设计,在边缘实践。继受国的现实虽然可以为是否移植、如何移植提供参照借鉴,但是法学知识本身在文明等级较高的国家的法学院中,仅仅依据事物的本质和形式逻辑生产出来。
(二)殖民批判范式
法学交流除了有它作为现代化之桥梁、文明互鉴之实例的光明面以外,还有其作为殖民征服的阴暗面。〔15〕关于比较法中殖民主义心态的一般性反思,参见Upendra Baxi,The Colonialist Heritage,in Pierre Legrand&Roderick Munday eds.,Comparative Legal Studies:Traditions and Transition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pp.46-75。80年代中期以来,受批判法学启发,比较法学的视角从民族中心转向自我批判,从法律中心转向对法律的批判,从关于法律简单明了的陈述转向对复杂和暧昧的观察。〔16〕See Gunter Frankenberg,Critical Comparisons:Re-thinking Comparative Law,26 Harvard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 411,411(1985).于是,一种聚焦于法学交流和法律移植之负面效应、揭露进步—现代性表象背后之社会现实的范式也就随之而来。这种范式强调,在19世纪的“文明等级”话语中,占据支配地位的是一种师心自用、以产生自中心国家之法律与法学去教化和征服边缘国家的心态。〔17〕参见[法]埃马纽埃尔·图尔姆 茹阿内:《承认的国际法》,朱明哲译,载《国际法研究》2017年第6期,第97-114页。就是在这种话语中,西方完全垄断了主体性,并通过把东方贬低为没有法律,或者只有很拙劣的法律的国度,正当化西方通过军事征服、强迫东方进入世界市场所取得的优势地位。〔18〕See Gerrit W.Gong,The Standard of Civilization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Clarendon Press,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4,p.98.
作为一种后殖民批判的“法律东方主义”提出了一种颇有启发的视角。〔19〕See Teemu Ruskola,Legal Orientalism,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3.它指出,一套关于法律的叙事创造出了“东方”与“西方”的差别,并在此过程中把前者变成认知的客体、言语的对象,赋予了后者认知与言语之主体的地位。从表面上看,对东方法律制度感兴趣的西方法学家正在通过比较研究建立关于人类法律经验的普遍知识。然而,这一历史进程的实质后果是从学理上确证了东方社会专制、落后的状态,并在比较中进一步确立了西方社会文明、先进的形象。在此过程中,西方的学者、学术和政治机构掌握了设置研究议题、观察与分析方法、价值判断的标准等一系列学术权力,东方的人物与机构只能遵循这些标准,并提供经验、素材。殖民主义不仅否定了被殖民地区的政治自主,更否定了殖民地人民在认识论上的自主。〔20〕See Boaventura de Sousa Santos,Epistemologies of the South,Routledge,2014,pp.40-42.不同于强调西方法学在帮助落后国家改造传统社会、实现现代化之工具意义的传统继受移植模式,法律东方主义揭示了“现代”与“传统”分类法背后、内在于全球秩序的结构性不平等:原本征服者—失败者之间的关系在西方的知识体系中变成了文明—不文明的关系,并进一步粉饰为教化者—学生的关系。
“权力—知识—话语”的重叠关系是批判殖民范式的贡献,但是,对于批判地理解中西法律交流和比较法的历史,它尚有缺陷。〔21〕针对法律东方主义本身实践后果的反思,参见鲁楠:《功能比较法的误用与东方主义的变异——从络德睦的〈法律东方主义——中国、美国与现代法〉谈起》,载《比较法研究》2017年第6期,第187-198页。本文的批判主要聚焦于东方主义的认识论问题。目前,这种范式大部分把东西方法律的相遇描述成一种单向叙事。如果把每一份文本当作作者对讨论的参与,那么前述关于东方法律的叙事本来应该是由来自各方的行动者共同书写的一场对话,而法律东方主义只记录了这场对话里西方法学家对自身优越性的建构,东方法学家的回应不见踪影。批判殖民叙事把“殖民地”视作一个整体,并简单地把它视作受害者,忽略了不同的人物和机构在关于殖民地的现代法学知识建立过程中不同的潜在或现实利益。类似地,它还简化了“西方”,忽略了参与对话的西方法学家对东方法律的认识和态度的多样性。过于简化、平面的“压迫者—受害者”区分和以去殖民化为目的的宏大叙事遮蔽了复杂多样的社会实践。而揭示宏大叙事背后的暧昧的多样性本应该是批判理论和知识考古学的贡献。“交流”所展现的应该是不同行动者的选择与互动,今人不能在只处理了一些经过选择的片面材料后就急于进行价值判断。
(三)反思实践范式
上述两种视角假设了主体—客体的二元对立,既忽视了双方的互动,又忽略了每一个行动者与其所处的社会条件之间的互动。在二元图式之下,要么是一方已经独立生产了规范和知识,要么是一方强加、另一方只能被动接受。最近,逐渐有研究关注到了继受国的地方经济、社会、政治现实在法学知识传播过程中的决定作用,强调多元的“中心”知识在“边缘”的重组和创新。〔22〕See Assaf Likhovski,A Colonial Legal Laboratory?Jurisprudential Innovation in the British Empire,67 America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Law 1,1(2019).不过行动者自身的利益仍然是知识传播研究中缺少的一块拼图。
在对法律移植的研究中,不同行动者根据自身利益采取的策略性行动所形成的互动本应得到更多重视。法律移植作为一种通过立法实现的变革,意味着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法律秩序中加入一些外来的改变,必然会引起不同观念和利益之间的对峙、冲撞、整合。在此过程中,法律精英发挥着其他群体所无法企及的作用。〔23〕参见刘星:《重新理解法律移植——从“历史”到“当下”》,载《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第24-36页。规范和知识的移植反过来也影响着法律精英在社会中的地位:“通过他们与所移植之外国法之间的关联,个人和群体可以创造出他们原本所缺乏的社会资本。外国学位、专业知识以及国际联系都可以用于在国内争取位置。”〔24〕Jonathan M.Miller,ATypology of Legal Transplants:Using Sociology,Legal History and Argentine Examples to Explain the Transplant Process,51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Law 839,851(2003).他们不必然出于自利和功利算计而移植规范和知识,甚至可以说大部分人认为所移植的学说能够为国家谋富强、为人民求解放。但从客观上讲,移植的努力是一种终将变现的投资。此外,对规范和知识的移植也可以为一个接受移植的国家或者机构提供合法性。〔25〕参见同上注。希望通过法律现代化实现不平等条约撤废的近代中国法律人对此再清楚不过。
社会理论法学可以提供一种不同于继受和批判的新范式。〔26〕参见同前注〔5〕,陆宇峰文,第99页。实际上,在针对法律全球化的研究中,已经涌现出了以社会理论法学为分析框架的作品。〔27〕See Gunther Teubner,Global Bukowina:Legal Pluralism in the World-Society,Global Law without a State,Dartmouth Publisher,1996,pp.3-28;高鸿钧:《法律移植:隐喻、范式与全球化时代的新趋向》,载《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第116-129页;鲁楠、高鸿钧:《中国与WTO:全球化视野的回顾与展望》,载《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第5-17页。正如前两种范式,受社会理论法学启发的新范式也试图从对具体的个人、机构、事件的研究中总结出一种关于法学交流的一般观念。微观上,这种新范式应当能够解释具体事件中行动者的实践逻辑。宏观上,它能够提出一种关于社会结构与法律、法学之间的一般性理论,进一步揭示不同社会领域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28〕参见同前注〔5〕,泮伟江文。
于是,作为社会理论法学在法学交流研究中的应用,一种新范式呼之欲出。这种新范式强调行动者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反思实践。它是一种实践范式,因为它把法学交流视为具体社会空间中的一种实践。和所有的社会实践一样,每一次学术交流都由具体的人在具体的时间、空间之内的互动形成。人们通过学术交流沟通、学习、探索、发现,也藉由学术交流交换、协作、对抗、斗争。在所有这些互动中,行动者投资着自己的社会资本,也在换取其他形式的社会资本。每一个行动者都出于某种具体的目的参与实践并不断进行决策,每一个决策都会产生现实后果。创造者固然可以出于文明教化或贬低征服的目的生产法学知识,传播者固然也可以出于祖国现代化或现实利益的需求移植法学知识,知识传播的过程固然也不妨形成一种文明话语的霸权。但主观的思虑都不可能支配传播的过程或决定传播的效果,客观的后果也不可能自上而下精心设计。构成历史的毕竟是一系列事件的碎片,而不是事先的构想。最后,每一位行动者在任何一个决策时都不得不充分考虑其他行动者的决策,却永远不可能确定地知道所有行动者的决策,而每一个行动的后果又最终取决于其他所有行动的合力。任何个体的主观意愿对于他的决策可能具有决定性,但是对于其决策的后果却无足轻重。无论决策的主观意愿是什么,决策的结果终将呈现为决策者客观、可以衡量的利益。
这是一种反思范式,因为它试图呈现两对反思性关系(reflexivity)。第一对反思性关系存在于社会的本相(reality)和表象(representation)之间。作为表征的文本背后,隐藏着一系列社会实践的现实。〔29〕参见王明珂:《反思史学与史学反思》,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8-29页。任何一种社会实践都发生在一个具体的社会条件之中,必须有一系列独特的政治制度、经济条件、生计状况的客观现实让该实践得以发生。与此同时,又必须存在一套认知方式、心智结构、知识体系为该实践及其所得以发生的客观现实赋予意义。客观现实所构成的本相让关于这些事实的认识与叙述所构成的表象得以存在;同时,表象又合理化或批判或否定本相的存在,并通过行动者基于这些判断所进行的实践创造出新的现实。〔30〕参见同上注,第50-76页。第二对反思性关系则存在于具体实践及其所发生的社会空间之间。包括了本相和表象的社会空间构成了行动者进行决策的外在条件。在每一个特殊的历史断面中,社会空间都限制了决策的可能性。但是,每一个社会空间的现状都无非是行动者之间持续不断的策略行动在此刻的凝结。当聚合于这一刻的社会条件为新的社会实践创造可能、施加限制的同时,它们也为新实践所创造的新条件打开了大门。结构/现实和实践/表象之间并不存在决定论的关系。它们时刻处于动态的对话和变化之中。
三、社会空间中的实践
(一)法学交流的时间、空间与行动者
继受移植范式下对西法东渐的传统研究忽视了空间和时间的意义。它名为历史,却往往把“西方”与“东方”分别理解成统一、有确定内核、可以用少数几个重要理论或者概念代表的质点,或是永恒不变地存在于彼岸,或是仅仅在其内部沿着一个确定的辩证法逻辑自我展开。无论是东方继受西方还是现代取代传统,事件凝结于时间中一个具体节点。在这种同质化的史观下,得到关注的只有文本,只有表象。具体的历史时刻、地理空间、经济社会状态现实并不重要,互动所创造出来的新现实也不重要。或者说,这是一种抽象、空洞的研究范式:“它承认空间却否定了位置,承认时间却无视其流逝。”〔31〕Pierre Legrand,Jameses at Play,65 America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Law 1,2(2017).殖民批判范式更加严肃地看待空间、时间和行动者。复数的殖民者在不同的殖民地创造了各种不同的知识,这些知识在不同的历史条件和不同的地点受到了不同的人群的不同的接受,于是又产生了复数的殖民故事、复数的现代性。〔32〕See Filipe Carreira da Silva&Moónica Brito Vieira,Plural Modernity:Changing Modern Institutional Forms—Disciplines and Nation-States,53 Social Analysis 60,60(2009).更重要的是,批判范式引出了对什么是时间、空间、人群的思考。
但是,实践反思范式下,法学交流的研究才可以从对文本的重述真正转变成一种历史社会学的工作。“法学交流中发生了什么”这个老问题被重述为两个新问题:参与法学交流的人在什么社会结构中决策?他们的决策又如何进一步改变了所处的结构?在一个由不同行动者、他们所占据的位置、彼此之间的关系形成的社会空间中,社会理论关心的是他们如何根据对自己在此间的位置的认识展开互动,永无休止的互动又如何改变他们所处的位置,并通过这样对人、象征性的位置、社会动力学的观察,最终揭示法学知识传播和法学场之间的反思性关系。〔33〕参见同前注〔10〕,Pierre Bourdieu&Loïc Wacquant书,第101页。每一个社会空间中都存在着客观真相和对外界创造的表象之间的差异;每一个场都会有参与其实践的局内人和只能从外部观察的局外人;每一个人也都会在人生的某个阶段成为某个或某几个场的局内人和其他场的局外人。局内人或多或少掌握了一些该空间中既稀缺又分配不平等的资源,同时必须受制于其竞争规则,并不断孜孜以求地追求竞争中的特殊利益。局外人则与这些特殊利益绝缘,甚至认识不到其中的利益和规则到底是什么,也就无法认识到参与这场竞争的意义何在,从而也就不会具备成为局内人所必须的习性。〔34〕参见同上注,第98-100页。
以学术场为例,学术界同时为局内人对自己关于学术场本相之知识的自我隐瞒和放大本相与表象之间的差异提供了其他社会场无法比拟的自由和制度支持。〔35〕See Pierre Bourdieu,Homo Academicus,in Peter Collier e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8,p.32.其结果是学术场的本相与表象之间的巨大鸿沟既遮蔽了发生在其中的象征性斗争,又让这一斗争之中无人必须出局,从而可以不断延续:“在这种形式中,同时并存这一切让人们无法理解的客观事实和对这些事实的否定。正是它们让那些最缺乏象征性资本的人也可以在这场人人为我、我为人人、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斗争中生存下来。这些局内人同时是彼此的竞争者和顾客、对手和法官,而他们彼此争斗的目的是决定社会场的真相和价值,也就是它象征性的生与死。”〔36〕同上注。
每个由特殊利益和习性组成的社会场都是整个社会宇宙的一个切面。每个行动者都处于不同的社会场中。所以,学术场的参与者同时也参与其他的社会实践,他们在其他场中获得的社会资本当然也可以用于学术场的投资,反之亦然。然而,相比于其他社会场,学术场的维系几乎全然取决于行动者对于科学独立和卓越的信念,以及他们以科学的名义要求局外人接受他们判断的能力。〔37〕参见同上注,第27页。换言之,学术场中的悖论就是行动者必须在使用各种社会资本逐利的同时否定他们的逐利竞争,也就是表象对本相公开的自我否定。局中人留下的文字记载只能提供他们集体创造出的表象,研究者必须借助各种材料发现他们象征性斗争的本相——亦即他们所掌握的资本、所竞争的特殊利益、让法学场得以存在的生存心态、投资策略与深层结构之间的反思关系。为了尊重空间的位置、时间的流逝、个人的主体性,必须从过去的行动者所留下的文字线索中,找到那些他们不愿说出的东西。〔38〕Marc Bloch,Apologie pour l’histoire ou métier d’historien,Paris,Armand Colin,1952,pp.19-22.为此,尤为重要的是同时发掘直接表述法学知识的著作论述和记录知识生产过程的档案。对机构和人物之档案的发掘,可以把此前扁平化为被动接受过程的中西法学交流以更为立体、全面、复杂的方式呈现。
(二)场与行动的反思关系
布迪厄所提出的“场域”可以作为一种中介工具来理解作为一种实践的法学知识传播。社会场提供了一种空间的隐喻,让我们得以理解行动者在实践中的位置、策略和对社会结构的影响(实践效果)。对法学知识传播的研究必须能够揭示参与知识交流的人和机构、他们所掌握的不同资本与权力、他们在知识界与实务界的位置、在知识再生产时的策略选择、他们之间的互动关系所形成的意义,甚至最终评价他们对中国当代法学形成的贡献。社会场的概念同时为行动者的互动提供了空间和时间的维度。但这种空间并非地理意义的空间,而是社会意义的。决定社会空间的不是甲地和乙地之间的长度单位或旅行平均时间,而是不同行动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形成的网络。类似地,各个事件之间的时间序列虽然重要,但时间的意义在于记录行动者之间永恒、持续、没有终结的互动。
在社会空间中理解知识交流的目的是“揭示构成社会空间的不同社会人群的最深层的结构,以及倾向于确保社会空间的再生产或变革的机制”。〔39〕[法]皮埃尔·布迪厄:《国家精英:名牌大学与群体精神》,杨亚平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1页。对学说史所发生的社会空间的探索意味着同时发掘客观条件和主观认知结构,因为每一个特定的行动者所形成的具体认识必然是当下、此地客观社会结构和他所具有的认知结构共同作用的产物。更进一步说,“在社会结构和心智结构之间,在社会世界的客观划分(尤其是不同场域中的支配者与被支配者)和行动者划分社会世界的关注原则与划分原则之间,存在着对应关系”。〔40〕同上注。所以,必须把个人重置于宏大社会结构中,正是后者让他们的选择和决策变得不可避免。尽管经验现象的观察者无法在不考察个人之行动的基础上建构社会场,但社会科学的首要目标不是合理化、正当化个人的行为和策略,而是发现社会—心智双重结构。
社会场为行动者之间永恒的互动提供了必要空间。它无法化约为一个物理意义上的力场、一个由客观的力线支配的空间。位置各异、能力各异、愿望各异的行动者彼此斗争,不断定义并重新定义着社会场的边界和结构。〔41〕See Loïc Wacquant&Pierre Bourdieu,For a Socio-Analysis of Intellectuals:On“Homo Academicus”,34 Berkeley Journal of Sociology 1,8(1989).于是,对行动者和结构的了解之间形成了一个永无休止的循环:要想描绘出社会场,就必须找到在其中运作的行动者能够用来博弈的资本形式;可是要了解有哪些形式的资本在博弈中发挥作用,又必须对场的结构有足够的了解。〔42〕参见同上注,第7页。下文将进一步解释社会资本的类型。
场的引入有助于揭示结构与行动的反思性,特别是对于揭示象征性权力实践至关重要的社会结构和心智结构之间的对应关系。权力不但要具备获得服从的能力,还要同时具备生产关于这种服从的合法性信念的能力:“正是在客观结构与作为其产物的认知结构之间的原始共谋关系的基础上,绝对的、即时的服从才得以建立,这种服从就是人们出生所在的人群的教条经验中的服从。”〔43〕同前注〔39〕,皮埃尔·布迪厄书,第7页。在布迪厄的社会学范式中,用以表达这一反思性关系的概念是“习性”(Habitus)。布迪厄同时反对人文主义的自由意志理论和科学主义的决定论:“社会行动者既非仅仅由外因决定的粒子,也不是仅仅受内在理性引导、执行某种合理行动计划的孤立社会单子。”〔44〕同前注〔41〕,Loïc Wacquant&Pierre Bourdieu文,第10页。每一个行动、行动计划以及它们的作者都是历史的产物,嵌套于每个具体社会场的所有经验的加总,并进而嵌套于整个社会场的历史中。于是,每一个决策都要放在决策者在社会场的位置上加以理解。
行动者在社会空间中的位置即是她所拥有的社会资本总量和各种资本的比例,社会空间最终取决于不同的社会资本类别之间的力量关系。不同社会资本(或权力)的持有者在这一社会空间中进行互动。行动者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机构。小到个人,到一个十几名教员的法学院,再大到可以为政府的合法性背书的学术重镇,乃至一国的政治机构,每个行动者都享有不同的特殊资本。这些资本的总量、每一种不同的社会资本在总量中的比例、各种社会资本之间的兑换率定义了每个行动者在作为社会空间的学术场中所享有的特定位置。他们依据其所处的位置进行决策,从而形成某些旨在维护或者改变彼此力量关系的策略,并因此展开互动。个体或机构的行动者的互动取决于所有这些策略旨在维护或改变的东西本身。〔45〕参见同前注〔39〕,皮埃尔·布迪厄书,第457页。与此同时,不管行动者的策略目的是改变还是维持他们的关系,每一次互动总归会形成新的资本总和、社会资本比例,乃至改变各种资本之间的兑换率。这种互动可以通过市场经济的隐喻解释:顾客从商家购物,不管买卖的目的分别是什么,顾客的总资产中金钱减少了,但实物增加了,于是顾客的资产中货币和实物的比例发生了改变;更进一步,当有人大量购入某种商品时,商品的价格也会发生改变。这些或微不足道或影响深远的变化又构成了下一次互动的背景和条件。的确,法学场就是一种权力场的独特形式。
(三)资本的类型
布迪厄称一个社会行动者所能掌握的一切资源为“资本”。对法学知识再生产的分析聚焦于法学家同时作为法学知识提供者和法律规范创造者的双重角色,也就是主要依靠文化资本和象征性资本的概念。任何一个社会场中,行动者的互动又表现为他们所掌握的资本之间的互相转化。资本只有在向其他资本的转换中才能凸显其实践意义。
经济资本(capitaléconomique)是所有经济资源的加总,包括了生产要素、财产、财政收入、经济利益等,其最重要的制度化表现即是财产权。之所以有必要引入经济资本既因为它是最直观的资本形式,也因为它最容易以货币的形式表达出来。换言之,经济资本的象征化程度最低。正因为如此,在了解了某个具体的场之后,也就是了解了每个社会空间中不同资本的兑换率之后,象征性程度更高的资本总是可以被转换为经济资本,最终以货币的形式表达出来。虽然很难用货币形式衡量一篇论文、一本书、一个学说、一个学位、一部法典起草委员会的位置、担任重要机构的领导职务等成就的意义,但是经济资本的存在让对知识社会学的定量研究变得可能。不仅如此,一定的初始经济资本往往是行动者参与外国法学知识传播的前提。以王伯琦为例,如果没有姑母的经济支持,他或许难以在巴黎大学攻读民法博士。〔46〕参见王启中:《王伯琦先生生平》,载王伯琦:《近代法律思潮与中国固有文化》,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页。
文化资本(capital culturel)并不是指行动者所享有的抽象知识或者“文化”,而是那些或者已经与行动者的人身相连,或者物质化,或者制度化的那些可以客观感知和测量的因素。既包括学位、学衔、学术界的荣誉和奖项,也包括了书写的风格、研究的领域、某种特殊的生活情调等等。这些因素都最终为社会行动者赋予了或高或低的定义和正当化某种知识的能力。在欧美名校取得博士学位当然本身可以为行动者带来大量的文化资本。民国时期的留洋博士往往一回国即可获聘学术重镇的教授职位。如人们早已遗忘的翟俊千,1927年从里昂法学院博士毕业后即获得暨南大学邀请出任副校长。他的校友卢干东也是回国后立刻成为中山大学教授。国外学位和名校教席当然也就让他们比那些没有出洋经历、厕身私立法学院的同行更容易说服他人接受其对某个法律规范或学说的解释。与此同时,对国外法学知识的了解和对人们难以阅读的外文文献的掌握,也同样可以在行动者书写和说话的时候具体化为一种文化资本。
社会资本(capital social)指行动者可以通过其所处社会关系网调动的所有现存或潜在的资源,也就是一个人或者机构能通过另一个人或机构调动的资源。在每两个相互联系的行动者之间,就构成了社会关系网的一段,在这一段所凝结的社会资本同时取决于其关系的紧密程度和各自可以调动之资源的总量。在20世纪初的中国,家族能为行动者提供的社会资本更是不可小视。如开启中法百年法学交流的马建忠,就在仕途上获二哥马建勋引荐,在学术上则受四哥马相伯襄助。年轻的商法学家埃斯加拉能够获中国政府的邀请成为顾问,也离不开同为巴黎法学院毕业生的前辈宝道推荐。〔47〕参见同前注〔4〕,朱明哲:《中国近代法制变革与欧洲中心主义法律观》,第155-170页。就连哈佛法学院的院长庞德,能够在1946年第二次来华亦有赖于他的学生、时任司法行政部刑事司司长的杨兆龙之邀请。〔48〕参见王婧:《培养中国的社会工程师——评庞德的中国法律教育改革建议》,载《中国法律评论》2017年第5期,第128-139页。通过血缘、乡谊、学缘,一层层社会网络铺开在跨国法学发展史的桃李江湖之中。
相比之下,象征性资本(capital symbolique)更为复杂。一方面,经济、文化、社会资本都有一定程度的“象征性”,即它们不仅构成了行动者所能够使用的资源,同时也合法化了行动者所占有的实际或潜在资源和不同的资本之间的转化关系。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自费留学国外的私立学校——占有较高经济资本的行动者通过支付高额学费而换取了名校所能够提供的文化资本,同时名校也通过生产文凭换取了经济资本,很少人会质疑这种“交换”的合法性。同样,政治地位可以为法学交流的行动者提供丰厚的象征性资本。以王宠惠为例,31岁回国即担任民国首任外交总长,此后一直身居政界,虽然主要的法学论述以介绍为主,其学术仍为人所称道。〔49〕参见刘猛:《法学家王宠惠的思想与学术》,载《政法论坛》2019年第3期,第153-163页。真正让象征性资本区别于其他资本类型之处在于它纯粹是一种要求其他社会行动者承认的权力。〔50〕Cf.Pierre Bourdieu,Langage et pouvoir symbolique,Paris,Seuil,2001,p.72.换言之,象征性资本是一种关于正当性的资本,掌握这种资本意味着掌握了决定特定的社会场之内资本转化规则的权力和获得他人认可的权力。
四、“法学场”的结构
法学交流过程中产生的互动都发生在一个可以称为“法学场”的社会空间中。法学家通过他们的话语行动同时完成了知识的再生产和规范的再生产,当然也因此进一步完成了社会地位的再生产。法学同时生产着一种关于法律现象的知识(广义的法学)或关于法律规范的知识(狭义的法学),也生产着一种解释和应用法律规范的技术和方法,并由此在每一个具体的个案中为每一个具体的法律规范确定了独特的含义。所有的法学家都站在法院与书院之间,同时追求两个不同的场中的特殊利益。法学场也因此同时服从法律场和学术场的规律。
(一)特殊利益与习性
布迪厄把法律场定义为“人们为了垄断说出法律(即好的分配或秩序)的权利而竞争的场所。在竞争中相遇的行动者具有一种兼具社会和技术性质的权能,其中最关键的方面是他们可以相对自由地解释一套把合法、正确的社会观念神圣化的文本,这种能力为社会所承认”。〔51〕Pierre Bourdieu,La force du droit,Actes de la recherche en sciences sociales,n°1,1986,pp.3-19.法律场的参与者竞争的特殊利益就是决定法律规范之意义的垄断权。法学论争的终极问题是谁有权以何种方式以法律的名义发言。以法律的名义发言意味着有权定义法律,并以无可争议的态度确定具体法律规则在实践中的内容。所以,掌握以法律之名言说的权力就等于掌握了一种关于权力的权力。两种不同的秩序以及它们之间的反思性关系使法律场区别于其他的社会场。①由规范和学说建立的象征性秩序,本身蕴含了发展的客观可能、却无法完全独自运作。②由行动者与体制之间客观关系建立的秩序,行动者和机制时刻处于竞争中。〔52〕参见同上注。
决定法律规范意义的权力必然同时包括定义法律的权力和定义“正确的”法律解释方法的权力。孟德斯鸠关于“法官是法律的嘴巴”的说法最为形象地道出了法律场的习性:由规范构成的金字塔同时具备效力与合法性,应该得到尊重,此间的行动者并不创造规范,仅仅“解释和适用”那些已经存在、已经由别人创造出来的规范。但是在每一次法律的适用中,法律的解释者总是在重新创造着法律。当法官把旁系血亲婚姻禁止限制在自然血亲之间时、〔53〕参见同前注〔46〕,王伯琦书,第106页。把不见于民法规范的祭田解释为共同共有时、〔54〕参见李启成:《外来规则与固有习惯——祭田法制的近代转型》,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63-266页。把夫妾关系解释为家长与家属共同生活的关系时,〔55〕参见黄茂荣:《法学方法与现代民法》,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304-306页。他们毫无疑问改变了这些规则制定者对那些需要解释的术语的理解,从而也改变着法律。改变一个法律规范的意义和适用就是改变这个法律本身,所以每一次对法律的解释都是微观层面上的一次法律革命。当人们争相提出关于解释法律的正确方法和对某个法律规范的正确解释的时候,他们竞争的正是定义规范和规范之意义的垄断权。在法律实践中,法官、法学家、律师、法警等一系列行动者采取不同的策略,从而最大化他们“象征性资本”的收益,在共同接受法律规范之存在和正当性(“习性”)的前提下,竞争着终局确定法律意义的垄断权(“特殊利益”)。每一个行动者可以采取的策略取决于各个行动者实际上拥有的资源。
类似于法律场,学术场的特殊利益也是定义知识、决定何为“正确知识”的权力,并进一步具体化为对知识再生产所必须的物质、组织、社会工具的控制。对这些工具的控制既是学术特权本身,又是进一步争取更多特权的工具。“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这种“马太效应”在学术界尤其明显。〔56〕参见舒国滢:《认真对待劣势知识生产与奖励之马太效应的畸形叠合》,载《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第82-83页。与此同时,参与学术场和参与其他场的实践一样,都要求行动者不断投入经济、文化、社会、象征性资本以在竞争中谋取权力和特权。学术界的规则一方面致力于建设一个客观、公正、中立的评价平台,另一方面却从来无法阻止学术外的因素影响竞争的样态。吴经熊在经营律师业时获取的经济收入自然让他有更多的闲暇从事基础性研究。马建忠接受的西学启蒙当然也让他在1877年留法后更容易适应法国学术界的口头与书面表达风格,其兄在上海学术界的人际关系也能为官场失意的他提供暂时的庇护。埃斯加拉、宝道、史尚宽参与法典编纂的经历不也让他们对于中国法律的评论和注释更有权威性和正当性吗?
法学场和其他学科的社会空间所不同的是它所产生的知识直接决定着法律的定义、正当性和“正确”的法律适用。认为中国民法接受了物权行为独立性理论的学者和他们的反对者对同一个法律争议可能持完全不同的立场。强调尊重立法者原意的人和强调要让法律文本适应时代发展的人可能对同一个条文解释出完全不同的意思。能否认识到判例无论如何都以分散、静默的方式改变着法律的风景也会让人们对如何使用先例持截然相反的态度。关于法律的知识同时具有了科学和政治的权威。在这个意义上,“知识就是权力”在法学场中表现得最为淋漓尽致。
(二)等级秩序
所有斗争或者竞争所服务的总的目的,并不是获取更多的权力,而是掌握那种支配其他权力的权力,即对总体权力的垄断。在法学场的等级秩序中,处在最高点的就是那些掌握了最多法学知识生产工具和资源的人,或者说是那些所有资本的总量最多的人。王宠惠、周鲠生、吴经熊、史尚宽等人的经历就是明证。他们在留学回国后任职于最重要的法学院,甚至出任院长等重要职位。他们的文章发表在最重要的法学期刊上,所撰写的教科书一次又一次再版。他们的学生出任大理院、平政院、最高法院的法官,或就职于重要的部门。有时候,他们自己也曾担任过重要司法机构的院长或立法起草委员会、调查委员会的主席。就这样,他们坚定地站在科学与政治之间,审时度势,时刻准备着用大学教职所证明的科学权威为自己的政治立场背书,或者反过来用公共生活所赋予的政治权威促进他们的科学发现。
在这些位极人臣、声震儒林的行动者的光芒掩盖下,还有形形色色没那么耀眼的人或机构,同样投资着自己所能动用的文化或象征性资本,力求在竞争中获利。王伯琦、马建忠、里昂中法大学、震旦大学法科已经是其中的幸运者,至少为后人留下了足够的作品。更多的人则深陷于遗忘中。他们可能任教于一个边缘的、只有本地学生的法学院,或者某个短命的私立大学。〔57〕参见沈伟:《摩登法律人:近代上海法学教育研究(1901—1937)》,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2020年版,第61-70页。他们可能偶尔有机会在本地出版社出版一些短篇的作品,但从来没机会撰写教科书。他们可能甚至根本没有大学的正式教职,只是作为律师在一些小的法学院中兼职授课。他们可能也出任过地方议会的议员,但是一生与更高级别的公职绝缘。无论是文化资本还是象征性资本,他们可以用来为自己争取更多特权的能力都小得多。相对较小的资本总量并没有妨碍他们精打细算地安排自己的投资。在精英主义支配下的学说史叙事中,这些人往往就成了“失踪者”。〔58〕主要的成就包括陈新宇:《寻找法律史上的失踪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在任何一个时代,学术权威终归只是少数,大多数法学家在传统学说史的视野中仍然只是“边缘人”和“失踪者”。然而作为同行,权威、边缘人、失踪者在一个具体的时间和空间中就算不在同一个机构共事,也总会以问题探讨或会议交流等种种方式产生互动,使法学场不断自我生产并与其他的社会场中的互动形成合力,改变一个社会本身的结构或者制度基础。不同行动者的互动在国内法的语境下很容易理解。如法国关于世俗化的讨论就广泛牵涉了狄骥这样的学术权威、厕身于共和政府支持的巴黎法学院的主流法学家、选择任教于天主教学校的边缘人,和那些仅仅在法律实务的余暇在法学院授课的失踪者。〔59〕参见朱明哲:《论法国“世俗性”原则的斗争面向》,载《欧洲研究》2016年第6期,第117-135页。今人眼中的“权威”并未主宰当时讨论的议程,更无法决定学说和实务的发展方向。同样,领事裁判权的撤废让政学两界精英和一般舆论在同一个问题上发声,并在相当程度上形塑了近代中国法学,乃至于大众情感。〔60〕参见李启成:《治外法权与中国司法近代化之关系——调查法权委员会个案研究》,载《现代法学》2006年第4期,第26-37页;张仁善:《论中国司法近代化进程中的耻感情结》,载《江苏社会科学》2018年第4期,第132-141页。同样的事件也发生在跨国的法学交流之中——边缘人和失踪者并不必然屈服于伟大作者的权威,而是利用自己所掌握的社会资本在法学场的竞争中积极地为自己谋得一席之地。
(三)作为社会实践的法学交流
为了说明不同地位的作者,特别是那些常常为学术史所忽略的边缘作者的实践逻辑,下面将在法学场的概念框架下,展现在里昂中法大学的留学生的学习状况。该校第一名法学博士吴凯声主动要求法国比较法学奠基人之一朗贝尔作为博士学位指导老师,并提出以对几份中国宪法草案的比较作为自己的论文主题。〔61〕Archives l’IFCL:Dossiers WU Kaisheng,Sous-dossier#1,No.25.1925年,他的博士论文完成并答辩通过。实际上,该书一半的篇幅是“双十宪法”法文翻译,质量只能说差强人意。即便如此,在吴凯声和中法大学管理人员的努力下,朗贝尔还是改变了最初的想法,同意放入他主编的“比较法丛书”中出版并作序。〔62〕参见同上注,Sous-dossier#1,Nos.37-38。毕业后,他很快回到了中国,在上海法租界开了一家律师事务所,事业蒸蒸日上。〔63〕参见同上注,Sous-dossier#3,No.81。在法国获得的文化资本迅速地转换成了经济资本。但是,在所有的资本都必须不断象征化的铁律下,吴凯声果断地抓住了进入政界的机会,在1929年成了国民政府驻国联大使,而且不忘致信母校报喜,并表达希望有机会从日内瓦前往里昂探访叙旧的心愿。〔64〕参见同上注,Sous-dossier#3,No.84。从外交事业回到律师界之后,他参与了为廖承志辩护等重大历史事件,此后又历任汪伪政权考试院考选委员会委员、驻意大利大使、外交部次长、撤废治外法权委员会秘书长,并以在南京审判中获刑的结局退出历史舞台。〔65〕参见陈同:《在法律与社会之间:民国时期上海本土律师的地位和作用》,载《史林》2006年第1期,第55-69页。他的师弟们的命运也大抵如此,翟俊千、卢干东、陈廪等人都成功说服学校管理方和自己的导师,选择用法国理论来分析中国问题作为博士的选题,甫一回国即就任重要职位,辗转于政学二界之间,本可以获得更高的成就,却无奈形势比人强。然而,就在从归国到沉寂之间短短十几年中,他们仍然通过选题、师承、就业等等一系列选择不断实现经济、文化、社会和象征性资本的积累。
这些青年精英必须依赖中法大学所能提供的奖学金方有机会留洋,而且也只能在一所1875年才成立的外省法学院就读。同时,里昂法学院也对比较法和法律社会主义持有较为开放的态度。中国留学生们敏锐地意识到了这种学术风气让他们可以更容易说服指导教师让他们去畅想中国种种问题的法律解决之道。而且,在要求导师支持他们出版著作和要求学校资助他们前往巴黎或者其他学术中心求学等方面,他们表现出了极大的耐心,不厌其烦地与管理层沟通。广东女生黄明敏便不顾管理方劝阻,执意前往巴黎,然后与管理方就中法大学是否要支付其在巴黎生活费展开了将近8年的争执。〔66〕Archives l’IFCL:Dossiers HUANG Mingmin(1921—1931).他们的档案中展现的并不是谦虚的学生勤勉学习西方法学的故事,也不是强势的教师把西方法学强加于人的故事,而是行动者在对祖国命运和个人前途的双重思考之下,面对多元、复调的西方法学知识进行自主选择的故事。
他们清楚地知道,在欧美获得的文化资本将是他们回国后参与法学场游戏最重要的积累,所以必须竭尽全力尽可能将其最大化。仅获法学本科学位的黄明敏都可以出任广东上诉法院的法官,国外法学知识与其他社会资本之间在中国的法学场中潜在的兑换率已经不言而喻了。不过,上诉法院的职位虽然是一个不错的开始,已经可以在重要的案件中决定法律条文的意义,却离法学知识生产的中心——国立大学的法学院——还远得很。他们还年轻,可以继续在法学场这场永无休止的斗争中继续谨慎投资。在他们回国后,正如他们在法国时所做的那样,中国法学家时刻准备着根据中国法律实践所面对的具体问题,从书架上挑选合适的外国理论,加以适当的阐释,在祖国的法学场中争取到确定关于法律之真理的话语权。此时,笔成了手中的投枪与匕首,卷宗和出版物则成了战场,不同源流的法学知识和对这些知识的不同阐释之间的象征性斗争不断重复,而他们的作者在法学场中的地位也随之不断变化。
每一个行动者分散的社会实践聚合起来也终将改变法学场本身的空间秩序。“今日中国法学之总体,直为一幅次殖民地风景图:在法哲学方面,留美学成回国者,例有一套Pound学说之转播;出身法国者,必对Duguit之学说服膺拳拳;德国回来者,则于新康德派之Stammler法哲学五体投地”。〔67〕蔡枢衡:《中国法理自觉的发展》,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8-99页。为了解释和评价通过移植而实现的法律现代化,有留洋背景的学者提供了多种相互竞争的解决方案。在这些纷繁复杂的西方知识占据主导地位背后,是传统律学和儒家经典知识的式微,也说明当时中国大学所能提供的文化资本很低,难以满足希望在法学场中占据一席之地的青年。在由海归法学生和他们所带回的法学知识的形塑下,法学场的风景图上丘壑纵横。一名行动者处于高峰还是谷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所能获得的外国法学知识。任何想要参与这场象征性斗争的人都必须接受这一现实。
五、结论
蔡枢衡的评论虽然较为准确地描述了当时中外法学交流的状况,不过,所谓“无一为国家民族利益之代表者,无一能负建国过程中法学理论应负之责任”的批评则过于严苛。当1840年以来的中国在外来压力下建立新的制度、机构,以及与它们配套的法学知识时,撼动的不仅是过去的知识体系,而且还有旧的社会关系风景图。中国社会产生了无数缝隙,让过去难以进入权力中枢的社会阶级突然看到了机遇。“摩登法律人”们要想在此时把握住难得的历史机遇,那就必须小心地讲述他们所了解的庞德、狄骥、施塔姆勒理论,把它们说成是中国问题的真解决。这一过程并不是一种对现成国外法学知识的完整转述或误读,而是一种关于中国法律实践的新知识的形成。在试图用西方法救国救民和处于文明等级压迫之下的宏大叙事之间,个体或群体的行动者在他们无法选择的时间、地点、社会关系之中,为了更多的资本总量和资本象征化不断互动。
传统的学说史研究关心人们说了什么、怎么说,亦即那些用以形成学说的“话语”。社会实践理论则把话语理解为一种通过语言而为的实践,去研究那些并不连续的话语实践所以形成的历史条件、它们彼此叠加的形态、它们转变和消灭的规则。在法律场中,人们竞逐着决定关于法律之话语真实性的垄断权。为此,他们必须既相信法学知识对法律规范的整合、评判和正当化功能,又相信法律规范本身的实在性与正当性。然后,他们必须接受不同的机构和职位之间存在的等级秩序,认清自己所掌握的经济、文化、社会、象征性资本,并谨慎地使用这些资本进行策略性实践,从而迈向法学知识生产的中心。在这场象征性斗争中,手握或多或少社会资本的人们不断进行法学知识的再生产,并同时再生产着文本背后的一套社会现实——不同群体、机构、地点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和对这种不平等的接受。然而,只要社会结构不产生剧变,无人需要彻底出局,直到下一次新的制度、机构、职位革新并产生对新法学知识的需求那一刻,直到新历史变迁彻底重写这一互动机制的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