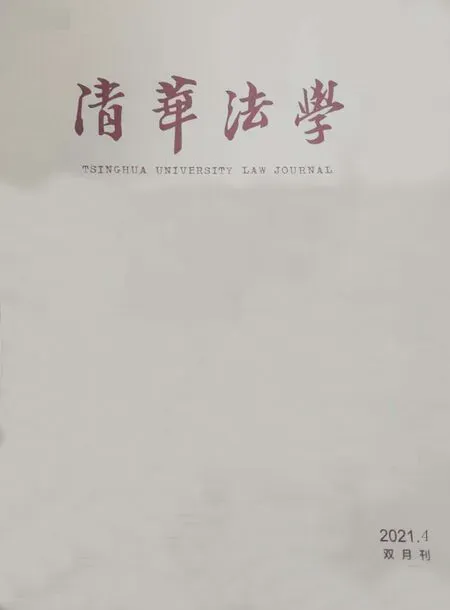法的渊源理论:视角、性质与任务
雷 磊
“法的渊源”是迄今为止法学理论中最复杂的概念之一。在西方学界,举凡历史渊源、理论或思想渊源、本质渊源、效力渊源、文献渊源、学术渊源等,在历史上或当下都不乏主张者。以至于民国时期学者胡玉度曾指出,所谓“法源”者,原系法学上之一种纯属人为的术语,故其涵义如何,可由吾人自定,而无必强以从同之必要。〔1〕转引自王勇飞:《法学基础理论参考资料》(第三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429页。这种较为极端的立场虽不值得赞同,但毕竟说明了情况的复杂性。而我国学者在继受西方学说的过程中不仅继受了这种乱象,而且有些学者在解读这些含义的过程中添入了自己的理解,从而使得局面变得更为复杂。本文认为,之所以既有研究对于“法的渊源”(以下有时简称“法源”)概念认识较为混乱,在很大程度上与对其前提性框架,即“法的渊源理论”(以下有时简称“法源理论”)的理解不明有关。具体而言,后者又包括三个问题:第一,法源理论应采取何种研究视角?第二,法源理论是一种什么性质的理论?第三,法源理论的任务是什么?下文将归纳中国学界的代表性立场,接着依次分析和回答这三个问题。
一、法源的界定:中国学界的代表性立场
首先要指明的是,尽管法理学和宪法、民法、行政法等部门法学的教材大多会将“法的渊源”作为基本章节纳入,但学者们关于这一范畴的理解是极其多样化的。〔2〕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一本关于中国法理学研究综述和评价的书中,编者纳入了十五个法学的基本范畴或主题,但根本就没有提“法的渊源”,参见王勇飞、张贵成主编:《中国法理学研究综述与评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这只能说明,要么编者认为这个范畴并不重要,要么因对这一主题上的各种学说进行综述的难度过大而放弃了它。笔者认为更多原因或许在于后一点。如果要勾勒一个光谱带的话,从一端到另一端会呈现流动和过渡的状态。往往一种主张与其他主张会存在交叠但又不完全相同的关系。在此前提下,要对现有的研究进行归类,只能采取“类型学”的分类方式。据此,我们将当下中国学界关于“法的渊源”的理解分为五种主要学说。
(一)表现形式说
“表现形式说”一直以来是中国学界的主流观点。它主张,法的渊源就是法的形式、法的存在形式或法的表现形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形式说都是法理学界的主流观点。或许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在宪法学、行政法学、民法学等部门法学界,均将形式说作为主流学说。〔3〕例如参见胡锦光、韩大元:《中国宪法》(第四版),法律出版社2018年版,第89页;姜明安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第七版),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年版,第47-48页;梁慧星:《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第25页。有学者指出,国内学界将法的渊源等同于法的形式的做法,可能源自日本学者的著述。〔4〕参见周旺生:《法的渊源与法的形式界分》,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05年第4期,第125页。例如,商务印书馆1913年出版的日本学者织田万的《法学通论》中译本,就把法的渊源分为两大部分,其中一个部分主要就是法的形式。〔5〕参见[日]织田万:《法学通论》(第1卷),刘崇佑译,商务印书馆1913年版,第43页。而民国时代专门讨论法的渊源的著作《法形论》直截了当地指出“法形就是法源”,也即法律形式就是法的渊源。〔6〕参见李火斤:《法形论》,公慎书局1922年版,第1页。新中国成立后,从20世纪50年代直至本世纪初,形式说都牢牢占据着统治地位。例如八十年代比较有影响力的教材中,王勇飞编辑的《法学基础理论参考资料》(1980年初版、1984年修订)一书在介绍这一主题时说,“法律渊源就是指法的各种具体表现形式”,“国家机关制定或认可的法律规范的种种表现形式……就是法律渊源”。〔7〕王勇飞编:《法学基础理论参考资料(下)》,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135页。此外,李放和张哲编著的《法学原理》(1981年)、〔8〕参见李放、张哲:《法学原理》,辽宁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38-139页。高等学校法学试用教材《法学基础理论》(1982年)、〔9〕参见法学教材编辑部《法学基础理论》编写组:《法学基础理论》,法律出版社1982年版,第250页。简明法学教材《法学基础理论讲义(试用本)》(1983年)、〔10〕参见《法学基础理论讲义(试用本)》,法律出版社1983年版,第179页。北京大学法律系法学理论教研室编写的《法学概论》(1984年)〔11〕参见《法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0页。都持这一观点。也有教材将法的渊源或者说法的形式进一步划分为法的创制方式和法律规范的外部表现形式两个层面。〔12〕参见孙国华、朱景文主编:《法理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57页。尽管形式说在后来遭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批评,但最近仍有学者试图“拨乱反正”,重新回归到“法的渊源=法的形式”这一等式上去。〔13〕例如参见刘作翔:《回归常识:对法理学若干重要概念和命题的反思》,载《比较法研究》2020年第2期,第112-113页。
(二)本质渊源说
“本质渊源说”在20世纪50年代以来影响甚巨,直到80年代也有一定影响。它来自苏联传统,认为法的渊源其实就是一定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和统治阶级意志的表现形式。当时对中国影响甚巨的一本苏联教材就明确认为,制法活动归根到底是以经济基础为根源的,但法的直接渊源则是具有各种不同表现形式的国家意志。因此,法的渊源就是表现统治阶级意志的特殊方式,统治阶级意志通过这种方式而成为法。〔14〕参见[苏]玛·巴·卡列娃等:《国家和法的理论(下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387页。当时的《苏联法律词典》也认为,“‘法的渊源’这一术语是一个假借的名词,因为统治阶级意志的内容归根到底是由该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来决定的,所以实际上构成法的渊源的,正是这些物质生活条件”。〔15〕[苏]库德利亚夫采夫主编:《苏联法律辞典》(第三分册),法律出版社1957年版,第108页。在此基础上,后来被翻译过来的苏联学者雅维茨的著作直接将法的渊源界定为“社会生活的物质条件和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类型”。〔16〕[苏]雅维茨:《法的一般理论》,朱景文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95页。受这一传统影响,改革开放后第一本以“法学基础理论”为名的教材就将法的渊源简要定义为“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17〕陈守一、张宏生:《法学基础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40页。。在大体相同的意义脉络上,亦有宪法学者指出,宪法渊源是“支撑宪法内容的内在根据,也是决定不同国家宪法内容差异性的隐形力量”。〔18〕王广辉主编:《宪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4-25页。
(三)效力渊源说
“效力渊源说”在时间上产生相对较晚,但近些年却获得了较多学者的赞同。这种学说将法的效力作为法的表现形式的依据或基础。例如,赵震江和付子堂主编的《现代法理学》将法的渊源等于法律的效力来源。〔19〕参见赵震江、付子堂主编:《现代法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周永坤认为,“法律渊源是指法律的权威及强制力的来源或法律的存在样态”。〔20〕周永坤:《法理学》(第二版),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42页。这里的“法律的存在样态”就是法的形式。张文显主编的《法理学》则更详尽地论述了法的效力与法的形式的关系。在其看来,一方面,法的渊源必然与法的效力相联系,只有产生法的效力的法律文本或其他规范才有可能成为法的渊源;另一方面,法的渊源必然要表现为一定的法的形式。法律文件的效力和形式是统一的,凡是具有法的效力的法律文本,都有一定的表现形式。两者都是法的渊源不可或缺的要件。〔21〕参见张文显主编:《法理学》(第五版),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87页。总之,在这种学说看来,法的渊源主要指那些具有法的效力作用和意义的法律的外在表现。简言之,法的渊源就是“有效力的法律表现形式”〔22〕刘作翔:《“法源”的误用——关于法律渊源的理性思考》,载《法律科学》2019年第3期,第4-5页。。但亦有学者明确区分了法的渊源与法的形式。如宪法学者上官丕亮就认为,宪法渊源的本意指的是宪法的效力来源,而宪法形式指宪法的外部表现形式,两者不可混同。〔23〕参见上官丕亮等:《宪法学:原理与应用》,苏州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9页。
(四)形成渊源说
“形成渊源说”认为,法的渊源指的并不是法的形式,而是法得以形成的原料或内容的来源。〔24〕要说明的是,之所以不称之为“立法渊源说”,是因为此说虽然主要适用于立法的语境,却不限于此。它的着眼点是法的内容来源或法形成的质料基础,也适用于判例法和习惯法的语境。民国时代学者欧阳谿就认为,法的渊源是“法律所据以产生之材料”〔25〕欧阳谿:《法学通论》,上海法学编译社1947年版,第140页。。据此,习惯、判例、先前法、外来法、国际条约、道德、宗教戒律、乡规民约、政策、学说(法理)等等皆可成为法的渊源,立法者可以它们为基础来形成法律规范的内容。〔26〕具体可参见Roscoe Pound,Jurisprudence(Ш),West Publishing Company,1959,pp.383-416;[美]埃尔曼:《比较法律文化》,贺卫方、高鸿钧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1页。在此意义上,有宪法学者将党和国家政策、马克思主义的宪法理论和学说、政治实践、人类文明成果等都列为我国宪法的渊源,〔27〕参见张庆福主编:《宪法学基本理论(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111页。因为它们都可能构成宪法内容的来源。在当代法理学者中,周旺生对此进行了最深入的论述。他将“法和法律制度是基于什么样的原料形成的”问题视为法的渊源的重要因素(他称之为“资源性要素”),并立足于此对法的渊源和法的形式进行区分。在他看来,法的渊源是未然的、可能的法,法的形式则是已然的法和正式的法的不同表现形式,它们分别代表了法的形成过程中两个性质不同的阶段和表现形态。〔28〕参见同前注〔4〕,周旺生文,第128页。法的渊源有可能被选择和提炼为法,或有可能形成为法,但还不是法;而法的形式在很大程度上是法的渊源发展的结果。〔29〕参见周旺生:《法的渊源意识的觉醒》,载《现代法学》2005年第4期,第33页。在此,法的渊源其实构成了法律形成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是预备阶段的法。
(五)司法渊源说
“司法渊源说”将法源这一概念的意义定位于司法裁判的领域,认为这一学说旨在帮助法官寻找到判决的规范基础或者说法律推理的大前提。李龙将对法的渊源的选择和识别视为法律适用的起点,认为对法的渊源的澄清属于一个前法律问题。〔30〕参见李龙、刘诚:《论法律渊源——以法学方法和法律方法为视角》,载《法律科学》2005年第2期,第4页。在陈金钊看来,法的渊源是一个专门描述司法过程的概念,是指法官在哪种法律形式中探寻针对个案的法律、发现探究判决理由的过程。〔31〕参见陈金钊:《法律渊源:司法视角的定位》,载《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05年第6期,第3、5、6页。进而,法的渊源就是法官发现法律的场所。〔32〕参见陈金钊主编:《法律方法教程》,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56页。这一学说的拥护者一般持有“多元法源观”,反对立法中心主义和制定法实证主义,认为在进行司法裁判时,所依据的除了以制定法的形式存在的“法”,还有许多以其他形式存在的规范。这一观点得到了不少民法学者的支持,〔33〕一些民法学者虽然在著作中没有专门论及民法渊源,但却通过其他方式涉及了这一主题。如,梁慧星通过将自由法学派所支持的社会学解释引入法律解释,使得特定裁判场合中法律发现的对象远远超出制定法之外,将社会中的“活法”也囊括在内,梁慧星:《民法解释学》(第四版),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第239-244页;再如,徐国栋将民法基本原则作为克服制定法局限性的工具,认为它们具有授权司法机关进行创造性司法活动的客观作用,徐国栋:《民法基本原则解释》(增删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3页;王利明则同时通过社会学解释、基于习惯法的漏洞填补、基于比较法的漏洞填补和基于法律原则的漏洞填补,引入了大量制定法外的“渊源”,王利明:《法律解释学》(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82-302、386-439页。也在部分行政法学者那里找到了共鸣。如何海波就认为,法的渊源是争辩法律时所使用的有说服力的“论据”,而不仅是必须遵循的“依据”,因而不限于具有法律效力的成文渊源,也包括法律原则、学说、先例等非成文渊源。〔34〕参见何海波:《实质法治:寻求行政判决的合法性》(第二版),法律出版社2020年版,第190-192页;应松年、何海波:《我国行政法的渊源:反思与重述》,载浙江大学公法与比较法研究所编:《公法研究》(第二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9-15页。要指明的是,何海波不仅将法源的概念应用于行政诉讼的场合,也应用于行政执法的场合,用来指称行政执法所依凭的论据。这里涉及行政法的领域特殊性。究竟是应将法源的概念仅限于司法裁判抑或应同时扩张至其他法律实施活动,对于这一问题本文保持开放。但无论如何,只要法律活动涉及法律论证,只要法律论证是一种基于法律拘束力和/或追求法律说服力的说理活动,“司法渊源说”的内核就同样适用于行政执法,因为行政机关与法院面临相似的任务:前者为“依法行政”,后者为“依法裁判”。但出于使用习惯和后文论述便利的考虑,本文仍采“司法渊源说”这一称呼。基于此,陈金钊进一步指出,法源的要义是在司法语境中,把制定法外的其他社会规范等视为法,即将某些社会规范(习惯、条约、判例、政策、道德、纪律规范等)、思维规则等同于法并加以运用,或者说将它们拟制为“法”。〔35〕参见陈金钊:《法源的拟制性及其功能——以法之名的统合及整饬》,载《清华法学》2021年第1期,第53页。有学者将这些被拟制的法称为“司法之法”,以便与以制定法为主体的“立法之法”相对立。〔36〕参见彭中礼:《论法律形式与法律渊源的界分》,载《北方法学》2013年第1期,第107页。
另有一些学者尝试将以上的两种或多种观点综合,从而试图将“法的渊源”变成一个内涵并不单一的复合型概念。代表性的主张有“二要素综合说”和“三要素综合说”。“二要素综合说”比较典型的例子,是舒国滢主编的《法理学导论》。它提出“所谓法律渊源,就是指被承认具有法的效力、法的权威性或具有法律意义并作为法官审理案件之依据的规范或准则来源”。〔37〕舒国滢主编:《法理学导论》(第三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66页。这事实上综合了效力渊源说和司法渊源说。“三要素综合说”或综合形成渊源说、效力渊源说与表现形式说,〔38〕参见魏再龙:《法学权利论》,湖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146-147页。或综合形成渊源说、本质渊源说与表现形式说,〔39〕参见王勇飞、王启富主编:《中国法理纵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16-217页。或综合形成渊源说、效力渊源说与本质渊源说〔40〕参见周旺生:《重新研究法的渊源》,载《比较法研究》2005年第4期,第3-7页。等,不一而足。
可见,中国法理学界已积累起了丰富的观点,但所持的立场也差异较大。这些观点和立场从各自的角度看或许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作为法学基本概念,“法的渊源”不可能、也不应该是个包括万象的范畴,否则它存在的意义就会存疑。这就首先要求我们来弄清楚:法源理论究竟要做什么?这个问题涉及法源理论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下文将分别从法源理论的视角、性质与任务三个方面来分述之。
二、法源理论的视角:法、法的创制抑或法的适用?
以上我们枚举了中国学界关于法的渊源的五种主要学说。关于表现形式说和效力渊源说,我们将在下文第四(一)部分论述相关内容时涉及。而对于其他三种学说,我们大体上可以区分出两大类研究视角:法本体论的视角与法认识论的视角。
(一)法本体论的视角
法本体论视角聚焦于法的本体问题,试图通过回答“法来源于哪里”的问题,来探寻对“法是什么”或“法的本质为何”等问题的回答。质言之,这种视角下的法源理论其实与法的概念与本质理论密不可分。例如,如果认为法来源于“主权者”或“社会规则”,那么无疑就持实证主义的概念论立场,将法(=实在法)视为一种自然或社会事实。如果认为法来源于“自然”或“上帝”或“人的理性”等等,那么持的就是自然法学的立场。而如果认为法来源于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则属于马克思主义法学的阵营。上面提及的早期的“本质渊源说”就属于法本体论视角下的法源理论。这种视角下的研究属于法哲学研究。要注意的是,法哲学的研究大体属于一种形而上学的思考,所以它在探究法的“来源”时并不是在做经验社会学式的实证研究,而更多是在进行哲学思辨和论证。即便是马克思主义法学,也是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方法论下研究法的本质问题的。问题在于,假如如此,似乎根本就没有必要在“法”或“法的本质”之外独设“法的渊源”的概念。〔41〕即便退一步,将“法的渊源”限于“形式意义上的渊源”,也无必要。因为一方面,在本质渊源说中,形式意义上的渊源就是“国家意志的表现形式”,它要服从于法的本质的其他两个层面,所以本身并不重要,这就无法说明“法的渊源”概念的独立重要性;另一方面,即便撇开这一点,又会绕回到法的渊源与法的形式之间的关系问题,对此容后再述。换言之,“法的渊源”这一概念在法本体论或法哲学的视角下是冗余的。正因为如此,目前鲜有学者从法本体论的立场出发来界定法的渊源,“法的渊源”和“法的本质”这两个范畴在今天也被相对清晰地区分开来。
(二)法认识论的视角
与此不同,法认识论的视角聚焦于法的形成或发现问题。根据法的形成或发现的语境不同,又可以将之区分为法的创制的立场(视角)与法的适用的立场(视角)。〔42〕这里要说明两点:其一,之所以在这里没有像有的学者那样,使用更为流行的“立法立场”与“司法立场”这一对称(参见彭中礼:《当代中国法律渊源理论研究重述》,载陈金钊、谢晖主编:《法律方法》(第11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336-344页),是因为考虑到这两个称呼偏狭,例如,前者无法涵盖司法性立法和习惯法的情况,后者无法涵盖非通过司法的合宪性审查的情况。其二,区分这两种立场或视角的前提是,法的创制与法的适用不是一回事,或至少是可区分的;但如果像凯尔森那样否认两者的区别,那么不仅法源的独特意义凸显不了,而且法源的概念也的确会像他认为的那样没有必要。
1.法的创制的视角
在法的创制的立场看来,法的渊源的主要价值在于法和法律制度的形成方面。〔43〕参见周旺生:《法的渊源的价值实现》,载《法学家》2005年第4期,第20页。英国学者克拉克最早提出,法的渊源要解决的问题是:“有争议的特定规则的内容是由什么决定的?是什么使得立法机构或法律宣告机构像事实上做的那样能够表述这些规则?如果说国家赋予法律规则以权威,那么是什么东西赋予法律规则以内容?”〔44〕转引自周旺生:《法理探索》,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91页。立法主体可以凭借法的渊源理论和知识,学会从法的渊源中选取和提炼素材并形成法;司法者及其他用法者可以借助法的渊源理论和知识,在既有的法或法律规则不敷需要时,并且在法所允许的情形下,从法的渊源中提取有关素材,形成规则。〔45〕参见同前注〔4〕,周旺生文,第128页。前者是制定法,而后者是判例法。基于此,法的创制的立场也将法的渊源与法本身区分开来:法的渊源未必同国家意志有关,如习惯、宗教戒律、法学著作、伦理道德这些资源性法的渊源就是可以同国家意志无关的,而法则是国家意志的体现。〔46〕参见同前注〔29〕,周旺生文,第33页。简单地说,只有通过国家意志的选择(体现为立法行为、司法行为等),法的渊源才会变成法。〔47〕支持这一立场的周旺生似乎也没有明确区分他所说的“资源性要素”和“进路性要素”。从论述看,他主要是在资源性要素的意义上来区分法的渊源与法的,但有时似乎又在进路性要素的意义上区分两者。例如他指出,“立法是一种法的渊源,而法律、法规便是立法发展的结果和表现;司法判决是一种法的渊源,而判例法便是司法判决发展的结果和表现;习惯是一种法的渊源,而习惯法则便是习惯发展的结果和表现”,同前注〔40〕,周旺生文,第10页。这里明显是在进路性要素的意义上来理解法的渊源的。但问题在于,如何可能一方面将“国家意志”作为区分法的渊源与法的标准,另一方面又将体现国家意志的“立法”“司法判决”和“习惯”这些行为作为法的渊源本身包含的要素呢?此外,“习惯”究竟是资源性要素还是进路性要素,也不清晰。显然,前文所说的“形成渊源说”持的就是法的创制的立场,它实际上是在探究特定法律或法律规范得以形成的质料或素材基础。这些质料或素材的范围有多大?学者们的论述不一而足,仅举几例。庞德认为,这一范围包括惯例、宗教信仰、道德观念、哲学观念、司法判决、科学探讨。〔48〕参见同前注〔26〕,Roscoe Pound书,第383-415页。按博登海默的看法,这一范围包括条约和其他经双方同意的协议、先例、正义的标准、理性和事物的性质、个别衡平、公共政策、道德信念和社会倾向。〔49〕参见[美]埃德加·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13-483页。日本学者大木雅夫则指出:“法源意味着‘单独或共同构成法律生活形态的一切东西’,即涵盖法律或规则的条文、判例、学说、注释书、教科书、政府的命令或惯例,以及其他未必严格遵循法律的实践,如公证人的实务、团体协议、交易惯例、法律惯例、普通契约条款、仲裁裁定等一切。”〔50〕[日]大木雅夫:《比较法》,范愉译,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92页。所以可以总结认为,其范围极其广泛,至少包括:习惯、判例(先例)、个别衡平、道德规范、正义观念、宗教规则、礼仪、乡规民约、社团规章、契约;先前法、外地法、外国法、国际法、法的解释;国家和有关社会组织的政策、决策、决定、行政命令;司法判决或报告书;法理、法学家著作、理性和事物的性质、哲学观念、科学探讨。〔51〕参见同前注〔40〕,周旺生文,第4-5页。如果对特定法律得以形成的这些质料基础进行考察,就属于法社会学的研究。
法的创制视角下的法的渊源理论尽管大体可以自圆其说,但不具备恰当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它会使得“法的渊源”成为空洞的纯描述性概念。例如就立法的语境而言,立法者所要考虑的立法材料的来源可能是多方面的,同时立法要受制的各种因素也是数不胜数的。就特定法律规范的制定而言,决定立法的内容的东西是什么,无法作一般性的理论限定。将法的渊源的概念运用于这个方面,会使法的渊源的外延无限扩大,确定性不强。〔52〕参见郭忠:《法律渊源含义辨析》,载《法治论丛》2007年第3期,第64-65页。退一步讲,即便可以将所有可能影响立法内容的材料在一般性的层面上完整地列举出来,也意义不大。因为这样的理论只是对现实或可能发生之事的描述式归纳而已。另外,研究法律内容的来源,尤其是当这种内容可以在历史上可以追溯到比较古老的来源时,事实上就会将法的渊源研究变成法律起源研究,从而造成混淆。〔53〕类似观点,参见同前注〔36〕,彭中礼文,第105页。当然,论者或许并不认为法的创制视角下的法源理论属于纯描述性理论,而试图将其纳入法政策学(立法政策学)的范围。如周旺生就认为,不是所有法的渊源(道德、习惯、乡规民约等)都适合转化为法,法律人应善于选择那些健康、向上且同法的特质相吻合的法的渊源,予以提炼、整合和改造制作,以形成良法美制。〔54〕参见同前注〔43〕,周旺生文,第20、24-26页。但很明显,立法政策学涉及对法的渊源的“选择”“提炼”和“转化”,而这些必然涉及立法者的价值判断和策略考量,所以法的渊源依然只是备选的质料,本身并不包含规范性标准。
2.法的适用的视角
法的适用视角下的法源学说要回答的问题是,法官在进行裁判发现时必须适用哪些条款,并根据其来源对这些条款进行体系化。〔55〕Vgl.Bernd Rüthers/Christian Fischer/Axel Birk,Rechtstheorie mit Juristischer Methodenlehre,8.Aufl.,2015,S.141.换言之,它涉及的并非普通公民的行为受什么样的规则管辖,而是法院在解决具体纠纷时应该适用哪些法律的问题。〔56〕参见[美]格林顿等:《比较法律传统》,米健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54页。相比于法的创制的视角,法的适用的视角更符合“法源”的原初含义:这一术语源自罗马法中的“fons juris”,后者产生于司法实践,是指法官选取和发现纠纷解决依据的场所,或者法官从中发现裁决案件所需要的裁判规范。〔57〕参见彭中礼:《法律渊源词义考》,载《法学研究》2012年第6期,第49、57-58、64-65页。“司法渊源说”即持法的适用的视角。
(1)广义的法的渊源
法的适用视角下的“法的渊源”概念可以在广义和狭义两种意义上来理解。广义上,它指的是一切对客观法有决定性的影响因素。在此意义上的法源范围与上述法的创制视角下的法源差别不大,区别只在于,它是立足于法的适用或法律发现的语境,从适用者(尤其是法官)因裁判之需要而去寻找之材料的角度出发而言的。这些材料能帮助法官正确地认识现行法,因而能起到法律认知辅助的功能。在广义上,一切影响司法裁判的真实因素都可被称为的法的渊源。它们属于社会学或心理学意义上的法源。〔58〕参见同前注〔55〕,Bernd Rüthers/Christian Fischer/Axel Birk书,第142页。部分持“司法渊源说”的学者就是在此意义上来使用法源的概念的。
在法的适用视角下,将这种社会学意上的法源推展到极致,就是法律现实主义者的法源观。这一进路的代表是约翰·格雷。格雷认为,在法官进行法律适用之前,法律并不存在,存在的只是制定法、先例、专家意见这些法的渊源。法律就是由作为任何国家或人类组织化团体之司法机构的法院所发布的、用以确定法律权利与义务的规则。〔59〕参见[美]约翰·奇普曼·格雷:《法律的性质与渊源》(原书第二版),马驰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71页。换言之,我们通常所说的“法律”并不是真正的法律,而只是“法的渊源”,真正的法律是司法裁判行为的产物,也即判决本身。因为法律原本就是法官的创造物,不判决、无法律。现实主义的法源(法律)观完全颠覆了既有的理解,看上去证明了“法的渊源”独立于“法”的概念必要性,但存在相当大的问题。一方面,在概念论或本体论上,将判决等同于法律,认为在法官没有判决前不存在法律的观点能否成立本身就存疑。正如哈特曾指出的,即便法官在确定法律义务存在与否方面具有绝对的权威,也不能说明法律的存在要以这种权威为前提,事实上大部分时候法律在法官裁判之前就已经存在了。〔60〕参见[英]哈特:《法律的概念》(第三版),许家磬、李冠宜译,法律出版社2018年版,第207-213页。此方面不是本文的重点,在此不赘述。另一方面,仅就认识论而言,格雷的理论也徘徊在两种法的渊源理论之间:一种是弱的法源理论。它认为,像制定法、司法判例、专家意见、习惯法这类法的渊源是存在的,但这些法的渊源实际上对于法官的司法审判没有法律意义上的拘束力,法官实际上是在任意决定着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但问题在于,当法的渊源失去对法官的拘束力之后,法的渊源这一观念本身对于法学家来说也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另一种是强的法源理论,它认为,尽管法院有权发布确定法律权利义务的一般规则,也即法律,但法院的这种权力并不是绝对的,依然要受到相当的限制。〔61〕具体论证参见马驰:《作为法院创造物的法律——格雷法律渊源理论探究》,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11年第6期,第89-90页。而这种限制就来自于法源。但如果这种限制指的就是法律拘束力,那么法的渊源至少就是法律的一部分,因为具有法律拘束力的东西就是法律。如果这种限制指的是心理学或社会学的意义上的拘束力,也即将法的渊源视为从外在和内在影响法官判决的真实因素,那么依然解决不了诸如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影响裁判的事实因素不被叫做法源,为什么损害赔损判决会使用的数学运算法则不是法源,为什么法官的个人情绪不是法源?〔62〕这里参考了马驰:《法律认识论视野中的法律渊源概念》,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16年第4期,第115-116页。换言之,法的渊源理论固然不能抱持“法律且只能是法律”的简单信条,〔63〕参见同前注〔34〕,何海波书,第180页。但“不是法律却可以作为裁判依据”的范围依然要根据一定标准受到限制。综上,在现实主义或法社会学的视角下,法的渊源的概念要么缺乏规范性意义,要么没有足够的区分度。
(2)狭义的法的渊源
狭义上的法的渊源属于真正法学意义上的法的渊源。在这种意义上,只有对于法律适用者具有法律拘束力的规定才是法的渊源。它认为,法源理论的研究重心,不在于考察法官判决得以形成的现实基础,或者说列明影响特定判决的所有因素,而在于为对司法裁判具有法律拘束力的规范基础提供理论证成,并将其与法的渊源之外的其他影响裁判的因素区分开来。在学科上,这属于法理论的研究。之所以要从法理论的视角去研究“法的渊源”,或者说持狭义的法源观,主要是基于两方面的考虑:
其一,狭义的法源观来自法教义学在法学中的核心地位。按照德国传统的二分法,法学可以被一分为二,即法教义学与基础研究。法教义学是法学的固有组成部分(被称为“狭义法律科学”),它是围绕现行实在法进行解释、建构和体系化的活动,〔64〕具体参见[德]古斯塔夫·拉德布鲁赫:《法哲学入门》,雷磊译,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第8-10页。最终服务于为具体案件提供规范性建议。因此,法教义学具有十分明显的实践旨趣和适用导向。相反,基础研究从别的学科视角出发来研究法律,比如从哲学角度研究法学就是法哲学,从社会学角度研究则形成法社会学等等。〔65〕参见[德]迪特玛尔·冯·德尔·普佛尔滕:《法哲学导论》,雷磊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44-45页。它们能够从别的学科中吸纳有益的观点和知识,以服务于法教义学的发展。但是,基础学科并不直接与法教义学发生关联,而是要通过中介性的学科分支,即法理论。法理论是关于实在法的一般理论,是各个部门法教义学的总论,它调控着相邻科学对于部门法学的知识输入,承担着知识筛选功能。〔66〕参见雷磊:《法理论:历史形成、学科属性及其中国化》,载《法学研究》2020年第2期,第33页。因此,最贴近法教义学、且与法教义学一起构成“法学”固有学科的,就是法理论。对于法源理论而言,首先要做的就是在民法法源、宪法法源、行政法法源等部门法教义学理论的基础上,构筑出一般性的法源理论。这种一般性的法源理论有别于法哲学和法社会学的研究,应当属于法学的内部视角。也只有这样的法源研究,才能对于以适用为导向的法教义学、乃至基于教义学的法律实践具有直接的意义和价值。
其二,狭义的法源观符合裁判之原因与理由的二分法。法源理论要为司法裁判提供具有法律拘束力的规范基础,也即裁判依据。法的渊源其实就是这种裁判依据的来源。在此,“裁判依据的来源”既可以被理解为裁判依据得以产生的原因,也可以被理解为裁判依据得以成立的理由。前者是对“规范如何成为法”所作的社会—科学上的说明,而后者是对“支持规范作为法”所作的法律—科学上的证立。〔67〕See Roger A.Shiner,Strictly Institutionalized Sources of Law:Some Futher Thoughts,20 Ratio Juris 310,311(2007).前者就是法社会学或法心理学所持的广义法源观,这种研究致力于因果科学式的探寻。在这种观点看来,法的渊源探讨的是司法裁判本身(“果”)产生的原因问题。更确切地说,它要追问的是“是”的问题,也即现实的司法裁判实际上受到了哪些因素的影响,从而使之成其所是。质言之,它将法源理解为“惯常的法律—社会行为的事实上的产生根据”〔68〕Ignatz Kornfeld,Soziale Machtverhältnisse:Grundzüge einer allgemeinen Lehre vom positiven Rechte auf soziologischer Grundlage,1911,S.73.。所以,只要是在现实司法过程中影响裁判的一切因素,无论是否具有规范意义上的法律性质,都可以被视为法源。在法律现实主义的极端版本中,甚至连法官的个性特征也可以被算作法源。〔69〕关于法官个性对于审判的影响,参见[美]杰罗姆·弗兰克:《法律与现代精神》,刘楠、王竹译,法律出版社2020年版,第84-96页。与这种法源概念相应的是,是将法视为经验—事实性行为规范的观点。〔70〕Vgl.Alf Ross,Theorie der Rechtsquellen,1929,S.305.相反,法理论的法源概念探讨的并非法官作出裁判的真实原因,而更多是裁判得以证立的理由。理由与原因最大的区别在于,它不仅能说明裁判为什么会产生,而且能为裁判的正当性进行辩护。在法理论的视角下,法源追问的是“应当”的问题,它具有规范性。
原因和理由的区分涉及裁判理论上的一个经典区分,即法的发现与法的证立。简单地说,前者是法官思考得出某个法律结论的实际过程或者说“真实”过程,后者则是他对这个结论提供论据进行论证说理的过程。〔71〕详细论证参见焦宝乾:《法的发现与证立》,载《法学研究》2005年第5期,第152-160页。从哪个层面对于司法裁判进行研究原本无可厚非,属于研究者个人的认知兴趣问题。但是,法学本身是一门规范学科。这样的特质决定了,它的主旨并不在于探究某项活动的现实成因和动机要素(社会学研究与心理学研究无疑更能胜任这项任务),而在于为这项活动提供辩护或者说正当化。所以,法理论关注的重点在于是否能充分而完整地进行对法学判断之证立,而不在于这个裁判事实上是透过何种过程发现的。司法决定的客观性置于司法证立的过程,即法官支持自己的结论时所给出的“合理化”。〔72〕See Martin Golding,Discovery and Justification in Science and Law,in Aleksander Peczenik et al.eds.,Theory of Legal Science,Springer,1984,p.113.规范学科关注的,是如何基于法律人共同体所支持的范式,通过正当和可接受的理由,以可检验的方式为司法裁判提供充分的证立。而法源则构成了这些理由和论证方式中的重要一环。相反,那些实际上影响创造法律机关的观念,例如,道德规范、政治原则、法律学说、法学专家的看法等,这些“渊源”本身并无任何法律拘束力。这些所谓的法的渊源是在“一种完全非法学的意义”上来使用的。〔73〕参见[奥]凯尔森:《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沈宗灵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7年版,第203-204页。只有将法源理解为理由,而非“裁判得以作出的原因或影响它的一切因素”,才能避免这一概念大而无当、缺乏区分度的缺陷。因此,法理论支持的是一种规范性的法源概念,它将法源视为法律论证活动中用以支持裁判结论的理由。
就此,可以得出结论认为:在法理论层面上,法源理论致力于在法律论证的场域内,寻找和证成对司法裁判具有法律拘束力之规范基础。从这一点而论,“司法渊源说”大体是可以成立的,但它没有说清楚的是,作为裁判规范基础的法律规范与法的渊源之间究竟有何区别和联系。这就涉及法源理论的性质问题。
三、法源理论的性质:宏观理论抑或微观理论?
从法的适用或法律论证的角度来看,法源理论旨在为司法裁判提供规范基础,因此法的渊源与法律规范之间存在着紧密关联。但问题在于,法的渊源指的就是作为司法裁判之依据或大前提的法律规范吗?一种流行的见解对这一问题给出了肯定的回答。例如,民法学界就普遍认为,法源指“一切得为裁判之大前提的规范的总称”〔74〕例如黄茂荣:《法学方法论与现代民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71页;朱庆育:《民法总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5页以下。。法理学界持此论点的也不在少数。持“司法渊源说”的学者就指出,法的渊源是裁判规范的集合(体),法官从中发现裁决案件所需要的裁判依据和裁判理由。〔75〕参见同前注〔57〕,彭中礼文,第64页;同前注〔36〕,彭中礼文,第106页。简单地说,就是“应当从中推导出裁判标准的法律规范”〔76〕Klaus F.Röhl/Hans Christian Röhl,Allgemeine Rechtslehre,2008,S.519.。“效力渊源说”也同样如此,其认为,法的渊源是指为当下法律所赋予法律效力的裁判案件的依据,或者说,是具有法律效力、能为人们所感知,能够在司法判决中加以明示但又无需再证明的理由。〔77〕参见周安平:《法律渊源的司法主义界定》,载《南大法学》2020年第4期,第35页。这些论点十分正确地看到了法的渊源在司法裁判中的功能,也即担当法律论证的大前提,或者说裁判案件之依据或理由的角色。但它们却模糊了法的渊源与法律规范之间的界限。事实上,尽管法的渊源的确要为司法裁判提供裁判依据(大前提),但它本身却不是法律规范。因为成文法、判例和习惯只是法律规范的可能物理载体,法律规范需要通过解释才能从它们中产生。〔78〕See Fábio Perin Shecaira,Sources of Law are Not Legal Norms,28 Ratio Juris 15,15-30(2015).因此,在审判中真正被适用的是法律规范,而成文法、习惯法、法官法等则是这些法律规范的渊源。〔79〕参见刘文科:《民法的法源是如何形成的?》,载《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第133页。
正是因为看到了这种“认识论间隙”,有学者区分使用了法的渊源与法律规范,认为法的渊源是承载法律的物理形式,法律规范是法的渊源这种物理表现形式的意义。在制定法和判例法的情形中,法的渊源是指由规范语句本身构成的语言形式,它们的意思属于规范命题,即法律规范。而在习惯法的情形中,承载法律规范的物理形式不是语句,而是在特定时空中频繁发生的社会实践。〔80〕参见同前注〔62〕,马驰文,第117-118页。当然要指出的是,是否有语言(语句)形式并非关键,习惯法同样可以用语言(语句)记载下来。所以下面对将法的渊源与法律语句相等同之观点的批评也适用于该文。这种理解相比于前一种理解具有很大的进步,但在很大程度上与前一种理解犯了同样的“范畴错误”。因为它给人的印象是:至少在制定法和判例法的情形中,法的渊源与法律规范这两个范畴属于同一个层面,也即微观层面,只是一个是语句或特定的社会实践形式,另一个是这种语句或实践的意义。〔81〕类似地,行政法学者何海波虽然区分了法的渊源与法律规范,但同样不自觉地从微观层面来看待法的渊源。因为他虽然基于反立法中心主义的立场,主张法律条文只是探寻法律规范的根据之一,但大体也是在同一个层面上来对待(区分)法律渊源与法律规范这两个概念的,参见同前注〔34〕,何海波书,第190页。虽然两者并不必然一一对应,〔82〕这里还涉及法律的个别化(Individuation of Law)理论,参见Joseph Raz,The Concept of Legal System,Clarendon Press,1980,p.70。这种理论区分了法律的表达单位(如法律条文)与法律的意义单位(法律规范),要求在不同的表达单位之间建立逻辑关系才构成意义单位。但至少处于同一个逻辑层次。但如此一来,“法的渊源”就无以区分于“法律语句”(在制定法语境中,也被称为“法律条文”)。
事实上,法的渊源既不是法律规范,也不是法律语句,因为它所指的并不是微观层面的事物,而是指涉“制定法”“判例(法)”“习惯(法)”等等这些宏观的物理形式本身。法源理论关心的是:特定司法裁判活动中作为案件裁判依据的法律规范,要从哪些宏观的物理形式中去寻找。所以,法源理论是一种宏观理论,而非微观理论。这是因为,从法学方法论的层面看,法源理论只负责完成法律适用的第一步。一旦确定了某种宏观物理形式(如制定法)是“适格的”,那么就可以从适格之规范文本形式(如制定法文本)中找到特定的规范性语句,以用作塑造作为案件裁判依据之规范命题的基础。至于找到的是哪个或哪些具体的法律语句,它们又如何重构或结合为法律规范,就属于规范理论层面的操作,而不属于法源理论的任务了。法源理论只负责提供它们的“来源”,而这种来源的范围是在具体裁判活动之前就被宏观认定了的,不依待解决之个案而定。〔83〕这里的意思只是说,例如,如果一个国家只承认制定法和习惯法为法源,那么就不会因出现一个新的案件就去承认判例法亦为法源。但是,在具体案件中有哪些法源类型出场则不一定。如在该国的多数案件中,只需制定法出场即可;但在出现法律漏洞的案件中,则同时需要习惯法出场。这是两回事。将法源理论定位为宏观理论,还可以解决一个在微观层面上令人困扰的问题:制定法文本中的非规范性条文是不是法源?这一问题的背景是,法的渊源虽然致力于为司法裁判提供寻找法律规范的指引,但并非构成法源之规范性文本的所有组成部分(法律语句)都表达法律规范。不直接表达法律规范的条文被称为非规范性条文,至少包括定义性条文、附属性条文、宣告性条文这几类。〔84〕参见舒国滢、王夏昊、雷磊:《法学方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16-118页。例如,我国《民法典》第1260条规定,本法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它就属于附属性条文。如果将法的渊源定性为法律语句,那么就会产生不表达(提供)法律规范的法律语句是否属于法源的问题,由此产生争议和解决困境。〔85〕参见同前注〔62〕,马驰文,第124-125页。但如果将法源理论定位为宏观理论,那么这就只是一个伪问题。因为无论在法律适用过程中这些非规范性条文与法律规范的关系为何,都不影响制定法作为法源的地位。反过来说,在此语境中,法源理论要解决的仅仅是“制定法是否属于法源”这一点,至于制定法文本内部的条文间关系如何,则属于法学方法论的下一阶段的任务了。
但换一个角度看,这种作为宏观物理形式的法源其实就是前面所讲的“法的形式”或“法的表现形式”。这也是主流的“表现形式说”的立足点。但上文论述已表明:更准确地说,法的渊源还不是这些法的形式,或者说各种类型的规范性文本或载体,而是产生不同形式的法的规范性行为或事实,例如立法行为(事实)、(判例制度下的)司法行为(事实)、社会实践等。不仅习惯法来源于社会实践,而且制定法和判例法也分别来源于立法实践或司法实践,只不过它们属于由特定机构主体来实施的制度实践,是集权式的、而非像形成习惯法时那般分散式的法的创制实践。当然,在这些规范性行为(事实)与法的表现形式之间的确存在一一对应之关系,如“立法(行为)—制定法”“司法(行为)—判例法”“社会实践—习惯法”。也正因为如此,“法源”一词经常在这两种意义——规范性行为与规范性文本或载体——之间交替使用。〔86〕See Riccardo Guastini,Fragments of a Theory of Legal Sources,9 Ratio Juris 364,368(1996).甚至有学者将规范性行为称为“内部法源”,将规范性文本称为“外部法源”,参见Felix Somló,Juristische Grundlehre,1917,S.330。再联系刚谈到的法律规范及其物理表现形式的区分,那么可以这么说:在特定个案中,具备适格物理表现形式的规范性文本或载体(如狭义上的法律)可以被称为适用于此案的特定法律规范的“渊源”,而这种规范性文本或载体的“渊源”则在于相应的规范性行为(如狭义上法律的制定行为)。所以,更准确的做法是用法源来指称法的创制行为,〔87〕要注意:其一,这里的“法律创制”既包括立法行为,也包括产生判例法的司法行为和产生习惯法的社会实践;其二,与前文所说的法的创制视角的法源理论聚焦于法律创制过程中的素材或质料不同,这里指的是法律创制“行为”本身。只有在此意义上才吻合法的“来源”这一身份。
从法律论证的角度看,准确地说,作为司法裁判之大前提的并不是“法律”规范,而是规范命题。两个规范可以内容相同(表述同一个规范命题),但在性质上或效力上截然有别,例如“不得杀人”既可以是道德规范,也可以是法律规范。所以,同一个规范命题既可以成为法律规范,也可以成为道德规范,关键要看这个规范命题具备法律效力还是道德效力。法的渊源在此恰恰扮演着“法律效力赋予者”的角色:正是上述这些规范性行为(事实)赋予了相应的规范性文本、进而赋予了作为这些规范性文本之组成部分的法律规范以“法律”的性质或效力。如果某个规范命题最终可以追溯到适格的法律创制行为(如立法行为),或适格的法的表现形式(如制定法),那么它就具有法律效力,它也就是“法律规范”。离开了法律创制行为,我们就无法知晓某个规范究竟是不是法律规范。所以“法律规范”的说法本身就包含着渊源的意味。虽然出于使用习惯的考虑,在本文中大部分时候并不仔细区分规范性行为与规范性文本,只是要清楚的是,在我们使用“制定法”“习惯法”等用语之处,其精确意义指的是产生制定法的立法行为或产生习惯法的社会实践。我们将这些产生行为视为法律规范的依据,或者说裁判依据的来源。
无论如何,法源理论是一种宏观理论,而非微观理论。它旨在确定法律论证之大前提(法律规范)的“适格”来源,而不涉及法律规范与其表现形式(法律语句)之间的关系及其具体适用问题。
四、法源理论的任务:外部范围与内部层级
上文的论述已然涉及法源理论的任务。司法裁判是一个说理和论证的过程。法源理论的任务为何,必须要放入整个法律论证的结构中去探寻。司法裁判中的法律论证在结构上可以被区分为“内部证成”与“外部证成”两个层面。前者涉及的是从既定前提中推导出作为结论的法律决定的有效性问题,而后者涉及的则是这些前提本身的正确性或可靠性问题。〔88〕Vgl.Jezy Wróblewski,Legal Decision and its Justification,in:H.Hubien(Hrsg.),Le Raisonnement Juridique,Akten des Weltkongress für Rechts-und Sozialphilosophie,1971,S.412.换言之,从得到证立的前提(外部证成)出发,合乎逻辑地推导出结论(内部证成),就构成了法律论证的全貌。需要在外部证成层面上得到证立的前提按性质可分为两类,即规范命题与事实命题。事实命题证成的核心问题在于,司法裁判所要采纳的小前提即案件事实是什么?案件事实的形成涉及法律规范与生活事实的匹配,也涉及证据问题,在此不赘述。规范命题的确立可能涉及四组问题:第一,应当去哪里寻找裁判的大前提(规范命题)?第二,大前提(规范命题)与小前提(事实命题)之间存在缝隙怎么办?第三,找不到可直接适用的恰当大前提怎么办?第四,所引规范命题是否来自于有效的法律规范?〔89〕参见同前注〔84〕,舒国滢、王夏昊、雷磊书,第215-220页。在这四组问题中,第二组问题涉及法律解释,第三组问题涉及法的续造,第一组问题涉及的就是法的渊源,而第四组问题是特殊问题(效力问题),它与第一组问题存在关联,但也不同。
(一)法源理论的外部任务
对于裁判个案的法官来说,首要的任务就是要“依法裁判”。但是,适用于当下案件的法律规范并不是给定的,而是需要他自己去寻找。这里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他在多大的范围内活动,才能算是依“法”裁判?换言之,依法裁判的“法”,也即可以用来证立裁判结论的大前提,其范围有多大?这个范围在不同的国家是有所不同的。例如对于德国法院的法官而言,这一范围包括宪法、法律、法规、宪法法院的判例、习惯(法)等;对于美国法院的法官而言,则既包括成文法也包括判例法,还有习惯(法)。而对于中国法院的法官而言,它主要包括规范性法律文件(制定法),表现为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还有习惯(法)、指导性案例等。超出特定范围去寻获的规范无法成为裁判的依据,据此得出的裁判结论也不具有法律效力。〔90〕从另一个角度看,法源范围的大小其实也代表着法官权力的大小:法官是必须较严格地受制于立法者向他给定的裁判依据(制定法),还是也可以在此范围外去进行“自由的法律发现”?这就涉及司法权与立法权的关系问题了,而这一问题是一个宪法问题,参见同前注〔55〕,Bernd Rüthers/Christian Fischer/Axel Birk书,第142页。因此,法官要面对的第一项工作,就是要确立,在特定国家的司法裁判中,可寻获裁判依据之范围有多大。只有以在此范围内寻获的法律规范为依据所作的判决才是具有法律效力的。而这个范围有多大,取决于法律规范的“适格的”来源包括哪些,也就是依法裁判之“法”去哪里寻找的问题。如前所述,立法行为、(判例制度下的)司法行为、社会实践等等都可能成为寻找的场所。法源理论最为重要的任务,就在于确定司法裁判之依据的来源及其范围。
在此,法的渊源与法的表现形式、法的效力之间的关系也一并得到了澄清。一方面,必须承认,在司法裁判中,法的表现形式与法的渊源往往难以区分,因为看起来各种规范性法律文件与具体的规范创制行为之间存在一一对应关系。例如在通常情况下,我们是说“司法裁判依据的来源是法律制定行为”,还是说“司法裁判依据的来源是法律”,是说“司法裁判依据的来源是行政法规制定行为”,还是说“司法裁判依据的来源是行政法规”,并不会产生实际差异。正因为如此,事实上“司法渊源说”的支持者通常也不反对“表现形式说”本身。例如陈金钊就曾指出,从法律适用的视角看,法的渊源与法的形式无法区分清楚:法的形式本身并不是法的渊源,但当法官判案把其作为构建判决的法律来源时,它就成了法源。因为人们无法在描述司法过程的时候驱逐法的形式,法的渊源与法的形式的结合才能使我们看到法官发现法律的场所。〔91〕参见同前注〔31〕,陈金钊文,第1、5页。郭忠也认为,从司法裁判的角度看,法的渊源和法的形式是重合的,只是所指称的各有侧重而已。〔92〕参见同前注〔52〕,郭忠文,第63页。类似的主张,参见同前注〔37〕,舒国滢主编书,第69页。该书虽然竭力区分法的渊源与法的形式,但也承认,它们只是“具有不同的意义和不同的认识角度”。
但另一方面,也要看到,法的表现形式与法的渊源虽联系密切,但毕竟有所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等制定法的不同表现形式,看起来对应于不同的具体规范创制行为(立宪行为、法律创制行为、行政法规创制行为、地方性法规创制行为),但它们事实上拥有同一效力的来源。因为制定法本身构成了一个依据效力链条联结起来的等级体系,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等从高到低依次位于这个体系的不同层级。下位法虽然由特定法律创制机关的行为直接创制而来,但这种行为只有符合上位法的授权时才会创制出“有效的”下位法,如此层层往上追溯,最终可以追溯至最根本的立法行为,即立宪行为。〔93〕当然,按照凯尔森的阶层构造理论,所有层级的法律规范最终都必须回溯到的终极效力来源并非立宪行为的事实,而是作为超验逻辑预设的基础规范,参见Hans Kelsen,Matthias Jestaedt(Hrsg.),Reine Rechtslehre(2.Aufl.,1960),2017,S.346 ff.。但这已涉入法哲学领域,本文不予考虑。所以这些规范性法律文件拥有相同的效力来源,我们笼统地称之为“立法”,以区别于先前的司法行为(判例)或习惯。不同的具体规范创制行为只是创制出了内容和表现形式不同的规范性法律文件,但却没有创制出不同的效力来源。所以,具体的规范创制行为本身并不是效力意义上的法源,而仅是为司法裁判提供各种内容之裁判依据的来源。恰恰在这里“效力渊源说”暴露出了不足。因为它固然看到了法的效力与法的表现形式之间的紧密关联,却没有看到它们之间的区别:同一种法的效力来源可以呈现不同的法的表现形式。〔94〕这一点至少适用于制定法。至于判例法和习惯法,情形较为复杂,在此留而不论。
当然,反过来说,这些不同的规范性法律文件毕竟构成了认识法的渊源的“表征”。因为法的表现形式作为各类规范创制行为的物理结果,毕竟要比作为立法行为的法的渊源本身更易辨识。在裁判时,法官更容易寻找的恰恰是这类法的“表征”或“表现形式”,而不是隐藏于其后的法律创制行为。在此意义上,主流的“表现形式说”有一定的道理,但它只是抓住了法的渊源的表层:法的各种表现形式只是各种具体规范创制行为之结果的呈现,而非法的渊源本身。所以,在准确意义上,法的表现形式并不等同于法的渊源,但它们是法的渊源的表征与识别依据。
(二)法源理论的内部任务
如果说划定司法裁判之依据来源的范围属于法源理论的外部任务,那么它还有一个内部任务,那就是确定不同法源(形式)的适用顺序。〔95〕类似观点参见韩荣和:《法的渊源的位阶结构》,载《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第34页。因为不同的法源(形式)可能会为司法裁判提供不同的法律规范,此时就必须明确何种法源或其提供的法律规范可以优先作为裁判的准则。这里又分为两种情形:第一种情形是,在性质不同的法源及其表现形式之间确立适用顺序。例如,如果在一个国家中,适格的法源类型包括制定法和习惯法两种,那么法源理论就需要在这两者之间进行排序,如确立“有制定法的从制定法,无制定法的从习惯法”这一准则(或者相反)。如此,制定法规范就优先于习惯法规范作为裁判依据,只有当出现制定法漏洞时,法官才去考虑习惯法规范。第二种情形是,在性质相同的法源及其表现形式之间确立适用顺序。例如,同为立法行为的产物,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等制定法形式亦可能提供各不相同的法律规范。此时并不像第一种情况那样,奉行“有宪法的从宪法,无宪法的从法律”“有法律的从法律,无法律的从行政法规”这类准则。因为假如如此,就会使得下位法的制定丧失意义。相反,基于“禁止向一般条款逃逸”的原理,在通常情况下,法官要优先适用规定得更为具体和细致的下位规范,没有时再去考虑相对抽象和一般性的上位规范。此谓“法律位阶的适用顺序”。〔96〕同前注〔37〕,舒国滢主编书,第76页。但是,在例外情况下,也即当法律规范在内容上相互冲突或不兼容时,就必须依靠法源效力的位阶来解决冲突。法源效力的位阶取决于立法权的等级,而立法权的等级主要取决于立法的主体。例如,在我国,人民权力高于一切国家机关的权力,因而宪法居于规范性法律文件位阶的顶端;立法机关的权力高于其他国家机关的权力,因而法律的位阶高于行政法规和其他文件;中央权力高于地方权力,因而行政法规的位阶高于地方性法规,等等。〔97〕参见胡玉鸿主编:《法律原理与技术》,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22页。所以,如果两个相互冲突或不兼容的法律规范所属的规范性法律文件恰好分别位于这些不同位阶,它们就可以依据“上位法优于下位法”的冲突规则来确定优先顺序。同时,这也会使得下位法失效。
也恰恰在这里,法源理论有可能与第四组问题,也即效力理论发生联系,但是两者依然是不同的。因为虽然这两组问题都与“法的效力”密切相关,但着眼点并不一致。首先,法源理论中的效力问题属于一般层面的问题,而效力理论中效力问题涉及具体的特殊场合。在大多数情形中,只要是在法源范围内寻找到的法律规范,其效力便不会受到质疑,因为法源划定范围内的一般都是“现行有效的法律规范”。所以,法的渊源只是根据规范性文本或载体是否具备“适格的”来源而对其效力作一般性判断。而效力理论涉及的仅是法律规范发生冲突这一具体的特殊场合,只有在这个场合下,下位法规范才会丧失效力。其次,也由此可见,法源理论中的效力只是初始的(prima facie),而效力理论中的效力是在确定性和终局性的意义上说的。前已述及,在法源理论中,只要具备适格的来源,或者说处于具有法律效力的文本或载体之中,法律规范就具有法律效力。但这种法律效力具有初始性,也就是说,虽然符合此条件的法律规范“应当被适用”,但这种“应当”只具有初步可行性。在具体的个案中,也许会存在种种情况(上下位法的冲突就是其中一种),在通盘考量(all-things considered)之后,使得此备选的法律规范最终被判定为无效。而判断个别法律规范之确定和终局效力正属于第四组问题的任务。再次,法源的效力情形无法涵盖效力问题的所有情形。法源的效力只涉及规范性文件的位阶和等级,但是,效力理论还涉及许多其他情形,例如同一位阶的法律规则间的冲突、法律规则与法律原则间的冲突等。在极特殊的情况下,它还涉及法律规范是否属于“恶法”的情形。这就将涉及法哲学上的讨论。〔98〕对此可参见雷磊:《法哲学在何种意义上有助于部门法学》,载《中外法学》2018年第5期,第1181-1187页。最后,即便限于上下位法冲突导致下位法律规范无效的情形,法源理论与效力理论的关切点也是不一样的:前者并不意在解决两条具体的法律规范之间的冲突,只是法源的位阶性恰好为法律规范冲突的解决依据——上位法优于下位法——提供了标准而已。因为归根结底,法源理论仍是宏观理论,在微观层面上解决规范冲突、乃至个别法律规范的终局效力问题,并不属于它的任务。
总之,法的渊源是一切围绕规范命题的法律论证活动(法律适用活动)得以开展的起点,只有依据“适格的”法源确定了可作为裁判依据的法律规范的范围之后,才有对在此范围内的法律规范进行解释、续造,乃至在特殊情况下判定它们的终局效力的问题。而法源理论本身的任务是双重的,那就是从外部划定司法裁判之依据来源的范围,以及从内部确定不同法源(表现形式)的层级或适用顺序。
五、结语
德沃金曾将法学中可能用到的概念分为三类,即标准型概念、自然类型的概念与解释性概念。与前两类概念不同,解释性概念鼓励我们去反思并且争论,我们已经建构出来的某些实践提出的是什么样的要求。〔99〕参见[美]罗纳德·德沃金:《身披法袍的正义》,周林刚、翟志勇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0-13页。“法的渊源”就属于一种解释性概念。评判这样一个解释性概念的得当与否取决于两个要点:一是它应当有自身独特的问题指向和实践旨趣,二是它应当有助于揭示法学(尤其是法教义学)视野中法律实践的特定面向。这就要求有一种法的渊源“理论”作为基本的认知框架。本文试图通过分析来说明,这样一个认知框架由三部分组成:一是法源理论的视角。法源理论应以法理论为核心视角,致力于在法律论证的场域内,寻找和证成对司法裁判具有法律拘束力之规范基础。二是法源理论的性质。法源理论是一种宏观理论,而非微观理论,旨在确定法律论证之大前提的“适格”来源,而不涉及法律规范与其表现形式(法律语句)之间的关系及其具体适用问题。三是法源理论的任务。法的渊源是一切围绕规范命题的法律论证活动得以开展的起点,肩负从外部划定司法裁判之依据来源的范围,以及从内部确定不同法源(表现形式)的层级或适用顺序的双重任务。与此同时可以认识到,法的表现形式不同于法的渊源,但却是法的渊源的表征与识别依据。在此框架下,本文支持一种修正版的司法渊源说,那就是,法的渊源指的是法律论证过程中对司法裁判具有法律拘束力之规范基础(裁判依据)的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