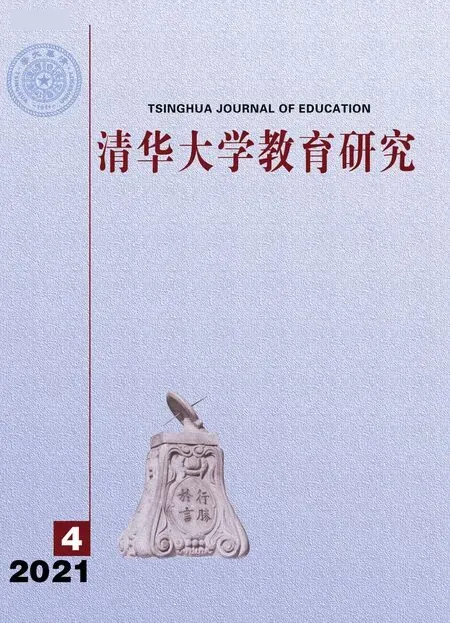教育理念如何型构社会预期?
张 静
(北京大学 社会学系,北京 100081)
我们已经是一个教育大国。在过去的150年中,中国受教育者从未达到今天的规模,教育对于社会流动的影响几乎是支配性的。根据社会学者的研究,1865-1905年清政府废除科举之前,超过70%的学生是官员或者士绅子弟;1906-1952年,超过60%的学生是地方产业人士和商人子弟,尤其是江南和珠三角地区;1953-1993年,超过40%的学生来自普通的工人家庭;1994年以来,超过50%的学生来自各地区的中产家庭和重点高中。(1)李中清.无声的革命:北京大学、苏州大学学生社会来源研究,1949-2002[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观察者网.中国教育精英四段论[EB/OL].https://www.guancha.cn/economy/2015_11_12_341076.shtml, 2015-11-12/2021-06-28.显然,目的是选拔精英的教育,已经转变成面向大众的普及教育,这是一个重大的结构性变化。
但是对照全球教育的发展目标,中国的教育理念是否适应了这种转变呢?这几天高中和职高各50%的分流试点政策,引起社会的不安。大量父母担心子女就读的中学被划入职高,中断孩子进入大学的路径。
为何非要进入大学?因为在中国,大学文凭是一次未来身份的筛选。文凭大致可以作为标识,确定人们初次进入社会时的基本位置——职业、阶层、地点以及社会地位。人们不能改变自己的出身,但却可能通过获得文凭改变自己的未来。在重要性上,文凭作为身份象征的意义,一向超过作为技能掌握的意义。在人们的评价中,“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即使不是优越于官吏,通常在社会地位上也被认为是与之平等的”(2)周荣德.中国的阶层与流动[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1.257-258.。
以筛选精英为目标的文凭教育,激励了一元化竞争的受教育动机和评价。无论对这个专业有兴趣否,自身适合否,人们都必须在筛选中赢,取得进入某种更高身份结构的资格。这种教育的理念和内容设置,不是产出掌握专门技能的劳动者,而是产出和普通劳动者不同的人。所以当毕业生落入普通劳动者阶层时,就被认为是不正常,会引起社会广泛的议论。
这和历史非常相像:只有受过教育者可以入选为“师”或者“吏”的后备,他们的身份显然区别于一般的劳动阶层。在社会分流中,脑力和体力的职业差别并非仅仅是劳动方式不同,更代表着社会身份不同。这种身份在获得教育文凭后就确定了,其后不会消失。看鲁迅笔下的孔乙己,家境破落到生活无着的地步,身份却还是一个读书人,自视与其他的劳动者有别。还比如,在袁世凯等上奏的“立停科举,以广学校”之“妥筹办法”中,官员们特别建议清廷,在取消科举时必做的一件事,是对“其以前举贡生员,分别量予出路”(3)清德宗实录(卷548)[M].北京:中华书局,2008.4-5.。可见,学历虽可消失,但身份不可不延续,那些曾经科举确立了功名者,其地位理应被朝廷和社会承认:即,旧式科举已经完成了他们的阶层进阶,科举改革虽废除了旧知识之有用性,但并不因此使得旧文凭持有者失去身份资格,所以须安排“出路”。
在这里,教育的角色,相当于是社会结构的门卫,控制着流动的社会身份分类以及再生产。正因为如此,才可以理解,为何中国历史上几次大的教育变革,客观上都曾改变不同人群的位置、职业和升迁路径,盖因为文凭具有变动不同人群之机会结构的效应。可以列举的,有科举制度的改变,这一举措曾切断了知识群体向官僚群体流动的固有格式,知识群体预期的机会结构和事业晋升模式也随之发生了变化。(4)邹谠.二十世纪中国政治[M].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4.52-53.这就是为什么在取消科举之后,整个社会的大变动随之发生。
这个基本现实,在今天还是没有大的转变。文凭提升社会地位并非仅指经济收入。它还包括更多的内容:有资格和机会进入的职业,有资格享用的政策特权(进入体制内,有福利保障),以及有资格享有生活地域的选择、工作稳定性、社会声望、资历的可积累性调动等等。显然,这些方面无法用金钱购买获得,经济收入高并不能代替社会地位高,后者须经过教育文凭获得。因此才有相当多的小企业主抱怨,自己虽然赚了钱但还是社会地位低。近年大量的毕业生蜂拥进入公务员考试,也不是仅仅在追求收入——实际上很多市场单位比公务员收入高——他们是在期望获得体面身份和受尊敬的职业,这也与社会地位考虑有关。由于教育和社会地位获得的这一特殊关系,很多人把自己晋升身份的障碍归因为学历,这一认识进一步巩固了文凭与社会地位预期的关系。社会上普遍的看法是,未来从事体力还是脑力工作,差别在是否经过大学以上教育。
令人惊奇的是,经由文凭获得地位,赢得安全和尊重,避免成为“劳动人民”的理念,并没有因过往几十年的“平等”教育而减弱。人们还是习惯人等的社会分类,力图与他人拉开距离,比如名片的抬头普遍愿意列出学历和职位,以显示较高的身份。文凭成为社会分类的前奏,意味着一个大学毕业生,如果还做与从前同样的工作,就会有浪费或丢人之感。大学生村官也必须用种种优惠政策推动,否则响应者少,原因是很少人认为,村官是大学生(身份)应当从事的工作。他们反问,如果要做村官,为何还要上大学?上大学难道不是为了离开农村吗?很明显,这些基层性的职业和工作地点,并不符合大学生对自己身份的预期,在学生心目中,取得文凭后进入更高级的单位或更大的城市是理所当然的,有文凭者与干部任职一样,终生可用,而且只能向上、不能向下流动,文凭越高就应离基层越远成为共识。在城乡二元体制短期内无法改变的情况下,文凭几乎是改变农民身份的首要途径,文凭教育也成为拖延就业的蓄水池,很多人宁愿不工作,也不愿意进入社会基层。
这些行为源自高等教育对于身份预期的生产,它让受教育者认为,自己已经脱离了原来的身份,有资格进入更高的社会结构位置。教育产出的社会身份“提升”预期,如果能够与社会实际的地位结构相符合,尚不存在问题,但如果二者背离,托克维尔所言“教育的缺点”就会发生。(5)托克维尔曾在自己的访美日记中写下如此感想:“在欧洲,最令我们头痛的是那些出身低微又接受了教育的人,教育使他们产生了离开本阶级的渴望,却没有为他们提供相应的手段。但在美国,教育的这一缺点几乎没有出现,教育总是提供致富的必要手段,并且没有引发任何社会问题。”(托克维尔,2010:38)此观察虽冷峻,但真实,值得思考。我们现在面临的挑战正是,教育生产出大量具有高身份预期的人群,但进入社会后他们不得不成为普通劳动者。市场需要的劳动者与教育制造的身份预期有极大错位,大量受教育者进入社会后,不得不面临再次的地位确定。在这种情况下,社会预期的稳定秩序被“扰乱”,就并非是个人、而是群体和结构性现象。而高学历教育的扩张政策,以及筛选人的文凭教育之等级理念,实际上加强了这种不确定性。(6)张静.社会身份的结构性失位问题[J].社会学研究,2010,(6):41-57.从政治社会学视角看,社会预期的不确定性,其实和社会稳定密切相关,当然也和社会治理密切相关。
这些现象,对于社会治理政策提出的问题是:由于教育生产社会预期,所以教育的目标和社会预期的管理有关。因为教育的目标是什么,决定了教育的产品——也就是一代一代年轻人的追求,他们追求身份地位还是追求成为掌握技能的劳动者。这提示了,从社会治理角度着眼,需要反思教育的基本理念和角色问题。因为教育在本质上,影响着国家未来的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