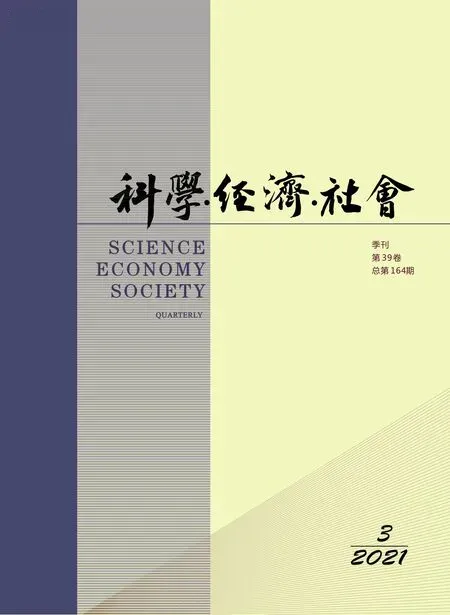《中庸》“诚”的思想
末永高康
佐藤将之 监译
序论
《子思子》一书,在《汉书·艺文志》[1]1724和《隋书·经籍志》[2]997中分别有“子思二十三篇”和“子思子七卷”的记载,今已失传。只是依据《隋书·音乐志》沈约的证言,一般认为,《礼记》的《坊记》《中庸》《表记》《缁衣》四篇应该是《子思子》的残篇。
关于《子思子》,武内义雄早已在《易と中庸の研究》一书中有过详细的分析[3]。武内将《中庸》一篇分为“中庸本文”(现行本中除十六章①本书为方便起见,依据朱熹对《中庸》的分章。以外,第二章至第二十章的“礼所生也”为止的内容)和“中庸说”(第一章,第二十章的“天下之达道五”往后的全部内容及章节)两个部分①武内将界定“中庸本文”时剔出的第十六章接续到了第二十四章。请参阅武内义雄:《易と中庸の研究》,东京:岩波书店,1943年,第22-24/55页。。他认为前者是子思本人著作,即便不是也至少可以说是最接近子思本人思想的文献,而推定后者为秦代子思学派的学者所作。另外,武内还将《坊记》《表记》《缁衣》三篇视为“子思子语录”,从而将之判定为《孟子》之前的作品。但在另一本著作《中国思想史》中,又推论“子思子语录”诸篇的成书应该晚于荀子。可见他的见解前后有变②武内义雄:《中国思想史》,岩波书店,1935 年,第116-117 页。就刊行年来看,虽然《中国思想史》比《易と中庸の研究》更早,但笔者认为后者更加反映出武内年轻时期的见解。。然而《缁衣》一篇,有郭店出土、与孟子几乎同时期的楚简写本《缁衣》(以下称“郭店《缁衣》”),也有上海博物馆藏楚竹简《缁衣》(以下称“上博简《缁衣》),可知《缁衣》成书晚于荀子的说法是不对的。本文基于从郭店《缁衣》和其他新出土数据中获得的见解,探讨所谓的《子思子》残篇与子思本人思想之间的关系。
一、关于楚简本《缁衣》
目前所认定的《子思子》残篇中,只有《缁衣》一篇得以完整地出土,因此,我们可以从这一篇开始探讨。目前掌握的《缁衣》的出土资料有郭店《缁衣》与上博简《缁衣》两种。由于两者内容大体相同③关于两种文本的对照,参照《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年;《上博简〈缁衣〉与郭店简字形对照表》。另外,虞万里的《上博馆藏楚竹书〈缁衣〉总合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以及《〈缁衣〉简本与传本,石经异同疏证》(上)(中)(下)中并列两种楚简本以及今本文本,比较方便对照。,本文将此两篇总称为楚简本《缁衣》,而将今本《礼记》中的缁衣篇称为今本《缁衣》,借以和楚简本区分。楚简本《缁衣》与今本《缁衣》之间除了部分文章不同之外,章次也不相同,而且今本中还加入了楚简本没有的章,据此,两者应该属于不同的文献。以下以简本的章次为标准,整理出两者章次之间的对应关系:
楚简本 → 今本
第一章 → 第二章
第二章 → 第十一章
第三章 → 第十章
第四章 → 第十二章
第五章 → 第十七章
第六章 → 第六章
第七章 → 第五章(按:今本第五章的一句《诗》的引文见于简本第八章)
第八章 → 第四章(按:今本第四章没有引《诗》,简本第八章引用的《诗》来自今本第五章)
第九章 → 第九章
第十章 → 第十五章
第十一章→第十四章
第十二章→第三章
第十三章→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七章前半部分(按:楚简本第十四章引用的《诗》来自今本第八章)
第十五章 →第七章后半部分
第十六章 →第八章(按:今本第八章引用的《诗》见于楚简本第十四章)
第十七章 →第二十四章(二十三章①括号内显示的是《正义》的分章方式,即没有把今本第十八章中两个“子曰”的部分归入别的章节时的章次。本文所用今本《缁衣》的分章方式并不依据《正义》。)
第十八章 → 第十九章(十八章后半部分)
第十九章 → 第二十三章(二十二章)
第二十章 → 第二十二章(二十一章)
第二十一章→ 第二十章(十九章)
第二十二章→ 第二十一章(二十章)
第二十三章→ 第二十五章(二十四章)在今本的内容中,简本中所缺的部分是,(今本的)第一章、第十六章、第十八章的前半部分、第二十五章(《正义》的第二十四章)中“兑命”以下的文字。
简本和今本之间的这些差异,一般认为是今本《缁衣》中存在文本错乱的结果,而简本《缁衣》则显示了《缁衣》的原型②参照泽田多喜男:《郭店楚简缁衣篇考》,东京大学郭店楚简研究会编:《郭店楚简の思想史的研究》第三卷,2000 年;佐川茧子:《郭店楚简〈兹衣〉と〈礼记〉缁衣篇の关系に就XIVて——先秦儒家文献の成立に关XIIItf一考察——》,《日本中国学会报》第五二集,2000 年。后者在《结语》中说:“比较《缁衣》与《礼记·缁衣》,就能知道前者为消失于先秦时期的现存最古的《缁衣》,经历后人增益和文章混乱之后变成了后者;同时亦可知《子思》《公孙尼子》(《汉书·艺文志》)中的《缁衣》皆非郭店本,而更近于《礼记》本。”顺带一提,关于今本错简过程的推定,有夏含夷的《试论〈缁衣〉错简证据及其在〈礼记〉本〈缁衣〉编篡过程中的原因和后果》(谢维扬、朱渊清《新出土文献与古代文明研究》上海大学出版社,2004 年)、虞万里《〈缁衣〉简本与传本章次文字错简异同考征》第六章、黄羽璇《郭店、〈礼记〉本〈缁衣〉比较──兼论传世本之形成与〈子思子〉的关系》(《简帛》第五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驳斥错简说,认为是今本编辑者刻意改编;无论是不是刻意改编,今本已失去祖本《缁衣》原貌的事实是不变的。。可以当作其证据的一个例子是,今本《缁衣》到了第二章才出现“缁衣”一词。先秦文献取篇名的习惯是从首篇中取有特色的几个字,而今本《缁衣》并未效法于此,可以说是十分奇特。相较之下,简本《缁衣》首章即相当于今本第二章,这符合先秦时代取篇名的习惯。另外,今本《缁衣》首章的内容并未出现在简本中,这种情况显示了今本首章是后来才添加的事实③《郭店楚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8年)、《缁衣释文注释》已经指出上述内容。。
因《缁衣》篇见于郭店楚简,几乎可以推断其撰写年代早于孟子。然而其作者是否为子思本人,尚有讨论空间。根据《经典释文》中引用的刘瓛之说,《缁衣》为公孙尼子之作,因而有宋代郑樵、叶梦得将《缁衣》当作《公孙尼子》的文章来引用的事情。然而《隋书·音乐志》中引用沈约之言,又说“中庸、表记、防记(按“坊记”)、缁衣皆取子思子,乐记取公孙尼子”[2]288,沈约在当时理应看过传世本《子思子》和《公孙尼子》,却并没有把《缁衣》归入《公孙尼子》。但依据刘瓛等的说法,当时的《公孙尼子》一书是包含《缁衣》的。也就是说,我们也不能排除《缁衣》一篇为公孙尼子之作的可能性。
目前最为支持“《缁衣》为公孙尼子之作”的学者是廖名春①廖名春:《〈缁衣〉作者问题新论》(《儒家思梦学派论集》,齐鲁书社,2008 年)。这篇论文整理了楚简本出现以后对《缁衣》作者的议论。郑樵、叶梦得将缁衣篇当作《公孙尼子》而引用的例子,亦可参照这篇论文。。廖名春将公孙尼子推定为《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记载的公孙龙,且以公孙龙较子思年长为由,推断《缁衣》作者为公孙尼子。廖名春又认为,《子思子》中之所以包含《缁衣》,是因为子思也将《缁衣》当作学习数据使用。然而廖说的不确定性在于,若要将公孙尼子推定为公孙龙,必须先得确认“尼”为“龙”(的草书)之误写的假设成立。而且他不知为何没有采用将《公孙尼子》排在《孟子》之前并判断其人为“七十子之弟子”的《汉书·艺文志》,却采用了撰写年代晚于《汉书》推测“尼,似孔子弟子”[2]997的《隋书·经籍志》。我们考虑到,文章形式与《缁衣》相同(关于这一点容后详述)的《坊记》《表记》都收录于《子思子》,那么推断子思为《缁衣》作者似乎较为妥当,至少没有任何线索表明这两篇曾收录于《公孙尼子》。笔者更倾向于认为,《缁衣》作者即便非子思本人,也应当属于子思学派,只不过后世因为某些原因而将其纳入了《公孙尼子》。
在研究《缁衣》与子思的关系时,简本《缁衣》的出土又拋出另外一个问题。唐代类书等文献中将《缁衣》当作《子思子》来引用的地方有三处,其中两处并未出现于简本《缁衣》中;剩下的一处与今本《缁衣》接近,与简本《缁衣》则有较大差异②《意林》卷一所引《子思子》为“小人溺于水,君子溺于口也”,见于今本《缁衣》第十六章“子曰,小人溺于水,君子溺于口”,楚简本《缁衣》中则无此章。另外,对于《文选》卷五一王襃的“四子讲德论”“君者中心,臣者外体”,李善注曰“子思子曰,民以君为心,君以民为体。心正则体修,心肃则身敬也”,对于同卷二四张华的“答何劭二首”“其言明且清”,李善注曰“子思子,诗云,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国家以宁,都邑以成”。今本《缁衣》第十七章有“子曰,民以君为心,君以民为体。心庄则体舒,心肃则容敬,心好之,身必安之。民必欲之。心以体全,亦以体伤。君以民存,亦以民亡。诗云,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国家以宁,庶民以生。谁能秉国成,不自为正,卒劳百姓”。对应到今本《缁衣》第十七章的楚简本第五章则为“子曰,民以君为心,君以民为体。心好则体安之,君好则民欲之。故心以体废,君以民亡。诗云,谁秉国成,不自为正,卒劳百姓”,画实线的语句部分一致,画虚线的语句则未出现。另外,画虚线的语句也未见于现行《毛诗》,“谁秉国成”以下三句则是《小雅·节南山》的语句。。这说明唐代类书等文献中引用的《子思子·缁衣》并未以简本《缁衣》为直接祖本。基于这一点,西山尚志进一步推论说:由于汉代文献从未引用过题为《子思子》的文章,《隋书·经籍志》所载七卷本《子思子》应该是六朝后期时根据《礼记》等文章编辑而成的。就这样,西山完全切断了《缁衣》与子思之间的思想关系[4]86-104。要是考虑到唐代类书等文献中引用的《曾子》皆与《大戴礼记·曾子立事》以下十篇一致,极有可能是根据《大戴礼记》编选而成,而非以《汉书·艺文志》所载“曾子十八篇”为直接祖本③参照拙稿《〈曾子〉初探——『大戴礼记』曾子立事篇PH中心にして》,鹿儿岛大学教育学部研究纪要(人文·社会科学编)第58巻,2007年。,那么七卷本《子思子》亦由《礼记》等材料编选而成的可能性也很高。然而,如果就此认为《缁衣》的《子思子》与子思之间没有任何关系,难免过于武断。
通过对照楚简本《缁衣》,可知今本《缁衣》曾有过很大的改动,笔者认为这种改动主要是因为历经了秦朝前后的各种灾难①前引佐川论文探讨贾谊《新书·等齐》中与《缁衣》重复的文句(楚简本第九章,今本第九章),进而认为“《新书》所采用的前汉初期《缁衣》并不是郭店本,而是接近于《礼记》”。。 汉代(以后)的许多文本都失去了先秦时代的原貌,这一点通过比较上博竹简《民之父母》与《礼记·孔子间居》②关于《民之父母》与《孔子间居》以及《孔子家语·论礼》的对应关系,参照《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附录:《民之父母》《孔子间居》《论礼》文字、用句比较表。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民之父母》中说明“三无”的“倾耳而听之,不可得而闻也。明目而视之,不可得而见也。而得气塞于四海矣”几句,错入在《孔子间居》中说明“五至”的地方。该部分的错简在《民之父母》出现之前从未被指出过,可见要复原一度错乱的文本有多么困难。以及上博竹简《内礼》与《大戴礼记·曾子立孝》③关于两者的差异,参照拙稿《〈曾子〉初探——『大戴礼记』曾子立事篇PH中心にして》,鹿儿岛大学教育学部研究纪要(人文·社会科学编)58巻,2007年。即可得知。由此推知,汉人所能看到的《缁衣》,恐怕业已失去简本《缁衣》原貌,而比较接近今本《缁衣》的构造和内容。《汉书·艺文志》所载“子思二十三篇”中的《缁衣》亦然,从中抽取出来收录于《礼记》中的缁衣篇亦然。因此,汉代以后从《子思子》或《礼记》中引用的《缁衣》都类似于今本而与楚简本不同,这倒是理所当然的,毫无不可思议之处。我们可以说,这一点证明了汉人掌握的文本已经失去了先秦原貌,却不能以此为根据切断《子思子》与子思的关系。
二、《子思子》之《缁衣》《表记》《坊记》三篇
即便如上所说,《子思子》所包含的一切篇章是否皆为子思本人所作,依然是一个问题。这种冠以某思想家名字的先秦文献,与其说是所冠人名的个人著作,不如将其当作是其学派之人著作的合集。但是就《缁衣》而言,似乎可以将其视为子思自己的作品。由郭店楚简《缁衣》的出土,几乎可以确定该篇成立于孟子之前。因为孟子属于子思再传弟子的世代,如果《缁衣》是孟子之前的子思学派的作品,那么就该是子思或者他弟子所作,但我们目前不具备判别二者的条件。因而,一方面保留有弟子所作的可能性,但另一方面似乎也可以将其暂定为子思所作以进行思想史的描述。要论述子思本人与弟子之著作的差异需要更高的分析能力,这只能等待新资料的出现才有可能实现。
同样,《礼记》中与《缁衣》文章形式相同的《坊记》《表记》两篇,就目前而言似乎也可视为子思之作品。此两篇虽然还没有比较完整的出土文本,但是郭店楚简中可以看到与《坊记》《表记》两篇共通的语句。最明显的两例有:《表记》第二段第五章④关于《表记》的分章,本书根据各个“子言之”分八段,以从“子言之”开始的各段为第一章,又以每个“子曰”来分章。但是第三段第三章与第四章之间的《小雅》引文属于第四章。有“仁者人也。道者义也。厚于仁者,薄于义,亲而不尊。厚于义者,薄于仁,尊而不亲”[5]1718一句,与郭店楚简《语丛一》(残八、残二二⑤本书依据李松儒《郭店简编联二题》(《简帛》第六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在此附加残二二。、简七七、八二、七九)的“仁,人也。义,道也⑥《合集》(《楚地出土战国简册合集》)注七一补充,并且引用陈伟说,以表记篇“道者,义也”为“义者,道也”之误。。 厚于仁,薄于义,亲而不尊。厚于义,薄于仁,尊而不亲。”几乎一致。另外,《坊记》第二章①关于《坊记》的分章,以“子言之”起始的部分为第一章,以下依据每个“子云”分章。的“礼者,因人之情而为之节文,以为民坊者也。”[5]1635一句也与《语丛一》(简三一、九七)的“礼,因人之情而为之节文者也。”几乎一致。除此之外,郭店楚简《忠信之道》(简五、六)中有“口惠而实弗从,君子弗言尔。心疏·而貌·亲,君子弗申(陈)②本书依据《合集》注一五引用的裘锡圭说补充“而貌”两字;依据《合集》注一六李天虹说解释“申”字。尔”,第一句与《表记》第七段第十五章的“口惠而实不至”[5]1744相似,第三句“心疏而貌亲”虽有缺损,但与《表记》第七段第十六章的“情疏而貌亲”[5]1745也几乎相同。如上所示,《坊记》《表记》两篇所记文章中,至少有一部分内容确实在孟子时代存在过③顺带一提,《缁衣》(今本第四章/楚简本第八章)中的“上好是物,下必有甚焉者矣”(楚简本把“是”作“此”,今本缺乏“焉”字)亦见于郭店楚简《尊德义》(简三六、三七)“上好是物也,下必有甚焉者”,《孟子·滕文公上》将相似的文句当作孔子之言引用,作“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正如今本《缁衣》曾历经后代改动,今本《礼记》中的《坊记》《表记》两篇理应也未能保留先秦时代的原貌④《坊记》第十七章中的“《论语》曰”等应该是后世的附加或改变。。尽管如此,在不具备条件知晓先秦文本旧貌的现状之下,将今本视作对子思著述的传述并加以分析的做法尚或可行⑤前引武内义雄书(1936 年)第十章之二中指出《表记》《坊记》《缁衣》中可以看见《易》的引文,并结合考虑《易》的经典化时期,从而将这些文献的时代定为战国末秦初;然而,《易》的引文未必可以证明这三篇是后出,参照浅野裕一《郭店楚简〈缁衣〉の思想史的意义》(《集刊东洋学》第八六号,2001年)。此外,见于今本《缁衣》里的《易》的引文并未出现在楚简本中。。
三、《子思子》之《中庸》
如上将《缁衣》《表记》《坊记》三篇视为子思所作的话,曾经被武内义雄认定为早于三篇的“中庸本文”,按理就变成子思以前的著作,推论也就出现矛盾。只不过,笔者认为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推论困境,是因为武内将三篇定为“子思子语录”这一点本身就是错误的。我们发现,《缁衣》《表记》《坊记》三篇均按照相同的形式记述:今本《礼记·缁衣》只有第一章开头为“子言之曰”,其他章节则为“子曰”;《坊记》也只有第一章开头为“子言之”,其他章节则为“子云”;《表记》共分为八段,各段只有第一章开头为“子言之”,其他章节则为“子曰”。武内接受皮锡瑞与简朝亮等学者的观点,认为“子言之(曰)”和“子曰/云”均为引用子思之言,因而才认定此三篇为“子思子语录”。此外,武内所谓的“中庸本文”也是仅第一章开头为“仲尼曰”,其他章节则多为“子曰”,这种形式与《缁衣》等篇也类似。对于这一点,武内认为“中庸本文”首章以“仲尼”开始,那么文章全体皆可视为孔子之言,并认为“中庸本文”其实是“子思搜集圣祖之言”的作品⑥参照前引武内义雄书(1943年)第三章《子思子の分析》。。然而,考虑到其他书籍中基本没有用“子曰”来指代孔子以外之言的例子,再由“中庸本文”推及《缁衣》等篇,就应该将“子言之(曰)”和“子曰/云”都解释为对孔子之言的引用①前引浅野论文(2001年)批判武内氏的说法,并提出此处见解。(是否真的源自孔子当然又是另一回事)。另外,楚简本《缁衣》仅首章使用“夫子曰”,其他章节则使用“子曰”,这个“夫子”当然也应当是孔子。由此可知,《缁衣》等三篇应当不是“子思子语录”,而是与“中庸本文”一样,是子思所著或编纂的文献②武内氏引用简朝亮说,认为《缁衣》(今本第十四章)中引用的是死于孔子之后的叶公的《顾命》;但是,楚简本中对应的部分(第十一章)其实将“叶公”写作“祭公”,与该章的“子曰”原本并不矛盾。。
至此,所剩的考察对象只有武内所谓“中庸说”的部分。不过,笔者认为探讨此问题之前最好先改一下名称。因为我们已经知道,正如《五行》的内容分为“经”和“说”一样,“中庸说”这样的名称恐怕是不怎么恰当的。
武内之所以称之为“中庸说”,是因为他把《中庸》的这一部分连结到《汉书·艺文志》所记载的“中庸说二篇”[1]1709。然而这一部分与《五行》的“说”不同,并非以“中庸本文”为“经”而为之作解释的文献,而是无论内容或形式,都是独立于“中庸本文”而存在的作品。《艺文志》所载“中庸说”是何种文献我们无从得知,但是将《中庸》的这一部分当作“中庸本文”的解说而称之为“中庸说”的做法却不可谓为恰当。或许正因为如此,梁涛等学者才依据其内容将其重新命名为《诚明》③参见梁涛《郭店竹简与思孟学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五章第二节《郭店竹简与〈中庸〉》。。笔者的想法是,这一部分历来作为《中庸》篇的内容而为读者熟悉,因而不便用与“中庸”完全不同的名称来称呼它。因此,笔者将武内所谓“中庸说”的部分改称为“中庸新本”④金谷治《秦汉思想史研究》(日本学术振兴会,1960年)早已使用“中庸新本”的称呼。参照该书第四章第一节《礼学の推移と〈中庸新本〉》。,将武内所谓“中庸本文”的部分对应称为“中庸古本”。至于如何界定“中庸新本”与“中庸古本”的问题,虽然存在许多种学说⑤参照前引梁涛书第五章第二节。另外,梁在第二十章“凡事豫则立”以下分段。,但暂时影响不到本书所讨论的范围,所以笔者姑且参考武内义雄的区分。唯有第十六章,因其开头为“子曰”,笔者不主张将其接续到第二十四章,而应该保留在“中庸古本”之中。
对于《中庸》当然也有不一分为二的观点⑥传统立场上并不将《中庸》二分。武内氏之后具有代表性的研究,赤塚忠《大学·中庸》(明治书院,1967年),板野长八《〈中庸篇〉の成り立ち》(《儒教成立史の研究》,岩波书店,1995 年)收录,原收录于《广岛大学文学部纪要》二二卷二号,1963 年。两者采取这种立场。近年浅野论文(2003 年)也驳斥武内氏的说法,主张“应该将《中庸》《表记》《坊记》《缁衣》四篇视为从春秋末年到战国前期同一学派的一连串著作。”。但是《中庸》首章为后世附加这一点大体是可以确定的。正如今本《缁衣》直到第二章才出现“缁衣”一词一样,《中庸》也是到第二章才出现了“中庸”二字。我们考虑到“中庸古本”《缁衣》《坊记》《表记》四篇的首章均具有不同于其他章节的开头语,而今本《缁衣》首章的内容又未见于楚简本《缁衣》,可见今本《中庸》的首章内容不属于“中庸”原文本的可能性极高。再者,“中庸古本”大多如《缁衣》等篇一样,采取引用孔子话语的形式叙述,而“中庸新本”除了二十八章有两个“子曰”以外全部以论述形式展开⑦第三十三章也有“子曰”,但是被认为是《诗》《书》般的引文。,且“中庸古本”以“中庸”为主题,“中庸新本”以“诚”为主题,二者主题也不同。综合以上考虑,我们认为将今本《中庸》看作由两种材料编成的观点较为妥当①金谷治《中庸篇の成立》(《日本中国学会创立五十年纪念论文集》,1998年)对向来的中庸二分说加以修正,提出《中庸》应该是局部采用了三种以上的资料编篡而成。今本《中庸》由三部分构成:以“中庸”为主题的前半部分(除第一章)、以“诚”为主题的后半部分,以及夹在两者之间以“孝”为主题的部分(第十七、十八、十九章)。据此考虑,虽然中间的部分独立于前后部分的可能性很高,但是目前尚未有资料能够确证,因此本书姑且依从二分说。附带一提,以“孝”为主题的部分可能源自不同资料的说法,内山俊彦《中国古代思想史におけtf自然认识》(创文社,1987年)第148页中也曾有指出。。
值得注意的是,怀疑“中庸新本”为后来所出的主要根据,向来都集中在第二十八章中。例如,武内义雄将“中庸新本”(“中庸说”)判断为秦代之作品的理由有如下三点②参见前引武内书(1943年)第三章《子思子の分析》。:第一,第二十八章的“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5]1700与琅邪台石刻的“器械一量,同书文字”[6]245或《史记》始皇本纪(二十六年)的“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6]239内容一致;第二,第二十八章的“愚而好自用,贱而好自专,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灾及其身者也”[5]1700似与《史记》始皇本纪(三十四年)李斯上奏的“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非当世,惑乱黔首……臣请,以古非今者族……”[6]255内容相通;第三,第三十一章的“舟车所至……日月所照,霜露所队,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5]1705与琅邪台石刻的“日月所照,舟舆所载,皆终其命,莫不得意”[6]245相似。
如上,三点中有两点是与第二十八章相关的。考虑到这点,梁涛等学者才将包含“子曰”的第二十八章视为错简,并将其从“中庸新本”(梁先生所谓《诚明》)中排除出去③参照前引梁涛书第五章第二节。。但是,无论是否将其视为错简排除,历来根据今本一、二章的情况断定其他所有章节为后出的年代推论法,却具有误导分析思路的潜在危险。就目前资料而言,“中庸古本”与“中庸新本”结合从而产生今本的具体时期是无法判定的,但可以推测最可能产生这种内容混淆的应该是在秦汉之际。如上所述,历经秦火的文献已经失去了先秦时期的原貌。今本中“中庸新本”夹杂着“中庸古本”的内容,这表明两个文本都曾经历过大规模的错乱。再考虑到楚简本《缁衣》与今本《缁衣》的差异,就能想象今本《中庸》的“中庸新本”部分肯定也经历过不少附加或改动。虽然今本的一部分包含使人质疑其为后出的要素,但不能仅凭这一点就将“中庸新本”的成立一并往后推。至少就思想内容来看,“中庸新本”完全可以在郭店楚简的思想范围内立论,可见“中庸新本”的成立或可追溯至孟子的年代。因此,我们不必拘于部分文句,从而急于将整部“中庸新本”推至秦代以后。不如先来探讨“中庸新本”本身的思想内容。
四、“诚”:使“性”显现的条件
众所周知,“中庸新本”的论述是从以下三句开始的: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第一章)[5]1661
前两句的内容实质上与郭店楚简《性自命出》中的如下文句相同:
性自命出,命自天降。道始于情,情生于性。(简二、三)
“中庸新本”中虽没有“情”,但第一章有“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5]1661一句,其中所谓已“发”的状态实际相当于《性自命出》的“情”。反之,“性”未发的状态则应该相当于《性自命出》的“喜怒哀悲之气”。因此,虽然“中庸新本”中没有出现“气”字,但实际上也可以说“中庸新本”立足于笔者所谓“性即气”的思维[7]8-10。如下所述,“中庸新本”中论述“性”之发出(或显现)的内容,如果全部置换为喜怒哀乐等“气”的呈现,其论述本身几乎是一致的。可见,“中庸新本”的“性”论实际上基于《性自命出》的“性即气”的思维。
由于未发的“性”尚未有具体的表现,倘如要预设能够教导的“道”的对象的话,其教导应该以作为“性”的表现的“情”为对象具体进行。“中庸新本”所谓“率性之谓道”不过是省略了“性”与“道”之间的“情”罢了。当然,无法将现实生活中人所表露的一切“情”视为“性”的直接显现,因而附加了“皆中节”这个条件。无论如何,实践顺从“性”的“道”的行为,也就是使人为人的“教”,亦即第三句的“修道之谓教”。
《性自命出》中没有出现与“修道之谓教”完全对应的语句,但是郭店楚简《尊德义》中有与此类似的句子:
教非改道也,教之也。(简四)
由于“天”赋人“性”而人才能为人,对人的“教”应该是教导这个基于“性”的人之“道”;反之,对“性”及基于“性”的“道”施以更改、矫正的行为,则无法成为此处所说的“教”。
关于此处所说的“道”,“中庸新本”(第三十章)中另有“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5]1704此句预设万物各有与之相应的道,具体而论,应该像是郭店楚简中出现的“水之道”“马之道”①原文作“马也之道”,本书依据《合集》(《楚地出土战国简册合集》)注二五,以“也”为衍字。“地之道”(《尊德义》简七)等“群物之道”(《性自命出》简一四)那样。只不过“中庸新本”开头的“道”与第三句的“教”相关联,可见此处具体所指为人之“道”。既然此一“道”为人“道”,人自然便不可离开其“道”。故而“中庸新本”(第一章)中又说“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5]1661
讨论到这里,下一个问题便是如何修习此道。就上述“中庸新本”的想法来看,若有人在现实中照着“天”赋之“性”行动,也就不需要“教”了。因为这样的人身上已经体现了顺从“天”赋之“性”的道的原状。因此,此处设想的“教”的对象应该是那些现实生活中未必合乎此“道”的人,按照“中庸新本”的说法,即从“天”秉受人“性”却“发而未必中节”的人。从“未必中”的状态回归到“发而皆中节”①这个“节”并非被设定在与“性”不同的地方,而是根据天赋之“性”按照原样如实发挥的情的状态来设定。因此,保持天赋之“性”原样的人一定会“中节”,否则不一定“中节”。,并由此达到“天”赋之“性”原状的尝试,才是所谓“修道”。所谓“中节”当然也包括行为上的恰当,但是此处涉及喜怒哀乐等表露的问题,因而“中节”不仅指外表行为的恰当,也要求此种行为背后所存在的“情”的恰当。比如,假设在面对朋友之死时,有所谓恰当的行为。但是实行这种恰当的行为时心里却无丝毫哀戚,那么即便外表上的行为恰当,也称不上“性”发而中节的行为。如此一来,“中庸新本”中设想的修“道”方法,不可能只是简单地照着某些作为人该履行的行为范例,适当地将之付诸实践。而是要求这样的行为中能够具有与之相对应的“情”。
此“情”的部分,除非呈现为身体上的举动,否则他人无法直接听到、看到。因此,内在的“情”在外表上有可能体现为与之不同的行为。然而,如上所述,在要求外表上的行为与内在的“情”一致的情境下,人不能因为他人无法直接听到、看到就忽略“情”的部分。因此,第一章中说“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5]1661也即所谓的“君子慎其独也”(第一章)。
郑玄注释“慎其独”,说“慎其间居之所为”[5]1661,也就是把这句话理解为在他人耳目未及的情境也不能轻忽举动。笔者认为,以这样的意思来解读《中庸》的这一部分是没有什么错误的,但是将“独”局限于“独处”之意似乎过于刻意。《五行》在解释“慎其独”的时候会区分“流于形式的行为”与“内在之情表露出来的行为”[8]113-114,比如《五行》第七章的“说”中有“夫丧,正绖修领而哀杀矣,言至内者之不在外也。是之谓独。独也者、舍体也。”也就是说,《五行》“说”的作者把“独”与内在的“情”联系起来,并将其解释为“专注其意于内(情)”。《中庸》“慎其独”的“独”也该往这方向理解,关注他人无法直接听到、看到的内心之“情”才是所谓的“慎其独”。
笔者想要指出的是,若按此解释“慎其独”,“独”势必包含“独处”的意思。如果将“独”单解释为“独处”,“慎其独”指的就是不管他人存在与否,都能实行同样的行为。这里要求的不过是外表行为上的一贯性,对于行为背后“情”的部分则不问。但如果按照上述《五行》的方式解释,就要求在任何场合,行为者都能使符合该场合的“情”恰如其分地显现于内。人生来秉受作为人的“性”,使作为“性”之表露的“情”总以恰当的形式呈现,这种行为就是“慎其独”。这种情况下,行为者当然被要求以合乎“情”的形式来行动。而这层意义下的“慎其独”自然也包含了“独处”的“独”,即无论他人存在与否,都要保持行为的一贯性。
那么,如何实践“慎其独”呢?因为这个问题涉及内在之“情”,所以仅为达成外表行为的恰当而做再多的努力也是不够的,还必须设法改变内在状态本身。换言之,行为者必须使其内在处于理想的状态,使“性”以其原本的形状通过“情”的方式展现出来。“中庸新本”将这个理想的状态称为“诚”。如下: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第二十章)[5]1689
“天”赋之“性”以符合各自场合的“情”为形式而恰如其分地表露出来,这也是人本来该有的状态。然而,从一出生便能如此的人极少。普通人出生时没有这样的状态。但是所有人又天生秉受同样的“性”。只不过一般人的内在并未处于“诚”的状态,因此“性”无法呈现出本来该有的样子,于是必须朝向“诚”的状态努力,使其“性”呈现出本来该有的样子。相较之下,已经实现“诚”状态的“圣人”,不需要任何努力,其“性”便以相应的“情”为形式,适宜、自然地表现出来。因为作为人“性”如实表现出来的“情”同样也显示着为人之“道”,这样的人便自然地合乎人“道”。
相比之下,尚未实现“诚”的状态的人,应该通过某种努力设法实现“诚”的状态。“中庸新本”将这种努力称作“择善而固执之”。“中庸新本”未定义“善”。但是,由上述论证明确可知“中庸新本”所设想的“善”为何。在各个场合中,“性”以其原状直接表现出的“情”的行为,就是人该做的、一定会做的行为,于是这行为就是合乎那些场合的“善”的行为。一般人或许尚未察觉到“善”的行为是基于“性”的表现而出,但是可以将这样的行为视作“善”而向人学习、并适用于自身的行动。对于“善”的行为,“中庸新本”中说“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第二十章)[5]1690,也就是说要求人们“明乎善”(明白善)且“笃行之”(笃行善)。当然,就算实践了这些努力,如果其善只在表面上,而内在“情”的部分没有发生变化,那么这份努力就无法促成“诚”的状态的实现。即便如此,由于任何人都秉受相同的“性”,只要他在各个场合都以“性”原本应该表现出的方式,如第二十章“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5]1690一样反复实践那行为,就会唤醒内在的“性”,合乎其“性”的“情”也会表露出来。至此终能获得“诚”的状态。
从出生便能保持“性”本来面貌,亦即实现了“诚”的状态的人,他的举动自然通通合乎人“道”之“善”,因此这个人不需要任何努力就知晓“善”是什么。相比之下,并非天生如此的人首先得明白“善”,通过反复践行合乎人“道”之“善”的行为,亦即“修道”(“教”)来实现“诚”的状态。所谓“诚”的状态指的是,所有人生来就被赋予的“性”能够如实表现出来的状态。所以无论过程如何,一旦实现了“诚”的状态,任何人都会获得相同的结果。故第二十一章说:“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诚则明矣。明则诚矣。”[5]1691其中最后两句中“诚则明”是无条件成立的,但是“明则诚”则需要以人的努力为前提,这是无需多言的。上述的这种遵守(人道之)“善”而达到天道之“诚”的思路,令人想起从“人道”之“善”到“天道”之“德”的《五行》的思路。笔者认为两者背后的思考模式应该是相同的。
然而,天赋之“性”被如实表现的状态为何被称为“诚”,而不是其他术语呢?“中庸新本”中没有明确说明。但或可参考《礼记·大学》中的语句。《大学》中论述“诚意”说:“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故君子必慎其独也。”[5]1859即主张通过“慎其独”实现“诚”的状态,也就是说,在“性”得以如实表现的状态下实行善的行为的人,其行动是自然而然发起的,而不是通过欺骗自己才形成的。正如对美的事物感受到美故而自会喜好它一般。因此,实现这个状态的人并不会欺骗自己。“中庸新本”中恐怕也是因为“不会欺骗自己”这一层内涵,才将这种状态称为“诚”的吧。
不管因为什么被称为“诚”,一旦被如此称呼了,“诚”这个字所具有的一般性意味便与此处“诚”的状态联系起来。因此“中庸新本”之中,两种“诚”——天赋之“性”原原本本表现出来的状态之“诚”,以及后文将要讨论到的、作为被信赖的基本条件的“诚”——几乎难以划分辨别。下面我们就来讨论“诚”的这一方面。
五、“诚”:实现化育的条件
首先,举《荀子·不苟》的文章作为参考之用:
善之为道者,不诚则不独①本文将这里的“不诚”“不独”视为接着上文“至其诚”“慎其独”,因而解释为“不至其诚”“不慎其独”之意。,不独则不形,不形则虽作于心,见于色,出于言,民犹若未从也,虽从必疑。[9]47-48
虽然我们尚未清楚此处“形”一词意指何种显现,但“诚”说的应该是令人顺从、备受他人信赖的绝对条件。心中思考值得人信赖的事、扮出令人信赖的外表、用令人信赖的语气说话,但如果仅仅如此,仍不足以使人真正信赖。根据此段文章,只有拥有“诚”才能为他人所信赖。这种思考方式令我们想起被认为是《子思子·累德》遗文中的语句:“语曰,同言而信,则信在言前。同令而行,则诚在令外。”(《后汉书·王良传》②范晔:《后汉书》,李贤等注,北京:中华书局,1965 年,第934 页。李贤注:“此皆子思子累德篇之言,故称语曰”。顺带一提,和此句几乎相同的文章,在徐干《中论·贵验》中被当成子思之语引用,《意林》卷一也当作《子思子》之语收录。另外,虽然不清楚《淮南子》与《子思子》的关系,但《淮南子·缪称》也有几乎相同的文句。)假设两个人说了相同的话,一个被信赖,另一个却不被信赖,那么就无法从表面的话语中寻求被信赖的原因,而应该从说话者内在的“信”或“诚”之中寻求。
《不苟》中“信”“诚”之想法的特色,可以通过比较《荀子》其他部分的“信”“诚”来得出。我们先排除如下三个部分:(1)《不苟》中包含先前引文的文段;(2)与荀子本人直接关系受到怀疑的《大略》篇以下,以及(3)易为后人附加的赋的部分。《荀子》中其他部分的“信”与“诚”基本上意味着“不欺骗他人”③《荀子》在这部分几乎没有在“诚”与“信”之间进行区分。除了当作副词、形容词来使用之外,这部分的“诚”字几乎不会被单独使用,而是作“端愨诚信”(《修身》)、“诚信”(《不苟》《致士》)、“端诚”(《非相》《君道》《正论》)、“诚能”(《儒效》《王霸》《君道》)、“端诚信全”(《王霸》《彊国》)等复合词出现。其中,“诚能”似乎是并列“诚”与“能”,但其他都应该视为连词,并且《不苟》中有“端悫生通,诈伪生塞,诚信生神,夸诞生惑”,通过分析可知“端愨”与“诚信”两词是彼此不同的概念;但是从“端诚”一词可知,“端”“愨”“诚”“信”之间没有明确的区分。从《不苟》这部分亦可知,由于“端愨”“诚信”的反义词是“诈伪”“夸诞”,“端”“愨”“诚”“信”共有的意思就是“不伪造”“不欺骗”。。譬如君主,只要是以刑赏为代表的政令约定,就一定予以施行,不欺骗民众①举例来说,《荀子·王霸》中称其为“信立而霸”的霸主,其具体行为即“政令已陈,虽睹利败,不欺其民。约结已定,虽睹利败,不欺其与”。。此种情况下只要约定内容客观地被遵守,就会被认为是“信”或“诚”,而不会特别追究君主内心的状态。因为荀子这位思想家无论是对人类界还是自然界,基本上只会在能够客观观察到的范围内构造自己的思想,而不会言及其背后看不到的地方[10]。
相对地,只有《不苟》这一段没有基于第三者能够客观判断的、外在的行为,而是基于其背后的、内在的部分来判断“诚”(信赖)之与否②这种特质足以令人怀疑《不苟》的“诚”说与荀子本人的关系。。在为什么能够相信这个人时,并不是回答:“因为他平时的行为是如何如何”,而是简单回答:“因为他拥有诚”。从语义来看“此人值得信赖”与“此人诚/拥有诚”当然指相同的事态,此两种回答之间不过是同义反复罢了。然而,后者的表达方式却给人以某种印象,让人觉得内在之“诚”似乎是某种实体的东西,并认为这个“诚”才是被他人信赖的根本原因。在这种思路下,只要是涉及某种信赖关系,甚至不局限于人与人之间,“诚”就会作为支撑这种信赖的根本而被讨论。例如《不苟》中针对“天”“地”“四时”说:
天不言而人推高焉,地不言而人推厚焉,四时不言而百姓期焉。夫此有常,以至其诚者也。[9]46
除了那位杞人,人确信不会发生“天地崩坠”,故信赖天地而聚居其间;确信四时循环的规律不会改变,故信赖其规律而日常生活。人如此信赖天地四时,原因为它们不变(“常”)。但《不苟》的这一段却在客观恒常的背后进一步设定了天地四时之“诚”。
要是这种信赖关系不限于天地与人之间,而模拟性地扩大到天地与万物之间,就会变成“天地为大矣,不诚则不能化万物”(《荀子·不苟》)。万物聚居于天地之间,随四时循环而成长变化。因而可以在天地与万物之间模拟性地设想出如天地与人之间那般的信赖关系。故此处才会以这种形式论及“诚”。至此,“诚”似乎被视为化育万物的条件。
当然,《不苟》所关心的并不在于客观追求天地化育的条件,而是以天地化育为类比,要求君主应该有“诚”。因此《不苟》中接着说道:
圣人为知矣,不诚则不能化万民。父子为亲矣,不诚则疏。君上为尊矣,不诚则卑。夫诚者君子之所守也,而政事之本也。[9]48归根结底,《不苟》的根本问题意识在于讨论如何获得人民的信赖。
其实,和《荀子·不苟》类似的想法也见于《吕氏春秋·贵信》。只是该文段将“诚”替换为“信”,如下:
天行不信,不能成岁。地行不信,草木不大……天地之大,四时之化,而犹不能以不信成物,又况乎人事。[11]
作支撑信赖之根本的“诚”与“信”被联系到万物育成,这样的思考方式在时代相对明确的传世文献中没有早于此两书的例子。不过,郭店楚简《忠信之道》中有“信之为道也,群物皆成,而百善皆立”(简七)一句。这里所说的“信”虽然并未记作天地之“信”,但根据《忠信之道》中“至信如时,必至而不结”(简二),“大信不期……不期而可遇①《合集》尚未隶定“遇”字,本书参考同书注一二引用的李零说,将其解读为“遇”。者,天也”(简四、五)等句,“信”被与天及四时联系起来讨论,可见此处的“信”在某种程度上亦给人以天地之“信”的印象。当然,正如《忠信之道》主张“忠积则可亲也,信积则可信也。忠信积而民弗亲信者,未之有也。”(简一、二)那样,其主要关心的亦在于获得民众的信赖,由此发端,以至赋予“信”以化育万物之条件的性格。郭店楚简中既如此,可见这样的思想在孟子当时已经存在。另外,此种思想也见于“中庸新本”,其二十六章中说:“天地之道,可一言而尽也。其为物不貳,则其生物不测。”此句虽然没有“诚”字,但从上下文来看,可知“一言”所表现出来的“天地之道”就是“诚”②朱子也注释为“天地之道,可一言而尽,不过曰诚而已”。,换个词也即后面的“不貳”。其用词虽与《不苟》有异,但天地因“诚”故而化育万物的想法是不变的。
不过,对于化育万物之条件的天地之“诚”,“中庸新本”之中将作为其表现的“常”进一步扩大。比如二十六章有:
故至诚无息,不息则久,久则征,征则悠远,悠远则博厚,博厚则高明。博厚所以载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5]1694-1695至此,所谓的信赖关系已不能用常理来解释。然而,究其缘由,好比说“一撮土之多”[5]1696的“地”也会在绵绵不息的作用下变得广邈,万物因此信赖并聚居此地(参考二十六章)。因此,这里所说的“无息”指的应该也是支撑信赖之“诚”的表现之一。
天地不“诚”则无法化育万物,亦如前引《不苟》,圣人不“诚”则无法化育万民,父子也好,君臣也好,若没有“诚”的话,其关系势必瓦解。以此类推,“诚”的效用遍及万事万物。第二十五章称“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5]1694也就是说“诚”为贯彻万事万物的一切,无诚则万事万物无法成立。总之,“诚”可以说是使万事万物得以成立的根本条件。
六、两个“诚”的重叠
“中庸新本”的独特之处在于两个“诚”的重叠。一是作为支撑信赖的根源,从而成为万物生成之条件的“诚”,二是前面讨论到的实现天赋之“性”原状的“诚”。比如第二十二章的“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5]1691,和第二十五章的“诚者自成也”[5]1694。若脱离上下文单看这两段的话,则可以将此处的“诚”理解为实现“性”之原状的“诚”。然而第二十五章引用文的后面紧接着就是“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5]1694此处“所以成物”的“诚”之中,就重叠出现了化育万物之条件的天地之“诚”的含义。另外,二十二章的“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之后也有:
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5]1691从发挥自己的“性”联系到使他人之性、乃至万物之“性”得以发挥——这样的逻辑虽然无法理解,但毫无疑问的是,化育万物之条件的天地之“诚”也重叠出现在这段引用中。可见在“中庸新本”之中,发挥自己的“性”的“诚”与化育万物之条件的“诚”的涵义彼此重叠。
那么,为何会有这样的重叠呢?首先可以确定的是,对“中庸新本”的作者来说,这两个“诚”作为自己内在的状态是彼此相同的。然而,我们无法弄清这个状态究竟是什么样,因为毕竟涉及人的内在状态的问题。打个比方,对于可化育万物的“诚”,或较为浅显层次上的、受人信赖的原因之“诚”,若要指出其外表上的表现,就可举“不欺骗”“行为有常”等例子;但这样的例子无论举多少,也无法显示其内在状态本身。若要显示其内在状态,则必须使用正好指示这个状态的语词来讨论。但其结果不过是“诚”的同义反复,实则难以讨论到“诚”的内在状态。因此,虽然我们无法得悉“中庸新本”的作者具体如何描绘“诚”的状态,但重要的是,我们知道“中庸新本”中这两种“诚”的内涵是互相重叠的。借由此种阐述方式,可以使化育万民这个外在为政的问题,回归到是否要发挥自己的“性”这个内在的,某种意义上属于个人修养的问题中。此种情况下,自我修养(内)与为政(外)的完成,同样是通过实现“诚”这个内在状态而达成的。恐怕正是基于这点,第二十五章中才说“诚”是“合外内之道也”[5]1694。此外,如果实现“诚”的状态,而发挥自己的“性”与化育万民相重合,那么“性”就不仅是使人为人,也将能够化育万民、甚至于辅助万物化育的“德”包含在其中。实现“诚”以后,不但“成己”而且“成物”,这也是二十五章中所称的“性之德”[5]1694。由于“性”具有的作用被如此扩大,于是未发之“性”的“中”,以及其“性”呈现出本来面貌的“和”,也不单纯是关于个人修养的词汇,而是如第一章中的“天下之大本”“天下之达道”那样,被冠以“天下”之语加以讨论。第一章中更进一步说:“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5]1662由于此两种“诚”的重叠,“性”所具备的功效也一样被扩大思考了。
七、“中庸新本”与孟子
以上大致上将“中庸新本”思想的概略论述完了。另外“中庸新本”第二十四章中还提到了意指某种预知能力的“至诚”,但这是较为独立的一个主张,与其他部分的关系相对薄弱。笔者也不知实现什么样的内在状态才能获得那种预知能力,但在“中庸新本”的作者的心里,获得这种预知能力的内在状态恐怕也被理解为像“诚”那样的东西吧。若所关注的不是呈现在外的作用,而是其背后的内在状态,那么那些由于内在同一质的析出过程不同,而外在表现的方式不同的事物,会实为同质内在状态的不同表现形式而已。
如果“中庸新本”的内容诚如上述,那么我们不必将“中庸新本”放在距离《性自命出》《五行》或《忠信之道》等郭店楚简诸篇所示思想圈太远的位置。“中庸新本”开头部分显示了与《性自命出》的密切关系,其“性”说又符合“性即气”思考模式;遵守(人道之)“善”以达成天道之“诚”的修养过程也类似于《五行》中从“人道”之“善”到“天道”之“德”的过程;视“诚”为化育万物之条件的类似想法也可见于《忠信之道》。而“中庸新本”的显著原创性在于:(1)明确说明了“诚”是使“性”得以发挥的条件和使万物化育成为可能的条件;(2)使“诚”的两种涵义互相重叠。而“中庸新本”的思考根源本身基本上都可纳入郭店楚简诸篇的论述范畴。这虽然不能直接证明“中庸新本”的成书年代与郭店楚简诸篇同时,但仍然充分暗示了这种可能性。要是这样,我们就需要重新讨论“中庸新本”与孟子的关系。
究竟而论,《中庸》是一篇不可思议的著作。“中庸新本”中对人的内在表示了那样强烈的关注,但是(包括“中庸古本”中)却完全见不到“心”字。“诚”在“中庸新本”中被说明为发挥“性”之原状的内在状态,若用《性自命出》的话来说,就相当于“心”具有“定志”的状态。处在此状态时,“喜怒哀乐”则会“发而皆中节”。既然说了“发而皆中节”那么必定也设想了“发而不中节”的情况,因而也一定会论及左右这两种不同情况的器官才对。然而“中庸新本”对此器官默然不语。就笔者所见,“中庸新本”是在对《性自命出》的“性即气”思考或者其中设想的(独特的)“心”①关于《性自命出》的“心”,请参阅拙稿《〈孟子〉和郭店楚简〈性自命出〉的性论》,《科学·经济·社会》2020年第4期,第10-12页。完全不加论述而自明的前提下,将意识专注于“诚”的状态的发挥效果而立论成篇的。从其论述来看,笔者不认为“中庸新本”的作者拥有孟子在“不动心”以后所论及的“心”思想。即便这位作者是孟子以后的人物,他在编写本篇时应当与孟子“不动心”以后的思想保持着一段距离。另一方面,《中庸》被认为属于《子思子》,因而其作者(若非子思本人)理应是在某种程度上继承且发展了子思思想的人物。要是如此,以下《中庸》与《孟子》中重合出现的文章的先后关系也自然明了。《中庸》第二十章说:
在下位不获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获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获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顺乎亲,不信乎朋友矣。顺乎亲有道,反诸身不诚,不顺乎亲矣。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乎身矣。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5]1689
《孟子·离娄上》则说:
孟子曰,居下位而不获于上,民不可得而治也。获于上有道,不信于友,弗获于上矣。信于友有道,事亲弗悦,弗信于友矣。悦亲有道,反身不诚,不悦于亲矣。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其身矣。是故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12]508-509《孟子》中说到的“诚”,只有两条具有思想意义的用例,本段引文是其中一条。《中庸》的“诚”首先是“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乎身矣”,明确说明“善”是达成“诚”的手段,最后以“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为总结,阐明“善”与“诚之者”——即“人道”——有关;相较之下,《孟子》只说到“善”,没有明确提及“善”是与“人道”相关还是与“天道”相关。笔者以为单从这一点,也能看出《中庸》的内容形式应该比《孟子》更早。而且,即使假设“中庸新本”的作者为孟子以后的人物,考虑到其上述内容离孟子思想有一段距离,可知他直接引用《孟子》的可能性很低。《中庸》的引文与子思思想的关联也与《五行》“经”的情况相同,从它将“善”配置到“人道”这一点就可以看出。应该是“中庸新本”的作者引用了当时存在的与子思相关的文献。几乎相同的文章见于《孟子》,可见“中庸新本”的成立即便晚于孟子,上段引文本身也应当出于孟子之前的人①依笔者来看,这段孟子以前的话被冠上“孟子曰”,或许是因为孟子在讲话时引述了这段内容,而弟子把这番话当作孟子之言记录下来。《孟子》中一般先明确指出说话者,再引用此人之言,但是并不一定所有引文皆是如此。我们不清楚记录者是否知道末尾两句以外来自《中庸》,但即便知道,也可能因为末尾两句为孟子原创,而误将整段文章冠上“孟子曰”来记录。。
如此一来,如果上段《中庸》的引文先于孟子,并与子思有关,那么就应该是子思或其弟子之言。然而,正如笔者强调过的那样,目前的资料状况不足以让我们区分讨论子思及其弟子。因此,本文暂将二者视同为子思之论。据此,“中庸新本”中至少有一部分,亦即“诚”思想的一部分应当源自子思。先前已有说明,今本《中庸》的“中庸新本”部分包含有疑为后出的内容,因而难以将其整篇直接归为子思之作。但必须得承认“中庸新本”中也包含了源自子思思想的内容。虽然不清楚这个范围有多大,但若考虑到其思想理应不会太脱离郭店楚简诸篇的思考架构,那么“中庸新本”的不少内容都很有可能源自子思。虽说如此,“中庸新本”的著述形式与“中庸古本”或《缁衣》《坊记》《表记》三篇完全不同,将“中庸新本”看成子思之作来处理的话,其论证上或许会碰到很大的困难。因此,笔者觉得应该在考察了《子思子》的其他篇章之后,再来讨论“中庸新本”与子思的关系②针对此项问题,笔者择篇再论。。不过,即便“中庸新本”或属子思后学之作,其中却也包含着源自子思的内容,并显示了子思思想的一个发展方向。单就这一点还是可以认同的。
在“诚”思想的展开上,我们观察到,孟子接受子思思想的时候是有选择的。至少说与“中庸新本”接受子思思想的方向不同。《孟子》中极少论及“诚”的事实也暗示了这一点。《尽心上》开头明确指出了这一点:
孟子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殀寿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13]877-878
显然,前几句明显与“中庸新本”第二十二章的以下部分关联: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5]1691我们并不清楚此段引文是否全部来自子思。不过,我们可以推测与子思有关的相似论述在孟子以前似乎就已经存在了,正如前引《孟子·离娄上》中出现“中庸新本”重合文的情况一样。应该不可能是“中庸新本”的作者改变《孟子》的内容,而是孟子将“至诚”→“尽性”的思路替换为“尽心”→“知性”,显示了他重视“心”之立场。然而更值得注意的是孟子的选择性接受:他舍弃了通过“诚”参与到“天地化育”之中的想法。
我们不清楚子思本人是否已抱有这样的想法。不过,以“诚”为“天道”,以想要达成“诚”为“人道”,并讨论从“人道”到“天道”的提升,这与《五行》“经”中所示的一样,是子思的思考模式。此处又将“诚”作为化育“天(地)”的条件(虽有一些逻辑上的跳跃),从而导出了人只要保持“诚”的状态就能参与“天地化育”的想法。这样的想法即使并非出于子思本人,也应该萌芽于子思思想,只不过孟子并没有继承。
笔者在前文中曾探讨过“性即气”的思考模式的几个问题①笔者在前文中论述了《性自命出》中有“性即气”的思维方式。请参阅拙稿《〈孟子〉和郭店楚简〈性自命出〉的性论》,《科学·经济·社会》2020年第4期,第8-10页。。此处再提出一点:此思考模式下,可能会出现“性”的原有内实超出了人的实际生活方式的危险。我们无妨设想与此相反的情形:站在“性即气”的思考模式之下,只要不以“性”的齐一性为前提②关于在中国古代思想中“性”的齐一性的思维方式的特色,请参阅拙稿《〈孟子〉》和郭店楚简〈性自命出〉的性论》,《科学·经济·社会》2020年第4期,第3-6页。,那么人的“性”因人而异,“性”的表现也因人而异,就可以解释人与人之间的实际生活方式为什么不同。因而,此“性”的内实超出人的实际生活方式的危险性就比较少。反之,若是以“性”的齐一性为前提,此危险性则便会大大提升。因为现实中人的生活方式未必一致,具有齐一性的“性”就必须得放在异于实际生活的地方。那么,就算现实中没有与天地并立且参与其化育的人,也仍可以说人“性”具备这样的能力。因为哪怕现实中没有一个这样的人,也可以说是因为所有人都没有到“诚”的状态。其实,《性自命出》中“性”的表现原本只限于情感与好恶、或善不善的判断之层次,它所设想的“性”一般来说并不会超过人类能力所及的范围。但是《性自命出》的“性即气”思考本身却隐含了这种,“性”的内实超出了实际的危险性。“中庸新本”的论述就显示了这种危险性。上述参与“天地化育”的主张是一例,通过“诚”获得某种预知能力的想法也是一例。而孟子则拋弃了这样的主张和想法。
这是因为孟子抛弃了“性即气”的思想还是另有原因,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如果像孟子那样,从“心”(或“耳目”等)推导出“选择的齐一性”的话,由于人无法选择不可能实现的选项,确实不会碰到前述的危险。人可以随意地期望如鸟般在天空飞行,但是既然人的生存方式不包含这一项目,人就无法选择(只靠天赋的身体)飞行于天空。人可以选择的事项只限于能够实现的、人本身的生存方式。在这个范围内,孟子通过设想“心”(或“耳目”等)最终选择的事物具有“齐一性”,从而推论出“性”也具有此“齐一性”。因此,孟子所说的“性”不会出现超出人的实际生存方式的可能。按照孟子的思路,既然“耳目之性”是自明的,就可以将探讨的对象限定于“心之性”,通过向“心”询问“心”究竟要选择什么,就能得知其“性”如何。正如《尽心上》所说的“尽其心,知其性”那样。相比之下,若是如同“中庸新本”那样,达到“至诚”的状态才能“尽其性”,那么尚未达到“至诚”的时候就完全无法预测“性”的全貌究竟为何。若设想“至诚”状态为超乎常人的程度的话,那么达到“至诚”后所表现出的存在方式也同样是超乎常人的。“中庸新本”所谈的“圣人”如第二十七章所描述的“大哉圣人之道,洋洋乎发育万物,峻极于天”[5]1698-1699。此圣人具有突破“人”的领域而冲至“天”的倾向;相较之下,孟子所谈的“圣人”则如《离娄下》中的“尧舜与人同耳”[13]1603,此种圣人始终仍在“人”的类別之内。由此亦可看出子思思想与建立“不动心”之后的孟子思想的差別。
结论
总而言之,子思或子思学派的思想之中,“仁义礼智圣”的“五行”在《孟子》中只有微末痕迹;而“诚”的思想,虽然只有两例,却清晰地显示在《孟子》文本中。由此可知,《孟子》接受“诚”思想的程度相对较高。只不过,从前文引用的其中一例也可以看出,孟子引进“诚”的思想,虽然保留了“天道”和“人道”之间的区分,但在结尾处还加上了“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这样的评论,可见孟子的关心几乎只局限于“人”的世界。第二条则见于孟子《尽心上》:“孟子曰,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13]882-883虽然不太清楚第一句所要表达的意思,但“反身而诚,乐莫大焉”一句中,至少看不出要突破“人”的领域而冲至“天”的、化育万物之“诚”的意思。这两条应该算是子思思想的残余,但是孟子在实质上其实拋弃了子思的“诚”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