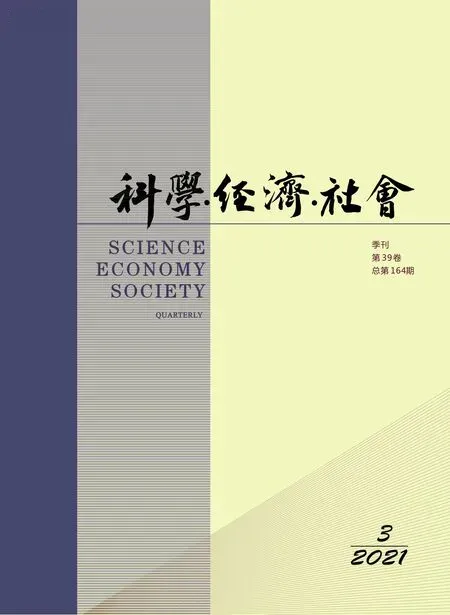破除“别无选择”的魔咒:社会技术进步的集体概念
克里斯托弗·科尔南
王誾 译
这篇短文非常复杂,充满了各种想法,以至于想要回答所有相关的问题可能需要写几篇文章。因此,在这里我只讨论三个问题,所有这些问题都与技术哲学的作用相关,或者涉及多学科的STS(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科学技术研究)的更广泛领域。关于这三个问题,我曾备受如下评论的鼓舞:
这三种方法也有不同之处:“大方案优化”回到国家的行政实践、热力学、气体定律、统计人口科学(Bevölkerungswissenschaft),特别是19世纪的情况,也回到一种特定的知识/权力统治制度,将克里斯蒂安·德斯顿、安东尼·福奇以及钟南山这类科学家提升到国家名人和权威专家的地位。从科学技术研究(STS)、建构性技术评估(TA)、共同设计(co-design)、开放科学(open science)和开放创新(open innovation)的角度来看,令人震惊的是,现代知识社会在危机时刻多么迅速地恢复到一种被视为过时的模式。虽然公民和“公民科学”(citizen science)的贡献在“拼凑满足”和“实时响应”中显现,但这并不根源于关于在21世纪社会中广泛动员分配能力之最佳方法的讨论①参见刘永谋等《新冠视角:全球瘟疫的哲学教训》(《科学·经济·社会》2021 年第3期1-4页)。。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正在从具体到一般,从内部到外部:从这些学科和领域如何才能最好地促进“分散力量的广泛动员”这一更实际的问题出发,经由一个关于我们自我反思的问题——上述学科和领域自己的一些模型,它们已经被研发了几十年,本身并不显得过时——到这些研究领域在快速变化的世界中可能扮演的新角色问题,这可能正是我们的关键任务,使技术行动作为政治行动变得更加显见易懂,同时有助于破除在政治和文化上的虚假的客观约束和别无选择(TINA,There Is No Alternative)的魔咒,尤其是通过对于技术化科学(technoscience)的批判。
1.公民STS
正如三位作者所言,这次疫情感觉更像是一场考验,人们的确可以认为,社会以及社会团体和个人“比以往更多地暴露他们的问题和性格”,包括“社会技术世界的居住方式”。
这场疫情的一个显著特征是,随着社交媒体的兴起,一种趋势愈演愈烈,即许多人越来越公开地在阴谋论的意识形态中寻求逃避现实挑战的庇护。然而,这个避难所不再是一个安静的壁橱,而是一个由无数安静的壁橱组成的数字反公共场所,这些壁橱正逐渐失控,并越来越多地单独出现在街道上(通常地标性场所),就像它早已在议会和政府中所做的那样。然而,尽管在“现实生活”中出现了这些现象,但这一趋势本质上是由无数技术(信息和通信)行为组成的,这些行为在不断增加,因为人们在家的时间越来越多,工作越来越少,在许多情况下,人们迫切希望创造意义。原先的日常生活在疫情爆发之前,很容易使公民在政治上墨守陈规,在生活中秉持消费主义。然而在日常生活中断所造成的压力下,各地的公民都不得不思考科学、技术和医学问题,以及各种与科学和医学有关的治理问题。
此外,正如我们从(大量)STS学术从业者组织的许多技术化科学活动的公共参与中所了解到的那样,在许多情况下,在围绕这些主题而展开的交流中的主要问题不是关于科学事实或技术选择的疑问,而是对科学内涵的根本误解,即科学思维以及科学与技术政治经济学。在一个一方面是“匿名者Q”①译者注:“匿名者Q”是一种极右翼阴谋论,其认为美国政府内部存在一个反对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和其支持者的深层政府。这个理论最早于2017 年10 月出自4chan 讨论版中的一个署名为Q 的匿名用户,“Q”这个名字出自美国机密许可中的最高级别“Q级许可”。参考自“维基百科”。,另一方面是对科学的老式和过时的尊重(这在很大程度上也被误解)的世界里,公民是STS 方法的专家,了解科学、创新和卫生系统,以及科学如何运作,与参与自然科学和技术发展的公民研究人员相比,我们更需要前者。技术哲学家可以在教育公众方面发挥关键作用,以使尽可能多的人实践“公民STS”,从而使社会更好地抵御阴谋论意识形态的诱惑。这可能促成“21世纪社会中广泛分布的能力”的真正动员。
2.疫情中的科学与后真相
然而,技术哲学家和其他学术STS 专家真的能够承担起在这些问题上帮助公众启蒙的角色吗?STS 领域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对抗三位作者所说的“技术统治论思维定式,这种思维定式似乎与政治领域和公共价值观的讨论脱节,并与之对立”——在其核心技术哲学受到反技术治理和反科学主义推动力的强烈影响。弗兰兹·塞弗特近期撰文写道,在STS中,科学权威的瓦解传统上与科学的民主化同时进行,因此与进一步的“民主的民主化”同时进行;并且,他也提出了该领域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延续过去几十年的这些范式的问题②Seifert,F.,“Die Grenzen Akademischen Zweifels”,science@ORF.at,14.10,2020-12-18,https://science.orf.at/stories/3201963/.。根据塞弗特的分析,“真相之战”中的演员群体已经发生了变化,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能还记得史蒂夫·富勒更早期提出的观点。塞弗特认为,对科学的怀疑(至少是作为一个系统)以前被视为民主化民主的机会,现在似乎对一个民主构成了威胁,而这个民主正受到新冠病毒和气候变化否认者的攻击,甚至是更绝望、更激进的现实否认者的攻击。塞弗特认为,现在就是这批人,他们正利用对科学理论和科学事实的(从来都不是决定性的)怀疑来影射进化论、工业引发的气候变化,疫苗的功效或冠状病毒的危害,并且也正是这批人,他们是许多社会中最有发言权和最明显的反制度团体,目前只有反种族主义活动家与他们抗衡。塞弗特认为,这场疫情以及美国毫无希望的两极分化的政治局面(有人会说,其他国家也存在类似情况)表明,对真相的基本共识的瓦解可能会成为民主秩序的问题。这并不意味着,塞弗特也不相信对科学的社会方面的批判性分析与科学与权力的交织是无关的,甚至两者交织在一起本身就是危险的;然而他强调,如果理想的科学民主化仅仅意味着废除和相对化科学权威,这最终将科学专业知识(包括社会科学的专业知识)与日常思维等同起来,无论其“技术性”如何,决策过程将完全取决于政治利益,并且在公开辩论中扼杀任何基于事实的辩论。正是基于他的这种观点,对科学真理进行积极的、建构主义的批判之局限性由此变得清晰起来。
在某种程度上,我同意塞弗特的观点,尤其是关于他对当前科学敌人的描述。事实上,这些人往往是理性和人性的法西斯之敌。然而,这些人攻击的不是技术治理思维定式。例如,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乐见自己的虐待狂冲动被欧盟境内的强制措施所满足,而这些强制措施皆出自于技术统治论思维定式。
在反科学的阴谋论思维的重锤和近年来日益受反民主右翼势力控制的以科学为基础的技治机构的铁砧之间,那些被三位作者称为“通过承认技术上的必要性来实现团结的‘理性的’人”,可能会因为没有对科学和真相的概念采取明确和强有力的立场而被击得粉碎。最近,“未来的星期五”运动重振了一种非常过时的科学信仰——但它只是从几十年前的学术和社会运动话语来看是非常过时的,而它本身是基于一种更古老的技术哲学。事实上,近二十年来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的新的、往往是超人类主义者的技术未来主义对科学抱有类似的坚定信念,然而与之相伴的却是对技术进步所持同样过时的信念。这两种运动,以及当前其他的非法西斯的学术和政治运动,似乎正在向一种共识靠拢,这种共识将19世纪的自由主义与文化进步理念(就迄今为止被边缘化和受压迫的社会群体的成功身份政治而言)以及或多或少的生态技术治理解决方案结合起来,以应对资本主义对自然的破坏性统治。
我们的确可以(不仅仅是在当前疫情之下)“将我们的技术治理状态描述为一种被流放在国内、对现在失去耐心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失去未来和过去等于失去了政治”,并且“剩下的只是一种对必然规则的反抗”,或者我们可以说是,选择“礼貌的沉默”。
20世纪的技术哲学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技术化科学的社会崛起、随之而来的技术化科学自身的危机以及与之相伴的现代人无家可归的问题——现代人固然都是“在世”的,然而,由于与过去另一个想象出来的世界或“超越”的世界纠缠在一起,他也是被流放的。由于目前科学思想的公众理解的下降以及理性敌人的崛起——与两次大战期间不同——至少对北美和欧洲的所有社会,特别是古典自由民主国家产生了显著影响,科学正在失去其指导社会制度的特性。公民科学和公民STS的提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这一缺陷。然而,倘若没有产生民主的、反资本主义的方式来替代当前的社会秩序,那么技术哲学和STS必将很快发现自身处于一种奇怪的境地,除了帮助重塑科学的权威之外,无法做任何合理或明智的事。有一个可疑但非法西斯的信仰作为一个人代表理性的人采取行动的动机,总比完全没有这样的动机要好。
3.关于行动
作为一个结论,我在这里所能提供的只是一个粗略草图,它勾勒出我们的领域在一个快速变化的世界中可能扮演的新角色。在自由民主的一日(光阴)结束时,破除虚假客观约束(Sachzwang)和“别无选择”的魔咒将归结为可能存在怎样的资本主义替代方式的问题。除了将(其他)公民引入我们自己的领域,不是将其作为研究对象或业余参与者或替补专家,而是作为创造此类替代方式的同志,STS的一个主要目标可能是与理想主义自然科学家和工程师以及像“未来星期五”这样的运动结成新的联盟。为了发挥这样的作用,技术哲学最杰出的任务之一必须是再次阐发社会技术进步的综合概念,以使我们的技术星球真正地、可持续地宜居。谈及道德反思,至关重要的是,要将其置于已达到的生产力水平之上,并避免任何基于可疑假设的争论,这些可疑假设均出自一种“规定的”资源稀缺,例如,在当前关于“分诊”的讨论中,该术语的使用与许多国家针对卫生系统发动的经济战争相呼应。
为了能够真正有助于“打开客观约束的黑箱”,STS需要重新发掘他们自己的领域。如果成功的话,这样的再发掘也可能让技术哲学在重新获得我们“为自己想象出另一个世界的能力”方面发挥关键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