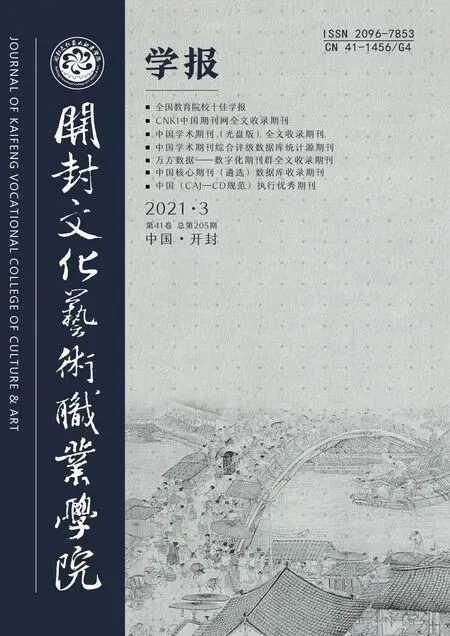近代英人旅华游记的历史地理内容和价值探析
——以托马斯·布莱基斯顿《江行五月》为代表
曾维英
(西南大学,重庆 400715)
一、近代西方旅华游记与《江行五月》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国门洞开,出于游历或者考察等目的,一大批西方探险家和游历家深入中国各地并留下文字记录。西方在中国的探险历程可概括为从海洋到内陆[1]。19 世纪上半叶的探险活动属海洋航行范畴,19 世纪后半叶的探险活动主要在中国内陆展开。特别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后,在1858 年签订的中英《天津条约》中,由于西方列强的威逼,清廷放宽了外商进入内地的条件,允许“英国民人准听持照前往内地各处游历、通商”,从此外人得以深入内地。这给西方人探险游历提供了可能性和便利性。相比中国其他地方,由东到西溯长江而上的英人游记比较集中,时间集中,路线也比较统一,呈现出系统性。代表性游记有托马斯·布莱基斯顿的《江行五月》、吉尔的《金沙江》[2]、阿奇博尔德·约翰·立德的《长江三峡及重庆游记——晚清中国西部的贸易与旅行》[3]等。
托马斯·布莱基斯顿(Thomas Blakiston)是英国著名探险家、博物学家。《江行五月》是托马斯·布莱基斯顿组建的“扬子江上游考察队”于1861 年溯扬子江而上,历时5 个月从上海到达今四川宜宾的游历行程记录。托马斯·布莱基斯顿一行是“第一批未加乔装打扮就深入内陆省份四川游历的欧洲人”,在其后,探险家们纷纷效仿,可以说他们是中国内陆探险的先锋队。此次考察长达5 个月,全部为水路,对川江①沿线的情况记载更为集中和真实。布莱基斯顿本身为博物学家,有丰富的科考经验,所以他的记录相对科学客观。由此,本文选取《江行五月》为主要研究对象进行历史地理学分析。
二、《江行五月》中的历史地理内容
(一)川江沿线的历史自然地理内容
《江行五月》中详细记载了川江的自然地理信息,包括航道险狭情况、通航条件、气候、动植物情况、矿产资源情况等。
第一,《江行五月》记录了19 世纪60 年代川江的险狭、通航条件差等情况。在该书中,作者对从宜昌上溯三峡间两岸的整体印象是奇峰陡立、峭壁对峙、风光奇绝,但是并不适合通航[4]116。上溯至万县河段以后,长江江面变得开阔,川江干流沿线进入平行峡谷地区,大江强行穿越平行山脉,河道也随着山脉走势变化。作者注意到,“当与山脉平行时,河道通常又长又直,当横穿山脉时,则曲折多变”。作为深入中国内陆的第一支考察队,作者一行对川江河流落差、流量和航路数据进行了精确测量,并与尼罗河、亚马孙河、密西西比河、泰晤士河等世界大河的落差进行比较[4]253,这些具体数据有助于我们了解长江河道、流速、流量等的变化。
第二,《江行五月》对当地的气象和气候记录十分细致。在此次航行中,作者记录了航行于扬子江上5 个月的气象情况,涉及每天早中晚的气温、气压、风力情况与天气状况。从记录中可以看到,1861年的春季,四川地区气温偏高,为暖春,“没到4月中旬,小麦和大麦已长穗,豌豆和蚕豆也即将成熟”[4]133“天气已经变得闷热难耐”[4]156;夏季雨季漫长,炎热潮湿。同时,作者认为这种特殊气候与四川的农耕相适应,造就了物产丰富的“天府之国”[4]275。
第三,《江行五月》记载了川江沿途主要的植被情况和植物种类。作者沿途所见为:川江沿岸的沿途只有为数不多的几片小树林,峡谷地带也只是山顶有些林木[4]166。可见,当时的农业垦殖和手工业发展对森林破坏十分严重。川江沿岸所见木材主要为桐树、松树、杨树以及成小片分布的竹林,这些皆为四川省常见树木种类。按照近现代植物分类体系及命名方式,威廉·胡克爵士对沿途遇到的蕨类植物进行了记录和分类,列了一个清单,清单中包含7 个科别23 种蕨类植物,并且对每种蕨类植物进行了一定的说明,具有系统性和科学性。
第四,《江行五月》中的动物记载相对较少,除了部分鸟类记载外,我国长江流域珍稀鱼类物种江豚也引起了作者的注意。江豚一直跟随探险队的船只上溯到宜昌,此后这种可爱的身影便消失在茫茫江水中[4]108。可见,近代长江中江豚数量较多,与江豚濒临灭绝的现状形成鲜明对比。布莱顿斯基还注意到长江江豚分布最西界为宜昌,川江段没有江豚的踪影。这主要是因为宜昌以上暗礁遍布,激流太大,不适合江豚生存。这为我们今天研究江豚分布和抢救性保护对策提供了一定的依据。
第五,《江行五月》还记录了川江沿岸的地质情况、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式以及淘金过程。“从扬子江沿岸所获地质样本”附录表记载了作者从宜昌到叙州期间采集的31 种样本,并标注了采集地点与时间。这份样本十分细致,对研究川江沿线地质情况提供了科学数据和标本。此外,作者还多次提到矿产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如“万县附近产煤,而且烧用广泛”[4]156,“南岸的安坪及其上游一带正在开采煤矿”[4]138。淘金也是沿途比较独特的景观,从万县至重庆“这一段扬子江遍布广阔的沙石浅滩,其间混杂着礁石,有大量采金场”[4]160,重庆上溯泸州段中也有“不少地方都在淘洗金沙”[4]204。密集的采金场让人联想到“金沙江”名字的由来,但据作者从淘金点带回的沙子样本检测,里面除了云母,没有其他贵金属的成分[4]160。可见,这种原始的淘金方式十分盲目和低效,并且对河床和河道的破坏也十分严重。
(二)川江沿线历史经济地理内容
《江行五月》中蕴含着丰富的经济地理信息,如川江沿线的农业结构、城市商业等。
作者对行船沿岸土地开垦程度、农业生产方式、农作物结构进行了描述。整体来看,川江沿线农业占地率和土地开垦率高,“每一寸可供灌溉的土地都精耕细作”[4]166。农业生产方式十分传统,水牛十分常见,大麦、小麦收割后直接“在田里用手工脱粒”;而此时,西方国家的工业革命已经开展,现代化农业开始。农作物结构上,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占绝对比例。粮食作物以小麦、大麦、水稻为主,此外还部分种植玉米、高粱、小米等作物。粮食作物的种植主要用于自给自足。在种植过程中,因地制宜,根据地形、地势和气候选择种植。但是,作者并没有写到清代四川地区常见的马铃薯、番薯。这可能是因为一直在江上航行,远处丘陵山地的作物不在视线范围内。经济作物主要以罂粟和烟叶为主,还有棉花种植,但数量较少。罂粟种植范围自夔州到宜昌皆可见到,种植规模以重庆分界,上游规模小于中游。“大规模种植烟叶”的是重庆以上沿江地区[4]205。此外,还种植了各种农副产品,以弥补粮食的缺乏,增加产出多样性。春季、初夏的川江沿岸广泛种植蚕豆、豌豆、四季豆、甜瓜等,盛夏黄瓜种植较为普遍。利于保存的豆类作物也广泛种植。果树一般有“大片的橘林”,桃树、杏树、山楂树等。从种植结构来看,19 世纪60 年代,长江中游地区的农业结构仍然以传统小农经济为主,精耕细作,自给自足。
《江行五月》展现了近代川江沿岸城市商业的区域发展差异以及重庆贸易情况。作者所见万县、涪州、重庆的商业比较繁荣,而夔州商业比较落后。万县城内,甚至是乡村,百姓的生活水平都比峡谷地带好[4]155。万县、涪州、重庆都属于河流交汇处,航运方便,码头文化发达,商业也较为发达,而以夔州为中心的三峡地区经济相对落后,川江沿岸城市商业发展区域差异较大。作者还在附录中统计了重庆进出口商品的价格,出口种类有生丝、白蜡、大麻、烟叶、煤等,以农副产品、药材和矿产资源等初级原材料为主。进口商品除了部分茶、棉花外,主要是从广东进口的洋货,如荷兰羽纱、英国羽纱、各色洋布、杂货等。进出口之间的价格差可达几十倍。这说明当时重庆地区已经成为西方的原料掠夺地和商品倾销地。
(三)川江沿线历史人文地理内容
《江行五月》中记载了丰富的人文地理信息,如人口、建筑景观,为研究川江沿岸历史人文地理提供了宝贵的史料。
人是社会历史的主体,作者记录了各色各样的人物,如纤夫、妇女、儿童,并记录了川内人见到外国人的表现,以及作者自身对川内人民的看法。首先描述最多的是纤夫。川江段尤其是三峡段河床起伏大,河道弯曲,暗礁遍布,上溯时往往不能凭借风力和船桨前进,只能通过人工拉纤。作者对纤夫拉纤的场景着墨甚多,生动的文字一方面表现出纤夫的辛苦,另一方面则体现了长江三峡的险峻。其次是沿途所遇到的农夫、孩童和妇女。虽然鸦片战争后中国的大门开始打开,西方人和西方事物逐渐涌入中国,但是对于内陆地区的四川人民来说,第一次见到没有乔装打扮的外国人仍然十分惊奇。好奇的孩童与急匆匆跑来围观外貌古怪的洋鬼子的农夫[4]166,表明外国人在当时十分少见,四川的开放程度仍然很低。妇女也是作者关注的对象之一,四川妇女给他们印象最深刻的是“她们时常在奇丑无比的脸庞上梳着古怪的发型”[4]168-169,大多数妇女都是小脚[4]169。这展现出英国人视角中晚清妇女的面貌。虽然沿途所遇到的农夫有些“古怪”,他们将外国人看作外来物种,并可能怀有敌意,称呼为“长毛”“洋鬼子”,但是作者认为,川内人民整体仍是友善的群体,“言行举止远比其他省份的人优雅、干净整洁,百姓整体生活富足”[4]167。与其他省份相比,“四川人精力充沛,生活富足,看不到南方人的阴柔、孱弱,也没有北方人的凝重、粗糙”[4]167。不论这种评价是否为作者的真情实感,但也从侧面反映出因为良好的自然环境、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与沿海相比较安宁的局势,川内人民生活富足,安居乐业。
《江行五月》还记录了上溯途中的风水塔与乡村景观。风水塔是四川地区比较常见的建筑,因为古人认为“大江东去,浪淘尽”,江水滔滔而下会带走当地好运,为了留住这种风水,往往沿江沿河修建宝塔。据统计,清代“长江从泸州到奉节流经县共23 座风水塔”[5]。作者记录了沿途的众多风水塔,塔与城池融为一体,构造出美丽的沿河景观。独特的四川农舍和农村景致在作者眼中也美不胜收。作者眼中“黑、白的四川农舍,非常独特”[4]166,同行的古察伯也说:“四川是帝国最漂亮的省份。”[4]166
三、以《江行五月》为代表的英人旅华游记的主要特征和历史地理价值
以《江行五月》为代表的英人游记的显著特征如下:
第一,科学性和客观性。英国游历者一般具有近代科学知识背景,通常能用较为现代化的思维看待国人习以为常的景和物,能从比较客观的角度对其进行分析和描述,特别是历史自然地理信息。比如,对川江沿岸地质地貌的关注,对气候气象的精确测量记载,利用现代科学体系对动植物进行分类命名等。
第二,以开辟内地、获取资源为目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西方开始将侵略眼光转入中国内地,尤其是长江流域。英国探险家们主要以探路或者勘探资源为目的深入内地,因此,他们在探险和科考中十分重视矿产资源的分布与开采,重视川江的通航条件,关注鸦片、烟叶等经济作物种植等,试图从长江上游攫取更多经济利益。
第三,游记作者带有发达文明的优越感。近代进行内陆探险的西方人主要是商人和科学家,他们接受过西方良好的教育,经历过西方蓬勃发展的工业文明。中国川内地区,普通民众受教育程度低。中外文化背景的巨大差异导致双方存在较大的认知差异,双方自然也就对各自产生不同的看法。外国游历者感受到的是中国的落后与中国人的愚昧,字里行间展现的是他们内心的优越感;川内人民看到的是“洋鬼子”奇怪的外貌和生活方式。
游记的价值可归纳为美学价值、史学价值、文学价值及历史地理价值[6]。以《江行五月》为代表的英人游记在近代川江历史地理研究中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和历史地理价值。
第一,具有历史自然地理价值。英人游记广泛而科学地记载了探险途中的自然地理信息,如地质、地貌、河流、气候气象、动植物、矿产资源等,能够弥补近代川江地区历史自然地理资料缺乏的现状,也能补中国传统自然地理资料之不足。
第二,具有历史人文地理价值。除了丰富的社会经济、人口、景观记载,游记多从英人的视角出发,记载了“他者”眼中晚清中国的形象和社会现象,极大地丰富了我们研究晚清社会的视角。托马斯·布莱基斯顿一行是“第一批未加乔装打扮就深入内陆省份四川游历的欧洲人”,四川人对他们的称呼和反应也为研究四川近代化过程提供了史料。这也提醒我们,在研究近代历史地理时,除了要重视正史、报刊、档案资料外,对于西方来华者所留下的游记、考察报告、日记等也应予以关注。
注释
① 本文所指“川江”为从宜宾到宜昌段的长江干流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