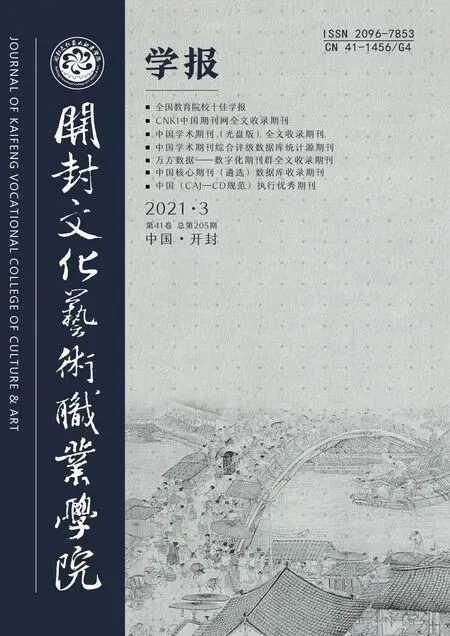柏拉图“节制”与其他“三主德”的关系论析
张蕴睿
(曲阜师范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山东 日照 276826)
节制是古希腊“四主德”(节制、勇敢、智慧、正义)之一,更是柏拉图所认为的城邦各阶级都应具有的美德。柏拉图的节制美德,是能够使个人在认知基础上适当地调控自身欲望并自愿服从统治者统治的品质或德性,这种德性不仅适用于古希腊特定的时空背景,在当今社会依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但就目前的研究来看,学界对其关注不够,对节制与其他“三主德”关系尚有争论。
一、“节制”与“正义”
学界对于节制与正义的关系争论最多,争论主要集中在“节制是否等同于正义”这一问题上。
首先,节制即正义。刘晓欣和赵璟指出,柏拉图认为,如果三个等级都能履行好自己的职责、互不干扰,劳动者能够克制欲望和快乐,该统治的统治,该服从的服从,形成一个和谐统一、协调一致的整体,这就是“正义”,节制就是正义[1]38。罗朝明和王晓涵也持这种观点,并进一步指出,就作用方式来讲,与勇敢和智慧分别存在于城邦的不同部分有别,节制“延伸扩展到全体公民,把各种各样的公民联合到一起,无论是最强的、最弱的,还是中等的”,正义“做自己分内的事和拥有属于自己的东西”的含义与节制德性并无二致[2]。
其次,节制非正义。David Carr 认为,正义包含了个人所有的美德,柏拉图的正义似乎像亚里士多德一律正义的概念一样,是对正确行为的总称,而节制可以粗略地概括为对食欲等的控制,二者不能等同[3]。王梦湖提出,在柏拉图看来,正义是在个人服从天职的情况下“做自己的事”,即个人对某种国家秩序的自觉遵守与维护。节制则是服从某种好的秩序,遵从节制的过程实质上是个人追求正义的过程[4]。Allan Bloom 从城邦的立场出发,认为节制乃是正义的等效物[5]。Nichols 赞成并引用了Bloom 的观点,并进一步指出正义高于节制和其他美德的地方——正义是三种美德的总称,正义就是完美的善,其他几种美德都是正义的表现形式[6]。Andrew Domanski 认为,在《法律篇》中,sōphrosunē 的意义广泛,包括节制、公正、秩序、和谐等,甚至超越了正义[7]。黄裕生对“四主德”进行了排序,他认为正义排在勇敢与节制之前,因为正义首先是使共同体里每个人各守天位而言,因此它必定要包含着勇敢与节制[8]。刘玉鹏认为,柏拉图是通过正义的包容性、生产性和自足性而将它与节制分开的[9]。
如此之多的争论,根源在于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将节制界定为“ 节制就是天性优秀和天性低劣的部分在谁应当统治,谁应当被统治——不管是在国家里还是在个人身上——这个问题所表现出来的这种一致性和协调”[10]152,将正义界定为“正义就是有自己的东西干自己的事情”[10]155。两者都指向一种和谐有序的幸福生活。此外,柏拉图还多次在文中将节制与正义并举,因此正义与节制在定义和作用方式上极易产生混淆。
但从逻辑的角度来看,柏拉图如此伟大之哲学家不太可能混淆自己提出的四种主要德性,况且在构建理想城邦时只提出了四种美德,因此这四种美德必定具有排他性,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节制不同于正义。柏拉图能多次在文中将正义与节制并举仅有两种可能,即二者相同或为包含关系,而出于对柏拉图的信任,后者可能性更大一些。
首先,从作用对象的角度来看,二者的相似性的确源于二者的从属关系。在《卡尔弥德篇》中,卡尔弥德提出了“节制就是做自己的事”[11]86,这种观点与正义为“各司其职”的定义看似十分相近,其实不然。苏格拉底对此观点给予了否定的态度并进行了反驳:“你认为一个城邦治理得好,就是法律规定每一个人都要织造和洗涤自己的衣服……绝不碰跟自己无关的事,专做一切属于自己的事情吗?”[11]88从苏格拉底的反问中可以看出,柏拉图认为节制不仅意味着管自己的事,同时也要管别人的事,但需要将自己的行为节制于职业范围内,进而在阶级总体上表现为一种各司其职。可见这里的节制是不能够等同于正义的。
其次,从作用对象来看,柏拉图的节制美德更聚焦于欲望。柏拉图将节制美德与灵魂三部分中的欲望部分对应,要求欲望应当自然地受到理性的制约,即“做自己的主人”。而正义美德从整个灵魂的角度出发,对应理性、激情、欲望三部分,要求灵魂的这三个部分各司其职,更倾向于是对所有正确行为的总称。其二者虽共同要求个人灵魂及城邦内部和谐有序,但前者是通过对欲望的制约使阶级个体不僭越,强调个人灵魂与国家内部的秩序,后者则是要求灵魂的三部分各司其职,着重于影响他人行为的合法性,前后呈递进关系,因此节制与正义之间应为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
二、“节制”与“智慧”
学界对于节制与智慧的争论主要集中在对《普罗泰戈拉篇》与《法律篇》的解读。在这两个篇章中,柏拉图都提到了智慧这一德性,这里的智慧是否与节制同质是争论的核心所在。
首先,节制与智慧同质。刘晓欣、赵璟认为,柏拉图赞同苏格拉底“美德即知识”的思想,将智慧放在第一位,并依据《法律篇》中“在最高意义上,可以说节制与智慧是同一的”的观点,进一步指出“节制的行为就是智慧的行为”,认为节制等同于智慧[1]40。刘玮在详细论述了苏格拉底“德性统一”的论证后指出,在苏格拉底看来,所有应该去交换的唯一正确的货币是智慧,有了它我们就有了勇敢、节制、正义。刘玮认为,智慧与其他德性之间是一种“整钱换零钱”的关系,智慧是德性的整体,是“那块整个的黄金”,有了它我们就自然拥有了它的各个部分,而节制即为智慧的一部分[12]。
其次,节制与智慧不同质。杨楹和徐双溪基于对《法律篇》的研究认为,节制是法治范式生成的内在伦理机制,而智慧是法治范式向善而生的执政者的伦理基础,节制作为智慧的内核而存在,二者只能在最高意义上等同[13]。黄裕生认为,“智慧是最高的德性,因为它知道善(好)本身而能够知道对每个人而言如何才是好(善)的”“只有智慧才能知道何为节制,节制才不会成为苦行或自虐,所以智慧因保障了节制而包含节制”[8]。
在《普罗泰戈拉篇》中,苏格拉底认为智慧是整块的金子,而节制等美德只是金子的一部分,因此智慧和节制是同质的。在《裴洞篇》中苏格拉底将智慧比作“大硬币”,将勇敢、节制、正义等比作“小硬币”,只有拥有大硬币才能得到小硬币,类似“整钱换零”的思路,所以也表明了智慧和节制的同质性。但上述智慧的概念已经超出了城邦政治伦理意义上的智慧,柏拉图将其解释为“健全的成分或真理”[14],已经不再是城邦统治者所应具有的智慧范畴。而柏拉图的节制美德作为一种具有明显政治意味的美德,应当与同处于政治视角下的智慧,即城邦统治者所应具有的智慧进行比较。城邦伦理中的“智慧”仅能作为“健全真实的成分”的一部分,在《理想国》中,柏拉图将“智慧”定义为:“用来考虑整个国家大事,改进它的对内对外关系的知识”“能够具有这种知识的人按照自然规律总是最少数”[10]146-147。通过上述对柏拉图节制美德的探求可知,节制是一种使人和谐有序的德性,它作为一种和谐的状态无时无刻不在指导着人的具体行为。由此可以推断,城邦伦理中的节制是不能与智慧等同的。在柏拉图的城邦伦理中,节制是智慧得以引导城邦向善的手段,处于统治地位的哲学王,理性地制定法律,循循善诱,给予热衷于利益、欲望满足的被统治者以指导,被统治者则因拥有节制这一美德自然地服从哲学王的安排,统治者的意志得以实现,城邦才能向“善”。
三、“节制”与“勇敢”
节制与勇敢的关系争论较少,因为勇敢与节制都不是柏拉图想要论证的主要德性。二者之间,勇敢在于控制人类对痛苦和艰辛的自然反应,节制可谓是勇敢得以实现的可能。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提出: “勇敢是无论在什么情形下他们都保持着关于可怕事物的信念,相信他们应当害怕的事情乃是立法者在教育中告诫他们的那些事情以及那一类的事情。”[10]147-148
按此定义,勇敢的关键就在于能否在诸多情绪及欲望之中坚定其通过法律及诗乐教育建立起的守法信念。而勇敢所要克服的痛苦、快乐、欲望和恐惧恰内含于节制思想中所要求克服的欲望与感性。此外,评判一个城邦是否勇敢,主要取决于护卫者是否勇敢,而在柏拉图眼中,护卫者也应具有节制的美德。勇敢的护卫者自幼接受诗乐的熏陶以及法律的灌输教育,逐渐培养出坚定的信念或对法律的恐惧,学会以理性克服欲望与感性,使其自身在战争的痛苦、面对敌人的诱惑等多种情形下都能坚守自身守法信念,服从统治者理性的调配,在战斗中无所畏惧,节制美德在这当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倘若一名护卫者没有在美德培养阶段获得节制美德,在柏拉图眼中,他就缺少了最基本的克制欲望的能力,理性对欲望的控制缺少了重要助力。人皆有趋乐避苦的天性,那么没有节制的护卫者在战场上极易因为恐惧死亡而叛逃,也极易因为忍受不住敌人的诱惑而出卖己方利益,这些行为是不节制的,也是不勇敢的。因此,一个人若是勇敢的,他首先一定是节制的,节制为勇敢的实现提供了可能。
结语
柏拉图认为,理想的城邦应具有智慧、勇敢、节制、正义四种德性,节制与其他三种德性有着紧密的内在逻辑关系。通过梳理节制美德与其他三种美德的关系可知,节制的作用是基础的,它是一种使城邦稳定有序的基本美德。它具有内部协调的自我约束性,是聚焦欲望的行为准则。厘清柏拉图的节制与其他“三主德”的关系,不仅有助于理解柏拉图的美德思想体系,而且有助于加深人们对节制美德的认识与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