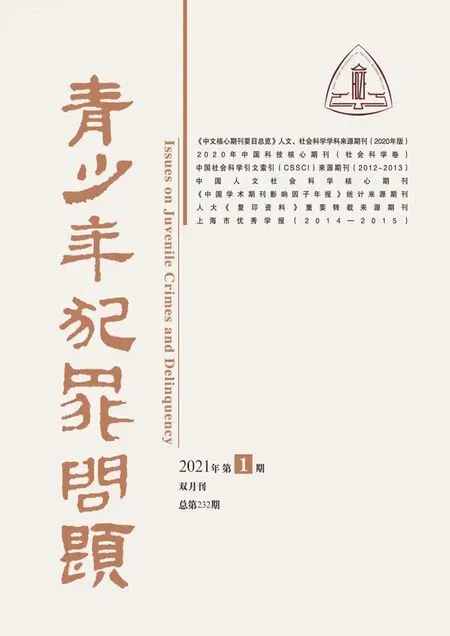论《刑法修正案(十一)》第27条的修改
——兼论性防卫能力削弱司法鉴定意见下强奸罪认定标准的本质回归
赵拥军
2020年12月26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十一)》第27条增设一条特殊职责人员性侵罪(1)为了行文方便,笔者先暂时以该罪名代指。作为《刑法》第236条之一,即“对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女性负有监护、收养、看护、教育、医疗等特殊职责的人员,与该未成年女性发生性关系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恶劣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有前款行为,同时又构成本法第二百三十六条规定之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一般认为,若该女性同意与特殊职责人员发生性关系的,以该条论处;若其不同意的,则按照该条第2款规定,多数以强奸罪追究特殊职责人员的刑事责任。(2)原《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第21条第2款表述为“有前款行为,同时又构成本法第二百三十六条规定之罪的,依照该规定定罪处罚”。笔者窃以为,为了防止绝对依照《刑法》第236条规定定罪处罚可能导致的罪刑不均衡,现《刑法修正案(十一)》将其修改为“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可以认为《刑法修正案(十一)》新增的该条规定,对处于特殊职责人员监护、看护等职责下的未成年女性的性权利及其背后的身心健康而言,可以起到很好的保护作用。(3)但同时,对于该条修正案可能存在的理解偏差等问题,也存在不同的争议观点。鉴于本文的行文重点,暂且不表。
尽管《刑法修正案(十一)》的修改已经尘埃落定,但笔者认为,为了更好地保护特殊身体状况的女性,以及更加规范性侵犯罪的司法认定,今后的修正案在此基础上应考虑再增加一款,作为第236条之一的第3款,即“明知女性是痴呆者(程度严重的)而与其发生性关系的,或者经鉴定该女性为无性防卫能力的,依照本法第二百三十六条规定论处。”之所以增设该款,大体原因在于:其一,并非所有患有精神疾病的被性侵对象都需要进行性自我防卫能力评定;其二,女性患有精神疾病与其性自我防卫能力是否存在并不存在直接对应关系;其三,即便经鉴定其性防卫能力削弱,与其性自主决定权是否受到侵害之间亦并非存在直接的对等关系。进而,笔者将对此展开探讨。
一、性自我防卫能力概念溯源
《刑法》第236条规定的强奸罪是指行为人在违背妇女意志的情况下,采取暴力、胁迫等手段奸淫妇女。强奸罪无论是既遂还是未遂,行为人在客观上表现为违背妇女意志,采取暴力、胁迫等手段,强行与妇女发生性关系;在主观上则具有违背妇女意志强行与其发生性关系的故意。因此,强奸罪要求行为人客观上的奸淫行为和主观上的奸淫故意均系违背了妇女的意志。是故,与一个精神正常的女性发生性关系是否构成强奸罪,其判断标准便是行为人是否构成违背了妇女的意志,即妇女是否同意与其发生性关系。若同意则不构成强奸罪,反之便构成强奸罪。
然而,对于妇女患有精神疾病障碍的特殊类型的强奸案件,是否违背妇女意志的判断就不能像上述精神正常的妇女那样,仅从形式上看该妇女是否同意,而应借助于性自我防卫能力进行,即判断的前提和关键应该是该妇女的性自我防卫能力是否存在。所谓性自我防卫能力,一般是指被害人对两性行为的社会意义、性质即其后果的理解能力,以及行为遵循法律规定的能力。即被害人是否了解性行为是其一种特有的法律保护的人身权利,具有不可侵犯性,以及是否了解性行为将会对自己肉体、心理产生的影响和后果。(4)霍克钧等:《精神障碍妇女性自我防卫能力及评定中的几个问题》,载《中国法医学杂志》2002年第6期。
在司法精神鉴定领域,首次提出性自我防卫能力概念的是郑瞻培教授。(5)贾谊诚:《对性自卫能力鉴定的探讨》,载《临床精神医学杂志》1998年第2期。该概念作为法定能力名称出现在相关司法精神鉴定领域的法律法规等依据中,则是1989年7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卫生部联合颁布的《精神疾病司法鉴定暂行规定》【卫医字(89)第17号】(以下简称《暂行规定》),该规定第22条第1款明确,“被鉴定人是女性,经鉴定患有精神疾病,在她的性不可侵犯权遭到侵害时对自身所受的侵害或严重后果缺乏实质性理解能力的,为无自我防卫能力”。正是由于《暂行规定》中的明确解释和定义,全国司法精神鉴定领域自1989年8月开始,在强奸或者疑似强奸案件中对被性侵的女性精神障碍者普遍使用了“性自我防卫能力”一词进行鉴定。(6)目前司法鉴定业界基本认同“性自我防卫能力”这一概念,有时称之为“性自卫能力”“性防卫能力”等。详见张钦廷等:《精神病人性自我防卫能力评定的回顾与反思》,载《中国司法鉴定》2019年第6期。根据该《暂行规定》,性自我防卫能力只存在有性自我防卫能力和无性自我防卫能力两种情形。按照一般理解,当妇女存在性防卫能力,即有性自我防卫能力时,若其同意与行为人发生性关系则不构成强奸;当妇女无性自我防卫能力时,即便其同意与行为人发生性关系也构成强奸。因此,结合是否构成强奸的认定思路,对于性自我防卫能力评定的分类便只应存在上述的两分法。但在法医精神病鉴定实践中,精神疾病的严重程度有从重到轻的移行过程,对两性行为的实质性理解能力也处于不完整状态的情况,这就很难把性自我防卫能力截然分为有和无两种,进而便有观点提出将性自我防卫能力划分为无、部分(削弱)、完全的三种。如有学者研究报道的56例精神发育迟滞者的中有5例(8.9%)轻度精神发育迟滞者评定为部分性自我防卫能力。郑瞻培教授则指出,在性自我防卫能力的鉴定案例中约有四分之一评定为部分性自我防卫能力。(7)参见张钦廷等:《精神病人性自我防卫能力评定的回顾与反思》,载《中国司法鉴定》2019年第6期。
可以认为,从法医精神病鉴定实践中提出的性自我防卫能力的三分法是比较符合客观实际,也是比较妥当的。因此,司法部2020年5月29日发布的《精神障碍者性自我防卫能力评定指南》(以下简称《指南》),将性防卫能力分为有性自我防卫能力、性自我防卫能力削弱和无性自我防卫能力三种。其中,有性自我防卫能力是指女性被鉴定人对自身性不可侵犯权利具有完整的认识与良好的维护能力;性自我防卫能力削弱是指女性被鉴定人对自身性不可侵犯权利的认识与维护能力受到损害,但并未丧失;无性自我防卫能力是指女性被鉴定人丧失了对自身性不可侵犯的权利的认识与维护能力。
一般情况下,在有性自我防卫能力与无性自我防卫能力两种类型中,判断行为人与涉案女性发生性关系是否构成强奸罪不会存在争议,即当有性自我防卫能力时,直接以该女性是否自愿进行判断;当无性自我防卫能力时,即便女性自愿也属无效的被害人承诺。问题在于,对于性自我防卫能力削弱的情形下该如何判断是否违背妇女意志,即该如何界定妇女“对自身性不可侵犯权利的认识与维护能力受到损害,但并未丧失”的实质意义,进而如何判断行为人是否违背了妇女的意志?进而如何对该类案件进行司法处断?如司法鉴定领域中有学者提出,“精神疾患妇女被动被奸淫的情况,无论性侵犯者采取任何手段(包括小恩小惠、甜言蜜语、诱惑行为挑逗患者性欲等),患者有无抗拒,甚或表现顺从,事后有无告诉,经鉴定认定患者性自卫能力丧失或有显著削弱的,对性侵犯者皆应以‘强奸罪’定性。如果经过鉴定,认定患者性自卫能力只有轻度减弱,在行为时并无抗拒或者顺从的,则应以奸淫精神疾患妇女行为按‘流氓罪’定性,比前者惩处较轻”。(8)贾谊诚:《对性自卫能力鉴定的探讨》,载《临床精神医学杂志》1998年第2期。郑瞻培教授则认为“在法律处理上,有的根据被告是否“明知”,结合性自卫能力的评定结果进行判决,例如:明知+无性自卫能力判为强奸罪;明知+部分性自卫能力判为流氓罪。新《刑法》虽无流氓罪的规定,但处理上仍可参照《刑法》第236条及第237条规定的精神”,(9)郑瞻培:《性自我防卫能力评定的法律基础及其鉴定实践中的问题》,载《中华精神科杂志》2000年第1期。即按照当时的强奸罪和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的精神处理。
但是,在罪刑法定原则下,司法实践中显然不会按照这些观点进行裁判。毕竟性自我防卫能力削弱当然并不意味着没有性自我防卫能力,但若将此种情形下的性自我防卫能力理解为处于若有似无、似无还有的状态也并不符合“性自我防卫能力削弱”这个概念本身的明确性;同时,司法实践中当性自我防卫能力削弱的妇女与他人发生性关系的,也并不存在行为人的行为既违背妇女意志又不违背妇女意志的情形,即不存在既构成强奸罪又不构成强奸罪的荒谬结论,因此便只能存在构成强奸罪和不构成强奸罪两种截然不同的处理方式。由于目前尚未有规范层面的法律法规等对“性自我防卫能力削弱”类型案件的司法处理予以明确,故在司法实践层面,对于“性自我防卫能力削弱”性侵案件的处理,一般是在区分不同精神疾病障碍类型下进行几乎完全相同的处理思路,即以强奸罪论处。(10)也有观点认为,在一起性自我防卫能力削弱案例中,通过对性自我防卫能力医学要件和法学要件的分析,认为“性自我防卫能力削弱”判断“违背意志”依据很难界定,因而也未侵害被害人性自由决定权,故认为不构成强奸罪。可见,对该种处理思路的所存在的问题展开梳理是妥当处理该类案件的基础和前提。
二、涉性自我防卫能力削弱性侵案件类型及现有司法处理思路的梳理
在法医精神病学鉴定实践中,司法机关通常委托对涉性侵案件的女性进行鉴定,以确定其在被性侵害时的精神状态以及性防卫能力状况,鉴定意见常作为判定嫌疑人是否构成强奸罪的重要证据。结合精神状况的鉴定意见,性防卫能力被评定为削弱的,在司法实践中常存在以下两种类型。
(一)涉性自我防卫能力削弱性侵案件类型
1.精神发育迟滞+性防卫能力削弱型
在该种情形之下,由于被性侵妇女的精神状况经鉴定为中度以上发育迟滞的,其性防卫能力在司法精神鉴定中基本上为无性防卫能力,此种情形下,审判实践中以此认定行为人违背妇女意志进而构成强奸罪并无异议。但少数情形下,被性侵妇女的精神状况经鉴定为中度发育迟滞的,其性防卫能力被评定为削弱的,审判实践中,一般直接以此认定行为人构成强奸罪。如被告人徐子刚与被害人王某于案发前通过朋友认识,于2016年5月某日,在被告人的家中,强行与王某发生性关系并致王某怀孕。经鉴定,被告人徐子刚血样与标记“王某流产物”的塑料容器内的流产组织在D3S1358等22个基因座符合生物学父母子关系。王某经诊断为中度精神发育迟滞,在此次被强奸时,受智力低下的影响,性防卫能力减弱,法院以强奸罪判处被告人徐子刚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11)辽宁省海城市人民法院(2017)辽0381刑初17号刑事判决书。
但对于精神状况经鉴定为轻度发育迟滞的,则司法实践中存在不予强奸罪立案以及判决无罪的情形。如2013年4月,某公安分局接报称女性肖某被人强奸。在案件侦办过程中,因家属反映肖某存在智力缺陷,该分局委托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对其进行司法鉴定,鉴定意见为肖某患有轻度精神上发育迟滞,为性自我防卫能力削弱。最终公安机关以证据不足为由对此案不予以强奸罪立案侦查。又如被告人张某系某县一个垃圾场的工人,与被告人同住一县的女青年李某患有轻度精神发育迟滞。某日,张某在捡拾垃圾时发现李某“表情异常,自言自语”。张某主动上前与李某搭讪,并在谈话的过程中察觉李某可能是个傻子。随后张某好言哄骗,并以给李某买好吃的为由将李某骗到自己在垃圾场的宿舍内。一进宿舍张某试图去摸李某的胸部,被李某躲避。后张某软硬兼施,连哄带骗将李某强行按到床上奸淫。李某由于受到陌生环境的刺激不停地哭闹。一个星期后公安机关接到举报,说张某在拐卖人口,公安机关接到报案立刻展开调查,经调查取证公安机关认为张某有犯强奸罪的嫌疑,将其移送检察机关以强奸罪审查起诉。法院在审判过程中,张某承认与李某发生过性关系,但为自己辩解说那是“她自愿的”,不认为自己犯有强奸罪。法院委托司法精神医学鉴定,李某患有轻度的精神发育迟滞,其性防卫能力削弱,有一定的认识能力和辨认能力。法院根据《暂行规定》等规定,判决张某无罪。(12)王庆泽:《关于强奸案件中精神病被害人的权益保护》,西南政法大学2011年硕士学位论文。同时,精神状况经鉴定为轻度发育迟滞的情形,在审判实践中也有以强奸罪论处的。如被告人张巨庆于2013年5月,在腾讯QQ网上结识被害人赵某,并诱骗其说出真实姓名、年龄和所在学校,后以“你想在学校出名吧”相威胁,迫使被害人到新乡市锦江之星宾馆房间,在该房间内强行对被害人搂抱、亲,并强行与其发生性关系。在案件办理过程中,因家人反映赵某智力低下,2013年11月,公安机关委托某司法鉴定机构对其鉴定,鉴定意见为赵某案发时为边缘智力,具有完全性自我防卫能力,公安机关拟不予以强奸罪立案,被害人家属对此提出异议。2014年4月,经重新鉴定,赵某患有轻度精神发育迟滞,评定为性自我防卫能力削弱。后公安机关以强奸罪立案侦查,此案被告人最终被以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13)河南省新乡市卫滨区人民法院(2015)卫滨刑初字第168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15)宝少刑初字第13号。
2.精神疾病障碍+性防卫能力削弱型
在该种情形之下,由于被性侵妇女的精神状况经鉴定为存在精神疾病障碍的,如双相情感障碍(14)双相障碍也称双相情感障碍,英文名称为Bipolar Disorder(BPD),英文别名Bipolar Affective Disorder,是指临床上既有躁狂或轻躁狂发作,又有抑郁发作的一类心境障碍(mood disorder)。双相障碍一般呈发作性病程,躁狂和抑郁常反复循环或交替出现,也可以混合方式存在,每次发作症状往往持续一段时间,并对患者的日常生活和社会功能等产生不利影响。参见郝伟、陆林主编:《精神病学》,人民卫生出版社2018年版,第120页。、钟情妄想症(花痴)(15)钟情妄想是妄想型精神分裂症的一种,也是存在于病理基础上的歪曲信念、病态推理和判断俗称“花痴”。钟情妄想常源于病人对爱情的错误感知。患有钟情妄想的病人对于自己被人暗恋有着异常坚定的信念,并借此对对方进行纠缠,即使遭到拒绝也不会认为自己的想法有错误,而会将之理解为对方在考验自己的爱情忠诚度。其主要表现是失去正常理智,常常裸露性的本能活动,并显示出高级意向(工作、学习等)减退,而低级意向(性欲、食欲等)亢进。参见郝伟、陆林主编:《精神病学》,人民卫生出版社2018年版,第19页。或者精神分裂症(16)精神分裂症,可表现为前驱期症状,主要有以下几种改变。情绪改变:抑郁、焦虑、情绪波动、易激惹等。认知改变:出现一些古怪或异常的观念和想法等。对自身和外界的感知改变。行为改变,如社交退缩或丧失兴趣,多疑敏感,职业功能水平下降,部分患者可能会出现一些新的“爱好”,如痴迷某些抽象的概念、哲学和宗教迷信问题等。躯体改变,睡眠和食欲改变、虚弱感、头痛、背痛、消化道症状等。部分非青少年患者会突然出现强迫症状为首发症状。显症状期,主要有阳性症状、阴性症状、焦虑、抑郁症状、激越症状、定向、记忆和智能以及自知力等。参见郝伟、陆林主编:《精神病学》,人民卫生出版社2018年版,第89-91页。等,且其性防卫能力被评定为削弱的,则司法实践中对于和该妇女发生性关系的行为人,有的被认定为强奸罪,有的没有被认定为强奸罪。如2016年4月24日晚,杭州市富阳区富春街道附近,被告人郑鑫梁、赵江丰坐在停在该处的浙AXXXXX长城哈佛越野车内候客闲聊时,遇被害人罗某经过,被告人赵江丰搭讪“是否送一送”,被害人罗某同意后上车。随后由被告人赵江丰驾车与被告人郑鑫梁一起送被害人罗某至杭州市富阳区,见被害人罗某不清楚具体住址,且说话开放,被告人郑鑫梁即到后座挑逗、引诱被害人罗某。被告人赵江丰驾车至某村一弄堂内后,也到后座一起对被害人罗某进行挑逗。后被告人郑鑫梁、赵江丰明知被害人罗某精神异常的情况下,在车内先后与被害人罗某发生了性关系。后在驾车途中谎称自己是哈佛大学研究水稻人员,留下假姓名和电话号码,将被害人罗某带至某处,让其自行打车回家。次日,两名被告人被公安机关抓获,供述了上述事实。同年5月,经精神病司法鉴定,被鉴定人罗某案发和目前患有双相心境障碍,目前为精神病性症状的躁狂;受到精神病病情的影响,当时对发生男女性行为的性质、后果及会对自己产生什么影响的辨认能力有限,控制能力明显削弱,评定为有部分性自我防卫能力。同年7月4日,两名被告人补偿被害人罗某损失费人民币12万元,取得谅解。同年9月24日傍晚,被害人罗某跳入富春江身亡。法院以强奸罪判处两名被告人有期徒刑十年六个月、十年九个月等刑罚。(17)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浙01刑终368号刑事附带民事裁定书。再如2018年8月初及8月17日,被告人邹垒羲在上海市浦东新区芦潮港镇附近,跟随素不相识的被害人王某并至王某住处内,先后两次与患有精神疾病的被害人王某发生性关系。在案件办理过程中,因王某存在精神障碍诊疗史,公安机关委托鉴定机构对其进行鉴定。经鉴定王某患有躁狂发作,且长期服药,无论外观还是言语行为均与常人有异。涉案期间处于发病期,评定为性自我防卫能力削弱;后被告人邹垒羲被以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18)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2018)沪0115刑初4582号刑事判决书。
(二)现有司法处理思路的问题梳理
从上述精神发育迟滞和精神疾病障碍两种精神异常且性防卫能力削弱的情形来看,在司法实践中,一方面,只要行为人明知对方系精神疾病患者而与其发生性关系的,法院便直接以强奸罪论处,而不再关注或者不再重点关注其性防卫能力方面的评定情况。如上述被告人赵江丰、郑鑫梁强奸案中,法院认为,被告人赵江丰、郑鑫梁明知被害人罗某精神异常,通过挑逗、诱骗手段,先后与其发生性关系,而被害人案发时患有双相心境障碍,系精神病人,梁被告人的行为均已构成强奸罪,且系轮奸。又如在被告人邹垒羲强奸案中,法院认为,被告人邹垒羲明知被害人是精神病人,仍先后与其发生性关系,其作为一名成年已婚男子,根据社会常人一般认知水平应该可以从被害人迥异常人的言行、举止、行为中判断出被害人精神病并非处于正常状况,但仍与之发生性关系,其行为属于以“其他手段”强奸妇女。甚至,也有法院直接以性防卫能力削弱作为认定强奸罪的依据,如“本院认为,被告人朱光荣与具有部分性防卫能力的妇女发生性关系,其行为已构成强奸罪,应依法追究刑事责任”。(19)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2015)宝少刑初字第13号刑事判决书。
显然,法院认定被告人构成强奸罪的上述判断思路的依据是基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当前办理强奸案件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答》(1984年4月26日〔1984〕法研字第7号)(以下简称《解答》)中的规定,即“明知妇女是精神病患者或者痴呆者(程度严重的)而与其发生性行为的,不管犯罪分子采取什么手段,都应以强奸罪论处。与间歇性精神病患者在未发病期间发生性行为,妇女本人同意的,不构成强奸罪”。但是2013年1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废止1980年1月1日至1997年6月30日期间制发的部分司法解释和司法解释性质文件的决定》废止了《解答》。同时,该《解答》制定于“严打”期间,且当时《精神疾病司法鉴定暂行规定》(1989)〔卫医字(89)第17号〕尚未制定,即“性自我防卫能力”这一概念在该份文件中首次作为法定能力名称正式提出,适用于强奸或者疑似强奸案件中被性侵的女性精神障碍者的鉴定。换句话说,上述《解答》第1条第2项的规定,即便废止后作为刑事政策精神来把握,则现在也需要在精神疾病障碍这个因素之外考虑“性自我防卫能力”的问题。且《解答》第1条第2项中也明确要求“痴呆者(程度严重)”,而前述案例中,被以强奸罪论处的被告人,与其发生性关系的却是精神发育迟滞轻度患者。
另一方面,即便行为人不明知对方系精神疾病患者而与其发生性关系的,事后只要被性侵的妇女性防卫能力经鉴定被评定为削弱的,行为人也几乎均被直接认定为强奸罪。甚至在实践中,可能存在一开始经鉴定为性防卫能力被评定为削弱,家属不服而重新鉴定为无性防卫能力,进而被认定为强奸罪的情形。如2014年6月女性朱某被同村一老年男性强奸。在案件侦办过程中,因朱某平素表现智力低下、反应迟钝,故公安机关委托山西省某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鉴定意见为患有精神发育迟滞(轻—中度),性自我防卫能力削弱。2014年9月,公安机关以证据不足作出不予立案的决定,朱某家属对此提出异议,申请重新鉴定。2014年10月,公安机关撤销不予立案决定,启动重新鉴定,最终朱某被评定为患有中度精神发育迟滞,无性自我防卫能力,公安机关依据重新鉴定意见对此案以强奸罪立案,最终嫌疑人被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20)山西省太原市晋源区人民法院(2015)晋源刑初字第23号刑事判决书。
尽管从保护妇女,特别是患有精神疾病障碍的妇女角度而言,司法实践中的上述做法有其一定的存在逻辑,但在特定的案件情形中,实践中类似上述做法不仅可能使得天平另一端的被告人存在被不合理入罪的情形,对于被害人妇女的相关权利而言,反而可能在保护的名义下侵害了其包括性权利在内的正当的权利。性权利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之一,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能以任何形式无理的干预和粗暴的剥夺。对公民性权利的保护是刑事法律的应有之内容,但司法实践中对绝大部分部分涉及与性自我防卫能力削弱女性发生性关系案件一律以强奸罪的处理,在事实上使得患有精神疾病障碍的成年女性正常的性需求表达除了通过结婚之外已别无他途,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导致了公权力对公民性权利等私权利的不当干涉,超越了法律调整的限度界线。(21)参见王庆泽:《关于强奸案件中精神病被害人的权益保护》,西南政法大学2011年硕士学位论文。进一步而言,实践中的该种处理思路及方式在社会关系的处理和修复上弊端尽露的同时,也背离了强奸罪的立法初衷。(22)如被告人李某,未婚,某日晚在下班回家路上的公交车站发现患有精神分裂症的女性刘某一人蹲在地上哭。李某上前说道:“这么晚,已经没有车了,你走吧。”刘某哭着回答说:“我没地方去”。在接下来的对话当中,李某了解到,刘某是四川人,独自到沈阳来打工,还没找到工作,已经有两天没吃东西。李某心生怜悯,将其带回家,为其提供食宿和衣服,在一个多星期的时间里,李某对刘某颇为照顾。之后刘某对李某提出要求想多待一段时间,李某同意。就这样两人开始了将近两年的共同生活,直到案发。公安机关接到举报,说李某没有结婚但家里有孩子和妻子,公安机关对此立案侦查。经过一审,沈阳市皇姑区法院认定李某明知刘某是精神病人,没有性自卫能力,仍与其发生性关系,构成强奸罪,判处李某有期徒刑4年。判决结果一出,社会为之哗然。几乎所有认识李某的人都认为:李某只是出于好心收留了一名精神病人,两个人在一起生活有两年了,好好的,怎么就构成了强奸呢?李某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在二审中,案件被提交到审判委员会裁决。最终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综合考量了法律、案件的具体情况和社会民意,判决李某无罪,当庭释放。参见:房丽、崔治:《留精神病人被判刑,邻居请命“强奸犯”无罪释放》,载搜狐网http://news.sohu.com/2004/01/17/92/news218649291.shtml,2020年 12月 1 日访问。
综上可见,司法精神鉴定领域中,对性侵犯罪中妇女的精神状况及其性防卫能力的评定意见对于司法裁判中强奸罪认定的重要作用不可谓不大,但强奸罪的认定不能仅凭司法精神鉴定作为出入罪的唯一依据,而是必须要最终结合刑法中强奸罪的明文规定以及法理演绎,即必须回归强奸罪的认定本质而展开。
三、以性自主权是否受到侵害为标准回归强奸罪的认定本质
通过上述对性防卫能力削弱司法鉴定意见下相关强奸案例的梳理,可以认为当前司法实践中对此类案件的处理,明显存在完全依赖于司法鉴定意见而脱离强奸罪的认定本质要求的缺陷。是故,笔者认为,在性自我防卫能力削弱的司法鉴定意见情形下,强奸罪的认定应当回归到行为人的行为是否违背了妇女的意志,进而侵害或者威胁了其性自主决定权的行使这一本质标准上来。换句话说,即不能从表象上,诸如前述案例中那样,以行为人明知对方精神异常且性防卫能力削弱而直接得出行为人与其发生性关系的就构成强奸罪,甚至仅仅以行为人与性防卫能力削弱的妇女发生性关系的就构成强奸罪的司法裁判结论。当的思路应当是:在是否侵害或者威胁了妇女的性自主决定权这一本质标准下,认定行为人是否构成强奸罪便可以围绕该本质标准,以该妇女是否同意和是否基于对自身性权利具有完整认知情况下的同意而展开性自主权是否受到侵害或者威胁的不同判断。
(一)以妇女是否同意发生性关系进行直接判断
由于精神正常的女性对自身性不可侵犯权利具有完整的认识与良好的维护能力,故只要该妇女同意与他人发生性关系时,行为人便没有违背女性的意志,进而不可能构成强奸罪,此时无需也没有必要对该女性评定其性防卫能力。但需要注意以下两个问题。
首先,对于行为人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奸淫妇女的,直接根据《刑法》第236条的规定,以强奸罪论处。因此,对于那些存在明确拒绝以及明显反抗的性侵案件中,不论该妇女的精神是否正常,无需进行性防卫能力评定便可以据此认定行为人违背了妇女的意志,进而以强奸罪论处。同时,对于精神正常的女性在醉酒、药物麻醉等情况下被人奸淫的,可以认为是与暴力、胁迫等同的“其他手段”,进而以强奸罪论处即可,亦无需进行性防卫能力评定。
其次,对于行为人未采取诸如暴力、威胁和其他手段与间歇性精神病妇女发生性关系的,意味着行为人征得了妇女本人的同意,只需对该妇女作出是否属于间歇性精神病患者以及发生性关系时是否处于其精神正常期间的司法鉴定即可,无需进行性自我防卫能力评定。但若经鉴定属于间歇性精神病患者以及发生性关系时处于其精神非正常期间,便需要对其进行性自我防卫能力评定。
(二)以是否基于对自身性权利具有完整认知情况下的同意进行刑法判断
由于强奸罪的保护法益是妇女的性的自主决定权,表现为是否同意与他人发生性关系,这种同意的效力是基于其对自身性不可侵犯权利的完整认知与良好的维护能力,即良好的“对性行为的实质性理解能力或者对性本能冲动的自我控制能力”。(23)霍克钧等:《精神障碍妇女性自我防卫能力及评定中的几个问题》,载《中国法医学杂志》2002年第6期。因此,对于那些无法完整认知以及不能很好的维护其自身性不可侵犯权利的人而言,即便其形式上有同意的表象,也不能认为该同意是在行使其性自主决定权。
首先,对于被性侵对象是幼女的。由于幼女缺乏对性行为的实质性理解能力,以及《刑法》第236条第2款规定:“奸淫不满十四周岁幼女的,以强奸论,从重处罚。”是故,只要行为人认识到女方一定或者可能是幼女,或者不管女方是否幼女,而决意对其实施奸淫行为,被奸淫的女方又确实是幼女的,就可以据此直接认定行为人构成强奸罪,(24)张明楷:《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872页。而无需进行性防卫能力评定或者无需参考性防卫能力评定意见。
其次,对于被性侵对象是痴呆程度严重者(起码精神发育迟滞中度以上)或与之等同类别的精神疾病障碍妇女的。由于这些对象自身受到精神发育迟滞等精神疾病障碍的影响,一般情况下是无法完整认知以及不能很好的维护其自身性不可侵犯权利,导致其对发生的性关系的后果缺乏认知等情形的,只要行为人在与其发生性关系之前或当时明知对方是有精神异常的,且事后经鉴定也是属于上述精神疾病类型的,则可以强奸罪中的“其他手段”认定行为人构成强奸罪。(25)但若行为人确实不知对方是精神病患者或痴呆者,也未采用暴力、胁迫等手段的,则不构成强奸罪。参见张明楷:《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872页。此种情形下,只需对被性侵者的精神状态进行司法鉴定即可,无需对其性防卫能力进行评定,否则可能会人为地造成案件审理复杂化,使犯罪分子有机可乘。(26)张钦廷等:《精神病人性自我防卫能力评定的回顾与反思》,载《中国司法鉴定》2019年第6期。同时,此种情形下的被害人无论是在外观表现上,还是言谈举止中,按照社会一般观念对其进行精神异常的判断是并非难以做到的。但若有证据证明行为人确实不知对方是精神病患者或痴呆者,也未采用暴力、胁迫等手段而与其发生性关系的,则不构成强奸罪。(27)张明楷:《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872页。
可能在例外情形下,对于精神发育迟滞中度的被害人需要进行性自我防卫能力评定。但是,一旦上述情形中的被性侵对象作了性防卫能力评定为削弱的,对其性自主权的行使是否受到侵害进行司法审查则是必要的。
(三)以性自主权是否受到侵害为标准进行综合判断
性防卫能力评定的复杂性在于并非所有的案件都适合进行性防卫能力的评定,且在司法精神鉴定理论和实践中已经得到大多数业内专家的赞同。(28)张钦廷等:《精神病人性自我防卫能力评定的回顾与反思》,载《中国司法鉴定》2019年第6期。由于性防卫能力的评定是以被鉴定人为精神病人作为基础前提的,属于医学要件,否则不适合成为性防卫能力的评定对象。(29)郑瞻培等:《性自我防卫能力评定在司法精神鉴定中的限制》,载《上海精神医学》2005年第6期。因此,将性防卫能力的评定限定在表面上看起来同意或者对发生性关系并未明确拒绝以及反抗的人是较为妥当的,即上述情形中痴呆程度严重者或与之等同类别的精神疾病障碍患者之外的精神疾病患者,如精神发育迟滞轻度以及精神疾病障碍的残留期、恢复期、双相情感障碍以及钟情妄想症等在外观上难以看出精神异常的人。
同时,对于强奸罪而言,表现形式是行为人采取了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其实质是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违背了妇女的意志,进而侵害或者威胁了妇女性的自主决定权的行使。这种性的自主决定权的行使,表现在司法鉴定学意义上就是性自我防卫能力的有、无或者削弱。在这个意义上而言,有精神疾病并不意味着一定无性防卫能力。(30)如实践中,被害人经鉴定系抑郁症,有性自我防卫能力。参加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2020)沪0104刑初857号刑事判决书。同时处于发病状态的精神病患者也并不都丧失性自我防卫能力,有的可能部分存在,有的可能属于有性自我防卫能力。(31)郑瞻培:《性自我防卫能力评定的法律基础及其鉴定实践中的问题》,载《中华精神科杂志》2000年第1期。因此刑法便不能因为该女性系精神疾病患者或者其性自我防卫能力削弱就不加区分地将其直接纳入强奸罪的保护之下,而应判断其是否在精神疾病的影响下,导致无性防卫能力或者性防卫能力削弱,进而其性自主决定权受到侵害或者威胁时,刑法才应当予以保护。因此,对于该部分的精神疾病患者,在性防卫能力被评定为削弱的案件中,便需要结合相关证据,对其性自主权是否受到侵害或者威胁进行综合判断。
如在一起涉嫌强奸的案件中,被告人张某系某快餐店外卖员,某日凌晨0时许,被告人张某接到被害人李某的一个外卖订单,因送餐时电话未接通,被告人张某便回到店里时发现被害人李某在店门口。经过简短交流后发现李某精神异常,便触摸其胸部和臀部。其后被告人又将李某拉至一店门口的拐角处,强行对李某实施触摸胸部等部位的猥亵行为。后李某主动脱掉被告人的裤子,被告人也脱掉李某的裤子并发生了性关系。案发当日10时开始,李某多次打电话给被告人,但被告人未接。当日21时许,李某再次拨通被告人电话后提出让被告人至其住所处。后被告人至李某住处,李某主动脱被告人的裤子,被告人遂与其发生性关系。被告人离开后将李某电话拉黑,李某因想与被告人保持恋爱关系但联系不上被告人,遂至派出所报案称自己被强奸。
后查明李某在案发前一个月左右有过近五年的婚史,且在案发前一年左右家属才发现李某开始表现出精神状态不正常,此前曾正常上班工作并与丈夫经营过网店。案发前半年左右,家属带李某至精神卫生中心,诊断为轻度分裂症(未做精神病鉴定),后李某按时吃了一个半月的药物就自行停药。本案案发后经司法鉴定,李某患有精神分裂症,在案发时处于残留期精神分裂症,在本案中被评定为性自我防卫能力削弱。
承前所述,由于本案中的李某案发时处于残留期精神分裂症,并非类似于精神发育迟滞(起码)中度以上,并不能当然的认为其对发生的性关系的后果缺乏认知,故即便被告人“经过简短交流后发现李某精神异常”而与之发生性关系的, 亦不能直接据此以强奸罪论处。关键还是应判断李某的性自主权有无受到被告人的侵害。根据上述《指南》中明确的内容,性防卫能力削弱是指女性被鉴定人对自身性不可侵犯权利的认识与维护能力受到损害,但并未丧失,其辨认能力削弱。同时,《指南》中对辨认能力损害程度判断的评估应结合的若干标准中的第一条便是“能否理解何为发生性关系、何为正当的性关系、何为强奸”。该案中,李某在案发前一个月左右有过近五年的婚史,其对于何为发生性关系、何为正当的性关系以及性关系本身等所具有的理解能力应当说是不言而喻的,且在案发后,被害人李某因为找不到被告人便去派出所以强奸名义报警,欲找出被告人。在其看来,其不仅能够正确理解强奸的意义,而且也利用强奸来帮助其找人。故其在与被告人的第一次性关系中,脱去被告人的裤子以及邀请被告人至其住所处并脱去其裤子进而发生第二次性关系等行为的理解上,肯定不能据此认定被告人违背了其意志,但能否据此认定李某是在行使其性自主权。换句话说,不能据此直接得出被告人与李某发生性关系的行为侵害了李某的性自主权或者没有侵害李某的性自主权。对此,需要进一步结合司法鉴定意见进行司法审查的是,李某作出的被视为其同意与被告人发生性关系的脱去被告人的裤子以及邀请被告人至其住所处并脱去其裤子发生性关系的行为,是否是因为其精神疾病的原因导致。本案的相关司法鉴定材料显示,李某在与张某发生性关系后欲与对方保持恋爱关系,但由于联系不到对方遂报警称被强奸,这种前后矛盾的观念和行为(既然发生性关系并想保持恋爱关系就不可能去报警称被强奸)是受其精神疾病的影响,或者说是精神分裂症的常见症状之一。但司法鉴定意见并未也不可能指出,本案中,李某主动与被告人发生性关系的行为本身是受其精神疾病的影响所致。
可见,尽管本案中被害人李某患有精神分裂症,在案发时处于残留期精神分裂症,其性防卫能力削弱,但在案的相关证据显示,李某的性自我防卫能力并未丧失到足以影响其性自主决定权的行使,故被告人与其两次发生性关系的行为不应构成强奸罪。(32)一个必须予以正视的事实及假设是,该案中的李某在案发前一个月曾有过五年婚史,且在该案中是想和被告人谈恋爱,假如被告人当时答应与李某谈恋爱,或者没有将其名单拉黑而是与李某在一段时间内保持着这样的关系,该案是否还会案发或者会以一种什么样的状态案发;该案案发以后李某作为一个成年女性,其正常的性需求除了结婚之外,似乎没有其他途径可言。笔者不愿以恶意妄加揣测:倘若李某以此方式与其他男性交往,在满足其正常的性需求之外,是否会因司法实践对被告人以强奸罪论处后,凭添了其假以公权之器,为其私利之用呢?同时,在案证据显示,在被告人第一次与李某发生性关系之前,被告人张某强行触摸李某的胸部等部位时,李某是明确反对的,因此属于强制猥亵行为。但此时尚无证据证明被告人具备强奸的故意,故可以认定该行为构成强制猥亵罪。
同样道理,对于部分精神疾病障碍患者在性欲亢进(一般称之为“花痴”)的自身精神障碍诱因下,因病使其控制意识和能力丧失,或显著削弱使其主动追求男性而发生性关系时,有的甚至采取威胁的手段以遂其情欲等情形的,此种情形下能否以强奸罪论处,首先需要考虑该男性是否明知对方系精神疾病患者(有时即便其辩解不知道,但可以根据案发时一般民众的判断力进行审查即可),其次即便该男性明知对方系精神疾病患者,但若存在以下情形的,就更应审慎对待。(33)参见贾谊诚:《对性自卫能力鉴定的探讨》,载《临床精神医学杂志》1998年第2期。若男方在“花痴”病人的强烈性诱惑下,意志薄弱,顺从了“花痴”病人的要求。这在其他国家、地区也不将这种情况视为犯罪,在司法实践中遇到此种情形的一般就不宜以强奸罪论处,若根据案情需要如此的,也应明显区别于普通强奸罪的量刑。若男方在“花痴”病人威胁下(甚至用刀、剪等利器)与她发生性关系者,(34)若男方在他人的威胁下(甚至用刀、剪等利器)与此种类型的“花痴”病人发生性关系的,则可以根据刑法理论中的期待可能性或者直接以刑法中的胁从犯予以减免论处。则该男方理当不能以犯罪论处。当然,若该男方明知该“花痴”病人发病后有此种表现而故意使其发病进而出现该情形的,则对该男方以强奸罪论处并无异议。
结 语
综上所述,通过将强奸罪认定的本质回归到女性的性自主决定权是否受到行为人的侵害或者威胁的标准上,对于实践中因精神疾病导致的性自我防卫能力削弱案件的处理或许才是妥当的。有鉴于此,笔者认为今后时机恰当,应在本次《刑法修正案(十一)》第27条之后增加一款,作为《刑法》第236条之一的第3款,即“明知女性是痴呆者(程度严重的)而与其发生性关系的,或者经鉴定该女性为无性防卫能力的,依照本法第二百三十六条规定论处。”
一方面,并非所有患有精神疾病的被性侵对象都需要进行性防卫能力评定。由于痴呆者(一般应当是指精神发育迟滞中度以上者)自身受到精神发育迟滞等精神疾病障碍的影响而无法完整认知和维护其自身性不可侵犯权利,故当行为人明知对方是痴呆者仍与其发生性关系的,或者精神发育迟滞中度以下以及患有其他精神疾病经评定其无性自我防卫能力的,可直接以强奸罪论处。另一方面,患有精神疾病与其性自我防卫能力并不存在直接对应关系,即便经鉴定其性防卫能力削弱,与其性自主决定权是否受到侵害之间亦并非存在直接的对等关系。故当前述精神疾病之外的其他类型的精神疾病患者便需要结合其性自我防卫能力评定意见,对行为人的行为是否侵害或者威胁了妇女的性自主决定权进行综合而审慎的司法审查。若能得出肯定的结论,则将行为人的行为依照《刑法》第236条规定的“其他手段”以强奸罪论处,否则便不能认定为强奸罪。
需要注意的是,对于建议增加的《刑法》第236条之一的第3款的性质,笔者认为,《刑法》第236条所规定的“暴力、威胁和其他手段”只是违背妇女意志的几种常见表现方式而已,并且是否违背妇女意志也只是妇女性自主权是否受到侵害或者威胁的外在表象;并且,就目前的一般理解来看,《刑法》第236条所保护的范围是精神正常的女性。因此,在笔者所建议的上述内容下,将精神正常的女性纳入《刑法》第236条所保护的范围,而将患有精神疾病障碍的女性纳入建议新增的第236条之一的第3款所保护的范围也未尝不是一个合理的方案,即认为该条是《刑法》第236条所规定的“暴力、威胁和其他手段”之外所拟制的一种强奸手段。同时,将患有第236条之一的第3款规定之外的精神疾病且性自我防卫能力削弱的女性的性自主决定权依然纳入《刑法》第236条中的“其他手段”进行保护,也正好印证了笔者认为在此种情形下是否构成强奸罪需要进行综合的司法审查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