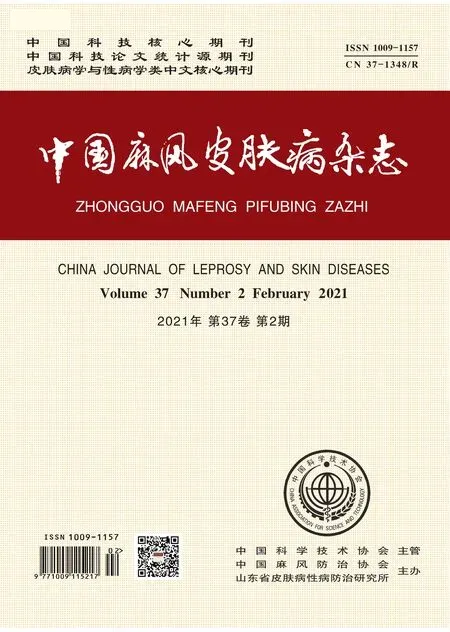疱疹样皮炎研究进展
房小凯 刘 红 张福仁
1山东大学,山东济南,250012;2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皮肤病医院(山东省皮肤病医院,山东省皮肤病性病防治研究所),济南,250022
疱疹样皮炎(dermatitis herpetiformis, DH)是一种少见的自身免疫性表皮下大疱性皮肤病[1],其发病与麦胶(曾称为谷胶)摄入相关,并被认为是麦胶敏感性肠道疾病乳糜泻(celiac disease,CD)的肠外表现之一[2]。近年来,亚洲范围内关于DH的报道逐渐增多,对该领域研究更加全面且深入,本文将从流行病学、发病机制、临床表现、治疗等方面综述DH的研究进展。
1 流行病学
1.1 高加索人群 高加索人群是DH与CD的相对高发人群。DH患者男女比例为2∶1~1∶1,且随患病年龄增长,性别差异逐渐不明显。DH可发生于所有年龄段,30~40岁的成年患者相对多见,亦可发生于儿童[3]。欧洲及北美地区统计数据中,DH患病率为11.2/105~75.3/105,年发病率为0.4/105~2.6/105[3],而在芬兰和英国,CD的患病率分别为661/105和240/105[4],虽然仅有13%左右的CD患者并发DH,DH已然是CD最常见的肠外表现。20世纪70年代CD和DH的年发病率较为接近,而随着时间进展,CD的年发病率明显上升,已达到最初的4倍以上,与之相反,DH却有少许下降,2003年在芬兰有18538例CD患者,其中约有17%患有DH,而2005-2014年的数据显示,仅有4%的新发CD患者合并有DH[5]。CD发病率的上升,除了客观数据以外,可能还和筛查手段更加丰富以及该病逐渐受到重视有关[6]。同时,亚临床及早期、未诊断的CD是发展为DH的条件之一,CD的早诊断、早治疗,可能避免了部分DH的发病[2]。
1.2 亚洲人群 DH在亚洲人群中患病率非常低。中国最早的DH病例报道于20世纪50年代,而自从把直接免疫荧光(direct immunofluorescence,DIF)作为确诊手段以后,中国的临床报道较前大为减少,甚至有学者认为中国不存在DH病例[7]。2012年[8]和2016年[9]国内学者曾一次性分别对22例、36例DH患者进行研究。于Medline数据库(PubMed), 中国知网(CNKI)检索相关文献,目前国内报道DH病例共80余例。综合日本100余例患者[10]和中国患者的统计数据,DH男女患病比例为2∶1,平均发病年龄44岁。而与高加索人群明显不同的是,亚洲DH患者与CD的关系尚未被验证,在一个包括91例患者的回顾性研究中,仅有3例(3.3%)有CD的表现,同样,在中国,22例患者中仅有2例(9.1%)通过肠道病理学确诊了CD,日本地区DH患者对无麦胶饮食(gluten-free diet,GFD)的敏感性也与欧洲报道有显著差异,这可能与地区性饮食习惯以及HLA-DQ2和HLA-DQ8频率很低的遗传学特点有关[8,9]。
2 病因
2.1 遗传 DH表现出明显的家族聚集性特点,超过10%的DH患者有DH或CD家族史[11]。曾有单卵双生双胞胎1人患有DH,而另1人患有CD的报道[12]。目前已证实HLA基因与DH、CD相关联,其中HLA-DQ2(由DQA1*0501、DQB1*02等位基因组成)和HLA-DQ8(由DQA1*03、DQB1*0302等位基因组成)在高加索人群DH患者中阳性率分别为85%、15%[13]。日本DH患者与正常对照HLA-DQ2阳性率无明显差异,HLA-DQ8阳性率则为37%[10,14]。中国DH患者与正常对照HLA-DQ8阳性率无差异,HLA-DQ2中有较明显差异的则为HLA-DQB1*0201(29.2%,正常对照11%)和HLA-DQA1*0501(27.1%,正常对照14.1%)[9]。中国汉族种群一项包括36例DH患者和730名正常对照的研究证实HLA-B*0801和HLA-DRB1*0301与DH的发病相关,在DH患者中,HLA-B*0801等位基因频率为18.1%,HLA-DRB1*0301则为25%,均明显高于正常人。同时,利用HLA-B*0801和HLA-DRB1*0301共同对DH患者进行筛查,阳性率可达61.1%,特异性为93.1%,并且HLA-DRB1*0301与DH患者无胃肠道症状表现出一定关联性[9]。在HLA基因区域之外,IRF1、STAT1、CGREF1、FAS、PLEC1等基因亦被证实与疾病相关,主要与细胞生长、凋亡及真表皮黏附等功能有关[15,16]。总之,亚洲人群和高加索人群DH患者的遗传特点存在明显差异。
2.2 外部因素
2.2.1 麦胶 摄入麦胶是导致DH的诱因。实验证实遗传基础和麦胶摄入对于DH的发病是缺一不可的[17]。小肠活检中,90%的DH患者有不同程度的CD表现,限制麦胶摄入后则逐渐好转。
2.2.2 肠道微生态 肠道菌群有人类“第二基因组”之称,在多种皮肤疾病及自身免疫性疾病起重要作用[18]。对于DH和CD高患病风险的人来说,肠道菌群失稳态可能会促进疾病进展[19]。研究表明麦胶消化后以麦醇溶蛋白的形式与组织型谷氨酰胺转移酶(tissue transglutaminase,TG2,tTG)相互作用,而肠道菌群对麦醇溶蛋白具有一定水解作用,即“良性”菌群可以降低麦胶对于肠道的刺激。同时,肠道菌群通过宿主-菌群交互作用,可以影响肠黏膜屏障及免疫功能,造成肠道免疫力及通透性改变,并且调整细胞因子网络,包括促炎因子(INF-γ、IL-21、IL-15等)及抗炎因子的释放。研究显示DH患者肠道菌群可表现出厚壁菌、拟杆菌(链球菌、普氏菌)明显增多的特点[20]。微生态失衡不仅是疾病活跃期炎症状态的结果,其与发病机制密不可分,DH和CD是由人类基因组和微生物组的改变,以及尚不清楚的表观遗传修饰共同作用的结果,肠道微生态的研究将为预防、治疗该疾病提供新思路[21]。
2.2.3 其它 很多因素可能诱发或者加重DH。系统摄入或外用碘化物可明显加重病情[22],Jimenez等[23]报道了一个多种治疗无效并长期摄入碘化物的DH患者,停止摄入含碘食物后,其症状明显改善,这可能与碘化物刺激中性粒细胞浸润相关,其机制尚不明确,但是研究证明碘化物可影响表皮型谷氨酰胺转移酶(epidermal transglutaminase,TG3,eTG)/IgA复合物在皮肤中的结合力[24],这可能会加速中性粒细胞介导的炎症过程。而消化道手术等造成的肠道炎症可能导致皮肤和肠道抗谷氨酰胺转移酶抗体的交叉反应,进而产生抗eTG的IgA抗体[25]。呼吸道病毒的感染也可通过抑制外周血Treg细胞,使麦胶对机体刺激增强,诱发麦胶敏感性疾病[26]。激素水平亦与DH有关,有报道称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类似物可以加重DH,而另一例病例中,垂体替代治疗治愈了DH。同时,以各种生物制剂为代表的药物引起DH的病例并不少见[5]。DH是一种复杂疾病,众多免疫、内分泌因素在其发生发展中起作用,调节其炎症反应,而对其病因的探索不应局限在HLA基因和麦胶等方面。
3 发病机制
麦胶进入肠道,引起特异性免疫及固有免疫系统应答为DH的主要发病机制。麦胶在肠道中的主要消化产物为麦醇溶蛋白,其与tTG进行脱酰胺基反应后,经由树突状抗原提呈细胞HLA-DQ2分子提呈给CD4+T细胞,进而由浆细胞产生可与eTG结合的IgA抗体。tTG是CD的主要自身抗原,而eTG则为DH的主要自身抗原[27],CD和DH患者中,有些抗体是同时针对tTG和eTG的,而DH患者的IgA抗体则唯独对eTG有高亲和力,其在肠道中产生,考虑到eTG和tTG的高度同源性,可能是一种表位扩展现象的结果。IgA与eTG结合后形成免疫复合物,沉积于真皮乳头,使中性粒细胞趋化,大量蛋白酶释放,破坏透明板,进而导致真表皮间水疱形成。同时,Th2等细胞激活,产生嗜酸粒细胞,也与中性粒细胞共存于水疱处。有理论认为,eTG/IgA是作为循环免疫复合物存在的,不仅沉积于真表皮交界处,亦可出现在真皮血管周围[2,5,21,28]。
固有免疫系统被激活,NFκB通路及天然杀伤淋巴细胞等共同作用导致肠黏膜隐窝增生和绒毛萎缩[21]。而肠道固有免疫激活导致了IL-8增加,进而激活更多中性粒细胞,通过炎症因子和纤维蛋白原作用,其在激活的内皮黏附,并迁移到真皮乳头。而Treg等细胞表达下调,则有助于维持炎症状态下的微环境稳定。角质形成细胞的破坏则可能加速eTG向真表皮交界处聚集[5]。
多种细胞因子参与DH的发病,如以IL-31、IL-17、IL-8等为代表的白细胞介素,以及INF-γ、TNF-a等[29],虽然其目前难以应用于临床检测,但是对于科学研究有重要意义。
4 临床表现
DH可发生于所有年龄段,30~40岁的成年患者相对多见,亦可发生于儿童[3]。DH皮损对称分布,好发于肘部、前臂伸侧、背部、臀部和膝部,多表现为红斑基础上成群分布的张力性水疱,伴严重瘙痒[30]。
5 实验室检查
5.1 病理学 DH典型病理表现为表皮下水疱,内含大量中性粒细胞,真皮乳头水肿、中性粒细胞浸润,浅层血管周围淋巴细胞浸润。DIF示真表皮交界处或真皮乳头IgA颗粒状沉积,亚洲病例中少数可为纤维状[10]。
5.2 血清学检查 血清抗肌内膜抗体、tTG抗体、eTG抗体、抗脱酰胺醇溶蛋白肽抗体应纳入常规检查项目。根据中国汉族人群的研究统计,DH患者中血清抗肌内膜抗体、tTG抗体、eTG抗体阳性率分别为44.0%、58.8%、47.1%[9],而其在高加索人群中的阳性率分别为52%~100%、47%~95%、52%~100%,特异性均超过90%[31]。抗脱酰胺醇溶蛋白肽抗体由于阳性率较低,在临床工作中则仅用于少数疑难或尚未产生其它抗体的婴幼儿病例。因为eTG在单纯CD患者中也有30%以上的阳性率,因此,其对于部分DH患者诊断价值有限[32]。
6 诊断
欧洲指南提出了DH的诊断标准。对于疑似的患者,首先应进行tTG和DIF检查。DIF示真皮乳头颗粒状IgA沉积是诊断DH的必要条件。高度怀疑DH但DIF阴性的患者如正在进行GFD,建议给予含麦胶饮食,并在至少1个月后进行活检,可提高阳性率。对于DIF表现典型并且tTG阳性患者,可以诊断为DH。如果tTG为阴性,建议进行HLA-DQ2/DQ8检查,阴性可排除DH或CD。而当HLA-DQ2/DQ8为阳性时,进行脱酰胺醇溶蛋白肽抗体和抗肌内膜抗体检查,如果阳性则可以确诊。如果为阴性,则进行肠道病理检查[33]。此标准适用于高加索人群,但对于亚洲人群并不完全合适。
国内目前仍无DH的诊疗指南或专家共识,但是有学者曾提出诊断方法作为DH临床研究的纳入标准,包括皮损形态、病理DIF[9]。相较于欧洲指南,将遗传学、血清抗体和肠道病理等检查纳入DH的诊断标准应是国内学者下一步工作的重点。
7 治疗
DH的治疗目前主要依靠氨苯砜配合GFD。
7.1 无麦胶饮食(GFD) 严格GFD应作为治疗的首要原则。对于部分轻症患者来说,GFD后症状即可逐渐消退。除日本地区多数DH患者无麦胶敏感,且药物治疗后可缓解,患者对GFD依从性差以外[10],GFD不仅对于DH和CD的疗效明确,其在预防包括淋巴瘤在内的多种并发症方面亦有效[34],因此长期保持GFD是DH良好预后的基础[30]。
7.2 药物治疗 对于皮损严重,瘙痒剧烈的患者,氨苯砜往往能迅速缓解症状。成人氨苯砜初始剂量为25~50 mg/d,平均维持剂量为100 mg/d。在进行氨苯砜治疗前,推荐进行HLA-B*1301风险位点和葡萄糖-6-磷酸脱氢酶检测,以预防氨苯砜超敏综合征。对于不能耐受氨苯砜的患者,使用柳氮磺吡啶或者两药联合治疗以减少氨苯砜用量也可作为备选方案[35]。研究显示氨苯砜可影响中性粒细胞的多种功能,包括抑制中性粒细胞与基底膜带抗体的粘附,这可能是氨苯砜对DH有效的原因之一[36]。
有报道认为利妥昔单抗等药物[37,38]对于DH有效。而对于顽固性DH,具有抗中性粒细胞作用的秋水仙碱,以及硫唑嘌呤、吗替麦考酚酯等免疫抑制剂亦是可尝试的方案[5]。另外,针对发病机制的治疗仍在研究当中,包括抑制tTG或eTG,HLA基因封闭,使用麦胶类似物竞争靶向位点和调节免疫耐受等[39,40]。
7.3 预后 DH预后良好,瘙痒症状可在服用氨苯砜48~72小时后缓解。而在治疗过程中,应定期检查血常规及肝功能,监测葡萄糖-6-磷酸脱氢酶,避免药物不良反应。多数DH患者通过严格而长期的GFD,减少或停止氨苯砜后,也可控制病情。
8 小结
中国和亚洲DH病例并不少见,国内临床医师和学者们应给予更多关注。经总结发现,亚洲人群DH的风险基因不同于高加索人群,但尚需国内外的进一步验证。DIF表现可呈现纤维状IgA沉积亦不同于欧洲报道。氨苯砜依然是治疗DH的首选药物,但其作用机制和GFD在亚洲尤其是日本人群的应用有待进一步探讨。鉴于国内目前仍无DH的诊疗指南和专家共识,且欧洲指南对于我们的借鉴意义有限。我们倡议,为了进一步认识并诊治DH这一疾病,国内合作开展临床研究,并以证据为基础制定中国DH诊疗指南的工作,应进入皮肤科学界的议程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