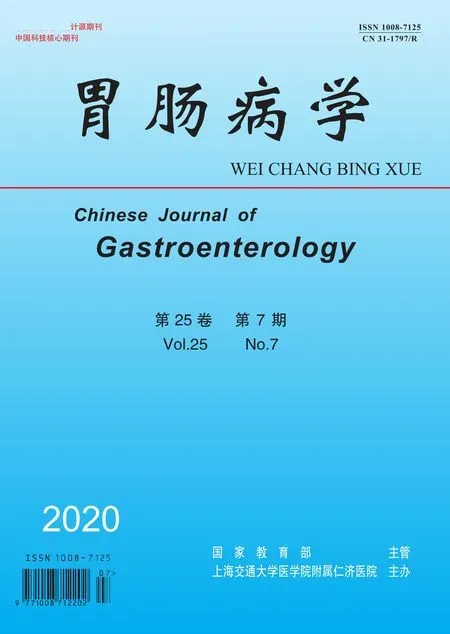肠道免疫调节细胞在维持肠黏膜稳态中作用的研究进展*
冯钟生 刘占举 吴 维
同济大学附属第十人民医院消化内科(200072)
胃肠道黏膜和肠道相关淋巴组织[包括派尔集合淋巴结(Peyer’s patches, PP)、独立淋巴滤泡、肠系膜淋巴结]构成了机体一个特殊的“免疫器官”,通过协调固有性免疫应答与适应性免疫应答,一方面防御各种有害病原体的入侵,另一方面避免对无害的细菌、食物等抗原产生过强的免疫反应。肠道免疫调节细胞包括调节性T细胞(Treg细胞)、调节性B细胞(Breg细胞)、调节性树突细胞(DC)、M2型巨噬细胞、固有淋巴样细胞(ILC)、成纤维网状细胞(FRC)等,在维持肠道免疫应答的平衡中发挥重要作用。哺乳动物的肠道容纳了大量微生物,包括细菌、真菌、病毒等,肠道菌群失调与多种疾病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如炎症性肠病、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甚至肿瘤。目前大量研究表明免疫调节细胞与肠道菌群的相互作用是维持肠道黏膜稳态的关键环节。本文就肠道免疫调节细胞在维持肠黏膜稳态中的作用及其研究进展作一综述。
一、Treg细胞
Treg细胞是最早发现的具有免疫抑制功能的淋巴细胞,根据其分化途径可分为胸腺内产生的Treg细胞(tTreg细胞)和外周诱导产生的Treg细胞(pTreg细胞)。Treg细胞的基本功能包括:分泌抑制性细胞因子IL-10、IL-35、TGF-β等;产生颗粒酶等诱导靶细胞裂解;干扰细胞正常代谢;与效应T细胞竞争IL-2;通过核苷酸酶CD39和CD73产生具有免疫抑制效应的腺苷;调控抗原呈递细胞(如DC等)间接影响效应T细胞的活化。
Treg细胞对肠道菌群的调节是其维持肠黏膜稳态的重要途径。一方面,Treg细胞能限制机体对肠道菌群的过度细胞免疫反应,促进共生菌在肠道内的定植。Campbell等[1]发现Foxp3GFPΔCNS1小鼠(pTreg产生缺陷)肠黏膜内细菌引起的Th2型免疫反应明显增强,进而干扰Mucispirillumschaedleri、Lactobacillusjohnsonii等边界定居菌的正常定植。另一方面,在PP等部位Treg细胞可促进滤泡辅助性T细胞(TfH)和IgA+B细胞分化,提高肠腔内IgA浓度,从而限制肠腔内定植的细菌(如节段丝状细菌)向深部组织移位,避免机体产生全身性免疫反应[2-3]。此外,Povoleri等[4]发现结肠固有层中全反式视黄酸诱导产生的CD161+Treg细胞亚型能促进肠黏膜损伤修复。
Xu等[5]发现肠道Treg细胞的发育和功能依赖转录因子c-Maf,条件性敲除c-Maf基因后Treg细胞限制肠道细菌特异性Th17细胞反应的能力明显受损;Neumann等[6]发现c-Maf可直接调控IL-10、CTLA4等基因转录,证实其对Treg细胞的功能具有重要作用。
二、Breg细胞
目前已发现多种具有免疫抑制功能的B细胞表型,小鼠体内包括过渡性2期边缘区前体(T2-MZP)细胞,CD5+CD1dhiB细胞(即B10细胞),边缘区(MZ)B细胞,Tim-1+B细胞,CD138+浆细胞;人体内包括CD19+CD24hiCD38hiCD1dhi细胞(相当于小鼠T2-MZP细胞),CD19+CD24hiCD27+细胞(相当于小鼠B10细胞)。
Breg细胞的免疫调节功能可能主要由IL-10介导,Yuan等[7]利用小鼠细胞移植实验发现B10细胞可通过产生IL-10抑制肠系膜淋巴结中Th1细胞作用,从而减轻DSS诱导的结肠炎症。Breg细胞也能诱导产生Treg细胞,该作用依赖于CD80/86等介导的细胞直接接触[8]。此外,Breg细胞能抑制DC分泌促炎细胞因子,进而阻止CD4+T细胞向Th1/Th17细胞分化[9]。Oleinika等[10]发现CD1d+Breg细胞通过呈递脂质抗原诱导恒定自然杀伤T细胞(invariant natural killer T cells,iNKT细胞)的产生,并进一步抑制Th1和Th17细胞介导的自身免疫反应并减轻实验性关节炎反应。实验表明以α-半乳糖神经酰胺等糖脂激活CD1d限制性NKT细胞能改善DSS诱导的结肠炎症[11],但该过程是否必须依赖于Breg细胞的参与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Toll样受体(Toll-like receptors, TLRs)信号参与对Breg细胞的调节。脂多糖(LPS)联合佛波酯、离子霉素能诱导B细胞分化成CD5+CD1dhiB10细胞。Lino等[12]通过直接给予小鼠静脉注射LPS,结果发现一群体内天然存在的LAG3+CD138+浆细胞受到TLRs刺激后能迅速产生大量IL-10。此外,在一个MHC-Ⅰ不匹配的皮肤移植模型中,将常规设备而非无菌设备中饲养小鼠的B细胞移植至皮肤受体小鼠能延长皮肤移植物的存活期,表明肠道细菌有助于小鼠B细胞获得免疫抑制和促进移植耐受的能力[13]。Rosser等[14]进一步发现肠道菌群刺激巨噬细胞和DC产生IL-1β和IL-6,从而诱导Breg细胞分化和IL-10产生。上述体内和体外研究均表明肠道菌群对Breg细胞正常发挥作用非常重要。但关于Breg细胞调节肠道菌群免疫耐受的机制目前知之甚少,今后需行更深入的研究来阐明。
三、巨噬细胞
哺乳动物肠道中有大量巨噬细胞定居,多数位于黏膜固有层。肠道巨噬细胞可有多种来源:在胚胎发育过程中,巨噬细胞起源于卵黄囊;出生后肠道巨噬细胞的更新主要依赖于血液循环中Ly6Chi单核细胞的迁移分化。
在稳定状态下,肠道巨噬细胞在清除入侵微生物的同时并不会产生大量促炎因子而引发过强的炎症反应,这非常有利于肠黏膜的稳态。早期体外研究[15]证实肠道固有层巨噬细胞不仅可分泌IL-10,在TGF-β存在的条件下还能高效诱导Foxp3+Treg细胞的产生,表明肠道巨噬细胞可主动发挥抗炎效应。Krause等[16]利用小鼠柠檬酸杆菌肠道感染模型证实结肠巨噬细胞是感染后IL-10的主要来源,IL-10不仅能调节单核细胞、粒细胞向肠道募集,还能以自分泌或旁分泌的方式抑制巨噬细胞IL-23的产生,从而避免过度炎症反应对自身组织的损伤;且IL-10+巨噬细胞高表达与血管发育、组织再生相关的基因。有研究亦证实肠上皮隐窝周围的巨噬细胞通过产生前列腺素E2(PGE2)等方式促进干细胞增生[17]。上述研究均表明巨噬细胞有助于感染后期的组织修复和创伤愈合,促进肠黏膜稳态恢复。此外,Kim等[18]亦发现,在特异性去除小鼠肠道CX3CR1+巨噬细胞后无法正常诱导对卵清蛋白的口服耐受。
越来越多的研究显示肠道细菌与巨噬细胞之间存在多方面的作用。Ueda等[19]发现肠道细菌通过TLRs刺激结肠巨噬细胞产生IL-10,进而以旁分泌或自分泌的方式激活STAT3、抑制IκB激酶等产生抗炎效应。而肠道菌群的代谢产物丁酸通过抑制HDAC,亦能限制结肠固有层巨噬细胞中促炎细胞因子的产生[20]。Yang等[21]通过给予无菌小鼠进行粪菌移植发现肠道细菌能促进肠嗜铬细胞分泌5-羟色胺,进而促进肠道运动和巨噬细胞向M2型转变。Kim等[18]发现在应用抗菌药物清除大部分肠道菌群后,肠黏膜内CX3CR1+巨噬细胞不再能抑制沙门菌感染引起的过度Th1型反应,亦不能诱导移植的初始OTⅡ T细胞分化成Treg细胞,表明巨噬细胞发挥调节功能需要肠道菌群的存在;该研究还证实肠道细菌的作用依赖于其对肠上皮组织的黏附,但具体机制有待进一步研究。
总之,肠黏膜内的成熟巨噬细胞主要表现为一种抗炎表型,通过产生IL-10等抑制性细胞因子、促进Treg细胞产生等方式参与诱导对共生菌以及食物抗原的免疫耐受;在感染引发的炎症反应后期亦能产生PGE2等因子促进组织修复,有利于肠黏膜稳态的重建。而在一些肠道持续慢性炎症过程中(如炎症性肠病),巨噬细胞的正常分化受到影响而转变为促炎表型,导致局部炎症和组织损伤加重。因此,通过确定影响巨噬细胞功能的关键细胞内外因子,人为调控巨噬细胞分化,可能为炎症性肠病等的治疗提供新的手段。
四、DC
作为专职的抗原呈递细胞,DC在联系固有性免疫和适应性免疫应答中发挥重要作用。越来越多的研究显示肠道中存在一群具有免疫调节功能的DC,即调节性DC。目前各种体内、体外实验确定的调节性DC的作用机制包括:分泌IL-10、TGF-β、IL-27等免疫抑制性细胞因子;产生穿孔素、颗粒酶等物质清除效应T细胞;表达吲哚胺2,3-双加氧酶(indoleamine-2,3-dioxygenase, IDO),催化色氨酸产生犬尿氨酸,通过芳烃受体(aryl hydrocarbon receptor, AhR)促进Treg细胞分化同时抑制效应T细胞增殖;产生PDL-1、FasL、TRAIL等诱导效应T细胞的失能和(或)凋亡[22-24]。DC对肠黏膜稳态的作用可能主要在于维持Treg细胞与效应T细胞的平衡。CD103+DC通过抗原呈递并以TGF-β和视黄酸依赖的方式诱导CD4+T细胞向Treg细胞分化。Nakahashi-Oda等[25]发现分布于肠上皮细胞周围的CX3CR1+CD103+CD11b+DC识别细菌成分(如LPS)后产生的IFN-β亦能促进结肠Treg细胞增殖。近年通过各种条件性基因敲除实验发现Notch受体[26]、热休克蛋白gp96(TLR的分子伴侣)[27]、TLR下游信号分子TRAF6[28]等对调节性DC正常发挥作用具有重要作用,去除DC中的上述分子会导致其促进Treg细胞分化和增殖的能力降低,肠道Treg细胞与效应T细胞的平衡被破坏。
Fung等[29]发现,肠系膜淋巴结等部位的淋巴组织定居共生菌可定植于DC内部,促进DC产生IL-10,在稳定状态下限制对共生菌的Th17细胞反应,在肠道面临损伤时(如DSS诱导的结肠炎模型中)还能增强肠上皮的屏障功能,减轻肠道和全身炎症反应。Martínez-López等[30]证实PP中的DC通过C型凝集素受体(C-type lectin receptor, CLR)Mincle识别黏膜定居共生菌,经下游SyK激酶信号通路产生IL-6和IL-23,最终促进Th17和ILC3分泌IL-22,从而增强肠上皮屏障功能。
DC作为重要的抗原呈递细胞,通过呈递细菌抗原和提供各种细胞因子,促进效应T细胞和Treg细胞分化,维持两者的平衡,保证了在清除入侵细菌的同时不影响共生菌的正常定植,这是肠黏膜免疫系统维持自身稳定的重要手段。
五、ILC
目前ILC主要分为3类:ILC1受转录因子T-bet调控,主要产生IFN-γ等细胞因子;ILC2受转录因子GATA3调控,主要产生IL-4、IL-5、IL-13等细胞因子;ILC3受转录因子RORγt调控,产生IL-22、IL-17、粒-巨噬细胞集落刺激因子(GM-CSF)等细胞因子。其中,ILC3主要参与肠道免疫调节。ILC3可进一步分成2种亚型:CCR6+群体,即淋巴组织诱导细胞(LTi细胞);CCR6-群体,表达自然细胞毒性受体,如Nkp44、Nkp46等。CCR6-ILC3亦可表达T-bet并分泌IFN-γ,参与抵抗肠道病原体(如沙门菌)感染。
ILC3可通过多种方式介导免疫调节功能:在PP和肠系膜淋巴结等部位的ILC3表达MHCⅡ同时缺乏CD80/86等共刺激分子,通过抗原呈递清除特异性识别肠道共生菌的效应T细胞,发挥类似胸腺内阴性选择的作用[31];肠道内ILC3受IL-1β作用后分泌的GM-CSF能增强固有层CD103+调节性DC促进Treg细胞产生的能力[32];肠系膜淋巴结中定居滤泡间区域的ILC3可抑制TfH产生IL-4,进而限制B细胞反应[33]。
早期研究已证实ILC3对肠道独立淋巴滤泡形成和T细胞非依赖性IgA的产生至关重要,而清除ILC3会导致共生菌向体内播散和全身炎症的发生。Melo-Gonzalez等[33]的研究证实肠系膜淋巴结中滤泡间ILC3能限制特异性识别“边界定居细菌”的T细胞依赖性IgA产生;Goto等[34]发现ILC3分泌的淋巴毒素α能促进小肠上皮细胞表面的多糖发生岩藻糖基化,这些作用有利于共生菌在肠黏膜表面的正常定植。因此,ILC3能非常精确地调控肠道细菌的定植和生长。此外,在生理状态下,肠黏膜IL-22具有促进肠上皮细胞再生、抗菌肽产生、杯状细胞黏液分泌等多种效应,而ILC3是IL-22的重要来源之一。TLR2信号刺激能促进LTi ILC3分泌IL-22。最近Chun等[35]的研究发现结肠中细菌代谢产生的短链脂肪酸可激活GPR43,进而通过AKT/STAT3通路促进CCR6+ILC3的增殖以及IL-22产生。有研究[36]表明在肠道独立淋巴滤泡等部位神经胶质细胞分泌的神经营养因子能以旁分泌的方式促进ILC3表达IL-22,从而增强肠屏障功能,提示免疫系统与神经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对维持肠黏膜稳态亦非常重要。
总之,ILC3在诱导黏膜相关淋巴组织形成、维持肠上皮屏障完整性、维持对共生菌的免疫耐受等过程中均发挥重要作用。ILC3的免疫调节功能很大程度上依赖于MHCⅡ的表达以及细菌抗原的呈递(如对效应T细胞的调节[31],对TfH的调节[33]),然而ILC3获取共生菌抗原的途径目前尚不清楚,需行更多的研究来阐明。
六、基质细胞
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淋巴结内的基质细胞也具有免疫调节功能,如FRC。FRC是淋巴组织中一种特化的肌成纤维细胞,亦可见于肠系膜淋巴结和小肠PP中。FRC介导免疫耐受的机制包括:以MHC依赖的方式清除T细胞;产生一氧化氮等抑制效应T细胞增殖;产生视黄酸促进pTreg细胞分化等[37]。有研究[38]发现在给小鼠提供缺乏维生素A的饮食时,肠系膜淋巴结中FRC的视黄醛脱氢酶活性明显下降,而肠道固有层中FRC仍能正常表达视黄醛脱氢酶,说明不同的微环境中FRC可表现出不同的特性。此外,Gil-Cruz等[39]发现肠系膜淋巴结和PP中的FRC在稳定状态下产生IL-15,以维持ILC1和自然杀伤细胞(NK细胞)生存;而感染病毒时,FRC通过TLR7识别病毒RNA后下调IL-15表达,限制ILC1和NK细胞参与免疫反应,表明淋巴结中FRC能帮助机体避免在急性感染等炎症反应过程中出现对自身组织的损伤。目前发现肠道微生物对FRC等基质细胞具有一定的影响。Vicente-Suarez等[38]发现无菌小鼠肠道固有层中FRC不能正常产生视黄酸;Pezoldt等[40]证实在肠道微生物的参与下,初生小鼠肠系膜淋巴结中的FRC即获得了促进Treg细胞产生的能力,这种特性即使在感染和炎症状态下亦能稳定维持,因而有助于控制炎症发展,促进肠道稳态恢复。
七、结论与展望
综上所述,免疫调节细胞作为肠道免疫系统重要的组成部分,其与肠道菌群之间的协调作用对维持肠黏膜稳态非常关键,但作用机制目前尚不完全明确。未来仍需要利用更多新的疾病模型与研究技术进一步探讨免疫调节细胞在肠道稳态中发挥的作用,以及可能存在的表观遗传学和基因表达谱变化,从而为各种肠道黏膜炎症相关疾病的治疗提供新的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