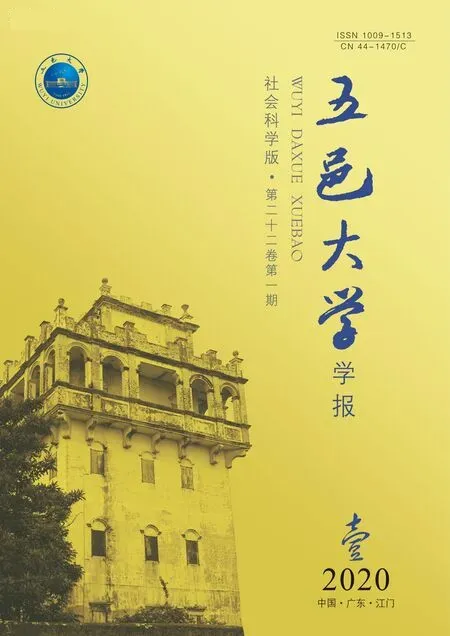《王荆公传》:梁启超新史学活态实践的一个突出文本
贺根民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 文学与传媒学院,广东 广州 510665)
激于晚清以来的千年未有之变局,现代学人在铸造中国学术话语的征程上博收广取,他们或援西学以资立论,或赓续中国传统文化根脉,寻绎展示民族性和世界性双重色彩的现代学术路径。晚清民初的大发现时代特质激荡出新知识和新学理所向披靡的文化锋芒,为近世学术营造了一个相对自由的学术环境。时局刷新了我们对传统文化的认知谱系,日益扩大的研究空间促使中国人文学术逐渐转型,从而铸造了丰富多元的中国话语大厦。梁启超作为世纪之交中国学术现代转型的关键人物,以其流质善变的文化特质张扬了过渡时期的时代向标。他以“梁启超式”的输入法来旁皇求索,建构中国现代新史学,其《王荆公传》以独特的时代论断和角色自喻色彩标举了新史学的活态样本。
一、加入论断:理想评传的文化承载
赵宋一代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一座文化昆仓,追求正心诚意的心性修养打造了宋代士人的内在超越精神,内敛理性、注重内省的时代特质致使士人收获感指数爆棚。超越时空隧道、千年而下的现代文人用心去体悟宋代文化内核,延续千年一贯的诗性文化根脉,在追步与效仿中沉淀了浓郁的崇宋文化情结。“笔锋常带情感”的梁启超引领晚清民初的思想解放潮流,他立足时局来推重科学精神,鼓吹“三界革命”并躬身实践,以富有前瞻性的论断来推动晚近学术话语更新。梁启超一生服膺宋代文化,玩赏宋代诗词、折服王安石,可谓其崇宋心理的一个基础。据其晚年的门生杨鸿烈回忆:“梁氏在病势沉重中,仍与‘死神’斗争,集中精力在搜集批判‘宋词’的发展的史料,并写成《跋(宋)程正伯书舟词》《吴梦窗年齿与姜石帚》《记兰畹集》《记时贤本事曲子集》等论文。临死前的数月,还拼着最后一口气,要撰述一部《辛稼轩年谱》。他虽然卧病在医院里面,仍托人去搜觅关于辛稼轩的资料。”[1]236-237梁氏钟爱放翁诗、稼轩词,以致将人生的最后时光交付给颇具刚强之貌的宋代文人文本,侧面传递了他蒂固根深的宋代文化情结。
自鸦片战争起,我国被动地步入万国时代,在西方坚船利炮叩开我国封闭的国门之际,我国的传统史学还在二十四史的框架内打转,仍沿袭以帝王将相为中心的王朝叙述模式。西方实证主义渐入国土,开启了现代史学研究的科学化路径,注重史学的济世救国效能,跨学科研究改变了传统史学的研究轨迹。梁启超以进化论来重新解读历史事件,其《王荆公传》诸作认可格林威尔“paint me as I am”理念, 凸显进化论对新史学的指导作用。西方新知识和新学理如潮水般涌进中国,四部之学逐渐替换为文史哲三分天下的局面,中国史学的研究空间逐渐扩大,各类研究史料日益增多,促使传统史学改弦更张。梁启超重估历史来镜鉴社会现实,以评传新例来探索适应时代所需的新史学范式。异域“他者”烛照,助推传统史学现代转型。在梁启超看来,史学并非循环往复、支床叠屋的存在,而是藉以人群进化来求得公理、公例的文化实践。1902年其《新史学》一文数落传统史学有四蔽二病,即有“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四蔽,[2]156-157传统史学“能铺叙而不能别裁”“能因袭而不能创作”等二病足以强化我国史料汗牛充栋的存在表象,但其述而不作之习,仍缺乏激励国民之效,这一史界革命的纲领性文献开启了梁氏援引西学论断来重新打量中国传统史学的新路径。
纪传体由司马迁发凡起例,它常以一人事迹行事来统辖全篇,不下论断而彰显信史风格,但此类少有史识的体例陈陈相因,束缚了撰史者的才情抒发。新史学是关乎世运的人物群史,更是史识哲理的形象呈现。1901年梁氏的《南海康先生传》与《李鸿章传》洞开了一片人物评传书写的新天地。梁氏的新式评传突破了《史记》以来的纪传体藩篱,其《李鸿章传·序例》中的夫子自道最能说明问题:“此书全仿西人传记之体,载李鸿章一生行事,而加以论断,使后之读者,知其为人。”[3]梁氏对这类赏奇析疑的新式评传爱不释手,以致新作迭出,1902年发表了《张博望班定远合传》《赵武灵王传》《意大利建国三杰传》《罗兰夫人传》,1903年又推出《新英国巨人克伦威尔传》,1904年则撰有《袁崇焕传》《中国殖民八大伟人传》。这些传记多刊发于《新民从报》的“传记”栏目版块。1908年的《王荆公传》与1909年的《管子传》就是梁氏的满意之作。这些新式评传选材宏伟、贯通古今、博涉中外,形成一个相对自足的首尾圆合结构。
梁启超认为服务对象逼窄是传统史学的最大缺陷,长篇累牍的帝王将相叙述遮蔽了大众平民的存在,故应变“皇帝教科书”为“国民资治通鉴”。新式评传沿袭了纪传体史书注重钩沉传主生平的本位,又适时对照现实添加某些议论,展露作者的史识和社会使命感。在梁启超的史学视野里,年谱等一类史作搜罗谱主生平行事,巨细无遗,却略显呆板。他推许的理想专传是“以一个伟大人物对于时代有特殊关系者为中心,将周围关系事实归纳其中;横的竖的,网罗无遗。”[2]230人物专传有别于年谱体例,它不必依循年代先后叙述,或议论,或叙事,改换相对自由,内容涵盖更为广泛。专传类的人物评传易于熔铸新见,它受到“不惜以今日之我攻昨日之我”的梁启超垂青自在情理之中。梁氏的新式评传立足于广阔的文化生态来勾勒传主形象,有利于从世运国是的高度来把捉人物特质,凸显“再发现”的新史学意识。
迥异于纪传体史作绘声绘态、复原现场的全知视角,新史学更乐意精选那些与时代或社会风云攸关的人物,采用限知视角为之作传,勾勒其社会周边,来显露现代学人的参与意识。发思古之幽情,落脚却在当下,这已成为梁启超物色传主的主要标准。在中西汇流节点上来改弦更张,包孕着梁氏孜孜创建史学书写范式的学术雄心。不阿其所好,客观求实素为史学的不二追求。盘点中华数千年的社会演变,梁启超断论我国古代成功的政治家多处于封建割据的乱世之秋。梁启超认为王安石是大一统时代与国外大政治家媲美的第一人:“吾读国史,而得成功之政治家数人焉:曰管仲,曰子产,曰商君,曰诸葛武侯。夷考其所处者,则皆封建时代或割据时代也。……其有一焉,则荆公也,而所成就,固瞠乎后矣。”[4] 128-129衡以王安石所处的时代,适时参照国外政治家的作为,“赋予了解之同情”,贴近传主时地来论断,原本就是尊重史实的绝佳表现。以关乎一个时代乃至中华文明的整体脉络来选择传主,这已跳出英雄创造历史的狭隘偏见,彰显了一个可以腾挪古今中外的考察界面。在梁氏那里,人物活性成为凸显传主跃然生动的艺术生命的选择标准,客观上赋予了传主超越时空的当下意义。
梁启超博涉众学,他曾经在南开大学、清华大学开设过“历史研究”一课,其讲课内容分别结集为1920年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与1927年《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姚名达曾问学于梁启超,为导人金针、指点迷津,梁氏慨然以治史自许,并向弟子推荐以此作为治学的首选门径。1901年的《中国史叙论》《史学之界说》 与1902年的 《新史学》绘制了新史学图景。有异于记述一人一家的谱牒积习,新史学更在意于所记事实的彼此关联、对原因与结果的梳理、厘清与钩沉国运社会关系。他认为中国史学之弊患在于汗漫而无一以统系的纲领,是只见君主而不及国民的历史叙事。就此而论,探究社会事件的因果,动态勾勒其演变之迹,何尝不是新史学的突出标识。对此,《王荆公传·自序》是一有力的注脚,其云:“自余初知学,即服膺王荆公,欲为作传也有年,牵于他业,未克就,顷修国史至宋代,欲考熙丰新法之真相,穷极其原因结果,鉴其利害得失,以为知来视往之资。”[4]76砸破入主出奴的观念积习,明因果知得失、参伍验证的评述路径,意在凸显史实之外的识见和裁断,这就有意拉开了与传统史学的距离。
二、废书而恸:辨诬翻案的著史初衷
历史是过往的存在,立足现代去触摸历史的门墙,那么任何一个朝代都能赋予我们思想选择的张力。我们不可能赤手空拳回到历史现场。秉持一副人文情怀去营造现代学科场景,从而做出富有识见的现代阐释,自是梁启超关注历史人物的初衷。“无组织,无选择,本末不具,派别不明”[5]97地输入西方新思想,梁启超构筑不中不西、即中即西的新学派,在短时间内大有振臂一呼、应者云集之效。在梁启超看来,历史上某些本应光耀史乘的人物,却因为经年的入主出奴之见,非常之人常泯灭于谬悠之口,因此对史著作一番洗冤清尘工夫很有必要。“若古代之管子、商君,若中世之荆公,吾益遍征两史,欲求其匹俦而不可得。而商君、荆公为世诟病,以迄今日。”[4]1撷取历史上为后世所丑诋的人物进行重新体认,如旧史上被视为“器小”的管仲、“以凿空见病”的张骞、有“奸邪”之名的王安石、被看作“奄竖”的郑和,复原历史文化生态,拨云见日,拂清蒙在旧史著述上的污垢,这已成为梁启超传播真知、盘活人物气神的重要途径。梁启超对管子、王安石、袁崇焕等一班人物的考辨,折射其推戴他们为历史前行原动力的考量。
钩沉任何一位历史人物,文献始终是评价其历史功过及定位的重要依据。还历史以本来面目,梁启超致力为王安石作“洗冤录”,他首先从廓清蒙在王安石认知谱系上的迷雾上赢得突破。梁启超细究《王临川全集》,再以宋人笔记和《宋史》诸志、诸传佐证,断论成于南渡之后的史官之言不足为信。盘点王安石的形象接受史,虽有清人蔡上翔《王荆公年谱》不懈为之辨诬。但此书流传狭窄,其力尚不能扫清观念误区。宋代的新旧党争致使变法自新的王安石被严重歪曲,后世史家不去考证,遂以讹传讹,人物形象得不到正面体认。职是之故,对人物行事作烛幽发微的梳理,便获得重新认知的新义:“又如研究王荆公的新法,追求他本来用意究竟何在。从前大家都把他看错了,都认为一个聚敛之臣。到底荆公采用新法,完全以聚敛为目的吗?其实荆公种种举动,都有深意。”[2]197将历史人物放在历史与现实的延长线上考虑,整体统摄王安石的家庭、社会关系、武功和学术的方方面面, 才不会有一叶障目之嫌。
梁氏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第五章“年谱及其做法”的论述中,在涉及“旧有的记载故意污蔑或观察错误的”一条之时,径以《宋史·王安石传》为例,指陈元初史家著述失实,明显带有故入人罪的意味。正因如此,追根溯源、考订文献的源头真伪是复原历史的关键步骤。毋庸置疑,文献既是影响王安石被误读的文化源头,又是后人传讹的话语资源。欲破除王安石接受史上的魔咒,还得从文献真伪甄别上着手。《王荆公传》逐条钩沉,从荆公之时代、荆公之略传、执政前之荆公等维度,并就传主、时代、环境等侧面作立体考察。对于后人诟病颇多的变法条目,尤其是那些政术法令,梁启超不厌其详,用四章的篇幅来仔细钩沉辩解,更是将其置于中外文化交流维度上评定:“公之此举,取尧舜禹三代以来之弊政而一扫之,实国史上、世界史上最有名誉之社会革命也。……两两相印证,则夫对于荆公,宜如何尸视而膜拜者。”[4]147不阿其所好,又设身处地,展示史家理性平视的考察力度。
1908年梁启超在撰写《王荆公传》之际,戊戌变法失败的余痛还在,他一度避祸国外,多年的流亡生涯,促使其自觉地援引西学视野来建构现代新史学。为王安石这类遭遇不公的历史人物来翻案辩诬,就成了其投身新史学研究的表征。王安石虽屡遭贬抑误读,但流俗不会遮蔽荆公的人格光辉,梁启超奋笔疾书,无不是特意展示伟人模范,以示后学之轨则。在恢复王安石人格魅力的过程中,梁启超反复断论《宋史》不足信。迨由宋代元祐党人及其子孙门人发轫,致使一时蜚语铸成铁案,这才是梁氏洞中症结、废书而恸的原初心态。至于如何辩诬,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方法或许直指问题的要害。梁启超援引陆九渊《荆国五文公祠堂记》、颜习斋《宋史评》、蔡上翔《王荆公年谱略》等文字,发潜德之幽光,再现王安石作为近世大政治家、大文学家的本色。欲辨《宋史》,当辨其所据之资料。在梁氏的视野里,陆、颜两先生,洵为一代大儒,其论断足可信之;而蔡上翔博览群书,集数十年之功,撰写该年谱,持论公允。相较而论,成于元人之手的《宋史》,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指陈,该著舛谬甚多。后世史家之所以丑诋王安石,大多基于其变法影响来判断,并非全因一己之私利。梁启超不厌其烦,逐一梳理那些误解王安石的论调,就时地维度展示王安石变法之艰难,以中西政治的对比来彰显王安石被诬的荒谬与可笑。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综括应作专传或补作列传的人物有七种,“从前史家有时因为偏见,或者因为挟嫌,对于一个人的记载,完全不是事实。我们对于此种被诬的人,应该用辩护的性质,替他重新做传”[2]235即位列其中,直接从史学理论高度来体认重新作传的价值,也道出其为王安石翻案的初衷。明代以前的史官几视王安石为蔡京、童贯之流,虽未将其拉入奸臣传之列,却李代桃僵将金国灭北宋的罪名移至王安石头上。编《宋史》之人未加甄别,才会沿袭前人误读之见。《宋史》本传选择性失聪,漠视王安石变法之利,而专门罗织罪名,进行片面的认定,违背史官唯实求真的文化立场。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梁氏阐述年谱体例,就力推客观求真的立场:“譬如王安石变法,同时许多人都攻击他的新法要不得,我们不必问谁是谁非,……并把王安石用意的诚挚和用人的茫昧 一一翔实的叙述,读者自然能明白王安石和新法的好坏。”[2]266盘点王安石被误解的历史,熙宁变法是一大关节点。宋代党祸由来已久,并非自王安石开端,但他立身处世及气量文章又确实非同常人。后来史家径以党争、八股来归罪王安石,衡以当下时地,诚为无稽之论。
三、角色自喻:借古喻今的形象指代
新史学注重中西比较,梁氏以其来呼应其所倡导的新民学,展示他紧跟启蒙与救亡时代潮流的考量。作为人物传记的典范之作,梁启超的《李鸿章传》《王荆公传》均先就《序列》或《例言》来阐发体例,进而在《绪(叙)论》上亮出评价人物的标准。开宗明义托出撰史的创作动机,铺设了构撰整个传记文本的逻辑起点。其评价人物的新尺度至少在1901年的《南海康先生传》已经成型,梁启超论定李鸿章是时势所造之英雄,将自己所钟爱的王安石、袁崇焕推为造时势之英雄的代表。在梁启超看来,历史人物可细分为社会原动力的先时人物与时势所造的应时人物,相较而论,前者无待,后者有待,二者高下之别判然自明。先时人物就是导引社会发展的真人物,先时人物专注于历史前行的方向,大多为继往开来的过渡人物。为时势所造之英雄,车载斗量;而造时势之英雄,则千载难逢。让历史人物现身说法,激发国人变法图强的政治豪情,大体允符了梁启超从维新立宪向文化启蒙的思想嬗变轨迹,展示了鲜明的政治用意。梁启超认为先时人物是理想、热诚、胆气三者的合体,梁氏抬举其师康有为纵横一世的先时人物,又何尝不是惺惺相惜的角色自喻。
在中国学术的现代化进程中,梁启超与章太炎、王国维、胡适一道,承担了现代学科开宗立派的历史使命。“全仿西人传记之体”的现代人物评传注重传主遴选,梁启超属意挑选跟国家和民族命运息息相关的传主,这已跳出昔日忠奸、善恶的二元对立标准。据亲炙其学的梁容若回忆:“任公先生崇拜王荆公,他的立身处世,学问文章也接近临川。越离他远,越感到他的声光魔力,震聋发聩,推倒一世豪杰,开拓万古心胸。”[1]289禀持一瓣心香,在德、学、识、才的史家四长之外,更以传主的一生行事来自我推许,撰者心迹与传主意念暗度陈仓。如此将自己胸中块垒牢骚,倾注于所书之传主,又何尝不是藉以钩沉人物行事来抒发某种文化认同。梁启超服膺王安石有年,意在复原历史人物真相,又何尝不是张扬新史学意识下的文化身份。设身处地凸显王安石等历史人物对社会发展的巨大影响,传达了梁启超呼唤重振乾坤的英雄出现的诉求,对此,《王荆公传·自序》的自陈足可参考:“而流俗之诋諆荆公、污蔑荆公者,……非欲为过去历史翻一场公案,凡以示伟人之模范,庶几百世之下有闻而兴起者乎。”[4]76梁氏自觉以欧美的社会政治人物来参伍对比,重新评估我国历史人物的历史地位,廓清其文化认同迷雾,彰显千载而下的榜样效应。若此,突破夷夏之辨的传统积习,将中国置于世界文化的版图中,将历史人物置于社会发展长河中来把捉,展示了其宽广的学术视域。
揆诸晚近以来的社会现实,梁启超这种惺惺相惜心理在《清代学术概论》中亦有形而上的反映,他自许为开辟新时代的思想界的陈涉:“以其人本身之魄力,及其三十年历史上所积之资格,实应为我新思想界力图缔造一开国规模。”[5]89梁启超慨然以输进新思想来自命,新学理和新思想赋予他重新解读历史的底气和勇气,突破千年制约王安石接受的文化怪圈,其文化实践冲击了学术界的既有秩序,其对王安石等人物的搜罗与辨说开创了学术新格局。戴着有色眼镜进入历史现场,或许会影响历史纪事的客观信实色彩,但这种情感与心理的相通,足以发抒自我独到识见,彰显其著史立说的当下效应。“至《王荆公传》、《意大利建国三杰传》,作者人格与书中人物融而为一,读之最足激发人之志气。《荆公传》尤有功于史学。”[1]101孜孜不倦树立史学新观念,为晚清民初史学界注入一股清流,富有时代新见的人物钩稽开现代新史学诸多法门。
大力提拔文官是宋代的治国传统。梁启超考证宋代崛兴的时代文化,探索赵宋积弱的文化基因,或许是替腐败无能的晚清下一剂催人猛醒的方药。从心理学角度剖析历史事件,展示了新史学的科际整合色彩。梁启超式的新式人物传记有意添加诸多议论文字,在断论和裁判之中不乏有寻求心理契合的考量,客观拉近了读者与传主的心理距离。在梁启超的笔下,历史人物并非滞留于故纸堆里的忠奸等符号指代,而是元气淋漓存活于当下的角色形象。梁氏对王安石的评价,并非一味地复原到宋代文化生态,也不只是简单地还原给传主本人,而是立足于世纪之交的社会和学术现状,援引现代新史学视野加以断论。梁启超藉以爬梳王安石形象来抒发自我襟怀,他特意拈出“执政前之荆公”与“罢政后之荆公”来述论,不无对自我参与变法维新之举的首肯,也难掩一份维新失败之后的失落心绪。他细数“荆公之武功”“新政之成绩”,隐约表达了期待再次被委以重任、再创辉煌的政治抱负。梁启超别具情怀,以强烈的现实植入意识来质疑与批判正史传统痼疾,侧面传递了其矢志思想启蒙和有所作为的角色自喻。
四、结 语
从支离破碎的史实瓦砾中寻觅金屑,20世纪之初的中国学人竞相提倡民史与群史来展示尊西趋新取向。新史学撰写的终极关怀情怀强化现代学人的国家认同意识,不断否定旧日之我的梁启超身体力行,突破传统史学纪传体的藩篱,矢志解构旧史学沦为帝王将相家谱的存在现实,他将王安石的生平事迹融进国运与社会发展的考察之中,旨在唤醒现代民族国家意识,彰显了史学为现实政治服务的功利考量。现代人物评传采纳西方史书的章节体叙述方式,对传主作细致入微的考察,注重传论结合,其史学风格一改《史记》重叙事轻评论的理路,对照社会境遇加以论断,凸显史学关乎国运世情、书写民众的文化本位。《王荆公传》从王安石的生平、家庭、时代到其政术、学术、文学、新政成绩、用人及交友等方面,纵横交织,绘制一个立体而全面的王安石形象。梁启超放眼世界,贴近现代文化生态来重新评价王安石的历史功过,梳理其政术与新政成绩,甄别原始文献,不懈为之辨诬翻案,重估其历史地位,建构了深具性情的人物传记书写模式,为我国史传加速向现代嬗变并早日与国际接轨开辟新路。革新旧思想,提倡史学革命,在气象万千的过渡时代境遇下,梁启超助推了中国史学的现代转换,打造了晚近学术转型中引领风骚的文化坐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