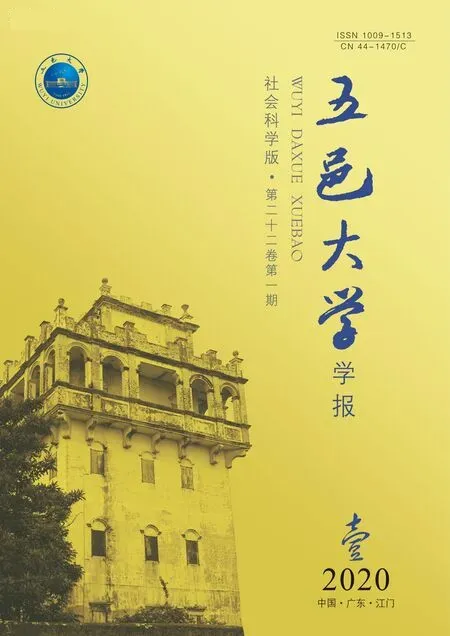试论白沙心学的哲学概念
——以“心”“自得”“自然”为例
高 卓
(南京大学 哲学系,江苏 南京 210046)
元明之际的儒学实际可以看作北宋兴起的理学的延续。理学在元代成为官方学问,明永乐年间编纂的《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亦显示对朱子学之推崇。伴随着官方权威的树立,学者治学更倾向于固守程朱传统。元末明初的朱子学虽占据统治地位,却愈发显出局促和狭窄的趋势。与此同时,“折衷朱陆”的学风开始兴起,一些学者在宗守朱子的前提下,顺应“朱陆兼宗合会”的潮流,对于陆九渊“发明本心”“尊德性”的学术观点多有发挥,理学的限制逐渐被打破。在此背景下,白沙之学应运而生,且与前人学术呈现完全不同的面貌。其批评当时恪守教条的学风,并提出“自得之学”“以自然为宗”“静中养出端倪”等,认为学术研究和道德修养都应向内心探求而非拘泥于书本,这在当时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
当代学界对白沙之学的研究非常丰富,但研究重点多为其近禅说、心学体系,并不涉及具体概念;论据多因袭前人,少有创新之处;且将其与陆九渊、王阳明的学说笼统视为一脉,忽视了白沙之学在明初表现出的特殊性。鉴于此,笔者尝试从“心”、“自得”、“道”与“自然”的角度分析白沙之学的具体哲学概念,展示其相较程朱之学的变化和独特之处,管窥明代以降哲学观念的发展过程。
一、 白沙之学的“心”
(一)白沙心学之“诚”
在古代中国哲学中,“诚”一直是与“心”紧密关联的概念。如《中庸》所言:“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1],经汉宋儒者的改造,“诚”已经作为天人关系的构成部分加以讨论。白沙之学亦不例外。他在来往书信中多次提及“诚”,并认为其事关学习指南:“其始在于立诚,其功在于明善,至虚以求静之一,致实以防动之流,此学之指南也。”[2]25亦主张为人处世应将“诚”放在第一位:“才与诚合,然后事可诚也。”[2]128由此可见“诚”实际上是作为基础性的道德要求而存在的。白沙曾详细论及“诚”的地位:
夫天地之大,万物之富,何以为之也?一诚所为也。盖有此诚,斯有此物,则有此物,必有此诚。则诚在人何所,具于一心耳。心之所有者此诚,为天地者此诚也。[2]57
诚不仅是人的基本道德要求,而且是万事万物构成的基本法则,其地位极似作为“物之所以然”的“理”。“诚”虽然并非具体的构成材料,但事物存在却必须具有“诚”,即使天地亦不能例外。白沙认为“诚”具于心,且“心之所有者此诚”,表明心中只有“诚”,这在某种程度上提高了“心”的地位。“诚”是构成事物的枢纽,作为其容纳场所的“心”亦成为枢纽(尤其在人身上),且“诚”只能通过“心”才能发挥作用。白沙还提到:“心者,其此一元之所舍乎。”[2]57“舍”即容纳场所之意,此中的“一元”即是“诚”,可见“心”在白沙哲学体系中地位确实不同以往。
值得注意的是,白沙对“理”这一概念提及并不多。究其原因,一方面因为白沙“恶宋儒太严”[2]131,并不盲从程朱学派的治学理路;另一方面,白沙提出的“心”这一概念将“理”包涉于人的内部,论“心”即论“理”。但早期的白沙无疑是极宗朱子的,其在诗文中曾写道:“吾道有宗主,千秋朱紫阳。”[2]279对于“理”的论述,也基本承袭朱子路数:
此理干涉至大,无内外,无终始,无一处不到,无一息不运。会此则天地我立,万化我出,而宇宙在我矣。得此霸柄入手,更有何事?往古来今,四方上下,都一齐穿纽,一齐收拾,随时随处,无不是整个充塞......此理包罗上下,贯彻终始,滚做一片,都无分别,无尽藏故也。自兹以往,更有分殊处,合要理会。毫分缕析,义理无穷尽,工夫无穷尽,书中所云,乃其统体该括耳。[2]217
文中提到的“分殊”“毫分缕析”都是对程朱学派理论的转述。“理”具有超越时空、贯通古今、映射万物的属性,而且一旦把握“理”,则可以达到“宇宙在我”的天人合一境界,是生存于人世间的第一等事。而这种特性和境界在后期便被赋予给了“心”,白沙提出“心具万理”:“君子一心,万理具备。事物虽多,莫非在我。”[2]55由此“心”便成为白沙哲学的重点,其内在涵义和道德地位都远高于前代。这一理论导致了两个结果:其一,万理具备,则为学重点不再是于外部事物中寻求“定理”,白沙的治学方法在修正程朱的基础上转向内部虚静、自得,并提出“为学需从静中养出端倪来,方有商量处”[2]133;其二,赋予人极高的自主性。作为道德根源的形上之“理”落实到人心中,成为人德性修养和道德践履的依据,并极大提高人的德行自觉。“心”对“理”的包涉,标志着白沙之学向内部的转变。
关于为何会在白沙的时代出现以“心”包“理”,沟口雄三曾尝试解释:“宇宙万物的法则性的存在这一朱子思想的核心,已经是个不言自明的前提。因此朱子学为证明其法则性存在而花费诸多手段的方法论(穷理、居敬)是浪费时间。它所面临的客体不是证明已经明了的理的存在,而是让人人能自觉其理、实得其理,向更广泛的层面渗透。”[3]因为明初朱子学的主要理论已经成为共识,宇宙论、法则论已近完备,故为学关键开始转向于如何使人真正成为“道德主体”,将道德性赋予人本身而非依靠外在的理,白沙心学便是在这一基础上开始对朱子学的修正。
(二)心的基本内涵
在朱子哲学体系中,心的主要内涵为“知觉”“身之主宰”“心体”[4]。白沙对“心”在“知觉”和“身之主宰”这两层面的内涵少有论述,却尤其推重“心”在本体层面的功能和地位。因此在他的描述中,“心”往往表现为一种超然的本体境界:
到得物我两忘,浑然天地气象,方始是成就处。[2]135
中庸曰:“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说者谓吾心之正,天地之心亦正,吾心之顺,天地之气亦顺。[2]36
一旦充分发掘内在的德性,人之心与天地之心便浑然一体,人成为天地万物之主宰。其基调在于强调涵养“心”所能达到的安身立命的天人境界,是对人主体性和内在德性的确认。并非如某些学者认为的对“自由”的过度发挥或主观唯心主义,如黄明同就曾对此作出论述:“人的主体精神,是应当予以充分肯定,但当人‘得道’之后,是否就可以与天地同体,与万物齐一,一切都可以为所欲为?事实上并不可能。”[5]117白沙论述的重点显然不在得道之后的神通,而是激起后学对“心”“道”的体悟和向往。白沙亦曾对此做过辩解:“然非知之真,存之实者,与此语则反惑,惑则徒为狂妄耳。”[2]55想要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需要笃实的涵养和践履,如果没有达到知真、存实的程度,所谓“心”的内在境界不过是蛊惑和狂妄而已。可见白沙之“心”并非超验实体,其作为德性本体和超然的精神境界,是建立在扎实的工夫论基础上的,标志着明初学术对人主体性的宣扬和内在转向。
(三)心的基本作用
白沙认为涵养“心”不仅可以保持德性,亦能实现功业:“君子一心足以开万世,小人一心足以丧邦家。”[2]57而且他认为“心”具有“巧”的功能:
是则至拙者莫如意,而至巧者莫踰心。[2]57
君子因是心,制是礼,则二者两全矣,巧莫过焉……圣人未尝巧也,心之仁自巧也,而圣人用之。[2]58
所谓“巧”,即是巧妙之意。“心”在世间发挥作用,无不灵妙莫测,非人意所能揣度、模拟。而且“巧”为心的自然发用,圣人不过借而用之。但亦有学者针对此提出反驳:“陈献章没有真正认识人的认识过程中的主客体关系……其君子之心被神秘化、道德化后赋予无穷的威力”[5]116。
值得一提的是,白沙还将“心”与病痛相联系。他认为心可以驭气,以保证身体健康,一旦心乱,则会导致疾病:“心寓形而为主,主失其主,反乱于气,亦疾病之所由起也……心之害大而急者,莫如忿争。”[2]237白沙晚年饱受病痛折磨,其书信中多有提及,盖此种“养心”之法由此而发。
二、白沙之学的“自得”
由于“心具万理”理论的确立,白沙之学由传统的外部穷理转向内部的体悟:“所谓未得,谓吾此心此理未有凑泊忽合处也。于是舍彼之繁,求吾之约,惟在静坐,久之,然后见吾此心之体隐然呈露,常若有物。”[2]145通过静坐的工夫感受心体与理的结合,白沙提出“自得之学”,即“具足于内者,无所待乎外”[2]48。具体而言,其强调内在心体之修养,而“自得之学”的展开便是虚静为主的涵养工夫。但“自得”不仅仅是修养方法,其还表现为鸢飞鱼跃的精神境界:
自得者不累于外物,不累于耳目,不累于造次颠沛,鸢飞鱼跃,其机在我。[2]89
故得之者,天地与顺,日月与明,鬼神与福,万民与诚,百世与名,而无一物奸于其间……人争一个觉,才觉便我大而物小,物有尽而我无尽。[2]242
真正实现“自得”的人,可以不为庸俗琐屑之事困扰,遨游于活泼的自然境界。无论是“鸢飞鱼跃”的境界,还是具体的工夫论,都显示出“心”开始作为某种区别于外部“定理”的独立判断标准而发挥作用,由此必然导致两种倾向:贵疑的精神、由道问学转向尊德性。
(一)贵疑的精神
前文提到,心之地位的提高引发了白沙对传统理学的修正,其明确提到过:“宋儒之言备矣,吾尝恶其太严也。”[2]131因此白沙虽然标榜自己宗孔孟周程,但却拒绝自己的学说完全是对前人的亦步亦趋,他认为即使没有圣贤可以依傍也应该无滞于物、笃实践履:“虽使古无圣贤之依归,我亦住不得,如此方是自得之学”[2]133。
在此基础上,白沙批评了当时的学界风气:
夫子之学,非后人所谓学,载籍多而功不专,二目乱而名不知,宜君子之忧之也……六经,夫子之书也;学者徒诵其言而忘味,六经一糟粕耳,犹未免于玩物丧志。[2]20
时人学习典籍却不能把握内在精神,仅仅空洞地背诵圣贤之言而不能理解道德意蕴,即使如六经也似糟粕一般,学习反而成了玩物丧志。当时的学者盲目跟从宋儒的为学方法,使得德性修养不是偏入一隅便是徒具形式,人的道德主体性和自主性都被忽视了。白沙认为治学方法未必只有一个模式,“同其心不同其迹可也,同其归不同其入可也”[2]65,只要把握住了“心”这个“霸柄”,即使采用不同的为学路径也可实现天人合一的最终境界,白沙在当时极力宣扬静坐、致虚立本的新颖路径便是明证。进一步地,白沙提出为学必须要存疑:“学贵知疑,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疑,觉悟之机也。”[2]167白沙认为存疑是不断进步的关键,甚至可以根据自身判断删改古书:“圣贤之言具在方册,生取而读之,师其可者,改其不可者,直截勇往,日进不已,古人不难到也。”[2]19这种质疑古籍的大胆想法在明初那种恪守程朱的年代无疑起到振聋发聩的效果,颇似陆象山“六经注我”之言论[6],其中的细微差别即在于白沙尚未将矛头指向经书,而是泛指前人之著述。
(二)由道问学转向尊德性
白沙将“心”作为为学修养的关键,不再迷信于历代典籍,其在《答张内翰廷祥书》中提到:“吾能握其机,何必窥陈编”[2]279,在《和杨龟山此日不再得韵》中亦有类似表述:“道德乃膏腴,文辞固秕糠”[2]279,带有浓厚的道德本位色彩。由此白沙对世间的知识做了两种区分:“然后尝一思之,夫学有由积累而至者,有不由积累而至者,有可以言传者,有不可以言传者。”[2]131可由积累而学的可以通过典籍进修,不可言传的“理”则需要对心体的感悟来获得,且在其理论框架中后者的地位明显高于前者。在《书韩庄二节妇事》一文中,白沙在赞扬两位妇女守节的同时,甚至认为这种品德“是岂资学问之功哉?是岂常闻君子之道于人哉?亦发于其性之自然耳”[2]77。即白沙更强调从内在之德性修习君子之道,若体悟心体即可实现,又何必求于外物?
但白沙亦肯定书本的积极作用:一者其可以提供细枝末节的知识,二者其可以作为涵养心体的辅助手段。白沙提到:
圣贤垂世立教之所寓者,书也;用而不用者,心也。心不可用,书亦不可废,其为之有道乎,得其道则交助,失其道则交病,愿吾子之终思之也。[2]48
学者苟不但求之书而求之吾心,察于动静有无之机,致养其在我者,而勿以闻见乱之,去耳目支离之用,全虚圆不测之神,一开卷尽得之矣,非得之书也,得自我也。盖以我观书,随处得益,以书博我,则释卷而茫然。[2]20
颔联首言为学当求诸心必得。所谓虚明静一者为之主,徐取古人紧要文字读之,庶能有所契合,不为影响依附,以陷于徇外自欺之弊。[2]68
书本是记录圣贤言语的载体,因此不可完全废除,应援以为助力。但是在读书的同时,应该将“心”放在首位,在保持虚明静一精神境界的同时做到“以我观书”而非“以书博我”,寻找书本与内心的契合点,这样既不会陷入玩物丧志的危险,又可以有效结合外部知识。
白沙针对的不仅仅是书本,其有关功名、文章、气节等外部成就皆持类似态度:
文章、功业、气节,果皆自吾涵养中来,三者皆实学也。惟大本不立,徒以三者自名,所务者小,所丧者大。虽有闻于世,亦其才之过人耳,其志不足称也。学者能辨乎此,使心常在内,到见理后明,自然成就得大。[2]66
白沙认为三者并非不可追求,但在其过程中如果丧失对心体的把握而流于外物,将会因小失大。此种态度显示的其实是白沙对崇尚“道问学”的朱子学风的扭转,力求将学问转向“尊德性”一途。
三、白沙之学的“自然”
白沙之学中“自然”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概念,宋儒虽有提及却从未将其作为重点。白沙提出“以自然为宗”在当时极具创新性。亦有学者认为白沙之学中频繁出现如“自然”“道”“坐忘”“无累”等词汇带有道家色彩。然而实际上“道”“自然”等概念在宋代以后便被注入浓厚的儒家道德属性,其具体内涵和意指都不同于前,而白沙之学则进一步赋予其独特意义,与宋儒亦不同。
在论述“自然”之前,不得不谈及白沙之学的“道”论:
夫道至无而动,至近而神,故藏而后发,形而斯存……夫动,已形者也,形斯实矣,其未形者,虚而已......戒慎恐惧,所以闲之而非以为害也,然世之学者不得其说,而以用心失之者多矣。[2]131
道至大,天地亦至大,天地与道若可相侔矣,然以天地而视道,则道为天地之本,则天地者,太仓之一粟,沧海之一勺耳,曾足与道侔哉?天地之大不足与道侔,故至大者道而已,而君子得之。一身之微,其所得者,富贵、贫贱、死生、福祸,曾足以为君子所得乎?君子之得者有如此,则天地之始,吾之始也,而吾之道无所增,天地之终,吾之终也,而吾之道无所损。[2]55
在白沙的哲学体系中,“道”为至大,高于天地,甚至高于“心”,它是“心”成为道德主体和判断标准的终极根据。朱子曾云:“道字包得大,理是道字里面许多理脉。”[7]2291可见即便宋代“道”的范围也应大于“理”。而白沙对“道”的强调实际上使得其在某些层面涵盖了“理”的本源地位,成为万物之根本,人的道德主体性和“心”之超越性均由其赋予。
白沙将道描述为“虚”“至大”“不可言说”“无”,确实非常类似老子有关“道”的定义,因此古今学者称其杂入道家不为无据。但更重要的是,白沙在学说中尝试将“道”与“戒慎恐惧”等儒家概念结合,他对“道”的描述意在说明儒家意义上的“得道”之后所能达到的物我两忘、天人合一的境界。换句话说,“道”的道家特征不过是对儒者境界的装饰,如“随时屈信,与道翱翔,固吾儒事也”[2]71。
在此基础上,白沙提出“以自然为宗”:
人与天地同体,四时以行,万物以生,若滞在一处,安能为造化之主耶?古之善学者,常令此心在无物处,便运用的转耳。学者以自然为宗,不可不着意理会。[2]192
盖廷实之学,以自然为宗,以忘己为大,以无欲为至,即心观妙,以揆圣人之用。其观于天地,日月晦明,山川流峙,四时所以运行,万物所以化生,无非在我之极,而思握其枢机,端其衔绥,行乎日用事物之中,以与之无穷。[2]12
白沙之“自然”初看极似先秦道家对“自然”的定义,即天地万物的自我生成、自我运动性。白沙认为“天自信天,地自信地,吾自信吾”[2]242,事物各自处于自我流转、无待外物的状态,即“甲不问乙供,乙不待甲赐”[2]242。然而白沙的“自然”与道家之“自然”绝不相同,因为在宋代以后,“自然”便逐渐与人之道德性不可分割,原本用来描述非人为状态或人力无法企及的自然规律,后来发生巨大转变,与道德秩序相结合,以论证道德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如“天理自然”等说法),成为“道德自然性”。
从白沙对“以自然为宗”的解释中,可见其核心不在“自然”而在“心”,白沙强调“无滞”“无物”“无欲”“忘己”,都是以“自然”来限定心体的本然状态。换言之,“以自然为宗”实际上指的是心体道德的自然发用和体悟。白沙认为“心”中道德流转是世间的根本规律,具有先天性和必然性,故此“自然”乃是德性的“自然”、儒者的自然。
值得注意的是,白沙的“自然”概念较宋儒更进一步。宋儒虽然转变了“自然”的内涵,但其重点在于先天性、命定性,人并非“自然”的主体,这一概念亦往往用来修饰社会秩序:“君臣之义,根于情性之自然,非人之所能为也”[7]1003,白沙则将其与心的本然状态相联系,使之成为内在于人的先天法则,“自然”成为人道德行为的依据而不仅仅是外在的命定规律。
结 语
白沙早期宗朱子之治学方法,后通过“心具万理”使得“心”在功能性上包括了“理”,由此开始对理学的修正,将心与天人境界联系,并强调心的巧用,提高了人的道德主体地位和自主性。其地位之提高,使得白沙心学转向内部求索,由此导致存疑的为学态度和尊德性的学术倾向。白沙在利用原始道家“自然”含义的基础上,将其转变为富有道德性的内在先天法则,并成为心体与天人境界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