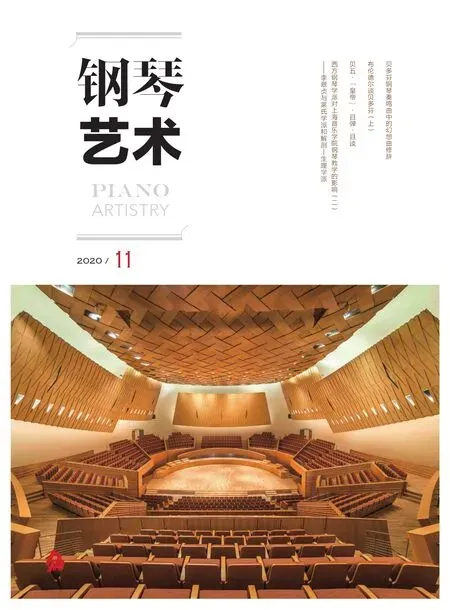布伦德尔谈贝多芬(上)
访谈者/马丁·梅耶尔 编译/行 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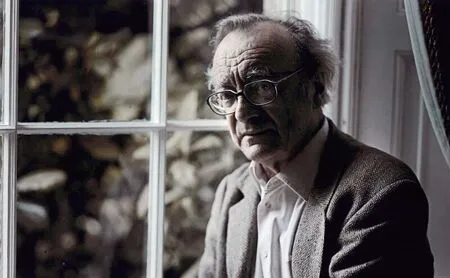
译者注:2001年,著名钢琴家阿尔弗雷德·布伦德尔(Alfred Brendel)与瑞士苏黎世《新苏黎世报》(Neue Züricher Zeitung)的艺术专栏编辑马丁·梅耶尔(Martin Meyer)一同出版了一本名为“Ausgerechnet ich”①的谈话录。其中既包括自传性的内容,也包括布伦德尔从事音乐演奏文学创作的内容。
书中,布伦德尔用大量篇幅谈论了对海顿、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李斯特、舒曼、布佐尼和勋伯格等音乐家及作品的认识。无论是对于众多的音乐爱好者,还是对年轻一代的演奏家们来说,这位著名演奏家所理解的作曲家及作品都十分有参考价值。
2020年,作为对“贝多芬诞辰250年”的纪念,现将其谈话录一书中有关贝多芬的部分翻译,供爱好者阅读。
梅耶尔(以下简称“梅”):对于贝多芬而言,他的精神总是反映在其创作过程中的。聆听他的一些著名作品,贝多芬的形象也自然会涌现出来。然而,莫扎特的情况则略有不同。你不觉得莫扎特与他的作品之间存在着无法贯通的某种隔阂吗?
布伦德尔(以下简称“布”):这个话题挺有趣的。我不认为试图以作品了解作曲家,或者以作曲家去了解作品是可行的,这是我基本的观点。当然也有例外,但仅局限于特例。我倒觉得作曲家们的日常生活都像莎士比亚那样被笼罩在一片昏暗之中,模糊不清的状态或许更好。而且对于演奏家而言,相关的知识越少越好。我想说的是,贝多芬并不只是创作出《第九交响曲》末乐章、歌剧《费德里奥》最后一幕那类充满对人类博爱精神的作曲家。

如果说到作曲家所要传递的信息,那么莫扎特的《魔笛》、巴赫的《马太受难曲》当然也都是包含着作曲家想要传递的信息的。而贝多芬作品的表现,无论是从包容力到私人情感、从个人到宇宙、从玩笑到永恒的真实,其涵盖范围非常宽泛。比如,《迪亚贝里变奏曲》可以说是音乐史上最没有悲壮感的作品,这部作品所包含的信息也是难以读取的。若是确有含义的话,那大概就是“当感知通过无穷大时, 优雅重新出现”般的克莱斯特②似的概念吧!当然,如果像过去那样固执于描绘出贝多芬的英雄形象的话,他的作品就存在被曲解的危险。
梅:但是众所周知,贝多芬是一位自我意识非常强的作曲家,同时代的辛德勒③或车尔尼都留下了证言。然而莫扎特的情况则不然,涉及莫扎特的人生形象,尚有许多内容仅停留在推测的内容上。
布:自从希尔德斯海默④的那本书问世后,莫扎特的人生形象越发显得模糊不清了。然而莫扎特也并非是那么令人费解的人物,尽管他晚年的信件遗失了不少,但有关他的人生还是有相当一部分信息留下来的。我们还是回到贝多芬,迄今为止,有关贝多芬的形象还是有许多不同的内容的。大家可以回忆一下贝多芬逝世一百周年时的一些证言,当时的人们也为摆脱那些过于主观的贝多芬形象而努力。如针对某种舆论调查,拉威尔就说贝多芬虽然耳聋,但却是平易近人的人。而雅纳切克则对此提出了批评的见解,随后贝多芬也被映射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上去解释。贝多芬的人生,都像是被过多地描绘了的。
梅:即便如此,你把作曲家“撇”在一边,只凭乐谱谱面去理解的想法行不通吧?
布:当然也无须如此极端。但是相对于作曲家本人的形象,我对作曲家每部作品的关心会更多一些。如果按照每一部作品都具有类似人的独立性格来看,那么每部作品都具有它的外貌和性格,和人一样,都会具有不同的特征、不同的力量、不同的可能性和矛盾,当然也会有不同的软弱和限度。一旦超过作品所具有的限度,就会被歪曲。直截了当地说,试图将作曲家的个人信息糅入理解作品的过程,所得到的谬误或曲解则更多一些。若是觉得不可思议,我倒是认为作曲家与其作品之间存在的差异才是最不可思议的事情,这样的差异显然无法用同一尺度来度量。用作曲家的生平信息仔细揣测作曲家,结果可能就会得出一个非常普通的人的形象来。然而视其为作曲家,会对其无限大的表现力惊讶不已。
梅:即便如此,完全无视作曲家人生与作品的关系也是不行的吧?
布:确实不能完全无视,这里就举一个反例吧!贝多芬在1821年创作的《降A大调第三十一奏鸣曲》(Op.31)中确有一小部分(仅仅是一小部分),反映出了作曲家黄疸病痊愈后的心境——那段著名的略带悲伤的“咏叹调”(Arioso Dolente),也就是所谓“悲叹之歌”(Klagender Gesang)最后标上“数次的逐渐恢复”的标记进入巡回的赋格的地方。可以说,此处音乐的精神性和他实际的生活是融于一体的。
梅:请容许我换一个方式,重提一下我的问题。比起弹奏贝多芬,演奏家在弹莫扎特作品的时候,是否就可以不用考虑作曲家就能弹了呢?还有,弹贝多芬和李斯特作品的演奏家是否就能说只考虑李斯特的特点就行了呢?
布:确实,相比其他作曲家,可以说李斯特的人格与其音乐作品的关联性要更紧密一些。但是出于对人物的误解和中伤等原因,人们对其作品的理解会产生不良的影响也是事实。这里我暂时先撤回“人物与作品无关”的论点,原因是这一观点在贝多芬身上有不可思议的例外。歌德在特普里茨第一次遇到贝多芬,并将对贝多芬的印象写在了信中“……如此单纯、充满活力、诚实的艺术家不曾遇到过”。或许歌德本人也未必意识到,这样的形容也正是贝多芬音乐重要的特征。“单纯”一如其作品所凝聚起来的形态,当然也能理解为其作品动机的素材。像《“热情”奏鸣曲》《“槌子键琴”奏鸣曲》等越是庞大的作品,其动机素材越是极其短小。“充满活力”则是其音乐的活跃感,也是作曲的过程,即一边摸索着是否存在着其他的可能一边向前行进着。何处而起,至何处而终,一步步地向前推进。而“诚实”正是成为贝多芬音乐重要核心的美德。其音乐让人如此清晰地感受到清澈见底的心,温暖的、温柔的作曲家贝多芬显然是首当其冲的。
梅:的确如此。这不正说明音乐能很好地映射出作曲家的人格吗?
布:是的,起码可以说明歌德对贝多芬的印象一如其音乐性格吧!
梅:贝多芬与同时期那些受到委约而创作的音乐家,或者宫廷音乐家完全不同,是否可以说他是执意追求个性的、新型的艺术家呢?
布:我觉得无论是哪一位作曲家都会针对其出发点,即原点进行超越。其他伟大的巨匠们也是这样的,就连被称之为“小巨匠”(petits——maîtres)的巴赫的儿子们,也都对父亲奋起直追,践行了父亲也不曾做过的事。所以,重要的作曲家也必须是有所革新的,无论怎样的杰作都应该这样。对我而言能成为判断基准的是——该作品是否带来了以前未曾有过的感受,即便是诸多要素的重组也行。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认为莫扎特才是伟大的改革者。
梅:比起每部作品个性鲜明并超越了整体作品关联性的贝多芬,莫扎特的作品虽然个性多样化,然而整体的统一感还是很强烈的吧?
布:贝多芬要比莫扎特长寿许多,毫无疑问,贝多芬是经历了最能令惊讶的创作过程的作曲家。莫扎特在35岁、舒伯特在31岁便谢世了。然而贝多芬,其音乐的宽泛也是其最大的特征之一,这一点也是了不起的。更令人惊奇的是,单单一人就能成就如此多样性、浩瀚的作品,这大概也是人们赋予贝多芬英雄形象的主要原因吧!
梅:我们来看一下贝多芬作品2号的三首钢琴奏鸣曲——《f小调第一奏鸣曲》和气氛完全不同的《A大调第二奏鸣曲》,最后是张扬华丽的《C大调第三奏鸣曲》。将三部作品比较来看,虽为同一作品号的套作,性格却截然不同。

布:是的,三部作品没有各不相同的性格当然是不行的。莫扎特最后的三部交响曲也是这样,作曲家通常都是主张以多样性来实现创作,尽可能表现更多的内容,并且努力写出类型完全不同的曲子,这就是作曲家们所追求的。贝多芬的三部作品都是这样的,舒伯特晚年的三部奏鸣曲也是如此。顺便提一下,让贝多芬的才能得以最大限度发挥的应该是他的变奏曲作品。
梅:这里借机一起探讨一下对作品的忠实性,或者说对作品恰当理解的话题。你刚才说为了正确地理解作品,有关作曲家的传记信息越少越好,要尽可能从作品自身所散发出的能量来理解作品,那么你觉得作品中是否存在着像灵魂一样的东西呢?
布:柏拉图式的灵魂或许是存在的。我一直觉得对于重要作品的探索是无止境的,音乐作品既有点通某个“穴位”才能使它栩栩如生、精神焕发的关键点,也存在更宽泛的演绎发挥的空间。所以,就像我曾说过的那样,我们既可以借用外光照射观察作品,也可以通过作品内在的东西摸索理解作品。当然,两种方法的区别使用也是相当重要的。这一点也是我20世纪50年代观看乔治·斯特拉莱尔(Giorgio Strehler)和彼得·布鲁克(Peter Brook)的舞台演出时学到的。当时我欣赏了他们的十多部作品,其中有一部作品就是典型的从作品内部照亮呈现的手法,而且舞台的布置也和现在完全不一样,这就是彼得·布鲁克的《仲夏夜之梦》,这部舞台剧我在不同的地方分别看了四次。
梅:能否举一个在音乐作品演绎上,以“内侧”或“外侧”来照亮作品的例子呢?
布:我觉得对于作品“从外侧随意打上光束”演绎的典型例子莫过于格伦·古尔德了吧。据我所知,他从未关心过从作品内部解读和理解作品的方式,而仅仅是肆意地从外面“挑灯照射”着作品而已。然而这种方式过于极端的使用结果是,妨碍作曲家原有意图展现,并产生侵害原作,进而成为演奏家自我独创性被突出、优先的结果,这对于他而言或许也是必然的。我和他第一次相遇是在维也纳,那时我们都还很年轻。他当时刚从他的加拿大经纪人那里回来,那位经纪人也曾处理过我的经纪业务,我们当时是在保罗·巴杜拉——斯柯达的家里见到的。记得午餐后,古尔德一屁股坐到了钢琴前,弹了他最近深有感触的恩斯特·克雷内克(Ernst Krenek)作品。接下来古尔德又弹了我也学过的贝尔格的《钢琴奏鸣曲》。他弹完之后,我挑刺说某个地方的节奏没有按照谱面的附点节奏来弹。过后,巴杜拉——斯柯达播放了一段我弹的贝多芬《“槌子键琴”奏鸣曲》的赋格部分,这时古尔德则指出我没按照乐谱上的要求弹出八度……这是非常有趣的记忆。年轻时的古尔德长相英俊,常受追捧,他后来也多次在他的文章中表示过对我的好感,并且给予我的莫扎特钢琴协奏曲录音以很高的赞誉。后来,他还在《法兰克福汇报》的采访中提到了我们经常电话交流,等等。当然,这都是他胡编的了。
对我而言,最不能成为像古尔德那样的演奏家——古怪而偏颇,无论什么都试图扭曲作曲家在作品中的意图,违反作品的性格,他就是这样的音乐家。如果要举例说明的话,那真是太多了。他经常采用只挑某个侧面的一两点放大,其他内容则完全无视的方式。巴赫的作品,因演奏法的提示原本就很少,或许也就不会有什么明显的抵触感。舞台演出中经常出现的“从外面挑灯照射着作品”的方法就是这样的,尽管有所违背作家原有意图,但毕竟也是演出。不得不承认这样的方式很有魅力。如果让我来编导莫扎特的《魔笛》的话,我也会想该如何设计一个收拾萨拉斯特罗⑤及其恶党的场面。然而,这里就出现了这样的疑问——演奏音乐作品的时候可以肆意改变音乐本该有的内容吗?
梅:音乐内在的必然性必须表现出来吗?
布:是的,这完全不是乏味的事情。反过来,许多人觉得古尔德是一位有个性的演奏家,对于作品的演绎幽默有趣,丰富的想象力让作品产生出新的模样,等等。并且这些人觉得努力理解谱面上的内容,并对其忠实地演绎是非常乏味、没有想象力的。这里我特别想强调的是,准确阅读谱面其实是一件相当困难的工作,并且远远难于演奏家肆意的自我发挥。通过准确理解谱面上的所有记号,并使其栩栩如生地展现出来也是一件需要想象力的活儿。当然,像计算机那样,或是像作曲家的奴隶一般的读谱也是不行的。如果一定要说的话,或许应该像作曲家的助手那种姿态比较好吧!我曾和皮埃尔·布列兹有过类似内容的交流,他也表示,如果能确保80%到90%的内容都遵从谱面演奏法的提示来演奏,应该是可以满足要求的。
梅:再次回到贝多芬的话题。你曾在各种文章中分析了各类音乐的性格,并用于贝多芬的奏鸣曲。那么贝多芬是否创造出了新的类型和性格构造呢?


布:这样说多少有些绝对,毕竟巴洛克时期对音乐的性格就是特别重视的。我们可以观察莫扎特在其舞台作品中采用的手法,他如何为音乐调配出不同的性格。我也很喜欢贝多芬的歌剧《费德里奥》,但贝多芬毕竟不是歌剧作曲家,即便如此,他还是极力避免同一性格的音乐不断重复。他的三十二首钢琴奏鸣曲之所以深受演奏者青睐,也正是因为无论哪一首作品都有相得益彰般的掩映。连续演奏他那五首钢琴协奏曲也能够清晰地感受到每首作品的差异,创作这些差异性如此之大的作品的作曲家,若是他自己不能记住的话当然是不行的,这是需要很强的记忆力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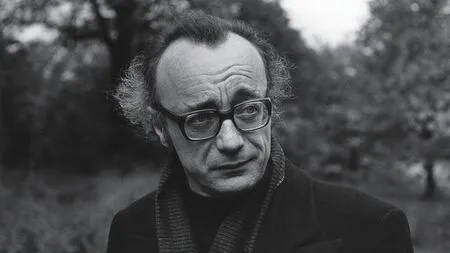
贝多芬正是以他非凡的能力记忆其内在的规律和已成就的东西而从事创作的,并且开拓了全新的音乐表情和音乐构造。同时,贝多芬通过奏鸣曲、交响曲和弦乐四重奏的创作所积累的经验,有意图创作庞大的作品,用更加综合的形式来表现的欲望也是相当明显的。正是这样的思量下,他晚年的创作量减少了许多。像《“槌子键琴”奏鸣曲》《迪亚贝里变奏曲》《第九交响曲》,以及晚年的弦乐四重奏的创作,等等。这些巨作的创作自然是耗费时间和精力的,也必然需要他花上以往积累起来的所有经验和技艺才行。
梅:你觉得贝多芬的音乐难在哪里?
布:要回答这个问题的话,我们恐怕需要再次回忆一下歌德对贝多芬形象的描述。这对于演奏家而言也是非常重要的事情,那就是需要在理解作品的核心内容和展开的过程、把握那些无可忽视的内容的基础上绘出蓝图来。接下来就是一块块地把石头堆垒上去,就像建造一幢结实的房子一样。还有就是必须读取出作品的情感、诚实和纯粹的心情,当然不能遗漏作品时代的道德观念。贝多芬本人是非常喜欢莫扎特的《魔笛》的,但是又非常厌恶《唐·乔万尼》和《女人心》,他认为那是不道德的……
梅:那是因为这些与贝多芬本人热心提倡的人类解放之精神相悖的缘故吧?
布:确实,从贝多芬的一些作品中能感受到人类解放的精神,然而并非所有作品都是如此。反之,若以这样的角度去看的话,完全被曲解的作品肯定会有很多,通过对贝多芬那些短小的变奏曲的推敲和弹奏,我非常轻松地避开了那种片面、崇高的英雄形象。
梅:和莫扎特相比,贝多芬音乐指向性的区别在何处?比如,他建设性地增加了素材的厚度等?
布:贝多芬的创作中的确有那样的倾向,但在莫扎特的小调钢琴协奏曲中已经出现了这种情况,就是将音乐的动机集约后,在对压缩(telecoping)的展开过程中增加素材的厚度。比如,《“暴风雨”奏鸣曲》就可视为其标准的作品。这并非某种特定的人物性格的刻画,而是具有更广泛性格的作品。其他如绘画般的、描述类的、舞曲风格的奏鸣曲等都是有的。对我来说,“华尔斯坦”则是体验大自然经历的表现,两端的乐章一如自己站在宽广无垠的大自然的面前,而慢乐章和回旋曲的序奏就像是视线向内,而并非向外。
梅:所以你将回旋曲乐章形容为“登上顶峰,环顾四周美景”的场面。
布:并且,耳边不时响起山下起舞着的人声和涓涓泉水声,还有向下俯瞰的样子。这是非常浪漫的描绘,对于《“暴风雨”奏鸣曲》的理解也会起到帮助。对于演奏而言,也并非需要多么难的技巧,但作为炫技的表演和利用都会导致对作品的曲解。相比贝多芬的其他钢琴奏鸣曲,这首作品的所有乐章都是从十分弱的“pianissimo”开始的,然而准确的演奏少之又少。
梅:但是紧接下来的部分,包括相当紧迫的部分,发展得相当快。
布:是的。然而和自然的呼吸一样,两端乐章的中间乐章还是回到某种状态。威廉·金德曼(William Kinderman)曾将这个乐章与《费德里奥》第二幕开场的牢房场面相联系,进行比较分析。
梅:音乐表现上,对若不用隐喻的手法就无法处理的一般性的状态,还会有哪些办法呢?
布:隐喻的手法相当重要,很多作曲家也很热衷使用。然而非常意外的是,最不常使用这一手法的或许就是肖邦了吧!
梅:你谈及贝多芬的音乐性格,特别是他的钢琴奏鸣曲,让人觉得音乐表现开始接近文学表现了。当然这是贝多芬自己的想法,并刻画出各个作品的不同的、明确的性格来。“悲怆”“热情”“告别”等都是很好的例子。“华尔斯坦”也是那样的,都是将典型的东西鲜明地描绘了出来。
布:将某个形象琢磨成乐曲的想法,让听众从一首交响曲作品中联系各个乐章特定的表现的做法,在海顿时代就已经有了。
梅:那我们换一个方式,弹奏海顿的奏鸣曲时,是否也像弹奏贝多芬奏鸣曲那样能明显地感觉到乐曲的性格呢?
布:是的,但方式是不一样的。这是因为海顿和莫扎特、贝多芬都不一样。海顿作品的主题性格具有两面性的比较多,就像歌剧或是纯音乐所描绘的那样,人物的轮廓不那么分明,有时需要捕捉多个面才行,这正是海顿作品的难度所在。比如,小调的主题,既可能是幽默的,也可能是优美的。正是这一点,印证了海顿天生就不是歌剧作曲家。
梅:贝多芬通过奏鸣曲的各个乐章,将某个主题无限展开,既有相当的趣味,也是至难的创作,并且所展开的内容的性格又各不相同。

布:确实如此,他的作品有两个内容。一个内容是展开,就像水中花一样,一颗小小的种子慢慢地展开花苞,并不断变化。另一个内容是性格的刻画,然而这并非是让单个内容在二者的关联性上显现出答案,而是需要独立处理的过程。两个内容逐步在作品中汇集,并寻找出那个交叉点来,这也是让演奏者为之苦恼、叹息的点。追随康德“性格概念论”的古典美学学者认为,这是和作品的主题相关联的,这显然是误解,是错误的。比如,作为《“槌子键琴”奏鸣曲》统一构成的三度音程,在主题甚至重要的调性中都有,但这还是无法解释奏鸣曲整体。将素材关联起来,也无非是让听众认识一些音乐的要素而已。而所有的要素都是在作品中自然关联起来的,局部和整体都同等重要,某个部分也是整体的重要构成要素。
梅:但是“槌子键琴”的三度音程跳跃和作品的主题是有着关联性的。这不正是用压缩的手法来表现的吗?反过来,“热情”第一乐章的降A大调副部主题,其性格不也是在音程旋律中得以展开的吗?
布:当然是的,并且“槌子键琴”的各个主题多多少少也是基于三度音程而写出来的,但性格还是各不相同的。这恰巧也更加印证了我的“动机式的素材对曲子的性格刻画起着更大的作用”这一看法是正确的。然而这对于演奏者来说,无论追求哪一点,结果都是不一样的。对于追求动机关联性的演奏者来说也是一种奢侈,不见动机的关联性,既不是画黑框,也不是抹红印。素材自然地浮现在表面,让人产生关联性的印象,演奏者应该是这样让作品的性格整体呈现出来。然而,像这样从作品的内部勾勒出性格来,需要有深刻的理解和明确的意识才行。
梅:你觉得若是按照时间年代来划分的话,三十二首奏鸣曲该怎样划分呢?
布:一般常见的按照三个时期的划分还是有道理的,毕竟大多数人都这样认为。但重要的是,贝多芬自己曾就作品31说过“这对我自己而言是一个全新的尝试”,所以也可以用其他的方式来划分。我倒觉得变奏曲风格的《降A大调奏鸣曲》(作品26)和幻想曲风格的《升c小调奏鸣曲》(作品27之2)就已经意味着贝多芬为了求变而开始了新的尝试阶段。而《降B大调奏鸣曲》(作品22)则反过来是为古典时代画上句号的作品,贝多芬的作品中,能称得上古典风格的作品是非常少的,而这首作品可以说是更加接近古典的作品。尽管说是按照年代变迁来划分,最后的年代也并不是可以随意确定的。最不能忽略的一点就是《大提琴奏鸣曲》(作品102)和《致远方的爱人》(作品98)是其转换期的作品。此外,《迪亚贝里变奏曲》应该是贝多芬第四个时期的作品。而《钢琴小品集》(作品126)则与晚期弦乐四重奏作品群属于同一个时期。
梅:你喜欢的钢琴作品是哪一些呢?不会对三十二首钢琴奏鸣曲的每一首都饶有兴趣地关心和演奏吧?
布:这真是难以回答的问题,以前我曾觉得有五六首是我完成度较高的作品。首先是具有让人非常惊奇的完成度极高的《D大调奏鸣曲》(作品10之3);然后是俗称为“暴风雨”的奏鸣曲;随后就是被频繁弹奏,“漏掉了不行”的《“热情”奏鸣曲》;最后就是作品109和作品111。当然,最高的杰作,也是最辛苦的作品,必然就是《“槌子键琴”奏鸣曲》了。
梅:三十二首钢琴奏鸣曲构成的“宇宙”中,既有紧张的对峙也有融洽的和谐,一如贝多芬本人精确计算的结果。你是否感到了这些作品间的对比和强与弱了呢?比如作品2的三部作品你觉得怎样?f小调、A大调、C大调这三部作品都各不相同。还有,比起《d小调奏鸣曲》(作品31之2),其后创作的《降E大调奏鸣曲》不是更显得生动且委婉动人吗?
布:是的,能感觉到贝多芬作品的性格相互对比是相当强的。但是《f小调奏鸣曲》和《A大调奏鸣曲》的完成度是不一样的,前者能让人感觉到作品的骨骼,这骨骼也正好让人体验动机是怎样辛苦地做出来的,非常有趣。刚才也提到过,所有由最初的主题发展起来的同时,按被压缩的过程行进下去,这是贝多芬音乐的重要特征之一。在《f小调奏鸣曲》的第一乐章,可以比较清楚地感受这个压缩的过程,这对于演奏者正确理解音乐是有很大帮助的。⑥
梅:《A大调奏鸣曲》被展开得非常完美,作品整体也让人觉得刻画得相当深刻。
布:我觉得作品2之2、3的内容更丰富一些,可以说是成型、规整的作品。《A大调奏鸣曲》中的幽默元素和第三乐章的优美程度起到了支配的作用,英雄式的、被拥戴着的贝多芬形象也具有独特的优雅呈现方式。值得注意的是,贝多芬的小步舞曲要比海顿和莫扎特的小步舞曲还要优雅,虽然没有那么明显,但略带哀愁的小步舞曲的性格就是这样被他巧妙地勾勒了出来。
梅:为什么19世纪和20世纪的部分作曲家觉得在他们的创作历程中,贝多芬那巨大的身影带来的压迫感如此强烈呢?
布:我们已经体会到贝多芬音乐中无法逃遁的必然性,也就是其音乐内在的那些无可回避的正当性。就这一点而言,要对他的作曲理论和精神表示敬意。从作品1到作品135的创作过程正是明晰可见的进步过程,从最初到最后,贝多芬时刻都会添加全新的要素,并巧妙地将其表现出来,而用之于表现的技艺也是全新的。被称之为杰作的作品中若是增加了崭新的内容,且呈现出完全不同的结果的话,其创造者贝多芬不就成为巨匠了嘛!对于他的作品,越是了解就越觉得感动,会喜欢上他,也会对他敬佩不已。尤其是我集中地弹奏贝多芬奏鸣曲全集的那些年,这种想法就特别明显。(待续)
注 释:
①原书名为Alfred Brendel Ausgerechnet ich. Gespräche mit Martin Meyer, Carl Hanser Verlag, München, 2001。2002 年10月该书英文版在美国问世,书名为Me of All People: Alfred Brendel in Conversation With Martin Meyer, by Alfred Brendel, Martin Meyer,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②海因里希·冯·克莱斯特(Heinrich von Kleist, 1777——1811),德国剧作家、小说家。生前因其直性而奔放的性格而未能融于当时的社会,但进入20世纪后,他的戏剧和小说作品得以重视并获得了相当高的评价,现在他也成为德国代表性的剧作家之一。布伦德尔引用的克莱斯特的原话为:So findet sich auch, wenn die Erkenntnis gleichsam durch ein Unendliches gegangen ist, die Grazie wieder ein。这是一句德语名句,出自于克莱斯特的散文集《论傀儡戏》(Über das Marionettentheater,也被译成《论木偶戏》)。
③安东·辛德勒(Anton Schindler, 1795——1864),贝多芬的助手,并写了第一本贝多芬传记的人物。至今其留下的笔记和他所写的贝多芬传记对于贝多芬及其作品的研究都有史料般的价值。然而根据近年来的学者研究,有迹象表明在贝多芬死后辛德勒曾大量销毁贝多芬的日记等资料,并伪造了一些伪称是贝多芬手记的资料。
④沃尔夫冈·希尔德斯海默(Wolfgang Hildesheimer, 1916——1991),20世纪德国作家、画家。布伦德尔提到的是希尔德斯海默写的莫扎特传记,德语版在1977年出版。中文版《莫扎特论》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出版。
⑤萨拉斯特罗(Sarastro),莫扎特歌剧《魔笛》中的角色。
⑥该内容已在布伦德尔《音乐的思考》一书中详细描述过。Alfred Brendel,Nachdenken über Musik, R. Piper & Co. Verlag, München,1977,pp. 64-72。
——贝多芬和钢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