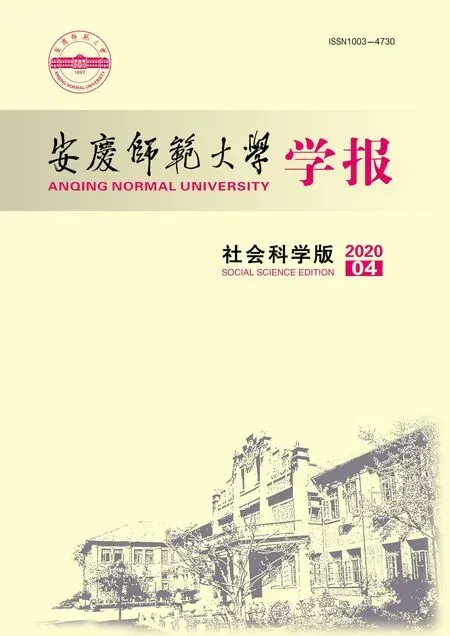《故都的秋》英译对比研究
刘梦吟,韩江洪
(合肥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安徽合肥230601)
一、引 言
语言顺应论(linguistic adaptation theory)这一理论最初由专注于研究语用学领域的著名语言学家维什尔伦(Verschueren)所提出。从广义上来说,语言顺应论中的顺应指的是在对于使用语言时所处的环境(context)进行适应的过程。从狭义上来说,它实际上所关注的主要是语用学层面上对语言进行选择的具体过程。此观点认为,从恰到好处地使用语言到恰如其分地使语言得到顺应,这整个过程都会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之中,他们分别是对于语境关系和语言在结构上的顺应,以及动态性和意识程度上的顺应[1]。顺应论最核心的理念即为选择,而选择的目的是为适应原文而服务。同时,它认为选择要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其中语言层面的因素所产生的影响最大,这包括语音、词汇、句子等各个语言单位;而除此之外,语言的选择还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其他方面因素的影响,这包括了政治、经济等多种因素[2]。
《故都的秋》这篇文章是一篇典型的抒情类散文,作者借以描写景物渲染出对秋的喜爱,并通过对比强调衬托出故都之秋的独特之处。这篇文章直至今日,仍受到世界各国读者的众多青睐与反复阅读。根据知网数据,可以明确地看到从1984年至今,对郁达夫先生本人及其相关创作的研究总数高达3 813 篇,并且在2007 年到2013 年之间到达巅峰状态。虽然国内对于郁达夫的作品进行了不少的研究,但是仍可以看到,在中英文学交流领域的相关研究数量较少,这主要是因为历来研究者们对于原作内在文化内涵的关注,相较而言,对于其英译作品的关注则比较少。目前,知网数据显示在英译作品领域内对此篇文章进行研究的作品仅有18 篇,其中对于多部英译作品的研究仅有5篇,且研究者关注的研究点和作品研究的角度都集中在对于美学内涵的挖掘。从纵向时间轴来看,早在2008年已有学者从韵味的角度入手,基于刘士聪先生对于散文节奏美,意境美等总结而出的美学理论对于《故都的秋》英译文进行研究比对。2020 年2 月知网收录的一篇名为《从翻译美学视角赏析郁达夫〈故都的秋〉英译文》仍然是从审美判断的角度切入,从美感和意境方面着手进行分析比对。
综上可知,虽然学界对此作品的研究不胜其数,然而较多地将关注点放到原作分析上,对于译作的分析则聚焦在美学的视点,角度局限且主要以张培基先生的译文为研究对象,而较少出现多篇译作的对比研究。因此,本文选取了张培基和张梦井两位先生的译文作为研究对象。其中,第一位翻译学者张培基先生是上海圣约翰大学英国文学系出身,有多年研究英国文学的学习经历,后于北京外文出版社从事编译的工作,不管是从学习经历上还是实践经历上来说,张先生都在文学翻译的领域上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并为往后的中国学者进一步做翻译研究提供了大量的典范文章。第二位翻译学者张梦井先生在太原理工大学外语系担任英语教授一职,有多年英语语言学方面的研究经验,对于中英两种语言在翻译中具体差异的研究有颇深的造诣。从1984 年起,他多次发表论文就英语的语法、语序、英文表达的逻辑、具体汉字在译文中的译法等问题进行深刻探讨,并且积极参加全国翻译理论研究的论坛,还曾于2008 年就如何正确理解原文,形成优雅的译文与史志康学者进行激烈的探讨,充分体现出其对于翻译的热情以及对于译文具体措辞,行文结构和语言表达的关注。因此,笔者试图从对语言选择的具体分析中探究译者对意群以及上下句关系的理解角度,由小及大,由点及面,从上文所说的顺应论角度出发,选取《故都的秋》这一散文原文为参考,同时收集张培基与张梦井两位先生的译文全文为研究对象,从译者翻译的差异入手进行分析,将两个译本之间的异同进行深入分析,不断地探索和发现译者作为翻译个体所具有的独特的语言选择角度,重点从顺应论角度去深入分析,探究《故都的秋》这两篇译文的翻译差异在具体文本中是如何体现的,并且试图总结出两位译者独有的翻译特点。
二、《故都的秋》译本对比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故都的秋》这篇散文进行翻译时,其过程不应当仅仅是单纯的源语文本和译语语言之间的语言切换过程,译者应当更多地考虑到如何顺应和传达出散文中所饱含的情感内涵。同时,由于中英两种语言体系所具有的文化背景以及语言表达方面都存在着或多或少的差异,因而译者要站在读者角度,依据译入语的语言结构和语言习惯做出相应的改变,从而达到适应的目的。借由顺应论的视角,我们可以通过语境、结构、动态以及意识程度这四种顺应来考察译者的语言选择,从而探究译者们在语言顺应方面的可取之处或不足之处。
(一)从对于语境的顺应程度来对比译本
语境,顾名思义,它指的是说话者在进行语言表达时所处的状态,主要包括交际语境和语言语境这两种形式。交际语境主要指的是说话人实际生活的物理环境,说话者自身的心理世界,以及交际时双方所处的社交环境这三个方面[3]。本篇抒情散文更多地是在描述作者的心理环境,因此在翻译过程中,如何积极地顺应和表达出原文中人物的个性和情绪是帮助读者更深入地体会原文作者创作意图的重点。而语言环境则指的是文章的上下文之间的衔接关系,即语篇意义上的逻辑相关性。
例1:
原文:一个人夹在苏州上海[4]227
张培基译:muddling along all by myself among the urban dwellers of Suzhou,Shanghai[5]209
张梦井译:A man living listlessly among the civilians of Suzhou,Shanghai[6]327
原作第一段提到作者特地从杭州出发,不远千里来到北平。随后在第二自然段,作者便描述到一个人在上海、苏州、杭州这样的地方会体会到的混混沌沌以及秋所给人带来的一丝丝清凉的感觉。因此,从上下文的描述中,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到文中所述的“一个人”实际上具体所指的就是作者本人,此段对于心情的描绘则涉及到主人公自身的心理世界的内容。因此,在翻译这句话的时候,是否能够将“一个人”准确地翻译出来则体现了译者对于原文作者创作意图的把握程度和原文作者内心世界的顺应程度。从译文中,我们可以看到张培基在后文中所使用的主语是“I”,在此句中使用的是“myself”来突显人物,而张梦井所使用的主语是“a man”。显然,后者是从第三人称视角进行描写,而前者是从第一人称视角。从人称视角的使用则可以明显地看出译者理解角度的不同所在,张培基先生认为此处的“一个人”实际上指的就是作者本人,而张梦井先生所使用的“a man”则可以指代任何一个人,并非特指。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张培基先生更准确地顺应了原文的交际语境,能够抓住说话人的心境,领悟到作者在此处触景生情的内心世界。张梦井先生更多地是从字面上意思出发,文字内容上做到了一一对应,然而缺乏对于情感内容的把握。
例2:
原文:在南方是非要上郊外或山上去才听得到的[4]229
张培基译:In the South, however, one cannot hear them unless in suburbs or hills[5]210
张梦井译:In the South, it is only in the suburbs or in the hills that one can hear their chirp[6]329
上下文的照应在英语文本中显得尤为重要,而这主要是因为英语语言对于形合的重视所导致的结果。一个长句的构成以及几个句子之间的逻辑关系的体现都主要依赖于各种连接词的使用。如若连接词使用不当,通常句子会变得晦涩难懂,即使不影响理解,也会使句子看上去不够地道自然。究其原文文本,此句为原自然段的第二句。首句主要描述的是在北国随处可闻的秋蝉的叫声。虽然原文在两句之间并未使用任何承接词,但从句义上可以明显察觉到前后两句鲜明的对比关系,即北国到处都可以听得到秋蝉声,而在南方,除非去到山上面或者走到郊外才可能有机会听得到秋蝉声。因此,在翻译实践当中,特别是译成英语文本时,这种前后对比的句子关系有必要通过词语进行承接。一个恰当的转折词的加入看似平淡无奇,实际上则会为句子增添色彩。张培基先生用插入语的方式加入“however”一词不仅具有承上启下的效果,使句子衔接得较为紧密,更能起到强调的作用,能够充分引起读者的注意,使整个语篇更具逻辑性,在阅读时更易得到理解。张梦井先生更多地从忠实于原文的角度出发,原文没有添加的转折词,在译文中也相应地进行对照翻译,这更偏向于中文的表达习惯,然而站在译入语读者的角度来说,相较前者而言,逻辑和理解方面稍有不足。
(二)从对于结构的顺应程度来对比译本
在具体的翻译过程当中,译者不仅要努力去顺应语境的关系,还应当去顺应结构层面上语言的搭配和安排,这涉及到从语音到词汇再到句式等各个方面的内容[7]。原文作品中作者的一字一句都是其反复斟酌推敲而出的结果,因此译者也有义务去对这样的语言组织进行最大程度的顺应。
例3:
原文:足见有感觉的动物,有情趣的人类,对于秋,总是一样的能特别引起深沉,幽远,严厉,萧索的感触来的[4]230
张培基译:All that goes to show that all live creatures and sensitive humans alike are prone to the feeling of depth, remoteness, severity and bleakness[5]211
张梦井译:The just proves that sensible animals including man, with their varied temperaments and interests can possess a sensation about autumn which can bring about a very deep,secluded and intense desolate sense[6]330
原文中此句的主语是动物和人类,描绘的是他们对于秋的情感体验。很显然,“深沉,幽远,严厉,萧索”这四组词语都是两个字构成,有使句子看起来层层分明,形象生动的效果。很明显,作者在这里使用的是排比句,借此种表达手段进行抒情,试图在音律上达到和谐的效果,使文章读起来有一定的节奏感。同时,与四字格词语相比,两个字的词语组成使所要表达的情感更为集中,语气更为强烈。因此,这种词语的安排在译文当中也应该得到合理的体现。张培基先生在翻译时,很好地顺应了原文的节奏感,使用了短小精湛的四个词语,同时将他们集中排列在一起,在语气上也顺应了原文的语言结构,使整个句子一口读下来能体会到原文所要表达的浓烈的情绪。而与之相比,张梦井先生的译文将“深沉”和“幽远”这两个词语放在一组,“严厉”和“萧索”这两个词语放在一组,用“and”这一连接词将四个词语分割为两个部分。从语义上来说,每一个义项都得到了一一对应,没有漏译的情况,但是从结构上来看,语气的停顿时间被拉长,朗读时语音上的节奏感相较之下减弱了不少,因而从这个角度上来说,这并未很好地对应了原文的排比结构。
例4:
原文:草木雕得慢,空气来得润,天的颜色显得淡[4]227
张培基译:plants wither slowly, the air is moist,the sky pallid[5]209
张梦井译:the grass there fades rather slowly and the air is moist.The sky seems pale there[6]327
原文中“雕得慢”、“来得润”、“显得淡”这三个词语组合的搭配使用的是中文中的偏正结构,由动词、助词“得”、形容词或副词这三个部分组成,成分的前后之间是修饰与被修饰的关系,这在结构上形成了排比。很明显,这里的句子组成结构也是原文作者精心构建和运用的表达手段。张培基先生的译文用最简单的句子结构,使每一个意群都仅由单个名词、动词、副词或形容词这三个部分组成,做到了语言结构上的顺应。同时,原文中“慢”、“润”、“淡”三个字均为仄声,即中文语调中的第四声,在语音层面上也形成了对比,更突显其音律之美。张培基先生在翻译时分别使用了“slowly”“moist”“pallid”三组词来进行表达,以此对应中文。这一点张梦井先生在译文中也做了同样的处理,达到了一样的音律排比效果,然而,从结构上来说,他加入了过多的修饰词,如“rather”和“seems”,同时用句号将句子的排比结构打散,分成了两个句子,这并未充分顺应原文的结构。站在读者角度看,源语文本传达出的义项在译文中都可以体现出来,读者不会丧失对于原文景色描写的理解。然而,站在原文作者的角度来看,作者所要借由排比结构传递出的韵律感却并未在译文中得到体现。
(三)从顺应的动态性程度来对比译本
不同于科技文本等所具有的文体特点,散文文体通常是对日常生活中的各种琐碎细节的描写,这就很容易使文本融入更多本土文化的色彩。因此在翻译过程中,译者需要顺应源语语言所具备的特点,设身处地地从当时当地的文化背景出发,同时又要自发地站在读者的角度,不断选择能够契合目的语的表达方式,在动态中把握顺应的程度,从而合理地还原作者的情感态度[8]。
例5:
原文:北方人念阵字,总老象是层字,平平仄仄起来[4]228
张培基译:(省略)[5]210
张梦井译:To the people in the north,"spell"is often pronounced as "smell". Talking about tonal patterns in classical Chinese poetry[6]328
语言障碍过大而引起的无法对应是翻译,特别是在散文翻译过程中普遍存在的问题。与英语语言不同的是,在汉语中,普通话通常分为四个声调,因而原文中“平平仄仄”一词对于中国读者来说很好理解。然而,译文读者无法领略其中的韵律,译者也无法在译文读者所处时代背景和文化语境中找到对应,因而张培基先生在处理此句时直接将其删除,借以虚带实的方法进行表现,使译文更易于理解,这顺应了目的语语言的表达方式。而原文中此句的下文直接跳到了对于北国秋天果树的描写,因此此句的删除也完全不会引起理解的断层和语篇的突兀感,从这个角度上,可以说是在动态中找到了合适的顺应节奏。而张梦井先生选择多做阐释,旨在完全贴合原文,用心良苦,他用中国诗歌中的音调作为阐释,然而译文读者对于中国诗歌的了解甚少,可能依旧无法理解其中的真正含义,这反而还有可能加重了译文读者在理解上的负担。
例6:
原文:有一个“秋士”[4]230
张培基译:qiushi (autumn scholar, meaning and aged scholar grieving over frustrations in his life)[5]211
张梦井译:"Autumn Scholars"[6]330
值得注意的是,在此处,例5 和例6 两个例子虽然都是译者对于原文特有的语言现象所进行的处理,但是实际上却有着细微差别。在例5中,“平平仄仄”一词在英语语言中完全没有可以对等的语音系统进行参照,因此理解上困难十分大,所以省略不失为一个好的翻译方法。然而,在例6中,就“秋士”一词而言,中文和英文的表达之间并不是完全不存在调和的空间。虽然当时的英美社会并不具备科举制度,但是却同样拥有各种能人贤士,在文理工各方面同样有具备过人之识的才学之人,因此读者对于“scholar”一词是存在一定的理解空间的,同时,此处的“秋士”与后文有着直接联系,所以对于译者而言有很大的翻译必要。
根据动态性的顺应原理来看,针对源语语言中特有的语言现象或文化环境,译者有必要在源语和译入语之间找到平衡,使得译文既不能表达出原文的语意,同时让读者可以很好地理解文章的内容。原文已经明确指出“秋士”一词为中国读本里常见的成语,它其实也是古时候的诗人们在诗歌中创造出的词汇,最早可追溯到《淮南子·缪称训》中的“春女思,秋士悲”一句。它主要是描述在秋季到来之时,面对秋风这般萧瑟的景象,男子从中体会到的悲伤和孤寂之感,在诗文中通常特指人到迟暮之年,不能再如年轻时一般大有作为的遗憾和感伤。作为一种中国文化里特有的词汇,如何能在译文中将其中的词义完美地呈现出来是译者需要细心推敲的重要问题。从译文中我们可以看到,张培基先生将“秋士”一次用汉语拼音的方式书写出来,同时在括号中进行了注解,表明这指的是年迈的学士充满着惋惜和沮丧的心情。这样的翻译既从字面上直译了“秋士”的意思,从文字上忠实地对应了原文的内容,同时,这个译文又借助了解释说明的方式,进一步把“秋士”所具有的词汇意义全部描述清楚,这让读者在阅读的时候可以直观地领略到这个词汇的真正内涵。而张梦井先生将其字面意义翻译出来,并未作过多阐释,也有其合理之处,但深究其义则不难发现,“Autumn Scholars”主要指的是秋天的学者,从译入语角度来看,这组词并不具备任何情感含义,所以原文作者所要描述的感伤之情无法在译文中得以体现。
(四)从顺应的意识程度来对比译本
顺应论所强调的意识问题主要指的是原文创作者在写作时想要通过文字传达出的深层含义[9]。散文的美感就体现在不言而喻的隐含意义之中,借景抒情,寓情于景,使得情景达到交融的地步是最常见的写作手法。因此,这就要求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很好地领悟字里行间的意义,把握原文的深层含义。
例7:
原文:北方的果树,到秋来,也是一种奇景[4]228
张培基译:Fruit trees in the North also make a wonderful sight in autumn[5]210
张梦井译:The fruit trees in the north are also a strange sight in late autumn[6]329
由通篇文章可知,全文旨在表达对于秋这个意象的喜爱之情,原文作者对秋的感情较偏向于褒扬和赞美。同时由此例句所承接的后文也可以看出,枣树慢慢长大,秋逐渐到了全盛时期,枣子红了以后,又来到了一年中最好的黄金时节。从此句中也可以窥见原文作者并未直抒胸臆却流露在字里行间的喜爱之情。秋天之所以是一种奇景,就在于果实成熟,庄稼丰收的美妙之中,这是只有在秋天这个季节才能见到的罕见景象。由此可见,开头所述的“奇景”一词在文中的情感意义应当是十分罕见但却美好壮观的景象。因此,张培基先生在译文中使用“a wonderful sight”来描述,体现出褒义的情感意义。而张梦井先生使用的是“strange”一词,在牛津词典中这个词的释义为“unusual or surprising,especially in a way that is difficult to understand”,它包含令人惊讶,很难发现和并不寻常三个义项,但是并不表达任何情感意义,不具备体现原文作者情感的作用,因此此句所要表达的对于秋的惊叹之感,对其美的无比欣赏则无法从中得以体现。
例8:
原文:说:“唉,天可真凉了”[4]228
张培基译:“Oh,real nice and cool”[5]209
张梦井译:“Ai,it's really becoming cold”[6]328
将此句放回原文中,我们可以看到,词句所处自然段的上文描写的是对于北国秋天下雨时景象的概述。原文作者认为秋雨下起来是十分有味且像样的,然后此段承接之后,通过两个说话人的对话进行详细举例,说明这种秋雨“象样”的特色,从上下文中可以体会到原文作者在描述此情此景之时所要表达出的对秋雨的欣赏和赞叹。对于句中“凉”这个字,张培基先生添加了“nice”一词,属于增译的翻译方法,将原文中的一个词拆译为两个并列的词。这说明他将“凉”这个字看作是此句的中心词汇,并希望用强调的方式将其突显出来,以引起读者注意,目的是站在读者角度,为读者准确把握说话人物所要表达的情感内容而服务,因而个性化处理的部分较多。“nice”一词在牛津词典中的释义为“pleasant,enjoyable or attractive”,从释义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个词带有令人舒适且快乐的感觉,说明译者翻译时充分考虑到了作者的内心感受,体会到因秋风而带来的凉爽之感,因此用在这里也是恰到好处。张梦井先生翻译“凉”一字时注重紧扣原文,以忠实于原文的方式将此字直译出来,更多关注字面意思,用“cold”一词来表达。然而这个词更偏向于因寒冷而引起人不舒服的感觉,却并未表达出作者原文在字面意义之外延伸出来的言外之情。此外,“cold”一词多用来指冬季的刺骨寒冷,用于此处则与当时所处的季节不符。此翻译方式形式上一一对应,平铺直叙,情感上却朴实直白,忽略细节,仍值得进一步推敲和修改。
三、结 语
通过运用顺应论视角来对比研究《故都的秋》译本,笔者发现两位译者在语言的选择上存在着或多或少的差异。总体而言,两位译者都在尽力还原原文的内容和结构的特点,但是每个译者又是从各自不同的切入点去理解原文,从而产生不同的细节处理的方式。张培基先生的翻译更多地是从译文的角度出发,为达到英文词语,句式等搭配的合适度而省略或添加部分原文意义,人为改动的成分较大,较为灵活,张梦井先生的翻译从基本出发,他尽量地使文本看上去一目了然,因此很多时候只译出中文词的基本义,而忽略其延伸义,更为平白。从对于译文的分析可以看到,不管使用哪种翻译的方法、策略或是手段,译者都有着共同的深刻用意,最终都是以服务于读者体验的同时尽量忠实地还原原文内容为目的。同时,他们也在不断地对语言进行打磨,试图在原文和译文之间能够取得很好的平衡,使语境能够得到顺应,让读者在读懂内容的基础之上进一步理解和领悟到原文作者的创作意图和所要表达的情感意义。两篇译文都有其值得借鉴之处,是广大翻译爱好者研读和学习的典范教材。本篇文章也只是究其一隅,稍作探讨,尚有其他未提到的问题仍待探究,可研究空间十分广泛,愿听取各方有识之士所抒之见,以作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