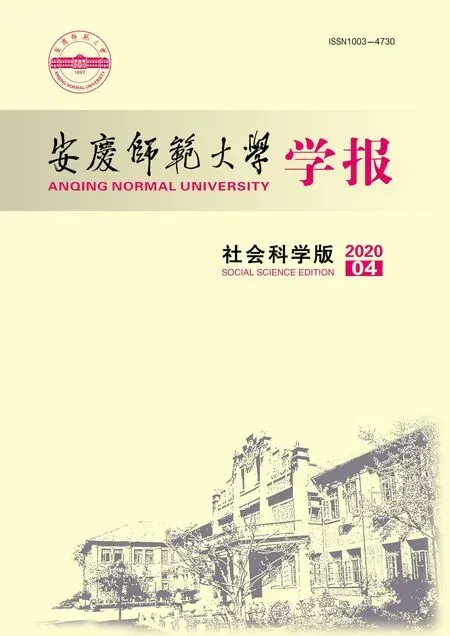“游击”“地理”与思想的难度
——读张承志《三十三年行半步》
李 强,吴 立 智
(1.北京大学中文系,北京100871;2.湖北省竹溪县教师学习与资源发展中心,湖北竹溪442300)
一直以来,张承志对当代文学乃至当代思想的研究者来说,都是一个复杂的存在。何吉贤将张承志这些思想文明、1960 年代等命题的复杂性概括为“张承志难题”[1],当前对张承志的研究,也大多是从这些方面切入的。不少论者似乎更为注重“难题”的内容,而对张承志的提问方式和解答路径讨论不多。这其中当然有现实原因,我们深知,在今天的语境中讨论张承志,关心他说了什么或许比他怎么说、怎么实践的更重要。有些问题能够被提出,本身就是一种胜利。
不过,有深度的思想,应该也包含对提问本身的反思。张承志的语言感染力较强,使得其文章多少都有某种鲜明的姿态。“姿态”是当代思想者的独特表达方式。如果只停留在他说了什么,我们是否能透过“姿态”而抵达他的思想核心?正如吴晓东曾指出的,“张承志在不安定的徘徊中寻找‘有意味的东西’,而我们寻找的可能只是这种‘寻找的姿态’和‘不安定的徘徊’本身。”[2]“姿态”和“寻找”,都是具有症候性的。如果能明白他是在何种意义上以怎样的方法去“说”的,我们才能在更深层面上把握他所提出的问题本身。
一、“文明的游击”与正义的探寻
张承志思考文明的方式乃至写作方法,都是游击战式的。他是训练有素的学者,可以从容游走于历史现场,打开“常识”而又在自己的世界观之内重构知识。其思考的深度超出一般作家,写作的情感强度又胜过一般思想者。任何对于他的研究,都面临着被他质询甚至嘲讽的危险。但是,也正是在讨论这个游击的“张承志”时,张承志的意义才真正呈现出来。我们只有通过讨论这样的他,才能真正进入他路径,进入他所面对的“当代”。其新作《三十三年行半步》(以下简称《三十三年》),有一种自我回顾的意味,方法论总结的特征亦较为鲜明。它向读者揭示了张承志是如何在“文明”与“空间”的坐标上,不断探索、表达,提出一个个“张承志难题”,寻求“思想”在当代的可能性。
张承志是对自己的思想历程有高度自觉的写作者和思想者,回顾和总结往往就包含着自我反思。《三十三年》的书名选定是有明确意图的,这篇文章是全书的压轴之作。“三十三年”从标题上就有明确的时间标示,意指从1984 年走进西海固到写作的当下(2017),1984 年是他的写作发生转变的时间点。
实际上,在此之前张承志也有一次“自我总结”的尝试了。2015 年左右,北岛主编了“视野丛书”,“丛书”包括张承志、韩少功、李零、汪晖、徐冰、李陀这六人的散文作品。所选作品侧重讲述“时代与个人、阅历与写作”相关内容,力图展现“艰难的思想图景”[3]V。这种文体要求,简直是为张承志“量身定做”的。循此思路,张承志在自己截至2014 年的作品里挑选了一些有代表性的,编为《鱼游小巷》一书。在“编成小引”中,他解释道:“此次编为一个小辑的文章,循着一个自我解说的思路:对我来说,自己的步履体验和影响自己的民族文化,以及自己想究明索求的领域大约有五个,它们也是这小辑的前五部分:蒙古(1)、新疆(2)、黄土高原(3)、西班牙(4)、日本(5)。与这些不同文化的关系,因介入方式与深度的不同当然有深浅优劣的差异,外在的语言也各有不同相貌。但前三者如过去常被我形容的乃是我安身立命的三块大陆,后二者则日益成为自己看待世界史(6)和中国(7)的眼光。”[4]VII
在这里,张承志将自己的思想地图明确地标示了出来。这也为他的读者和研究者们提供了一个解释的入口。循此入口,可以抵达他的思想起源:“这一切又都能追溯到一个沉重的开始。于是关于革命的内省,就成了一种缘起、动力与注释。我坚信‘他者’的观点,将愈来愈成为人类思想的焦点;而在内蒙古草原萌芽进而在‘心的新疆’养成的他者立场,改变了我自己。”[4]VII不难理解,对于“‘他者’的观点”的渴望,成为他纵横边荒、跋涉异域的重要动因。其他文明的特质,为他思考“中国”提供一个有力的参照。
“小引”的最后,张承志引述了日本诗人谷川雁的句子,原句认为,在这个“一边活着一边被杀死”的时代,有一种“与大众和知识人都尖锐对立”而且“从哪里都没有接受援助的可能的游击队”。张承志对这个称呼格外认同,“我喜欢这个表达。是的,文明浸透的游击队,‘拒绝知识分子的翻译法’”[4]VII。“文明的游击队员”,也是一个贴近张承志形象的描述。
年鉴学派史学大师布罗代尔在《文明史:人类五千年文明的传承与交流》中指出,20 世纪以来,“文明”应该指向的是复数形式而非单一的某种文明,这是与人们思想观念的发展密切相关的。“单数的文明”,则是典型的18世纪时期的观念,“它主张存在文明这样一种东西,这种东西与进步的观念相关,仅为少数特权民族或特权集团(也就是人类的‘精英’)所拥有。”但在20世纪,人们在一定程度上放弃了这类判断,很难再说何种文明是最好的[5]8。“文明”成为诸多可以选择、参照的系统,而非一个整齐统一的存在。它打破了某种中心文明观,诸多文明之间,不再有高下低劣之分,只是呈现出了不同的差异性特征。对于思想者而言,在各种丰富的文明之间游走,一边吸取资源充实自身一边寻求反思的“文明的游击”才是可能的。
具体到“游击”而言,它是一种现代的斗争文化,有实践的意义也富有理论的潜能。卡尔·施密特认为,游击队员具有非正规性、高度灵活性、强烈政治责任感、依托土地等四种品格。张承志的“文明的游击”,显然具备这四大品格,他采用“非正规的”民间的、个人的方式,灵活地行走在大地上,同时永远保持着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即“正义”的理想探索:“正义——Al adal,没有比它更美好的理想了!……如今回顾,在冥冥之中强大的拨派和指引之下,数十年光阴之中,一步一步逆境求学,逢险化夷,一举事成。从清华园到巴勒斯坦,生命画上了一条长长的轨迹,不用说,它更是一支笔的酣畅墨迹。”[6]在《三十三年》中,“正义”仍然是张承志行动的旨归。这个词在书中随处可见,“求取正义”是贯穿他三十三年的行走始终的。这种追求在书中有时被简单表述为,“人民和底层再也不会受难,资本压榨和帝国霸道被淘汰的日子。”[7]277
对“正义”的探寻,是一条可以将张承志的写作版图清晰勾勒出来的线索。但三十三年的时间里,张承志要斗争的“敌人”也是在变化的。它们强大到无所不在,但又并非具体可见,很多时候是“无物之阵”。张承志要辨析、清理文明的轨迹,寻找某种“正义”的出路,就需要自己创造出某些方法。
二、“人文地理”:从空间抵达历史
文明与地理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按布罗代尔的说法,“文明,无论其范围广大还是狭小,在地图上总能找到它们的坐标。它们的本质特征取决于它们的地理位置所带来的局限或便利。”[5]10同时,“游击”也是一种基于空间的战争艺术,“因为游击队员并非出现在公开战场上,并非在公开的前线战争中的同一层面战斗。游击队员将自已的敌人逼到一个空间……只要充分利用地形,相对较小的游击队便可箝制大量正规军。”[8]315在这个意义上,“文明的游击”必然是与地理空间一起发挥作用的。在正面批判收效甚微时,地理即是抵达“正义”的幽径。
1999 年,张承志担任三联书店创立的《人文地理》杂志主编,并撰写发刊词《人文地理概念之下的方法论思考》。在该文中,他描述说,大地就如同矿藏,年轻人投身其中时,不需要带着表格,只需要体察原汁原味的世界,其中有真正鲜活的学问和规律。强调“人文地理”概念,就需要人们去发现,形成“对于文明的合格发言”[9]。
“人文地理”的说法,容易被直观地理解为地理学中与“自然地理”相对的一个学科分支。地理学者唐晓峰提出“地理学是一种思想方法”,“人文地理”更需要思想、文明的视野。“人文地理的东西常常隐在人类的各种行为当中,要是不开启一种思想方法,这些东西还真是很难被发现。……人文地理思想,或者说人文地理观念,往往具有民族文化特色。”[10]这种学科观念也是强调将地理与文明相融合的,希望通过思想文明来激活、发现地理中的丰富因素。不过,张承志所主张的“人文地理”,更多的是将“地理”作为一种思想路径,而非固定的自然场域。在地理的空间坐标中,“行走”才能摆脱现实经验的限制而实现自我拓展。通过空间的调整与移动,来实现某种时间(历史)的超越。在这个意义上,“交通条件不会成为决定的限制。对求知的旅途来说,最重要的条件是一颗追寻的心,以及感悟与融会的能力。”[11]125
历史考古学专业出身的张承志,深入历史现场,却并非为了获得一种“实证性”来强化某种历史固有的叙述,而是要借助空间中那些实实在在的节点,去触发一些时间性的命题,进而把握时代的症结,思索文明的未来问题。
《三十三年》的开篇之作《从伶仃洋到扬子江》,就是从中国近现代史的起点鸦片战争出发,去突破、重构某种历史想象。“我”从汉口盘龙城的古代文明起步,听到汉口的一句歌,便决定去南方。到虎门、淇澳岛、澳门、香港,再回汉口。南方地理中本来已经模糊的历史记忆,通过大江大海被翻出来,水域勾动了回忆思绪。在近代民族的屈辱起源地,张承志找到了文天祥这样的历史形象。在空间的交错中,中国近现代史的路线图被勾勒出来,殖民主义的复杂性体现在可以触摸的遗物、草木上。在这个意义上,“屈辱”不再是抽象的描述,而是一个笼罩了每个当代人的具体实在。其中有时间的沧桑印痕,也有对文明幻觉的揭露:当人们被热闹地裹挟进当代资本主义景观之时,自然也就身处近代史的屈辱之中。
面对这样丰富的存在,张承志需要特殊的呈现方式,要调动更多的资源。例如写到澳门,他的开篇谈的就是《鲁滨逊漂流记》[12]14。通过一部耳熟能详的作品,一段耳熟能详的殖民历史,却在澳门这个繁华空间中被陌生化。经过分析,鲁滨逊这类“英雄”的“自由灵魂”和“合理愿望”,变成了一百多年前殖民主义的“流氓的道白”。读者经由这样的文字的提示,再次踩入这片繁华空间,才会发现自己与大历史如此深刻地交织在一起。这便是“地理”作为思想方法的意义,它可以击穿当下五花八门的意识形态迷雾,让人在空间“行走”之中获得历史本真的启示。
三、思想的难度
张承志解释说,书名中的“三十三年”指的是1984年到2017年。1984年这个时间起点,在张承志的个人讲述中一直都是有明确意义的——这是他走进西海固,写出了《心灵史》的时间。这个节点也被张承志描述为一个决裂的时刻:“在一九八四年冬日的西海固深处,我远远地离开了中国文人的团伙。他们在跳舞,我们在上坟。”[13]267“上坟”即便在今天,也是极具象征意义的表述。它让人联想到理性主义的哀悼、挽歌。张承志没有停留在悼念追思之中,或者说,他是在异域唱响了挽歌,同时也发起了战斗的号角。
实际上,张承志的“行走史”可以越过1984年,追溯到1960年代,他出发的缘由是“革命”“正义”,那是充满革命激情的起点。因此,他的“三十三年”实际上有五十多年。在《三十三年》里,他带着这些遗产上路,让“行走”成为一种新的思考视角。求新声于异邦,更有反照中国的可能。在《一点一滴》一文中,这种特点尤为鲜明,日本、西班牙、亚马孙河流域里,往往有中国的影子。他重读白求恩、瞿秋白,在异域重访英雄的足迹,发掘出了国际主义精神和抗争意志。也正是在地理位移中,张承志再次确立了“中国”的主体位置。
施密特认为,虽然游击队具备战术上的灵活机动性,但总体来说,仍然是处于守势的,“如果游击队员认同一种世界革命或者一种技术至上论的意识型态的绝对攻击性,他们便会改变自己的本质。”[8]363也就是说,“游击”的作战策略,天然具有区域防守性的特征,而非普泛的攻击性特征。“文明的游击”,往往也只能受限于既定的地理空间,无法承载“世界革命”之类的宏大诉求。但在张承志那里,“世界革命”的诉求,已经超越了现代民族国家的视野,在文明格局中获得了一种“新国际主义”的命名。这就意味着,“文明的游击”必将超出“游击”自身的限度,而成为某种“文明的阵地战”,成为大规模的、尖锐的文明的冲突与对抗。
需要注意的是,在当下的语境中,“阵地战”又会让张承志思想的境遇变得复杂起来。在《往事迭印》中,他说自己在微信公众号上发表了《安乐寺的苏菲》文章之后,被一些读者误解、质疑。面对这些质疑声,张承志大惑不解,“如果不是读到,我还真不敢相信”,愤懑地判定他们“不是自己的读者”:“我从来就不曾被你感受。我的信仰,也从来与你不一样。”[15]105虽然张承志一开始就自觉地做到了“从群众中来”,不曾与自己的思考对象隔膜,但在互联网的环境中,这种单向度的表述方式,却会遭遇误读的尴尬。不可否认,这种误读在任何时代就有,甚至在姿态化写作的张承志那里,读者的“有意义的误读”本身也是必要的,它可以促成思想的发酵、轰动。然而,写作姿态越鲜明,中心化、一元化的趋势就越无法避免。在多元嘈杂的语境里,这样的表达方式往往会被检视,一些作者本人不希望出现的“无意义的误读”也会被直接暴露出来,反馈到作者那里,引起反弹。这个过程当然不会削弱思想自身的质量,却会作为思想的效果一起被传递出去,形成有现实意味的“思想史景观”。这一景观,会让“张承志难题”的讨论更加复杂化。
在众声喧哗的新语境中,思想传播的有效性问题前所未有地凸显了出来,作家、思想者的“理想读者”在哪里?共同体的想象与分裂的现实之间如何协调?在媒介变革时代,“思想”在当代如何可能、如何有效,也是“张承志难题”的制造者张承志自己要面临的难题。
张承志的句子掷地有声,给人“所言即所是”的感觉,仿佛启示录一般,但真正深入语境去体察时,会更明白“言”与“是”之间是有张力的。他的思想在现实之中可能会遭受误解,但不管认同与否,他的理想追求都值得我们敬重,他提出的问题,也值得深入思索。
作为“游击队员”,张承志是无法被总结和描述的。或许,我们只能通过他的提问,他的思考,来启动自我反思;通过探寻他的提问方式和解答路径,争取在更大的格局和更长的时段里(“长时段”与总体文明史观恰恰也是布罗代尔的理论主张)把握那些难题。“三十三年”是一个总结回顾的时段,但对一个思想者来说,这种反思性的总结必然是从一开始就存在的。如此,思想才会有这般深邃持久的魅力,才有“踏遍青山人未老”的豪迈诗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