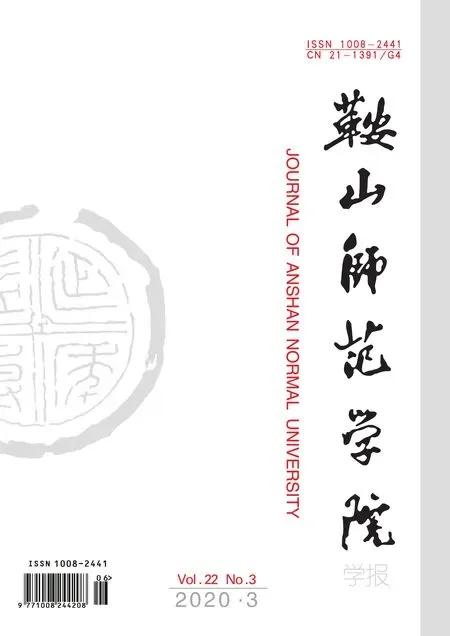《成为》之从一到多的美国非裔文化身份解读
莫 竞
(江门职业技术学院 外语系,广东 江门 529090)
据美国盖洛普民调(Gallup World Poll)显示,美国前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1964—)当选为2018年美国最受尊敬女性,其自传性著作《成为》(Becoming)更登上2018年最畅销书籍榜。该书体现了米歇尔真诚、无私的宝贵品格,更折射出非洲裔美国黑人生存处境的艰辛与自我认同的不易。在后奥巴马时代,在“白人至上主义”抬头的当下,聆听美国历史上首位非洲裔第一夫人——米歇尔在《成为》一书中对其人生历程的醇醇自述,或有利于思考非洲裔美国黑人文化身份的建构过程。
一、“成为自己”:被言说的“身份”
《成为》一书分为三大部分,以米歇尔的历时性成长经历为线索,讲述了其童年、少年、青年时代的经历,与奥巴马相互扶持并赢得总统选举的经历,以及成为第一夫人之后的经历。三段经历横跨了米歇尔不同的人生阶段,在遵循时间维度的基础上,既各有侧重,又保持一致的自述风格。在娓娓道来的追忆中,米歇尔语言之朴素,感情之真挚以及经历之丰富,都是其获得广大读者认可的重要原因。
从内容上看,该书不乏诸多之前没有公之于众的信息,包括米歇尔对当下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个人态度。米歇尔愤怒地指出特朗普对女性的蔑视,对尊严和道德的践踏,毫不掩饰地写出自己的反感和厌恶之情[1]。米歇尔的愤怒——从自述上看,主要有两方面的根源:一方面是因为特朗普对自己丈夫奥巴马的污蔑性评语;另一方面则因为特朗普对少数族裔的贬低与排斥言行(demeaned minorities)。显然,对于奥巴马和米歇尔而言,他们既为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对非洲裔美国黑人总统夫妇而骄傲,也为一直备受他人对自己种族身份的质疑与指责而愤怒。
对于非洲裔美国黑人而言,相比骄傲,愤怒更是一贯存在的事实性处境。在开篇序言中,“愤怒的黑人女性”(an angry black woman)[2]是米歇尔多次提及的身份标签,此类标签却是被动赋予、被动言说的,是基于西方主流社会话语体系下的产物,不仅是对米歇尔一个人的丑化,更是对整个非洲裔美国黑人群体形象的歪曲。它的存在体现了种族歧视主义,以及力图将少数族裔与白人精英阶层截然分开的仇外心理,暴露出美国社会一直潜在的单一性理念。在21世纪初期,在亨廷顿大肆鼓吹“盎格鲁-新教文化居于美国国民身份的核心地位”[3]的当下,如何应对由种族身份带来的困扰和焦虑,如何在不同文化对峙与对话中重塑少数族裔文化身份,成了包括米歇尔在内的非洲裔美国黑人群体所面临的共同问题。基于此视角,贯穿《成为》三部分的主线,除了米歇尔自我成长经历外,还有一条潜在的逻辑线索:非洲裔美国黑人自我身份的建构历程。具体到米歇尔身上,就是她如何将“愤怒的黑人女性”身份转变为“睿智的妻子和细心的母亲”(a brilliant wife and attentive mother)[4]身份。
有关“文化身份”(Cultural Identity)的探究从20世纪初逐渐成为热门话题,体现的是社会各要素历时角力的结果,其建构过程始终处在持续的状态中。以非洲裔美国黑人群体为例,不可抹去的被殖民经历,以及与“贫民窟”“堕落”或“暴力”等固定形象,是西方中心主义者建构其文化身份的常用符码。但这一命名是沉默的被言说过程,并非对整个族群的真实体现,体现了非洲裔美国黑人在面对白人精英阶层时的生存困境以及由此而来的对话困难。具体来看,言说危机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非洲裔美国黑人丧失言说的权利,成为沉默的被言说者。在《成为》第一部分中,米歇尔有意无意地揭露出当时美国社会随处可见的种族歧视现象,以及这种现象背后的身份认同危机。米歇尔出身于早先的奴隶家庭,家中很多长辈虽然不再背负奴隶的枷锁,但却无法摆脱被奴隶过的精神创伤,致使那段“丑陋历史”无法被真正抹去,而是不断地复现在日常生活中。这些种族歧视现象以及由此而来的被边缘化生存状态,不是米歇尔父辈甚至更早一代人所能改变的。如此一来,整个族群身份的言说权利自然落入强势的他者手中,“黑人具有与生俱来的面纱……一种总是依靠别人的眼光来看待自己、总是依靠另一世界的标准去衡量自我的灵魂[5]。”
另一方面,非洲裔美国黑人处于如何主动言说的焦虑中。文化身份不是简单的肤色区别,而是一种不可忽视的过往历史。每个非洲裔美国黑人都背负着一段看不见的历史:“南方不是天堂,对我们却有特殊的意义。先辈在南方的经历深深吸引着我们,它有一种深沉的熟悉感,建立在更深沉也更丑陋的历史遗产之上[6]。”更直接地说,“在我们的背景中可能有另外一个沉重的事实,那就是……奴隶的后代[7]。”这种源自被殖民、被奴役的过往历史,反而成为老一代非洲裔美国黑人自我言说的障碍。某种程度上,摆脱不了过往经历遗留下的集体性心理创伤,是他们无法自立于美国主流社会而普遍采用回避、否认、对抗等生存策略的根源之一。
从结构主义语言学视角来看,文化身份的建构本质上是一种指意行为,是对某一个体或群体具体属性的赋予。语言学家索绪尔对能指与所指的区分,用意就在于强调符号本身不具有实意,而是由内在的所指赋予符号以具体的实意。但当老一代非洲裔美国黑人身处“沉默”状态而失去“发声”权利时,失去的不仅仅是立足于当下社会的机会(因为身份被丑化),更失去了对文化身份进行指意的机会(因为身份被虚构)。因此,文化身份建构的关键不是摆脱、抵制他者言说,而是对自我身份进行主动性言说,通过赋予外在符号以真实可信的所指内涵,从而摆脱那些模式化的表层符号,这也是《成为》第一部分“成为自己”所呈现的主要问题。要想解决这一问题,只靠简单的个体行为恐难以实现,毕竟对某一族裔的刻板印象属于约定俗成的群体性行为,面对普遍化的种族歧视现象时,采取回避的态度既是对集体创伤的延续看不见,也是对言说文化身份的主动放弃。
二、“成为我们”:对固化身份的抵制
如同后殖民主义学者赛义德在《东方学》中阐释西方文化如何塑造东方形象一样,非洲裔美国黑人形象同样处在被他者言说的建构中。“在美国社会结构中,非洲裔的‘黑人性’与主流的‘白人性’相比,前者属于受支配的边缘范畴[8]。”更关键的是,这份被固化、被歪曲的文化身份还被用来强化主流社会的话语霸权,“黑人性”的存在不仅泯灭了族群主动言说的可能,还进一步美化了现实中的种族歧视现象。在《成为》中,米歇尔多处提及已成常态的不对等现象,比如以黑人为主的南岸社区小学里的白人学生越来越少,普林斯顿大学无论白人还是男性都占据绝大多数等。在这种白人至上的种族主义大背景下,少数族裔个体成员的努力行径究其实质不是解决温饱的生存性行为,而是抵制固化身份的革新性行为。
不同于老一代对社会现实的不信任,读者在米歇尔关于自我身份的主动建构行径上,看到了非洲裔美国黑人自主意识的觉醒。“米歇尔·奥巴马与这种刻板印象的关系更多地在于她如何偏离这种刻板印象[9]。”这里的“偏离”,既是消解旧有的所指内涵,也是抵制已被固化的能指符号。这其中,米歇尔关于乘车经历的多处不起眼记述,成为我们窥视她自主意识觉醒的窗口之一。
对于号称“车轮上的国家”的美国而言,“车”是常见的象征符号,既是成功人士的标配,也是融入精英圈子的基本要求。但米歇尔认为,“车”是有待书写的流动符号(如同文化身份一样),既是拓展生活、丰富体验的工具,更是言说自我的自由平台。从米歇尔的记述中可见,早年家中的别克汽车是一家人可以于其中无限放松的私密场所,这种自由自在的氛围,恰是老一代长辈所欠缺的“在场意识”。车外的世界是不可信、不可控的,但在车里,没有任何外界指定的身份标签限制着他们,他们可以自由地彰显自我,可以拥有对自我的绝对可控感。在米歇尔自行搭乘公交车前往学校的中学时期,更大范围的视野与更切身的生存体验更是伴随着车轮滚滚而来,对其个人而言,“车”这个符号的内涵不在于品牌,而在于个体对身份建构的自主掌控,意味着对所指内涵的主动言说。
更主动的抵制行为不仅限于乘车体验,更表现在米歇尔工作以后的各种自主行为。在律师事务所工作时,为了改变非洲裔美国黑人占比不足的现状,米歇尔督促招聘组考虑从其他州立学校或传统黑人学院招聘法学专业学生。再后来,米歇尔不满足于高薪生活的稳定,内心充斥着主动变革的言说冲动:“在内心的某个层面我被吸引住了。我感到另一种刺痛,它在默默地把我推向一个与我计划中完全不同的未来[10]。”显然,从积极建构文化身份来看,类似行为的践行不是为了满足私人目的,而是为了推广族群文化以及提倡多元文化,凸显对固有身份的抵制意识。
米歇尔的丈夫贝拉克·奥巴马正是一位文化身份充满建构性的人物,其父亲是肯尼亚黑人,母亲则是地道的美国白人,自己出生于夏威夷,成长于印度尼西亚,后在美国本土上学,同胞姐妹散布于不同大洲。这种文化背景的多元化造就了奥巴马身份意识上的多元与包容,以及对固化身份的坚决抵制态度。“贝拉克大部分时候都是在跟人们——尤其是黑人——内心的那种极度的疲惫感作斗争,那是从过往成千个不如意的事情中滋生出的愤世嫉俗[11]。”在其丈夫的影响下,米歇尔更加明确地意识到非洲裔美国黑人对固有文化身份的抵制、主动意识的建立要比单一个体的成功更重要,毕竟单一个体的身份塑造离不开群体身份的搭建。这种不断提升的主动意识,或是“成为我们”对于非洲裔美国黑人文化身份建构的意义所在。
既然文化身份不是绝对固定的,也不是由拥有话语权的强势他者最终确定的,那么,偏离或抵制就成了觉醒的表现:“要么放弃,要么去努力改变……我们是要安于这个世界的现状,还是努力让世界变成它本应该有的模样[12]?”任何力图将少数族裔身份固定化、模式化的抹黑行径,都既是一种本质主义的思维定式,也是一种殖民主义的话语霸权。所以当米歇尔为“愤怒的黑人女性”耿耿于怀时,当奥巴马力图摆脱“出生地不明”的困扰时,他们所做的都不是简单地解决具体的个人问题,而是消解固化的“非我”身份,抵制渐成体制性顽疾的种族歧视主义。因此,当米歇尔与奥巴马成为美国第一对黑人总统夫妇时,其意义在于这是对非洲裔美国黑人固化身份的重大反驳,不仅实现了马丁·路德·金多年来的“未尽的梦想”[13],更有效地“降低了美国的种族主义倾向”[14]。
如此看来,“成为我们”不单单是指米歇尔与奥巴马成为一对情投意合的伴侣,更隐喻着非洲裔美国黑人自主意识的觉醒。从过去的沉默,到逐渐的觉醒,从个体的努力,到更多人的共同面对,那种依附单一个体的努力而取得的暂时性改变,逐渐成为志同道合的共同努力。相比老一代绝对而又被动的沉默,新一代的成长意味着非洲裔美国黑人摆脱固化“身份”的群体性行为成为事实性可能。此时的“成为”虽然并不意味着绝对的成功,但至少意味着“抵制”与“破除”,而它们必然蕴涵着真正的群体性成长。
三、“成为更多”:对族群身份的重构
“作为历史上第一位住进白宫的非洲裔第一夫人,我被默认是‘另类的’。假定我之前的历代白人第一夫人的恩泽和权利被默认是与生俱来的,那么,对我来说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在经历了总统选举一路上的各种磕磕绊绊之后,我清楚地知道,现在的我必须要比过去更加坚强,要行动更快、做得更好。我的恩泽不是天生的,而是需要我去打拼才能获得的[15]。”不懈的打拼精神贯穿着米歇尔的成长历程,赢得的不仅是个人的物质成就,更重要的是对固化身份的不断消解。在《成为》第三部分“成为更多”中,米歇尔充分利用成为第一夫人的机会,将自我言说扩大为族群言说,为推进整个非洲裔美国黑人群体的文化身份建构而不懈努力。
与老一辈身份建构的经历(沉默于被言说、焦虑于无法言说)相比,米歇尔的第三部分记述从这两方面展现了群体性建构行为:其一是摆脱被他人言说的沉默地位;其二是学会群体性共同言说。“在她们能够自我定义之前,就有人以各种方式去给她们去定义。她们必须抵抗这些刻板印象和来自他人的定义。她们必须进行反抗,让自己不因贫穷、性别以及肤色而被忽略。她们必须努力发出自己的声音,争取她们的话语权并保持其不被削弱,从而保证自己不被打倒[16]。”由于言说权利的丧失,老一代非洲裔美国黑人被动接受的固化身份总和“贫穷”“暴力”等符号关联,而新一代米歇尔们的奋斗行为则是对非洲裔美国人群体身份的主动彰显,与其被动地被建构、被固化,不如主动地言说、重塑,少数族群才不会再深陷于沉默的边缘地位。
任职第一夫人期间,米歇尔一直致力于将一种更平等、和谐的种族多元关系带入现实,改变国内复杂的种族歧视主义与仇外心理。比如刚进入白宫时,米歇尔主持的“一起行动”(Let’s Move)活动号召全国人民共同支持儿童健康饮食事业,甚至不惜亲自动手在白宫开辟菜园。这一活动是“面向全国的倡议”[17],既着眼于对儿童健康成长的关注,也力图打破阻碍交流的社会屏障,让不同种族、肤色的人们参与进来,进而达到弥补种族隔阂的间接目的。“学校是一个可以定义自己人生的地方……教育能帮助我们走向更远的未来[18]。”所以,米歇尔不遗余力地前往各地学校发表演讲,呼吁更多人对不同种族接受同等机会的教育事业予以支持。
另一方面,集体性共同言说意味着在现实处境下,非洲裔美国黑人拥有对外言说的共同根基。这一根基并非来自外在世界,而来自整个族群的“隐藏的历史”(hidden history)和“潜在的共性”(underlying unity)。老一辈在面对不同文化的碰撞时往往选择回避或忽视,仿佛那份略显丑陋的被殖民史不曾存在一般。但文化身份的“建构”不仅意味着对旧我身份的突破与重建,亦包含了对过去的承认与重塑:“作为想象共同体,它(民族身份)又须依赖本民族的文化传承,确保其文化统一[19]。”之于非洲裔美国黑人,那份源自历史的种族记忆并未完全消失,依然是族群身份的重要拼图。因此,在新时代的族体身份重建中,既应强调非洲裔美国人采取积极的言说行径,也应承认或澄明族群原有的历史底蕴与文化传统。从书中细节可见,米歇尔坦诚对其影响最深的仍是非洲裔族群,而非主流社会标榜的经典范例。之前备受湮没的民族历史与传统得以真正显现,而这份显现对于整个族群而言,恰是言说自我的开始。
文化研究学者斯图亚特·霍尔认为文化身份既有历史源头,也在不断变化,“它属于过去也同样属于未来[20]。”由于文化身份建构本身是持续的过程,没有绝对被固定的时候,因此,弗朗兹·法侬笔下那种“没有落脚地、没有视野、无色、无国、无根的种族[21]”要想从沉默的边缘地位觉醒起来,有关族群身份的持续性言说就必须不断进展下去。对此,以米歇尔为代表的新一代非洲裔美国黑人自信地表述道:“我经历得越多、越深入,就会越加大胆、坦诚、直接地讨论种族和性别问题[22]。”言说不再是隐秘的被动隐喻,而渐成集体性公开讨论,沉默不再是多数,更多非洲裔美国黑人将会觉醒,共同参与有关族群身份的主动言说。
作为非洲裔美国黑人后代,米歇尔关于本民族及身份建构的记述具有流散书写(diasporic writing)的特质。作为社会边缘的外来移民群体,非洲裔黑人的族群意识及文化身份长期在美国主流文化中呈现出被刻意丑化的状态。社会不应视其为扰乱美利坚民族“纯洁性”的不良分子,而应意识到“流散现象直接促进了民族、种族和文化的融合”[23]。从最初的集体缺席、失声以及被言说,到单个个体对固化身份进行积极抵制,再到更大范围地对族群身份的积极建构或彰显,具有流散书写特质的《成为》呈现了非洲裔美国黑人文化与主流文化之间的对话历程,以及多元主义观念对单一性理念的对抗历程。
诚然,“当下美国并没有真正进入所谓的后种族主义时代”[24],非洲裔美国黑人重新建构整个族群的文化身份不会是一帆风顺的过程,真正持续下去的正是不断建构、不断言说的行为本身。简言之,种族歧视主义的彻底消除,或多元文化的真正共存,目前看来仍旧是遥远的理想彼岸,但不断的“成为”应是永不放弃的建构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