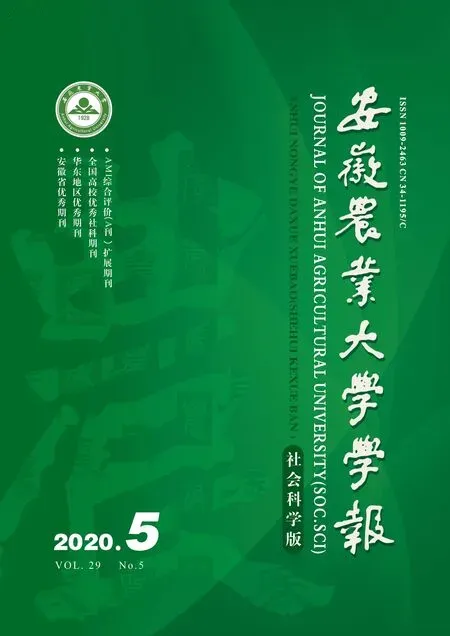禁锢与关怀:徽州建筑遗存的女性主题演绎*
陈 泓, 罗云云
(安徽大学 艺术学院,安徽 合肥 230601)
在人类的艺术想象和艺术创造中,女性题材总是以不同的形式生长于各类艺术作品之中,从绘画与雕塑一类的精英艺术到乡土建筑装饰等民间艺术,莫不如此。徽州建筑深受地域环境、封建礼教和宗族社会的影响,形成了独特的建筑类型、建筑形态以及聚合方式,目前,徽州地区保存地面文化遗存11 000余处,明清古村落100余座,古建筑7 000余栋[1],类型丰富,其中祠堂、牌坊和民居,更是被称作“徽州古建三绝”,闻名于世。然而,正是在这如画般的徽州建筑中曾经生活着的徽州女性,深受封建礼教的禁锢、宗族制度的束缚、纲常人伦的压抑,但又走不出这深深宅院。一方面,她们受到重重限制,另一方面,徽州建筑已然成为她们无法摆脱的安居之所。徽州建筑类型、形态、空间组织方式以及装饰等在展现徽州建筑艺术美的同时,也体现了对徽州女性精神、思想和行为的禁锢和关怀,折射出明清时期徽州女性的社会地位和生活状况。
一、 牌坊与宗祠——封建礼教的纪念碑
(一)贞节牌坊
徽州地区历史上有各类牌坊1 000余座,现存130余座[2],而“贞节牌坊”便占据了其中半数,据嘉靖十五年《绩溪县志》记载,为贞妇烈女们建造的贞节坊便有八十多座[3]。与此同时,徽州各地方志谱牒中,对于贞妇烈女及其事迹,也有大量记述。民国《歙县志》16卷,其中记载烈女竟占据了其中4卷,同治《祁门县志》记载烈女2 839名,可见徽州地区对女性守节的重视[4]。徽人赵吉士曾写道:“新安节烈最多,一邑当他省之半。”[5]而贞节牌坊正如一座座纪念碑,诉说着封建时期徽州女性悲惨的命运和压抑的生活状态。
徽州多节烈,与其文化与社会环境密切相关。程朱理学将就理灭欲的封建礼教对女性的束缚推向顶峰,严格要求并鼓励女性从一而终,恪守妇道。而徽州堪称“程朱阙里,理学之乡”,程朱理学在徽州地区影响之深,不言而喻,因此,徽州女性在理学盛行的环境下生存,唯一能做的只有遵理学之教,守贞洁之名。
宗族制度也是促成徽州节烈之风盛行的重要原因。徽州地广人稠,生存压力促使徽州先民不得不走出深山以谋生计,久而久之,形成雄踞一方的徽州商帮。然而,“商必远出,出恒数载一归,亦时有久客不归者,新欢之别,习为故常”[6],徽州男子普遍外出,势必形成数量庞大的留守女性群体。无论是出于个人、家庭或是宗族的利益,都必须保障徽商集团后方的稳定,因此,徽人极其重视对徽州女性传统道德的教育和规范,借助宗族势力,极力宣扬女性贞洁观念,从现存的徽州文献中可以看到,家法和族规中所涉及女性道德规范的条款极多,对女性的一言一行都有极其严格的要求。徽商和宗族也毫不吝惜,耗巨资修建贞节牌坊,以表彰守节的贤妇烈女,宣扬贞节观,也为有志守节的徽州女性提供精神和物质上的支持。
当我们仔细审视这一座座宏伟的石坊,欣赏着石坊上精美绝伦的雕刻,品读着“节孝流芳”“节劲三冬,脉有一线”“贞心矢日,劲节凌风”这些褒扬的词句时,却发现透过这些石坊,我们无法知道这些伟大又可悲的女性的事迹,甚至她们的真实姓名,石坊上仅刻有“吴氏”“汪氏”等家族姓氏,有的石坊甚至连节妇的从父姓都未曾提及,如休宁县富溪村“富溪节孝坊”等,可见徽州女性在“男尊女卑” 观念严重的封建社会地位的卑微。而这些褒扬的辞藻,更像是纪念碑式的口号,除了颂扬石牌坊后的节妇烈女,更多的是在宣扬和鼓励守节这一行为,而修建一座贞洁牌坊,需朝廷颁布圣旨,且耗资巨大,绝不是普通人家能够完成的,此时,它的存在又是显耀拥有贞节牌坊的家族势力和财力的大好机会。修建贞节牌坊,绝不仅仅是为那些苦命的徽州女性树碑立传,更重要的是为其家族增容添光。
清道光十八年,婺源县城建成一座孝贞节烈坊,旌表自宋朝以来的贞洁烈女两千六百五十八人,而到了光绪三年重建时,旌表的人数已增加至五千八百余人[7]。光绪三十一年,设立在歙县的徽州府城所建的一座孝贞节烈牌坊,样式简陋,材料寒酸,额枋上镌刻了“徽州府属孝贞节烈六万五千零七十八名”,可见,只有那些富可敌国的徽商家族才有可能建造起属于自己家族的牌坊[8]。它们存在的目的更是向后世的徽州女性传达一个明确的信号——“笃礼宗义,抱淑守贞”,此时的贞节牌坊,便如一件件沉重的枷锁,束缚着徽州女性的精神与思想。
(二)徽州女祠
歙县棠樾村现存一座女祠“清懿堂”,坐南朝北,规模宏大,装饰也相当精美,三进五开间,面阔18.9米,进深48.4米,规格与鲍氏男祠“敦本堂”大体相当[9]。 “清懿堂”为清嘉靖年间鲍氏第二十四世祖鲍启运和鲍有莱主持建设,建造原因则是“家祠旧奉男主,未附女主,遗命其子有莱重建女祠”,旨在颂扬母德[10]。鲍启运更是捐义田一千二百亩,在女祠西侧建“四穷仓”,专门救助族内“鳏、寡、孤、独”四类穷人,鲍志道夫妇亦购置义田入女祠,自此,女祠专祀节烈、孝贞的鲍家女性牌位。徽州地区建女祠较为罕见,但“清懿堂”绝非孤例。现今遗存或有文字记载的包括歙县潭渡村黄氏宗族的“黄氏享妣专祠”、歙县呈坎村罗氏宗族女祠、休宁县黄村黄氏宗族女祠、祁门县渚口倪氏宗族“庶母祠”等。《歙县志》所载的官办女祠也有两处,“其一在县城上路街,雍正元年建祀,历旌节烈;其二在府城南街参将署左,为光绪三十一年知府黄曾源购民宅为之”[11]。此类女祠,与今日纪念碑作用相仿,供人们瞻仰、怀念,然而因其专于旌表节烈女性,从而宣传女德、宣扬节孝的作用亦非常明显,对女性精神和思想上的束缚也相当严重。从女祠的建置中,我们却也能窥见对于徽州女性的人文关怀。明清封建社会的徽州,除“男尊女卑”外,“长幼有序”的伦理观也发挥着巨大的作用,而在视“程朱理学”为圣典的徽州,尊孝道极受推崇。关于祠祀,朱熹在《家礼》中有所记述,祠堂内既供奉男祖先主神,又供奉女祖先主神,因此,绝大多数的徽州祠堂,均同时供奉男祖和女祖先主神。但也有例外,如棠樾之所以兴建“清懿堂”,正因为“家祠旧奉男主,为附女主”,其子为报母恩,兴建女祠,这也是徽人重孝道的体现。而《潭渡黄氏族谱》记载,康熙年间,潭渡黄氏兴建女祠,其中《新建享妣专祠纪略》中写道:“吾乡僻在深山之中,为丈夫者,或游学于他乡,或服贾于远地,尝违其家数年,数十年之久,家之绳勉维持,惟母氏是赖,凡子之一身,由婴及壮,抚养教诲,从师受室,以母而兼父者多幼稚,母氏之恩何如其重耶!正持幼母慈,长承母训,以有今日” ,但“切见吾乡设立宗祠,敬祀其先,统之以鼻祖,于报本追远之意可云得矣,然多祀祖,而不及妣。蒸尝时祭,子孙入庙,顾瞻座位,母氏之主咸阙如,于私心每有未安者”①。为弥补这个缺憾,潭渡黄氏宗族“庀材鸠工”,建造了“潭渡黄氏享妣专祠”。“报本之礼,祠祀为大”,黄氏建造女祠,更多体现的是孝道,以报慈母养育之恩。徽州女性历尽艰辛,也能聊以慰藉。呈坎罗钦梅体恤母亲不能入宗祠,甚至敢冒“再嫁者不准入祠”的族规,另辟专祠供奉其母,并未受到宗族惩戒,也体现出“孝”在徽人心中的地位。祁门渚口倪尚荣侧室金、王二氏,“善承大志”,受到族人高度赞扬,倪氏冒“庶母不可附祠堂”的族规,兴建“庶母祠”以纪念,受到族人的拥护[12]。由此可见,徽州女性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和家庭环境中,能够取得一定的社会地位。然而,一个普通的徽州女性,为获得如此荣光,需要历尽多少苦难,是我们难以想象的。女祠的设立,让我们看到了徽州女性的价值,但寥寥数座女祠,始终难以改变徽州女性的社会地位。歙县呈坎村的“贞靖罗东舒祠”中,有一座女祠依附,称为“侧内”,三开间,面阔9.14米,进深19米,高7.8米,面积约180平方米,与规模宏大、装饰精美的贞靖罗东舒祠相比,女祠规模不值一提,且几乎没有雕刻和彩绘,可见明清时期封建社会下徽州“男尊女卑”的观念是根深蒂固的。而当我们步入女祠,会发现所供奉的仍旧是孝贞节烈的徽州女性,她们用一生的幸福,才换取这祠堂中的一席之地。
巫鸿在《中国古代艺术与建筑中的“纪念碑性”》中写道:“一座有功能的纪念碑,总要承担保存记忆,构造历史的功能;总力图使某个事件,某种制度不朽,总要巩固某种社会关系,或某个共同体的纽带,总要成为界定某种政治活动的或礼制行为的中心。”[13]徽州的贞节牌坊和女祠,正是承载封建礼教和宗法制度的纪念碑,而徽州女性,则是这座纪念碑背后的牺牲品。
二、民居与宅院——徽州女性的精神家园
在封建礼教和宗族制度的影响下,徽州民居呈现出内向性封闭院落的空间格局,它的设计和建造,也反映出一系列针对女性的制约。
《礼记》有载:“七岁,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始诵孝经、论语,虽女子亦宜诵之。七岁以下谓之孺子,早寝晏起,食无时。八岁,出入门户,即席饮食,必后长者。始教之以廉让,男子诵尚书,女子不出中门。”[14]这种沿袭千余年的男女有别、男尊女卑的礼制思想,对古代的建筑形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中国传统建筑呈现“前堂后室”的居住格局,礼制和宗法制度极其严苛的徽州民居自然也不例外,稍有规模的宅院,便可形成明确的“前堂(厅)后室(院)”的空间格局。明朝杨继盛在《杨忠憨公遗笔》中写道:“居家第一要紧处在于内外界限要严格,女子十岁不能出中门,男子十岁不可进中门。”[15]可见内外之别的严格程度。未出阁的少女闺房,多置于建筑二层,是整个建筑私密性最强的空间。在崇尚程朱理学的徽州,绝大多数女性七岁之后,唯一的宿命便是待字闺中,等待自己的婚姻。若要嫁于好人家,除门第之外,女子的自身素养也很重要,徽州各族深受程朱理学影响,都非常重视对子女的教育,即使男女有别,也只不过受教育内容有所不同。徽州少女在出嫁之前,轻易不会下楼,整日都在闺房内操习女红,学习琴棋书画,为日后的婚嫁做准备。《绩溪华阳邵氏宗谱·先儒家训》记载:“……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娩听从,执麻枲,治丝茧,织紝组紃,学女事以共衣服。观於祭祀,纳酒浆笾豆菹醢,礼相助奠。十有五年而笄,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年而嫁。”②可见封建礼教对女性日常教育的严苛。少女们唯一接触外界的便是与闺房相连的一方天井,大户人家还会围绕天井建造“跑马廊”,如此一来,便大大增加了女子的活动空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一做法也不失是对徽州女性的一种关怀。也有在“跑马廊”靠天井一侧设置“美人靠”的,想必,少女们倚靠于此,“坐井观天”之时,是她们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吧。而闺房与厅堂之间的联系,也处理得非常巧妙,常用雕刻精美的格栅窗分隔,由闺房内可清晰地观察到厅堂,厅堂却无法窥见闺阁之内。黟县西递村“桃李园”,建于清咸丰年间,十分罕见地在临街转角处设一绣楼,辅以“美人靠”,这种设计在徽州地区是非常开放的做法。由于村落中街巷狭窄,路人看不到绣楼内的情形,相反,绣楼内的人却可以自上而下鸟瞰全村景致。这既确保了绣楼的隐私,又扩大了绣楼的视野,给深处闺阁的少女们提供了更多的生活趣味。
出嫁后的女性,面临更加严苛的束缚,在建筑创作中也有体现,甚至表现在对女性的称谓上,如“正室”“偏房”等,而在建筑空间组织中,表现则更加明显。墨子有言:“宫墙之高,足以别男女之礼。”[16]徽州民居采用内向性的格局,建筑外立面,是清一色的高大封闭的风火墙,向内开窗,建筑外侧开窗极少,甚至不开窗,即便开窗,也在极高的位置,足以限制视听,阻隔建筑空间内外联系,功能上满足了防火防盗的需求,也体现了对徽州女性日常活动的限制和禁锢,进而保障了徽商常年在外,妻子独自留守徽乡时,必须恪守妇道纲常的需要。
在徽州,往往身份地位越高的家族,对女性的限制也越严格,有关的族训家规数不胜数,婺源《王氏家范十条》“别男女”规定:“《易》之家人卦口:‘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内,男女正,天地之大义也。至哉,圣人之言。盖天地之风化始于闺门,若不先正以男女,则家风何以厚哉?男子出入宜行左,女子出入从右,违者罚在本房族长。”[17]72黟县《余氏家规》“辩内外”规定:“闺门内外之防,最宜严谨。古者,妇人昼夜不游庭,见兄弟不逾阈,皆所以避嫌而远别也。凡族中妇女,见灯毋许出门,及仿效世俗,往外观会,看戏,游山,谒庙等项,违者议罚。”[17]161歙县《潭渡孝里黄氏家训》也有规定:“奉化肇始闺门,各堂子姓当以四德三从之道训其妇……并不得出村游戏,如观剧,玩灯,朝山看花之类,倘不率教,罚其夫。”③由此可见,徽州宗族对女性的要求就是孝顺公婆,相夫教子,和睦妯娌,目的便是将其困于闺阁之中,断绝其与外界的联系。徽州女性的生活空间被限制在宅院的后堂之内,就是人们常说的“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司马温在《居家杂仪》中关于住宅“内外”的记述:“凡为宫室,必辨内外。深宫固门。内外不共井,不共浴室,不共厕。男治外事,女治内事。男子昼无故不处私室,妇人无故不窥中门。男子夜行以烛。妇人有故,出中门,必拥蔽其面,如盖头面帽之类。男仆非有缮修,及有大故,谓水火盗贼之类,不入中门。入中门,妇人必避之。不可避,亦必以袖遮其面。女仆无故,不出中门,有故出中门,亦必拥蔽其面。”[18]徽州民宅以厅堂太师壁为界,划分为前厅和后堂,太师壁两侧各有一扇门联通后室,此处便是中门,女性的生活空间被牢牢限定在中门以内,后室之中。女性不可轻易出入“大门”和“前厅”,因此,徽州民居均设有“后门”“偏门”,内部空间的组织中,也都专门设计了女性的专用通道,且十分隐蔽。而两侧厢房入口避开厅堂,由“退步”相连,退步于厅堂之间设置雕刻精美的格栅门,与厅堂四周的装饰融为一体,便将厢房入口巧妙隐藏起来,如此一来,徽州女性不必经过厅堂,便可以在家中自由活动。这样的设计,既满足了男女内外有别的礼教和宗族要求,也为女性在家中的活动提供了方便,也不失是一种相当合理和人性的做法。
徽州行商者众多,常年在外,对家中留守女性做出一定限制,也是可以理解的,徽商家中常见一种“半月桌”,布置于厅堂显著位置,如男主人在家中,则拼成圆桌使用,若男主人外出,则仅摆设半月桌,如有宾客到访,只要见到半月桌,便会自行离去,以减少不必要的误会。
徽州女子绝大部分的活动是在室内完成的,妯娌们常常聚集在后堂天井下聊天或者做家务,天井成为宅院中最重要的公共空间,也是家族内部联系的重要纽带。而更多的时间,徽州女性只能独处私室,以九连环来熬过长夜。清末宏村映月楼主人有《商人妇》词三首,其中《行香子·寄香囊》写道:“镇日兰房,静修鸳鸯,有余闲,制个香囊,正逢邮使,密寄檀郎,莫与人知,与人说,与人望。他人识得,问君索去,到斯时,笑话难当,休藏箧里,佩在身旁,只自家看,自家玩,自家香。”[19]从词中,我们可以读出一个徽州女性的无奈,窥见封建礼教和宗族制度对徽州女性的束缚。
一些规模宏大的徽州民居中,常常在后院兴建私家花园、水园,如宏村德义堂等,其间广植草木,置盆景,养花、鸟、鱼、虫,为森严的建筑平添几分自然气息和人文趣味,也为家族中女性的日常生活增添了一些活动空间和生活情趣,也体现了对徽州女性的一丝关怀。
三、雕刻与装饰——妇德教育的图像之书
徽州建筑精于雕饰,其中被称为“徽州三雕”的木雕、砖雕、石雕最富盛名,常散见于建筑的梁枋、斗拱、雀替、门罩、隔扇门窗等各个部位,此外,常见于天花板的仰顶彩绘也十分精美,雕饰的工艺精湛,题材丰富多样,集中体现了徽人独特的审美观念和价值取向。其中有关徽州女性题材的建筑雕饰也很常见,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徽州女性的社会地位、价值取向和审美情趣。
在极力推崇程朱理学的徽州地区,徽州建筑雕饰中,传达“忠孝节义”的儒家思想的题材,最为常见。“节孝”的图像内容,多是针对徽州女性的妇德教育,鼓励他们侍奉公婆、相夫教子、恪守妇道等,也起到控制徽州女性思想的作用。卢村志诚堂过厢格栅门裙板雕刻了“唐妇乳姑”等二十四孝故事;棠樾女祠清懿堂枋上开光雕刻“跪拜母恩”的故事,以褒扬女性哺育子女伟大,类似宣扬妇德的图像比比皆是。徽州先民正是通过建筑雕饰这本图像之书,传达作为徽州女性应有的基本素质和要求。
祈求美好爱情,是徽州女性终其一生的愿望,在建筑装饰中也有所体现,常见的题材有“凤穿牡丹”“百鸟朝凤”“双凤朝阳”等,如黟县南屏一座民宅门罩上石雕“百鸟朝凤”,非常精美;婺源李坑大夫第雨搭板雕刻“凤穿牡丹”;婺源江湾萧氏祠、曹溪振源堂、宏村春晖堂厢房天花,均以木雕或彩绘形式装饰了“双凤朝阳”图像,以显示“夫贵妻荣”。徽州民居常在雀替上雕刻“和合二仙”,以祈愿婚姻美满,家庭和睦。而隐喻美好爱情生活的花、鸟、蝴蝶的组合图像,也极为普遍。宏村振绮堂格栅门涤环板上雕刻了《西厢记》戏文故事,表达了徽州女性对美好爱情的渴望。歙县黄村一座民居格栅门上雕刻了一幅《商旅归乡图》,画面中,男人身背包袱,夹着雨伞匆匆而行,女人则倚在门边翘首以盼,神情哀伤忧怨,这正是徽州女性婚姻和爱情生活的写照。
繁衍子孙也是徽州女性不可逾越的话题。徽州建筑雕饰中,有关生殖崇拜的题材也非常常见。宏村承志堂后堂冬瓜梁上雕“百子闹元宵”,卢村志诚堂的格栅门涤环板上雕刻了“百子闹春”,都是对儿孙满堂的美好祈愿。“麒麟送子”也是极为常见的图像,表达了徽人求子的殷切期望。而其他反映生育主题的图像也有很多,如“瓜瓞(蝶)绵绵” “松鼠戏葡萄”常配合建筑构件出现在格栅门、挂落等处,寓意子孙绵延久长;而多籽、宜生长的葡萄、石榴、芡实、南瓜、葫芦等植物形象,也常出现在徽州建筑中作为装饰,如宏村承志堂后堂装饰有大型葡萄挂落,作为生育崇拜的主题,隐喻多子多孙,多子多寿。
综上所述,徽州建筑通过多元化的装饰主题,对女性的精神、道德、思想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强调了女性为家族传宗接代、繁衍子嗣的重要作用。同时,也从女性的角度表达了对幸福美满的爱情与婚姻生活的渴望和追求,体现出对女性的些许关怀。
四、结语
徽州男性成年之后,大多外出谋生,婚后也常年栖居外地,徽州女性却要留守徽乡,独守空房,更要承担起侍奉公婆、教育子女的重任,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徽州女性才是家中真正的主人。然而,徽州女性却生活在封建礼教和宗族势力的重重压迫下,无法逾越男尊女卑的社会秩序,而她们生活的主要空间,也处处受到规范和限制,民居中的闺阁绣楼、厅堂间的夹道退步、梁枋上的雕刻彩绘,连同徽州城乡随处可见的贞节牌坊和女祠,共同诉说着贞节烈女凄婉悲凉的故事。同时,徽州建筑亦不断做出尝试,默默关怀着徽州女性从生活起居到精神需要等方方面面的诉求。它们承载着徽州女性的生活愿望、伦理观念和价值取向,是徽州女性特殊的文化符号,为徽州女性文化的研究,提供了丰富且具体的物质遗存。
注释:
①《潭渡黄氏族谱》卷六《祠祀·新建享妣专祠记略》,安徽省博物馆藏。
②宣统《绩溪华阳邵氏宗谱》第18卷《先儒家训》,安徽省博物馆藏。
③雍正《潭渡孝里黄氏家训》第4卷《家训》,安徽省图书馆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