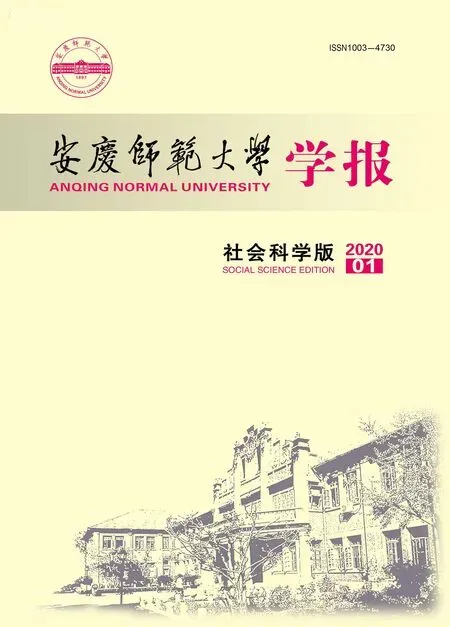方以智“中边言诗说”论
宋豪飞
(安庆师范大学文学院,安徽安庆246011)
一、明代“格调说”要旨
明代诗学理论最有影响的当属“格调说”。“格调说”为茶陵派领袖李东阳所首倡,至弘治时期,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相承袭且有所发展,郭绍虞先生即指出:“由格调说言,李东阳可说是格调说的先声,李梦阳可说是格调说的中心,何景明则可以说是格调说的转变。”[1]367再迨至嘉靖朝,以李攀龙、王世贞为代表的后七子继之而起,皆尊崇此说,奉为圭臬。“格调说”成为明代中叶以降诗坛诗学理论的核心范畴。
李东阳倡导“格调说”的理论内涵:首先,重诗体,诗歌要合乎体裁,依其诗格而作诗。李东阳认为:“古诗与律不同体,必各用其体乃为合格。”[2]529其次,重“格”“调”,即从诗法、声律等方面论诗。《怀麓堂诗话》:“诗必有具眼,亦必有具耳。眼主格,耳主声。闻琴断知为第几弦,此具耳也;月下隔窗辨五色线,此具眼也。”[2]530他取“眼”“耳”譬喻“格”与“调”。所谓“格”,意指诗歌的字句结构、表现手法等形式、法则方面,犹如月下眼之可辨五色线一般;所谓“调”,是指诗歌的声音节奏、音调抑扬等音律声调,乃耳之可听可辨者。在“格”“调”二者中,李东阳更看重“调”,强调诗歌的本质特征在于诗歌具有音乐性。
李东阳此说为明代诗坛所接受。前七子领袖李梦阳极力“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明史·文苑列传二》),掀起声势浩大的诗文复古运动,以汉魏和盛唐诗为创作典范,以“格调说”为其理论支撑。他提出“文必有法式,然后中谐音度,如方圆之于规矩”(《答周子书》)[3]449,即重视诗文法度格调。在《驳何氏论文书》中这种观点阐述得更为明确。李梦阳于诗文创作主张复古,主要是针对当时文坛盛行的虚饰雍容萎靡的台阁体而言,故而强调诗文自身的审美艺术特质,从“格调”入手以达到复归文学本性的目的。他坚持强调从“格调”方面刻意模拟汉魏、盛唐诗歌,恪守“圆规而方矩”的诗法规则,以致深陷拟古之泥沼却不自省。究其原因,郭绍虞先生认为:“他要于诗文方面复古,而不是于道的方面复古。易言之,即偏重在文之形式复古,而不重文之内容复古。因此,他的复古论终究偏在格调一方面。”[4]167可谓一语中的。
与李梦阳固执于“规矩”以为“法”不同,何景明在学习古人创作的同时较为注重革新。他在《与李空同论诗书》中说得明白:“追昔为诗,空同子刻意古范,铸形宿镆,而独守尺寸。仆则欲富于材积,领会神情,临景构结,不仿形迹。”[5]575何氏力求领会古人的神情,以期根据描写对象来构思作品,“不仿形迹”。李、何二人缘此相争,竟至反目,然二人论诗本于格调,却是一致,但何景明的这种革新意识很显然接橥“格调说的转变”。只是这种“转变”并未持续发展下去,也未能成为文坛的主导思想。及后七子主宰文坛,其领袖人物李攀龙极其推崇李梦阳,几乎全盘吸收其复古主张和“格调说”。王世贞主盟文坛,所著《艺苑卮言》,从根本上说,亦重在研究古法,为复古指明路径。“诗有常体,工自体中”[6]40,强调各体诗文的法度,包括字法、句法、篇法、声律等,“首尾开合,繁简奇正,各极其度,篇法也。抑扬顿挫,长短节奏,各极其致,句法也。点缀关键,金石绮彩,各极其造,字法也。”[6]38要求诗人在诗歌创作时要严格遵守规范,讲究格律法度。
及至明末,方以智以“中边言诗”论诗歌创作,亦是遵循“格调说”理论,并对“格”与“调”的内涵进一步深化,论述更为详赡周全。方以智“中边言诗说”可视作明代“格调说”诗学理论的最为系统的阐发和最后总结,值得重视。
二、“中边言诗说”对“格调说”的遵循与阐发
方以智是明末清初著名的哲学家、科学家、文学家、书画家等,博学多才,在诸多领域成就显著,被视作十七世纪百科全书式的大学者。作为诗人,他不但创作有大量的诗歌作品存世,而且还写有《诗说》专文(《通雅》卷首三),系统地阐发其诗学思想。本文仅就其诗学思想“中边言诗说”展开探讨,以究其实,以申其义。
方以智以“中边言诗”谈论诗歌创作的根本问题,其论诗先尊“诗体”,其次谈字法、句法和形式、声律等问题,即谈“格”论“调”,遵循“格调说”的理论主张。
其《诗说》开篇即写道:
姑以中边言诗,可乎?勿谓字栉句比为可屑也。从而叶之,从而律之,诗体如此矣,驰骤回旋之地有限矣。以此和声,以此合拍,安得不齿齿辨当耶?落韵欲其卓立而不可迻也,成语欲其虚实相间而熨帖也。调欲其称,字欲其坚。字坚则老,或故实,或虚宕,无不郑重;调称则和,或平引,或激昂,无不宛雅。是故玲珑而历落,抗坠而贯珠,流利攸扬,可以歌之无尽[7]55。
方氏认为,诗歌创作首先要明确“诗体”,诗歌创作要合乎“诗体”,受诗歌体裁的束缚。“诗体如此矣,驰骤回旋之地有限”,只有在符合诗歌体裁规范的前提下,诗人方可纵横自如、逞才使性施展才华,若淆乱“诗体”则无从“言诗”,更谈不上作诗。
诗体既明,诗歌创作须讲求“格”“调”,不但要重视字法、句法,锤炼字句,而且还要注意韵调,讲求声律。他说:“勿谓字栉句比为可屑。”对于像梳篦齿那样密密排列的字句,我们不可以认为过于琐屑而不加重视。诗歌写作要讲究“字栉句比”,一字字比较,一句句梳理,字敲句炼。那么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呢?方氏指出,这就要把握两点:一是在词语的选择、搭配上要“叶之”,即要和洽、合韵;二是在用韵、节奏上要“律之”,即要合乎音律规则。做到这两点,也就基本达到了“诗体”的要求。诗歌创作必须“以此和声”“以此合拍”,符合平仄和节奏音律的基本规则,这样创作诗歌才称得上“齿齿辨当”,即词语的相合、押韵得以仔细辨别而明确妥当。如果诗句中用词出韵,“落韵欲其卓立而不可迻”,但因使用该字词显得“卓立”而不可更换;“成语欲其虚实相间而熨帖”,某些“成语”的运用达到了“虚实相间”的效果反而更加贴切,方氏认为,这是可以接受的。这也反映出他论诗并不死守格律法度,有其灵活变通性。由此可知,方氏论诗歌创作,在尊“诗体”的前提下,重视诗歌词句的锤炼和格律的要求,这是诗歌创作最根本的法则。
众所周知,中国古典诗歌与音乐的关系极其密切,“诗”与“歌”二者的合称,就包含着“诗”具有可“歌”的本质特性,而“歌”之腔调圆润、抑扬顿挫等则是通过“调”体现出来,因此中国古典诗歌理论多有论“调”之言。上文论及,李东阳“格调说”就突出强调了诗歌的音乐性,而方以智“中边言诗说”也持论相同。李东阳《怀麓堂诗话》写道:“后世诗与乐判而为二,虽有格律,而无音韵,是不过为排偶之文而已。使徒以文而已也,则古之教,何必以诗律为哉!”[2]529“观《乐记》论乐声处,便识得诗法。”[2]532将“乐声”与“诗法”联系起来,是对诗歌与音乐紧密关联的正确认知。
注重诗歌的声调节奏,这揭示了诗歌创作要合乎“调”且能“歌”的内在属性,表明了诗歌具有音乐性的特征。对此,方以智就认为:“字坚则老,或故实,或虚宕,无不郑重;调称则和,或平引,或激昂,无不宛雅。是故玲珑而历落,抗坠而贯珠,流利攸扬,可以歌之无尽。”诗歌创作上运用字句的根本要求就是要做到“叶之”“律之”,从而“和声”“合拍”,而要做到这一点,还要“调称”“字坚”。这样所作诗歌吟诵起来“郑重”“宛雅”“流利攸扬”,以致于“歌之无尽”。如此则诗歌创作就达到了较为完美的艺术境界,诗歌之音乐特性就得以充分张扬。由此可知,方以智对诗歌的音乐性亦是十分重视,与李东阳的观点相一致。
通过上述分析与比较,笔者认为,李东阳的“格调说”,只是倡导了一种理论架构,即要重视诗歌的体格法度(“格”)和音调声律(“调”),并未展开深入系统地论述,但为诗坛指明了学诗的途径,这是他的理论贡献。很显然,方以智不但从唐宋诗论中汲取论“格”“调”的养分,而且也接受并承袭了李东阳等人“格调说”思想,论诗同样讲求“格调”,但他在论述上更为具体细致。这是方以智对“格调说”的继承,更是对此说的进一步深化,对论诗、作诗更具明确地指导意义。
三、方以智对明代“格调说”诗学理论的建构
虽然锻字炼句、讲求音调声律是诗歌写作最基本的要求,但决定诗歌作品好坏还得从根本上看其内容和形式以及作者所抒发的思想感情等要素。方以智论诗重视“格”“调”,而且他还拈出“中”“边”这两个概念,藉以指称诗歌的思想情感和内容形式,辨明二者的涵义及其相互关系,以期建构合乎逻辑的诗学理论体系。
(一)“中”与“边”:论诗歌创作的艺术构成
方以智提出“中边言诗说”论诗,以“中”与“边”分别指称诗歌创作所包含的艺术构成的三个层面,在理解上也蕴含着明显的三重涵义。那么,何谓“中”?何谓“边”?《诗说》写道:
如是者:论伦无夺,娴于节奏,所谓边也;中间发抒蕴藉,造意无穷,所谓中也。措词雅驯,气韵生动;节奏相叶,蹈厉无痕;流连景光,赋事状物,比兴顿折,不即不离;用以出其高高深深之致,非作家乎?非中边皆甜之蜜乎?又况诵读尚友之人,开帱覆代错之目,舞吹毛洒水之剑,俯仰今古,正变激扬,其何可当?由此论之,词为边,意为中乎?词与意,皆边也。素心不俗,感物造端,存乎其人,千载如见者:中也。俗之为病,至难免矣。有未能免而免免者存。闻乐知徳,因语识人,此几知否[7]55?
其所谓“边”,指的是“论伦无夺,娴于节奏”,意指包括诗歌的节奏在内的艺术表现形式;所谓“中”,是指“中间发抒蕴藉,造意无穷”,指的是诗歌创作内容及其思想情感。诗人写作诗歌,十分注重内容与形式的统一,即“措词雅驯,气韵生动;节奏相叶,蹈厉无痕;流连景光,赋事状物,比兴顿折,不即不离”。具体说来,我们衡量诗歌创作优秀与否的标准,首先就是看诗歌的艺术表现形式,如用字、措词、节奏、韵律等是否合乎法度,所写内容无论写景还是咏物,其表现手法“比兴顿折”的运用等,这些都是“边”的范畴,即诗歌创作形式方面的问题。而诗人的情感抒发,“中间发抒蕴藉”,表达出“造意无穷”之“意”,要表现出诗人“高高深深之致”的情怀,则属于“中”的内涵,显然,这是诗歌创作内容及思想情感方面的问题。如果诗歌创作达到了“中”与“边”两方面的完美结合,这样的作品就完全称得上是“中边皆甜之蜜”,即形式、内容与思想情感相结合达到了非常完美的艺术境地。这样的作品理当经得住历代“诵读尚友之人,开帱覆代错之目,舞吹毛洒水之剑,俯仰今古,正变激扬”的品鉴,自然能够为人传诵。至此,方氏论诗,以“中”“边”相指称形式、内容与思想情感,其义自是明了。
但是,方以智随之却否定了他对“中”的内涵的界定,他说:“词与意,皆边也。”他所认为的“中间发抒蕴藉,造意无穷,所谓中”,竟然也被他视作“边”的范畴。那么,真正的“中”指的是什么呢?在他看来,那就是“素心不俗,感物造端,存乎其人,千载如见者”。我们可以理解为,方以智论诗歌创作,最为看重的是诗中所蕴涵的诗人独特鲜明的艺术品格、诗中所抒发出来的永恒的艺术个性特质——他将此视作诗歌创作的最高境界和准则。这里,我们姑且称之为“中边之上之中”。
综上所论,方氏所指称的“中边”,包含了诗歌创作艺术构成的三个层面,即“中”指诗歌的内容与思想情感,是诗歌的内部层次;“边”指诗歌的艺术形式、表现手法等,是诗歌的外部层次;“中边之上之中”指诗歌的艺术品格和个性特质,这三者用以阐释诗歌创作艺术构成的三个层次及其意蕴。只是其“中边之上之中”,建立在“中”“边”基础之上,是对诗人及其诗歌创作提出的更高的要求。这种“中边之上之中”显然最受方氏的重视。方氏关于诗歌创作艺术构成的思考对诗歌创作与品鉴极具指导性和启发性。
(二)“中”与“边”:二者的辩证依存关系
方以智言明“中”“边”之意,接下来进一步阐述“中”“边”二者具有辩证的依存关系,彼此不可偏废。他首先指出“不以中废边”。他说:“舍可指可论之中边,则不可指论之中无可寓矣;舍声调字句雅俗可辨之边,则中有妙意无所寓矣。”[7]55诗歌的内容和思想情感及其表达的艺术形式是相互依存的统一体,如声调、字句等表达形式是“雅俗可辨”“可指可论”的,可以感知的,而诗歌情感内容是不可独立存在的,必须寓于诗歌文本之中,并借助于“声调字句雅俗”之“可辨”而得以表达出来。如果离开了诗歌文本,那么,诗歌的情感内容、诗人的诗情妙意也就无所“寓”之地。
正因为诗歌内容、思想情感与艺术形式之间相互依存、密不可分,故不能过分强调诗歌的情感内容而轻视诗歌的艺术形式,尤其是艺术形式中诗歌语言的使用。比如说,同样是为了抒发情感,方氏认为,那些“急口愉快,优人之白,牧童之歌”等文字所流露出来的情感尽管真切自然,但那毕竟不能称之为诗歌,因为它缺少作为诗歌必备的艺术表现形式,其语言与《诗三百》就有着根本的区别。另外,各地语言虽说千差万别,但人们如果都能“从正韵而公谈”,这样就可以避免因语言的差别而造成的隔阂。推及到诗文创作上,就是学习《史记》《汉书》、韩愈、苏轼、《离骚》《大雅》、李白、杜甫等著名作家及作品,这就是“诗文之公谈”,即是文人学习的典范。方氏批评那种固执于“但曰吾有意在”之论,如果诗歌只是单纯重视情感的因素(“中”),而不顾及诗歌本身所应具有的语言艺术形式(“边”),那么“执樵贩而问讯,呼市井而诟谇”也就称得上是诗歌,这显然是很荒谬的。因此,诗歌创作必须措词高雅、声中节奏,不可“以中废边”。
其次,也不可“以边废中”。方氏论述道:“法娴矣,词赡矣,无复怀抱使人兴感,是平熟之土偶耳。仿唐泝汉,作相似语,是优孟之衣冠耳。”[7]56这也就是说,如果诗歌写作技法娴熟,词采华赡,但缺乏情感(“怀抱”),不能感染读者,那么,此诗就如同人们平常熟视的泥塑土偶而已,尽管具有优美的躯壳,但缺少艺术灵魂。另外,如果写诗一味地模拟汉唐诗歌,作相似语,不脱前人窠臼,甚或剽窃,那样的话,诗歌就会丧失属于自己的个性心灵和艺术品格,无异于优孟衣冠,徒有外在华丽高超的艺术形式而没有诗人真实的情感,这样的诗歌也是毫无意义的。因此,以“中边”言诗,“中”“边”都不可偏废,不但内容与艺术形式要和谐相配,“措词雅驯,气韵生动;节奏相叶,蹈厉无痕;流连景光,赋事状物;比兴顿折,不即不离”,而且诗歌要表达出作家内心真实丰富的情感,“用以出其高高深深之致”,这才是诗歌创作的要求,这样的诗歌作品就如“中边皆甜之蜜”。诗歌要抒发“真情”,诗中要有真我的存在。如果缺乏真情,那么诗歌就毫无生命力。
方以智以“中边言诗”,其实就是从诗歌形式、内容、情感及个性品格等艺术层面来论诗歌创作,并且他还认识到“中”与“边”之间辩证的、相互依存的关系。这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表明人们对于诗歌创作的艺术构成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为传统的感悟式诗学增添了更多的思辨精神和理性色彩。
四、“中边”的“言诗”之义
方以智于《诗说》开篇即直截了当地提出“中边言诗”,拈出“中边”一词作为其论诗的理论范畴。我们现在探讨方氏“中边言诗”的诗学思想,就有必要理解清楚“中边”这一概念,这样或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其诗学思想的内涵。
“中边”一词,源自佛典。检索文献可知,佛教唯识宗有一部重要的论典,即《辩中边论》,本论流传中国后,有南朝陈时真谛法师译本《中边分别论》(两卷)和唐玄奘法师所译《辩中边论》(三卷),皆收在《大正藏》第三十一册。玄奘译本尤著。其译本最后一颂“此论辩中边,深密、坚实义,广大、一切义,除诸不吉祥”是结释,总结并解释这部论为什么叫《辩中边》。“此论能辩中边行,故名辩中边,即是显了处中二边能缘行义;又此能辩中边境,故名辩中边,即是显了处中二边所缘境义;或此正辩离初后边中道法,故名辩中边。”[8]477(《辩中边论》卷下)“中边”二字,释为三义,其阐扬佛法义理,但以中道立宗。“中”是中道,“边”是边见。破除边见,如虚妄、分别、诸障、边所缘境、远离初后二边等,即是中道妙法。中道是佛教的重要思想,中道就是真实之道,远离二边之见,其目的是为了能够正确地认识真实,证得真实之道。
笔者不谙佛学,在此不敢妄谈佛典奥义,但由上述对“中边”意旨的阐释,或约略理解“中边”之义及“中”与“边”二者的相互关系。那么,方以智以“中边言诗”与佛典之“中边”意思是否有关联呢?他是不是以禅喻诗呢?
以“中边”论诗,其实在宋代苏轼《评韩柳诗》文中就有先例:“所贵乎枯淡者,谓其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渊明、子厚之流是也。若中边皆枯淡,亦何足道。佛云:‘如人食蜜,中边皆甜。’人食五味,知其甘苦者皆是,能分别其中边者,百无一二也。”[9]215很显然,苏轼较为欣赏诗歌的审美风格是“枯淡”,这种“枯淡”美有其艺术特点,即“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他指出陶渊明、柳宗元的诗歌就具有这样的风格。苏轼又进一步指出,如果诗歌创作“中边皆枯淡”,那就根本不值一提的。这里他所说的“中边”,应该是内外或表里的意思,分别指代诗歌的内容与形式。陶、柳的诗歌外在的语言形式看似“枯”且“淡”,但内容却是“膏”而“美”,蕴藉丰富,情感真挚,达到了内容与形式的统一,其艺术风格才臻于至善,从而达到了艺术审美的最高境界。
对于这样一种境界,苏轼还借用佛教经典里的语句来作比,使人更加形象地领会其意。佛云:“如人食蜜,中边皆甜。”此语出自佛教经典《四十二章经》(第三十九章):“佛所言说,皆应信顺,譬如食蜜,中边皆甜,吾经亦尔。”笔者以为,此句中以饮食蜂蜜为喻,蜜总是甜的,并不因一碗蜂蜜,位于碗的中间或边沿而存在差别,意在告诫佛门信众对各种佛教经典予以同等的信奉与修行。《宋真宗御注四十二章经》所注解也较为贴切:“佛言:人为道,犹若食蜜,中边皆甜。吾经亦尔。其义皆快行者得道矣。注:佛言我所说经,由如蜜味,若人食之,中外尽甜,更无二味。慕道之士,若悟经深旨,身心快乐,当证道矣。”[10]宋真宗还进而将对佛经的领悟与启示产生的快感与饮食蜂蜜的甘甜等同起来,由此获得身心的快乐,即是证道的表现。
论述至此,我们就十分清楚,“中边”这一概念其实包含着三重理解:
“中边皆甜”之“中边”所指称的是方位概念,指中间与边沿;“中边皆枯淡”之“中边”意指内外或表里,借以分别指代诗歌的内容与形式;《辨中边论》所辨析的“中边”是指中道与边见,涉及佛典的深奥义理。中道是佛家修行的不二法门,破除一切的边见最终感悟中道的要义。
苏轼因为精通佛典,故而拈出“中边”以论诗,要求诗歌内容与形式皆须统一,并以品味蜂蜜作比,指出对“枯淡”美的感受和鉴赏的难度。而方以智只是借用佛典之“中边”概念来“言诗”,其论诗歌创作较为细致而周全,形成较为完备的理论范畴。因此,正如佛典《辨中边论》所阐明的“中边”即中道与边见的问题,方氏藉此概念来明确“中”即是指诗歌创作最核心的问题,也是他所最为重视的诗歌的内在本质。诗歌外在的形式、写作的内容、诗歌中所抒发的蕴藉着的诗人的真情实感,其实这些都是“边见”,而诗歌的艺术品格和个性生命,处于统领诗歌的核心地位,这才是“中道”,是诗人从事诗歌创作的最高追求。
笔者以为,方氏以“中边言诗”,仅仅是借用佛典“中边”概念以此更好的论述诗歌创作问题而已,而并非以禅喻诗来论述诗歌,这一点显而易见。
五、“中边言诗说”的理论价值
李东阳关于“格调说”的观点散见于他的多篇文章中,并非系统的表述,因其当时身居高位,一度主盟文坛,故而对当时文坛产生极大的影响。“格调说”在诗学理论及其创作实践上的运用,与“格调说”本身所具有的诗格法度和可操作性有着必然的关联。至前后七子沿袭其说,倡扬复古,以“格调”为取法汉魏、盛唐诗歌之方式,故而“格调”在他们的诗歌理论中都占有极其突出的地位。明代诗学批评的理论体系最终以“格调说”为基础,在体制、字法、句法、声律上做细致的辨析,作为一种文学批评理论,他们的着眼点与最终目的决非仅仅局限于此。《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论《怀麓堂诗话》称:“李、何未出已前,东阳实以台阁耆宿主持文柄。其论诗,主于法度音调,而极论剽窃摹拟之非,当时奉以为宗。至李、何既出,始变其体。然赝古之病,适中其所诋诃,故后人多抑彼而伸此。此编所论,多得古人之意。虽诗家三昧,不尽于是,要亦深知甘苦之言矣。”[11]2756当然,明人论诗讲求格调,在复古的旗帜下,以致于把拟古当复古,走向拟古与模仿甚至剽窃的歧途,将诗歌创作引向了死胡同,为后世所诟病,则是需要批判的。
方以智以“中边言诗”,尊“诗体”、强调诗歌创作法度和声律韵调等等,与李东阳的“格调说”相一致。李东阳乃“格调说”的首创者,而方以智写作此文正值明朝灭亡前两年①方以智《诗说》一文,其题下自注:“庚寅答客”,庚寅是指顺治七年,即1650年。而文章前一部分以“中边言诗”论诗歌创作,其之后写道:“崇祯壬午夏,与姜如须论此而笔之。”崇祯壬午,即1642年,则这部分是方以智与友人姜垓(1614—1653,字如须)谈论诗歌,然后加以整理写作而成。文章后部分则是1650年“答客”所记,主要阐述诗歌风格论、鉴赏论等内容。由此可知,该文写作是方以智前后两次与友人论诗的记录,其实也是他关于诗歌一些基本问题的深入思考和理论总结。,从明代诗学发展的历时性而言,方以智此说是对“格调说”的继承与发展及其最后阐发。周维德先生将明代诗话的发展过程划分为初、中、后三个时期,他认为后期的诗话以批判复古思潮、总结诗学理论为主[12]16,所论符合实情。其主编《全明诗话》,收录方以智的《诗说》,题为《通雅诗话》。本文对方以智关于“中边言诗说”诗歌创作理论内涵的探讨,将其与明代较具影响的“格调说”理论加以比较,显然可知,方以智的诗学思想对明代诗歌的回顾与反思意识较为强烈。尤其值得重视的是,方以智的“中边言诗”说,从最基本的诗学原理入手,以“中”“边”作为理论概念,不仅仅强调诗歌创作的“格调”,而且他还明确指出诗歌创作要重视“中”与“边”,即内容与形式、情感和个性品格等要素,并且还进一步指出“中”“边”二者辩证的依存关系,这样就使其论述形成逻辑周全的理论内涵和严密的话语体系。相较于传统的诗话著作更多的表现为随感式、笔记体的言说,方氏《诗说》意在加强诗歌理论的探索,以其深入透辟的理论分析,形成系统性论述,体现出极强的思辨性,这可以视作他对明代诗歌理论发展所做的一份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