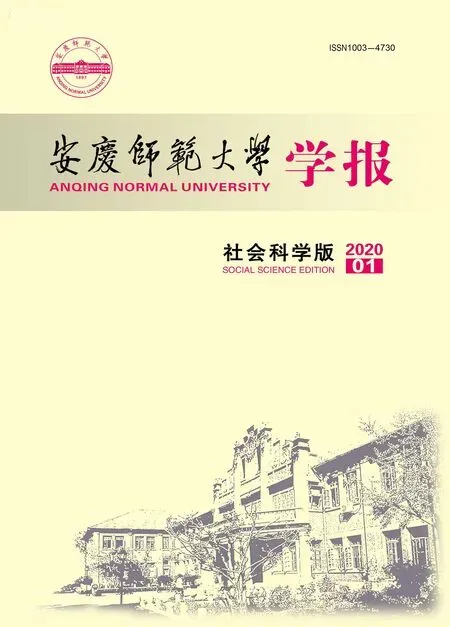《狂人日记》与现代生命伦理的建构
谭桂林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江苏南京210097)
《狂人日记》问世已经百年,其流传之广,影响之大,在百年中国文学中鲜有能与其比肩并立者。关于它的研究成果,其数量之多,意见之纷纭,也堪称现代文学之最。不过,历来对《狂人日记》的主题意义和历史价值的评价,学者们一直习惯于从破的角度来思考,譬如暴露宗法礼教制度的弊端,抨击封建礼教“吃人”的罪恶,等等,这无疑与30年代鲁迅在为《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写序言时的自我评价有直接的关联,或许也受到百年来的“五四学”中大家所形成的一个共识的影响,这个共识就是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本质看做是反叛乃至破毁中国文化传统的运动,把鲁迅看做这一以破为目的的运动本质的代表性人物。近些年来社会文化界颇为流行的胡适鲁迅比较论,也无疑与这种学术共识有着密切的关系,或者说就是这种学术共识衍生的必然结果。其实,当年的胡适与鲁迅在文化策略上都是有破有立的意见领袖,胡适提倡重建文明,但也主张评估一切价值,甚至主张到国故中去捉鬼打鬼,鲁迅当然呼喊过要扫荡千百年来中国传统中的“人肉宴席”,但鲁迅也写过《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这类正面阐述新文化观念的文章,而“立人”则是他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发生前十年就已经抱持的坚定信念。所以,在《狂人日记》发表百年之后,我们对它的认知是否能够超越这种破的视点,从立的角度来重新估价它的意义与价值呢?我认为是可以的,这不仅是因为经典作品的意义本来就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延展与丰富的,只有这种不断的延展和丰富才能真正展现出经典的生命魅力,而且也是因为《狂人日记》这部作品的主旨诠释存在着一个模糊空间,在最为原初的立意与现在流行的观点之间一直存在着遮蔽与反遮蔽的演绎过程,澄明这个模糊空间,最大可能地释放这部作品自身具有的生命能量,乃是今天对这部伟大经典最好的纪念与致敬。
一
按照《狂人日记》的小引所言,小说虽名日记,其实“不著月日,惟墨色字体不一,知非一时所书”[1]444。小说中也有“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1]447,“太阳也不出,门也不开,日日是两顿饭”[1]453之类的描述,显示出小说时间背景上的混沌性。但时间的混沌并不意味小说没有故事的演绎进程,“吃人”是致使“狂人”内心恐惧的中心意念,也是《狂人日记》讲述的中心事件。围绕着“吃人”事件,小说有两条时而交叉时而又重合的故事情节链条。一条是诅咒“吃人”,一条是劝转“吃人”。从作品的结构看,全部日记是十三节,前七节重心在诅咒“吃人”,从第八节开始,后六节重心在劝转“吃人”。从小说主旨的功效发挥上看,诅咒“吃人”是破字当头,而劝转“吃人”无疑体现出作者立的愿景。
在小说叙事的具体描写上,诅咒“吃人”的情节链处理的主要是“狂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有月亮、赵家的狗、“眼色便怪”的赵贵翁、古久先生的流水账簿、“满眼凶光”的大夫、打儿子的女人、“脸色也都铁青”的小孩子等等,故事更为丰富,细节更为生动,人、历史、自然构筑的“吃人”的环境像天网一般笼罩在狂人的周边。在这样密密麻麻、难以挣脱的吃人之罗网中,鲁迅通过狂人的生命感受,揭示了吃人历史的悠久(从来如此)、吃人行为的本质(礼教吃人)、吃人主体的含混(既是被吃者也是吃者)和吃人方式的鬼祟(软刀子)。第八节以后,情节主要以对话的方式展开,一场对话是与“二十左右”的年轻人,一场对话是与自己的大哥,对狂人的生命感受的生动描写也被对狂人的未来愿景的观念揭示所取代。毋庸置疑,从小说叙事艺术自身的规律来看,对生命感受的具体描摹,较之人物对话与观念的表达,在艺术效果上更能引人入胜,也更具有深度阐释的不尽空间,所以在本来就已形成的学术共识的引领下,对这两条情节链,过去的研究成果呈现出明显的偏见也就是很自然的事了。学者们都把分析的才华挥洒在鲁迅诅咒“吃人”的深刻性与尖锐度的分析上,而对劝转“吃人”的情节链的分析往往用力不够,对鲁迅通过这一情节链表达出的未来愿景(“将来是容不得吃人的人”[1]453),轻描淡写地评价一句空洞渺茫不再深究。
其实,从小说的整体结构上看,这两条互相交叉而又重合的情节链是同样重要的,甚至从结构的功能意义上看,诅咒“吃人”乃是劝转“吃人”的铺垫和前戏,劝转“吃人”才是情节发展的高潮与结果,是作者所要表达的中心观念,因而劝转“吃人”的情节链或许在理解鲁迅创作此部小说的动机方面,在评价此部小说的历史价值方面,显得更为重要。对劝转“吃人”的情节链的分析,有两个关键的词语需要引起特别的重视。一个是“将来”。“将来”是一个时间概念,相对诅咒“吃人”的情节链中的时间混沌而言,“将来”用的是明确的肯定句式,显示出鲁迅对“将来”的确定性的自信。鲁迅的《呐喊》自序中也曾提到过“将来”,鲁迅说他之所以在寂寞与绝望中听从朋友之劝写起小说来,就是“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2]。这个“将来”用的是委婉退步的语气,显示着的是一种难以预证的无奈。悬疑与确信,鲁迅的自叙与小说中的狂人对“将来”的判断显示出的差异是值得重视的。鲁迅相信,任何一种文化的革新总包含着破毁与建立的两面,破毁的一面固然痛快淋漓,而且像自己这种从旧营垒出身的人反戈一击更容易制敌于死命,但是建立的路程则更其任重道远,充满着艰辛曲折。这种感悟和信念,即使后来在左翼文学时代来临时,鲁迅也没有动摇过。所以,在《狂人日记》中,鲁迅的个人情怀与新文化战士对“将来”的自我判定上的差异性,恰恰说明了鲁迅对于文化革命中立的路径的重视,也就是说,鲁迅尽管自己如何地绝望于铁屋子的万难破毁,但是对于新文化战士建立新文明的愿望与构想,他是从来不会也不忍心予以否决和嘲讽的。
另一个词是“真的人”。严格说来,“人”在这部小说中的含义,不同之处有不同的用法。“吃人”中的“人”,人不过是一种食材,同鸡鸭乃是一样的,所以小说第三节写狂人被拖回家,“进了书房,便反扣上门,宛然是关了一只鸡鸭”。而“吃人的人”中的“人”,想吃自己的同类,甚至敢吃自己的兄弟亲人,这样的人当然也不是人,乃和禽兽等同。所以,小说中不断地写到赵家的狗,写到狗的本家狼,写到狼的亲眷海乙那,写到狮子式的凶心,兔子的怯弱,狐狸的狡猾,都是在暗示“吃人的人”其行为和这类禽兽的同伍。相对而言,“真的人”当然既不是被吃的食材,也不是吃同类甚至吃人的禽兽。在小说中,“真的人”应该有两个层面的意义,一个层面是“没有吃过人”的人,一个层面是“不吃人的人”。“没有吃过人”的人是一种客观描述,但他是动态的人格,他可能在生命伦理的规范下永远不吃人,也可能在环境演变中坠落成为“吃人的人”。而“不吃人的人”则是一种文明程度的主观判定,是一种意志与信仰的表述,也是一种生命伦理觉悟的显示。他可能“没有吃过人”,也具有不吃人的信念,当然是“真的人”,他也可能过去曾吃过人,但真心改过了,成了不吃人的人,他也是“真的人”。所以,小说中的劝转“吃人”的情节链里,狂人对大哥的劝转用的就是进化论的“变”的理论:“大约当初野蛮的人,都吃过一点人。后来因为心思不同,有的不吃人了,一味要好,便变了人,变了真的人。有的却还吃,——也同虫子一样,有的变了鱼鸟猴子,一直变到人。有的不要好,至今还是虫子。这吃人的人比不吃人的人,何等惭愧。怕比虫子的惭愧猴子,还差得很远很远。”[1]452狂人对于众人的呼喊就是“从真心改起”,不仅“可以改了”,而且要“立刻改了”。“可以改了”是告诉众人,你们本来具有改过自新的能力,“立刻改了”是警告众人时间已经紧迫。因为“你们要不改,自己也会吃尽。即使生得多,也会给真的人除灭了,同猎人打完狼子一样!——同虫子一样”[1]453。
五四时期,作为进化论的信徒,较之其他的新文化运动前驱者,鲁迅更为注重也更为理解生命自身的价值和意义。他知道,“既是生物,第一要紧的自然是生命。因为生物之所以为生物,全在有这生命,否则失了生物的意义。”“依据生物界的现象,一,要保存生命;二,要延续这生命;三,要发展这生命(就是进化)。”[3]135生命是个体的,每一个个体生命为了保存自己的生命、延续自己的生命,在竞争的环境下应该怎样同别的个体生命相处呢?这就是鲁迅所谓第三项发展这生命也就是进化的意义之所在。在进化的途中,人之所以超越于虫子、猴子,甚至超越于野蛮的民族,不仅仅在于人创造了文明,拥有了享受文明的能力,更重要的还在于人在文明的创造和享用中养育了良知,产生了敬畏,具备了自省的能力。有良知就会怜悯同类的生命,有敬畏,就不会轻易地剥夺同类的生命;能自省,就能在同类的身上看到自己的命运,于是,从猴子进化而来的人类成了“真的人”,作为人之道的核心的人类生命伦理学也就应时而生。小说中有一段狂人内心活动的描写,非常贴切地展现了鲁迅对生命问题的思考。狂人面对周边的吃人者,充满了正义与勇气,“我可不怕,仍旧走我的路”[1]445。但他也有困惑和苦恼,“最可怜的是我的大哥,他也是人,何以毫不害怕;而且合伙吃我呢?还是历来惯了,不以为非呢?还是丧了良心,明知故犯呢?”[1]450在这里,鲁迅几乎是天才般地揭示了良知、敬畏和自省这人类生命伦理得以形成的三大基石。“毫不害怕”,当然指的是对生命没有敬畏之心,“历来惯了”,当然是指生命的主体缺乏自省能力;“丧了良心,明知故犯”,则是生命之恶所以作孽的根源所在。人类生命伦理的三大基石全面坍塌,“吃人”现象的发生也就不足为奇的了。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鲁迅通过狂人对“吃人”事件的尖锐质疑、深刻反思和透彻剖析,展示了生命伦理在人类文明体系中的绝端重要。小说的叙述曲曲折折,言说疯言疯语,但有一个中心观念确是十分明白的,这就是,小说中的这些“吃人的人”和“被吃的”人,无论他们拥有多么古久的历史(“这历史没有年代”),无论他们拥有听起来多么动听的文明词汇(“仁义道德”),只要他们还在吃人,或者还在想吃人,他们就毋庸置疑地还是“野蛮人”,甚至是虫子、猴子,“难见真的人”。
二
鲁迅是一个喜欢谈论自己作品的作家,关于《狂人日记》的主题,他也有过明确的解释,虽然这些解释前后之间有所变化,但这些变化也可以从时代精神和鲁迅思想的变迁中找到它的缘由与痕迹。考察这些解释以及这些变化的缘由与痕迹,对全面、客观地评价这部经典的意义与价值而言,是很有必要的。
1918 年8 月20 日,鲁迅在给老友许寿裳的回信中首次谈到《狂人日记》的主题。许寿裳收到鲁迅寄给他的《新青年》四卷五期,在来信中问鲁迅《狂人日记》作者是否是他,鲁迅回答道:“《狂人日记》实为拙作,又有白话诗署‘唐俟’者,亦仆所为。前曾言中国根底全在道教,此说近颇广行。以此读史,有多种问题可以迎刃而解。后以偶阅《通鉴》,乃悟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因此成篇。此种发见,关系亦甚大,而知者尚寥寥也。”[4]这段话有两层意思对理解《狂人日记》极其重要,一层意思是指出《狂人日记》的主题即是揭示“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这一现象。“中国的根底全在道教”和“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这是鲁迅非常自许的关于中国历史的两大发现,这两大历史发现,鲁迅在五四时期用各种不同的文体形式表达过。譬如几乎写于《狂人日记》同时的一些“随感录”,对扶乩、灵学等等妖化科学的社会乱象的猛烈批判,显然是“中国的根底全在道教”这一思想发现的体现,而《狂人日记》“因此成篇”的则无疑是来之“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的觉悟。这里“尚是”一词特别重要,意谓吃人事实不仅历史上如此,而且现实中依然如此。历史上记载有吃人的事实并不足奇,而在文明进化的今天仍然有吃人的恶性遗存就是令人震撼的事了,这也就是所谓“悟”的意义。另一层意思是表达了鲁迅对这两个发现的评价。“关系亦甚大”,说明鲁迅认为他的这两大发现对于中国国民性改造和文化重建,都有着重要意义。但前者“近颇广行”,如周作人在《祖先崇拜》等文章中也多次表达过对道教的批判,所以鲁迅只是建议朋友用这种眼光去阅读历史。后者是“知者尚寥寥”,鲁迅在这里用了鲜明的、强烈的比较描绘,显示出进化论者的鲁迅对这一现象的深深忧虑与敏锐的警觉:如果国人还不明白不觉悟到“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这一点,就有可能在进化途中被文明世界挤落到野蛮民族乃至非人中去。了解到鲁迅的这一忧虑,我们就能够理解为什么鲁迅要采用“狂人日记”的形式来表达“吃人”主题。因为用狂人作为叙述者,狂人的语态也就是所谓的“疯言疯语”恰恰最适合于启示录式的文学表达。一方面,它能够以其零散中的尖锐与无序中的机警有效地阻断人们习惯的思维定势,另一方面,它又能以其独断的语气与非逻辑的外在形态,使得狂人得出来的结论无论如何偏至与激烈,都无须证明。这样就可以省去许多外围的叙述环节,不仅使“吃人”意象直捷鲜明、简洁干脆地突出在读者面前,而且也能够极大地强化“将来是容不得吃人的人”和“救救孩子”这些先知语言的震撼力度,从而达到振聋发聩的社会效果。
鲁迅的这种忧虑在五四时期得到集中的爆发,除了《狂人日记》外,这一时期鲁迅在不同文章中不断提到中国民族各种类型的“吃人”现象。小说《药》,以人血馒头作为情节展开与人物塑造的中心意象,简直可以说就是《狂人日记》中“吃人”的一个现实版本。又如《随感录·四十三》:“土人一字,本来只说生在本地的人,没有什么恶意。后来因其所指,多系野蛮民族,所以加添了一种新意义,仿佛成了野蛮人的代名词。他们以此称中国人,原不免有侮辱的意思,但我们现在,却除承受这个名号以外,实是别无方法。因为这类是非,都凭事实,并非单用口舌可以争得的。试看中国的社会里,吃人,劫掠,残杀,人身买卖,生殖器崇拜,灵学,一夫多妻,凡有所谓国粹,没一件不与蛮人的文化恰合。”[5]343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中,鲁迅指出:“况在将来,迷信破了,便没有哭竹,卧冰,医学发达了,也不必尝秽,割股”[3]144;在《论照相之类》中,鲁迅在批评S城人关于“洋鬼子”挖眼睛、挖心肝的传言时,也指出:“道学先生之所谓‘万物皆备于我’的事,其实是全国,至少是S城的‘目不识丁’的人们都知道,所以人为‘万物之灵’。所以月经精液可以延年,毛发爪甲可以补血,大小便可以医许多病,臂膊上的肉可以养亲。”[6]即使到了1926年,鲁迅在撰文纪念自己的老朋友时,也还特地提到“徐锡麟是被挖了心,给恩铭的亲兵炒食净尽”[7]。这些例子都可以直接证明,鲁迅《狂人日记》的主题正如其言,就是“乃悟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
一直到1935 年鲁迅为《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写序,鲁迅对《狂人日记》的主题才表达了一种新的说法。“从一九一八年五月起,《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等,陆续的出现了,算是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又因为那时的认为‘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颇激动了一部分青年读者的心。然而这激动,确实向来怠慢了绍介欧洲大陆文学的缘故。一八三四年顷,俄国的果戈里(N.Gogol)就已经写了《狂人日记》;一八八三年顷,尼采(Fr.Nietzsche)也早借了苏鲁支(Zaratuustra)的嘴,说过‘你们已经走了从虫豸到人的路,在你们里面还有许多份是虫豸。你们做过猴子,到了现在,人还尤其猴子,无论比那一个猴子’的。而且《药》的收束,也分明留着安特莱夫(L.Аndreev)式的阴冷。但后起的《狂人日记》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却比果戈里的又分深广,也不如尼采的超人的渺茫。”[8]《狂人日记》的主题陈述正式从“乃悟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转变为“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而且是由作者鲁迅自己完成这一转变的。当然,这种转变并不是突然的,期间有一个中间站,那就是写于1925 年的《灯下漫笔》。在这篇文章,鲁迅指出:“所谓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所谓中国者,其实不过是安排这人肉的筵宴的厨房。”“因为古代传来而至今还在的许多差别,使人们个个分离,遂不能再感到别人的痛苦;并且因为自己各有奴使别人,吃掉别人的希望,便也就忘却自己同有被奴使被吃掉的将来。于是大小无数的人肉的筵宴,即从有文明以来一直排到现在,人们就在这会场中吃人,被吃,以凶人的愚妄的欢呼,将悲惨的弱者的呼号遮掩,更不消说女人和小儿。”“这人肉的筵宴现在还在排着,有许多人还想一直排下去。”[9]这一段话,标志着鲁迅直接将“吃人”行为同中国文明联系起来了,或者说标志着鲁迅将“吃人”从具体的吃人行为引申到了礼教吃人①小说中的从仁义道德的字缝中看出“吃人”二字细节,并没有将“仁义道德”直接等同于吃人。这种描写导致了以后有些研究者认为鲁迅并不是写仁义道德吃人,而是写仁义道德没有阻止住中国人吃人的行为。可以参见贾泉林《〈狂人日记〉中的章太炎因素》一文,发表在《上海鲁迅研究:〈狂人日记〉100年》(上海鲁迅纪念馆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8年版,第38-43页。。比较一下《狂人日记》和《灯下漫笔》,可见两篇作品存在着这样的不变与变:不变的是“尚是”和人肉筵宴“一直排到现在”,变的是在《狂人日记》中吃人的人和被吃的人主体是含混的,而在《灯下漫笔》中,人肉筵宴中有了贵贱、大小、上下之分,也有了“凶人”与“弱者”之分。从这些分别上,我们可以看到鲁迅思想和关注点的变化,也就是从五四时期的生命伦理关注向后期思想中的政治伦理关注的转型。所以,当30年代中期,鲁迅已经习惯于以政治伦理立场来观察事物和分析问题时,鲁迅重提《狂人日记》的主题时将其表述为“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这种政治伦理命题,也就是必然的事了。
自此之后,“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就成为《狂人日记》的标准主题,从历史书中满篇写着“仁义道德”的字缝里看出“吃人”二字的细节,就自然地被解读为“仁义道德”吃人,而“吃人”这一具体的历史事实和现世行为也就演变成了一个象征意象。当然,也有不少学者提出异议,要将《狂人日记》的主题正名到鲁迅最原初的陈述。如汤晨光《是人吃人还是礼教吃人——论鲁迅<狂人日记>的主题》一文认为,《狂人日记》长期以来被定论为揭露礼教吃人,但从鲁迅的一贯思想和小说发表时鲁迅的自述可以断定,其原初的核心的动机是表现人吃人,是揭露存在于中国的食人蛮性,它通过对被吃的恐惧感传达出鲁迅对民族摆脱野蛮状态的热望以及对人的肌体和生命的强烈关注[10]。应该说,这些学者要求回到鲁迅最为原初的意指上去,都是合理的。值得指出的是,如果仅仅只是要求回到鲁迅自述的原点,而看不到这一原点所包含的深广的意义的话,这种回归反而有可能遮蔽或者损害《狂人日记》所具备的经典性。笔者认为,不仅是鲁迅对生命本身的强烈关注,而且是鲁迅对生命伦理建构的强烈关注与思考,才是《狂人日记》“乃悟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这一主题的深广意义所在,而这一点恰恰与五四时代的精神特质以及鲁迅对这一时代精神的积极呼应有着密切的关系。
“乃悟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狂人日记》的这一原始主题在五四新文学革命时期,其实是得到大家公认的。《狂人日记》发表之后不久,《新青年》的主要作者之一吴虞在第6 卷第6 号上发表了著名的《吃人与礼教》一文,后来学术界普遍认为,正是这篇文章成为始作俑者,将《狂人日记》的主题阐发为礼教吃人,其实这是不确切的说法。这篇文章影响固然很大,而且标题就是吃人与礼教这两个十分刺眼的词汇,但通观全文,吴虞还是将吃人与礼教这两个词分开来议论的,吃人是吃人,礼教是礼教,两者本来就是矛盾的。吴虞为了证实鲁迅“乃悟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这一主题,列举了许多中国历史上人吃人的故事,而且这些故事都是正统史书上有所记载的,其可信度与野史和传说是大不一样的。值得注意的是,吴虞所列吃人史实是有所选择的,入他之眼的吃人者往往都是大谈礼教的王公大臣。吴虞双管齐下,一面列描述其尊周公讲礼教的姿态,一面列举其啖吃人肉的故事。如春秋时的齐候,很讲君君臣臣的纲常名教,就是关于小小的一块祭肉也不能苟且,可就是这位在葵丘大会上说了许许多多敬老慈幼的门面话的五霸之首,居然对为他调和膳食的易牙说想吃蒸的婴儿,以致易牙“蒸其首子,而献之公”。汉代开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汉诛梁王彭越,醢之。盛其醢,徧赐诸侯”。唐时张巡守睢阳,弹尽粮绝时杀其妾以飨军士,被史家称为忠烈,哪怕到了近代,曾文正灭太平军时,其日记中也有记载:“洪杨之乱,江苏人肉卖九十文钱一斤,涨到一百三十文钱一斤。”正是在这样的对比中,吴虞盛赞鲁迅的《狂人日记》“把吃人的内容,和仁义道德的表面,看得清清楚楚。那些戴着礼教假面具吃人的滑头伎俩,都被他把黑幕揭破了”。最后大声呼吁,“到了如今,我们应该觉悟!我们不是为着君主而生的!不是为圣贤而生的!也不是为纲常礼教而生的!什么‘文节公’呀,‘忠烈公’呀,都是那些吃人的人设的圈套,来诳骗我们的!我们如今应该明白,吃人的就是讲礼教的,讲礼教的就是吃人的呀!”由此可见,吴虞奇怪的是吃人和礼教本来是矛盾的,怎么在中国就成了并行不悖的,他发现原来这是讲礼教的人所设的圈套,吃人是真的,礼教是假的。吴文最终也没有说“礼教”吃人,而是落在“吃人的就是讲礼教的,讲礼教的就是吃人的”这一骗局的揭穿上。在这一点上,鲁迅和吴虞有着共识,他一生都在批判古代儒生的伪善,认为儒生并不真正相信或者坚守孔子的学说,大都是在将孔子的学说当做敲门砖。这些论述,也是鲁迅深知儒生骗局的一个证明。
三
《狂人日记》发表后,事实意义的吃人与象征意义的吃人这两种思路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度极其深远。关于象征意义的吃人,学术界已多有研究成果,不再赘言,这里对事实意义的吃人的影响,略举例证说明。1925年3月,鲁迅的私淑弟子川岛在《语丝》上发表《人的叫卖》,不仅谈到了庄季裕的笔记中所载唐初朱桀“以人为粮”“谓啖醉人如食糟豚”,靖康时,山东京西淮南等地“盗贼官兵以致居民更互相食,人肉之价贱于犬豚,肥壮者一枚不过十五千,全躯暴以为腊。登州范温率忠义之人绍兴癸丑岁泛海到钱塘,有持至行在犹食者。老瘦男子痩词谓之‘饶把火’,妇人少艾者名为‘不羡羊’,小儿呼为‘和骨烂’,又通目为‘两脚羊’”,而且作者对现世中的事实吃人也有所记载:“北五省旱灾以前的那次旱灾时,就在平定,人如果饿死,家人都不敢哭。因为哭声出去之后就有人拿了明晃晃的刀和篮子来分割人肉。”[11]《语丝》编辑周作人虽然一向认为学术研究应该严谨,注意常识,“平常所谓风俗,当以现代通行者为准,不能引古书上所记录,或一两个人所做的事,便概括起来认作当世的风俗。倘若说这是可以如此说的,那么我们知道德川朝有通火烧,锅煮,浇滚汤,钉十字架种种死刑方法,也可以称他是世界无比,根据了男三郎的臀肉切取事件,也可以说日本有吃人的风俗。但是头脑略为明白的人便知道这是不对,因为后者是个人的事情(虽然人肉治病是民间的迷信),前者乃是从前的事情了。”[12]但在给川岛的回复中,周作人还是很明确的说:“吃人,这是我中华古已有之的事。要说是坏,固然也是的,但是在重精神文明的国民,只要保住精神,吃掉了物质或者也不很打紧,即使不主张毁物质即所以保精神。”周作人还说,“我所最感到趣味的是《鸡肋编》里所说,登州忠义之人带了人腊到钱塘的行在来吃。吃了人肉做忠义之民,这是中国礼教的具体的象征。”[11]“忠义之民”带了人腊行在来吃,而吃了人肉还要做“忠义之民”,这和吴虞的“讲礼教的吃人,吃人的讲礼教”其实是同一种观察结果,洞察之见何其相似乃尔。
在现代文学史上,有一些小说为了塑造人物性格或者为了展示生存环境,也写到了种种的吃人情节与意象。如谭正璧的小说《莎乐美》,写皇后的活吃人心,较之现实生活中恩铭的亲兵炒吃徐锡麟的心肝更为残暴:“又是疯狂般地把那颗心向自己嘴里送,淋得胸衣上、被子上都是血,满手满嘴也都是血,不知怎地,竟被她活生生地喫了下去。在旁的宫女太监都吓得呆了,一时不知所措都立着不动。忽然哇的一声,血像喷雾般从皇后嘴里射出来,喫下的心也吐了出来,跟在心的后间,血更像潮水般向地上涌。皇后的脸上尽是血,仿佛是燃上了火焰,身体在抽搐着。血还在涌,她的身子软得倒了下去。”[13]又如李拓之的小说《遗袜》,写安史之乱带给百姓的生灵涂炭。小说中杨玉环死在马嵬坡后,无以为生的老妇和孙子拾荒刨坟,发现了杨玉环美丽光洁的身体。老妇居然情不自禁地吻了上去,而年幼的孙儿则由于太过饥饿,狠狠地咬下尸体的乳头将尸肉吃下肚去。温泉水滑洗凝脂,侍儿扶起娇无力,这是千百年来一直在国人的文学想象中承传下来的关于女性身体的美丽故事,但在这一小说中,一代仙女杨玉环的尸身不幸成了山民的果腹之物。美的肉身,人的恶性,两相对照,既是写实,也是反讽,虽然都是历史事件,也不难让人想起现世中灾荒之年饥民“以人为粮”的困境。当然,人在没有任何资源来维持生存的状况下,啖吃同类的血肉来延续自己的生存,从高标准的文明底线来衡量,这也是不符人之伦理的。但从低标准的文明底线上看,这毕竟显示出的是人类在生存与伦理之间难以取舍的悖论。只有在20世纪人类文明进化到物质生存已经不再是无法克服的困难的状态下,居然还有人类像贾平凹的小说《带灯》等作品里面所描写的那样,为了美味,为了养生,或者为了治病,不仅吃女人的胎盘,而且吃打下来的已经成型的胎儿,这才不仅是一种吃人的蛮性的残留,而且简直就是一种民族劣根性的发露。这种现象的存在,恰恰证实了鲁迅“乃悟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这一洞见的深刻,也证实了《狂人日记》所揭示的主题还远远没有过时。
1915 年,陈独秀痛感民国建立之后国家政治尚没有真正实现现代意义的转型,共和国只有政党的政治,只有政客的政治,没有国民的政治运动,所以他创办《青年杂志》启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启蒙工作,目的就在于唤醒和促进国民的政治觉悟。在《吾人最后之觉悟》一文中,陈独秀明确指出中国的问题要获根本解决,“犹待吾人最后之觉悟”。而他心目中的“最后之觉悟”,则包含“政治的觉悟”和“伦理的觉悟”两种。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尽管思想启蒙的目的在于唤醒和促进国民的政治觉悟以催生中国的国民政治运动,但陈独秀还是先知般地悟到了在这两种觉悟中,后者也即伦理的觉悟更为重要。因为“伦理思想影响于政治,各国皆然,吾华尤甚。儒者三纲之说,为吾伦理政治之大原,共贯同条,莫可偏废。三纲之根本义,阶级制度是也,所谓名教,所谓礼教,皆以掩护此别尊卑明贵贱制度者也”。“自西洋文明输入吾国,最初促吾人之觉悟者为学术,相形见绌,举国所知矣。其次为政治,年来政象所证明,已有不克守缺抱残之势。继今以往,国人所怀疑莫决者,当为伦理问题。此而不能觉悟,则前之所谓觉悟非彻底之觉悟,盖犹在惝恍迷离之境。”所以,陈独秀以其一贯的坚定态度和独断语气指出:“吾敢断言曰,伦理的觉悟,为吾人觉悟之最后觉悟。”[14]这一断言,不啻是五四新文化思想运动最有洞察力与预见性的一个启蒙方略。先进的政治制度建立起来了,现代的社会治理方式完善起来了,前沿的科学技术发达起来了,但人的伦理观念还处于前现代阶段,还没有完全实现现代化的转型,社会的进步就只是一个跛脚的前行,甚至面临倒退与翻转的风险。大到五四之后百年来的启蒙运动发展,风风雨雨,曲曲折折,反反复复,小到贾平凹笔下的人物还在偷偷摸摸的以成型的胎儿为药材来治病,这些都无不验证者陈独秀这一方略的重要性。
就鲁迅思想而言,早在辛亥革命前的思想启蒙工作中他就已经疾呼“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而他在立人方面树之为标杆的则都是拜伦、雪莱、尼采、易卜生这类英哲与精神界之战士,他们的共同特点就是在思想上不惮异端,在伦理上争天抗俗。由此可见,如果说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一文显示出他是陈独秀文学革命观的知己,而鲁迅投入文学革命的第一掷投枪就是《狂人日记》,这恰恰说明在伦理觉悟之为最后觉悟这一启蒙观念上,鲁迅也是陈独秀思想革命观的知音。鲁迅一旦投入这场《新青年》发起的思想启蒙运动中,就已催生“伦理的觉悟”为己任,这既是听取前驱者的将令,也是鲁迅自己内心的一种自觉。尤其值得重视的是,伦理作为一种价值体系,包括社会伦理、政治伦理、经济伦理、学术伦理、生命伦理等等多层次的内容,而作为生命体的人,乃是一切社会、政治、学术活动的中心和目的,因而在伦理这一价值体系中,生命伦理居于核心的地位,生命伦理的现代化也显得格外重要和迫切。鲁迅从一开始就把生命伦理的现代化摆在了首要位置上,他抨击“吃人”,呼喊“救救孩子”,相信“将来是容不得吃人的人”;他反对祖先崇拜,提倡“幼者本位”,鼓励“老年人欢欢喜喜地死去”,让年轻的一代欢欢喜喜地走向前去,这些都是五四新文学在中国生命伦理现代转型方面的最为重要的标志性成果,也是他作为《新青年》同仁对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的启蒙方略的实施与推进。而在他后来一系列的文学创作中,鲁迅对病人安乐死的肯定,对统治者虐杀酷刑的批判,对残疾者的创造精神、自强意志的尊重,等等,可见鲁迅毕其一生都在呼喊着生命伦理的现代化,也可见出鲁迅真正是五四新文化精神最为深刻也最为杰出的坚守者与践行者。礼教杀人,这在封建时代就已有思想异端者道出其中利害,而在新儒家回归的今天,“仁义道德”吃人的命题又屡遭质疑与攻击,虽然有不少学者力图为鲁迅辩护,力图把“吃人”这一意象的强烈色彩予以淡化或者模糊,但这些做法与鲁迅当年创作这部小说的原初动机也是渐行渐远。鉴此,或许只有在生命伦理现代化这一启蒙路径上来看《狂人日记》,这部经典作品的意义与价值才会得到更深刻的彰显,更广泛的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