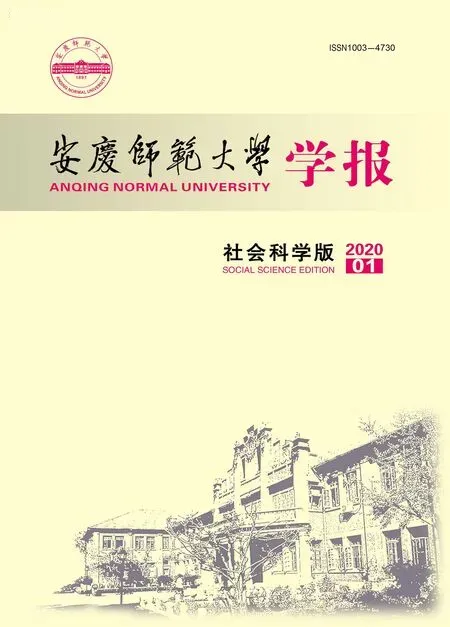厦门风景与鲁迅的识物意识
杨 姿
(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重庆401331)
“如画”是贡布里希解释人类后天接受概念化物象对审美体验产生决定性影响作用所引入的术语:“我们形成习惯,不仅把‘如画’一词用于倾圮的古堡和落日的景象,而且用于帆船和风车那样简单的东西。细想起来,我们之所以说那些简单的东西‘如画’是因为那些母题使我们联想到一些画。”[1]通常来讲,风景如画是一种还原的错觉,可仍然是人们对风景表现成效的高级评价,鲁迅在厦门看与写的风景,逆“如画”而行,却取得别样的发现,即远离那种被普遍认识所构造起来的厦门。
鲁迅对风景的描写在他早期的小说和散文创作中已经出现,并烙有他显著的个人性,究其写作理路如下:第一,烘托或塑造社会环境的风景。以“鲁镇”的搭建为例,《祝福》中福礼的准备:“杀鸡,宰鹅,买猪肉,用心细细的洗,女人的臂膊都在水里浸得通红,有的还带着绞丝银镯子。”[2]《风波》中晚饭前的景象:“临河的土场上,太阳渐渐的收了他通黄的光线了。场边靠河的乌桕树叶,干巴巴的才喘过气来,几个花脚蚊子在下面哼着飞舞。面河的农家的烟突里,逐渐减少了炊烟。”[3]祭祀和用饭都是乡村里寻常得不能更寻常的事件,作品中的风景一律顺承着事件的展开,对风景的勾勒是鲁迅贴紧生活的完整显现。第二,有意混淆现实与虚拟的场景,风景在这种似真似幻的是是而非中存在。以《故乡》为例,对究竟是谁看见了故乡的破败,研究者早已见仁见智,可文中反复出现海边之景,鲁迅的用意为何?闰土有着深刻的恋地性——他竭尽全力地让自己依存于此地却艰难生活——对小说中的“我”而言,不仅是看到了这种人地相恋,还看到了这种人地盲目相连的无出路,因为它无法保证自己的原始性,这种悲剧性使得海边沙地永远只能作为虚幻之景,准确地讲,鲁迅实写虚景代表了象征的现实意义。第三,几乎以一种异端的取景角度和成像技巧来虚构或重构景观。以夜景为例,鲁迅对夜的偏好是一个庞大的话题,这里仅以风景层面的组织为讨论对象。从《狂人日记》“今天晚上,很好的月光”[4],到《药》里关于夜“街上黑沉沉的一无所有,只有一条灰白的路,看得分明。灯光照着他的两脚,一前一后的走。”[5]再到《秋夜》“他仿佛要离开人间而去,使人们仰面不再看见。然而现在却非常之蓝,闪闪地䀹着几十个星星的眼,冷眼。”[6]很明显地有一种凝视感的增加,在夜景的背后隐藏着鲁迅内在的视距。三种风景的写作理路,不断地趋向异类的夜的诞生,是鲁迅自我主体性强化的表现。可是,进入到厦门风景,逐渐褪去早前三类的入景风格,而是物的形近和意的反叛同时生成。
一
仔细回顾鲁迅对厦门的印象,总的概述是“风景一看倒不坏,有山有水”,并且辅以同事的介绍“山光海气,是春秋早暮都不同”,而鲁迅并没有按照这种叙述的惯性逐一铺陈厦门景致,相反,笔锋一转,说到“我对于自然美,自恨并无敏感,所以即使恭逢良辰美景,也不甚感动”[7],但又立马给许广平讲述自己看郑成功遗迹的见闻感受。类似这样的盘绕和转折,一方面是鲁迅自属的语言范式的延续和再现,另一方面,也是散落在整个厦门阶段有关风景写生的呈现样式。以看风景和写风景之间的张力大小为依据,鲁迅的风景成文有如下三个特点:
第一,作为事件或地名的记载,鲁迅并不将其作为风景对待。即便以风景记之,文内也不作多余的叙写,如《两地书》中“此地背山面海,风景佳绝”[8]107(1926 年9 月4 日),“我暂住在国学院的陈列所里,是3 层楼上,眺望风景,极其合宜”[8]117(1926 年9 月12 日),鲁迅与许广平极为密集的通信中,事无巨细,总是尽其所能地写得可触可感,然而这些“佳”处和“宜”处,却毫无下文。这种貌似无意的遗忘,背后却有着不易察觉的观念。1926 年12 月11 日,鲁迅的日记记有“晴。上午丁丁山邀往鼓浪屿,并罗心田、孙伏园,在洞天午餐,午后游日光岩及观海别墅,下午乘舟归”[9],而在当日以及日后写给许广平的信笺中无一字提及“鼓浪屿”。首先,鲁迅非常清楚鼓浪屿的景点性质,在抵达厦门寄给许广平的第一张明信片就备注了“前面是海,对面是鼓浪屿”[8]116(1926 年9 月11日);而且,在谈及闽粤局势时,也提到“听说鼓浪屿上已有很多寓客,极少空屋了,这屿就在学校对面,坐舢板一二十分钟可到”[8]119(1926 年9 月14日);从日记和书信的时期来看,鲁迅此前也并没有格外地观览过该屿,“鼓浪屿也许有罢,但我还未去过,那地方无非像租界,我也无甚趣味”[8]142-143(1926 年10 月4 日)。在这样的前提下,鲁迅受邀游玩,却表现出对这一区域的目中无景,那种有意的疏离和隔膜,并非不解风情,而是自身的立场和态度所决定。鲁迅此后还去过鼓浪屿(1927 年1月8日),同样也只留有极其常规的日记。如果对比同时期的文人篇章,反差更是鲜明,巴金于1930年的初秋第一次到鼓浪屿,后来写下“美丽的、曲折的马路,精致的、各种颜色的房屋,庭院里开着的各种颜色的花,永远是茂盛和新鲜的榕树,……还有许多别的东西,鼓浪屿给我留下的印象是新奇。我喜欢这种南方的使人容易变为年轻的空气。”[10]即便在厦门的沦陷时期,作家笔下的鼓浪屿仍是“一个小型的香港”,施蛰存于1938年10月31 日写下自己的观光体会:“在这个孤岛上,生活程度也显然很高了”“我上了日光岩。在那个光光的山头上瞭望内海的一盛一衰的景象,听着山下观音庙里唪经击磐声,和喧豗的市声”[11]。很显然,近代以来的鼓浪屿从未因战乱或其他客观原因失却过名屿的声誉。像巴金、施蛰存以游客身份表达对鼓浪屿喜爱与认同的作家还有许多,更遑论当年林文庆、林语堂等厦门居住人对鼓浪屿的深情描绘,鲁迅的所识所记无论如何都是少数。
第二,虽有景入文,但山水之境总会退让到鲁迅的新发现中。前文所引的郑成功之例,便是如此。1926 年9 月23 日,“郑成功的城却很寂寞,听说城脚的沙,还被人盗运去卖给对面鼓浪屿的谁,快要危及城基了。有一天我清早望见许多小船,吃水很重,都张着帆驶向鼓浪屿去,大约便是那卖沙的同胞。”[12]鲁迅的白描手法一流,无论城墙还是帆船,寥寥数笔都能勾勒出物的神韵,然而他并不止于景物在刹那之间给人的第一印象,却是从现时的景所刺激的情绪而跳脱到风景缔造者的情智判断。又如,1927年1月16日,鲁迅给李小峰写信讲述自己在离开厦门的船上所见:“海上的月色是这样皎洁;波面映出一大片银鳞,闪烁摇动;此外是碧玉一般的海水,看去仿佛很温柔。我不信这样的东西是会淹死人的。”联系信的开头:“船正在走,也不知道是在什么海上。总之一面是一望汪洋,一面却看见岛屿。但毫无风涛,就如坐在长江的船上一般。小小的颠簸自然是有的,不过这在海上就算不得颠簸;陆上的风涛要比这险恶得多。”[13]将此文中海的书写放在历来的海上记游里面,都算上乘文字,可是鲁迅的用意却在刻画经历海船的人的体验,这种体验也远远不是一时一地之感,更深地渗透着他生命所受纷扰和煎熬的反刍。两处写景恰好是鲁迅到厦门一来一去的剪影,两处内容的异同或许可以另文再谈,值得关注的是,鲁迅描述风景的策略和动机,在这样的辨认和识别中,已经超越了风景本身。柄谷行人曾以“风景的发现”去观察“明治20年代”所发生的某种认识论的颠倒,他认为“风景的被发现并非源自对外在对象的关心,反而是通过无视外在对象之内面的人而发现的”[14]3,其核心在于对内心的专注,景物变成心灵的对象化。鲁迅有相似的“颠倒”,但是,鲁迅颠倒的并非是柄谷行人所界定的内外,他从未单纯地陷于个人的情感世界,并以此作为观察外部的镜头,鲁迅对社会的异化、时代的变形以及历史的变异有着敏锐的感知,并将这种丰富的体验与自己的生命体验合二为一。所以,他不是简单地用柄谷行人所说的内心去发现外界的风景,而是风景的发现和个人的发现同时完成。
第三,风景所隐含的常识和常情,在鲁迅的记叙中,每每走向另类的呈像。关于厦门气候所形成的植物景观,在给友人的信中鲁迅先后多次提及。1926年11月7日,“秋葵似的黄花。我到时就开着花的了,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开起的;现在还开着;还有未开的蓓蕾,正不知道他要到什么时候才肯开完。(中略——论者注)还有鸡冠花,很细碎,和江浙的有些不同,也红红黄黄地永是这样一盆一盆站着。”然而,“荷叶却早枯了;小草也有点萎黄。这些现象,我先前总以为是所谓‘严霜’之故,于是有时候对于那‘廪秋’不免口出怨言,加以攻击。然而这里却没有霜,也没有雪,凡萎黄的都是‘寿终正寝’,怪不得别个。”[15]而且他还持续地观察着这里的植物,1926 年12 月31 日,同样是给李小峰的信里,继续写到,“天气,确已冷了。草也比先前黄得多;然而我那门前的秋葵似的黄花却还在开着,山里也还有石榴花。苍蝇不见了,蚊子间或有之。”[16]及至1927 年1 月12 日,鲁迅给翟永坤的信里仍旧关注着这一对象,“此地没有霜雪,现在虽然稍冷,但穿棉袍尽够。梅花已开了,然而菊花也开着,山里还开着石榴花,从久居冷地的人看来,似乎‘自然’是在和我们开玩笑。”[17]按照南北不同,风时各异的常理,厦门的亚热带气候所孕育的花草百树天然地与鲁迅此前所生活的地方不一样,但是鲁迅不是在一般的差异原由中解释这种反差,他所秉持的识断标准极端的个人化,不但对花期所引发的反常态提出了有别于乐观的看法,“现在可又有些怕上天堂了。四时皆春,一年到头请你看桃花,你想够多么乏味?即使那桃花有车轮般大,也只能在初上去的时候,暂时吃惊,决不会每天做一首‘桃之夭夭’的。”而且,刻意地将“自然”的一部分割裂出来:“宋玉先生的什么‘皇天平分四时兮窃独悲此廪秋,白露既下百草兮奄离披此梧楸’等类妙文,拿到这里来就完全是‘无病呻吟’。”[14]3这并不是鲁迅在科学方面的无知所致,他早年就对自然科学有极为广泛而深入的涉猎,之所以凸显出厦门草木生长的别致,在于他潜在地启用了一种大众观感为参照,并与这种公众观逆向而行,就算他和观看者是一致的写照,可传递的意味却毫不相同。
鲁迅所看所写的厦门风景区别于普通风景篇章中对抒情的重视,他扭转了人与景、情与景在一贯的风景叙写中的比重,他并不以眼中所见为言说心境的直接结果,图景的描摹中间充满了多重的转换,风景从来都不是发现的目的和终点,在这个意义上,他的风景识物律总体上是反抒情的。当然,他也不是为了昭示自己的理智基础和哲学深度,对风景的获得仍然以感觉的发生为前提,但并不陷于风景的唯情论,因而比惯常的情景合一的“情”更敏锐、更清醒,即对由景及情的“情”有着自觉的反思,进而得到在此基础之上的对风景的再认识。
二
鲁迅留下的厦门印象,最有代表性的一句是“硬将一排洋房,摆在荒岛的海边上”[8]173(1926 年10月23日)。他的“看见”,既不是忘情地乐享,也不是从众地认同为人称道的混和着南方气息与域外格调的南洋风采,他念念不忘的是被历史和现实共同倾轧中的厦门。他曾有一感慨,在那么偏远的离京之地,人群关系和社会空气却顽固地惊人相似,“逃来逃去,还是这样,”都令他觉得,“世事大概差不多,地的繁华和荒僻,人的多少,都没有多大关系”[8]173(1926 年10 月23 日)。牺牲和背叛,拯救和麻木,这些对峙性经验煎熬着他的内心,当他意识到自己寄希望于超人意志而感受到痛苦与绝望,由此,他寻求着对自己痛苦和绝望的反抗道路。既然在前期的景物精神化建构中,未能突破民众的心理壁垒,那么,他放弃个人视力或他者视力的启用,是否可能带来新的接受可能?
贡布里希从绘画史的进程对风景画的动机做过诠释:“虽然通常的提法是,风景画发展最基本的动机是再现‘世界的发现’,我们还是很想把这个公式颠倒一下,声明风景画先于对风景的感觉。”[18]按绘画和文学相通的理论,这就意味着如果读者读到某篇厦门文章,便觉得文章和厦门很像,但事实上不过是读者在阅读这篇文章之前,就已经看过无数的厦门文字了。而这,恰好是鲁迅极力反对的,他不但不会重复别人的文章,甚至连自己的文章也不会重复,他所追求的是挑战庸常的观感,自然是要做出过去文学中的厦门所没有的样子来。所以,他动用了更形似的一种绘景,但仅仅是在外形和细节上的酷肖,骨子里和他早先的特立独行并无二致。这并不只是“只有在对周围外部的东西没有关心的‘内在的人’(inner man)那里,风景才能得以发现”[14]13,与之悖反,鲁迅从来没有将自己作为一个“内在的人”对待,始终将心灵与广大的世界,与“无穷的远方”和“无数的人们”连在一起,所以,他的识别用柄谷行人“风景乃是被无视‘外部’的人发现的”[14]13来定义是残缺的。鲁迅的识物在厦门的微调,只是从减法到了加法,即对事物本相的揭示,过去是剥落它的装饰,让其兀立于世人面前,以其造成官能的不适感给人以刺戟,而此时是保留其纹饰,但增大外饰和内底之间的距离,再和盘托出,令人看出其中的端倪,采取一种貌似“回归”物象的逻辑,更精准地为事物定性和定位。
鲁迅到厦门大学任教的选择,客观地看,与他当时同军阀官僚、“正人君子”的纠葛有直接关系,鲁迅南下有避祸的意图,这符合他的“壕堑战”之说;同时,他对地处南方的厦门也有一种期待,希望它的边与远能够维持一种非政治文化中心地带的宁静和简单,而且,作为高校学府能以现代学院学术为轴心运转,以此偿还他的学术研究之心。可是在厦大所接触的差役、职员、同事、领导,不但显露出厦门与北京的文化本质一致,还强化了鲁迅认识到国民在权力的奴性之外的金钱的奴性,“有生活而无‘费’,固然痛苦;在此地则似乎有‘费’而没有了生活。”[19](1926年9月26日)他不止一次地提到,这座南方城市的特点是“死海”①鲁迅在给韦素园的信中说:“周围是像死海一样,实在住不下去”(《261121 致韦素园》),“这样下去,是要淹在死海里了,薪水虽不欠,又有何用?”(《261208 致韦素园》)。一样,“这里是死气沉沉,也不能改革,学生也太沉静”[8]215(1926 年11 月20 日),“我看厦门就像个死岛”[20],及至1935 年,他给台静农写信,还提及“所遇与我当时无异”,指出“厦门不但地方不佳”[21]。特别是在那样一种变化的样态之中,鲁迅一方面要直面“死岛”的“死”,更重要的是需要向死而生。
对于“死岛”的赋形,没有比“坟”更突出的对象。厦门大学的校舍当时营建的位置较为偏荒,林语堂曾在1928年12月6日第28期的《中国评论周报》上有英文《鲁迅》发表,文中有过这样的描述:“那地方的四周是中国人的公共坟地,并不是‘神圣之野’(Campo Santo,按即意大利国内的一公葬场),绝不是呵,不过是一些小山,山上面遍布一些土堆和一些张口于行人过道中的坟坑罢了,这正是普通的公共坟地之类,在那里有乞丐的和士兵的尸体腐烂着,而且毫无遮拦地发出臭气来。”[22]鲁迅在给许广平的信中也多次提及自己穿行坟地的事,而且还特意以坟茔为背景合影,“今天照了一个照相,是在草木丛中,坐在一个洋灰的坟的祭桌上,像一个皇帝”[23](1927年1月2日),并且为这张相片题写“我坐在厦门的坟中间”寄送给川岛。无论是林语堂所叙述的坟地的景象,还是鲁迅亲自给许广平讲述的拍照观感,都与他的“死岛”言说有距离。林语堂渲染的是一种荒冢惨愁的氛围,而鲁迅讲述中洋溢的是独享荒凉的自信,坟地与死气的关联性由来已久,“死岛”上的坟地却在鲁迅的笔下脱离了死的可怖,反而有了衬托死亡,并洞察死亡的功效。文学意象的形构与作家意识密切相关,且不论现代作家中如徐志摩在《契诃夫的墓园》中所说的“坟墓只是一个美丽的虚无,在这静定的意境里,光阴仿佛止息了波动,你自己的思感也收敛了震悸,那时你的性灵便可感到最纯净的慰安”,也不论当代作家中如莫言在《狗道》中描绘“千人坟”所突显的自然主义倾向的平等观,尽管坟的意象的千差万别,但死亡的相对性或绝对性都是作家绕不开的核心。不过,鲁迅在厦门所写的坟的意象有一种超越死亡的冲撞力,《药》《过客》等文章中已经出现过他对坟的写照,在厦门时期选编的文集更是起名为《坟》。1926 年10 月30 日《坟》的《题记》写到,“虽然明知道过去已经过去,神魂是无法追蹑的,但总不能那么决绝,还想将糟粕收敛起来,造成一座小小的新坟,一面是埋葬,一面也是留恋。”[24]41926 年11 月11日《写在〈坟〉后面》又写到:“不过将这当作一种纪念,知道这小小的丘陇中,无非埋着曾经活过的躯壳。”[24]303从留恋到纪念,并非字面上的对人生终点的肯定,更是从现在到终点的路径的选择,这就暗含着他将向死而生确立为自己的人生原则。
一个人的识物惯性和识物方式不会简单地因为某一种外力或内力便形成且固定下来,鲁迅的识物逻辑在厦门时期有着特殊的调适与重组,既延续了早期的重估一切的先锋性,同时对物事和物象的赋形有了超现实性,这种超现实并非鲁迅虚构,而是他真实地看到了风景,并从风景中获得了与生命经历和体验相连的纽带,进而在这种关联中建立了肇始于自然,而超越于视觉上的风景。所以,读者在阅读鲁迅的风景写照时,会有一种印象,既是大众熟视无睹的一种呈现,更是鲁迅深沉体味之后的浮现。这种印象,从景物形态上讲,不一定是风景在公共视野中最鲜明的一面,但是经过鲁迅的有意塑造,已经成为风景的新生,成为风景质地中最应重视的一维。鲁迅丝毫不曾掩饰对死岛的不满,正如他曾经对盲诗人爱罗先珂评价北京是沙漠的赞成,但鲁迅也体会着死岛上一丝一毫的生机,比如“挂旗”,他在《头发的故事》中记载过北京双十节的情形:“早晨,警察到门,吩咐道‘挂旗!’‘是,挂旗!’各家大半懒洋洋的踱出一个国民来,撅起一块斑驳陆离的洋布。”[25]到了厦门,这里的“商民都自动的地挂旗结彩庆贺”,鲁迅为此还说:“我因为听北京过年的鞭炮听厌了,对鞭炮有了恶感,这回才觉得却也好听。”[8]152(1926年10月10日)我们不能就此说,因为有这样的鼓舞,所以鲁迅后来才有对死岛的改造,一方面以“坟”祭旗,另一方面,真的做成“火老鸦”①卓治在1927年1月29日《北新》第23期发表《鲁迅是这样走的》,文中写道:“鲁迅先生离厦门赴广州给人的信中说:‘不知怎地我这几年忽然变成火老鸦,到一处烧一处,真是无法。此去不知何如,能停得多少日。’‘火老鸦’是火烧时飞飏的火星,他落在邻近屋上,也就烧起来了。所以火烧地的邻屋极怕‘火老鸦’。可是,焚烧积污的火老鸦该是被到处欢迎的。”,搅动死海。可是人对事物的发现、理解以及个人认识的建立,未尝不是在这些必然律之外的事件中逐渐受其影响发生形变,鲁迅将自己所看到的景致与过去的经验相对比,由此再现当下的风景。换而言之,如果不是以前的观察结果,那么也难以有此时的风景意识,所以,鲁迅的识物永远地处在一种动态之中。
三
鲁迅在厦门阶段对物与意的倒置,对形的特殊转换,都与这种动态过程有关。这种动态的认同,保证了鲁迅不会孤立地看待一事一物,而总是在一物与他物的多种关系之下进行思辨和考察。由此,识物者的亲历性虽然有强烈的主导力量,但也会因为有比对和相较的如实在场,而使风景脱离一种纯粹心理感觉的镜像反映,而维持恒定的客观性。要成为风景,离不开视觉的捕捉和心灵的沉淀,更重要的是,需要“看”的主体对所见之物的认可。鲁迅对厦门风景却一直有一种转折:“此地风景极佳,但食物极劣,语言一字不懂,学生止四百人,寄宿舍中有京调及胡琴声,令人聆之气闷。离市约十余里,消息极不灵通,上海报章,到此常须一礼拜。”[26]鲁迅对许寿裳所言,正表明厦门美景的“在”与“不在”,美虽在眼前,可那是在人们之间流传的美,鲁迅难以引此美为美,与美景的“在”作为对衬出现的,是对现实的参与度,鲁迅从来不可能以融入的方式去欣赏美景,他总是有一种清醒,有一种距离,使得自己同时看见现象和现象周边的所有关联,他的识物,恰恰在这种“隔”中,变得深刻,变得独异。
总体地看,鲁迅对厦门有两种形容出现的频率最高,一为单调,一为无聊,前者倾向于外部氛围,后者倾向于内部感觉,而且,两者交织作用,互为依存。“此地初见虽然像有趣,而其实却很单调,永是这样的山,这样的海。便是天气,也永是这样暖和;树和花草,也永是这样开着,绿着。”[27]562鲁迅对于厦门的景象判别,“自然”不在首位,“一者这学校孤立海滨,和社会隔离,一点刺激也没有;二者我因为编讲义,天天看中国旧书,弄得什么思想也没有了”[27]562“这里虽然不欠薪,然而如在深山中,竟没有什么作文之意。因为太单调,而小琐事却仍有的,加以编讲义,弄得人如机器一般了。”[28]可也正是这种“自然”的陪衬,鲁迅的反思更为深重,鲁迅的思想资源离不开大体量的文化摄入,但更重要的是他对物事的体验和反思,即他的识物个性。从厦门的风景观到鲁迅对社会、对历史的判识,这中间的推衍,让人看到,自然的审美在鲁迅的识物层级中,处在一个交错的点上,没有孑然的自然,只有被组织的自然。自然若要想成为一种美的构成,那么,其旁边一定有作为主体观察的社会文化以及社会文化现象。因为在鲁迅的知识结构和文化心理结构的作用下,他会对现实社会人生的生存与发展给予更多的重视。
按理说,厦门的风景无论如何都应当在鲁迅的官能和心灵上留下痕迹,然而鲁迅却以极度冷峻的方式表达了对风景的体察和感受。与厦门大学的同事相比,他对风景的感知也是另类,如果说在现代中国的学术版图上,厦门大学像是一座教育的孤岛,那么,在鲁迅《理水》中出现的“文化山”就不是无本之木。文化山上的学者总是受到社会的特殊礼遇,在身份认同中也把自我归于精英阶层。他们的食粮是用“奇肱国的飞车”运来的,因而“所有的是闲工夫”,做研究就和他们用饮食一样,是延续身份的一种象征,所以研究对象与他们不曾有丝毫的生活乃至生存的联系。而这却是现代中国学院知识分子的真实写照,从北到南,无一不是在文化山上自我崇拜与自我迷幻,他们叫卖知识,却不生产思想。就算是对风景的观察,也是一种自我的炫耀。风景在那一部分人的笔下,被写作的主体所遮蔽,让阅读者只能看到写作者对风景的贴牌,却遗落了风景的真实之形状,但是鲁迅用自己特有的把握方式,留下了风景的全貌。从自然风景的体会,到学院文化内部的体验,再到30年代鲁迅在上海对社会革命的细察,一脉相承,对风景的贴牌包含沿袭前人之观点以及夸大主观之判断,与鲁迅后来所批评的“挂扁”一样是缺乏精神意志的显现。
现代作家的游记已蔚为大观,无论是游历海外,还是对中华大地山川的观览,其写作或者延续中国古典文学的文人山水化传统,或者是借助于西方文化的视角来反观本土景观,更有一些作家有新的拓展,比如郁达夫的《屐痕处处》就是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现代旅游业兴盛发展而催生的产物①经过吴晓东详实的考证和严密的分析,“1934年6月现代书局出版的《屐痕处处》一书,反映的是风景游记散文的‘生产’与资本以及政府的新关系。作家游记与政府行为、旅游产业以及出版触媒一起催生了中国现代‘风景的发现’。”(参见:《郁达夫与中国现代“风景的发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2年第10期)。亲临风景,作家都会心弦受牵,而诉诸笔端,沈从文两次重返湘西,成《湘行散记》多篇目②张箭飞从外在人和内在人两种视角,细致而谨严地论证了在《从文自传》《湘行散记》中,沈从文一方面用城里人的眼光看自己的故乡,同时又将自己定位在“本地人”,而作故乡的代言人,由此诠释风景从直觉地占有风景现象到建构风景现象的意义。(参见:《风景感知和视角——论沈从文的湘西风景》,《天津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对比来看,鲁迅有关风景的笔记,无有上述写景的类似表达,鲁迅不会刻意为自己的身份而与一地一景建立联系,而且,常人对风景的判断,总有一个以现时所见去印证记忆和心理结构中存留的风景观念,譬如塞北和江南,便以特定的编码方式在历来的文人书写中一遍又一遍重复。但是,鲁迅几乎格式化了此前的风景言语,这也是他识物的经典性所在,不陷于任何一种知识或权力为主导的风景背景,而强调一种生命的介入所得的比较性的认知。无论是后来去香港,还是定居上海后先后两次返回北平的旅途通信,所有可能写作风景的机会都被他滤过,而且相关的记录更是大异于普通的记游。比如返京的路上,他所突出的是京沪之别,如“这里的空气,真是沉静,和上海的动荡烦扰,大不相同”[8]300(1929 年5 月22 日),“北京不冷,仍无需外套,真奇。(中略——论者注)不似上海文人之反脸不相识也。”[29](1932 年11 月23 日)这俨然就是后来京海之辨所依据的素材。鲁迅的风景观从来都是在其独创的识物律作用下展开实践,这种识物不是简单地以研究对象的现有认识为依托,相反,它抛开了既定的成见,注重对研究对象的了解与认识,阐释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重新赋形,而得到一种新的真实,能够在动荡不居的事变中恒有的真实。鲁迅看到的厦门风景,是经过了他对自然状态以及自然规律的洞悉,并与民族文化、社会文化相关联,以现代中国的一隅,来思考整个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一个精神现象的结果。同时,它又区别于精神化的风景、镜像式的风景,它是鲁迅在个人精神成长和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也饱含着对中国社会思想的感受和体验。这是鲁迅“属己”的厦门风景,一旦作为文学的风景落于纸上,“属人”的厦门风景就消失其中,而且,其风景的思想意义又会无形地注入到鲁迅的识物意识中。在治学路径上,鲁迅对文史材料的有形素材总有超越,而精准地捕获那种文化之根的精神力量;在文艺创作上,又能摒弃那种在局部和细末问题上的纠葛,而从或相近、或相远的联系中,表达和揭示属于个人,更是属于人类的共同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