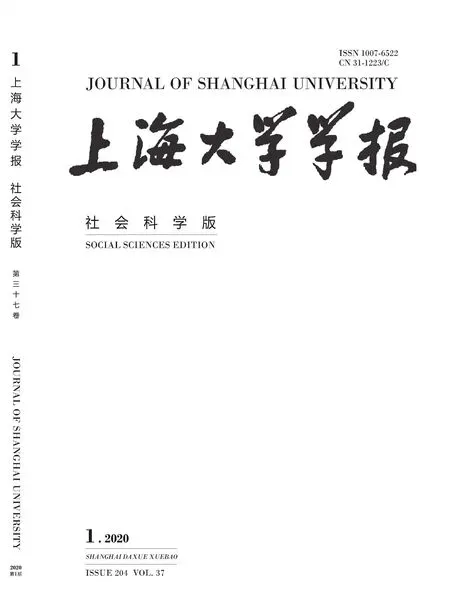被害人视野中的强迫卖淫罪
骆 群
(上海政法学院 刑事司法学院,上海 201701)
强迫卖淫罪是由新中国第一部刑法典规定的“强迫妇女卖淫罪”演变而来,迄今已多次对其进行了修正,但是在理论界和实务部门中产生的争议一直存在。之所以产生这种现象,既有立法技术上的原因,也有社会发展变化带来的脱节。强迫卖淫罪虽然规制的是行为人(强迫者)构成犯罪乃至于承担刑事责任的规范要求,但是其涉及的主体往往除了强迫者之外,还有被害人和嫖娼者。并且被害人因素与强迫者的定罪量刑等各项认定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同时被害人也是强迫者和嫖娼者之间的纽带,从而使得被害人因素对该罪的认定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作用。
一、卖淫的含义
关于卖淫的含义,我国并没有一个法律界定,但个别全国层面的规范性文件中有所涉及。比如,2001年公安部在答复广西壮族自治区公安厅《关于对同性之间以钱财为媒介的性行为定性处理问题的批复》中指出:“不特定的异性之间或者同性之间以金钱、财物为媒介发生不正当性关系的行为,包括口淫、手淫、鸡奸等行为,都属于卖淫嫖娼行为,应当依法处理。”2003年9月24日,公安部《关于以钱财为媒介尚未发生性行为或发生性行为尚未给付钱财如何定性问题的批复》(以下简称2003年《批复》)中指出:“卖淫嫖娼是指不特定的异性之间或同性之间以金钱、财物为媒介发生性关系的行为。”即使如此,公安机关内部的解释也并非完全相同。不过,这些只是公安机关办理案件以及进行行政处罚的依据,对于人民法院审理案件来说并没有法律约束力。
另外,我国省(市)级地方上的规范性文件对卖淫的界定也是各不相同。(1)至于我国省(市)级地方上的规范性文件对卖淫的界定,有学者将其分为两类:一是各省、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发布的禁止卖淫嫖娼条例或规定中的界定;二是各地方人民法院所做的解释。参见徐松林:《以刑释罪:一种可行的刑法实质解释方法——以对“组织卖淫罪”的解释为例》,《法商研究》2014年第6期。至于学术领域,对于卖淫的定义,按照我国传统的观念,有学者认为“卖淫是指妇女以获取金钱或财物为目的,与他人性交的行为,即卖淫的主体仅限于妇女,内容仅限于性交。”[1]85我国刑法学界一致认为卖淫是“以营利为目的,与不特定的对方发生性交或者其他淫乱活动的行为”。[2]599
通观现有的各种解释或看法,对于卖淫含义的理解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卖淫的目的;二是卖淫的主体和对象;三是卖淫的方式。
首先,关于卖淫的目的。
目前,关于卖淫的目的,普遍认为是以营利为目的,或以金钱、财物为媒介,虽然表述不同,但其核心就是以获取物质性利益为目的。不过,笔者认为,将卖淫的目的仅限于获取物质性利益对卖淫所含括的内容进行了限缩。正如有人所作的论证,卖淫是肉体与性服务相分离的,肉体只不过是生产性服务的工具,故而性交易提供的是性服务,而非肉体。于是,卖淫的本质就是出卖性服务的交易行为,“卖”即“交易”,“淫”即“性服务”。[3]47既然卖淫就是用性服务进行交易,那么,交易所获得的利益就可以是性服务载体即具有肉身的人所认为的所有利益,其理应不局限于物质性利益。易言之,卖淫的目的所含括的内容除了物质性利益之外,还应当包括给卖淫者带来的其他利益。比如,卖淫女向小学校长卖淫以获取自己的孩子进入该校就学的机会,卖淫女向外资企业负责人卖淫以获得其丈夫进入该企业工作的机会。(2)当然,有人可能认为这类情形属于性贿赂,但笔者认为性贿赂的本质就是用性服务进行的交易行为,符合卖淫的本质特征,故性贿赂应当属于卖淫的范畴。也许还有人会认为这类情形应属于通奸行为,笔者认为通奸是双方有感情因素的长期且较为稳定的婚外性行为,而卖淫是没有介入感情因素的短暂甚至只此一次的交易行为。
其次,关于卖淫的主体和对象。
虽然传统观念中卖淫的主体只是妇女,卖淫的对象也只局限于男性,但现实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情形已完全打破了传统的认识,不仅男性可以卖淫,而且同性之间也可以卖淫。这一认识已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接受,且在我国的立法或规范性文件中也得以体现。比如,上述公安部的规范性文件中对卖淫嫖娼的解释,以及我国《刑法》中将强迫卖淫罪中之前规定的“强迫妇女卖淫”修改为“强迫他人卖淫”,也是对卖淫主体可以是男性的认可。至于同性之间的卖淫,正如刘宪权教授所说的:“认定同性卖淫是符合刑法原理的,而不需要对此专门作出司法解释或者立法解释。”[4]当然,对此看法的接受前提是建立在卖淫所提供的性服务不局限于性交这一种方式的基础之上的。另外,卖淫对象的不特定性不应是卖淫含义中的限定性因素。虽然现实中主要是对不特定对象的卖淫,但不排除某卖淫者被某些特定的嫖娼者所承包而不再向其他人卖淫的情形。
最后,关于卖淫的方式。
卖淫的方式,也就是卖淫过程中提供性服务的内容。性交方式是最普遍也是最传统的性服务内容,除此之外,还有其他方式在当今社会也普遍得到了认可。对于性交之外的口交、肛交、手淫、鸡奸甚至“乳交”“波推”等行为,哪些可以是卖淫中性服务的内容,尚有较大争议。一种观点认为,卖淫的方式除了性交之外不能包括任意的性行为,只能包括那些与性交行为具有相当性的行为,如口交、肛交等。[1]88也即在我国法律和司法解释均未对卖淫作出明确界定的情况下,根据实践中的情况,将卖淫的方式理解为性交、口交和肛交较为可取。[5]184因为口交、肛交不仅同性之间卖淫可以进行,异性之间也可以进行,并且它们与性交有一个共同特点,都属于进入式性活动。[6]另一种观点认为,卖淫的方式不仅包括传统的性交方式,同时包括只要以身体直接接触的方式实施的口交、肛交、手淫、鸡奸、“乳交”“波推”,甚至还包括同性之间以发泄性欲而进行的“爱抚”等行为。[7]49笔者认为,卖淫行为中所提供的性服务不应该局限于性交、口交、肛交等行为,应当包括所有能够满足性心理的并与性意识相关的直接身体接触的行为。因为性服务并不一定是提供性器官或者对性器官的服务,而是具有性意识、能够满足性心理的身体部位的接触行为。所以,性服务的本质是唤起性意识而满足性心理,并不局限于双向或单向的性器官接触。即使在有身体部位的接触甚至对性器官的接触,若没有性意识下满足性心理的行为,也不能成为性服务行为,比如,医生对病人性器官的检查行为。但是,若病人为了免除疾病的治疗费用,同意医生用手对其生殖器或其他部位进行抚弄而满足他的性心理,这就是病人用性服务进行的交易,应当属于卖淫。之所以需要身体部位的直接接触,不仅是因为身体的直接接触更易于唤起性意识和满足性心理,主要是因为这符合卖淫提供的性服务是依附于卖淫者肉体的本质特性。故而上述第二种观点应当得到认可。
于是,现在我们可以将卖淫的含义理解为:以获得物质性或其他其认可的利益为目的,男女向他人提供性交或其他能够唤起性意识、满足性心理直接接触的性服务而进行的交易行为。
二、强迫卖淫罪之被害人
强迫卖淫罪的被害人,也即被强迫卖淫的人。那么,该罪被害人的范围或特征如何?根据我国《刑法》第358条之规定以及对卖淫含义的解释,强迫卖淫罪的被害人既可以是女性也可以是男性应该并无异议。但是,仍然有四个方面的问题有待于进一步厘清。
第一,妻子、女儿等家庭成员是否可以成为强迫卖淫罪的被害人?过去,在女性的地位极其低下且依附于男性的社会里,女性相当于男性所拥有的财产,男性当然具有对女性包括人身权在内的处置权;同时,家长对家庭成员的绝对权力甚至可以与国家权力相比肩。因此,家长将妻子女儿等家庭成员作为商品进行的交易属于其权力范围之内的行为。但是,在现今社会中,女性与男性不仅具有平等的地位,而且家庭成员在家庭生活中也具有相对独立的地位。于是,作为人身权的性自治权的专属性,也即其只能专属于某个特定的人的特性才真正得以实现。进而言之,一个人的性自治权的行使只能专属于其本人,未经其本人同意,任何人都不能对此予以处置。对于强迫卖淫罪而言,虽然法律没有对家庭成员是否可以成为加害人做出明确规定,但有学者对其中“其他手段”进行列举时有所含括。比如有学者认为:“其他手段,包括以断绝生活来源相威胁,迫使家庭成员卖淫;利用他人走投无路的困境,采用挟持的方法迫使他人卖淫;以迷信方法、欺骗方法蒙骗被害人,达到精神强制的效果,迫使他人卖淫等。”[8]也有人从社会危害性的角度阐述了妻子可以成为强迫卖淫罪的被害人,比如认为:“丈夫强迫妻子卖淫的行为与强迫妻子以外的人卖淫行为的罪质以及行为所体现的社会危害性程度毫无二致,丈夫不享有任何侵犯其妻子人身权利的特权。”[5]199这些观点都为笔者所赞成。家庭成员中,不仅妻子,其他无论是继子女还是养子女抑或亲生子女,性自治权都专属于其自身,任何人都不具有任意处置权,因此,只要具有抚养、赡养关系的一切家庭成员都可以成为强迫卖淫罪的被害人。
第二,强迫卖淫罪的被害人是否包括被强迫卖淫的人之外的人?强迫卖淫罪的被害人,在我国法律中只是规定为强迫他人卖淫中的“他人”,此处的“他人”是否仅局限于暴力、胁迫或其他手段的直接承受者,还是可以包括其之外的人,存在着意见分歧。有学者认为,这些行为必须都是实施在被害人身上,[9]也即强迫卖淫罪的被害人只能是强迫行为的直接承受者。也有学者认为,强迫手段既可以实施在“他人”身上,也可以实施在其之外的“其他人”身上,比如殴打其亲属、朋友从而迫使其卖淫。[7]50其实这也是对被强迫卖淫者的胁迫行为。但根据该学者的表述来看,此种情形的“其他人”不属于强迫卖淫罪的被害人。从现有的观点来看,被强迫卖淫的人属于强迫卖淫罪的被害人,不会存在异议。现在的问题是,没有被强迫卖淫但又承受了强迫者的暴力、胁迫或其他手段的人是否是强迫卖淫罪的被害人?
笔者认为,只要是受到某种犯罪行为直接侵害的人就是该犯罪的被害人,他们之间就存在着犯罪人和被害人为主体的刑事法律关系。若被侵害者为多人时,侵害行为没有将他们作为相互关联的整体时,他们与犯罪人之间形成各自的刑事法律关系,也即他们属于各自犯罪的被害人。比如,甲对乙实施伤害行为,之后又对路上遇到的丙实施抢劫行为,而甲的行为并没有将乙和丙作为相互关联的整体,故而乙是故意伤害罪的被害人,丙是抢劫罪的被害人。但是,在被侵害者为多人的情况下,若侵害行为将他们作为相互关联的整体时,那么,他们都是与犯罪人相对的一方处于同一个刑事法律关系之中,也即都是该犯罪行为中的被害人。比如,甲绑架乙而向丙勒索财物的犯罪行为中,乙和丙都是该绑架罪的被害人。针对强迫卖淫罪而言,受到暴力等强迫行为的人与被强迫卖淫的人在强迫者眼里属于相互关联的整体,所以,他们都应当是强迫卖淫罪的被害人。
第三,无意识或减弱意识能力的人是否可以成为强迫卖淫罪的被害人?无意识或减弱意识能力的人由于他们认识能力的缺失或减弱,从而使得他们难有真实明确的表达和控制能力。这类人群主要是指不满14周岁的幼女,智障人员,精神病人员,醉酒、熟睡或被麻醉的人员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于2017年7月21日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组织、强迫、引诱、容留、介绍卖淫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2017年《解释》)中对强迫卖淫罪的“情节严重”的规定,智障人员和不满14周岁的幼女可以是强迫卖淫罪的被害人。至于不满14周岁的幼女属于法定的特殊情形,在此不予讨论,相关内容将于下文讨论。
所谓智障人员,一般是指大脑功能水平存在实质性缺陷的人员,他们主要表现为智力功能水平明显低于正常水平。并同时存在多项精神活动方面的异常或迟滞,如沟通、自理生活、家庭生活、社会生活、社区认可、休闲娱乐、安全技能、学习等方面。属于多基因人类遗传病。病灶在患者体内的遗传(基因)系统里。分高度智障、中度智障、低度智障。(3)百度百科对智障人的解释。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9%BA%E9%9A%9C%E4%BA%BA/173931?fr=aladdin.不过,从医学角度来看,智障不同于精神病,一般认为在认知的能力缺失方面,精神病要比智障还要严重。
另外,有人对强迫卖淫罪的强迫手段的“其他方法”中也提出了醉酒、熟睡和麻醉的人可以成为强迫卖淫罪的被害人,比如有学者认为:“所谓其他方法,是指利用被强迫人患病、醉酒之机,睡觉或被麻醉之时,致其处于无力反抗或不知反抗的状态。”[2]722那么,这类人群是否都应当成为强迫卖淫罪的被害人,笔者认为不能一概而论。
强迫卖淫罪的本质特征是强迫他人提供性服务而进行交易,被强迫卖淫的人只是性服务的生产者,其被迫实施的性服务从商品的两个属性来看,“能够满足人的心理与生理上的需求,从而具有使用价值。生理需求源自于人的自然本能,心理需求则或者源自于男人占有尽可能多的性资源的内心欲望,或者源自于男人表现自身男性气概的欲望,等等。并且,性服务之中也凝结了人类的抽象劳动,这使得性服务具有价值”。[3]46也就是说,强迫者是将被强迫卖淫的人实施的性服务作为商品与嫖娼者进行交易。那么,作为嫖娼者也是知道自己在购买这种特殊的商品。若性服务不具有商品的属性时,此时进行交易的是人的肉体,即人本身,而人本身无论是整体还是部分都是不允许进行交易的。无意识或减弱意识能力的人被强迫者提供给嫖娼者并没有凝结人类抽象劳动,不具有商品的属性,故而不允许交易。言下之意,嫖娼者若知道(包括确知和应知)卖淫者是无意识或减弱意识能力的人,也即提供的性服务不具有商品属性时,虽然有一定的付出,也不具有商品交易的特性,此时,嫖娼者难辞其咎,可能构成强奸罪或强制猥亵他人罪。而强迫者此时是片面帮助犯,也应构成强奸罪或强制猥亵他人罪。因为对于强迫者来说,其不仅对提供的性服务不具有商品属性的事实有认识,同时也明白自己的强迫卖淫行为为嫖娼者的行为提供了帮助。于是,强迫者构成犯罪出现竞合情形,应当择一重而论处。至于强迫卖淫罪与强奸罪或强制猥亵他人罪孰轻孰重,要根据具体案情所对应适用的量刑档次进行比较。当然,嫖娼者不知道提供的性服务不具有商品属性时,也即其自认为是在进行一种特殊商品的交易行为——嫖娼,根据现有的法律规定,卖淫嫖娼是不追究刑事责任的,故其不构成犯罪。但是,强迫者仍然构成犯罪,应当构成强迫卖淫罪。
因此,对于现有的规定和看法,笔者认为,对于强迫无意识或减弱意识能力的人卖淫的情形不加区分地一概认为强迫者都构成的是强迫卖淫罪,这是与强迫卖淫罪的本质特征不相符合的。总而言之,无意识或减弱意识能力的人在被强迫卖淫的过程中,他们未必都是强迫卖淫罪的被害人,也可能属于强奸罪或强制猥亵他人罪的被害人。
第四,不同年龄段的人是否都一定能够成为强迫卖淫罪的被害人?强奸罪和强制猥亵他人罪的构成必须以被害人不同意为要件,而理论界一般认为,未满14周岁的儿童无性行为的同意能力,也就是说对他们实行的是严格责任。但是,现有的规定又并非一以贯之。于是,出现争议较大的问题就是,未满14周岁的儿童是否一定能够成为强迫卖淫罪的被害人?笔者认为,不能一概而论,未满14周岁的儿童也有可能不能成为强迫卖淫罪的被害人。
首先,看看强迫未满14周岁的幼女以性交的方式卖淫的情形。有学者认为:“嫖宿幼女罪取消后,幼女不再成为组织卖淫罪、强迫卖淫罪的对象,对于组织、强迫未满14周岁的幼女进行性交易的行为,通常应当以强奸罪的共犯论处,已满14周岁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仍然可以成为组织卖淫罪、强迫卖淫罪的对象。”[10]也即未满14周岁的幼女不可以成为强迫卖淫罪的被害人。但是,2017年《解释》又将未满14周岁的幼女规定为强迫卖淫罪的被害人。笔者认为,这种一刀切的认识和规定都是不可取的。因为根据我国现有的规定,与未满14周岁的幼女发生性关系的未必一定都构成强奸罪。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关于审理强奸案件有关问题的解释》规定:“对于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对于与幼女发生性关系,情节轻微、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不认为是犯罪。” 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关于行为人不明知是不满14周岁的幼女双方自愿发生性关系是否构成强奸罪问题的批复》中规定:“行为人明知是不满14周岁的幼女而与其发生性关系,不论幼女是否自愿,均应依照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以强奸罪定罪处罚;行为人确实不知对方是不满14周岁的幼女,双方自愿发生性关系,未造成严重后果,情节显著轻微的,不认为是犯罪。”虽然该《批复》出台之后引起了非常大的争议,以至于几个月后即被停止实施,但是对强奸罪中不完全适用严格责任的理念还是被2006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为2006年《解释》)及2013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发布的《关于依法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见》(以下简称2013年《意见》)所继承。其中,2006年《解释》明确: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偶尔与幼女发生性行为,情节轻微、未造成严重后果的,不认为是犯罪。2013年《意见》明确:对于不满12周岁的被害人,仍然适用严格责任,即无需行为人明知被害人未满12周岁,但对于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的被害人,需要行为人明知是幼女,且只要从其身体发育状况、言谈举止、衣着特征、生活作息规律等观察可能是幼女即可。
通过以上的规定可以看出,嫖娼者若是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即使知道卖淫者未满14周岁,也可能不构成强奸罪。嫖娼者若不是明知卖淫者是未满14周岁的人,也可能不构成强奸罪。所以,对于强迫未满14周岁的幼女卖淫时,当嫖娼者构成强奸罪时,强迫者形成强迫卖淫罪与强奸罪的竞合关系,幼女未必一定属于强迫卖淫罪的被害人。当嫖娼者不构成强奸罪时,强迫者构成强迫卖淫罪,此时,幼女是强迫卖淫罪的被害人。
其次,再看看强迫未满14周岁的儿童以性交以外的方式卖淫的情形。由于我国强奸罪的构成只是性交的方式才能构成,性交之外的性行为构成的是强制猥亵他人罪。根据2013年《意见》的规定,猥亵儿童若造成儿童轻伤以上后果的,可能构成的是故意伤害罪或故意杀人罪。那么,强迫不满14周岁的儿童以性交以外的方式卖淫,强迫者也有可能构成强迫卖淫罪与故意伤害罪或故意杀人罪的竞合关系。也就是说,此时不满14周岁的儿童也未必一定就是强迫卖淫罪的被害人。
三、强迫卖淫罪被害人之不同意内容
强迫卖淫罪的成立还需要被害人不同意卖淫这个要件,当然,这是一个规范要件,而非事实要件。因为对于某些特殊群体的保护,比如精神病人,即使其事实表现出来的是同意,但法规范仍然视为不同意。目前,虽然《刑法》中被害人不同意的要件没有明确予以规定,但这是隐含在“强迫”之中不言自明的要求。不过,我国台湾地区“刑法”中有类似于大陆强迫卖淫罪的规定,即“意图营利,以强暴、胁迫、恐吓、监控、药剂、催眠术或其他违反本人意愿之方法使男女与他人为性交或猥亵之行为者,构成强制使人为性交或猥亵罪。”[11]但是,在强迫卖淫的过程中,对于嫖娼者而言,被害人呈现出来的又是同意卖淫,否则嫖娼者就有可能构成强奸罪或强制猥亵他人罪。那么,被害人对于强迫者的不同意与对于嫖娼者的同意的内容是否应当一致?以及他们不同意和同意的内容具体何指?这在复杂的现实生活中并非简单明了,需要作进一步的深入分析。
强迫卖淫罪的被害人不同意卖淫而在暴力、胁迫或其他手段下又被迫同意卖淫,也即被迫同意以自己的性服务进行交易。虽然性服务的内容除了性交之外还有口交、肛交等各种满足嫖娼者性心理的行为方式,但是,被害人在不同意或被迫同意时不必对所有行为方式达到统一反对或被迫同意所有的卖淫方式,即可构成强迫卖淫罪成立要件中的被害人不同意。比如,被害人对以性交的方式进行卖淫是表示同意的,但对性交之外的口交、肛交等方式表示不同意,后在暴力、胁迫下被迫同意以口交、肛交等方式卖淫,强迫者应当构成强迫卖淫罪。即使此时被害人还没有进行其之前不同意而现在被迫同意的口交、肛交等方式卖淫,而是以其之前同意的性交方式卖淫,假若符合组织卖淫罪的构成要件,也不定为组织卖淫罪,而应当定为强迫卖淫罪。(4)虽然我国《刑法》第358条将组织卖淫罪和强迫卖淫罪规定在同一法条,适用相同的法定刑,也即据此不能看出两罪之间的轻重。但是,根据2017年7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关于办理组织、强迫、引诱、容留、介绍卖淫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对这两个罪的“情节严重”的解释来看,组织卖淫罪要轻于强迫卖淫罪。比如,组织卖淫罪的“情节严重”须“卖淫人员累计达十人以上”,而强迫卖淫罪的“情节严重”须“卖淫人员累计达五人以上”。因为对于同一被害人而言,其提供的性服务应作整体评价,并且以对其最有利(对行为人最不利)的标准予以判断。对被害人最有利的标准就是对被害人来说行为人对其造成的危害性最大,这是保护被害人和惩罚行为人的必然要求。显然,被害人不同意的性交方式卖淫相对于被害人来说对其造成的伤害要大于被害人同意的性交方式的卖淫。言下之意,只要被害人对性服务的方式中的一项不同意,行为人即构成强迫卖淫罪成立所需要件中的被害人不同意,而无需对所有性服务方式的不同意。
总而言之,对于强迫者来说,被害人不同意的内容只要是概括的性服务方式即可,而不以具体方式为要件,即使被害人对某些具体的方式表示同意,也不影响强迫者强迫卖淫罪的构成。
对于嫖娼者而言,被害人呈现出的是对性服务方式的同意,但其同意的内容要排除被害人自始没有同意且得到强迫者认可的方式,否则嫖娼者可能构成强奸罪或强制猥亵他人罪。比如,被害人虽然受到强迫者的暴力、胁迫等方式的强迫,但始终并没有同意以肛交的方式进行卖淫,而只是被迫同意以其他方式进行卖淫,后来得到了强迫者的认可,那么,肛交的方式就不属于被害人对于嫖娼者的同意内容,若嫖娼者非要以肛交的方式进行嫖娼,嫖娼者可构成强制猥亵他人罪。据此,我们是否可以认为被害人对于强迫者不同意的内容与对于嫖娼者同意的内容应当一致呢?还不能。因为还可能存在被害人并非因为强迫者的强迫而自始同意的情形,这显然不属于被害人对于强迫者不同意的内容,但属于被害人对于嫖娼者同意的内容。比如,被害人自始是同意以性交的方式卖淫,但不同意以口交、肛交的方式卖淫,后在强迫者的强迫之下,被迫同意以口交、肛交的方式卖淫。在这里,被害人对于强迫者的不同意内容是口交、肛交的方式,而不包括性交的方式,但对于嫖娼者而言,被害人同意的内容既包括口交、肛交的方式,也包括性交的方式。也就是说,被害人对强迫者不同意的内容与对于嫖娼者同意的内容有时也并非一致。
四、被害人对强迫卖淫罪犯罪形态之影响
我国《刑法》对犯罪形态中的既遂标准并没有明确予以规定,既遂的标准可以说是游离于实定法之外的理论抽象,故而一直以来存在着多种学说。但《刑法》又有规定,对于预备犯,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对于未遂犯,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对于中止犯,没有造成损害的,应当免除处罚,造成损害的,应当减轻处罚。据此可以看出,对某一罪既遂的认定就成为其他犯罪形态的处罚关键,同时还可以看出,对犯罪形态的认定主要适用于量刑。那么,对于强迫卖淫罪的既遂标准,理论上也同样存在不同的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强迫卖淫罪是行为犯,“只要行为人出于迫使他人卖淫的目的而对他人实施了暴力、胁迫或者其他强制手段,即可构成既遂,而不要求被害人答应卖淫或者实际从事了卖淫活动”。[12]
第二种观点认为,强迫卖淫罪的既遂,“应当是行为人实施了强迫行为,被害人主观上因被强迫行为而意志不能自主,客观上着手实施违背自己意愿的卖淫行为之时”。[1]98也即只要行为人实施了强迫他人卖淫的行为,他人也被迫进行了卖淫活动,即使未能完成卖淫活动,强迫卖淫罪就已既遂。[5]193
第三种观点认为,强迫卖淫罪是结果犯而非行为犯,它具有行为人的强迫和被害人“被迫就范”两个因素,因此只有被害人在行为人的强迫之下实施了卖淫行为,才能既遂;即使行为人的强迫行为已经实施完毕,但由于行为人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没有发生与他人卖淫的犯罪结果的,属于犯罪未遂。(5)详见赵秉志主编:《中国特别刑法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656页。这种观点的前半段表达的意思与第二种观点是一致的,只是后面所说的“与他人卖淫的犯罪结果”是否属于卖淫活动的完成,语焉不详。因为根据公安部1995年8月10日下发给河北省公安厅的《关于对以营利为目的的手淫、口淫等行为定性处理问题的批复》指出,卖淫嫖娼是一个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卖淫妇女与嫖客之间的相互勾引、结识、讲价、支付、发生手淫、口淫、性交行为及与此有关的行为都是卖淫嫖娼行为的组成部分。因此,对于作为一个过程的卖淫活动,若此观点中“与他人卖淫的犯罪结果”表达的是无需卖淫活动完成的意思,那么,这种观点就与第二种观点相同。不过,笔者在此将“与他人卖淫的犯罪结果”理解为需要卖淫活动完成的意思,也就是说,被害人卖淫活动结束后方可构成既遂。
在笔者看来,以上观点都没有恰当地给出强迫卖淫罪的既遂标准。因为既遂的标准是为了给其他犯罪形态提供处罚的基准,也就是在量刑时为了实现罪刑相一致的处罚原则,而这又以行为人的社会危害性为根基。在强迫卖淫罪中,强迫者的社会危害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被害人因素。
于是,对于上述第一种观点,强迫者只要实施了暴力、胁迫或其他手段强迫被害人卖淫的,就构成既遂,这种完全不顾被害人因素的看法难以具有科学性。首先,这会完全排除中止、未遂的成立,将犯罪既遂标准与犯罪成立标准混为一谈,也使犯罪既遂的认定失去了意义。当然,从现实来看也会出现对强迫者不公正的情形。比如,强迫者在对被害人进行暴力、胁迫其卖淫时,忽然幡然醒悟而停止了其强迫行为,若按照此种观点强迫者仍然构成既遂,显然有失公允。其次,在被害人还没有被强迫者的强迫行为所控制时即对其认定为既遂,也有违刑法的谦抑精神。比如与普遍认为属于结果犯的故意伤害相比,甲欲伤害乙,乙毫发未损反而将甲制服,甲不构成故意伤害罪的既遂,一般并无异议,而在强迫卖淫中出现被害人的意志并没有被控制的情形时认定行为人既遂,显然也是违背刑法谦抑精神的。因此,将强迫卖淫罪作为不考虑被害人因素的行为犯是不科学的。
对于上述第二种观点,即被害人被强迫后实施卖淫行为时,无需卖淫行为完成,强迫卖淫罪既遂的看法,也有违法理。首先,被害人在被强迫后其身体或精神受到控制而被迫同意卖淫时,其性自治权就已受到侵害。因为此时被害人的意志已被强迫者所控制,之后的卖淫行为只是其随时可实现的后续行为。另外,其后续行为也主要发生在被害人与嫖娼者之间,而他们之间的关系并非刑事法律关系,也不属于强迫卖淫罪的刑事法律关系。强迫卖淫罪的刑事法律关系只存在于强迫者和被害人之间。因此,被害人实施的卖淫行为只是其性自治权受到侵害的具体表现形式,只是体现强迫者意欲得以实现的距离变得较近。其次,我国强迫卖淫罪是置于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之下,除了卖淫属于妨害社会治安管理秩序的行为,强迫者对被害人实施的强迫行为也属于妨害社会治安管理秩序的行为,故而无需被害人实施卖淫行为时才是对社会治安管理秩序的侵害。退一步来看,即使认为被害人实施卖淫时才是对社会治安管理秩序的侵害,但根据刑法理论,在复数法益的情况下,只要侵害一个法益时就构成既遂。于是,对于强迫卖淫罪而言,在被害人实施卖淫行为之前意志受到控制使其性自治权受到侵害时犯罪就已经既遂。最后,卖淫在我国属于一般违法行为,而不属于《刑法》规制的行为,若在强迫卖淫罪中将其纳入《刑法》的评价范围,有违现有刑事政策的价值取向。其法理就如盗窃罪所体现的,若行为人盗窃了100元人民币,由于盗窃100元人民币没有进入我国《刑法》的评价范围,因此行为人只是一般违法行为。若行为人以珍贵文物为盗窃目标的,由于“以珍贵文物为盗窃目标”进入了我国《刑法》的评价范围,从而对盗窃罪的既遂和未遂产生影响。所以,作为一般违法行为的卖淫不应成为强迫卖淫罪构成中的评价因素。
对于上述第三种观点,其不足之处与第二种观点相同。只是被害人卖淫行为由于意志以外的原因在完成之前停止的,按照第二种观点已构成既遂,但按此观点应构成未遂。显然,这种观点使得对强迫者的惩罚过于滞后,也有些不合理。比如,嫖娼者事后在没有支付嫖资的情况下,这时卖淫的过程还没有完成,若强迫者只构成未遂,可能难以被人们接受。
综上,笔者认为,强迫卖淫罪虽然被置于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之下的一个罪名,但同时侵犯的作为被害人人身权的性自治权是其重要特征。因此,其犯罪形态的认定中被害人因素起到了关键作用。当被害人的意志因受到强迫者的强迫行为而被强迫者控制时,强迫卖淫罪构成既遂。即使之后被害人自愿卖淫的,也不影响强迫者构成强迫卖淫罪既遂的事实。在被害人的意志没有受到强迫者的控制之前,若由于强迫者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的,构成未遂。若强迫者自动放弃强迫行为或者有效阻止被害人产生卖淫意识的,构成中止。至于既遂之后被害人是否已经实施卖淫活动,或者卖淫活动进行到何种程度,只对强迫者的量刑产生影响。
五、结语
卖淫在我国不构成犯罪,但强迫他人卖淫而从中获利的行为受到《刑法》的否定评价,并以强迫卖淫罪对此种行为进行了规制。在强迫卖淫罪的认定中,不仅涉及强迫者和被害人,而且还有嫖娼者的介入,从而使该罪变得复杂化。但是,被害人因素在其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关键作用。所以,从被害人视角对强迫卖淫罪的相关问题分析不失为是一种可行的路径。除了本文阐述的强迫卖淫罪的被害人范围、被害人不同意的内容以及被害人对犯罪形态的影响之外,还有被害人因素对侵害法益之影响,对罪名之间界分的影响,对刑罚适用之影响等等,这都有待于进一步作深入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