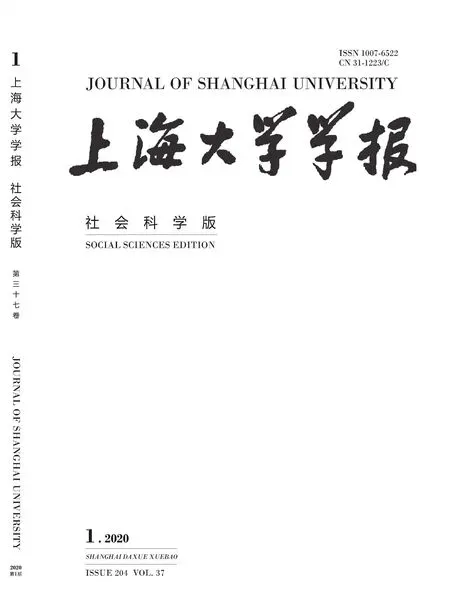本土、异域与形式的演变:从施蛰存的“妻子”谈起
罗 萌
(华东师范大学 国际汉语文化学院,上海 200062)
一、“妻子”:形式与主题
在《我的创作生活之历程》(1933)一文中,施蛰存提及20世纪20年代末在《无轨列车》上的发表经历:“于是我在第一期上写了几段《委巷寓言》,在第四期上写了一篇完全摹仿爱仑·坡的小说《妮侬》。在这时期以前,我所写的作品大部分都是习作,都是摹仿品。”[1](1)此引文中的爱仑·坡,与下文中出现的爱仑·坡、亚伦坡,所指是同一人,因译本不同译名有所差别。《妮侬》(1928)并未收入施蛰存的任何个人选集,直至2011年《十年创作集》出版,才作为“集外”一篇收录其中。可以猜想,《妮侬》并非施蛰存的得意之作;在此语境中,所谓“摹仿”的定论也可能是一种对早年实践的自我批评。根据施后来的自述,[2]678以及他对阿图尔·施尼茨勒(Arthur Schnitzler)作品的翻译,文学史一般更重视这位奥地利作家对他的影响。研究界对《妮侬》的讨论极少,但毋庸置疑,爱伦·坡(Allan Poe)是施蛰存在二三十年代最关注的西方作家之一。除了自认的“仿作”之外,他曾数次谈及这位美国作家。1934年,在《现代·美国文学专号》的导言中,他把象征主义看作美国文学创造力的代表,因为“主要的虽然是法国的产物,但是根底上却是由于美国的爱伦·坡的启发”。[3]1181在《从亚伦坡到海敏威》(1935)中,施蛰存把标题中两位美国作家的区别作为对19世纪以来短篇小说的不同点的概括:“亚伦坡的目的是个人的,海敏威的目的是社会的;亚伦坡的态度是主观的,海敏威的态度是客观的;亚伦坡的题材是幻想的,海敏威的题材是写实的。”[2]464在这一陈述中,施蛰存并未明显表现出个人偏好,不过显然,作为公认的新感觉派代表人物,他更多被当代批评家贴上“色、幻、魔”“色情-怪诞”(2)可参见[美]李欧梵著,毛尖译《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67-202页;[美]史书美著,何恬译《现代的诱惑:书写半殖民地中国的现代主义(1917-1937)》,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84-420页。等标签,肯定了他与爱伦·坡之间潜在的亲缘关系。
尽管施蛰存未作标注,但不难发现,《妮侬》受到两篇爱伦·坡小说的影响——《丽姬娅》(“Ligea”)和《莫蕾娜》(“Morella”)。前者讲述了“我”过世的妻子丽姬娅凭借后妻的身体复活的故事。在《莫蕾娜》里,亡妻留下的女儿和她别无二致;后来,女儿亡故,“我”发现坟墓里没有妻子的痕迹,仿佛她俩原本就是一人,于是在惊恐中陷入癫狂。两篇短篇小说的共同之处,除了魔幻诡异的气氛营造以及第一人称的使用外,还有女性形象的塑造:无论丽姬娅还是莫蕾娜,都学识广博,无所不通,对男性具有至高的支配权,举手投足充满神秘感,“我”在其面前,好像一个孩子,既迷恋又压抑。两者均超出了具体个人的限度,成为一种超现实、不可控制的神性力量。《妮侬》在氛围铺陈方面借鉴了《丽姬娅》,使用“好几百年”“忘却了悠久的岁月”等描述语,将叙事置入一种永恒的时间体验之中;另外,外貌描写方面也可见摹仿痕迹:
我曾端详过那高洁而苍白的额顶——真是白璧无瑕,实际上,用这个字眼来形容如此圣洁的端庄是多么平淡!那象牙般纯净的肌肤,那宽阔而恬静的天庭,左右鬓角之上那柔和的轮廓,然后就是那头乌黑、油亮、浓密而自然卷曲的秀发,真是充分解释了荷马式形容词“风信子般的”之真正含义!(《丽姬娅》)[4]73
那时候,妮侬,我瞧着你,用小心的眼色,瞧你有着庄严的形相,你底脸,你底嘴,你底腮,如幽谷中的百合,你有深黑而光泽的发,如夕照中的鸦。你有精湛的眼,如水滨的鸽。你有挛生的小鹿俯伏在喜马拉雅山万古不融的积雪似的胸前,你有着云石,白玉和象牙的肢体,你是个封闭着的花园。(《妮侬》)[5]596
除了对女性的超时空性和神圣感的有意识效仿之外,因为跨语际迁移的缘故,使得“妮侬”的形象带上了一定程度的异域色彩,同样弥散出迷幻气息。但是,即便吸收了某种超现实基因,《妮侬》与《丽姬娅》《莫蕾娜》之间的区别还是显而易见:一方面,《妮侬》综合了《莫蕾娜》中的叙事走向(“异常的爱慕”向不知名的“恐怖”转化,最终以妻子的死亡为解脱)和《丽姬娅》中的“复活”意象;另一方面,爱伦·坡小说里的超自然因素,移植进《妮侬》之后,似乎更多作为一种修辞存在,而非真正的魔幻。“妮侬”最终“死而复生”的场景是这样描述的:
我在战栗中,凝视着她底尸体,那样地纯洁,那样地无瑕。我凝视着,凝视着,我从梦中觉醒了。啊,是我底妮侬,我底妮侬!我喊着。然而她不能再应我了!不能再应我了!
我紧啮着唇抬起头来,我看见斜阳从窗棂间射上古璧,啊!她底画像,在斜阳中显现着永久的红色。啊,妮侬,永生的情人!
……
“啊,你吸血鬼,你妄虚的妖魔!”我喊着:“一切的形相,一切的声音,一切的彩色,一切的香味,都会因着妮侬永生!啊,妮侬,从一切的残毁中获得了永生的妮侬,我底情人,你还活着!”[5]599
此地,女主人公妮侬所谓的“复活”,只不过是通过她留存的画像,在“我”的心中得以永生。那幅“她处女时候的画像”,妮侬病重时要求“我”挂在墙上,她预感到自己的死亡:“我底情人,来,我底情人,那黑色的日子到了,那黑色的日子,是的,便是今天。我底情人,我知道我们底结婚撕碎了我们生命底彩衣,摔断了我们爱恋底葛籐。”[5]599在这一语境下,前文中看似诡异的一连串呼告:“不啊!我底妮侬,non!她不是妮侬,她不是妮侬!……哦!我发现了,我终于发现了!不是这个人呀!”[5]598也变得很好理解:少女妮侬的“变”来自婚姻的摧残,或者说,来自“我”不堪忍受的生活对理想女性的“祛魅”:“从她无邪的唇间渐听得了经验的字句,从垂睫的眼睛里渐发觉憎厌和寂寞的眸子……啊!至今遗留着给她的,只是人间的,可怜的,纤小的妮侬……”[5]597是“我”爱情的冷淡加剧了妮侬的毁灭。而最终,在“我”眼里,她肉体的消逝竟成了让她曾经的美获得永生的唯一途径。
如果说,爱伦·坡的小说里充斥着“理性很少起作用”[4]86的无边幻象,那么,施蛰存的“仿作”《妮侬》则将谵妄体验相对合理化、生活化了。这种改写,或许是出自施对爱伦·坡作品的个人解读,也可能是他自己不愿意陷入谵妄,而试图将叙事理性化。无论如何,《妮侬》是一次充分体现能动性的“摹仿”实践,而非单纯的搬套。在施蛰存的早年作品中,《妮侬》中婚姻的折磨以及丈夫以冷漠摧残妻子生命的情节模式,业已存在。1923年,施蛰存自费刊印第一部短篇小说集《江干集》(署名“施青萍”),其中一篇《冷淡的心》,堪称《妮侬》的先声。小说主角陶雯是一个新派学生,服从家里安排,娶了一位何女士。因为没经过自由恋爱,陶雯坚信自己和妻子之间不会有爱情,成日冷脸相对,妻子则日益陷入抑郁。后来,他们有了孩子,妻子因为孩子转移了注意力,情绪好转;但对陶雯来说,那不是爱情的结晶,他仍旧爱理不理。有一天,他突然因为婴儿的笑脸激发了热情的冲动,继而奇迹般地发现自己对妻子的情感。和《妮侬》相比较,《冷淡的心》立足日常生活情境,且设置了一个解决了矛盾的结局,但两者的主题是相关的。而且,无论是《冷淡的心》里的包办婚姻,还是《妮侬》中以爱情为先决条件的婚姻关系,结婚开始的那一刻,都被呈现为“不祥”的开端:
于是在一个好日子上,他终竟痴痴地做了一个旧式婚姻中的新郎。(《冷淡的心》)[5]478
在狂欢的节日中的春雷似的鼓吹里隐隐地已听得了萧寺里的丧钟哀磬!啊!那被咒诅的日子啊,它将黑暗从光辉里抛出,它将地狱从天国中分开。那被诅咒的七月初二!
在那个不祥的日子,我没有顾到两个不幸的灵魂在幽隐处叹息,……啊!她是这般娇弱不胜,我是这般痴愚!在红烛光中,青油幕下,我们竟演映了虚妄的人间幻景。(《妮侬》)[5]597
两处皆突出了“婚礼”的表象与实质之间的反差;当然,后者以一种极度铺陈的手法,将前者简约语言中包含的社会判断抽象化、迷幻化了。
一般来说,对施蛰存小说的讨论,往往从形式出发;然而,倘若对施氏创作中高频率出现的主题作出辨别和梳理,可能会发现一种与我们习惯的论述视角“颠倒”的情况:不一定是在形式创新的前提下,引导出相应的主题;而是在已有主题的基础上,进入不同的形式。施蛰存创作《冷淡的心》时,年方18,尚未婚配;(3)1928年11月,施蛰存与陈慧华女士在松江举行婚礼,参见沈建中编撰《施蛰存先生编年事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122页。但从那时起,以“夫妻关系”为主导的小家庭生活就成了他小说创作最重要的主题之一。这一点,与新感觉派另外两位旗手形成鲜明区别——穆时英和刘呐鸥的作品殊少涉及婚姻生活。这一创作主题的偏好,或许同他早年在《礼拜六》等通俗文学刊物上的发表经历以及与鸳鸯蝴蝶派作家的私人交集有关,因为婚姻生活、夫妻关系一向是鸳鸯蝴蝶派最热衷的话题之一。 从特定主题与不同形式之间的互动关系入手,我们或可丰富和补充对施蛰存小说的解读,考察形式对主题的拓展能力,并进一步对他走入继而走出“魔道”[5]624的创作历程展开整体性诠释(虽然早在1936年,施蛰存已经完成了他最后一本小说创作集《小珍集》,此后投身于散文写作、文学翻译、古典文学以及碑帖研究的学术工作)。
二、非家幻觉:被颠覆的在地性
1933年对于“文学史中的施蛰存”而言,极为重要。同一年中,其小说集《梅雨之夕》和《善女人行品》出版。(4)1933年3月,《梅雨之夕》由上海新中国书局初版印行;同年11月,《善女人行品》由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初版印行。这两部小说集中的部分作品,后来成为施蛰存小说研究的主要关注篇目,譬如《梅雨之夕》《在巴黎大戏院》《魔道》《春阳》等。在《〈梅雨之夕〉自跋》中,他强调本集中数篇与1929年8月初版、1931年初重版的《上元灯》“气氛完全不同”,区别在于《梅雨之夕》收录的作品“都是描写一种心理过程的”。[6]39另在《〈善女人行品〉序》中,施把文集主题定位为“一组女体习作绘”,“完全研究女人心理及行为的小说”。[6]41-42可见两部小说集均提倡创作革新,且在方法上具备共通性,即重在心理描写。不过,就形式风格而言,两者并非孪生姐妹,简单说来,《善女人行品》的叙事氛围基本是写实的,所涉及女性形象,如施所说,“都是我近年来所看见的典型”;[6]42《梅雨之夕》则谈不上人物典型性,而专注于“非常心理”的探讨,行文间充斥着神秘感和魔幻色彩。相比《善女人行品》,《梅雨之夕》显然更富于形式震撼力,也因此被标榜成作者作为新感觉派的代表作,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其他作品的存在感。
当然,这么说的目的不在于贬低《梅雨之夕》,进而提升其他作品的地位,而是为了提供一种提示:由于过度聚焦某一种形式,我们或许忽略了主题本身的稳定性及其在不同形式之间流动的能力。无论《梅雨之夕》《善女人行品》,还是更早的《上元灯》,皆维持了对家庭生活书写以及妻子形象塑造的偏好,以前两者为例,小说集《梅雨之夕》中的《梅雨之夕》《在巴黎大戏院》《魔道》《四喜子的生意》和《凶宅》,以及《善女人行品》里除《雾》和《特吕姑娘》之外的10篇作品,都涉及婚姻家庭生活。相比起《冷淡的心》《妮侬》里忐忑不安的新婚,这些作品所呈现的往往是更为习惯化的婚姻状态;在这种具有某种恒定性的关系里,男性和妻子处在各自相对稳定的位置上。在《梅雨之夕》一辑中,我们可以看到那种类似穆时英和刘呐鸥笔下的符号化的女性,只不过,她们并非与都市空间天然绑定的摩登女郎,有能力令男性在她们的速度和能量面前自惭形秽;她们往往具有妻子的身份,或者说,她们是“家里的女人”。相对于妻子的静止,作为丈夫的男性游移在家庭/私人空间和城市/公共空间之间。不过,男主人公并未因此获得支配地位;相反,他们常常在妻子显在或潜在的目光里感到惴惴不安。
《魔道》里的男主人公从城市出发前往乡村,在火车车厢(一个可能引发私人性错觉的封闭的公共空间)里,“我”的内在性被激发了。一瞬间,周遭世界变成魔境。令人毛骨悚然的魔幻感伴随着“我”进入乡村,又再度回到城市。这种恐怖的魔幻感首先来自具有异域色彩的想象活动。值得一提的是,“我”在自由联想时,本土化的本体指向了西化的喻体:中国老妇人被比作骑着笤帚的西洋女巫,窗外绿野中的大土阜被比作“某一朝代某王妃的陵墓”,“里面躺着一个紧裹着白绸的木乃伊”,“曳着她的白绸拖地的长衣”,有着“放散着奇冷的麝香味的嘴唇”,而“我”作为潜在的女巫的受害者,立刻变身那只埋在丽达两腿之间的天鹅。[5]161一般来说,喻体代表主体的经验基础,是主体更为熟悉的事物;这样看来,小说里的比喻方式可以说是倒转的。史书美借用柄谷行人的观点,指出施蛰存小说中的内心描写根源于西方在文化上的占领,也就是说,互文性介入了内在性的建构,从中获得一种世界主义的共时性幻觉。[7]385不过,就《魔道》这一文本内部而言,半殖民地性质的内在性得到揭示,似乎并非来自一种深入潜意识的对民族身份的篡改在叙事层面的不经意流露,而是作者有意张扬出来的,鉴于“我”早已主动打开随身的小皮箱,将那些西洋阅读书目(培育“我”想象力的温床)公之于众:“啊,不错,那本TheRomanceofSorcery倒不能拿出来了。难道是因为我这两天多看了些关于妖术的书,所以受了它的影响么?……我该拿哪一本书出来看呢:Le Fanu的奇怪小说?《波斯宗教诗歌 》?《性欲犯罪档案》?《英诗残珍》?好像全没有看这些书的心情呢。还有些什么书在行箧里?……没有了,只带了这五本书。……还有一本《心理学杂志》。”[5]160这一段如数家珍般的自白,赋予小说元文本的色彩,对“非常心理”描写的生产机制展开某种反思。
小说中的乡村能指同样被西方资源的所指有意识地填充了——它被“一所小小的西式房子”所占领,房子里是陈君和他的妻子,一位和木乃伊王妃一样穿着白色曳地长裙的女人。[5]161-165需要注意的是,施蛰存是一个熟悉乡村生活的人,然而在小说中,他一方面刻意拉大了主体认知与乡村之间的距离,另一方面让中国乡村以一种陌生化的面目呈现在读者面前。陌生感营造的关键,还不在于那个时隐时现的黑衣老妇,而是依附于“西式房子”的家里的妖妇,符号化、抽离于外部环境的空间与人物联手,让家“非家”(unhomed),让本土成为异域。
“Uncanny”是弗洛伊德在写于1919年的文章里提出的概念[8](现有中文翻译里,相对准确的可能是“暗恐”),用于描述这样一种压抑的心理状态:有时,人会感受到突如其来的惊恐,难以名状、突兀陌生,但当下的惊恐可追溯到心路历程中的某个源头;因此不熟悉的其实是熟悉的;“非家”幻觉总有家的影子在暗中作用。霍米·巴巴使用类似“暗恐”的表述来描写殖民以及后殖民语境中新的不连续时空的生产:在经历“超域(extra-territorial)以及跨文化开始时期的情况下”,会体验到一种“家和世界的位置重置引起的陌生化效果”,“非家的那一刻像影子般偷偷袭来”,突然之间,人发现自己“居留在一种‘多疑的惊恐’状态之中”。“家庭/本土(domestic)空间的深处成为最错综复杂的历史侵袭之地。经过位移(displacement),家和世界的边界被搅乱;并且,很诡异地,私人和公共彼此融合。”[9]
以此为参照,我们可以对施蛰存小说的核心主题/情境——基于婚姻关系的“小家庭”——作象征式解读:与以父子为轴心的传统家庭相对照,小家庭在组织结构方面体现出现代性;以城市空间的公共性为对照,小家庭是私人性的承载物,且往往进一步具象化为空间位置稳固的妻子形象。不过,在像《魔道》这样的作品中,读者感受到家庭空间的不稳定,而且,“非家”体验的突袭不是因为外部公共空间的侵入;实际上,是潜藏于内部的异己力量令家庭空间突然被置换了。从《妮侬》到《魔道》,随着作者心理描写手法的日益娴熟,家非家、妻非妻的诡异气氛升级了。“不啊!我底妮侬,non!”[5]598这一句揭示了小说标题,或者说,妻子芳名的潜藏信息。由“是”而“非”(non),家庭空间遭到颠覆的并非其私人性,而是在地性,在异域色彩的喷涌之中,形成一个时空断层。
小说《梅雨之夕》刻画了一幅梅雨中的异常心理图景。在消失了清晰轮廓的城市空间下,游荡着的“我”进入幻觉世界。可以注意到,随着“我”思绪的展开,城市空间处在一种“熟悉/陌生”的辩证之中:一方面,城市由熟悉变得陌生——尽管“我”对路名如数家珍,行动模式却变得让自己难以理解;另一方面,城市本是陌生人的聚集地,此时,“我”却在过路人的脸上看到熟悉的迹象:陌路少女在“我”眼中成了远在家乡的初恋情人,街边的女掌柜是“我”的妻子。在这里,我们看到公共性和私人性的融合,或者说,恰恰是催生“白日梦”心理机制的公共空间保障了游荡者泛滥的私人性,通过私人性所生产出的心理位移,引发非在地性。而当“我”回到家时,发生了反向位移,在妻子身上察觉到少女和女掌柜的影子,让“家”面目可疑。
三、“家”/“本土”的复位
在1933年出版的《善女人行品》里,出现了一个女性游荡者。《春阳》里的婵阿姨同样是一个“妻子”,和一般妻子的区别在于,她嫁的是牌位。她的经历,在现代目光的衡量下,成为“异常”,但这或许反过来保障了她在现代语境里游荡的必要性:来自昆山的婵阿姨,在上海的南京路上,听从力比多(libido)的驱使,感受到“对于自己的反抗心”。[5]257不过,虽然婵阿姨漫步于城市空间,她的目光流连于城市景观,但她并没有真正被城市感召。在她的注视下,城市空间成为家庭/私人空间的延伸:
她凝看着。旁边的座位上,一个年轻的漂亮的丈夫,一个兴高采烈的妻子,一个活泼的五六岁的孩子。她们商量吃什么菜肴。她们谈话,她们互相看着笑。他们好像是在自己家里。[5]258
婵阿姨仿佛踏入别人的家门,在不受干扰的观察和窥视中,她甚至完成了自己作为那个孩子母亲的代入感。此外,“有一双文雅的手的中年男子”让她联想到银行保管库的职员——尽管他们只有一面之缘,但他可算是她在城市里的一个“熟人”。婵阿姨以银行职员为好感对象,显然有象征意味——他帮她开启她的保管箱。这一联系不见得指向银行所象征的现代经济运行制度以个人为对象建立起来的公共信赖机制;对于婵阿姨而言,保管箱关乎她私人生活的核心,代表她付出的代价和得到的补偿。保管库职员是婵阿姨和保管箱的中介,在他身上,她错觉/假想出一种私密的亲近感;借由对他的欲望,婵阿姨仿佛把公共空间私有化了。
类似于《梅雨之夕》,《春阳》里人物的“心理位移”令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发生融合;不同之处在于,后者的位移是单向的。具体说来,婵阿姨的“情欲”并非由特定的城市机制所激发,而是她已有生活经历和需求的延续;她的情感逻辑覆盖城市时间,城市却没有真正进入她的个人领域。《梅雨之夕》和《春阳》的微妙差异,或可象征性地标记出小说集《梅雨之夕》和《善女人行品》之间的分野:两者皆专注于“描写一种心理过程”,但是,如前文所述,《善女人行品》表现出鲜明的写实风格,这种写实性,着重体现在心理活动的充分合理化,读者可以轻松代入人物的情感,不会体验到误入“魔道”的失措。而且,《善女人行品》几乎是“妻子专辑”(唯有《雾》和《特吕姑娘》两篇关于未婚女性),比起《梅雨之夕》,家庭主题更为突显,且往往以实体的家庭空间为基本叙事情境。小说集题名中的“善女人”与“妻子”身份之间似乎建立起不言自明的绑定关系。“善女人”的“善”自然不应当作“美德”解,理解为“无害”更恰当些,或者,根据作者自己强调的“典型”价值,[6]42也可以包含“熟悉”“易于辨认”的意思。李欧梵指出,施蛰存的女主人公,“都不是解放了的女性……似乎是对‘五四’小说中‘解放了的娜拉’之综合症的一种反动,施蛰存存心让他的那些潜在的‘娜拉’选择呆在家里”。[10]182可以这么说,“善女人”是与都市同构的“摩登女郎”的某种对立物,她不仅不具备刘呐鸥和穆时英作品里女性的“摩登”外形,同时还坚守着“不摩登”的精神实质。以“善女人”为核心扩展而出的家庭空间,因此也变得稳定且不容置疑。
《善女人行品》中数篇故事皆表现丈夫在妻子的坚忍品质面前的回心转意。《莼羮》展现了丈夫和妻子之间的一场角力战,争论发生在星期日,中心是丈夫肯不肯做一碗莼菜汤。最终,妻子重新获得了家居生活的话语权,令丈夫心甘情愿地洗手做羹汤。转折点在丈夫负气离家后再回家时看到哭泣的妻子的那一刻。他自我批评道:“真的,一个卑劣的男子的无礼貌的高傲壅塞了我的恋爱的灵感,我的确曾使她大大的失望了。”[5]252“恋爱的灵感”在这里不是作为都市空间下陌生人偶遇时转瞬即逝的突发感受,而是一种夫妻生活的日常道德。值得注意的是,在双方角力的过程中,具象化为文学读物的西方扮演着如影随形的重要角色:“我”最期待星期日,“因为在这一日,我可以全日委身于我自己的工作”。[5]250“我”试图阅读朱利安·格林(Julian Green)的小说,试图翻译理查德·阿尔丁顿(Richard Aldington)的六章短诗,却不断被妻子的情感需求打断,构成“自己的工作”(围绕西方文学)与“家庭生活道德”之间潜在的冲突关系。最后,与妻子和好后,“我”重新回到书桌前,面前是预备续译的理查德·阿尔丁顿的《意象》第二章:
The blue smoke leaps,
Like swirling clouds of birds vanishing.
So my love leaps forth towards you,
Vanish and is renewed.
(缕缕的青烟升起,
像回翔的群鸟那样消失。
我的爱情也这样飘浮向你,
消失了,又重新升起。)[5]252
这里呈现了一个语言转换的过程。通过翻译,英文诗的内容成为中文语境中的“我”和妻子爱情复燃的直接说明;进一步来说,小说中的异域因素虽然一开始以“内患”的面目挑衅着妻子所固守的家庭空间,但最终并未构成对在地性的干扰和破坏,相反,它融入了家的氛围,变成它的一个注解。
有了《善女人行品》作为铺垫,《小珍集》(1936)的到来并非那么突兀。评论者一般认为《小珍集》是在左翼文学大环境的压力下顺应特定文学要求诞生的作品,[7]415[10]198施蛰存也自陈道:“我最后一本小说集《小珍集》可以说是我回到了正统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成果。”[2]678所谓“正统”,一方面指题材上对底层话语的运用,一方面是主动从带有明显实验风格的美学形式中撤回。不过,从另一个角度看来,《小珍集》其实是对此前家庭主题书写变化的继续发展。尽管《小珍集》里专注于夫妻关系的家庭故事不多(只有《失业》和《新生活》两篇可算),但“家”的观念拓展了,“家”这一概念原本隐含的本土意味,在《小珍集》中得以明晰化;具体说来,是相对于城市空间的乡村的有形化——在像《牛奶》《汽车路》那样的故事里,乡村作为许多小农户的集合,和城市处在一种不对等但尚未完全落败的经济关系里。《小珍集》中多数作品都以乡村为故事背景,而且,与《魔道》中刻意陌生化、被篡夺了在地性的符号化乡村(譬如《魔道》里的“乡村”)比较,诸如《牛奶》《汽车路》《猎虎记》《嫡裔》等作品里的乡村,显然重返施蛰存熟悉的经验世界,从中得到了复位。这一变化,最终与施蛰存在1937年发表的关于小说形式回归/改造的思考关联起来。
四、自我反动:“驱逐”心理描写
除了左翼文艺同行的施压之外,史书美将抗日战争的逼近作为更有力地促使施蛰存回归传统的动力:“成为一位爱国主义者的压力使得上述文本性的世界主义倾向走到了尽头。……虽然中日之间的战争并未将西方本身裹挟进来,但这一冲突却促成了中国人针对外国人的民族主义回应。”[7]393史书美显然意识到抗日和拒斥西方之间的非连贯性,但仍坚持使用“民族主义-帝国主义”的笼统模式来解释施蛰存在风格形式方面的中途折返。这种坚持的结果,一方面肯定了时代环境对作者的作用力,另一方面却让施的转型显得颇为被动,仿佛纯粹取决于外部因素。实际上,施蛰存的创作历程内部已经包含了转向的自发驱动;尤其以特定主题为纬,可以观察到一以贯之的“妻子-家庭-本土”隐喻性结构,于在地性的消解和重立中形成风格的流变。
发表于1937年3月的《黄心大师》讲述了名号黄心的比丘尼为抗衡“外道”,跳进装有铜液的锅炉里以身铸钟的神异故事,小说笼罩在一种幽明意识之中。6月,许杰就小说发表读书随笔一则:“这是不是要把我们带回宋人的评话小说,明清人的章回小说之路上去……如果说是现代人的创作,说是在现代的文艺刊物,作为现代的一种文艺创作而出现的东西,那末,我的天哪!这一条把老路当作新路的新路,且请你自己把它当作稀世之宝吧!”[11]由此判断,《黄心大师》作为一种创作转型,当属不合时宜,但它并非异军突起;向前瞻望,《小珍集》中的《塔的灵应》同属这一类,甚至在更早的《宏智法师的出家》(收录于《上元灯》)里也可以看到某种雏形。针对许杰忧心忡忡的批评,施蛰存很快作了回应:“近一二年来,我曾有意识地试验着想创造一种纯中国式的白话文。说是‘创造’,其实不免大言夸口,严格地说来,或者可以说是评话、传奇和演义诸种文体的融合。我希望用这种理想中的纯中国式的白话文来写新小说,一面排除旧小说中的俗套滥调,另一面也排除欧化的句法。”[3]954
“纯中国式的白话文”被设想为“既旧且新”,其主要功能,在于“不回老路”的同时,制衡现代白话文中的欧化影响(在这方面,似乎与作者笔下黄心大师降服“外道”的宏志产生微妙共鸣)。施蛰存解释说,自己采用了故事(tale)的形式来传达旧式的传奇志怪无法涵盖的内容,只不过,“我的说明是在黄心大师本身的行动和思想上去表现,而并不直接做破除迷信的论文,因为在说故事的技巧上,这一部分,我可以不负责的”。[3]956这里点明了,因为故事形式本身的特点,说明行为需要被限制在一定程度之内,不放任为鞭辟入里的论说作风。也就是说,施蛰存提倡一种留下解读缝隙的叙事文体,这种缝隙感,本身体现了“纯中国式”的重要表象。
《关于〈黄心大师〉》并非施蛰存在1937年唯一涉及小说形式改造思考的文章;当年4月,《宇宙风》即刊登他的《小说中的对话》一文,该文借谷崎润一郎在《春琴抄后语》中的观点,从两个方面提出对新文学学习西方的反思和反诘:一方面是对话:“在我们刚刚对于会话与叙述文区别不明的旧文体表示憎厌的时候,他(谷崎)却说这样可以表现出日本文的美,因而自己也苦心于会话与叙述之联系,从分行改为不分行,甚至从用引号进步到不用引号。”[2]491施蛰存认同古崎的观点,认为刻意区分叙述和会话令小说显得幼稚笨拙,堪称碍眼。[2]490-491另一方面是心理描写,他引用古崎的话:“‘实则若从引起读者的实感之点来说,素朴的叙事的记载似的总能副其目的,至于运用小说的形式则越巧越象虚构。’‘我写作《春琴抄》……对于未曾写出春琴和佐助的心理之批评,很想提出“为什么有心理描写之必要呢,那不是已经明白了吗?”的反问’。”施蛰存由此联想中国小说传统中“素朴的叙事”:“曹雪芹描写一个林黛玉,不会应用心理分析法,也没有冗繁地记述对话,但林黛玉之心理,林黛玉之谈吐,每一个看过红楼梦的人都能想象得到,揣摩得出。”[2]493
这篇文章写于1937年2月。无从知晓,如果再晚几个月,施蛰存还会不会借鉴谷崎润一郎的观点,甚至会不会写这篇文章。反过来,从《小说中的对话》一文来看,施蛰存的回归传统理念并非因战争引发的、应激反应式的民族主义,否则,他没理由绕开日本,把西方作为反对的对象。而且在文章中出现“东洋”“我们东洋”的说法,与“西洋”形成对照,[2]490,492将“中国”和“日本”一同纳入“东洋”范畴,流露出一种知识、美学体系角度的东方认同。另外,相比起对会话形式的异议,更重要的是他对心理描写的质疑——从当代施蛰存研究的立场来看,这种态度无异于自我反动,鉴于心理分析一向被设定为施蛰存小说最显著的形式特点。
事实证明,施蛰存并非纸上谈兵。《小说中的对话》之后,就从1937年到1947年的10年间发表的为数不多的叙事作品来看,施蛰存确实在兑现他的回归/改造理念,尤其表现在心理描写成分的大幅度减缩。譬如,1937年的《同仇日记》(5)施蛰存《同仇日记》,载《宇宙风》1937年第53期:183-187;1938第60期:452-457。和1938年的《西行日记》,(6)施蛰存《西行日记》,载《宇宙风》1938年第70期:198-203;1938年第72期:314-319。均以当时战争背景下的家庭生活为叙事对象,全篇平铺直叙,既无对话,亦无对心理世界的窥视袒露,唯有一件件琐事的白描串联,侧面投射出战争环境。日记作为一种早在“五四”时期已充分合法化且专以建构和呈现主体内心活动见长的文学形式,在此时的施蛰存手中,竟仿佛成了真正的生活日记的公开展示。此外,1946年到1947年,施蛰存在《文艺春秋》《文潮月刊》上发表了三篇短篇小说,(7)施蛰存《三个命运》,载《文艺春秋》1946年第3卷第2期:34-37;施蛰存《在酒店里》,载《文艺春秋》1946年第3卷第4期:106-110;施蛰存《超自然主义者》,载《文潮月刊》1947年第3卷第3期:1053-1056。均表现抗战时期逃难途中的人物场景片断。在这三篇小说中,对话形式依然被充分使用,心理描写却无一不削减到最少。在这些作品中,可以观察到两个层面的在地性:一方面是从西洋技巧中蓄意撤回而得以强化的形式上的在地性;另一方面,在文本内部,由于行文间心理空间的取消,心理位移不再可能,读者通过人物行动的展开所获得的,是一个不存在中断、缺乏游移、立足当下世界的连续时空。在战争的动荡与家国的废墟中,这样的写作形式似乎包含着建立起一种稳定的、内外一致的中国人形象的努力。不过,此时已至施蛰存小说创作实践的末期,其用“纯中国式的白话文来写新小说”的雄心壮志,最后无疾而终。
五、结语
本文试图厘清的问题主要有三:首先,同以往施蛰存研究更关注形式的着眼点有所区别,本文着重对施氏小说创作中持续稳定的、以夫妻关系为基础的家庭主题作一探究,目的在于重新定位主题和形式之间的生产关系。具体来说,是把前者作为后者的前提,考察类似主题在不同风格的形式之间流动的可能性,以及由此生发的丰富意义空间。
其次,本文的讨论以小说中的“妻子”为起点,相较于刘呐鸥、穆时英小说中与城市同构的摩登女郎,施蛰存在女性形象选取方面是独特的。以“妻子”为核心的家庭私人空间与城市公共空间的并置,似乎天然体现对立关系。不过,就对《魔道》《梅雨之夕》《春阳》《莼羹》等文本的解读来看,关键问题并不在于私人性与公共性之间的冲突,抑或后者对前者的侵犯,而在于两者之间边界本身的模糊和游移。游移感的产生来自于心理空间的介入——浓墨重彩的心理描写滋生了位移,消解了在地性,令现实空间瞬间变得面目混淆,暧昧不明。在这一过程中,潜藏于内部的异质性迸发,让“家”“非家”。本文把家庭看作一种隐喻性结构,作出了象征性解读:作为表征私人性、内在性的常规意象,“家”在施蛰存的小说中成为本土性和异域性展开竞争的场域;而随着心理空间的调整和压缩,随着本土性的复位与在地性的重新明确,“家”也由气氛怪诞的超现实“魔境”重新投向稳定的现实空间。
以上述论断为前提,本研究第三个关注点针对的是施蛰存小说创作历程的再诠释问题。研究界一般重视《梅雨之夕》一辑,而更多把之后发生的现实主义转向和回归传统倾向理解为外力作用的结果。本文试图从文本内部寻出一条前后衔接的轨迹,以揭示和证明施蛰存在小说形式、风格与问题意识演变方面的内在驱动和自发性。经过梳理和辨析,可以发现,小说内部本土性和在地性“复原”的趋势最终拓展到文本之外,形成作者对于传统文类形式和文学手法的重新选择。在专门文章里,施蛰存自我颠覆般提出“放弃心理描写”,并在此后有限的创作实践中做出对应性尝试。不过,20世纪40年代以后,施蛰存的小说创作日益鲜见,用“纯中国式的白话文来写新小说”的文学愿景,最终成为读者们的共同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