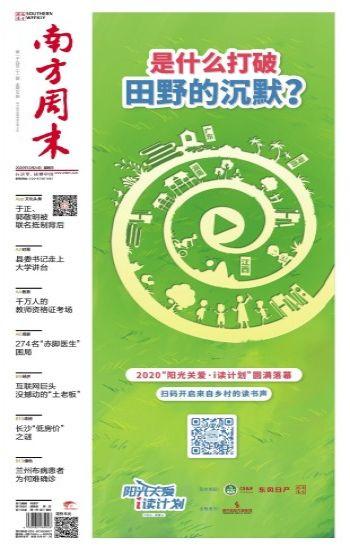李敬泽:跑步、文学、鹅掌楸梁鸿:梁庄十年



梁鸿演讲视频

李敬泽演讲视频
2020年12月11日,南方周末N-TALK“文学之夜”,李敬泽、梁鸿、徐则臣、笛安等四位作家分别登台演讲并与读者现场互动。上期报纸发表了笛安和徐则臣的演讲,这期报纸发表李敬泽和梁鸿的演讲,限于篇幅,有删节,全文和演讲视频见南方周末App。
那天,我在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的北园跑步,回来的路上,接到了《南方周末》编辑的微信,说李老师,再不给题目就来不及了。他要的就是今天晚上演讲的题目。从奥森东门出来,有一座过街天桥,看到这个微信的时候,我正好站在桥上。抬眼一望,看见了那三棵树,用鲁迅的笔法,左边那棵是鹅掌楸,右边那棵是鹅掌楸,中间那棵还是鹅掌楸。鹅掌楸是非常漂亮的树,高大,大概有十五六米高,这说的是我眼前的三棵树。实际上鹅掌楸最高能长到四十多米,年轻的时候,从0岁到20岁,它长得比较慢,最多长到十几米吧,然后从20岁之后,它就放飞自我了,它就开始拼命长、拼命跑,很快就能长到三十米、四十米。
那天我跑步回来,就站在那儿,看着鹅掌楸,叶子黄了,金灿灿的好树。鹅掌楸,非常挺拔、非常帅的一种树,它的叶子如同鹅掌,也很像清朝人穿的马褂,所以这个树的名字又叫“马褂木”,深秋时节,叶子黄了,恶俗的联想就是一树的黄马褂哗啷啷响。它的花很美,像郁金香。花落之后结果,果实像什么呢?像秋葵。
每次跑完步,我都要站在天桥上看它一会儿。这是从白垩纪留下来的树,侏罗纪之后就是白垩纪,那是一亿六千四百万年到六千六百万年前,那时候地球上霸王龙、地震龙横行,天上飞的不是鸟,天上飞的是翼龙,没有什么迹象表明今后会出现一种动物叫人类。那时候这树就已经长在地球上,然后它就这样一直长着,长到了现在,还长到了奥森公园的东门外。
鹅掌楸从白垩纪长到现在,不小心就碰上了人类。人要盖房子、打家具,楸木轻而硬,据说打了衣柜绝对不生虫。于是,它就成了国家二级珍稀濒危保护植物。话说到这儿,我显然就应该好好说说鹅掌楸的可怜和人类的贪婪,为了地球,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我们要好好保护鹅掌楸。
我忽然想起一位古地质学家的话,现在地球正在变暖,我们大家忧心忡忡,善良的人们喊出了口号,要拯救地球。但是这位古地质学家冷笑着说,想什么呢你们,地球根本不需要你拯救,在地球四十六亿年的历史上,温度比现在高的时候多的是,二氧化碳浓度比现在高得多的时候,也多的是,但地球还是地球。所以,地球没问题,不用你替它操心。问题的实质是,必须拯救人类。在可预见的未来,地球会一直在,而人类是不是还在,那可说不定。
地质学家的冷笑充分地暴露了我们人类特有的这么一种思维惯性和话语惯性,明明是我们撞上问题了,明明是我们快过不下去了,我们却说我们要英勇地、无私地拯救地球。这种惯性要用一个词来概括,就是“傲慢”,一种自我中心的傲慢。
站在鹅掌楸那边想,它已经存在了一亿六千万年,以它的尺度而言,人类的存在只是几秒钟的时间,它其实远比人类更知道如何在这个无情的地球上生存下去,而一个人,除了为它分类命名,除了思考怎么砍了它做家具,除了欣赏它的叶与花然后写诗写小作文,除了拯救它保护它,其实还有另外一件事可做,就是意识到我只是它面前风吹过的一粒微尘,作为有智慧的微尘,我要在这缕风中想象,我不是我,我就是这棵永恒的树。
——终于要说到文学了,我不能在“文学之夜”一直谈论植物。当我们谈论文学时,是否有另外一种可能,能不能想象一种“无我”的文学,在这样一种文学中,我可能成为一棵鹅掌楸,成为这棵树上的一片叶子。
这看上去似乎是不可能的。就在刚才这段话里,我已经说了一串的“我”,所以怎么可能“无我”。这个第一人称代词几乎是人之为人的第一条件,当一个人科动物站在一棵鹅掌楸下,说出“我”这个词的时候,他就成为一个人了,他就把自己从自然区别出来了。任何一堂文学课都会从“我”出发,再归结到“我”,很大程度上,我们理解的文学就是作者的独一无二的“我”与读者独一无二的“我”的遭遇和映照。
今人古人常不相通,据说人和香蕉的基因差异只有百分之四十到五十,而从精神或思想上看,我们与古人的差异可能比我们和一只香蕉的差异大得多。古人当然有“我”,但是这个我是他的出发之地,这个我甚至不是他的坐标点,就像一个人走在大地上、荒野中,他知道他没法把自己当坐标,他必须抬头看太阳、看北斗,太阳和星辰指引我们,如果只看自己,那你肯定迷路了,被狼吃掉。所以,我们能不能想象另外一种文学,在这种文学中,“我”是必须克服的。我们的写作与阅读,不是为了求证我的“在”,或者说,我们必须通过“不在”来体认“在”,在这样一种文学中,“我”不是“我”,“我”是“你”或者“他”,我可以是山上一块石头,一只飞鸟,一棵鹅掌楸,我可以进入天地间万事万物。由此,我把自己交给了更大的坐标,交给了地球或者星辰。
这是可能的吗? 我觉得这是可能的,甚至在我看来,这是文学最根本最深邃的一重意义。故事、虚构与诗,它们在人类生活中的深刻意义就在于它可以短暂地,让人们放弃自己的这个有限的“我”,而进入某种无限的事物。当我们的祖先说出“我”字,他成为了人,但是,当他有一天接着说,我是那棵树,我是那匹狼那只鸟那颗星星时,他否定了“我”,在这个伟大的否定中开辟了文明。
但是,无“我”的文学,非常难。现代以来的陈词滥调,大家听文学课,必说一定要有“我”,你们要努力啊,找到你的那个“我”。其实,哪用找啊? 我们这个“我”是一定在的,所谓“我心”,它就在心里,是我们身上最顽固的东西。所以,道家从老子开始,就讲要虚心,要放空,“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到了禅宗,第一要义就是“心如明镜台”,宋明理学以降,反反复复讲空心、白心,到王阳明,“此花不在你心外”,此心宇宙,至大无外。这么多道士、和尚、儒生,整天念叨这事的时候,说明什么呢? 说明这事儿太难了,克服这个“我”,超越这个“我”,用一个学术热词,叫“超克”这个“我”,进而获得这个世界,这太难了。
怎么办?我也没有好办法,我当然不比先贤们、那些高僧大德们更高明,我只有一个笨得要死的办法,就是跑步。跑步与文学有什么关系?我想来想去,好像也没有什么有关跑步的重要文学作品,《水浒》里有个神行太保戴宗,那是懒人想出来的办法,跑步太辛苦,腿上绑个符相当于发动机。孙悟空一个筋斗十万八千里,那更是连走路都懒得走。徐则臣写过一篇小说叫《跑步穿过中关村》,但我知道徐则臣是不跑步的,他是一个宅男。跑步的作家,据我所知中国的只有刘震云,外国的只有村上春树,他们都比我跑得快、跑得远。
每天跑步的时候,都是自己身体里、心里上演一场激昂、复杂的戏剧。前边的三公里、四公里,这个时候那个“我”,盘踞在懒惰肉身中的那个我,还在充分起作用。你会觉得我很累,我的身体是多么沉重,我跑步的姿势是不是正确,旁边过去的那个人怎么跑得那么轻松,跑还是不跑,这是个问题。忽然想起厄普代克写过一部小说:《兔子,跑吧》,我又不是兔子我为什么要跑? 哎呀,你想的事多了去了。这个时候,你必须和自己作斗争,你必须镇压自己,那个“我”就是你的敌人,那个奔跑的你,就是要甩开盘踞你身上的虎狼,你拼命跑,你披襟当风了澄怀静虑了,你只有一个念头,就是跑。跑到五公里、六公里、七公里之后,你知道那个“我”不在你身体里了,你把它卸载掉了,你轻了你空了,你停不下来,多巴胺内啡肽如风,风劲马蹄轻,所向无空阔,你都不是你了。
所以就我的体验来说,跑步是一个去掉“我”的好办法。一个写作者或者一个阅读者,如果我们能像跑步那样,把自己彻底交出去,从有限的、顽固的肉身中的那个“我”跑出去,然后这个时候你可能会觉得至大无外,会觉得这个世界如此清新饱满、进出无碍。
——我还得说说鹅掌楸与跑步的关系。鹅掌楸,生长在秦岭以南的山地,它是一种南方的树。那么为什么三棵鹅掌楸会出现在北京的仰山桥边? 后来我发现此事真不是偶然。2008年奥运会的时候,为了在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周围营造美妙的景观,把中国南方的鹅掌楸和美国的密苏里鹅掌楸撮合到一起,就变成了北方的鹅掌楸,所以,我所见到的树另有一个名字,叫“奥运楸”。
这就与跑步有关系了。我们都知道奥林匹克运动最古老的项目之一,就是马拉松。我们也都知道,公元前490年,雅典在希波战争中获得了马拉松战役的胜利,一个战士跑了四十二公里回来报信。开始的时候,战士还是那个战士,领了命令要完成任务,但是我相信,跑到二十公里、三十公里的时候,他已经跑出了身体,他已经跑出了那个“我”,他已经不是他自己了,他就是他的城邦,他的人民,他的土地,他的土地上的万物,甚至就是他的敌人——那些波斯人,然后他跑得太快了,太爽了,身体都追不上了,到了终点就死掉了。这样一个战士,这样一个跑者,我觉得他最终达到了伟大诗人的境界,他就是荷马。这么多年过去了,我相信,我们依然有可能像那个战士一样,像马拉松运动员一样,在奔跑中放下那个我,进入广大无边的世界中去。
跑步、文学、鹅掌楸,全联系起来了。这也体现了我对文学的另外一个基本看法,文学就是要把大地上各种不相干的事情、各种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各种像星辰一样散落在天上的事情,全都连接起来,形成一幅幅美妙的星图。
我想先给大家分享两个梁庄的故事。
2020年7月,我又回到梁庄。我发现梁庄村西头有一座高大洋房,特别高,站在四楼的豪华阳台上,左边可俯瞰绿意盎然、一望无际的河坡,右边可俯瞰整个村庄的房屋,它开拓了梁庄新的高度,特别美,欧式的,院子四周是月季花、凌霄花,院子里是很时尚的院林设计,灰色大理石围墙、罗马柱、假山、草地、休闲区、运动区,它完全可以媲美世界上任何一座城市、任何一个度假胜地的房屋。可以说,世界元素已经嚣张且牢固地扎根在梁庄。
打开房门,左侧客厅的正墙上挂着三个巨幅照片,分别是这座房子主人的曾奶奶、奶奶和爷爷,他的爷爷就是我在《中国在梁庄》和《四象》中都写过的原型,基督教长老韩立挺,方圆几十里都很出名,奶奶是一个妇产科医生,非常慈祥温和。客厅放着墨绿色真皮沙发,周边是北欧风的雕塑、摆件、画作等等。当时我很震动,一座如此现代的房子,里面最显著的地方,挂着身穿上世纪服装的老人照片,客厅的人,不管走动到任何位置,都能感觉到三双眼睛的追随,你好像无形中得庄重一些。特别冲突,又特别和谐。这究竟意味着什么?我被这座房子给深深迷惑了。
第二个故事是关于我的五奶奶。2020年11月,我回梁庄。五奶奶没在村头红伟家门口聊天。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
我一问,说是五奶奶骨裂了,躺在床上不能动。我到屋子里看五奶奶,躺在床上的五奶奶越发矮小了,小小的一团,白发蓬乱着。她抓住我的手就哭起来,说,“你看你奶奶成啥样子了啊,七十九,扭一扭,阎王爷要来把我抓走了。”我说,“那不也是没扭走你吗? 以后你还要长长远远地活呢。”“可是我疼得受不住了啊,我快控制不住自己了,我精神都快失常了。”聊了一会儿,说起家长里短,五奶奶又恢复了响亮的腔调,依旧是一个乐观自嘲的老太太。可是,我在走出屋子的一瞬间,想到把她一个人留在黑暗的屋子里,突然有些悲伤。孤独、衰老、恐惧,这些人类最根本的东西正在降临这个坚强的老人。
那么,这座最高的房屋和五奶奶的故事究竟意味着什么? 更进一步来说,我为什么要再写“梁庄”?“梁庄”新的表现形式在哪里? 新的思想和新的哲学在哪里?
就这座房屋而言,我想,不是把它描述出来就是“梁庄的存在”了,它也应该包括:围绕这座房屋所弥漫的精神状态,房屋主人和村庄人的心理,那三幅照片所辐射出的过去及与今天的关联,它对村庄总体地理面貌的影响,等等。的确如此,这座房屋成了一种标志和象征,它提高了梁庄的空间高度,在此之前,梁庄的房屋最高两层或两层半,那半层是储藏室,但自它之后,我想,梁庄人可能要有新的追求方向了。而更为重要的是,在这座房屋里,传统与现代、过去与现在以如此紧密的、赤裸裸的方式结合在一起,它似乎在昭示着一种可能性,过去以什么方式呈现出来,过去的生命能否对当代的生命产生真正的影响? 这是一个根本性的课题,也是梁庄未来命运非常重要的原点。
这十年之中,我仍然保持着一年回家两到三次的节奏,每次回家——一开始是父亲陪着我,2015年以后是我的姐姐们和霞子陪着我,我都会坐在村庄路口的红伟家,和大家一起聊天、说话、打牌,间或看着路边来来往往的人,大家打招呼,或聊几句天。五奶奶还是其中最活跃的、话最多的,大堂哥仍然经常醉着,龙叔仍然在那个大茶杯里泡着酽酽的浓茶,一句话一口痰,花婶仍然站在门口,勉强撑着笑容。我看着他们,看着时间在他们脸上慢慢流逝,就像看见我自己和我自己的生活,我也在变老,也在时间之中,我的父亲已去世,那么多人,一个个去世。我们互相看着,已无法分出彼此。
我到每家聊天说话,找各种理由,组各种饭局,老年人的,青年人的,小孩子的,把吴镇的饭馆吃遍,我也在各家吃,在丰定家、赵嫂家、五奶奶家,谁回来了,谁又走了,都是吃饭的理由,我出入他们的厨房就像在我自己家,因为他们知道,我自己家的房屋已经几成废墟。
一切都回到了最初的状态。我和梁庄的关系变成了一个人和自己家庭的关系。爱,欢喜,关心,深深依恋,但同时也忧心忡忡。我就像一个孩子,蹦蹦跳跳的,依赖梁庄的每一个人,喜欢梁庄的每一个人,无论是生者还是死者。我的爱多得我自己都兜不住,要溢出来。他们不知道我那么爱他们,不知道我在听到他们的快乐时有多快乐,听到他们的悲伤时有多悲伤。这是我的秘密,也是我的荣幸。
五奶奶就是五奶奶,明太爷就是明太爷,吴桂兰就是吴桂兰,梁庄、吴镇和所有的历史都隐在后面,没有地域性格,没有社会因素,我只看见他们的容貌,他们的欢笑、悲哀,看见他们身后的那个空间,电线杆、老公路、燕子、湿得要滴下水的乌云。我看见的是他们本身,非常具体,他们的每一个行动、表情和神态,都如浮雕一样,栩栩如生,超然于时间和空间之外。就像我们看待我们的亲人,你很难用一种整体性来叙说,因为你和他/她太熟悉了,爱恨情仇交织在一起,无法用抽象的概念来衡量。
一切都更加日常化,稍微有一些幽默,个人性写得更为充分一些,包括个人的故事、整个生活的样态。比如五奶奶那一章开头第一句是“五奶奶坐在孙女的粉红小电车后面,上街去理发”,我写她上街去理发,但是走了一圈没有理发,她为了去见她的女儿、见她的孙子,又显摆自己的孙女,我想把这个人内在的样态,一种乐观、一种要求写出来,但这里面仍然是现实的。我写少年阳阳,他在《出梁庄记》里面是那样一个少年,而现在,他也回梁庄了。我请他吃饭,和他聊天,了解他的内心,还肩负着他父亲让我劝他好好学习的重任。最后,我们在大街上相遇,阳光灿烂,我们遥遥相望着,互相叫喊着,他叫我的名字,我答应他,说,“你要好好学习啊”。然后,各自继续前行。
明太爷已经去世了,他去世的原因也非常离奇,让人无限感慨。这样一个刚愎自用的人,一个不合作主义者,最后却因为一个偶然的意外事件死亡了,但说意外好像又不意外,往深处想想,又是他的必然。他的老婆,灵兰大奶奶一直信主,他俩因为这个经常吵架。今年我回去听说灵兰大奶奶也在镇上住,我就到了他们家去看。明太爷在时的那个破败的长满荒草的小楼,经过新的改造,已经完全变样了,房间非常温馨明亮,那口让明太爷致命的大缸也不见了。灵兰大奶奶谈到明太爷的时候,依然非常生气非常愤怒,就是一个饱受丈夫折磨的普通农村女性,但是,当她让我们唱赞美诗,让我们祷告的时候,她又非常明亮、非常自信,整个神态,完全像换了一个人,精神焕发。真的像谜一样的存在,很难叙说清楚。另一方面,明太爷彻底被遗忘了,那个房间里边,再也没有明太爷任何一个影子了,他的倔脾气、他的正义,他的固执,都随着这房屋氛围的转变而被彻底遗忘了。我希望把这种状态写出来,一种矛盾的、暧昧的,同时又是真实的人生。
这几乎让人吃惊,而且感觉美妙。因为有共同的经历和度过,因为有真实的时间长度和真实的人生长度,感觉到人物本身也具有矗立于山河之间的、近乎永恒的真实性。包括我自己。就好像进入到一个时间隧道里边,时间隧道里边每个人都栩栩如生的,在历史的长河里边,时间的洪流面前去体会浪花的击打,我自己也成为其中一分子,完全融入在当中。
我也期待着,十年之后,二十年之后,2030年,2040年,再写梁庄,那时候会是什么样子,我自己,梁庄,梁庄里的那些人,五奶奶、姐姐、霞子、龙叔、阳阳,等等,我充满好奇和期待,我几乎等不及时间的到来。
但愿我能活到那个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