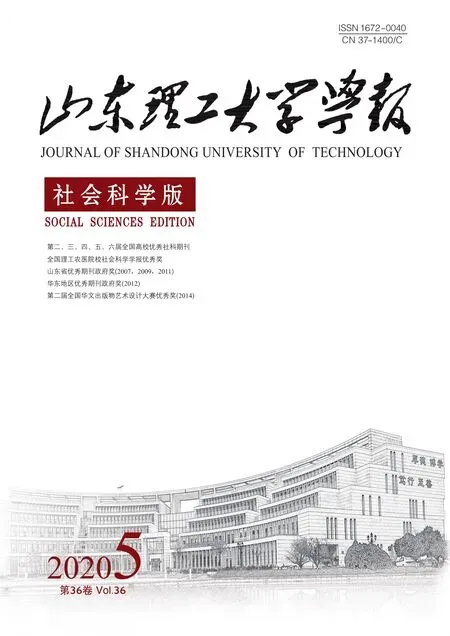食品安全领域大规模侵权法律救济问题研究
安婧婧,姜超夫
一、引言
随着科技的快速进步与经济的迅猛发展,在大大提高生产力的同时,企业已基本实现批量化的大规模生产方式。但是,伴随着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趋势,批量化的生产方式一旦出现产品质量问题,将大规模侵害消费者权益。近年来,由于食品安全领域大规模侵权事件频发,我国对食品生产企业的监管力度正逐步加强,但是相关制度并未完善,尤其是对受害者的权利救济手段不能很好地维护其权益。在立法方面,我国仅在《侵权责任法》中对一般侵权做了相关规定,并未就大规模侵权进行具体、明确的界定,因此无法很好地对食品安全领域大规模侵权事件进行有力救济;在执法方面,我国虽然形成了行政主导型的损害救济机制,但是“企业侵权、政府买单”的行为却严重违背了公平原则,极大损害了纳税人的合法权益[1]。食品安全领域大规模侵权事件在世界范围内均有发生,各国对其进行了不同形式的法律救济,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例如,美国的集团诉讼制度、德国的民法典模范程序、日本的选定当事人制度等。相较于发达国家,我国应以国情为出发点,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救济机制,以此更好地杜绝食品安全领域大规模侵权事件的发生,维护国民的身体健康以及社会的和谐稳定。
二、食品安全领域大规模侵权的概述
大规模侵权这一概念并非传统大陆侵权法律体系中的固有概念,我国《侵权责任法》虽然涵盖了大规模侵权中的部分情形,但是并未明确规定大规模侵权行为这一概念。大规模侵权一词最早源于美国侵权法的规定——“mass torts”。有学者指出,大规模侵权本质上与一般侵权行为并无不同,但是具有侵害范围的大规模性、社会影响的巨大性以及损害后果的严重性等特点[2]。而美国法对于大规模侵权行为的描述为“基于一个或同一性质的不法行为,给人数众多的消费者造成人身、财产损失的行为”。我国法学界对于大规模侵权的界定有不同的观点,杨立新教授认为:“应当将大规模侵权界定为基于一个或多个性质相同的法律行为,造成侵害了大量的法益以及产生了一定后果的侵害的行为。”[3]朱岩教授将大规模侵权界定为“基于一个不法行为或者多个具有同质性的事由,如瑕疵产品,给大量受害人造成人身损害、财产损害或者同时造成上述两种损害”[4]。赵庆鸣、孟妍认为:“大规模侵权是由于加害人所实施的一个侵权行为而同时造成多数人的人身或财产损害,其强调受害主体的多数性。”[5]虽然大规模侵权这一术语已经被国内外理论界、实务界接受,但是对于其概念的界定学术界并未有统一的观点。
笔者认为,大规模侵权与单一侵权在本质上均是一种侵权行为,并非相互对立,其构成要件都符合侵权行为构成的一般性要件,最主要的区别在于大规模侵权由一个侵权行为或本质上同质性的多个侵权行为引起不特定多数人的人身、财产遭受损害。基于上述界定,食品安全领域大规模侵权具有如下特点。
第一,被侵权主体的广泛性与不确定性,这是食品安全领域大规模侵权行为最主要的特征。但对于广泛性的界定并无确定的标准,有学者主张为数人,有学者主张为十人以上,有学者则主张更多。因为引入大规模侵权行为的根本目的在于节约司法资源,更有效地解决侵权问题,如果人数不足十人则完全可以通过单独诉讼的方式进行解决。同时,由于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及广泛应用,多数企业开始使用现代化的先进生产技术进行大规模生产,凭借经济全球化创造的便利渠道将产品销往世界各地,加之转基因技术、人工合成技术、添加剂技术等也给食品安全增添了许多不确定的因素。“民以食为天”,食品是大家赖以生存的基础,对于食品的巨大需求,使得食品安全领域一旦出现质量问题,将会有众多消费者的身体健康受到侵害。经济的全球化使得食品安全领域一旦发生侵权行为,其侵害范围可能为一个市、一个省、一个国家,甚至可能遍布世界各地;人数也可能为几十、几百、几千、几万甚至上亿人不等,而且由于不同消费者的具体情况不同,其产生的损害程度也不同。这些因素都为大规模侵权案件的处理、救济、赔偿等环节增添了极大的困难与不确定性[6]。
第二,侵权者与被侵权者地位的悬殊性。食品安全领域大规模侵权事件中的侵权人一般为大规模的食品生产企业,而被侵权人一般为普通的食品消费者。如2008年的“三聚氰胺”案件,造成大规模侵权事故的食品生产企业三鹿集团,不仅具有雄厚的资金以及专业的律师团队,而且在信息获取方面凭借其地位及在市场多年的经验具有极大优势。而消费者作为大规模侵权中的被侵权人,由于我国食品安全市场信息的不对称性以及维权成本过大等原因处于极大劣势地位。例如,耗费巨大的财力成本与时间成本,加之消费者对食品安全领域的专业知识如添加剂的种类、用量、安全标准等并不精通,所以导致侵权人与被侵权人无论在信息的获取、资金以及专业的法律团队等方面都具有差距。
第三,食品安全领域大规模侵权行为的损害后果具有隐蔽性与不确定性[2]。食品安全领域大规模侵权行为的隐蔽性源于随着科技的进步,食品添加剂等迅速更新,新食品种类的出现速度远快于相关法律法规、鉴定标准的更新速度,导致对新产品的安全性无法保障。同时,伴随商家的逐利性心理,偷工减料、以次充好,致使产品不能达到国家的食品安全标准,对人体造成不同程度的损害。而由于损害的间接性,这类食品并不一定第一时间导致消费者健康出现问题,从而造成了损害的隐蔽性与不确定性。
第四,食品安全领域大规模侵权损害后果的严重性[7]。如“三聚氢胺”案件中,毒奶粉产生的后果不仅需要花费家庭大量的医药费,还对婴儿造成不可逆转的身心损害,案件的恶劣影响极易引起社会的不稳定。
三、我国食品安全领域大规模侵权法律救济存在的问题
(一)行政主导型损害救济模式弊大于利
在立法上,我国《侵权责任法》对于大规模侵权行为并无明确的规定,在具体处理过程中,司法机关根据大规模侵权行为本质上的侵权属性按照一般侵权行为进行处理,但是由于大规模侵权的复杂性以及司法资源的不足,我国在司法实践中对于大规模侵权行为的处理并不理想。例如,在“三聚氰胺”案件中,由于婴儿食用了三鹿集团生产的添加有三聚氰胺的奶粉,造成患儿多发泌尿系统结石,致使四万多名婴儿身体受到损害。同时,由于这些婴儿分布在全国各地,给案件的后续处理造成极大的困难。在该事件爆发后,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立即成立应急处置领导小组对该事件进行处理。在对三鹿集团进行查处的同时,由国家拨款对患病婴儿进行免费治疗。根据最终确定的赔偿方案由相关责任企业筹集巨额资金,对患病婴儿进行具体的救治以及赔偿,并且在赔付完毕后拿出2亿的资金设立了医疗赔偿基金,用于后续对患病婴儿进行赔偿[1]。从该案件可以看出,我国对于大规模侵权案件的处理模式已经形成了行政主导型的救济模式。这一救济模式,一方面通过政府的介入可以迅速协调各个部门进行大规模侵权事件的解决;另一方面也让政府背负了本属于责任企业的负担,使得原本属于民事领域的大规模侵权事件,最终由政府“掏腰包”进行解决,损害了纳税人的相关利益,显失公平正义。
(二)代表人诉讼救济模式不能发挥作用
由于食品安全领域大规模侵权诉讼案件普遍具有受害者人数众多、分布广泛以及社会危害性巨大等特点,所以依据我国现有的法律制度,代表人诉讼是解决此类案件的最佳途径,但在具体司法实践中,受害者通过代表人诉讼寻求救助却屡屡受阻[8]。其未能发挥作用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
1.立案困难以及时间、金钱成本高昂。在食品安全领域大规模侵权案件中,由于受害者数量众多且分布广泛,造成的社会危害大等因素的影响,受害者在提起诉讼时,法院对此类案件的立案非常谨慎,诸如“三聚氰胺”案件发生时,受害者多次提起诉讼而法院均未立案。即使立案后,由于案件巨大的社会危害性以及社会影响力,法院在此类案件审判中,也会很慎重而不轻易做出判决。食品安全领域大规模侵权案件一般比较复杂,因果关系的证明也比较困难,导致案件可能经过一审、二审、再审,审判结束后还涉及执行难等问题。由于受害者数量众多且造成的损害巨大,有可能导致企业破产,一系列的司法程序会使受害者付出极大的时间成本[9]。由于案件审理的慎重本来就付出了极大的时间成本,再经过多级审判以及强制执行、清算等程序,受害者更需要付出极大的金钱、时间成本。而且一旦涉及企业的破产,对于受害者的清偿就更加困难,致使受害者通过代表人制度寻求救济的过程困难重重。
2.对于食品安全领域大规模侵权的受害者——普通消费者而言,举证难仍是其寻求救助的巨大阻碍。对于食品安全领域大规模侵权通常适用无过错责任的原则,受害者无需证明侵权企业存在过错,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受害者举证的难度。但是,即使采取无过错责任原则,受害者仍然需要证明其受到损害及其所受损害与企业的侵权行为具有因果关系。但在司法实践当中,由于受害者欠缺相关的专业知识,所以证明这种因果关系也非常困难。这些都是受害者通过诉讼寻求救济道路的障碍。
四、国外对于食品安全领域大规模侵权的救济机制
(一)美国
为应对食品安全领域大规模侵权案件,美国采用了集团诉讼的处理模式。集团诉讼是指当发生大规模侵权案件时,遭受大规模侵权的部分受害者可以为了所有受害者的利益,无需经所有受害者的同意,自愿地为其提起诉讼。在美国的集团诉讼中,遭受侵权的部分受害者提起诉讼时需向法庭证明其众多受害者因同一法律问题或同一事实问题而提起诉讼,因其人数众多所以请求合并审理[10]。法官通过对受害者提起的诉讼进行审理做出判决,此判决不仅约束提起诉讼的部分受害者,还约束未参加诉讼的受害者。如果未参加诉讼的受害者不同意以集团诉讼的方式参与诉讼,其可以通过选择退出的方式从而使自身不受集团诉讼结果的影响。美国针对食品安全领域大规模侵权的事后救济机制设立了市场份额机制,在清偿阶段具体责任的承担上,生产该致害产品的生产商通过其在市场所占的份额承担赔偿责任即可。
(二)德国
为应对食品安全领域的大规模侵权案件,德国政府采取了民法典的模范程序。具体是指针对性质相同的诸多案件,法官在诸多案件中选取几个典型的案件进行合并审理。同时,性质相同的其他案件的当事人也可参与该典型案件的审理过程。该典型案例的审判结果适用于该时期所有的同性质的案件,并且其审判产生既判力,以后国家相同性质的案件也适用该典型案例的判决结果[5]。德国民法典的模范程序有两大优点:其一,通过典型案例的审判在对该案例发生效力的同时,也对该时期所有相同性质的案件产生效力,而且由于其既判力,也适用国家日后相同性质的案件,极大地节约了司法成本。其二,食品安全领域大规模侵权案件由于其对人体损害的间接性,所以造成其损害结果的隐蔽性、不确定性。德国民法典的模范程序对典型案例的审判产生既判力,也对日后相同性质的案件产生效力,使在食品安全领域大规模侵权案件中未在第一时间出现健康问题的消费者,在日后出现问题时仍然可以寻求救济,更好地保护了消费者的生命健康权。
德国采用了“团体诉讼”的救济机制来更好地处理食品安全领域大规模侵权案件,即德国政府允许消费者协会等民间组织来提起诉讼,引导大规模侵权纠纷的解决。在司法诉讼过程中,消费者协会等民间组织被赋予了实体的处分权,有利于民间组织更好地维护食品安全领域大规模侵权中被侵害的消费者权益。消费者协会等民间组织可以凭借其在该具体领域的专业知识更好地维护消费者权益并极大地发挥本行业组织的价值。
(三)日本
日本为应对食品安全领域的大规模侵权案件,规定了选定当事人制度[5]。该制度是指诸多当事人因同一事件而具有相同利益请求时,且该诸多当事人并非日本《民事诉讼法》当中规定的非法人社团,该具有相同利益请求的团体可以选定一人或数人来进行诉讼,法院对提起诉讼的案件做出判决。该判决不仅及于做出判决的选定当事人,同时及于该事件中的所有利益相关人。由于法院对选定当事人的判决有既判力,所以该案件中的其他当事人必须以书面形式对选定当事人进行授权。
为应对大规模侵权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日本政府还创设了“恒久救济”。对于基于同一损害事实在诉讼结束后产生损害结果的受害者,其仍可以向大规模侵权的企业请求赔偿。日本的选定当事人制度实际上是集团诉讼制度的发展,一方面日本的选定当事人制度避免了因当事人众多而导致的集团诉讼审判难等问题;另一方面也节约了司法资源,提高了司法效率。
五、完善我国食品安全领域大规模侵权法律救济机制的建议
为应对食品安全领域大规模侵权案件,我国形成了行政主导型损害救济机制,其对大规模侵权造成的损害进行及时有效救济的同时也大大降低了救济的成本。但目前我国相关的法律救济机制仍不完善,缺乏科学的参与机制、完善的责任承担机制及事后的追偿制度等。我们必须立足于具体国情,有选择地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建立以行政主导型损害救济为主,全方位、多层次的损害救济机制[11]。具体建议如下。
(一)完善食品安全领域大规模侵权案件的参与机制
食品安全领域大规模侵权案件在对众多消费者的人身、财产造成重大损害的同时,也严重影响了社会的稳定,所以对其处理的公平性、公正性、透明性是处理好该类案件的关键。当下对于食品安全领域大规模侵权案件的处理,虽然也有消费者协会、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等的参与,但其更多的是在配合行政部门的工作,并未很好地发挥其本身促进案件的解决、提出有建设性的建议等作用。为了使行政主导型损害救济机制更加完善,也为了在处理大规模侵权案件中可以更加公平、公正、透明,必须在食品安全领域大规模侵权案件中引入科学的参与机制,保证侵权人、被侵权人、公益组织等的充分、有效参与。尤其是在社会上具有中立地位的民间组织参与其中,可以更好地发挥行政机构与侵权人、被侵权人之间的桥梁作用。一方面,我们可以很好地借鉴德国的“团体诉讼”模式,在大规模侵权诉讼中让消费者协会等民间组织充分地参与到诉讼中,更好地维护食品安全领域大规模侵权中被侵害的消费者权益;另一方面,可以更好地解决行政主导型损害救济机制的弊端,纳税人的参与,对于合法、合理地使用纳税人的税款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为了使资金的使用更加透明与合理,相关专业人士的参与也是完善食品安全领域大规模侵权案件参与机制必不可少的方面[1]。
(二)完善我国食品安全领域大规模侵权的诉讼救济机制
我国形成行政主导型救济模式的原因之一即为我国目前的诉讼制度无法很好地解决大规模侵权案件。而美国通过多年司法实践而形成的集团诉讼制度对于完善我国食品安全领域大规模侵权诉讼救济机制有很好的借鉴意义[10]。食品安全领域大规模侵权诉讼救济机制的完善,使得大规模侵权诉讼的判决效力具有更大的扩张力,在节约司法资源的同时也提高了司法效率;且通过此方式减少行政的干预,使得对案件的处理结果更加公正与透明。
(三)完善食品安全领域大规模侵权案件赔偿责任的承担机制
在2008年三鹿集团的 “三聚氰胺”案件当中,随着对案件的逐渐揭露,国家质检总局公布的检验报告中,除三鹿集团外还有21个厂家多个批次的奶粉检验中均被检验出含有三聚氰胺。尽管在最后的赔偿当中也向多家责任企业征收了赔偿款,但是对具体责任的分担,法律并无明确的规定。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借鉴美国创设的市场份额责任制度,在我国的食品安全领域大规模侵权案件中引入此制度,由生产该致害产品的企业按照其在该产品市场所占的份额来承担赔偿责任。引入市场份额机制,一方面可以解决食品安全领域大规模侵权案件中受害者的受偿不能的问题;另一方面,在审判环节,法院无需查明受害者也无需证明其受损是由哪家企业的产品所致,只需证明该企业生产该产品即可,降低举证难度的同时也提高了诉讼的效率。这对于完善我国食品安全领域大规模侵权案件的救济机制具有重要作用[5]。
六、结语
随着现代化社会的不断发展,批量化的生产模式已经非常普遍,其中包括对人的生存与发展至关重要的食品安全领域。而随着工业化的高速发展,大规模侵权事件频发,尤其食品安全领域大规模侵权更是造成了严重的人身、财产的损害以及恶劣的社会影响。基于我国司法机关资源的有限性,目前的司法诉讼无法很好地解决食品安全领域大规模侵权的法律救济问题。当下我国行政主导型损害救济模式在降低救济成本的同时也存在显失公平的问题。美国、德国、日本等国家的食品安全领域大规模侵权救济机制对于完善我国相关的救济机制有很好的借鉴作用。为了更好地解决我国食品安全领域的大规模侵权问题,应立足于我国治理现状,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充分利用行政、司法、社会等多方面的力量,建立以行政主导型的损害救济模式为主,全方位、多层次的损害救济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