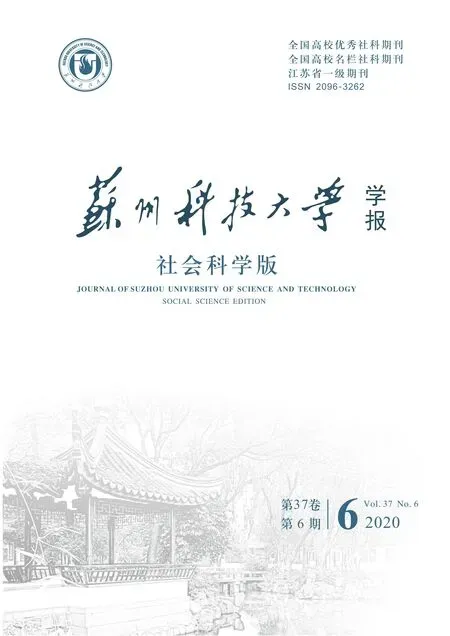十八世纪末仙台藩与潮州船员漂流事件*
许美祺
(苏州科技大学 社会发展与公共管理学院,江苏 苏州 215009)
近来笔者在研读日本大阪民间知识人山片蟠桃(1748—1821)的《梦之代》(1820年)一书时,发现一则对十八世纪末中日漂流民事件的记载。这两次漂流事件的时间接近,内在也有紧密关联,是反映当时各地社会样貌的好材料。海上生活向来凶险,人们因发生船难而漂流至外国的事件在东亚史上时有发生,救助漂流民也是各地政府长久以来的重要工作,从而留下了大量关于漂流民的官方记录。史学界对这些官方资料进行了多方整理和研究,厘清了政府救助遣返体制、漂流民多发的原因、漂流民对国家外交的作用等重要问题。(1)战后,漂流民和东亚海洋贸易研究领域具有代表性的日本学者有大庭修、松浦章、村井章介、中岛乐章等人。中文史学界的代表性成果有:松浦章、汤熙勇、刘序枫的《近世环中国海的海难资料集成:以中国、日本、朝鲜、琉球为中心》,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科学研究所1999年版;孟晓旭《漂流事件与清代中日关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而山片蟠桃此项记载的特别之处在于,他作为一介无官无职的民间商人,是通过非官方渠道接触到漂流民信息的。日本江户幕府奉行“锁国”政策而严防民间与外国接触,因此蟠桃对漂流民的记载非常珍贵,尤其可从中窥见日本民间知识分子对外国信息的态度。对其进行介绍,相信有助于学界相关研究的推进。
《梦之代》的记载分为两段:前段记录1794—1797年日本仙台藩船员漂流至安南,途经澳门、广东、江西、浙江等地回到日本的事件;后段所记则是1796—1797年广东潮州船员陈世德等人漂流至仙台,后在仙台藩护送下抵达长崎归国。送还中国漂流民和接回日本漂流民是仙台藩护送队的一次完整任务,所以这两次中日漂流事件也就结合在了一起。十八世纪末发生的这两次横跨东亚海域南北的漂流事件,为我们了解同时期安南、澳门、广州、乍浦、长崎等地的社会样貌提供了一个具有高度共时性的观察窗口。
对于上述中国漂流民事件,孟晓旭在《漂流事件与清代中日关系》一书中有所提及,但比较简略[1];李杰玲在《18世纪仙台藩儒与潮州渔民唱和文献钩沉——从〈陈林诗集〉说起》一文中予以详细论述,并根据仙台藩文人留存的《陈林诗集》《萍水奇赏》《三珠树集》等文献进行了很好的考证复原[2]。而《梦之代》的记录与仙台藩官儒的记载并不完全相同,其不仅对日本漂流民事件进行了完整叙述,后一部分还可与孟晓旭、李杰玲的研究互为印证、补充和参考。
一、仙台漂流船员的际遇(2)本文第一节和第二节的段中引文皆出自原文,参见山片蟠桃『夢の代』,水田紀久、有坂隆道『日本思想大系(43):富永仲基·山片蟠桃』,岩波書店1973年版第246~253頁。
日本宽政六年(1794)七月,陆奥国仙台名取郡閖(3)閖,音shuǐ,水口、水洞、桥洞之意,我国潮汕地区的地名亦常用此字。上村(今日本仙台市东南)彦十郎名下的定期运粮船“大乘丸”执行航行任务,载着日本南部氏盛冈藩(今日本东北地区岩手县盛冈市)的大米,从仙台的石之卷出发开往江户。船组成员有船头清藏和15名水手。八月二十三日,他们不幸遭遇风难,船舵折损无法控制航向,在海上漂流了五个月,方在闰十一月二十日见到一无人小岛上岸。在此之后,他们经历了一段奇异的旅程。
(一)安南国
在无人岛,他们遇到了一艘渔船,但是来人与之语言不通。他们以大米相赠,双方划地笔谈后才了解到此处是安南国。于是,在当地人的护送下,他们来到了渔民的居所西山(今越南归仁)(4)这些日本船员上岸的地点应是越南西山王朝(1778—1802)的旧都归仁府西山邑附近。。不久便有官吏将他们带到官衙,通过笔谈来进行询问,并给予粥食。十二月朔日,船头清藏生病,于是转由源三郎作为代表溯河而上觐见安南王(应是阮光缵)。三日,他抵达王都。安南王举行了盛大的阅兵仪式,鸣放火枪火炮,人员全无佩刀。五日,两名官吏带着通辞、医生等人来到西山,将剩下的15人全部带到王都。这位名叫Tenkuhan的通辞来自中国,是南京人,多次去过日本长崎。留居安南期间,可能是对当地气候和医药不太适应,日本船员死了6人,包括船头清藏和水主宗八。他们都葬在当地的永长寺,受到了郑重礼遇。安南方面想将他们送往广东,但是一直无船。直到次年四月一艘澳门船到来,他们才得以乘船离开。澳门船的船长是葡萄牙人,名叫Gabou。临行前,安南王又送了许多粮食,并赠给他们五十贯铜钱以及写给广东方面的书信。于是在遇难次年四月二十一日,他们离开了安南。
(二)澳门
五月五日,剩下的日本船员10人抵达澳门。他们见到了宛如西洋城市里一般的风景和人物,称赞其“尽皆华美”。澳门民居皆有楼阁,屋顶用瓦,柱壁用石,庭院也用石砌;山上城郭有石门石壁,又有火炮。他们观察到澳门由葡萄牙人掌管,因而诸藩汇聚于此,既有着白棉布、袈裟等衣物的黑肤色“莫尔人”(来自莫卧儿帝国的印度人),也有着桶装下装和葡萄牙人长得相似的白肤色“马尼拉人”。此地虽然非常美丽,但因为日本在禁止基督教传播的过程中残忍杀害了众多教徒,两地历史上结下血仇,所以这里对日本人非常敌视。澳门方面对这些漂流民置之不理,既不让他们上岸,也不给他们食物。从五月到七月,他们险些饿死,幸亏有安南王赐予的粮食,他们靠着这些大米熬的粥坚持了下来。日本船员多次到船主Gabou家哀求,终于得到机会跟随广东香山县的巡视官吏离开此地。
(三)广州
七月十六日,日本船员跟着香山县官吏出航,十七日到达广东省属岛香山,停留三日,又乘船于二十日抵达“广东”(今广州市)。抵达当日,日本船员又有一人去世,只剩下9人。他们谒见“太守”(5)可能是时任两广总督的爱新觉罗·长麟(?—1811),1793—1796年在任。,将遭遇一一禀报。此后,这些日本船员对广州风土人情的记录颇为详细,大概是终于可以安心在城内外游览了。他们眼里的广州治城广大、海口辽阔,可同时停泊数千艘大船,汇聚来自荷兰、澳门、莫卧儿(6)他们观察到的可能是来自印度的英国船。等“万国之船”。商贾皆美丽,道路砌着整齐的石块,市场店铺和日本一样争利交易。此处描绘的大概是当时正值盛期的广州十三行。他们还留意到:当地妇女在农家可见,而市街上就见不到了,因为贵妇不能出门;男子剃头编发,头上戴着黑色的帽子;官员或乘轿或骑马,随从众多;官员家门内有堂,与日本寺院的形制一样;民居造楼敷粉壁,市内和农村都用瓦,屋顶没有铺草的。十八世纪末广州城的富足生活在他们的记录中栩栩如生。不过,他们虽然称赞广州“稻粱易熟、田地丰饶”,但也不忘评论其“大热国也”。终于在八月十二日,“太守”通知将令人护送他们前往江西,并赠予他们十八件衣服和四枚银钱。
(四)从广东至浙江
八月十三日,剩下的9名日本船员在官吏护送下由广州沿水路北上。官吏和难民分乘两艘船。座船非常精美,船上插着大旗,写着“奉旨护送日本难民归国”几个大字,一路敲锣打鼓。十四日至三水,又经清远、英德、曲江、始兴,抵达南雄府保昌县。其后,日本船员都转乘轿子于九月朔日越过大庾岭抵达江西境内太庾县。一过大庾岭,天气就凉快了下来。
九月五日,他们在南康县再次换船顺“章江”(今赣江)而下,经万安、泰和、庐陵、吉水、峡江、新淦、清江、丰城,十一日抵达南昌。他们在江西省府停留三天,不过并未下船逛过市街。他们知道城北就是古称彭蠡的鄱阳湖,由于距离较远,未能前往观湖。此后,他们沿余干、安仁、庐溪、弋阳、河口、铅山东行(7)护送这些日本难民的船队选择了东行路线,而非由南昌北上九江、再入长江东下。为何如此,笔者尚不太明白。船队在南昌停留三天,可能是在此期间于江西省府决定路线并办理手续,选定这一最终路线或许是综合考虑了交通便利性和当时的某些特殊情况。,经过上饶,于二十二日抵达玉山,由此便离开江西省进入浙江省境内。
九月二十四日,他们抵达浙江西安(今浙江衢州市境内),途经龙游、兰溪、建德、桐庐、富阳,眺望西湖之后,于九月三十日抵达钱唐县(今杭州市内),即浙江省府所在。他们没有停留,紧接着经石门、嘉江、平湖,最终在十月六日抵达了乍浦。
(五)乍浦
浙江省嘉兴府乍浦是江苏、浙江地方的出海口。十八世纪前期以来,清廷主要通过设在苏州的官商和额商两铜局从日本采办国内紧缺的铜材,两局也在乍浦设立会所。[3]乍浦港由此一跃成为中国赴日贸易的最大港口。日本船员被送至此处,等候搭乘前往日本长崎的商船回国。日本船员称赞乍浦是“富饶繁华之地,天下宝货于此云集”。地方官对他们十分礼遇,摆台连唱八天大戏安抚难民,又赠予其衣服和珍器,接待无微不至,还给他们配了一名专属通辞王兆龙,他们称其为“龙官”。
在乍浦,他们不仅受到官府的厚待,还受到中国大海商陆名斋的热情招待。陆氏多次前往长崎做生意,由海外贸易致富,其时已经隐退。他对这些日本船员非常同情,招呼他们说:“来到这,就和在日本一样了。不要难过,就让我按照贵国的做法来招待你们吧!”然后便将他们请进其家中。一看之下,这些日本船员惊呆了,陆家营造了一个纯日式风格的“书院造”空间!他们记载,天花板、下门坎、上门木、书房、拉门、隔扇、洗手钵甚至树木都来自日本,宴席上使用的榻榻米、烟盘、烟管、茶、酒器、餐具、托盘也全是日本货,甚至宴会上的鱼肉菜羹用的都是日本食材。在这个纯日式空间里,日本船员终于安下心来,暂时放下了归国之思,一时宾主尽欢。如果说广东和浙江官员对漂流民的隆重接待尚有执行乾隆皇帝“怀柔远人”上谕(8)乾隆二年(1737)浙江总督嵇曾筠、布政使张若震在处理琉球漂流船事件后上奏,建议往后沿海地区处理和遣返漂流民的费用一律由官府公费开支。乾隆皇帝于同年闰九月庚午日下谕批准并著成定规,“以示朕怀柔远人之至意”。春名彻、刘序枫、汤熙勇、孟晓旭等人均认为此条谕旨是清朝救助外国漂流民的定规之始。参见孟晓旭《漂流事件与清代中日关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92页。的考虑,那么民间商人陆名斋招待日本普通船员的热情体贴则纯然是当时中国社会对海外难民淳朴友善之心的体现。
他们在乍浦停留三十天后,于十一月七日乘坐开往长崎的商船踏上返日之旅。他们分乘两艘船:一艘在十一月二十二日抵达长崎;另一艘遭遇风难漂到萨摩的片浦,最终在十二月十四日到达长崎。在遭遇船难而离开日本在外漂泊一年半之后,他们终于返回了故国。
(六)长崎
日本宽政七年(1795)的冬天,9名日本船员抵达长崎后,立马被召至官衙禀告详情。长崎奉行中川忠英(1753—1830)等人向江户汇报了情况,此后得到江户幕府命令,准许将他们送回仙台。在此期间,源三郎在长崎病逝,自船头清藏在安南去世后他就一直担任一行人的领袖。剩下的8人由官府供给食物和杂费,每个月都有两三天休闲时光,以安慰其长年之辛劳。源三郎是一位优秀的记录者,他将自安南以来的地图和见闻都写成日记。回到长崎后,他将其誊抄出来交给长崎奉行,草稿也一并上交。在此期间,中川忠英指示助手近藤重藏(1771—1829)(9)近藤重藏后来成为著名的清朝研究者和北方探险家,作为清史研究的学术前辈,他常被近代日本的中国学研究大家内藤湖南提及。等人编纂《清俗纪闻》《安南纪略》《亚妈港纪略》三部海外资料。这些资料所涉及的正好都是这次日本漂流船队回国途径之地,这或许并非巧合。源三郎的记录可能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漂流船员们在正式上交记录时借机留下了一部抄本带回,所以在他们返回仙台途经大阪期间,民间知识人山片蟠桃才有机会从其手中抄写到此次漂流记录。
此次日本漂流船队里有16人,其中船头清藏、水主宗八、与五郎、久之丞、松兵卫、藤吉6人死于安南,清之丞死于广州,源三郎归国后死于长崎。平安回到家乡的只有8人,包括忠吉、幸太郎、门次郎、平五郎、兵吉、巳之松、周藏和另一位同名的清藏。
二、广东船员与仙台藩护送队
日本宽政八年(10)《梦之代》明确记录为“宽政八年”,与李杰玲文中考证得出的他们漂流到仙台上岸的时间一致。、清嘉庆元年(1796)四月朔日,广东省潮州澄海港(今广东汕头市)一艘渔船出海。船主是广东省新宁县(今广东台山市)大澳港的陈受合,实际船头是潮州人陈世德,另有水手13人。他们在海上遭遇了意外,幸运的是,他们在六月七日漂流到日本仙台藩本吉郡十三浜大室(今日本宫城县石卷市)。他们暂时寄居在村长太郎右卫门的家中,于六月二十二日接受了从仙台赶来的仙台藩儒臣的询问。(11)此事亦记录在石卷市的志书中,参见北上町史編纂委員会『北上町史通史編』,北上町2005年版。
(一)仙台
经检查,这批广东船员有:船头陈世德,水手林光裕、林元江、陈让光、林招声、陈阿猪、陈元合、陈阿嬢、林阿松、朱阿高、林隆辉、陈阿厦、陈阿意、陈贤生,共14人。船身刻着“广州府新宁县大澳港渔船户陈受合大字十七号”,船锚上写着“怡来损谦陈世德书”。仙台藩校养贤馆的学头(相当于校长)儒官志村士辙(12)志村实囚(1746—1832),诗名士辙,日本陆奥国人,曾就学于江户昌平黉。志村三兄弟皆是仙台藩有名的儒学者,被称为“志村三珠树”,他们对日本东北儒学的发展作用甚大。末弟志村弘强(1767—1843)后与兰学家大槻玄泽共著《环海异闻》(1807),记录漂流至俄国的仙台藩水手津大夫一行之事。前往船上,和船头以笔谈进行问答。他们的对话如下(13)《梦之代》所记的谈话内容与仙台藩文献所记颇有不同,可为李杰玲论文补充。:
志:问,尔等何国人?
陈:弟等是广东省潮州府澄海县北门之人,船户是陈受合,船是澄海港之船,过港以广州府新宁县之牌矣。
志:闻广东至五月中,则日中不见影,如何?
陈:午时人影,照在本身上。
志:贵国年书中所书,今年清明、夏至、冬至,是何日么?有所记则书之。
陈:今年清明三月十二日,冬至十一月二十三日。
志:米一斗价几钱?
陈:今米一斗价以三百二三文。
志:广东教小儿,先习何字?先读何书?
陈:先习是“上大人孔乙巳化三千七十士尔小生八九子往作可知也、上士居山水、中仁坐竹林、平生自在志、王子本留心”。先读是《大学》之册,《大学》是四书之内。第一本是为《大学》,第二本是《中庸》,第三本是《论语》,第四本是《先进》,第五本是《上孟》,第六本是《下孟》。
志:传闻,大清商客到长崎港,与本地人说:“鞑靼人不奉中国之命,大清帝命官府,欲以兵击之。然而中国东南之地,亦有不奉中国命者,惹出事来大闹了,故海上多盗贼。商船之来往,大不便了。”兄等在本国之日,闻有此事么?
陈:弟等在乡之日,少闻有此事,未知其详。[4]251(14)此后的问答在《梦之代》里省略了。
在这之后,仙台藩藩主(15)仙台藩藩主伊达齐村(1775—1796),1790—1796年在任。向他们赐予物资,陈船头为此奉书一封,表达了恳切谢意:
国王之大恩,官府之大力,先生之大爱,乡老先生引船入港之恩,我众人之大恩,无物报恩。我众拜谢国王如天,拜谢官府老先生如泰山,拜谢乡老先生如父母。云云。[4]251
在他们停留期间,仙台藩向其提供日常用品和食物。在通报江户幕府并获得批准后,仙台藩决定派出船队送这些中国船员至长崎,同时也将上述日本漂流船员接回家乡。
(二)从仙台至鸟羽
中国船员漂至日本东北地区大约五个月后,在仙台藩官员的护送下开始了回国之旅。护送队的成员包括:护送监志村勘右卫门(即志村士辙)、勘定官野泽驹之丞和古山顺次、通辞志村笃次(可能是志村弘强)、医官竹中道稳、外科胜田寿闲等人。(16)仙台藩文献记录随行人员名字为:医竹中玄畅称道隐、外科医胜田长恭称寿闲、古山世享称顺治。参见李杰玲《18世纪仙台藩儒与潮州渔民唱和文献钩沉——从〈陈林诗集〉说起》,《中国典籍与文化》2016年第3期第137~149页。两处文本略有不同。
十月二十九日,船队从漂着地大室出发,进入临近的大港石卷港。当时由日本东北地区的石卷港至关东地区的浦贺港,水上航行需一百八十里,中途没有其他港口,所以是非常凶险的海域。他们在石卷港大约停留了一个月,可能是进行出航准备及等待自北向南的冬季季风。十二月初他们从石卷出航,于十五日平安抵达了江户湾的门户大港浦贺港(今神奈川县横须贺市)。
十二月二十日,他们从浦贺出航,沿日本东部海道南下。这段航程开始非常顺利,但在即将抵达伊势湾的“三崎”(今日本爱知县田原市伊良湖水道的伊良湖海岬一带)这个地方遭遇了突如其来的强风暴雨。他们与另一艘大船发生冲突,座船的后部被撞破,而晚上的雷声轰鸣如岩石崩塌一般,一行人都以为会命丧于此。幸喜最后有惊无险,他们支撑着越过伊势湾,于二十八日抵达位于三重半岛的鸟羽藩。鸟羽藩藩主(17)鸟羽藩藩主稻垣长续(1771—1819),1794—1819年在任。见到不认识的外地船入港感到非常意外,但随即很热情地接待了他们。鸟羽藩帮助他们修理船只,并邀请他们一起迎接新年。
鸟羽藩之后,仙台船队就有了江户幕府的“公命”,后面的航程中,在每个津浦都有预先准备的引航船带领,因而再未遇到类似的险境。但这段近在咫尺的海上风雨让仙台船队的成员们此后一直心有余悸。
(三)鸟羽
在鸟羽藩的邀请下,中国船员和仙台藩护送队一起参加了新年汉诗联欢会,和汉双方诗人在此欢聚一堂,彼此切磋诗艺。仙台藩校的校长同时也是本次护送队的队长志村士辙继续抓住机会向中国客人询问感兴趣的信息:
志:贵国之音甚多也。
陈:中国大抵正音。广东有广音、有正音、有白音、有客音、有鸟语音、有尖音、有蛇子音。各州各府有乡谈,官府皆是正音。广东通辞之人,各州各府各蕃语共晓得。客音、鸟语、蛇子是深山之人。[4]252
(四)大阪
正月十日,船队离开鸟羽藩,沿着纪伊半岛向西行进,于二月十二日到达关西地区的兵库港(今神户)。仙台护送队的副领队野泽驹之丞此前曾在关西的重镇京都和大阪供职多年,此次来到附近特意前往大阪访问旧友,以消解船中郁闷。接待人员包括蟠桃供职的升屋商行的主人山片重芳(1764—1836)(18)豪商山片重芳也是这一时期大阪著名的兰学爱好者。。此次在大阪举办的宴会也是一次和汉人物齐聚的诗文交流会。据记载,升屋主人山片重芳向中国船头陈世德赠送了十支水笔——典型的文人交往礼物,而陈世德则以扇面题诗回谢:
浪华山片君,见惠水笔五对于陈世德,赋诗谢之。怜君彩毫赠,偏慰远人情。羞将挥洒拙,添得墨华生。[4]252
除这首诗外,陈船头还送出了许多扇面诗。舞文弄墨应该并非船长的本职,但是对于日本官民这一路上密集的社交应酬阵仗,陈世德船头等人还是成功应对了下来。
(五)长崎
仙台船队先后途经日本濑户内海和九州北部海域,于四月十日抵达长崎。江户幕府派驻长崎的长官奉行平贺贞爱(1759—1817)即刻前来慰问。十一日,仙台护送队将中国船员交给长崎奉行所。估计此后不久,这些中国船员就随来日本做生意的中国船队(19)按仙台文献记录,接收陈世德一行的是陈晴山、朱鉴池两位清商。参见李杰玲《18世纪仙台藩儒与潮州渔民唱和文献钩沉——从〈陈林诗集〉说起》。回到了广东。
不过,长崎奉行当时不能立刻将漂流至安南的日本船员交来,所以他让仙台护送队在长崎稍候,准许他们四处游览。接下来两周时间,仙台藩众人在日本当时的“对外特区”长崎尽情游览,参观了在长崎的清人和荷兰人的居住地。
清人驻在长崎的侨领热情招待了仙台护送队。仙台人记载,宴会上珍馐众多,席上罗列的珍果就有四十多种,甚至连石阶上都摆满了,大家从中间走过取用,顺道就将整个馆舍都参观到了。如此看来,当时中国人所设的答谢宴会很可能还采用了时髦的自助餐形式呢!
仙台人还参观了位于长崎出岛上的荷兰商馆。荷兰商队亦为他们举办宴会,以酒水和菜肴招待他们,但他们喝不惯也吃不惯,感到不合口味。宴会上荷兰人安排了昆仑奴奏乐,但仙台人觉得音律不和谐,并不怎么好听。1795年荷兰共和国亡于法国革命军入侵,管理东亚贸易的荷兰东印度公司陷入混乱,长崎的荷兰商馆正处在一个艰难时期。而荷兰商馆此次宴会仍安排了乐队,应该属于比较郑重的西式接待。当时的仙台藩人士却并未觉得这些西洋酒菜和音乐如何受用,可见当时日本内地的藩国人士对西洋文化尚未产生特别的倾慕之情。
(六)回程途经大阪
四月二十四日,仙台藩众人接到了本藩的漂流民,次日即出发离开长崎返回,这次他们选择了陆路。五月二十日,一行人到达大阪。此年春天,蟠桃正奉命离开大阪到仙台出差,因此错过了上一次仙台护送队去程途经大阪的机会。而这一次,他幸运地赶回,于五月二十一日在大阪旅舍拜会了一行人,并向漂流船民了解到许多异邦的事情。
照此推算,日本漂流船员们返回仙台家乡应该是1797年的下半年,即离开家乡出海执行航运任务整整三年之后。中国船员应该也于当年返回了老家,距其出海一年多。若论此次双方的际遇,相对而言中国船员还是幸运一些的。
三、中日漂流民经历所见的十八世纪末东亚海域社会样貌
海上谋生之路风险莫测,对漂流人员的救助和送还也是东亚海域各国政府必须肩负的一项长久责任。发生在十八世纪末期日本和中国船民的这两次漂流事件,虽然只是留下历史记录的众多漂流事件之二,却自有特殊的意义。首先,这两个事件碰巧形成一个对照,位于东亚海域南北两端的南海和日本东岸因之联系起来,而中日两队船民前后两年内穿越对方国度的长途旅行际遇也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共时性资料。其次,这两次事件都由于日本民间知识人的参与而留下了记录,这与一般的官方记录相比又体现出另一番视角。
作为记录者的日本民间知识人、大阪商人,山片蟠桃对自己接触到的这两次巧合事件也是十分感慨。他首先感到东亚和平盛世的可贵,衷心赞颂当时“天下泰平”、四海一家的清明政治。但他也因中日船民在对方社会中不同的文化表现而感到当时日本社会的文化程度与中国差距甚大,为此生出一种自责的心情:
广东人漂着至仙台,仙台人漂着至广东,同得慰劳,同得护送归国,此乃天下泰平之效验、四海一辙之政事,口不言而心同一也。可不谓盛事哉!然,汉人来日本,渔夫亦可与儒士对谈诗赋;日本人至他邦,唯默默悲泣,不乃可耻乎?[4]253
不过,以笔者的眼光来看,蟠桃的这番自责恐怕有些不必。十八世纪末,日本人受制于江户幕府在十七世纪定下的锁国禁令而不准私自出海,曾经纵横东亚海域的日本商队疏离国际海洋贸易已超过一百五十年。日本船员在折损多名成员的困难情况下保持了队伍的团结,还在陌生的安南、中国留下了准确而生动的完整记录,他们的表现也非常优秀,并没有什么可指责的。汉文毕竟是汉人母语的文字系统,而能带领一支船队的陈世德船长在一系列外交场合应对得体,显然是位优秀的人物,可能也曾是一位投身举业的读书人,“渔夫”本人并不简单。蟠桃因其一人的优秀表现而推论出日本人应感到可耻云云并不太合理。但是这也反映出,当时日本文化界存在一种要在汉文领域与中国文人比肩的自我期许,以及在国际格局中获得尊敬的渴望,甚至隐约流露出某种“小中华”心理。
通过这两支漂流船队的际遇,我们也可对十八世纪末中日各自的行政特点有一些直观的认识。
首先,若以中日两国送还漂流人员的行政效率而言,乾嘉时期的清政府应是胜过了日本的江户幕府。日本船员从澳门进入中国官员的管辖范围是乾隆六十年(1795)七月十六日,十月六日便抵达归国港口乍浦候船,历时不到三个月。而中国船员漂至日本陆地是宽政八年(1796)六月七日,抵达归国港口长崎是次年四月十日,历时超过十个月。同时,日本船员在中国跨越广东、江西、浙江三省的行程连续而顺畅,可见地方政府间衔接紧密。而中国船员在日本的海路行程因有无“公命”分成前后两段,江户幕府并未在全程显示存在。可见,日本的中央与地方以及各地方之间的关系欠协调,存在隔阂疏漏。中央集权国家中国与藩国林立的封建制国家日本之间的区别在此体现得十分明显。江户时代中后期,日本社会出现要求建立中央集权政府的呼声,并因此引发天皇权威的高涨与江户幕府统治体制的动摇,最终通过明治维新完成这一国家政治体制的转换。从此种历史的发展趋势来看,江户时代日本的武家封建体制在行政效率上确实存在较大制约。
其次,日本社会体现出非常旺盛的信息搜集欲望和突出的搜集能力。从接触开始,日本东北的地方政权仙台藩就派出藩校校长这类高级专业文官对漂流民进行询问,护送途中又抓住各种机会进行观察和深入了解;同时幕府直辖的长崎港也在长官的指示下进行系统的海外信息整理工作。不仅官方态度热切,日本的民间知识人也积极抓住机会参与对外国船员的接待和对外游归国船员的询问。他们希望了解的内容未必与漂流民本身的需求有关,往往是出于自身的知识兴趣,尤其是对中国地理、经济、教育、政情等重要内容的关注。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漂流船员自己也对外游行程有明确的记录意识,在外期间多方观察,回国后也十分配合本国官员的信息搜集工作。可见在十八世纪后期,日本社会通过各方人士的共同努力实现了对国内和国外漂流民信息渠道的充分利用。
最后,这两次漂流事件的细节还透露出十八世纪末东亚海域社会值得注意的一些状态。
其一,安南西山政权在接触日本漂流船员的仪式上完全采用火枪火炮,而弃用刀剑等冷兵器,这大概是东亚海域空间在法国等西方势力的影响下即将迎来新一轮武器换代的前兆。安南西山政权与华南的海盗组织有密切关系,不知当时广州官员是否对这些途经安南的落魄异国漂流人士保持了足够的好奇心。
其二,澳门社会对日本船员态度冷漠。其中或许有某些偶然的原因,但日本船民和知识人将其理解为断商和禁教造成的隔阂。他们认为,日本与基督教势力在一百五十多年前结下的禁教血仇并未被时间冲淡,而这些倒霉的仙台渔民是承担了十七世纪江户幕府将军在九州血腥屠城的报应。他们很自然地首先付诸历史原因,而并不考虑经济往来等共时性因素。可见在前条约时代,历史记忆在东亚国际关系的思维逻辑中比重颇高。
其三,汉文、中国通辞、佛教寺院在当时东亚海域社会发挥的桥梁和网络作用在这些史料中再次得到了印证。日本船员靠着书写汉文得到安南渔民的帮助;而中国船员也因此得以与日本儒者笔谈沟通,并因汉文水平成为社交宠儿,一路上备受礼遇。安南、中国、日本各地凭借汉文得以开展有效的漂流民救助合作。可见,在英语盛行之前,汉文曾在此海域发挥国际语言的作用。许多中国人也因汉文和语言能力活跃于世界舞台,如当时在安南担任至少中日越三语通辞的南京人Tenkuhan,在乍浦充当日本船队通辞的王兆龙。他们以及在乍浦打造纯日式居所的退休海商陆名斋、在长崎唐人商馆举办宴会的驻日华人,都体现出十八世纪末中国商人广阔的海外视野,以及其思想行动中的开放意识。而佛教寺院如安南的永平寺,则为漂泊在这片海域讨生活的各国人士提供了一方生前死后肉身和灵魂的安放之地,成为海域社会居民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结 语
综上所述,1794—1797年发生在东亚海域的两次漂流事件,因时间的相近与地点的相关,尤其是日本社会各方面力量和民间知识人的参与,留下了一段别具意义的历史资料。日本仙台藩船民漂流至安南,途经澳门、广东、江西、浙江,由长崎、大阪最后返回家乡,在多地积累了丰富的见识。几乎与此同时,中国广东潮州船民漂流至日本仙台,经由日本东海岸、纪伊半岛、濑户内海、北九州,顺利抵达了返乡的港口长崎,一路备受日本官民礼遇。可以说,大难不死的中日两队漂流船员分别在对方国家有不一般的际遇。
他们的经历如跨越南北的横截面,折射出十八世纪末期太平洋西部这片东亚海域各地的社会样貌。比如安南西山王朝完全采用枪炮的武装实力、澳门商人主政的西洋风情和对日冷漠态度、广州汇集世界商船的富足生活、中国内部顺畅通达的河运交通、浙江乍浦对外国客人的体贴和巨大财力、日本各地学者对汉诗文的交流热情等等。
我们尤其应该注意,当时中国文化在东亚区域内具有高度的影响力。汉文是这片海域的通用文字,中国通辞和中国商人的足迹遍布海内,在越南、日本等地都能获得令人尊重的社会地位。与之相应的是,中国政府在应对漂流民事件中体现出行政的高效和妥帖,广东、浙江等地社会对待外国难民也表现得善良、热情,总体呈现出社会安定的大国心态。
同时,日本社会对世界情报的高度求知欲和信息搜集能力也表现得非常突出。日本幕府、地方政府、官方和民间知识人、漂流民众都主动自觉地致力于搜集外部世界信息,他们的共同努力形成对这两次漂流事件的详细记录,并且此次经历很可能为其后日本文化界汇集资讯和培养人才提供了启发和训练。此后大约十年内,长崎奉行所先后编纂了《清俗纪闻》、《安南纪略》(稿)、《亚妈港纪略》(稿)一系列海外资料,而仙台藩儒者又通过询问漂流至俄国的归国船员编纂成《环海异闻》;参与其事的幕臣近藤重藏和仙台藩儒臣志村兄弟后来均成为外国问题研究专家。可以说,日本社会非常充分地利用了这两次漂流事件带来的信息和经验。
由此可见,日本学界对漂流民经历的研究确实由来已久,可以说是始自前近代。不过中文学界也自新世纪开始投入对这一史料宝库的发掘,如今研究正待推进。希望本文对十八世纪末期这两次中日船员漂流事件的介绍和解读可以对此项事业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