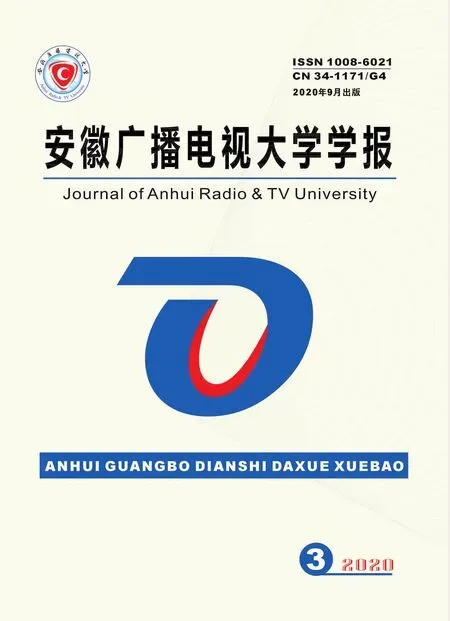吐蕃时期敦煌寺院的赋役探析
徐秀玲
(河南大学 文献信息研究所,河南 开封,475004)
入唐以后,官方文献中不断出现沙门“逃租赋”“避征徭”“避役奸讹”等的记载,可知此时的佛教寺院已经向官府缴纳赋税、承担徭役。中唐时期的敦煌地区,敦煌文书记载寺院缴纳赋税,僧人承担劳役的情况记载更多。对此,谢崇光、姜伯勤、郝春文、苏金花、王祥伟等先生主要从敦煌佛教世俗化的角度分别对僧尼承担赋役等情况进行了探讨(1)参见:谢崇光《略论唐代寺院、僧尼免赋特权的逐步丧失》(《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3年第1期);姜伯勤《唐五代敦煌寺户制度》(中华书局1987年版);郝春文《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僧人的税役负担》(《敦煌研究》,1998年第2期);苏金花《试论晚唐五代敦煌僧侣免赋特权的进一步丧失——兼论归义军政权的赋税制度》(《敦煌研究》,2000年第3期);李正宇《8至11世纪敦煌僧人从政从军——敦煌世俗佛教系列研究之七》(《敦煌研究》,2008年第1期);王祥伟《归义军时期敦煌寺院的税役负担析论》(首届中国经济史学博士后论坛: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历史探索,2014年)。。为更好地了解中唐时期吐蕃统治下敦煌寺院的赋役全貌,笔者从寺院的赋税、军役及其他杂科役等方面对相关内容进一步考述。
一、吐蕃时期敦煌寺院的赋税
中唐时期吐蕃统治下敦煌寺院缴纳赋税有官布、地子、税草、税柴等。王祥伟先生指出,在吐蕃本土曾明文规定寺院及其属民征税及课役可免,敦煌地区的寺院及属民是要交税的。由于寺户的经济规模较小,其税负可能主要还是由寺院承担。作者所依据的间接材料是榆林寺财产清册中把寺户、奴仆与牲畜、公产等列入财产一类以及Ch969-72《唐(开元九年?)于阗某寺支出簿》中于阗某寺为家人缴纳税草及其他负担等记录[1]。但是敦煌寺院缴纳赋税的情况确实存在。
(一)官布
吐蕃统治时期敦煌寺院缴纳官布。S.2228号《辰年巳年(9世纪前期)麦布酒付历》文书比较全面地记载了寺院以布纳官情况。为明白起见,迻录文书如下:
“日□发布九疋,并付兴胡胡充悬欠(用)。断麦五硕五斗,至秋还。其布纳官用。又张老于尼边买布一疋卌二尺,至折麦壹硕五斗两家合买,其布纳官用(各半)。吊田秀妇平意布三丈三尺,其布于寺家贷。又于寺家取布两疋,辰年十月折麦纳官用。又于寺家取布一疋,智秀受戒时告裙衫用。巳年四月九日,共曹延断空设热布一疋,墨两挺(已上)当家送纳……又索家贷粉紬一疋,其紬四月十日却对面分付惠照上座于……五月十四日,于李日荣边买小钗子一三升,其钗子折麦十硕,并汉斗。于阴兴兴边付本身麦三驮,又对僧员岸付麦一石八斗,又对僧觉义[付]麦三石,并汉斗,施本身麦六汉斗,□五付磑课用。后五月付宋澄清酒半瓮。廿二日,付王□□麦半驮。廿五日,又付宋澄清麦六汉斗,又酒半瓮,付□□□布□□。”[2]
本件文书的时代,唐耕耦先生定为吐蕃统治敦煌时期[2]149。从账历内容看,属于某寺院的支出历,历中多处记载了某人从寺院取布纳官的情况,如第1~2行载某于寺家贷布,“断麦五硕五斗,至秋还。其布纳官用”;又如张老在某尼处买布“一疋卌二尺”,“折麦壹硕五斗两家合买,其布纳官用”。第5~6行有“又于寺家取布两疋,辰年十月折麦纳官用”。这里官应指吐蕃政权。因此本件文书应是吐蕃时期某寺向官方缴纳官布的一份证据。
(二)地子
吐蕃统治敦煌时寺院缴纳地子。据王祥伟先生研究,吐蕃时期寺院的自营地收获归寺院所有,即使是寺户分种地,由于寺户的地位低下及耕作的不自主性,收获物的绝大多数依然归寺院所有,故此时基于寺院土地上的税负应由寺院承担。但是到归义军时期寺院土地的耕种方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出现了租佃经营与寺院自营,寺院出租部分土地的税收应由承租方承担,而少量的寺院自营地,应该由寺院承担税负向官府交纳地子,但是因相关文书残破,这方面的明确记载阙如[3]。然而据P.2222《僧张智灯状》等资料中的“承料役次”及归义军“据地出税”的原则,僧人可能也要缴纳地子。
(三)税草、税柴
敦煌文书中记载的税草与税柴也是寺院与普通百姓向官方缴纳的重要赋税之一。吐蕃“马年(718)夏,赞普驻于跋布川。夏季会盟事于卓布尔,由尚赞咄热与论绮力心儿藏热二人召集之。达布王立红册木牍。冬,赞普驻于札玛牙帐。征三茹之王田全部地亩赋税、草税”[4]。资料记载的虽然是吐蕃征服三茹地区后对三茹王田全部土地上的赋税、草税。然而这从一定程度上说明吐蕃对统治区域内赋税的征收是包括税草的。吐蕃统治敦煌以后对税草的征收也不可避免。
二、吐蕃统治敦煌时期寺院的徭役
吐蕃时期敦煌寺院承担的徭役, S.542v《戌年(818)六月沙州诸寺丁口车牛役簿》记载得比较全面,转部分录文如下:
戌年六月十八日诸寺丁口车牛役部。龙兴(寺)王仙:泥匠。仙玉:看硙。张进国:守囚五日,四月廿四日差回造粳米三日稻壹驮半寅年死回造稻谷两驮。张善德:团头,丑年九月七日死。曹进玉:六月修仓两日修仓五日子年正月守囚五日子年送瓜州节度粳米丑年送刘教授廓州。张进卿:逃走。史朝朝:修仓五日,园梨(放)五日,回造稻两驮。朱进兴:差入山(西同)廿日,取羊亥年役,子年十二月差舂稻两驮。张光子:六月修仓两日车头,回造米粟一驮半。张买德:车头,守普光囚五日。张光进:修仓五日,丑年阿利川算人户卅五日子年十二月差舂稻两驮。薛咤奴:守囚五日子年十二月差舂稻两驮。张小汉:车头,子年六月死。尹莽塞:守囚五(日),修仓两日。张进朝:放羊,守普光囚五日。史英俊:木匠,修安国五日,造革桉凡两日。李王子:修仓五日,亥年瓜州送节使粳米。成意奴:修仓五日,子年十二月差舂稻两驮。孙承太:三月守囚十日修安国佛五日。曹进兴:放駞。曹奉进:蕃教授手力。申太太:扫地,造修桉两日。张像法(?):蕃卿手力。张清清:怗看硙。索再晟:打钟,守普光囚五日,贴駞群五日。张国子:与王仙五日,子年十二月差舂稻两驮。史升朝:放羊,贴駞群五日。曹小奴:守囚五日修仓五日,子年三月差剉草十日。张观奴:守仓,张像尼子年十二月差舂稻两驮。李庭秀:团头,回造粟一驮半。李君君:丑年五月萨请儭羊,又九月阿利川请羊。段周德:丑年常乐过瓜州节度,又阿利川请羊。曹进进:送瓜州节度粳米,又阿利川请羊,卯年历梨请羊。张荣荣:送西州人户往瓜州,阿利川请羊。张仙进:死。兴国:持韦皮匠,贴马群五日。赵卿卿:报恩。加进:守囚五日,贴马群五日。薛归奴:看园守永安囚五日。曹莫分:判官駈使。
朱宝昌:团头,卯年二月死。阎先章:放羊。大云寺李日兴:回造粳米三日壹驮半稻洛回纥。樊鸾鸾:死修仓五日。安保德:煮酒一日回造粟一驮半。成孝义:死车头修桉两日修仓五日。史加进:团头,看硙。王进兴:修仓送节度粳米。刘孝仙:团头造革桉凡两日回造米粟一驮半送刘教授廓州。李加兴:六月修仓两日,南波厅子四日送节度粳米子年十二月差舂稻两驮,洛回纥。安俗德:子年十二月差舂稻两驮。安满奴:子年十二月差舂稻两驮,洛回纥修仓五日。李顺顺:死。安买德:持韦洛回纥。史兴进:守囚五日回造稻两驮。安苟苟:回造粟一驮半。赵孝谦:死。刘孝顺:回造粟一驮半。刘孝忠:看硙,送西州寺户往瓜州子年十月六日[5]。
本件文书中记载的吐蕃统治时期敦煌寺院的四十余种徭役,姜伯勤先生把其分为八类:田园役(艾稻、剉草、看园、园收)、畜牧役(放羊、请羊、取羊、放驼、贴羊、贴驼群、贴马群)、匠役(泥匠、木匠、持韦皮匠、纸匠、毡匠、持韦)、加工役(看磑、看樑、回造米粟、差舂稻、煮酒)、修造役(修仓、修佛、修函斗、修鞍)、杂役(守仓、厅子、手力、扫洒、送米、送寺户、算人户、迎送官员、窟收、纳佛殿佛麦夫、打钟)、车役(车头)、官差(营田夫、守囚)[6]。可知吐蕃时期敦煌寺院寺户承当的劳役,涉及种植业、畜牧业、手工业、建筑业、官差科、迎送官员及各种人事往来等,几乎包涵了敦煌社会生产生活的每个方面。而这些劳役应该属于吐蕃统治敦煌时期,寺院以寺户的名义承担的世俗政权的各种徭役。
此外,吐蕃时期寺院僧人的徭役还包括写经。如S.5824《经坊供菜关系牒》记载中的抄经人[5]142。陆离先生指出,吐蕃王朝崇奉佛教,以僧人为相总理国政,实行三户属民制度(后来又发展为七户属民制度)和寺院属民制度,供养各级僧侣;广建寺庙,举行法会,组织译经;在敦煌地区则多次组织部落民户抄经。吐蕃官府组织部落民户抄经实际上也是一种劳役[7]。又,比较明确记载吐蕃时期僧人承担看磑劳役的是P.3774号《丑年(公元821年)十二月沙州僧龙藏碟》第48~49行载:“齐周去酉年看丝绵磑所得斛斗,除还外课、罗底价、买鉴一面及杂使外,余得麦粟一卌石,并入大家用。”[5]285齐周身为僧人,去丝绵部落看磑可得斛斗若干,可知寺院僧人也有看磑的徭役。
郑炳林先生指出,中晚唐时期敦煌的人口数量,一般在3万至4万之间[8]。吐蕃占领敦煌初期佛教教团人口400多人,此后虽然没有记载,但每个寺院的人数一直处于增加的趋势。况且,当时敦煌的寺院还荫蔽有相当数量的附属人口,站在赋税与徭役的角度,敦煌寺院僧尼及附属人口的数量,对于世俗政权来说,也是一笔较大的数字,直接影响着政权财政税收的总量与政权的稳定。为了世俗政权的生存,敦煌寺院的僧人或许除了身份上是僧人,有重要佛教活动必须按时参加以外,其他方面实则与敦煌普通的百姓一样,成为缴纳赋税、承当徭役的重要群体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