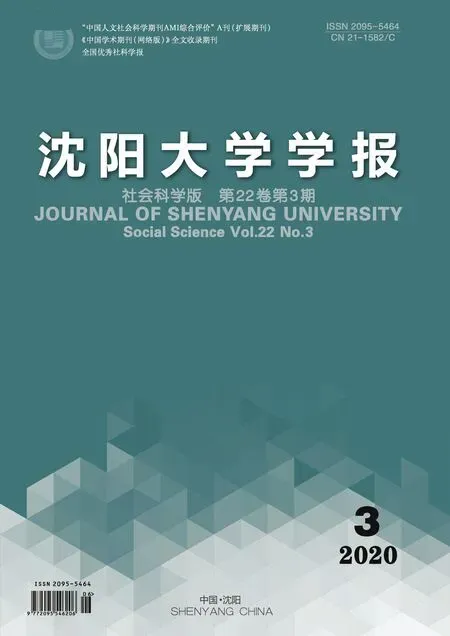空间表征与身份表演:《心是孤独的猎手》中的双重变奏
吕佩爱, 李子阳
(同济大学 外国语学院, 上海 200092)
长篇小说《心是孤独的猎手》作为卡森·麦卡勒斯(Carson McCullers)的处女作,被美国现代文库评为“20世纪百部最佳英文小说”。麦卡勒斯笔下的人物在不同地点的辗转往复构成了一幅独特的美国南方社会图景,赋予了小说极强的空间叙事感,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强烈关注。他们分别从空间意象的“幽暗”“奇异”“狭隘”等角度解读小说中的怪诞和哥特式风格。如格里森·怀特(Gleeson-White)认为其中的空间意象弥漫着幽闭恐惧的氛围;肯尼斯·查米李(Kenneth Chamlee)指出,麦卡勒斯笔下的空间具有封闭的倾向;路易斯·威斯特林(Louise Westling)则认为,由于麦卡勒斯小说中的活动几乎总在为数不多的几个内景中开展,所以其笔下的空间景观具有狭隘的特点。这种“空间转向”(spatial turn)使更多学者关注到了麦卡勒斯小说中的“空间叙事”(spatial narrative),为小说的解读提供了全新的“空间批评”(spatial criticism)视角。但他们的研究多是针对小说中的地理空间意象,如酒吧、医院、学校、房间等,侧重这些意象的怪诞氛围和哥特风格,而忽略了主观意象上的心理空间及其对人物塑造的影响。包括金莉在内的中国学者都强调了小说中哥特式的空间所塑造的幽闭主题对人物的重要性;林斌从社会身份建构和多元化的女性主义视角阐释了“精神隔绝”这一典型哥特主题。他们推动了麦卡勒斯研究在中国的发展,但仍旧以“怪诞”“哥特”为切入点来解读作品中的“孤独”主题,在一定程度上缺乏研究的多样化和整体性。
总体而言,国内外诸多研究都认为这部作品体现了“南方文学哥特流派”的写作特征,然而麦卡勒斯本人却认为这个标签不恰当。从哥特文学的角度解读这部文学作品,过度强调了空间意象的幽闭恐惧,忽略了空间表征对人物身份表演的重要作用及其中的社会内涵。生产的社会关系是一种社会存在,以至于是一种空间存在,它们将自身投射到空间里,在其中留下烙印,与此同时又生产着空间[1]。空间和社会关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身份建构即在空间中完成,探讨人与空间的辩证关系,对于确认个体身份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本文尝试突破哥特式的空间解读视角,不再聚焦于小说中空间的“怪诞”“哥特”风格,主要结合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爱德华·W·索亚(Edward W. Soja)等思想家的空间理论,探讨小说中无名南方小镇的空间意象及其折射出的人物社会关系,揭示小说中人物在身份建构过程中的阻碍与矛盾,分析他们通过不同空间建构身份的过程与尝试,反映20世纪40年代美国南方社会支离破碎的生活状态,以及社会边缘人群对建构新身份的执著追寻。
一、 第一空间:伤痕与迷惘
第一空间是对空间的一种物质性解读,指的是真实、具体的物理概念空间,而在空间实践中,物理空间是一种重要的空间表现形式和社会生产实践场所[2]。“第一空间认识论”最早由列斐伏尔提出,索亚根据他的理论进行完善和发展。索亚认为人们所能感知的、物质的空间,都可以采用观察、实验、测量等经验手段来直接把握。对第一空间的认知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原始的空间分析法,通过地点和环境等就对象进行集中描述;另一种是在社会过程中,对地点和场所对象进行定性分析。人类的生存居住环境,还有社会与自然的关系都与第一空间不可分割。在《心是孤独的猎手》这部小说中,所有的故事都在一个南方小镇上悄然发生,然而隐匿在小镇背后的却是种族隔离和等级制度划分带来的伤痕与迷惘。根据索亚的空间理论,第一空间包含房屋、城镇、地域、国家等,这些空间的特性往往隐喻了人际关系的亲疏。本节对原文中的南方小镇这个物理空间进行探讨,通过对第一空间的第二种认知方式,分析第一空间中不同人物所面临的身份危机。
小说开篇就描写了小镇作为物理空间,即第一空间的全貌。小镇位于深南地区的中部,镇子很大。主街上有几个街区,由两三层高的店铺和写字楼组成[3]。随之,作者便强调了镇子上最大的棉纺厂的作用,它生意兴隆,雇佣了很大比例的小镇人口,是城镇的景观中心及小镇的经济支柱,同时也是大部分小镇居民的工作场所。但与之对比强烈的是街道两旁的行人,脸上常常显露出饥饿和孤独的绝望神色[3]6。列斐伏尔认为社会空间中存在“空间三一论”的概念,而小镇是以棉纺厂的生产运作为中心的“空间实践”(spatial practice),即包括生产与再生产和具体场景所形成的特殊的空间体系[4]。镇上的居民通过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在棉纺厂这个特定的空间里进行空间实践。然而,隐匿在小镇空间背后的是社会资源分配的不公,而资源分配不公则直接导致了等级制度的划分,从而引发了空间内各个阶层的矛盾与个体的身份危机。小说中的非洲裔医生科普兰是一名马克思主义者,一直以来,他都因为种族问题而饱受歧视。为了改变这种情况,他把改变同胞乃至于整个小镇居民的生存状况当作自己的使命。面对镇上大部分人穷苦潦倒的生活与棉纺厂阶级压迫般的权力运作机制,他曾对棉纺厂的工人们说:“土地、黏土、木材----这些东西叫做自然资源。人类并不生产这些自然资源----人类只是开发利用它们,只是使用它们来生产。因此,任何一个个人或团体是不是有权拥有这些东西呢?一个人怎么能拥有种植庄稼的土地、空间、阳光和雨水呢?”[3]180他挨家挨户地宣传自己的使命和理念,他认为自然资源是大家共有的,不应该被任何个人或团体利用而盈利。然而棉纺厂的生意兴隆,但工人们却一贫如洗;拥有工厂的是百万富翁,辛勤工作的工人们却填不饱肚子。
在这样的“空间实践”的背后,掌握经济命脉的百万富翁们处于社会高层,是支配者的身份地位,没有任何自然资源的小镇工人们处于社会底层,是被支配者的身份地位。南方小镇的运转机制产生了权利和资源争夺,贫富差距不断加剧,阶级对立一再激化,人们想改变这种状况却无所适从。长此以往,这样的权力运作机制在小说中每个人物身上都烙下了深刻的伤痕。辛格失去相伴多年的好友来到小镇寻求知音,米克为了实现梦想在青春期拼命挣扎,比夫在婚姻中承受着无法言说的伤痛,杰克迎着日出前行踏着暮色晚归,在小镇上打工、流浪。
南方小镇作为物理空间完成了“空间实践”后,成为了一个“空间表征”(spatial representation),造就了身处其中的特殊个体。这个表征是一个概念化的空间,“相关团体”和人群以他们构想的方式居住并生活在这个空间里[4]190。人们生活在被规划的区域里:穷人区、富人区、工业区、商业区,这些区域的划分以等级制度、社会功能等元素为依据。整个小镇居民的生存状态也如地图般清晰地划分,人们不断做出努力,试图摆脱原有的身份禁锢,不断徘徊挣扎:哑巴辛格漫步于城市街道,丧失了生存感与归属感;处在青春期的少女米克怀有音乐梦想,却对成长充满恐惧;性无能者比夫以独特的方式经营咖啡馆,却遭遇着婚姻危机;流浪汉杰克四处为家,妄想着一场工人运动;非洲裔医生科普兰因为肤色问题同时承受着社会歧视和亲情破裂……南方小镇作为第一空间,除了拥有地理学的物质性内涵以外,还被赋予了权力与压迫、等级与冲突,种族与反抗等社会内涵。人们在第一空间里承受着社会制度所带来的伤痕与建构新身份所带来的迷惘,从而对整个小镇的社会格局和个体的身份认同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 第二空间:觉醒与探寻
与第一空间具有单纯的地理性质不同的是,第二空间指人类认知形式中的空间性,它形成于空间观念之中,是人类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对空间概念进行的再表征。在认识第一空间的基础上,人们从地理学的想象中获得对空间的概念,进而投射到现实世界中,对第一空间进行命名,逐渐形成了例如“学校”“医院”等具有特定社会功能的第二空间。小说中以“咖啡馆”和“南方游乐场”等不同的认知形式来看待不同空间时,就是以第二空间认识论的形式来进行对空间的认知。“咖啡馆”和“南方游乐场”同时也是小镇中最显眼的两个场所,是对社会现实写照的第二空间,人们在第二空间里的社会活动反映了其身份意识的觉醒,以及个体建构新身份的思考与探寻。
首先,咖啡馆与游乐场激化了社会矛盾与种族问题。作为一种个性化的活动场所,形形色色的人都来这里试图用第二空间的精神概念来寻找空间的实际意义,而充满“混杂性”特征的空间本身就意味着矛盾与冲突。在咖啡馆,当科普兰与杰克一同走进来时,有的顾客便提出了抗议。不同的种族对咖啡馆的空间认知有所不同,一部分人认为这里是特定种族进行消遣娱乐的空间,而另外一部分人则认为这个空间能给人带来舒适和自由,是公共的、任何种族都能够平等享用的空间。同时在南方游乐场里,这样的矛盾与冲突也时常上演。人们对游乐场的空间认知不同,从而导致种族和阶级矛盾不断在空间里被激化,最终被点燃,以暴力的形式不断上演。首先是因为一张门票而引起的纠纷,为了体验旋转木马的娱乐项目,一个女孩和一个非洲裔女孩在打架,人群各有偏袒,场面嘈杂,一片混乱。然后一个非洲裔年轻人被谋杀。最后是小说的结尾部分,骚乱接二连三地发生,没人能让骚乱停下来,最终引发了族群的集体斗殴,伤亡极其惨烈。在咖啡馆与游乐场发生的种种冲突中,种族矛盾不断被激化,人们在这种具有排他性的精神空间里有了身份意识的觉醒,渴望被平等对待。
然而,充满矛盾的场所也成为了个体进行身份探寻实践的空间。咖啡馆和游乐场在不断激化小镇矛盾的同时,却又被人们赋予了不同的理想状态及精神意义,成为了一个带有乌托邦色彩的理想王国。在其他店铺打烊时,咖啡馆的老板比夫坚持经营,同时游乐场也营业至深夜。无论是咖啡馆还是游乐场,都是具有娱乐性质的场所,小镇上所有的居民都可以到这样的地方来,全民都可以参与。在美国南方社会中,不同的客人都可以到这些地方进行第二空间的实践,他们代表南方社会的不同群体与阶级,代表不同的种族、文化和社会身份,无论是残疾人还是妓女,医生还是流浪汉,成年人还是青少年,都可以聚集于此,探寻自身的理想身份,造就一个具有开放性的精神空间。如咖啡店老板比夫尤其善待弱势群体,并宣称“我喜欢怪人”[3]14,他把咖啡馆塑造成边缘人群的庇护所,寻求边缘人群的身份认同。“他对病人和残疾人有一种特殊的亲和感。任何时候,只要有兔唇或结核病人走进店里,比夫都会请他喝啤酒。或者,如果顾客碰巧是个驼背或瘸子,那么准会为他提供一杯免费的威士忌”[3]21。游乐场亦是这样的场所,它模糊了阶级与种族的边界,各色人群在此狂欢,所有人都可以在此找到容身之地。“晚上,游乐场点亮彩灯,显得花哨而俗气。旋转木马跟着机械音乐转圈子。秋千飞转,掷币游戏周围的栏杆处总是水泄不通”[3]144。流浪汉杰克也在此成为一个自食其力的工人。“他不再是一个陌生人。到现在,他认识镇上所有乱七八糟的贫民窟里的每一条街道,每一条胡同,每一道篱笆。他还在南方游乐场工作”[3]144。无论是咖啡馆还是游乐场,人们都在此进行了不同的身份探寻。在被赋予理想状态的第二空间里,全民参与的特性与第一空间里的社会等级制度相对抗,在第二空间里,阶级差别与种族矛盾被逐渐淡化和缓和,咖啡馆和游乐场成为了具有开放性特征的小镇边缘人群避难所。
小镇的咖啡馆与游乐场既具排外性又具开放性,福柯把这样的空间称为“异托邦”(heterotopia)。它与乌托邦相对,是人们生活在其中的空间,却同时也是让人们被隔离其外的空间。人们的生活状态与历史轨迹都被镌刻在这样的异质空间里。咖啡馆与游乐场既是存在着的真实空间,又是让大家生活其中却又存在矛盾的空间。它们以异托邦的形式存在于小镇的第二空间里,排他性让人们有了身份觉醒的意识,同时它的开放性又让人们进行了身份探寻的尝试,体现了空间与身份建构的张力。
三、 第三空间:成长与疗愈
爱德华·W·索亚认为,第一空间与第二空间并不是孤立的状态,它们彼此有一定的关联,但这样的二元模式解读存在一定的弊端。在社会历史领域,作为有不同社会功能的第二空间已经完全控制了只具备地理性质的第一空间。然而,第二空间体现的控制力,同时也是具有霸权性与统治性的社会关系的反映。有鉴于此,索亚试图突破这种二元论的模式弊端,引入了第三空间的概念。索亚把第三空间界定为一种方法,目的在于改变人类生活的空间性,鼓励人们对城市和地理景观加以思考,用不同的方式开辟新视野。这是一种独特的批判性空间意识,正可适应“空间性-历史性-社会性”重新平衡之三维辩证法中体现新范域、新意义。由此开始一个漫长的故事或者说旅程[1]13。第三空间融合了第一空间和第二空间的范畴,同时又进行了地理性与空间性的想象,在体现空间社会功能的基础上融合了内心体验与感受。第三空间概念的提出,使空间突破了地理性质和社会功能性,具备了心理空间的建构特质。在小说中,米克面对成长的困惑,通过“里屋”和“外屋”这样的第三空间建构起了自己的身份,寻找到了心灵的归宿。“里屋”和“外屋”既是真实存在的物理空间,又拥有想象的概念,是米克融合了现实空间与心理空间而建构起的“第三空间”。
处于青春期的少女米克面临着成长的恐惧,这种恐惧投射到了她对两种空间的徘徊当中。一方面,她苦苦挣扎于捍卫让自己成长的私人空间;另一方面,她因无法融入公众的、陌生的空间而感到懊恼。英国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在《一间自己的房间》里写道:“女人要想写小说,必须有钱,再加一间自己的房间”[5]。对于女性而言,要想实现自我成长,一间自己的房间尤为重要,然而由于米克家境贫寒,她从小就没有办法拥有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她与姐姐们共用一间房间,在姐姐们试图把她赶出房间时,米克捍卫自己的权利。在成长的过程中,米克一直没有放弃过寻找可以让她独处的空间,这样她就可以琢磨脑海中曼妙的乐音,绘制梦想的蓝图,可是在她生活的诺大却拥挤的房屋里,并没有这样一个私人空间存在。同时在家庭之外,米克也在寻找着能够让她舒适成长的空间。在米克的职业学校里,她意识到似乎每个人都属于某个特定的小圈子,但是她不是任何小圈子的成员。米克计划加入某个小圈子,所以在家里筹办了一场派对,对待邀请极其严格。然而在派对结束过后,她却没有融入职业学校里的新朋友,以及每天都想加入的小圈子。“她认识到他们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像其他任何小孩一样。关于这场被搞得一团糟的派对,这就不错了。不过,一切都已结束。这就是结局”[3]111。米克的个性独特,不似同龄的女孩子那般温柔娴静,她假小子的外形与同龄人的世界格格不入,一直被同龄人所排斥。米克一直渴望有一隅属于自己的空间,她在第一空间“自己的房间”和第二空间“职业学校”里都没有找到容身之处,从而无法建立起个人的成长空间和身份认同,于是,米克试图从第三空间中找到能容纳自己成长、实现梦想的地方。“在她身上,好像有两个地方----‘里屋’和‘外屋’。学校、家庭和每天发生的事情在‘外屋’。辛格先生既在‘外屋’也在‘里屋’。外国、计划和音乐在‘里屋’”[3]154。“里屋”和“外屋”是相对立的空间存在,“外屋”代表真实的物理空间,“里屋”代表想象的心理空间。“里屋”和“外屋”作为融构了真实和想象的第三空间,也是米克的私密空间。私密空间对于主人公来说尤为重要,因为它能赋予主人公安全感,让她成为自己的主人,从而寻求自我认同。“外屋”是客观存在的真实空间,而“里屋”迥然不同,是米克虚构的内心空间。对于内心空间来说,一切内心空间都自我隐藏[6]。这里藏匿着米克对成长的期待及成为音乐家的梦想:她去国外旅行的计划,她的绘画艺术作品,她对音乐的独特感悟及把哑巴辛格当作知音的复杂感情……在“外屋”时她把这些秘密埋没在心,除了对辛格倾诉以外没有让任何人得知,然而当她走进“里屋”的内心世界便敞开了心门。在“里屋”这个心理空间里,米克把自己建构成了一名伟大的作曲家,她敏感的思绪、艺术的灵感,以及跳跃的思维全都迸发出来。米克会成为交响乐队中的一员,在舞台表演时为她自己创作的乐曲进行指挥。她的穿着也不再受性别二元对立的社会规范之限制,她既可以穿着男人文质彬彬的燕尾服,也可以穿一袭优雅的红色长裙,烫金的名字在红色天鹅绒质地的舞台幕布上熠熠生辉。在有限的、真实世界的“外屋”,米克始终是一个被同龄人所排斥、迷失自我的女孩;而在无限的、想象世界的“里屋”,她却是一个追求梦想的音乐家、拥有个人空间的主人。在米克的整个青春期里,她在第三空间的“里屋”成长起来,建构起了自己音乐家的身份,能够实现穿衣自由,并且拥有和知心朋友畅谈娱乐的空间,寻找到了梦想的归宿。
四、 结 语
奥尔罕·帕慕克(Orhan Pamuk)认为小说是第二生活,在写作中作家乐此不疲地虚构一个世界,并在这个世界里得到幻真的体验,有时便混淆了虚构与现实的世界。弗洛伊德认为艺术创作就如同白日梦,创作者通过写作来释放自己在现实生活中被压抑的潜在欲望,在类似白日梦的幻想世界中来宣泄自己的情感。无论是小说的“第二生活”,还是创作者的“白日梦”,都与现实生活息息相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现实生活的投射。《心是孤独的猎手》被认为是一部具有自传性质的小说,其作品中的社会边缘人物,尤其是双性人,反映了麦卡勒斯自己被边缘化的生活状态,也反映了她在生活中对个人身份建构的尝试。对此,麦卡勒斯沉浸于自己创作的小说人物中,小说人物的动机与本人紧密相关,自己便成为了自己笔下的人物,这部带有自传色彩的小说也成为麦卡勒斯在第三空间里进行身份建构的体验。凭借敏锐的感知力与自由的想象,她把笔下的文字创造成了融合真实与想象的心理空间,并在此进行着身份建构的尝试。
麦卡勒斯对社会边缘人身份问题的高度关注,通过空间叙事得以展现。她刻画出了美国南方社会个体生命的孤独体验,展现了他们在传统身份阴影下的焦虑和孤独。《心是孤独的猎手》以同性恋哑巴辛格为中心,围绕他的活动引出其他几位主人公,医生科普兰、咖啡馆老板比夫,流浪汉工人运动者杰克,以及怀有音乐梦想的假小子米克。他们由于行为或性格上的与众不同被视为社会边缘人,并想急切地摆脱传统身份格局中的他者身份,以建构身份认同。他们在第一空间中经历了阶级压迫的伤痕与身份遗失的迷惘,在第二空间内有了身份觉醒意识并进行身份探寻的尝试,最终在第三空间里得到成长,找到了实现梦想的归宿,疗愈伤痛。他们怪诞行为的表象是对真实自我的痛苦表达,他们建立新身份的执著追求实质上是对独立人格和自由精神的追寻,他们的信念和勇气有力地冲击了20世纪40年代美国南方社会传统的身份格局。边缘人群要想寻求身份认同,需要不断寻求理想自我和独立人格,通过在第二空间的身份觉醒和探寻达到和谐状态,最终在不同于现有社会状态的第三空间重新定位和建构起自己的新身份。